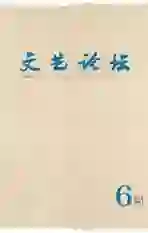新时期女性小说人物引语的修辞学解读
2021-01-13孙桂荣
摘 要:人物引语方式涉及到人物语言是小说中人物的直接表达,还是叙述人对人物所思所想的转述、转述的方式与程度等问题。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这四种引语方式,在女性小说中不但有着不同的文体功能,还有着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性别意涵。本文选择新时期以来女性小说不同时段代表性文本的人物引语为研究对象,对其直接引语与自由直接引语中的女性声音、间接引语中叙述人的话语干预、自由间接引语的文体功能等,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翔实细致的修辞学剖析。人物引语的女性话语研究学界尚鲜有涉足,呼唤性别形式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女性小说;引语修辞;叙事话语;新时期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质料”,这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已经耳熟能详。不过在研究界,作为文学基本“质料”的语言本身似乎远远不及其所传达的对象世界更能引发人们的关注兴趣。像在新时期文学中,针对底层、乡土、都市、边地等书写的研究层出不穷并向系列化、精微化发展,但是对作家以怎样的词汇、修辞、句读、节奏等语言要素去表达这些对象世界的探究还是相对薄弱的。将文学与思想史、社会史联系起来的内容研究一直是学界主调,形式研究被边缘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形式研究中,相对于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的叙事学分析,针对句式结构、标点符号等的语言修辞探讨更处弱势和边缘。新时期女性小说研究便是如此,内容层面的女性形象、女性身份、女性权力等性别政治研究备受青睐,而语言形式层面的社会性别探索却较为鲜见,本文所要研究的新时期女性人物话语的引语方式就是这么一个似乎至今仍“乏人问津”的研究领地。
一、人物引语的修辞学解读:不该被忽略的研究領地
修辞是一种说服的艺术,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将修辞术界定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①。作为加强言辞、语气、文句等文体效果的艺术手段,修辞是使文学语言“陌生化”的主要方式,并逐渐衍生到人文,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像将作为艺术手法的隐喻、象征、借代提升到民族寓言、文化症候等社会指涉的宏观架构层面。修辞学解读,便是对作者通过怎样的修辞手段、艺术技巧来影响读者,以达到自己的修辞性目的的探讨。肯尼思·博克在《当代修辞学》中说,修辞学“将视角从传统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的交流活动”②。人物引语也是在文本是“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动”层面被纳入到修辞学范畴的,因为引语是就小说中人物对话、独白等话语表达的方式而言的,涉及到人物语言是小说中人物的直接表达,还是叙述人对人物所思所想的转述、转述的方式与程度等问题,是影响叙事文学美学效果、修辞方式的重要元素。关于引语的分类,学界一般是将人物引语分成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几种不同形态。能够自由运用各种引语方式是小说文体的一大便利,因为它不必像影视作品那样只能利用摄像机、呈现动态的人物原话,小说作者可以用引号、原原本本叙述人物言辞,或不用引号,以叙述人的语气、口吻转述人物语言,这些都为塑造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文体研究者申丹曾言,“表达人物话语的方式与人物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同样的人物话语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③。人物话语的不同引语方式能够对小说的情态传达、形象塑造、美学趣味、意象指涉等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的引语研究对此已有所涉及,中国知网显示,截止到2021年10月共有相关文献40篇,其中大部分是针对新闻报道(11篇)、外国文学(8篇)、翻译(10篇)等进行的研究,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只有针对鲁迅、陈忠实、方方等的寥寥5篇,相对于视角、人称、结构等其他文体要素的研究来说,人物话语引语的修辞学解读无疑也是边缘和薄弱的。而至今尚没有一篇专门从性别话语角度对女性小说中的引语方式进行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更是表明这一角度的修辞学探讨还未充分与女性文学研究进行有效结合。这是与性别形式分析在先声夺人的性别政治批判面前,其言说声音往往不像前者那样广受瞩目分不开的,也不排除作为语言现象的人物引语在某些层面上与性别话语并非都是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怎样,将女性小说人物引语的修辞学解读纳入研究视域,笔者认为是当务之急,其研究价值可以体现在这样几点:1.为文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定学术实践,文学与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近年多起来,强化了文学研究的“外部”指向,但与语言学相联系的“内部”研究偏弱,深入到语言技巧、话语方式、文体规约等文本隐形层面的修辞性引语研究为此提供了丰富可能性;2.破解女性文学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过分倚重的本土化呼声在学界时有响起,但在具体如何破解、怎样本土化层面上的实践性成果还不多,对女性小说赖以存在的现代汉语载体的引语修辞学分析,是一个有力和有效的研究角度;3.为新世纪以来波澜不兴的女性文学研究寻找新的话语生长点,女性文学研究传统上有“对社会历史学模式的偏爱”④的倾向,性别政治的内容研究占主流,意识形态色彩较为鲜明,要激发其活力需要突破这种研究模式的羁绊,将修辞学、文体学研究融入女性文学研究中正当其实。本文中,笔者愿涉足女性小说人物引语分析这一研究盲区,以期推进对女性文学的修辞学探讨。
二、从直接引语到自由直接引语的女性声音
新时期之初的女性小说用直接引语表达女性声音的现象,要比后来的女性小说更明显和普遍。直接引语是由引导词引导并用引号标识出的对话或独白,一般有动词“说”“道”等引导词,以与叙述性语言相区别,具体引语部分往往用冒号、双引号(双引号内如有特别强调的内容用单引号)标识。修辞学上,引号有表示特定称谓、着重论述、特殊含义、反语等突出强调的作用,人物语言用引号标识后在文本中与叙述语言相区隔,有着不受叙述人干预、鲜明体现出言说者个性与独立性的文体学意味,这在单独成段的直接引语中体现得更鲜明。像张洁《方舟》中这样一段梁倩的发言:
“‘我怎么不严肃了?……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还应该包括妇女本人以及社会对她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正确认识。妇女并不是性而是人!然而有些人并不这样认识,就连有些妇女自己也以媚态取悦于男性为自己的目的,这是一种奴性……好吧,就算女人是祸水,那么男人个个是柳下惠也行,干嘛一出了问题都要怪女人,骂女人?啊?”⑤
直接引语在柏拉图看来是种“完美模仿”,因为叙述人不参与人物话语,诗人“竭力造成他不在说话的错觉”⑥,再现在纸上的语言与现实生活中人物的语言有同质同构的关系,而用引号将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相隔离方式也更容易展示人物不受叙述话语风格影响的个性气质。梁倩的这段话后面“干嘛一出了问题都要怪女人,骂女人?啊?”中一个“啊”字、两个问号生动无比,將其心直口快、疾恶如仇、遇事爱刨根问底的个性暴露无遗,这成为梁倩尖锐女性立场的个性基础。平心而论,这一段话中前面有关妇女解放的文字理论化、书面性太强,与直接引语的生活化、个性化气息不太符合,但也正是这种“越轨”的风格使《方舟》中的激进女性声音突破了叙述人评议的传统文体方式,让不受叙述干预的人物言说直接呈现到读者面前,强化了言说者的个性特征。
以直接引语表达的女性声音因为有着明确的言说者和指涉对象,在对抗男权文化方面往往比叙述人普泛性议论的间接引语有着更强烈的目的性和文本针对性。像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采取了四个女人轮流发言、彼此互为听众的方式,女性言说也多是以“在世人眼中,我不过是一个轻薄下贱、水性杨花的女人,有谁知道我正是为了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才如此身败名裂呢?”“嗯,‘难道女人追求的目标仅仅是做贤妻良母吗?’这算不算警句?”⑦之类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有直接受众的女性言说比起叙述人的评议,有着更鲜明的感情色彩。另外,直接引语的引号还能产生独具特色的“音响效果”⑧,这对女性声音的传达也能起到强化、凸显的作用。像《方舟》是以女性抽烟表现其悲凉、苦闷心境的。“梁倩一扬眉毛;‘你抽烟了?’荆华靠了过来:‘我也抽烟了。’柳泉……寂寞地笑笑,说:‘我也抽烟了。’”⑨整齐有序的冒号、引号,频繁出现的“抽烟”二字及助词“了”,构成了抑扬顿挫、复沓回还、旋转缠绕的音响效果,烘托了女性苦闷阴郁的心理氛围,对塑造人物、强化主题有着鲜明作用。
自由直接引语是直接引语的一种变体,省略了引号、冒号等直接引语的标志性符号,有时也不用“说”“道”等动词引导词,将人物语言直接混入叙述语言之中。自由直接引语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引号所标识的强调突出,却也因为拆掉了引号的壁垒,卸下了叙述语境的压力,让读者在无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触到人物的“原话”,这无疑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因此,自由直接引语被称为是在直接性、生动性上堪与有引号的直接引语相媲美,又有着人物话语与叙述话语相叠印的“可混合性”的特征⑩。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形式探索使自由直接引语的应用比率大幅提升,自由直接引语取代直接引语似乎已成为一种文学常态。细读文本会发现,《叔叔的故事》《长恨歌》《永远有多远》《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私人生活》《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大老郑的女人》《水姻缘》《誓鸟》《陌上》《芳华》这些1990年代以来的重要女性作品在描写人物语言和对话时,几乎全是用的自由直接引语方式。去掉了引号、冒号,可以让读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到人物语言,消除了引号、冒号、引导词等带来的阅读壁垒感。因此,自由直接引语被认为在体现人物话语的直接性上比带引号、冒号的直接引语还胜一畴,是“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的一种引语形式”11。像池莉小说《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采取了直接引语与自由直接引语并用的“双引语”方式:
小瓦说:“豆豆真是豆豆,胆大包天,竟敢擅自把文章中间的句子换到最后。”
是的,我是胆大包天,我喜欢小瓦和他的豆腐房就是因为我在这里可以胆大包天。这里没有告密者,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不会因为擅自串联了鲁迅的文章而受到严厉批判和处罚。我就是喜欢这最后一句,我最懂得这一句,我就是要用它结尾……
小瓦脱口而出地赞赏道:“好!说得好!”12
从小瓦的“说得好”的赞赏来看,“我”(豆芽菜)的大段言语是“说”的,而不是叙述人的代言。这一段是豆芽菜与小瓦的对话,但两个人的引语方式是不同的,小瓦是通常的直接引语,主人公豆芽菜的话却省去了“豆芽菜说”这样的引导词以及冒号、引号,成为自由直接引语的典型表达。这一大段豆芽菜的自由直接引语,镶嵌在小瓦的直接引语中,本身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热奈特曾言,自由直接引语“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话语是内心的,而在于它一上来就摆脱了一切叙述模式,一上场就占据了前台”13。因为没有标点符号的壁垒,去掉了语境压力,自由直接引语使人物心理无需任何中介便自动呈现出来,有利于潜意识表达,能够让读者直接接触到人物的“原话”,提升其认同接受度。相比小瓦,豆芽菜坦荡自然、率性而为的个性更加鲜明,是与自由直接引语这种让人物语言直接走到文本前台“现身说法”的话语形式相关的。
不带冒号、引号的自由直接引语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那就是节约文字篇幅,减少标点符号总量,这在一些频繁进行人物对话的文本中尤其体现出节俭、高效的一面。像付秀莹2016年出版的《陌上》中银花与大全媳妇对话的这一段:
黄花闺女家,谁敢往这个上头想呢。银花说老是不见好,就带她去找会开看,会开给摸了脉,说是喜脉。这个不死的妮子!大全媳妇说,当时旁边有没有人?这个要是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银花把大腿一拍,哭开了。谁说不是?会开倒是把我叫到一旁说的。可这种事儿,怎么瞒得住?我这张脸哪,叫我往哪里搁!三姐,你看我这命!看我这命!14(粗黑字体为笔者所加)
银花与大全媳妇两个农村妇女絮絮叨叨的家常话,如果用《方舟》中直接引语的方式,会需要很多引导句、引导词、冒号、引号,单独成段的话占用篇幅会更多。《陌上》的做法是对话以自由直接引语的方式全部省略这些,也不单独成段,而是将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融为一体,只是以口语化、个性化的语言和蕴含丰富的标点符号标识出来(笔者用加粗字体标注),让读者很容易辨析出来哪些是人物语言,哪些是叙述语言。对于通常谨慎、内敛、不轻易敞开心扉的女性人物来说,这种方式提供了修辞学层面上自我展示的便利。不直接点明哪句话是谁说的言说方式,也与少女怀孕这种难以启齿的隐私性言说内容相契合。
自由直接引语的流行是与当下快节奏的文学传播语境分不开的。有人曾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场景,一场谈话,就看见满眼的冒号、引号,你烦不烦,简直影响阅读”15。话糙理不糙,繁琐的标点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阅读速度,影响了阅读快感。在不影响理解情节发展的情况下,去掉冒号、引号的人物话语目前已被不少读者所接受,这是直接引语慢慢向自由直接引语转换的时代原因。网络作家邢育森说过,“人们在网上看东西,一是信息太丰富太多了看不过来,二是这几眼一定要把读者留住,拖沓冗赘要不得,所以网文大多简洁明快”16。其实不光网文,很多纸媒文学也采取了流畅明快、简洁自如的自由直接引语方式。因为与读者的叙述距离更近了,它对于女性声音的传达也起了一定作用,有利于女性人物更流畅、自然地傳达个人心声,为人物主体意识的增强提供了一定便利。
三、间接引语与叙述人的话语干预
间接引语是以小说叙述人的语气对人物语言的转述,往往有“XX说”“XX道”之类的引导词,在人物称谓上也会依具体表述对象的不同而做相应的调整。间接引语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用得极少,因为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为了将人物话语与叙述者的话语相区分,一般不会用容易混淆的转述方式,而多以“XX道”的方式将人物语言标识出来,语气上亦尽量与叙述语相区别,话本小说爱模仿人物原话的传统也强化了这一特征。现代白话小说产生以来,由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和新的文学观念的出现,间接引语的使用大大增强了。从叙述人角度转述、概述人物话语的间接引语,有利于加快叙述速度、提高叙述节奏,可以直接进行性别话语的评议、传达,增强文本的理性色彩。《方舟》中这段文字可与前面引述的直接引语做下对比:
①刚才,骑着摩托疾驰在雷电下,在暴雨中,她觉得自己很有些顶天立地的气概,她意识到自己可以驾驭生活的能力。②哦,这种自由感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得到的。③女人,女人,这依旧懦弱的姐妹,要争得妇女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放,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自信来实现17。(序号为笔者所加)
在这段文字中,①是对梁倩日常行为、心理的描写,②是从梁倩个人心理向女性普遍境遇发言的过渡句,其中“哦”这一语气词的使用增加了叙述语的生动性,③是叙述人由小说人物、情景延伸到对女性共性问题的评论。与前面所举的例子相比,间接引语发出的性别之声在人物个性化、言说生活化上要弱一些,但理论性、权威性骤然增强,这是由间接引语是由故事外叙述人转述的文体特征决定的。苏珊·兰瑟将其称之为“作者型叙事”,“由于作者型叙述者存在于叙述时间以外,而且不会被事件加以‘人化’,他们也就拥有某种常规性的权威。比起那种赋予小说人物的、甚至是正在叙述的小说人物的权威来,这种作者型叙述者的权威更为优越”18。就《方舟》中的例子而言,同是对女性问题的言说,从愤激争辩的人物梁倩口中说出来(以直接引语的形式),与拥有“作者型权威”的非人格化叙述人本身点出来(以间接引语的方式),权威效果是不一样的,后者显然会更强一些。
在叙述人的话语干预与叙述距离的操控方面,间接引用是所有引语形式中程度最深、效果最明显的。间接引语中人物语言往往不像直接引语与自由直接引语那样直接面向读者敞开,而是经过叙述人的转述与中介,这拉开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也为叙述人的话语操控提供了一定空间。王安忆《长恨歌》是鲜明的例子:
他抬头看看,一个声音对他说:要走快走,已经够晚了。他没有推敲这句话的意思,就站起身跨出了窗台。窗户本来就开着,好像在等待程先生。有风声从他耳边急促地掠过,他身轻如一片树叶,似乎还在空中回旋了一周。这时候连鸽子都没有醒,第一部牛奶车也没有启程,轮船倒是有一艘离岸,向着吴淞口的方向。没有一个人看见程先生在空中飞行的情景,他的一具空皮囊也是落地无声。19
程先生是王琦瑶的忠实爱慕者,也是《长恨歌》中对她真正有关怀体恤之情的堪称“暖男”的男性人物,但这段他的死亡描写在叙述情感上是漠然的,“要走快走,已经够晚了”“窗户本来就开着,好像在等待程先生”“身轻如一片树叶”“空中飞行”“落地无声”等言说增加了文学性的诗意色彩,却大大减弱了对一个逝去生命的伤痛之感。这显然与间接引语的表述方式相关,叙述人掌控了文本,而不是人物心理、行为的自行呈现,在程先生跳楼的关键时间点,还饶有兴致地描述鸽子、牛奶车、船的动静,这是有意识地淡化悲伤效果、离间读者对程先生情感认同的间接引语在起作用。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曾言,“作者借助于确保读者以潜在作者感受到的超然或同情的程度来看待题材,从而实际上正在精心地控制读者的摄入或离开故事中事件的程度”20。没有一个冒号、引号,间接引语与自由直接引语贯穿全篇的《长恨歌》可谓这种叙述姿态的代表,其总体上采取了超然(而非同情)的基调,不仅将写作对象放在一个(群)时代边缘人身上,写作手法也力避女性写作通常的移情、共情、煽情等,相对于《方舟》中人物形象的鲜活、热辣,《长恨歌》中无论哪一个人似乎都有着凄清阴郁的色彩,与读者隔了偌大的叙述距离,这是与其间接引语的出色运用相关的。
间接引语中的人物话语由于叙述人的干预,往往体现的是叙述人的个性、风格,而非人物的个性、风格。《长恨歌》中的人物语言个性化不强,王琦瑶与母亲、严师母、张永红等不同年龄、身份、时代的女性说话时,都有着分寸、节制、绵里藏针、话里有话、不说破的特性,这是由王安忆有意在这部小说中设置的叙述人风格决定的。如果比照其他同时期女性小说文本,我们会发现《长恨歌》似乎自始至终有一种淡然、凄清、迷离、忧郁的叙述基调,这种叙述基调更多彰显的是叙述人而非人物的话语风格,间接引语的有效运用起了重要作用。徐坤的小说大多也是采取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人物由叙述人以间接引语形式传达出来,但像“陈维高的眼神挺不好意思地热了,在暧昧的灯影下咬紧审美对象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目光灼灼地不愿意松开”,心里想着“廉颇老矣,尚能爱否”等描写,也更多体现的是嬉笑怒骂、妙语如珠,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叙述人的个性与风格,而同人物本身的身份、职业、年龄、具体言说语境之间的联系已相对稀薄了。
语言形式化,形式个人化,让语言形式本身成为叙述人印证自我、表达自我的一种工具,这是现代小说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文体意识、叙述主体意识增强的一种体现。具体到引语修辞而言,那就是很多女性小说尽管用了作者型叙述的间接引语方式,但以强化叙述人话语干预的方式传达出了一定的女性声音。
四、自由间接引语的文体功能及其社会性别分析
自由间接引语是介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的话语类型,它“在人称和时态上与正规的间接引语一致,但不带引述语……常常保留体现人物主体意识的语言成分,如疑问句式或感叹句式、不完整的句子、口语化或带感情色彩的语言成分,以及原话中的时间、地点、状语等”21。自由间接引语比直接引语少了引导词和标点符号的约束,比自由直接引语多了叙述人的介入,又不像间接引语那样明显受到叙述人的干预,既在人称和时态上与叙述语相同,又能同时呈现人物的话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从人物的视角叙述人物的语言、感受、思想的话语模式”22,因此受到了形式批评的重视。尤其是因其有着叙述人话语与人物话语相纠结的双重特点,又可以对二者的话语立场、价值姿态进行基于性别视角的分析。不过,目前的相关研究多在外国文学领域、以英文小说或英文翻译小说为主。自由间接引语的“自由”主要体现在摆脱从句的限制,而“汉语中不存在引导从句的连接词,无大小写之分,因而作为从句的间接引语的转述语与作为独立句子的自由间接引语之间的差别,远不像在西方语言中那么明显”23。因此,自由间接引语并非是汉语的一个语法术语,与自由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区分也不是太明显,“两可型”或“混合型”的自由间接叙述较多,我们的研究思路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笔者认为新时期女性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主要体现了这样几种文本功能。
(一)人物话语及其性别独立性的增强。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人的话语干预减弱了,人物言说的独立性有所增强,这是有利于其性别主体性的彰显的。凯西·梅齐甚至将自由间接引语看成是女性人物与男性权威(或隐或显)斗争的场所,认为“这一叙述技巧构成作者、叙述者和聚焦人物以及固定的和变动的性别角色之间文本斗争的场所”24。叙述话语与人物话语之间的叙事干预与反干预、控制与反控制的隐形冲突,有着性别冲突的意味,这在女性小说文本中并非鲜见。像王晓鹰的《春无踪迹》对女主人公邵心如的一段心理描写:“她只是暗自发笑:实在难以相信,那么生气勃勃、仿佛浑身每块肌肉都凝聚着用不完的精力的晓岱,竟然能够坐在这样一张摇摇欲坠的旧椅子上吃饭、看书、写论文!”25对坐在椅子上晓岱的想象通过“发笑”、冒号、感叹号的使用强化突出了,是一种没有引号的自由间接引语。但从上下文语境来看,人物的这种自述是有些突兀的,因为小说并没有提供出椅子引人发笑的足够理由;邵心如对晓岱暗含着性吸引力的“生气勃勃、仿佛浑身每块肌肉都凝聚着用不完的精力”的男性魅力的神往,也和后文叙述人描述的心如矜持、内敛的性格不太相符。这种内容上的突兀性,是与其在叙事形式上以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叙述人的话语干预相关的。《春无踪迹》与同时期不少女性小说一样是有一定道德化叙事倾向的,“姐弟恋”并不被包括叙述人在内的当时社会习俗所接受,在叙述人的话语干预下邵心如最后与其起初并不爱的陈天俊走到了一起,她对晓岱的欲望常常被压抑。但在这段言说中,作为人物的邵心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某种程度上,是自由间接引语为人物正视自己的性别主体欲望提供了形式上的便利。“自由间接引语是处于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之间的形式,比間接引语要更为直接”26,作为人物的邵心如就是利用了这种直接性,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冲破世俗、遵从自我爱情感受的性别独立性。
(二)个性化、风格化的人物话语与叙述人话语的混融,增强了话语言说的情感吸引力,有利于性别诉求的有效表达。像池莉《小姐你早》中说:“女人所需并非金钱!金钱太狭隘太有限并且总在散发臭气。但是,男人的准则是金钱。所以,你必须首先重视金钱然后升腾自己,让一切都是新的,你们明白吗?亲爱的。”27这段言说从叙述人概述的间接引语出发,逐渐滑入了没有引号和引导词、但联系到上下文语境能够看出具体言说人物的自由间接引语。从说话的内容、风格、语气来看是借用了人物艾月的口吻与思维,像文末的“亲爱的”所表征的亲昵感、时尚感,如同网络流行语中的称谓“亲”一样,只有时尚前卫的一代才能说得亲切自然。因为小说中艾月的身份,她的性别言说是有一定争议的,笔者此前曾认为其表现了消费时代“‘女人意识’的生成之路”28,但在这段自由间接引语中,有关“你必须首先重视金钱然后升腾自己,让一切都是新的”的言说,给了艾月自我辩护的机会,因为自由间接引语去掉了“XX说”“XX道”“XX想”等概述语,也去掉了冒号、引号的壁垒,卸下了叙述语境的压力,使人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叙述人的话语干预,与读者进行无障碍交流,这大大增强了读者对其性别言说的理解程度。这段文字除了以“亲爱的”这种表亲昵语气的词拉近读者距离,还使用了第二人称“你”这一吸引型叙事常用的叙述人称,“你”具有诱使读者迅速进入文本进行“角色扮演”的功能,增强了言说的对话性特质,也提升了人物性别话语的传播效果。
(三)反讽效果的营构。人物的价值准则与叙述者相悖,或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反差都能产生反讽的艺术效果。自由间接引语兼具人物话语与叙述人话语的“两可”性为二者产生一定裂隙、悖谬的反讽修辞提供了可能。当然,针对不同的人物对象,自由间接引语体现的反讽修辞在话语指向和尖锐程度上往往并不一致。女性小说有激烈的呐喊或咄咄逼人的嘲讽,也有很多形式和力度都相对含蓄的反讽。像《方舟》中的这段——“那时候,梁倩胖得像刚灌好的香肠,浑身的肉,紧绷绷的,现在呢,像根已经风干了的香肠,干得没有了一点水分,肠衣上还析出了一层盐霜”29,既有人物视角的自我调侃,也不乏叙述人的微讽,没有像通常那样将主人公写得柔美可爱,而包含了对疲于奔命的女性人物的怜惜之情,有着名贬实褒的修辞效果。还如王安忆《我爱比尔》结尾中从女监中逃出来的阿三手握一枚处女蛋时的情景:“忽然间,她手心里感到一阵温暖,是那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30“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有着明显的口语化、个性化语气,是人物走到文本前台直接面向读者的言说。一枚“壳上染着一抹血迹”的处女蛋,让她产生的联想表面指向的是小母鸡的贞操,实际却是对自己从一个艺术大学生走向白茅岭监狱的沉沦生涯的追问。对于这个结尾,王安忆解释为它是与阿三第一次与比尔发生关系时故意显示出的性开放姿态相对照的,阿三想像她认为的西方人那样迎合比尔,但也是因为这一点(模仿西方的性开放,失去了中国性,也失去了东方女性的矜持美)而失去了比尔,“我们从离群索居中走出来的时候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被侵略的不仅是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经济生活,还有我们的情感方式”31。因此,对于阿三这段自我言说的引语,叙述人是有着痛惜和批判之情的,从大学生到女囚,面对如此大的生活落差都在淡然应对的阿三在看到小母鸡的处女蛋时却“哭了”,也映照出叙述人对人物的扼腕叹息的反讽姿态。
(四)叙述人以人物身份、口吻言说,或人物挺身而出代叙述人发言的自由间接引语,为女性话语与道德的、理想的、伦理的,乃至世俗的等其他社会话语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增强了文本的多元性、混融性话语力量。巴赫金对这一引语的解释是:“按照语法(句法)标志,它属于一个说话人,而实际上是混合着两种话语、两种讲话习惯、两种‘风格’、两种语言,两种表意和评价的视角。”32两种话语的复沓表达是会增强其话语力量的。像在张抗抗的《北极光》中,岑岑在被傅云祥催着去照结婚照的路上看见一个滑冰的小姑娘时,原本第三人称的叙述人话语变成了无引导词、无引号的“我”的直接发言:“让我再看你一眼吧,小姑娘。你的金红色的滑雪帽,同我当年那顶一模一样,我差点要以为自己变小了呢。可是这一切都是一去不再复返了,都要结束了。童年、少年、青春的梦,统统都要消失了,不会再回来……”33人物岑岑走到叙述人的位置,面向读者进行大段的内心独白,发一段青春不再来的感慨。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这段引语形式并不突兀,因为虽是不带引号的“我”言说,但与追寻生命激情与诗性爱情的小说主题(“北极光”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种非凡俗化的高蹈精神追求的隐喻)相一致,叙述人下意识地附到岑岑身上,让她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双声叠印,自然增强了言说的话语力量。1990年代以后,随着女性小说逐渐向日常化、凡俗化、经验化叙事的推进,自由间接引语中人物语言与叙述人声音的话语指向,也出现了疏离理想、奋斗等精英女性观而向大众女性观倾斜的一面。像池莉《生活秀》中的这一段:“来双扬无法同来双媛对话。一个人既然要甘于寂寞,何必要宣称呢?宣称了不就是不甘于寂寞了吗?来双媛总也长不大,皮肤都打皱了还是一个青果子,只有少数白头发的老文人和她自己酸掉大牙地认为她是一个纯美少女。”34从凌厉的言辞来看,这些应该出自吉庆街卖鸭颈的女人来双扬之口,但也为有着“市民作家”之称的池莉感同身受,第三人称叙述的《生活秀》在价值姿态上是认同来双扬,而非来双媛的,这里便出现了叙述人与来双扬双声齐叙的自由间接引语现象。可以说,不管是人物言说与叙述人声音有着或隐或显的冲突,还是基本叠印在一起的多语和弦,自由间接引语都成为小说作品美学增值的一种话语技巧,为女性小说的修辞学解读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探索空间。
文学是语言修辞的艺术,语言形式的修辞学解读不应该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缺席。文艺理论家赵毅衡曾说过,“小说形式特征的变迁往往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变迁相联系,不是内容,而是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文化对文学文本产生方式的制约力和推动力”35。因为文体学、修辞学、叙事学等是对事关文学本体的“文学性”研究,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派别、传承,俨然已是文学研究的主流。但国内学界因为意识形态批评传统的强大,文学形式研究一直在边缘处徘徊,而语言修辞的解读相对于叙述人、叙述模式的叙事学解读似乎更为暗弱。笔者认为,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从微观处着手,将文学语言的时态、语态、句读、节奏等具体要素进行细致深入剖析,才能推进文学修辞学研究的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适当结合社会性别批评视角,则有助于为近年来波澜不兴的女性文学研究寻求突破。或许这种研究方式不像身体写作探讨那样广受瞩目、引发各界争议,但却能摒弃各种浮躁与喧嚣,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推动女性文学研究的稳步发展。惟愿本文对新时期女性小说人物引语的修辞分析能够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崔笑:《方方叙事模式的修辞学解读》,河南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③2326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第149页、第156页。
④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⑤⑨1729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
⑥转引自晏杰雄:《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页。
⑦胡辛:《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参考阎纯德主编:《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第332页。
⑧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2页。
⑩112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第299页、第289—290页。
1234池莉:《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07页、第229页。
13[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14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15转引自吕德强:《试论网络文学的美学原则》,《宁德师专学报》2007年第1期。
16参考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组编:《人文前言——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18[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19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20转引自舒凌鸿:《“冷漠”叙述者的“镜城突围”——<长恨歌>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
22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24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25王曉鹰:《春无踪迹》,《花城》1984年第6期。
27池莉:《池莉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28孙桂荣:《“女人味”及其在消费时代的生成之路》,《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
30王安忆:《我爱比尔》,见王安忆、陈丹燕等著:《女人二十》,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31王安忆与刘金冬的对话,见李小江等著:《文学、艺术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页。
33张抗抗:《北极光》,《收获》1981年第3期。
35赵毅衡:《叙事形式的文化意义》,选自《礼教下延之后——中国文化批判诸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女性小说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项目编号:19FZWB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