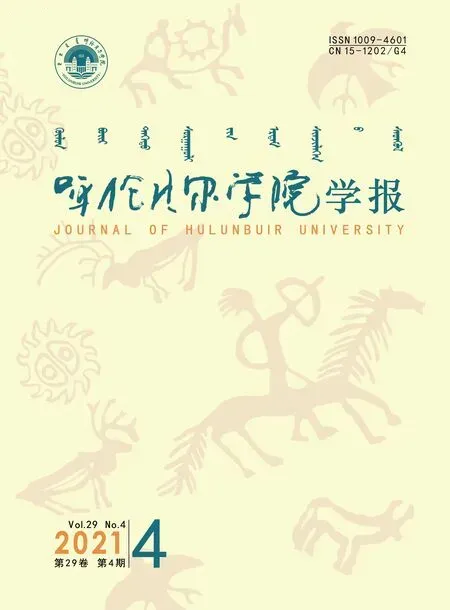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历史作用
2021-01-13王广利胡雪艳
王广利 梁 云 胡雪艳
(呼伦贝尔学院 内蒙古 海拉尔 021008)
东汉、魏晋时期,拓跋鲜卑与中原政权以及北方草原各部族频繁接触,有时和平交往,有时发生战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交往交流,拓跋鲜卑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政治上积蓄力量,逐渐发展为中国北方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本文仅讨论东汉时期拓跋鲜卑的民族交往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和进步状况。
拓跋是中国古老民族东胡的后裔,最初活动在中国东北,在鲜卑诸部中影响最大。呼伦贝尔是拓跋鲜卑人的摇篮。拓跋鲜卑先世在“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繁衍生息七十余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不交南夏”[1](卷1《序纪》,P.1),即拓跋部在夏、商、周“三代”及秦、(西)汉时期,与中原政权均没有交往。拓跋鲜卑是否有与毗邻民族的交融交往关系,同样因为史无明文,我们无法定论。《魏书·序纪》记载,自(拓跋)始祖“积六十七世”,至毛“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1](卷1《序纪》,P.1)这里只交代了首领毛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史实,却没有直接记载由99个氏族构成的36个部落联盟成员的部族名称,我们无法直接证明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是否包含拓跋部之外的部族。嘎仙洞遗址发掘考古成果[2]亦未显示拓跋鲜卑与临近民族交往交融迹象。由于缺少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支撑,西汉(或之前)时期拓跋鲜卑毗邻各族的民族交往情况尚无从考证。
首领推寅率领拓跋部从起源地“大鲜卑山”向西南迁徙到“大泽”(呼伦湖)周边地区[1](卷1《序纪》,P.2)。关于迁徙时间,虽无确切文献依据,但学者依据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述推断,大致是在东汉时期。黄烈先生依据《魏书·序纪》关于诘汾之子力微“元年,岁在庚子”[1](卷1《序纪》,P.3)的相关记载推断,“东汉前期,拓跋族由大兴安岭南迁到呼伦池”[3]。田余庆先生主张,早期拓跋鲜卑第一次迁徙是在东汉中期桓帝年间[4]。同时,从呼伦贝尔草原地区诸鲜卑墓葬遗存出土的五铢钱、汉锦残片、漆器等其原件显然来自汉代中原遗物的考古成果证明,东汉时期,拓跋鲜卑迁徙到呼伦贝尔草原。在这里,拓跋鲜卑与中原东汉政权和毗邻的匈奴、高车等周边部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相互间的学习和借鉴,推动拓跋鲜卑社会向前发展。
一、历史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与毗邻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魏书》是记述北魏、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记载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年)共165年的历史,130卷。《魏书》作为现存最早的系统全面著录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史籍,是考察拓跋鲜卑民族交往历史最基本的史料。虽然《魏书》由汉人用汉文来书写,会受到中原汉地历史编撰学传统的影响,“但它所反映的,基本上还应看作是北魏官方乃至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对自身根源性的解说”[5]。其《序纪》《乌洛侯传》《官氏志》《礼志》《刑罚志》均有早期拓跋鲜卑历史的记载。其中,《魏书·官氏志》“七分国人”内容记载了拓跋邻以自己兄弟数目为前提对部落进行的一次整合,将“大鲜卑山”时期的36个部落整合为7个,拓跋邻指派自己的7个兄弟担任不同部落的酋长。拓跋邻统领拓跋氏,连同7个兄弟统领的纥骨氏、普氏、拔拔氏(“拓跋邻之统国也,以次兄为拔拔氏,厥后孝文帝用夏变夷,改为长孙氏。史以华言书其后所改性”)[6]、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氏等七姓,以及乙旃氏、车焜氏等另外两个亲族统领的部落,组成以“帝室十姓”为统治核心的十个部落集团。在献帝以及兄弟、叔父、旁系亲属摄领“国人”中,其兄管理“纥骨氏”和叔父之胤管理“乙旃氏”为典型的高车族姓即高车人,次兄管理“普氏”当为匈奴卜氏[7]。文献史料“七分国人”记载表明,拓跋鲜卑迁徙至“大泽”后,匈奴、高车等部族加入到拓跋部为首的部落联盟之中。关于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已经与驻牧在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匈奴、高车等部族交往融合这方面的论述,拙文《拓跋鲜卑早期迁徙中的民族交往与经济发展》[8]已有阐释,此处不再赘述。
二、考古成果反映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自1959年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呼伦湖周边陆续发现了扎赉诺尔鲜卑墓群、完工墓群、伊敏河地区鲜卑墓(包括伊敏车站墓葬和孟根楚鲁墓葬)、拉布达林鲜卑墓葬群、七卡鲜卑墓葬群、伊和乌拉墓群、团结村鲜卑墓葬群、鄂温克旗二道沟墓群、红星生产队墓葬、满洲里蘑菇山墓群等10余处墓葬,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属于早期拓跋鲜卑的墓葬(群),是拓跋部迁徙至“大泽”时期的考古遗存。亦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例如曹永年先生认为,“完工、扎赉诺尔墓群是否是拓跋鲜卑的遗迹,或遗迹的‘标本’,尚需论证”[9]。这些墓葬遗存与历史文献记述的拓跋鲜卑迁徙到“大泽”的史实相互印证,为我们研究拓跋鲜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考古学支撑。
(一)拓跋鲜卑与中原东汉王朝汉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因为地域相隔较远,拓跋鲜卑南迁“大泽”地区后与中原汉民族的关系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在考古发掘方面有所体现。
在呼伦贝尔地区鲜卑墓葬(群)发掘的考古遗存中,发现诸多拓跋鲜卑和中原汉民族有联系的器物。例如,在陈巴尔虎旗境内完工墓葬群中发现“具有三个袋形足的陶鬲,陶鬲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标志之一,类似这种形制的鬲,即使在华北平原的最北部,它的时间也不会迟于公元前三世纪”[10],可以推测,至少在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和汉族发生联系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各处墓葬中许多人骨附近出有绢或麻布制成的衣物残片,绢、麻都来源于汉族地区,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汉族所特有的漆器残片;挖掘出土的作为装饰用的绿松石、玛瑙、珊瑚和海贝、海螺,大约也都是来自南方的汉族区域”[10];另外,在扎赉诺尔墓葬群中出土的“轮制双耳陶罐和角器上刻画的龙形纹饰,都标示了鲜明的汉文化的影响”,“还发现了几件标准的中原地区的输入品——规矩镜、‘如意’锦片和木胎漆奁”,这些都具有汉代中原地区手工业制品的特点。出土“较多的铁器,其原料可能来自汉族地区”[10]。
正如干志耿、孙秀仁先生在《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总结的那样:“早期(拓跋)鲜卑遗迹,通常可发现可作为断代标志的中原文化遗物,如陶鬲……如意纹锦,木胎漆奁,麻和绢织物,东汉式陶壶和陶器上的汉字纹饰,以及角器上的龙形纹饰等;还有来自汉族地区的绿松石、珊瑚、海贝、海螺等。这些不仅说明早期(拓跋)鲜卑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构成了它的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11]。
从上述这些考古遗存中可以发现,在呼伦贝尔地区驻牧的拓跋鲜卑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联系,拓跋鲜卑生产生活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在拓跋鲜卑经济领域中,抑或已经形成了与中原东汉王朝农业生产区域的产品交换关系。
(二)拓跋鲜卑与匈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在“大泽”地区与匈奴进行了交流、融合,这从“考古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与人骨的体质人类学分析结果两相吻合”[12]得以证明。
墓葬文化中存在拓跋鲜卑与匈奴文化交流的因素。在呼伦贝尔草原拓跋鲜卑墓葬的遗存中,有一些具有相当浓厚的匈奴文化因素。例如,从完工墓葬群出土的“一些铜制的小型饰具如各种式样的环、扣上,可以看到它的西邻——匈奴的影响”[10]。扎赉诺尔墓葬群随葬品证明匈奴的影响也最为突出。“双耳铜鍑和各种动物形铜饰都具有明显的匈奴器物的风格”;铁质马具和武器的形制表明“它和匈奴同类器物相接近”[10]。拓跋鲜卑“扎赉诺尔墓葬和完工墓葬同出的骨制鸣镝、羊距骨,也都和匈奴的同类器物相似,受到匈奴文化影响”[13]。从上述考古资料可以发现,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北段迁徙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后与匈奴进行了交往交流。
现代体质人类学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拓跋鲜卑和匈奴在血缘上有交融。考古学家通过将采自时代大致相当于东汉时期的陈巴尔虎旗完工、扎赉诺尔两地古墓葬的颅骨材料与在时代上相近的贝加尔湖西部地区匈奴墓的颅骨平均数进行比较研究,结果使我们看到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扎赉诺尔组中也可能含有某些匈奴的血统”,“从扎赉诺尔组所显现的体质特征的复杂性,使我们看到了一些民族融合的蛛丝马迹”。“完工组与扎赉诺尔、匈奴两组的亲疏程度几乎是相等的”[14]。体质人类学者认为,扎赉诺尔墓葬人骨具有匈奴血统,此时的拓跋鲜卑很可能在血缘上已与匈奴融合。“扎赉诺尔汉代A组与外贝加尔匈奴组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反映出两者之间在体质特征上异乎寻常的相似性”;“扎赉诺尔汉代B组或许就是一组‘胡父鲜卑母’或‘鲜卑母胡父的混血类型的代表[15]。“扎赉诺尔居民中种系成分的复杂性,表明了他们很可能是鲜卑、匈奴两族混合的产物”[16]。
(三)拓跋鲜卑与不同文化的人群在呼伦贝尔地区融合交汇
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既表现出了几个方面的共同文化特征……同时,这些墓葬还体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文化影响,如有来自外贝加尔地区、大兴安岭东麓松嫩平原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不同的文化、人群在呼伦湖附近地区融合交汇,也许拓跋鲜卑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的[17]。
三、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作用
迁徙至“大泽”之后,拓跋鲜卑的视野随着与东汉王朝、匈奴、高车等部族交往交流交融而拓宽,民族之间多领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增多对拓跋鲜卑社会演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成为推动拓跋鲜卑社会演变的动力之一。通过与汉族、匈奴和高车等部族的往来和学习,东汉时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的经济、社会形态、司法等方面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向前发展。
(一)拓跋鲜卑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大鲜卑山”时期,拓跋鲜卑作为渔猎民族,主要从事原始的狩猎、捕鱼、采集业。“大泽”时期,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草原与邻近的其他民族(抑或包括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接触机会增多,经济模式发生变化,经济向前发展。
拓跋鲜卑狩猎经济得到发展。弓箭的发明和使用,是狩猎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和保障。呼伦贝尔地区各拓跋鲜卑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弓弭、箭镞、镖、鸣响等,其数量不在少数,质地有石制,有骨制,有铁制,进一步证明了拓跋鲜卑人弓箭使用的增加,这使拓跋鲜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拓跋鲜卑原始畜牧业产生。东汉时期,拓跋鲜卑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开始将牛、马、羊驯养成为家畜。在生活资料方面,拓跋鲜卑人从“大鲜卑山”时期较多依靠和适应自然,转变为改造自然;从食物的采集者转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拓跋鲜卑人应该能够生产出超出维持自身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在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狩猎经济成分减弱,牧业经济成分增长[18]。
拓跋鲜卑手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大鲜卑山”时期,拓跋鲜卑手工业制作工艺简单,但也已经出现了加工精细、形状规整的石镞[2]。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陆续从呼伦贝尔境内的扎赉诺尔、拉布达林、满洲里蘑菇山等多地古墓群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手工制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和兵器。这些考古资料表明,拓跋鲜卑在桦树皮制作、骨器制作、金属器加工、木器加工制作、装饰品制作等方面手工业技艺更加完善。
拓跋鲜卑生产力进入金属器时代。在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出土的大量金属器生产、生活工具表明,拓跋鲜卑似乎已经开采、冶炼金属铜、铁,开始锻铁为兵器,他们能够自己制造各种金属弓矢、各种生产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品,这也标志着拓跋鲜卑的生产力发展此时已经进入到金属器时代。
(二)拓跋鲜卑社会组织演进
随着经济发展、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分工出现,拓跋鲜卑内部出现的阶级分化,社会组织发生变化。
1.出现了初步的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分工和贫富分化
伴随经济发展,拓跋鲜卑内部出现了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分工。从各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看,男性随葬品多数为铁矛、铁刀、铁镞和骨镞等。在1960年夏发掘的扎赉诺尔古墓群中,M25男性单人葬,棺内放置的遗物包括铁矛、环首铁刀、铁镞和骨镞、铁衔,弓囊内放置有木弓。女性墓葬随葬品多为装饰品的情况表明,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社会出现了社会分工,男子主要承担金属生产工具制作、打猎等,女子主要承担采集、家务等较轻的体力劳动。但女性随葬品中也偶有铁刀、铁镞、铁衔的随葬[19]。M10母子合葬,大人的尺骨上套着一个铜手镯,在两只手的指骨上各套一个铜戒指;M29女性单人葬,墓内放置铜饰、鱼肋骨制成的骨簪32根、5个鱼椎骨钻孔的串珠[19],这种随葬品方式表明,拓跋鲜卑的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分工还不十分明显,男、女均可作为战士或狩猎者。拓跋鲜卑已经逐步进入父权制社会阶段,但母权制时代的风俗和观念在社会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女子与男子共同参加生产与战斗,分工差别也不大,这是拓跋鲜卑妇女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现实基础。从墓葬中殉葬不同数量牛、马、羊骨的情形能够判断,此时拓跋鲜卑社会居民已有贫富分化,阶级逐渐形成。
2.拓跋氏家族成为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氏族贵族
拓跋部游牧于“大泽”地区时,部落为其整个社会组织的基础。拓跋邻“七分国人”,拓跋鲜卑社会发展为由十个氏族组成的部落,部落最高权力机构由拓跋邻、邻的兄弟、叔父、各氏族长构成。“可汗邻,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车惃氏分统部众为十族”[6]。邻使其诸兄弟七人、叔父、旁系亲属等拓跋氏家族成员为主担任氏族长,管理本氏族的生产、生活等事务。拓跋邻为拓跋部落联盟酋长或军事首领。原来的异姓酋长全部被拓跋邻家族成员取代,使原来不是鲜卑的氏族部落逐渐融合于拓跋鲜卑。“大泽”时期,拓跋鲜卑的氏族部落组织规模在“大鲜卑山”拓跋毛时期“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拓跋氏家族已经成为最富有并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氏族贵族。
3.出现了世袭制的萌芽,拓跋鲜卑由选举制向世袭制过渡
拓跋邻指派诸兄弟统摄“国人”以前,氏族、部落产生酋长的制度应该还是选举制,即部落大酋长由民主推选产生,每个酋长都有被选为部落大酋长的可能。“到拓跋氏兄弟统摄‘七分国人’以后,盟主的推选对象就集中到八个宗氏的姓氏之内,而拓跋氏在其中更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推选制已经不是原来具有充分民主性的选举,而是一种‘世袭’制”[20]。献帝邻将首领职位传给了儿子诘汾,“以位授子”[1](卷1《序纪》,P.2)。这表明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地区时期已经进入世袭制。
(三)拓跋鲜卑采用习惯法处理纠纷案件
“大泽”时期,拓跋鲜卑人处理案件的最高决策者为勇健能战、公平,能解决争讼的“四部大人”。“宣帝(推寅)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王庭决辞讼,以言语约束……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决遣”[1](卷111《刑罚志》,P.2873)。此时尚无监狱和考讯的办法,有了纠纷,犯罪案件都是由部族首领临时共同商议,按照以往拓跋鲜卑族内的约定俗成来决判处理,还没有法律法规作为处理案件的依据。
结语
拓跋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重要的民族之一,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文献记载和呼伦贝尔地区有关拓跋鲜卑的考古成果,对东汉时期拓跋鲜卑在呼伦贝尔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人类体质、手工业生产等各方面所体现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在此过程中拓跋鲜卑部族在经济、社会组织、司法诉讼方面所呈现的发展变化态势加以分析,反映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拓跋鲜卑社会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研究拓跋鲜卑在发展初期与中原政权和周边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历史、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