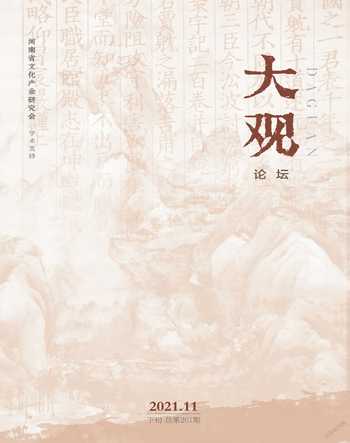夏皮罗对海德格尔之辩
2021-01-12秦燕楚
秦燕楚
摘 要:艺术界有一场有名的辩论,辩论双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艺术史家夏皮罗,辩论的主题是凡·高的一幅画作中靴子的归属。后者对前者的质疑与批判,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关于作品与真理、艺术品与艺术家之间的思考。后来德里达的加入为这场辩论提供了新的视角。故此,基于以上争论和夏皮罗提出的绘画艺术中的个人性和面相学特征,探索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的存在。
关键词:夏皮罗;海德格尔;德里达;艺术作品;艺术家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艺术系教授迈耶·夏皮罗写了一篇名为《作为个人物品的静物画:关于海德格尔和凡·高的札记》的文章,针对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于凡·高画作的描述与解释,质疑他把凡·高的一幅画作上的鞋子视为“农妇鞋”的合理性。夏皮罗认为海德格尔所解释的那双鞋,分明就是画家本人的鞋子,而不是农妇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这幅画只和凡·高本人有关,离开艺术家去谈作品,肯定存在某种程度上意义的缺失。关于这番说辞,海德格尔没有多作回应。针对二人的争论,德里达发声了,他提出“凭何认为这是一双鞋呢”的思考方向。
一、海德格尔的“农妇鞋”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为了揭示器具的器具存在,海德格尔以日常器具为例,选取了凡·高的一幅以鞋为主体的名画来对他的观点展开解释。他认为,不同的鞋根据用途的不同,材料和样式也就有所不同,一双鞋的存在就在于它的有用性。对于农妇来讲,鞋子服务于她,然而她却很少注意它们,甚至从来不朝它们看一眼。农妇穿着它们站立和行走,鞋子发挥了它们的用途,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于这种有用性之中。借助凡·高的这幅画,海德格尔想象了农鞋与农妇的关系[1]。海德格尔在此想从关于器具的器具存在的讨论过渡到讨论艺术作品的存在。针对海德格尔对这双“农妇鞋”的想象,夏皮罗提出了质疑。
在鞋子的归属问题上,夏皮罗指出:“海德格尔教授注意到凡·高不止一次地画过这些鞋子,但是他没有指出他所说的究竟是哪一幅,仿佛不同的版本是可以互换的,每一幅都敞开了同一个真理。”[2]对于这个质疑,海德格尔在回信中提到那幅画是他1930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展览上看到的。据夏皮罗考证,1930年阿姆斯特丹画展上参展的凡·高的作品中只有两幅是以鞋为主体的画。但是,这两幅中没有一幅能使人确信凡·高所作的画表达了一双“农妇鞋”的存在或本质。夏皮罗认为,那些画作描绘的很有可能是艺术家本人的鞋子,而不是一个农妇的鞋子,海德格尔认为从艺术作品中看到器具的器具存在,其实就是在自欺,因为他是事先想象好了一切,然后再把它投射进画面中。这种投射带着他对原始与大地的强烈同情。他见到凡·高的画作,联想起农妇和土地的种种,然而这些很少能得到画作本身的支持。
夏皮罗说在与作品的接触中,海德格尔既体验得太少,又体验得太多。“少”在海德格尔把画作上的鞋子局限在“农妇鞋”的范围,没有考虑其他的可能性;“多”在他关于农妇的生存图景想象太多,并把这种想象和作品叠加在了一起。总而言之,在夏皮罗看来,海德格尔的此番注解完全没有涉及这幅作品想要表达的真正本质,而是他自身想象的主观投射。
二、夏皮罗的“凡·高靴”
夏皮罗认为海德格尔忽视了绘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艺术家在作品中的存在。艺术家在作品中的存在表现在艺术家对于母题的选择。关于凡·高为什么要多次把靴子入画这个问题,夏皮罗认为,正是靴子的个人性和其面相学特征使其成为对凡·高来说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主题,如苹果之于塞尚。夏皮罗曾说:“一个艺术家对某类主题的习惯性选择,表明了其品质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家的价值观或世界观之间有所关联。在某些主题中,人们或许可以发现许多品质和内涵,但是要说明何种品质和内涵吸引了画家并非易事。”[3]凡·高也画过农民鞋,不过,他在画农民鞋和画自己鞋子时是不一样的,当他画自己鞋子的时候是“将它们孤零零地放在地上,似乎是正面向观众,一幅破损又皱巴巴的样子”[4]。为了佐证凡·高这幅画画的正是他自己的旧靴子,夏皮罗列举了克努特·哈姆生的经典小说《饥饿》中的一个段落,认为哈姆生对于靴子的描绘接近于凡·高对自己靴子的感情:“因为我以前从未看过我的靴子,我开始研究它们的外貌和它们的特征,我摇动自己的脚,再研究它们的形状和破损的口子。我发现它们的折痕和白色的接缝令它们表情生动,赋予它们一种面相学特征,我本性的某些东西已经传递到这双靴子之中,它们感动了我,就像我的另一个自我的幽灵,我的自我的一个会呼吸的那部分。”[5]
艺术家个人的经历也影响着艺术作品的创作,于是夏皮罗援引了高更回忆录中关于凡·高的一段话:“在画室里有一双大大的、钉有平头钉的靴子,破损得厲害,到处都是泥沙,他将它画作了一幅令人惊叹的静物画。”[6]夏皮罗将高更提及的这幅有靴子的画与海德格尔论及的那幅画相联系,再次确认画上的靴子是凡·高本人的。
夏皮罗在许多年后又写了一篇《再论海德格尔与凡·高》,作为1968年那篇文章的补记。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画上的靴子其实就是凡·高本人的镜像,凡·高在画靴子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审视和感知他自己。为此他列举了福楼拜的一封书信,书信里讲到福楼拜对靴子的感知,他把它们视为一种个人物品——一个人类境况的明喻。夏皮罗认为这封书信很有可能被凡·高读到,他是一个狂热的福楼拜崇拜者,有可能从这封书信中受到启发。夏皮罗说:“不规则、生硬的图案,以及延伸到靴子侧影外令人吃惊的松弛而扭曲的鞋带,不都是凡·高对靴子那古怪看法的构成性特征么?”[7]
夏皮罗认为孤零零的靴子是一个独特的隐喻,背后潜藏着凡·高残疾的主体。他认为,海德格尔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忽略了这双靴子对于画家本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把画家主体抛到一边,同时又虚构出一个想象的主体。夏皮罗严格地循着自己的方法去反思,去追寻作品与艺术家的关系。
三、德里达的解构
德里达作为一名解构主义者,也是见证这一公案的后来者,他的解读方式非常特别。他认为,在界定靴子究竟归属于谁时,夏皮罗和海德格尔都下了独断的判断,即这一定是一双鞋,两人对艺术作品的解释都带有一种“被规定性”。
在《绘画中的真理》一书中,德里达推测:“让我们假定两只(有鞋带的)右鞋或两只左鞋。它们不再构成一双,那么,整件事就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开始以怪异、令人忧虑,或许还是唬人的,略带恶毒的风味,斜睨或坡行。”[8]凡·高只是画了靴子,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说这是谁的靴子。德里达没有偏向夏皮罗或海德格尔的任何一方,而是指出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对应,他们都不假思索地认为,画作中画的是一双靴,在他们的思考中,一直被这种想法所支配。作为被使用的器具,一只一定得对应着另一只,因为人们没办法穿两只左靴或者右靴走路。因此,无论是夏皮罗还是海德格尔,都默契地认定这是一双靴,他们都囿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藩篱。对此,沈语冰教授说:“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仅凭理论上这一点可能性的论说力,到了现实中,究竟还剩下多少?一旦我们走出单纯的文本——这一点必定是德里达所否定的。在他看来,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它的说服力和有效性还剩多少的问题,对德里达来说无疑将是致命的。”[9]
总之,这场争辩可以说是艺术与哲学的一次交锋。丹托认为艺术使人神魂颠倒的、對人有吸引力的和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常常与哲学无关。在讨论艺术时,哲学家常常倾向于使用自己的体系,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对于艺术作品的解释丰富了艺术阐释的一个向度。作为艺术史家的夏皮罗在艺术阐释上更重视建构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之间的关联。对于凡·高的这幅画作究竟想表达什么,什么样的解释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一幅画作绝对正确的注解应该被我们所寻求吗等一系列问题,在艺术阐释中或许没有绝对正确的解答,我们也无法穿梭时空再去还原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但是,夏皮罗的解释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注重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的存在,尽力去理解艺术家创作时的情感表达。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9-20.
[2][4][6][7]夏皮罗.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术家和社会[M].沈语冰,王玉冬,译.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6:134,137,138,145.
[3]夏皮罗.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M].沈语冰,何海,译.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5:23-24.
[5]HAMSUN K.Hunger[M].New York:Alfred Knoph,1941:27.
[8]魏柯玲.画与真:论德里达《绘画中的真理》[J].文艺研究,2020(2):148-160.
[9]沈语冰,夏皮罗,王玉冬.艺术史的人文主义基础:再论海德格尔-夏皮罗-德里达之争[J].文艺研究,2016(1):31-43.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