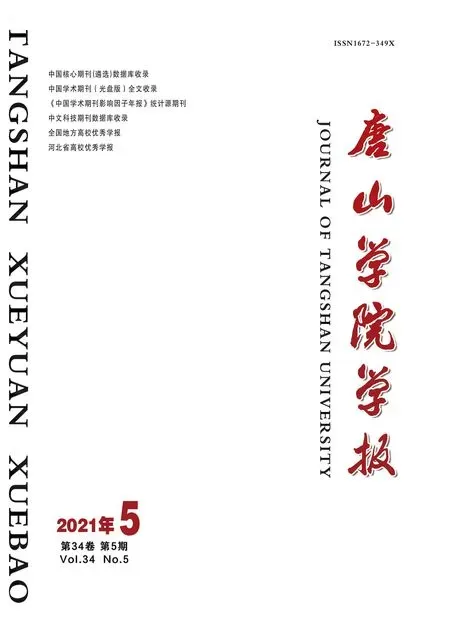建党初期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与斗争
2021-01-08刘贵福
刘贵福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一、从张国焘的一则记述说起
2002年《百年潮》杂志发表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B·舍维廖夫教授提供的新发现的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据舍维廖夫先生称,讲稿写在1929年印制的笔记本上,估计是在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党史教研室成立后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这两篇讲稿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诸多史事,其中有一部分谈到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时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张国焘写道:
北京小组成立(在上海之后),于1920(年)七、八月间,由李守常、张松年和我三人商量筹备(叫北京共产党)张松年不久赴法。我与守常与无政府接洽,他们也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争斗,一共有八人。……
1920(年)十月组织S·Y,共有30人分三派:
A)马克思主义派——马克思共产主义
B)无政府派——无政府……
C)与研究系有关系——社会主义
发行劳动音(周刊)、到长辛店、唐山……组织工会。与无政府党有争论。当时罗素讲演“自由联合”等,无政府派赞成,以此引起争执,自认是巴枯宁共产主义,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只同情苏联。我与他们大吵,守常想调和,结果,他们退出三人,其余三人仍赞成马克思共产主义。北京新中国杂志宋介也加入。当时在广东、上海……等处与无政府派都起争论,争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等。……
……当时虽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但都带了一些无政府的色彩。在开会(一大——引者注)以前有两个意见:汉俊与守常等是一个意见,国焘与独秀等是一个意见。……与无政府党争斗,守常也有些动摇。但独秀对这些问题当能坚决,对我的意见表同情。曾写信给我说:如守常动摇,就不客气的开除他。[1]
对于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激烈的论争等问题已为研究者所熟知,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学界也较多提及,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亦有学者涉猎,如任武雄的《试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问题的破解——兼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始末》[2]。但李大钊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过程中主张“调和”被张国焘视为“动摇”甚至陈独秀要将其“开除”的问题,似乎未见相关讨论。考虑到张国焘是北京党组织的最早成员,并参加了中共一大及中共创立前后的许多重要活动,因此他早年撰写讲稿所述史事应是可信的。并且,其所谈及的李大钊对于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也可从其他早期党的领导人的相关说法中得到印证。如蔡和森在1925年底至1926年初给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就曾提到李大钊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很为踌躇”。蔡和森说:
我党开始形成时,去那里找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呢?真正能够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人呢?且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派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宣传(在广东及各地都有组织且发行了许多小册子),并且在知识阶级中已有相当的影响了。当时曾有一部分激进分子相信了无政府主义。因此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仍占多数;在北京开始组织党部时有五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五人,而我们的同志则有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三人;在广东的党部又为无政府党人占多数,尤其是青年团大部分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并在共产党的机关组织他们的党团;在北京他们霸占宣传机关,叫守常做庶务,国焘去跑路。故在北京、广东组织上往往发生冲突……但在北京我们同志既占少数,所以守常很为踌躇,而国焘则主张与之决裂,后来结果把他们赶出去了。[3]22-23
蔡和森当时虽然不在北京小组,但蔡自1921年11月从法国回到上海后即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并在二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他的这份离建党时间还不是很久的“凭记忆所及而作”的报告,所言内容应该也是可信的。那么如何认识北京党小组建立初期,李大钊主张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以及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动摇”问题呢?
二、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
无政府主义自清末传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强烈批判资本主义,这种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流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立即引起了共鸣,并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重要力量。民国初期,因帝制被推翻,思想解放,无政府主义在国内进一步传播。到五四时期,作为一种思想,无政府主义已经传播得十分广泛;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化,他们深入到工厂中,组织工会,开展活动,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初期联合的主要力量。如蔡和森所说的那样:“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均有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我们开始工作时,在上海、广东、北京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是不行的。”[3]23
有研究指出,联合无政府主义者是从来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开始的。最迟从1919年起,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在中国寻求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宣传开展社会革命。在这一合作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亦主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结盟,并主张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1)关于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参见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对于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李大钊是赞成的。张国焘在回忆中曾提到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他说李大钊“研究社会主义较早,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4]83。张国焘在回忆中还提到李大钊当时还曾提出过“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的主张,李大钊表示“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4]107。据姜般若回忆,李大钊曾向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生命》投稿[5]。有研究表明,在布尔什维克党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李大钊曾在京津协助工作[6]。在俄共党员鲍立维创建社会主义者同盟时,李大钊曾积极参与。1920年1月,李大钊就曾参加鲍立维与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姜般若,山西无政府主义者平社首领、《太平》杂志主编尉克水,南开学生、觉悟社社员胡维宪,及《晨报》《时事新报》驻天津特派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在天津召开的会议,讨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酝酿组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问题[2]。社会主义者同盟是一个各派社会主义者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信仰者。所以,在北京党组织建立之初,李大钊和张国焘联合无政府主义者建立北京党小组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但无政府主义毕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二者间的分歧从合作之初就存在,但合作初期双方基本上是求同存异,矛盾并不凸显。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始于1921年初,主要原因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无政府主义批判的背景有关[6]。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陈独秀和张国焘态度较为坚决。在广东,陈与无政府主义者曾公开争论;早在北京党小组内部发生争论时,张国焘就主张“决裂”。张国焘的这种决然态度从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中可得到印证。朱谦之就曾评论张国焘:“作风很凶恶、专制。我们对他不满意,心想如果无产阶级专政都像他这样专制又凶恶,不是很糟糕吗,因此,和共产党思想上有距离。”[7]李大钊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一切国家、政府乃至无产阶级专政是坚决反对的。他说:“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8]360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说:俄国“为什么须以此种阶级专政为一过渡时期呢?因为俄国许多资本阶级,尚是死灰复燃似的,为保护这新思想、新制度起见,不能不对于反动派加以隄防”[9]4。“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9]104-105。虽然如此,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又与张、陈有所不同。如前引资料中张国焘所说的,一大前,“当时虽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但都带了一些无政府的色彩。在开会以前有两个意见,汉俊与守常等是一个意见,国焘和独秀等是一个意见”。蔡和森从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力量对比的角度对李大钊的态度予以解释,而张国焘则迳视李大钊为“动摇”。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时,李大钊与张国焘及陈独秀的态度有所不同呢?
理解李大钊的思想,应回到李大钊的思想体系中。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前,他曾提倡调和论。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调和论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修养上的美德。李大钊认为,调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宇宙间有二种相反之质力焉,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10]306“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者”[11]“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10]289。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李大钊说:“人类社会,繁矣颐矣。挈其纲领,亦有二种倾向,相反而实相成,以为演进之原,譬如马之两缰,部勒人群,使轨于进化之途。以年龄言,则有青年与老人;以精神言,则有进步与保守。他如思想也,主义也,有社会主义则[即]有个人主义,有传袭主义即有实验主义,有惰性即有强力。”[10]306李大钊系统提出了调和所应遵循的法则。这些法则是:①“言调和者,须知调和之机,虽肇于两让,而调和之境,则保于两存也”“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故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②“言调和者,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李大钊反对将新旧视为水火,强调新旧之关联;③“言调和者,须知各势力中之各个分子,当尽备调和之德也。夫调和者,乃思想对思想之事,非个人对个人之事。……然则欲二种之思想,相安而不相排,相容而不相攻,端赖个人于新旧思想接触之际,自宏其有容之性、节制之德,不专己以排人,不挟同以强异,斯新旧二者,在个人能于其思想得相当之分以相安,在社会即能成为势力而获相当之分以自处,而冲突轧轹之象可免,分崩决裂之祸无虞矣”;④“言调和者,当知即以调和自任者,亦不必超然于局外,尽可加担[袒]于一方,亦惟必加担[袒]一方,其调和之感化,乃有权威也”“言调和者,自当于新旧二者之中,择一以自处。盖虽自居于一方,若为新者,而能容旧势力之存在;若为旧者,而能容新势力之存在,究于调和何害者”[10]36-40。
应该指出的是,李大钊早年的调和思想,重点是强调在政党政治中不同党派间的调和与妥协,如他赞成章士钊在《甲寅》上提倡的政治当局“要节其好同恶异之性,而尚有容之德”的观点,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当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放弃了政党政治的主张,赞同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对政治问题的彻底解决,这样也就放弃了政治上的调和主张。但在处理和对待思想问题时,从李大钊的思想看,他仍然以调和为指导处理不同思想间的分歧。
以“调和”解决不同思想分歧的思想,态度理性,不趋极端,强调对不同思想的包容,然又不否定思想间的竞争;反对将新旧视同水火,强调新旧间的关联与代谢,尊重客体的主张而又坚持主体的鲜明立场,反对无原则的调和。这种调和论是李大钊联合各派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也是他处理思想文化纷争包括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歧的原则。如,在对待新旧文化的问题上,李大钊主张创造新的路径、新的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10]291-292;在对待东西文化问题上,李大钊主张“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西文明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10]311。对于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如贵族与平民、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佃户、老人与青年之间的分歧,李大钊认为也应协力与调和,“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10]43。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赞成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说,但认为阶级斗争说有所不足,主张以互助思想来补正,主张社会物质的改造与精神的改造(人道主义、互助思想)一致进行,实行物心两面、灵肉一致改造(2)参见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极端推崇的互助论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理论基础。以此,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发生矛盾时,李大钊主张调和,这与张的“决裂”主张和陈的“坚决”态度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大钊的态度显然不是张国焘所说的“动摇”,也不是如蔡和森所说的因为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者人数少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因所致的“踌躇”。
三、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
前面谈到,李大钊主张不同思想和政治力量间的包容与调和,但并不排除不同思想间的竞争。李大钊说:“今人不解调和之真义,因于一切分当竞进之事,而皆有所怀疑不敢自主之概。似一言调和,即当捐禁竞争;一言竞争,即皆妨碍调和也者。”[10]37同时,他更反对那种不偏不倚的中立式的调和,主张旗帜鲜明,如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于来自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李大钊起而反驳,并明确表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8]53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极端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摆脱一切来自国家、社会或在思想道德上对个人束缚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因),李大钊都明确反对。在批评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时,李大钊既反对极端地强调个人自由的主张,也反对极端地扩张社会权能的做法,他主张将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有机地统一起来,调和二者的分歧与矛盾。这一观点集中体现在他在1921年1月所写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
在《自由与秩序》中,李大钊指出,社会的学说就是要解决个人与社会的权限问题。在个人与社会的权限问题上有两种观念,一是极端地主张发展个性权能,尽量要求自由,减少社会及于个人的限制;二是极端地主张扩张社会权能,极力重视秩序,限制个人在社会上的自由。李大钊认为个人主义可以代表前说,社会主义可以代表后说。但李大钊反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他认为个人与社会二者并非互不相容,而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李大钊写道:
个人与社会,不是不能相容的二个事实,是同一事实的两方面,不是事实的本身相反,是为人所观察的方面不同。一云社会,即指由个人集成的群合;一云个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8]326
李大钊认为,人不能生来就离开社会环境,自己过一种孤立沉寂的生活,这样的人没有自由可以选择,也就没有个人的意义。而社会完全抹杀个性的发展,社会必然呈现出死气沉沉的现象,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也就失其活动之用而日就枯亡与陈腐,也就更无所谓秩序了。所以,李大钊的结论是:
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的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
我们所要求的自由,是秩序中的自由;我们所顾全的秩序,是自由间的秩序。只有从秩序中得来的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中建设的是秩序。个人和社会、自由和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8]327
在关于李大钊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研究中,研究者都会引用《自由与秩序》一文的观点,但皆没有指出这些批判中的调和思想。如将该文置于李大钊的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出,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是在其调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即从反对极端的个人自由的主张和极端的扩展社会秩序的主张的“两让”出发,达到合理的社会主义和合理的个人主义二者“保于两存”的目的。李大钊在写作《调和之法则》时就曾阐述过秩序与进步不可绝对分离的关系,他说:“有徒务进步而不稍顾秩序与安固者乎?有徒守秩序与安固而不求进步者乎?盖无有也。”[10]38-39其后他在《青年与老人》一文中再申此意:“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10]44可见,李大钊在《自由与秩序》中对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论述,是他的调和思想的发展,也是他的调和思想的一个具体体现。
前面,我们讨论了建党初期李大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在建党初期,李大钊积极联合无政府主义者,这对于党早期开展的工作“有相当的作用和益处”[3]23。在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李大钊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主张开展批评,他既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张,也反对极端的扩张社会权能的思想,努力探索自由与秩序和谐共存的理想之境。可以说,李大钊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与批判,体现了他对于不同思想的“涵纳”和“有容”[10]40,是他运用调和方法处理不同思想流派关系的一次实践,其所含意蕴非“动摇”和“踌躇”所能体现和描绘。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其早年所形成的政治思想仍在发挥作用,其思想发展是辩证扬弃的,而非割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