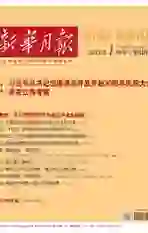93岁灰娃不老的鸟儿在唱歌
2021-01-06陈娟
陈娟
这是一座两层小楼,坐落在北京西郊山中。院内有两棵老树,一棵枝叶茂盛,尽展秋色;一棵颓败,留下光秃秃的枝干和树杈。房间内陈设简单、素雅,窗台上摆着各种古陶罐,壁炉上是佛头、石马和泥马,沙发和座椅铺着布垫,用民间毛蓝土布缝制而成。10多年来,灰娃一直居住在这个被称为“大鸟窝”的家里,很少进城,疫情期间更不出山。她读书、记笔记、写诗,坐在藤椅上回忆往事。
“大鸟窝”的名字,来自灰娃的先生、画家张仃多年前做的一个梦。梦里,灰娃偶遇一地,有山、有森林、有河,河边林间有一只硕大的鸟窝。她赶紧跑回来叫张仃,两人就住进了大鸟窝。“张仃讲述梦的情形,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个清晨……”灰娃对记者说,当时张仃已80多岁了,“却还像少年一样,满脸天真”。巧的是,家里的枫树上也突然冒出一只鸟窝,此后,他们便将这处家园唤为“大鸟窝”。
张仃离世已整整10年。今年4月,灰娃怀念他,写下一首诗:难得的日子,仿佛一只相思鸟儿/躲进荼蘼花丛幽寂阴影/与自己聊天、忆往,夜夜走入无从察觉/销蚀关于人、关于灵魂记忆的噩梦……
诗的名字叫《带着创伤心灵的芬芳》,收录在她新近出版的诗集《不要玫瑰——灰娃自选集》中。这本自选集,收录了灰娃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创作的部分诗歌,共65首,有思念、有批判、有关于死亡的理解和追问,也有对张仃的绵绵回忆……“所有的文字,都是我的生命热度,我内心的表达。”灰娃说。如今她已93岁,仍精神饱满,吐字清晰,完全不像耄耋老人。
理想的召唤
灰娃写诗近50年,始终信奉“诗从灵魂中来”,“必得诗自内心催我,我才能写”,常常灵感来了,抓起笔就写。有时睡至半夜,梦中想起一些词句,立马起身记在纸上。她给记者看手稿,大都是书本大小的纸张,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和线,红、蓝、黑,难以辨认。
“这些手稿让我联想到大脑条条的沟壑,秋日树林里的层层落叶,交织的蛛网,重叠的影像,与作曲家的草稿很像。”出版人汪家明说。他和灰娃相识15年,曾编辑出版过她的上一本诗集《灰娃七章》,也是《不要玫瑰》的特约编辑,读过她的每一首诗。在他看来,灰娃的创作,一部分是天生之才,一部分源自生活,“其背后是血雨腥风悲喜交并的大时代和与时代紧密相连的一个人的传奇人生”。
灰娃这一生,的确是一部传奇大书。
1927年,灰娃出生在陕西临潼一个大户人家。祖父是前清举人,一大家子住在庄园中。院子很大,种着玫瑰、石榴、木槿、刺梅、忍冬,四面有排水的孔道。大门厚实笨重,“我们一群小孩合力齐推,它才缓缓地、艰难地、吃力地开启少许。一面发出吱——痛感的声音”。后来,祖父母过世,大家族解体,她跟随父母、姐姐搬到西安。父亲是读书人,谋得一份教职,以薪水养家。
10岁那年,父亲去世,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母亲带她回乡下避难,在外婆家住了一年多。后来,表姐、姐姐说要带她到汉中读书,“原来她们当时都是左翼青年,也想让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灰娃离家时12岁。她记得那天清晨,母親帮她穿好童子军制服,戴好宽边呢帽。她和表姐先乘火车到西安,后坐马车日夜兼程,来到一个小城堡。城堡四面是高高厚厚的城墙,已然有些破损,里面则是另一番景象:亭台楼阁、池水假山,桌椅板凳、穿衣大镜、大匾额、小挂件,皆镶满螺钿,闪闪发光。这城堡原是大文学家吴宓的故里,后来成了著名的安吴青年训练班——来到这里的,全是汇入革命潮流中的年轻人。
灰娃和表姐一起被编入行军队伍,在这个集体里,她的名字是“理昭”,意为理想的召唤。因为年龄小,个头不高,整日傻乎乎的,大人们便亲昵地唤她“灰娃”。多年后,她对这一名字做了解读:“灰,直意是一种颜色,转意为暗、苦、涩。‘灰娃,是苦命的、令人怜惜、疼爱的小孩。这里面有一种意味,对被叫者没尽到责任而致使其命运坎坷清苦,一种歉疚味儿的痛惜之情。”
在安吴堡,灰娃跟着大伙儿上课、唱歌、军训,每
天都接触新事物。1939年底到1940年初,安吴堡的青年们经历漫长的行军,抵达延安。“当时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艺术家,画家张仃,诗人艾青、塞克,作家萧军等,文艺活动异常活跃。”灰娃回忆说。
也是在这里,懵懂的她开启了思想、文学、艺术的启蒙,获得精神上的成长。
在延安,人们都喜欢她
灰娃时常会怀念在延安的日子,在她内心深处,延安是自己的“精神木马”,“往事种种,虽已遥远,但依然温暖地活在我的心上,抚慰着我的生命”。
到延安后,灰娃进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她年龄小,被编入儿童班。当时,延安经常开大会、听报告。儿童班的孩子大都听不懂,“只是听指挥,看着大家激动,也跟着兴奋”。大会多在山间举行,搭一个简陋的台子,四周山崖挂满标语。一散会,孩子们便一窝蜂地撕下标语,拿回窑洞,裁成小块,钉成本子,等到上课、听报告时,在大字的缝隙处做笔记。后来,指导员发现了,将他们批评一顿,之后就再不敢了。延安物资匮乏,没有墨水,他们就从医务室领一些灰锰氧,用水化开,变成“紫墨水”,“好像任何困难都不怕,总能想到办法”。就是在那个时期,灰娃养成了在纸片上记笔记、写心情的习惯,一直持续至今。
1941年,“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解散,学员分配到各处。儿童班仅留下17人,组成儿童艺术学园。学园从延安各单位聘请艺术家、学者为他们上课。课目有国文、算术、自然、英文、音乐、戏剧、美术、形体训练等,此外还有专题讲座,塞克讲怎么写歌词,张仃讲美术欣赏,音乐家杜矢甲讲发声法,等等。
灰娃印象最深的,是“作家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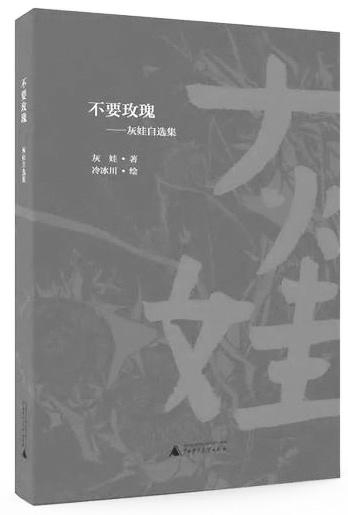
俱乐部由“文抗(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艺术家自己建立,张仃设计施工。他在山坡上发现一大间房子,找来两个木匠,先做一些矮板凳,上面铺上牛毛毡,放在墙根,权当沙发。再找来白土布,一些做窗幔,一些围成高高的筒,留一个进出口,里面放一个木台子,就成了吧台。四周墙上的壁灯,是用农民筛面的箩做成,将箩从中间切开,变成两个半圆,分别扣在墙上,里面放盏小油灯,灯光从细网孔里射出。正面墙的高处,悬挂着“文抗”的会徽,也是张仃设计制作:一大团火苗中一把钥匙,象征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盗取光明。
那些艺术家喜欢小孩,常常接他们过去。在那里,孩子们唱歌、跳舞,演童话剧《公主旅行记》等,公主一角常由灰娃来演。周末俱乐部有晚会,大家都戴上张仃做的黑色面具,跳舞、聊天。有一次,俱乐部举办了一场西方现代派绘画作品复制品展览,有野兽派、立体派等,张仃一幅一幅给孩子们讲,“打开了我们原本蒙昧的眼界,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画”。
“在延安,我一直都很羡慕身边的大人,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为理想献身。”灰娃说。她每天努力学习、劳动,被选为模范儿童。大人们都夸她,唤她“小公主”。后来,晚年的张仃对灰娃回忆,那时候艾青曾说:“灰娃这个孩子很奇怪,延安的人没有人不喜欢她的,甚至很娇惯她,可是她没有自己娇惯自己。”
无意中走到诗的森林里
灰娃说,他们那个年代走出的人大都不会娇惯自己,“很多时候被时代、被命运推着走,没有选择”。
她听从组织安排,曾到军队做文化教育工作,也曾在紧急情况下接受命令,带领上百人转移。19岁那年,她和一位兵团作战参谋武昭峰结婚,两人随部队南征北战。1951年,武昭峰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牺牲。噩耗传来时,灰娃正在南京陆军医院治疗肺结核,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再受打击,当场大口吐血,只好到北京西郊疗养。两年后,她身体康复,到北京大学求学,磕磕绊绊地开始了新生活。
在北大读书时,灰娃小有名气。诗人谢冕和她是同学,但不同系——灰娃是俄语系,他是中文系。当时两人并不相识,謝冕只是听说俄语系有个女同学来自延安,一袭白色连衣裙,是当时校园里一道风景。因为穿着,灰娃在学校被指责“不像个老干部”。后来在种种运动中,她总是被批判,“走路、神态、讲话、穿衣……似乎一切都是错的”。
“但凡看到有人举手,必会恐慌害怕,认定对方要打我。” 灰娃痛苦地挨着日子,这时旧疾肺结核又复发,不得不请假,到东四十条的一个房间里养病。她开始自学中国古典文学,每日读《楚辞》《诗经》,由此爱上古诗词,精神上也获得安慰。康复后,经外交官黄华推荐,她到北京编译社工作,翻译外文书。
武昭峰去世后,很多人关心灰娃,给她介绍对象,都被她拒绝。1964年,她在朋友处遇到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的白天。“白天曾是开国少将,有着深厚的中西方文化修养,品性刚正不阿。”灰娃说,她选择伴侣最看重的就是品性。两人很快结婚。但好景不长,“文革”到来,白天摔断了股骨,靠拐杖度日,之后又患上肺癌,卧床不起。那段日子,灰娃的情绪起伏不定,渐渐患上抑郁症,一边照顾白天,一边忍受精神疾病的折磨。

最痛苦的时候,灰娃甚至想到了死亡。1972年,她拾起往日的习惯,在纸片上写写画画,大都是各种心情文字,“有时是一句、一词,有时是一个字,或一段话”。写出后,她又害怕,担心成为“罪证”,就赶紧撕碎,偷偷丢进马桶冲掉。
后来,社会气氛一天天宽松,朋友间也开始走动。灰娃拿着纸片到张仃家,给他看那些文字。张仃看后,既震惊又激动,让她把纸片藏好,并鼓励她:“如果你给自己心里的美找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就是你写的这些文字。这是诗,我们中国人需要这样的诗。”从那时起,灰娃把每天写诗的纸片放进一个铁盒子,悄悄挖开大花盆中的泥土,把铁盒子埋进去,再放上一摞空的小花盆。
“每当写诗时,我的思绪好像有个落脚的地方,不再害怕、不再恐惧。我沉浸在诗的意境中,如鱼得水。”灰娃说。怀念家乡时,她写《大地的母亲》,“窗外树林/星空/门前溪水晃荡着圆满金色的月亮”;想象自己的死亡,她写《不要玫瑰》,“不/不要玫瑰 /不用祭品 /我的墓/常青藤日夜汹涌泪水/清明早上/唤春低唱/一只文豹/衔一盏灯来”;她也会呐喊,在《鸽子、琴已然憔悴》里追问“灵与魂被强暴?被偷换?亲手捧献?/千秋深意有谁品味过?/什么人匆匆停下一霎把心观照一回?”
“我是无意中走到诗的森林里来的,事先并没有做一个诗人的愿望。诗是主动的,我乃被动者,是诗催促我把它表述出来。”灰娃说。在治疗和写作中,她的精神分裂症慢慢痊愈。多年后,学者王鲁湘说,灰娃在“文革”中的文字是一种“自我谈聊”,用以疗愈自己。
“她有一颗孩子的心”
现在的灰娃,每日作息按身体的自然规律来,累了、困了就休息,清醒时看书、写作。有时也会坐着发呆,想念张仃。她眼前常常浮现一个画面:张仃从远处走来,满头白发,含着冒烟的大烟斗,全身环绕着月晕辉光。之后,她和张仃坐在一起,看书、聊天,聊惠特曼、聊鲁迅,也聊毕加索,周边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有鸟叫,“最是愿望不过,人世忘了我。”她知道这是个梦,但她不愿醒。
张仃曾是她的艺术启蒙者、人生导师,后来成为她最后的爱人。两人结合于1986年,在白天过世13年后。那一年,灰娃59岁,张仃69岁。

“当时张仃已经离休,一心想到外面写生,画山水画。我就整个为他服务了。”灰娃说。10多年间,她陪着张仃六上太行山、五赴西北、三进秦岭,登泰岳、下苗寨、进九寨……“那些年他像疯了一样,争分夺秒地画。一进山,就像中了魔,看到吸引他的地方,拐棍一扔,提笔就画。夜里想起来哪里画的不好,起身就去修改。”
因为四处游走,灰娃的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与张仃结伴壮游神州大地,灰娃的诗风在沉郁的基础上,开始变得乐观、明亮、大气。”学者李兆忠说。他因研究张仃与他们夫妇二人成为好友,相交多年。
1990年8月,两人赴甘肃河北走廊写生。在大漠中行进,她感到“大口大口/咀嚼太阳的味道”;在空荡荡的戈壁滩,她目睹“日头一落就出发/在大漠上空滚动/轰隆轰隆地巨响”……每次写完诗,灰娃第一时间拿给张仃看。在张仃眼中,灰娃始终是那个在延安唱歌、跳舞、演戏的孩子,“一般人一长大,就世故,世故以后就不再有诗,灰娃到老年还能写诗,她有一颗孩子的心,心里就只有一个美字”。
1997年,在王鲁湘、李兆忠等人的推动下,灰娃的第一本詩集《山鬼故家》出版,引起诗坛轰动。对于她的诗,诗人屠岸称其“是一种新的个性化语言的爆破,是灵魂的冒险、灵魂遨游的记录”;诗人牛汉说,《山鬼故家》是不受诗坛圈养的“野诗”;唐晓渡则评价为,只能用“高贵”来形容。
后来,张仃生病,停止外出写生。为了全心照顾他,灰娃很少再写诗了。她和张仃搬进“大鸟窝”,过起隐居山林的日子。白天,她收拾屋子,张仃看书、画画。张仃要写字,灰娃就提前准备,先挑一些有意境的诗,把纸张按字数折好,铺在画案上,检查毛笔、墨汁,取出张仃选好的那首诗,用篆书词典查出他记得不太准的字,照猫画虎在旁边用铅笔写出,给他参照。偶尔,两人会去市里,逛逛公园、看看展,大都是张仃坐在轮椅上,灰娃慢慢地推。
2010年,张仃去世,灰娃深受打击,多年不发的抑郁症再度袭来。后来,依然是诗歌拯救了她——张仃不在的日子,她陆陆续续写下30多首诗,其中组诗《在月桂树花环中》《童话·大鸟窝》等,专为悼念张仃而作,屠岸读后,称这组悼亡之作“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史诗的铜碑之上”。
从《山鬼故家》到《灰娃的诗》,再到《灰娃七章》《不要玫瑰》,迄今为止,灰娃出了4本诗集,总共不足百首,算不得高产。“但每一次创作的感受是幸福的、奇妙的、迷人的,是我在这人世间最高的享受。它让我的心摆脱了现实的折磨,超越于平庸繁琐的日常。”
采访临近尾声,灰娃突然想起很多年前读过中国现代作家高长虹的一篇文章,名字是《诗人》。高长虹写道:“一首好诗,一定是当代文化的最高点……诗人是人类的一首好诗。”她曾把文章抄在笔记本上,时时拿出来读,字字句句铭记于心。
“那么,您觉得诗人是什么?”记者问。
“诗人是一只鸟,不停地在唱歌,唱人类的痛苦,唱人类灵魂的疾病。把这些都大声唱出来,从而促成人类灵魂的改变。”灰娃说,她写诗就是在拿灵魂去和自己、和他人、和世界交流,在这交流中,她汲取力量、修身养性,并获得重生。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2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