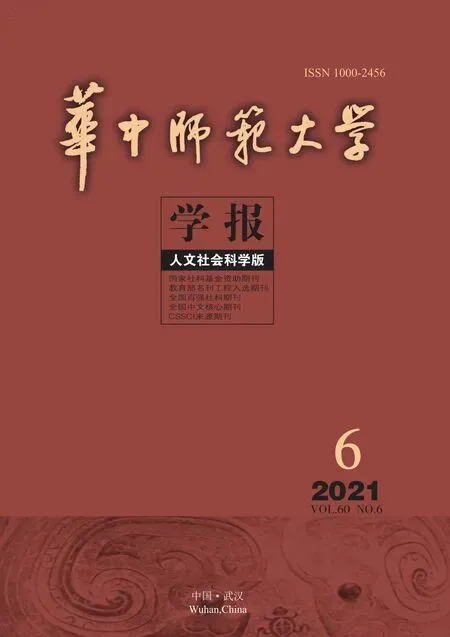朱英诞山水诗与唐宋山水诗的精神汇通
2021-01-06王泽龙薛雅心
王泽龙 薛雅心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诗歌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9)
山水诗贯穿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它萌芽于《诗经》、《楚辞》、汉赋,形成于魏晋,至唐宋到达艺术高峰。朱英诞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派诗人中的代表性诗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山水诗歌创作的代表性诗人。谢冕曾评价他:“学贯中西,艺通今古,诗文灿烂。”①朱英诞对中国古代山水诗素有关注,他说山水诗“源远流长,上溯陶、谢,旁及储光羲,有泉一线,下开隐佚之士以及诗画同源的广阔,但有时是泛滥无归,这些都是很清楚的。”②他也注意到现代山水诗:“在我们当代,它还如水就湿地触及新人(例如宗白华、闻一多——尤其是孟浩然,他曾有专文论及)的地步。”③朱英诞深受古代山水诗影响,经笔者统计,他在近半个世纪的诗歌生涯中共计创作山水诗有1300多首。他还编订多部诗集,并从古代山水诗句中选用字词为其命名,如从李迥秀“霁云开就日,仙藻丽秋风”中取“仙藻集”,从王安石“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取“花下集”,从范成大“草草鱼梁枕水低,匆匆小驻濯涟漪”取“枕水集”,从庄子“空门来风,桐乳致巢”取“桐乳集”等。他的山水诗继承传统,又化古为新,体现出一位现代诗人与唐宋山水诗精神的自觉汇通。
多位学者已关注到朱英诞的山水创作。有学者看到他诗歌中古典与现代交织的风味,称其为“古典的现代田园诗”④。其实朱英诞描写农事的田园诗并不多,较多的是表达对自然景物喜爱的山水诗。陈子善对其诗给予高度评价:“他的许多诗,表面上是写春风秋雨,花木田园,这些原本是中国历代诗人咏颂的对象,但因诗的内里真切抒发现代人的复杂的情感,故而呈现出既继承又创新的前卫姿态”⑤,“如果说朱英诞是中国现代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绝非过誉。”⑥
一、回归自然的心灵舒放
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起初,自然景物在诗歌中处于陪衬地位,不具备独立的审美价值,晋宋之交山水诗取代玄言诗登上诗坛,如刘勰所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⑦自然景物一跃成为诗歌主体,唐宋时期几乎无诗人不写山水诗。
(一)意象世界:人与自然的融合
唐宋山水诗沉浸于自然世界之中,苍凉烟雨、壮阔山水、鱼跃鸢飞、荒寺夜月、桃花流水举目皆是,诗人通过回归自然获得心灵的慰藉与美的享受。山水书写不仅仅是个体对自然的向往,更是唐宋文人普遍的一种精神情结。朱英诞赞同晚明王季重所说的“诗近田野,文近庙廊”,一生钟情山水,沉浸自然。他很重视山水诗,认为“它的文化上的位置,我们应该清醒地对待,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承认我们的民族过去是‘诗的民族’”⑧。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他深切表白:“诗夹着田野的气息,如春云而夏雨,秋风而冬雪,点缀了我的一生,生命的四季。”⑨
回归自然是朱英诞与唐宋山水诗人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不仅描绘自然世界的山水花鸟,也通过自然意象表现个人理想、进行人生思索,赋予意象以丰富的内涵。朱英诞结合个体诗思从唐宋山水意象中进行择取,多凭借鸟、荷、月等意象通向回归自然之径。唐宋诗人通过鸟意象表达自我匡扶社稷的志向与渴望超越尘俗的自由。如杜甫的“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为君除狡兔,会是翻鞲上。”(《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再如刘禹锡《乌衣巷》中的燕意象与命运、历史相关,诗人在宏观世界中思考关于时空的哲学命题。朱英诞也有:“二十世纪的梦寐,/很相像,/于任何别一个世纪/它是过去或未来的巢。//飞翔吧,过去的鸟,/飞翔吧,未来的鸟。”(《飞鸟》)他立于20世纪,在生命的迷茫中将目光投向高飞之鸟,看着鸟儿衔着诗人对未来的企盼自由翱翔。现实世界无法实现理想的抱负,现实人生无法穿越时空的阻隔,那么自然世界给他们创造梦想的空间,诗人们通过鸟意象为自身构筑精神园地,使诗思奔向更绵长广阔的时空。
唐宋诗人也常用荷、月意象来表达自身的精神追求与人生之思,荷、月蕴含人生的清浊、虚实等问题。莲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洁净人格的象征,月喻指佛性清净与人生虚幻,如“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皎然《水月》)此外常与荷、月密切联系的还有镜、灯。镜有明净鉴照之意,如“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戴叔伦《兰溪棹歌》)佛家常把灯作为禅心的象征,寓意心灵烛照一切,如“师亲指归路,月挂一轮灯。”(寒山《诗三百三首》)朱英诞也常用这些意象,他将“荷”“月”喻为“灯”“镜”,如:“荷花是一盏奇妙的灯,/它只照着自己的影”(《荷》),“月亮是美幻的镜,/仿佛是美好的梦”(《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晚对月夜深有雷雨》)。这几种意象蕴含着诗人对人生虚实的思考,这些思索也赋予山水风景以智慧的灵性。山水意象成为诗人表达理想、凝集思想的中介,体现他们回归自然的精神追求,诗人也借此陶醉于山水花鸟之中。
正如唐宋山水诗人各有特色一样,朱英诞的诗歌也有独立而鲜明的特点。受到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朱英诞强调诗歌主体之“我”。他通过主体来投射山水的多种姿态,同时又将自身置于自然界,主体诗思与自然规律相应和,完成人与自然的诗意交会。“有时候我发现:/我的右臂是垂柳,/而左臂是那芦中的风;/我的左眼是一只飞鸟,/我的右眼是一串葡萄;/我的心是充足的阳光,/我的鼻子是花香氤氲如云,/我的耳朵是岩石间的雕像,/我的眉毛是草叶,/我的双腿被雕塑成功/奔驰的马如龙。”(《恍惚》)诗人将自我物化,除自然景物之外,“我”也成为诗歌意象之一,获得空灵自在的生命形态,这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山居秋暝》)物我同一的状态有些相似。但在朱诗中,“我”是被突出的,他特别强调主体“我”与客体“你”,如“你变作一个瘦弱的儿童了,/惊讶我曾倒在那大地上,/如一件暗杀案,/啊迷途的鸟!”(《登高作》)“悲哀的,温柔的鸟儿,/你永远徘徊着吗?/悲哀的鸟儿,/多思的鸟儿。”(《海鸥》)虽说唐宋山水诗有“有我之境”,但仅是“物皆著我之色彩”,相较现代诗,它较少使用理性思考本体的存在。而朱英诞则突出个体,不愿让自我完全消融于自然之中,在山水之中葆有个体的理性诗思。
(二)以诗还乡:城市与乡村的对照
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它“历经数千年,大致可分为春秋战国奠基期、魏晋南北朝成熟期、唐宋鼎盛期、元明清衍变期”⑩。从叔齐、伯夷,到陶渊明、谢灵运,再到柳宗元、寒山,隐居逐渐成为文人表达心志的行为。唐代孟浩然、王维、李白以隐求仕,白居易通过“中隐”免除饥寒,躲避纷争,宋代苏轼游西湖“未成小隐成中隐”,范成大“中隐堂前人意好”,此外还有“禄隐”“酒隐”“半隐”等。诗人在隐居环境中书写山水,使山水诗成为隐士文化成熟期的艺术结晶。在此风气下,他们以否定态度书写城市,表达对乡村田园的向往与追求,如白居易诗《题元十八溪亭(亭在庐山东南五老峰下)》有:“怪君不喜仕,又不游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声满耳。饮君螺杯酒,醉卧不能起。见君五老峰,益悔居城市。”北宋时期随着坊市结构的改变与夜禁制度的松弛,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忧心的诗人对城市化进程非常警觉,如张俞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苏轼也有“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和归田园居六首·其四》)乡村的纯净和安宁,与城市的复杂和喧闹成为对立的两面,唐宋诗人们在乡村中寻找心灵的归属与精神的栖息。
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自然环境、人的异化、工具思维为代价的社会发展引发人们思考。这种城市化要比宋代的城市化程度更深,影响更大。朱英诞一生居于城市,又恰逢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对城市的书写有自己的视角。他笔下的城市是“不夜城”:“完全是灰色的墙垣/遮栏在眼前(夜来,/他们消失了)而脚步/遂永无休止//但只有高耸的广告牌/点缀着虚无的天和海/那些星辰更高了,吸烟的女郎;/它们是一些虚无主义者”(《不夜城》)。城市相对农村是“不夜”的,但这灯火斑斓却有些恐怖,灰色的墙垣、永无休止的脚步、五光十色的广告牌、吸烟的女郎……星辰去哪了?只剩下空虚的外壳。都市的“白昼里也颓废如夜”(《都市小景》),这种颓废、恐惧、空虚感受不就如同张俞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他们都对城市的繁华与欲望保持警惕,对乡村的宁静与纯真充满渴求。这种文化心理是由农耕文化影响长期积淀而成,乡村寓意返璞归真的淳朴,城市则代表追求名利的浮华,古代诗人在官场受挫后归向自然,以求内心慰藉。朱英诞则从自然中寻求平静:“当我对着人时,我被束缚着/而对着天空,如释重负”(《岭头》),从而“避人如逃寇”。
同样渴求乡村、警惕城市,唐宋山水诗人返归乡村感受自然,诗歌是乡村美景的一种呈现方式。而朱英诞因居于城市,选择在诗歌中构筑精神家园,在他看来诗歌就是乡下,其山水诗充满“以诗还乡”的向往。“贪噬的城市酷嗜和平,/只有死亡会把我还给乡村?”(《幻灭的诗》)一个“还”字已表明诗人的态度。可他不在乡村,“我是这样爱乡下,/平静的乡下仍怀有古昔月色;/然而要居住在这里来,/却必须等到死去之后,亲人们!”(《扫墓》)既然无法去往乡村,那就利用想象在诗歌中构建乡村美景,通往心中自然之径。他强调要将诗作为乡下:“如果现代都市文明里不复有淳朴的善良存在,那么,至少我愿意诗是我的乡下。”作为“大时代的小人物”,他在诗歌中搭建山水自然之景,创造一方宁谧自由之地,使“小人物”拥有自在广阔的生活空间。“历史像流水逝去,/哲学像山果堕落;/惟有你,诗啊,/让城市化作农村。”(《诗》)朱英诞充分发挥了诗歌之用,诗歌是想象的艺术,它以诗人的精神向往为导向,创造个体想象的生活空间。只有在诗歌里,他才能短暂逃避城市,抓住乡村的影子,并用文字的形式赋予乡村以诗意。乡村承载诗人对自然的向往,诗便是承载手段,山水诗成为独属于诗人的至乐天地。此时,诗不仅是诗,也是诗人的还乡之途。
(三)归于自然:生与死的超越
“未知生,焉之死?”(《论语·先进》)孔子的一句话几乎抹去死的地位。道家看到生死乃自然现象,但道家不愿“尽人事”,选择与自然合一,达到死生齐一的境界。“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至乐》)甚至趋于妻死鼓盆而歌的乐死境界。这种哲学思想渗透到唐宋山水诗中,无论是月的阴晴圆缺,还是季节的春夏秋冬,都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一部分。诗人在山水间忘却死生、获得至乐,沉醉于悠闲自在、欢快欣然的精神境界。如杜甫“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后游》)自然涵养了诗人乐生的思想,山水诗也就成为这种生命观的物质载体,两者相辅相成。朱英诞称赞杜甫:“你是那窗的坚强的爱者/在一个诗人的功力上说/我赞美你的极端的冷静/像蜥蜴,它是绿色的蛰居人”(《窗——杜甫赞》),将杜甫比作“极端的冷静”的“蜥蜴”,赞赏杜甫于国破家亡时的沉着。唐代山水诗的生命态度不自怜自艾,而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的豪情,“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的潇洒,“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李商隐《花下醉》)的乐观。
唐代诗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山水诗所呈现的生命气度,影响了朱英诞对生死的态度与书写生命的方式。他将这种洒脱超然的生死观念附于诗文中,其山水诗呈现乐观向上的生命观。“啊,大地的爱者,/斑斓的蝴蝶飞舞起来。/我走到水边静听微响,/于是你啊,也许正在想:/是否已经开始了春天。”(《挽歌辞》)这是诗人对墓中人所说,告诉墓中人春天已经来临,以温柔奇妙的方式呈现出对逝者的关怀。《挽歌(一)》写道:“让花儿朵朵阴覆着你长眠,/辛辣的春天里盼着蝴蝶翩飞。”《挽歌(三)》写道:“一切在你都变成了仙乐,/从此却再也没有了凄苦的夜。”逝者有自然之景的陪伴,一切都变成了仙乐,这是何等美妙的存在方式。“没有一丝儿感伤(死亡是一场小病,/与读诗的时刻相像)/但有泪要流落到大地上”(《迟疑》),死亡虽要落泪,但没有感伤,生病时“我还得忍耐,/也还得马上快乐起来。”(《人体之秋》)他的诗里没有死亡的骇怖,对之不逃避不恐惧,勇敢乐观地面对疾病。对于生,朱英诞接受庄子“保生全身”的主张,“如果有人劝说我不要去安命,那可确实是无知之徒了。读枕边书,难得有此一枕之安。”对于死,他在《泠泠七弦(遗嘱试作)》中写道:“最好是科学地对待死亡”,并作注:“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已包含在生命本身之中;死也是生命的重要因素,一切事物都在其自身的存在中间又包含着否定他们自身存在的因素。”死亡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当人们死去,你毋须悲哀,/人是活在人们的心里的;/挽歌是可以唱的,你就唱吧,/既然死是那么美好。”(《拟挽歌辞》)这与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生死观相似。朱诗呈现出向死而生的乐生心态,没有死的悲惨与荒凉,他理性地思考死亡,又感性地赞美死亡。
朱英诞还探究了死亡之后的世界,他说:“你不觉识死亡不过是一场睡眠,/(你饮过一杯千日醉?)/春天总会归来,在草叶上摇摆,/朝阳总归会回来,果实累累,/从我们的心上回来,仿佛/自五岳遨游归来。”(《无知吟》)死亡不是结束,它意味着新的生成,诗人尝试在自然世界的发展进程中探究关于生命和人生的答案。这是一种永不停止、永不放弃、永不绝望的生命哲学。自然物如此顽强,甚至不会受死亡的束缚,它们凭借微弱但倔强的努力,使生命不断延续。“我不过是一只冻僵了的雀鸟,/从树上坠落下来,就这样自由自在地,/任其自然而然地埋掉吧。埋掉吧。/这样,我死了我身边的这一棵/树,将依旧生长,布叶,着花,年复一年”。(《挽歌诗》)朱英诞将死亡看作万物生长进程中的一部分,不是终点,而是中间站。这种蓬勃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自然世界中,也存在于人世,生命超越了死亡的虚无,使人获得生存的意义。就像鲁迅笔下那位不断前行的“过客”,朱英诞山水诗不畏生死的生命观念投射于自然世界:“落叶落在大地上很好看,/仿佛是一座美丽的坟墓”(《秋坟小唱》),在这里行将就木之物却充满着无限美感,因为死亡亦是新生,正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万物生于自然,超越生死,生命连续不断,永向新生。
二、生存境遇的寄兴书写
相比欢愉性经历,创伤性经历更能激发创作冲动,有更高的审美价值,如韩愈所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朱英诞与其所熟习的谢灵运、杜甫、李贺、白居易、韦应物都多病多思,他们都将苦闷寄托于山水书写。疾病、失恃、战争是朱英诞的生存境遇,也是诗人山水诗创作的主要动因。
(一)疾病与生命之思
“疾病提供了一种非常规的观照世界的视角,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激发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灵感,成为人类创作活动的一种潜在诱因。”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谈到疾病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古往今来,许多文学创作者都疾病缠身,山水诗人谢灵运便是其一。因为患病,他处于出世与退隐的矛盾中,时常思考生命的存在,其诗将生命之理、苦闷之情、自然之景合为一体,达到情景理的融合,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唐宋时期众多诗人也遭遇病痛,如朱英诞喜欢范成大即是因为:“石湖诗之所以常置案头者,并不是因为他位高而又能发展了田园诗,也是知道石湖是一个多病的诗人,岂企望同病相怜欤?”病痛加强诗人对生死的感知,赋予诗人触摸世界微尘、体悟自然变化的能力。唐宋山水诗中有“古冢”意象,它是诗人对生死感悟的自然投射。晚唐诗人曹松有《古冢》一诗:“代远已难问,累累次古城。民田侵不尽,客路踏还平。作穴蛇分蛰,依冈鹿绕行。唯应风雨夕,鬼火出林明。”他不仅描述古冢与人类世界的关系,也将其与自然世界联系,去除对死亡的直观感受,烘托荒凉静穆的氛围,将生死之思融于自然世界之中。再如李贺,作为多病早逝的诗人,其诗多用“鬼”“血”“死”“泣”等字,山水诗也如此,如《感讽五首·其三》有:“月午树立影,一山惟白晓。漆炬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月夜失去朦胧优美的意境,变得鬼气森森,他将疾病之感投入自然欣赏之中,使读者能从景色中感到死的凄凉与恐惧。朱英诞为李贺写挽歌:“你撷取了生命的精华/(并不是春天的姿媚)/其余的便都抛弃了/我把那些叫做浪费……你的宁静高出了肉体/那蓝天,正当秋深的夜/拥抱着四海和桑田/而永恒的蓝天高于一切”(《蓝天——李贺赞》)。疾病让李贺拥有超越“肉体”的“宁静”,仿佛在“永恒的蓝天”中拥抱“四海和桑田”。
与这些“同病相怜”的唐宋诗人一样,朱英诞一生疾病缠身,多灾多难。六七岁患淋巴腺肿大,十岁开刀却未痊愈。在南开中学因淋巴腺结核病休学,二十岁病愈。因先天性胆道狭窄,三十五岁患急性肝炎,长年累月服用中草药,四十八岁被诊断为肝管阻塞。六十岁左右,患脉管炎,落下右腿大筋萎缩的病根,走路微跛。此外一直有高血压和慢性支气管病,六十八岁左右日益严重,1983年,七十岁的诗人病逝。朱英诞常在散文中写道:“因病几殆”这四字,但疾病也给予诗人灵感:“我写诗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北京一隅的事,百分之百是病中之事,我尝以为我的诗歌可以譬作药草之华。”其实“病中‘瞬间起灭’的思想,似乎恰好对应于‘诗’经验发生的独特性。”疾病带来浓厚的诗意:“但愿我的小病日日推广,/像肥沃的田土和细水长流,/以致我能够终身落在病中:/那些美好的思想是多么爱人,/使得人们永矢不忘。/在病后,它们永远是新鲜的,/正如每日的花束由小园里折来”(《过露筋祠》),诗人甚至希望疾病能长久留存于身体,以使思想保持新鲜。疾病让诗人回归自身处境,关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以己之感体察外物。因此他并不厌恶疾病,“小病像冬眠,/蜷卧在一颗星的指环里,/轻轻的穿过梦境。”(《小病》)“小病教我以温暖/我不数那过窗的落叶/但一片又一片的落下来/一片是绿色的/黄色,又是一片了/又一片是微红的/我不数,轻轻闭目/什么时候了,三星在户”(《小病(一)》),他观察每一片细小的落叶,透露出敬畏生命的情怀。
朱英诞并未止步于疾病视角中的自然书写,他进一步感知到身处自然中的病躯。疾病加深诗人对自然客体的感悟,被感知的客体也显现出主体的状态,诗人从自然万物中看到身体的形貌,身体同自然一起进入了创作的美学场域。《病中的一念》有:“午后树木多阴,/白昼很长而且坦裸得如神仙的智慧了,/但天的彼岸在哪里呢?/静室里是黄草的天涯,/令人念生活简单之可爱;/几时血肉化作清冷的水流去,/任骨骼作天外的奇峰:/种种过去都无丝毫之实感啊。”这是诗人的病中所思,他躺在房室中,望着多阴树木,思考天的彼岸,将身体器官想象为自然之物,血肉化为流水,骨骼化作奇峰,以身体的姿态感受自然,或以自然的视角观察身体。他多次在诗歌中将身体与自然物相联系,将身体比作水:“肉体将化为一湾碧水,/没有源头/无目的的流吧,/围绕着坟墓的圆周。”(《病中呻吟》)比作雪:“晴天属于卧病的人,/但四肢疲如一片残雪。”(《卧病》)将自然物拟作人:“乍冷的日子里雪花冻红了,/枫叶如温柔的小手摊开”(《秋深》)。唐宋山水诗也有诗人以病躯观自然,如崔道融的《梅花》:“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与此相比,朱英诞山水诗的疾病书写对身体的感知更为真切,重视山水诗中被自然物遮蔽的主体身份。他不仅在诗歌中突出“我”的存在,以病躯观自然,更能将自我融于自然,甚至赋予自然以主体的身体形式,我即自然,自然即我,从中体验个体与自然的生命之思。
(二)失恃与感物之情
母爱是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主题,唐宋诗歌多有对母爱的歌颂,如李白的《豫章行》、李商隐的《送母回乡》、陈去疾的《西上辞母坟》、王安石的《将母》等,对崇尚儒家伦理道德的民族来说,儒学与诗密不可分,怀母诗成为文化传统。除了写人世间的母爱,有些诗人注意到自然世界中的母爱,如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雉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凫雏傍母眠”描述凫雏依偎着母亲的温暖场景。白居易的《鸟》:“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从鸟儿间的母爱出发劝告人莫打枝头鸟,自然世界的母爱使山水诗更有人性。朱英诞有较多怀母诗,他九岁丧母,对母亲的思念与怀母的伤痛延续了一生,《梅花依旧》中写道:“今年届古稀,好声犹在耳边,并无任何种的风吹可以吹去。”母亲的声音历经岁月绵延,依然未曾衰减。“房中放为你爱吃的水果/心头放着歌儿/然而,年轻的母亲/永远年轻的母亲/你为什么永远在徘徊”(《杨柳春风——怀念母亲》),母亲永远停驻于“年轻”时,迫切的呼唤如水滴入大海,杳无音讯。“当风吹着草叶的时候/我想往访您,/母亲。我想抓住您的衣襟,依旧/像儿时”(《怀念母亲》)。丧母的悲痛、怀母的忧伤带给诗人一生的创伤体验,他沉浸于山水自然,试图从中弥补对母亲离去造成的缺憾。
与唐宋山水诗仅表达自然世界的母爱不同,朱英诞将怀母情感与对自然复杂的生命感受融为一体。唐宋时期表达母爱的诗歌主题较为明确——母爱,无论是人世间的母爱还是自然界的母爱,都专注于对“母爱”的抒发,较少旁逸斜出。而朱英诞的怀母诗既表达对母亲的想念,又传达出丰富的山水情感。“明月照在我脸上/母亲啊是我的镜/我看梦/仿佛照着一池春水”(《追念早逝的母亲》),诗句运用多种意象:“明月”“母亲”“镜”“春水”,将怀母之情、自然之味、哲理之思融为一体,呈现出较复杂的诗思。诗人怀念母亲的方式,是将其融于自然万物中。如果说上述还属于怀母诗的范畴,那么以下完全是山水诗,如写母亲摘来的花枝:“那是年轻的母亲摘来插瓶的花枝,/它们的阴影很小而小得有趣;/午后的房中充满了新鲜和温柔,/阳光抚摸着垂遮着的帐幔。”(《午后睡起》)诗人在描绘自然景物时提到母亲,但主体仍是自然世界。他写一次春游:“我喜欢小船,摇篮;沿着驼岗/我喜欢碧绿的河流,母亲至上:/当我上岸的时候钟声弥漫/桃花,杨柳,黄土,波浪!”(《西沽春游》)诗人在河流与母亲之间作比较,得出“母亲至上”的结论,但读者并不会因此忽视、贬低河流,反而会觉得可与“母亲”比较的“河流”更加温柔。在日常可见的自然景物中,他时常提到母亲,每一枝花、每一条河、每一只鸟都可有与母亲联系的方式,这样的书写使怀母诗增添了自然的灵动,山水诗充满温暖的人情。
(三)战争与和平之歌
由于朝代更替、外族入侵,唐宋诗人有大量战争书写,形成边塞诗的壮丽景观。如山水诗人也写边塞诗,边塞诗人也不乏山水诗佳作。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在塞外送别、雪中送客之中描写西域飞雪的壮丽景象,《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描绘边塞狂风乱作、严寒交加的气候。高适《塞上听吹笛》、王之涣《凉州词》都是边塞风景佳作,诗人用粗犷的笔调勾勒山川轮廓,为山水诗增添别样的艺术魅力,它不仅可以“小桥流水”,还可以“大漠孤烟”,“骨骼”坚硬、气势磅礴。至宋,“靖康之变”使大宋王朝一蹶不振,偏安东南。“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土分裂,山河破碎,为山水诗提供了新的题材。正如朱光潜所说,“社会动荡愈剧烈的时期往往也是山水诗愈抬头的时期”。陈与义、刘子翚开创山水诗的新境界,如陈与义的《牡丹》:“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金人的入侵使洛阳路漫漫,牡丹也不再雍容华贵,而是“老态龙钟”。再如刘子翚的《山寺见牡丹》:“倦游曾向洛阳城,几见芳菲照眼新。载酒屡穿卿相圃,傍花时值绮罗人。十年客路惊华发,回首中原隔战尘。今日寻芳意萧索,山房数朵弄残春。”战争过后,原先“芳菲照眼新”,如今“数朵弄残春”。南宋时期山水诗整体格调倾向凄凉哀伤、荒寒孤寂。
朱英诞生于1913年,逝于1983年,这期间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但诗人也因沉浸于一方小屋,书写山水庭院被评论家所诟病,钦鸿曾评价朱英诞:“在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诗人,自外于人民的斗争,闭门研究自己的诗艺,苦心经营山水田园之诗,终究是个缺憾。”但朱英诞诗中并非没有战争书写,与疾病、失恃同样,战争也是诗人的一大创伤体验。他讨厌战争:“我讨厌/战争;大旱的天空平静,/像一枚鸡卵平静地躺在窠里;/汲水的女孩,绿匆匆……”(《杨柳》)他期待和平:“当黎明消失的时候/月亮冷如一掬残雪了/鸡鸣告我以远方/战争有了和平的消息”(《鸡鸣》),思考战争与和平的精义:“离开屋宇/披一肩旷野的风/默诵着战争的精义/沉思着和平的解说”(《重荷》),可见朱英诞书写战争不是拿起大刀长矛嘶吼,他的诗没有马革裹尸与鲜血淋漓,没有激情的怒吼或垂死的哀号,有的是冷如残雪的月亮与旷野吹来的风。较唐代边塞诗人笔下的山水描写,这类诗歌更贴近宋代山水诗的风格趣味,冷静沉思、内敛节制。再如《魔术的箫》:“初月照耀着松动的土壤,/蚓笛发出不很扰人的色彩和音响,/自花间如自远方,呜咽的,/魔术的箫吹遍乌江。//淡黄的夜来香突然绽开,啊顷刻花!/号角又吹向声空,音符零落……/祝福啊,那边尘和战云弥漫,/你的大大的幸运来自其间,啊过客。”这是作者回想几十年的“战况”,从“公战”到“私斗”,不免悲从中来而作的诗歌。诗歌意象从月、土壤、蚓笛、箫,到夜来香,然后才是号角、战云,诗人是这其中的过客,从战火纷飞的年代走来,可谓“大大的幸运”。诗人对纷乱的世事进行冷静思考,从身边自然入手,经过多重意象的步步筛选,抵达吹向天空的号角,这是智性思维的酝酿,是新鲜诗情的畅想。
相比宋代与战争相关的山水诗歌,朱英诞的描绘更有距离感,他不直接讲述身处战争的个体,而是拉开距离,通过第三视角书写战争。他将战争比作鸟儿,而不是描写战争下的鸟儿:“战争,飞渡海的鸟儿,/我们应该学学网开三面;/啊幸福!幸福终于会来,/只怕说‘和平已久’。”(《未来的寂寞》)他拉开时间距离,思考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三十年是一只一叶之小舟,/在烽烟和旗帜之间漂浮,/它航得缓慢啊,/可是只有一会工夫……回想我深居的一生,/查看这美丽的大地——/像是谛听战争的春风,/或是和平的叹息。”(《回想》)“战争的春风”“和平的叹息”,多么讽刺,期待的和平迟迟未到,只能化为声声叹息。于是诗人做出选择:“生在动乱的岁月里,/我的心享受着和平,/这是我需要的,/啊,北京,我的老保姆!”(《和平的城(和象贤)》)经历多年提心吊胆的生活,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成为诗人心灵的庇护,那一定是笔下的诗歌与身边的山水自然。吴晓东认为:“日本侵略者的高压统治和严密的文网制度使得沦陷区诗人们无法直面现实……求生存已经成为几乎每个诗人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使朝不保夕的诗人们空前强烈地体验到生存的个体性。”他指出沦陷区的“现代派”诗作是“与‘大地的气息’相异的温室里‘诗人的吟哦’与‘沉重的独语’”,朱英诞的山水诗一定程度上属于这种“独语”。他写战争,但不痴迷战争,不使战争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或道德的附庸,也并未让战争限制诗人的想象力。他在自然空间与诗歌世界中,安放对战争与人生的领悟。
三、心灵驰骋的广阔世界
“想象”赋予诗歌以活力,孟浩然云:“想像若在眼,周流空复情。”(《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这一“想像”即刘勰所说的“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李贺一生未到过巫山,却发挥奇想,加以楚襄王梦遇神女之事,写出《巫山高》:“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飔然,晓风飞雨生苔钱。”李白以发令者的身份让自然为我所用:“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李商隐一生颠沛,常梦归家与婚恋,诗歌呈现出“我是梦中传彩笔”“十年常梦采华芝”的梦中世界。朱英诞1932年来到北京,之后仅1946年与1948年短期到过外地,他说:“我写诗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北京一隅的事。”朱英诞重视想象,他一生未到过江南,却将其作为故乡;平生较少做梦,却常以梦构造诗篇;常住于北京小巷,其诗却有海天之景。现实不能束缚诗思,正如他常引用的诗句:“谁能够筑墙垣,围得住杜鹃?”
(一)想象的江南故乡
江南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地,“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白居易《忆江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牧《江南春》)……江南在古诗中随处可见。江南早已非单纯的地理位置,它凭借富庶安逸的经济环境与温润感性的诗性精神,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情感皈依,成为令人遐想的“文学的江南”。江南湿润的雨季、精致的亭台、富庶的丝织带来的自由与美的精神,给予无数文人充满激情的向往,“江南”逐渐成了一种文化心理与品格。受古诗词熏陶的朱英诞接受了这种江南风味,他笔下的江南有红得天衣无缝的花:“江南的花/红得如天衣无缝”(《花坛》);如音乐般浮过马耳的风:“小溪流水呜咽,/江南的风春天吹来,/我是忧郁的:城市里的/音乐浮过马耳”(《雨》);如中古之飘带的虹:“雨后的虹以外淡淡的风与霞的夏晚/若中古之飘带忆恋着江南的绿水边/晚天不带情意又现出病青的颜色来/在一个黄昏里另一番雨声的暂停前”(《虹以外》)。这些如诗如画的山水美景,是江南情结在现代诗歌中的畅快表达,映现的是一种现代文人精神品格的倔强生存之态。
朱英诞笔下的山水江南仿佛披上了一份幻美的滤镜,诗歌极少梅雨的烦闷与离别的惆怅,看不到“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州人未归”(寇准《江南春》)的伤感。即使写江南的霉也毫无烦闷情绪:“北国里怀念着江南,/我感到霉味的窒息,/树叶和寒鸦翩飞,/月亮是一块鹅卵石。”(《断续的风》)诗中虽出现“窒息”二字,但读至“月亮是一块鹅卵石”,仍然令人颇感清新。朱英诞的江南书写其实都是想象书写,他祖居江西婺源、湖北武昌,家谱在江苏如皋刻印成书,寄籍北京宛平。他1913年生于天津,家在河北首善里,在此居住19年,后迁至北京。天津才是朱英诞有迹可循的故乡,但相较天津,他对江南之地的怀念更加迫切,文学的江南与家族的历史深深吸引着他的目光,但江南始终仅处于想象之中,“我的乡愁是混茫的,广漠的乡愁。烟波浩渺,如在目前,然而又非常辽远。”通往江南的现实之路不可至,那么就于诗中去往江南,“灯光有一些烟草味了/寒冷依旧拂动过客的衣裳/也拂动了虫鸟的翅膀/游子,江南是我的故乡”(《春夜》),甚至梦境都披上了江南之衣:“我睡,我醒,/六十天的春深的日子呵,/饱看了草飞草长日出日落。/哎,怎能不多梦呢,/我的故乡在江南?”(《多梦的春天》)
诗人此时处于革命退潮的20世纪30年代,个人的力量在时代洪流面前微乎其微,他唱不出郭沫若式的激昂旋律,寻不到定位自我的稳定位置,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不定。作为地域漂泊的异乡人,精神漂泊的寻游者,哪里才是他可安定的居所?此时以游子的身份眺望江南成为依稀可以触摸的方式,他暂避于梦想的“桃花源”中寻得一夕安枕,现实的隔膜被心灵的巡游所打破。江南,这个未曾到过的乌有之乡,成为一个漂泊者的心理定位,一个寻游者的精神抚慰。他创造一方诗意空间,安放江南的小桥流水与草长莺飞,故乡与异地得到调和,想象寻到安身的居所。于朱英诞而言,江南是一个地理的、文学的、故乡的多位合体。他乘着想象之风,在江南故乡遨游,“落花在他自己的影子里安眠/故乡不可见,/却在蓝天丽日之下/推敲着星月的门”(《怀江南江北故乡》)。
(二)白日梦的清吟空间
“梦”在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中占一席之地,科学地说梦只是大脑在睡眠时的活动。但在科学还未探索梦境的年代,梦是人类探索自我与世界的途径。中国文学中的梦境如楚襄王梦神女、庄周梦蝶、玉茗堂四梦等,诗人在梦中思乡怀人、观景怀古,完成现实中难以触及的愿望,以梦作诗毫无拘束,恣意纵横。李白梦观美景:“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元稹梦中思人:“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酬乐天频梦微之》)刘禹锡以梦归乡:“逆旅乡梦频,春风客心碎。”(《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陆游于梦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诗人以梦为马,在真与幻的情境中、在现实与文学的交界处,纵情驰骋。
朱英诞也以梦归乡、以梦思母、以梦观景。他写过从未到过的江南之梦:“你羡慕谁的行止呢/游子:你总是说/江南是春天的梦”(《游子界说》);永难忘记的怀母之梦:“青天老是蜷卧着,/我也轻轻入梦/夜的深处是母亲/梦乃若轻舟触岸而醒”(《追念早逝的母亲》);深处其中的自然之梦:“夜来我梦见与虎为伴,/我们在深山大泽里闲散着,/它哺乳着野花,我照着潭水,/那颓倒的镜做着什么梦呢?”(《秋天的梦》)。朱英诞还对梦精细描绘,如梦的颜色:“蜜金的梦寐是家家的/每一座美丽的小窗前/飘拂过香味胜似芳草”(《夜景》);梦的行为:“我梦想着/梦环绕我如一团野火”(《静夜》),“七月的夜与清晨联袂,/梦则留恋着人寰”;将梦比作自然物,“深夏的梦是海上的风,/让星天做我们的罗盘,/热情做帆”(《七月》)。更特别的是除了写自身之梦,他还写自然之梦,如海的梦:“梦里的花开了/乃去对着静水照着/海的梦乃在池水中/烟静静地升上天空”(《海的梦(二)》);瓦雀的梦:“阳光将托足在瓦雀的梦里,/我走到篱下看寒冷的花盛开”(《玉泉山塔影》);鱼的梦:“风的花朵落在水上,/鱼的梦寐沉入天空”(《涟漪》)。诗人不只记录梦境,不仅描写梦的状态,也能感知自然物的梦境,这拓宽了梦的边界,也扩宽了山水自然的边界,奔向更大的白日梦的空间。
朱英诞向来少梦:“我是少梦的人”,“其一,过家门而不入,门内棕榈二株,藤萝花自上垂垂而下。门如一幅画。其一,我站里山谷中望月。此外就只是些乱梦也随时忘掉了。”作为少梦的诗人,却以梦构筑诗篇,可以说是“痴人说梦”了。他“喜欢在夏日昼长时耽于寂寞地写着,似乎得以同时享有‘清吟杂梦寐’的景光。我没有午梦的需求,却常时在人们遗弃的白日里,独自一人跑到园林中做我的白日梦。”朱英诞曾将作诗喻为游戏,在动乱年代,他只能以游戏与梦境来逃离生活的枷锁。梦境中有一个坚不可摧的、玄秘深奥的、纷繁阔大的世界,它几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在,使诗人在令人窒息的生活中划出了狭窄而永恒的缝隙。朱英诞诗歌的“梦”就是这样的缝隙,它那么小,只属于诗人一人,但又那么大,属于时代中的另类书写。同时这种梦的书写也是对心理缺失的文学补偿,他常引用秦观的“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梦中作》)。生活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早年丧母,远离江南故乡,诗人只能通过梦境奔向自由,“醉卧古藤阴下”成为他最合适的选择。然而作为一个爱自然的诗人,他的梦充满山水情调,甚至“梦”就是自然,看似沉醉于梦中,实则是游乎四海之外。
(三)海天之景伴哲思
海在空间与时间中无限绵延,它或平静安宁或波澜壮阔,承载着诗人凝望的沉思与征服的激情。天与海交相呼应,共同鸣奏出自然之曲。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展现海天相映、动静皆具的海景;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用高远的天与壮阔的海表现人对自然界征服的决心;苏轼被派杭州期间作“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望海楼晚景》),碧色的海与紫色的电光相交,气势迅猛,用色出彩。李商隐擅写海天之景,他写的神话,涉及瑶池、银河、天宫等,打造诗歌的“海天境界”,如“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碧城三首·其一》)仙子用仙鹤传送书信,而人类只能“当窗见”“隔座看”。这些在唐宋山水诗中非常难得。中国文明是“黄色文明”,我们熟悉土地与河流,但对海洋经验则比较匮乏。朱英诞觉察到:“玉溪生诗中有一种海天境界,似乎比他的无题、咏史之类更值得注意。”读李诗如于海里泛舟:“当我幻想那一座长桥/一朝随水漂去如虹之消失/像你的孤舟,那时候//到大海里的一夜/并不为以捕鱼为业/只想看看那灯塔在哪里”(《万物之灵——李商隐赞》)。与李商隐一样,朱英诞的诗中也有一种海天境界。
朱英诞少时居于天津,秦皇岛的海:“正如一个冬眠的人,/那藏青的和少许灰白的船儿,/像一些仙景,却被你弃置着。”(《归来》)“美丽是又清晰又朦胧,/一只天鹅在天边飞过,/我要航过天的好望角,/它比海更幽深,更辽阔!”(《海天私语》)天空的倒影在海面上,海与天相互对映。“但也有一个大缺憾,那就是乘月观海了。年少时不准夜出,于是我所写的海,连上下四旁都不是,了无神秘。”他充分调动想象力,将海天期待蔓延在诗歌中。海与天无边无际,思绪信马由缰,纵情驰骋,他常能通过身边景物联想到海天之景,通过天上落下的雨:“雨落在我家落花的窗前/也落在海上吗/海鸥是奇妙的船/南国马儿不践踏芳草”(《风雨如晦》);通过高悬于天空的月:“月光清白而温柔/赤足走过夜之阴凉/影子消失在海里了/小树赤裸而辉煌”(《月色》);通过空中吹来的风:“寒冷的风由远而近,/梦携来泥土的香味;/有风自南,来自海上,/风啊,吹来了,徐徐地消逝。”(《枕上》)这些日常的自然景物仿佛一座桥梁,成为想象沟通海天的媒介。但是朱英诞未曾亲自乘船出海,未曾亲身感受浪涛的击打,他的海天之诗缺少“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王安石《狼山观海》)的力量与动感。相反,诗人在想象之中建造了一片高远无边的天与平静开阔的海,海里蕴藏的是无法命名的智慧与哲思。
朱英诞赋予海多种象征。“我仿佛是那码头,只管卸货,/背后是一片神秘的海,/每一棵树有着美丽的负载;/今天有上帝从我心经过”(《侵晨》),“我”是码头,“海”是“我”于日常劳作之外的内心世界,是所思所想,是智慧的浩大空间。再如“我浸在午梦如海里,/海,是甚么的阴影呢?”(《小伏满月作》)午梦如海,这一比喻突出海的朦胧混茫之境,是一片未知与神秘的领域。再如“如果是那天风海雨的寂静,/那么航吧,航吧,小小的夜航船,/以船的时间作罗盘。要不要月亮作帆?”此诗名为“深闺”,深闺为何有夜航船?它以时间作罗盘,以月亮作帆,将要航去何方?船是媒介,它沟通深闺与外界,载着诗人航向一片无边无际的自由之境。朱英诞笔下的海既有现实的海天描绘,也有通过日常自然物的媒介对海天之景的想象,这些在唐宋诗人笔下并不缺少。但朱英诞的海意象不是佛家所说的人间难以脱离的苦海,如苏轼的“沧海寄余生”,蕴含着佛家关于人世的智慧,但他与古为新,运用象征,赋予海天之景以丰富的哲思。关于海的书写是讲“每个人的孤独个体,深渊的体验,对自由的向往,对未知和神秘的探索。”朱诗即是如此。海与天是如此广阔与深厚,仿佛藏着世间所有的神秘,给诗人充分的想象空间,使诗人以此为依托来思考世界与人生。朱英诞将生命体验融于海,海是人类的智慧空间,它深邃博大,又变化万千,它表面平静,又暗藏凶险,充满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呈现出混茫又自由的境界,囊括一切可说与不可说。诗人选择海意象来容纳哲思,既是对唐宋自然意象的精心发现,又是对佛家智慧的有效创造,同时也是个人创作的独特经验。
每位诗人都难以逃避传统的影响,“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就是他前辈诗人最足以使他们永垂不朽的地方。”诗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经验,又以个人的诗才重塑传统,王维的禅意、李白的浪漫恣意、杜甫的民族忧虑、杨万里的幽默欢笑……这些都构成了山水诗的多种形态。朱英诞山水诗与唐宋山水诗在精神境界上相通相应,诗歌体现出回归自然之态与乐观向上的生命意识,江南情结与海天向往是诗人共同的心灵追求。朱英诞面向传统,但不为传统所拘,他将个人遭际、时代精神与新诗特质汇于诗歌,呈现出境遇与自然交融、主体与客体交织、想象与梦境驰骋的智性山水。他的现代山水诗构成了现代诗歌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注释
①谢冕:《暮年诗赋动江关——纪念诗人朱英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④眉睫:《发掘诗人朱英诞》,见朱英诞著,朱纹、武冀平选编:《朱英诞诗文选:弥斋散文、无春斋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311页。
⑤陈子善:《序》,见朱英诞著,朱纹、武冀平选编:《朱英诞诗文选:弥斋散文、无春斋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⑥陈子善:《一座诗的丰碑——为〈朱英诞集〉问世而作》,《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⑦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⑩章尚正:《中国山水文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