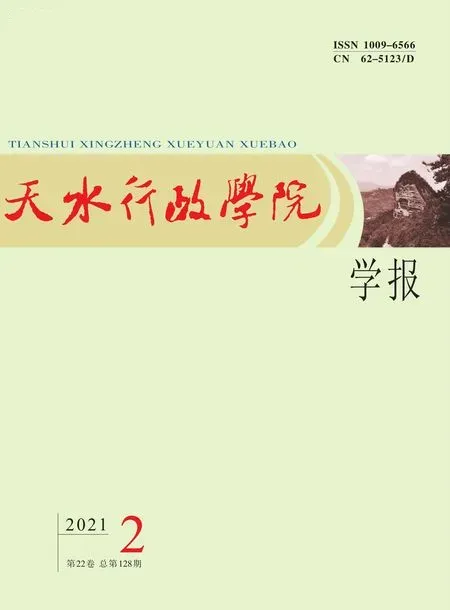新时代弱势群体劳动幸福何以实现
——基于马克思劳动幸福思想的思考
2021-01-06滕文艳
滕文艳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00)
弱势状态绝非一成不变,它随自身、社会等综合因素变化,而以动态性呈现,每位社会成员均可因难以预估,之不确定性而成为弱势群体一员,因而关注弱势群体劳动幸福,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更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未来幸福增加了确定性。将马克思劳动幸福理论,链接于新时代历史背景下,探寻弱势群体劳动幸福的可能性与现实路径,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大有裨益。
一、弱势群体面临的幸福困境
无论中外古今,文明社会总伴随着“强弱并存的分化状态”[2],比较意义而言,有强便有弱,“弱势群体”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身份符号。本文采用社会学范畴中的“弱势群体”(disadvantaged group;vulnerable group) 界定,即先赋性因素与社会性因素的差异所致,较其他社会成员而言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以脆弱、贫困、高风险、边缘化等弱势形态为特征,面临着一定生存困境与发展危机的人群。人作为全面、立体的丰富存在,追求、创造、享配人之为人的真实幸福,属人的幸福离不开合乎人性的物质生存与生活条件,离不开精神世界的充盈丰裕,是人自由自觉本性的充分实现与展开。当前“弱势群体”面临着双重幸福困境:
(一) 能力低于正常状态,所致物质匮乏
为维持和延续生命存在,人首先作为自然生命体,必需满足于吃饱饭、穿暖衣、有屋住,一定的物质状况作为人存在于社会的基础,是享有和追求幸福最基本的保障。具备一定水平的能力,才有创造幸福的机会和获致幸福的可能,然而先天生理、体能上的缺陷或后天地域阻隔等因素,使得“弱势群体”劳动技能与体力相对逊色(或丧失),他们发掘、获取、利用社会资源,以及改造、转化、发展社会生产等实际技术能力,与潜存可行能力短板尤为凸显,风险抵御与应对、社会参与与竞争、创新发展与提升等方面能力更为不足。能力所致机会匮乏,不断压缩着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极为有限的劳动适应性,使他们困于单一的生存手段,境遇变动不居,囿于层次普遍较低、范围极度有限的劳动岗位,获得相对低水平、且缺乏稳定性的收入,且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他们生活拮据,部分弱势群体甚至朝不保夕,愈发陷入脆弱、无助、忧虑、无安全感的生存困境,更无所谓在劳动中获得尊严,实现幸福了。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上的安乐与幸福感是……更可靠的东西!”[3]“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连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4],剥离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便丧失了稳定生活的必要舒适与安全感,幸福更成为了一纸空谈。
(二) 消极的身份认知,所致精神贫瘠
实现幸福必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前提,精神层面更不容轻视,脱离充盈、富有且强大的精神世界的支撑,幸福便难以持存。作为弱势一方,弱势群体“已经把自己看成是该群体的一员,并将此群体的特征纳入其自身的身份感。”[5]他们往往以残缺、可怜、无能等身份标签定义自身,给自己扣上“无用之人”的帽子,这种消极、负面的自我身份认知与评判,左右着弱势群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审思,开始产生怀疑、抵触自身,极易陷入自卑、自闭、自哀的否定之境。
“弱势”一词更犹如一把枷锁,桎梏着弱势群体的精神世界,精神贫瘠仿佛无形,却是一种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当一个人的精神生命熄灭、耗尽的时候,他将完全无视人之为人的能动性,在悲观、焦虑、迷茫中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自甘堕落,逐渐丧失参与自由自觉活动的欲望,甚至连他们自身尚存的部分可行能力,都无以得到充分发挥,更无所谓发展,丧失内生动力的人,剥离了靠自身努力改变生存境遇,向强势逆转的一切可能性,最终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虚耗生命,沦为精神贫瘠的躯壳存在。弱势群体愈发麻木不仁、反应迟钝、冷漠无心,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网也因这种自弃与沉沦,日益冷淡进而濒临断裂,易怒、敏感、悲观使其不再轻易相信他人,甚至是亲人,精神情感难以在脉脉亲情中找到慰藉,家庭不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难以融入社会,使其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也荡然无存,陷入更为糟糕的困境。
二、弱势群体劳动幸福何以可能
幸福的前提在于人以真正的人的方式存在,劳动作为人的自为、自在存在,决定着人的真实存在状态,因而是人之幸福最深刻的发源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是一切平等、自由与价值的根源,部分能力不足(未完全丧失) 的弱势群体,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具备投身劳动、实现幸福的可能。正是劳动自足其诉求、自立其能力、自强其精神、自尊其价值,满足弱势群体物质之需与精神之维,实现其能力与情感的整体发展,建构起与生命价值相称的社会身份,在劳动中,弱势群体唤回自我、肯定自身、找回自爱、挖掘价值,获致真实且深层次的劳动幸福,劳动构成了弱势群体实现幸福的重要前提。
(一) 劳以自足”:劳动满足生存
幸福不是既定存在,而是现实的创造,它绝不会从天而降,不劳而获不是幸福,更是对人之为人的否定,反而钳制着人的幸福。“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首要基本条件。”[6]马克思赋予劳动以生活第一性原则,有劳动活动的产生,才有生活形态的形成,进而才可能有结果形态的幸福。“饥饿是自然的需要……为使自身得以满足、解除饥饿,人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以及自身之外的对象。”[7]在马克思看来,人首先是作为自然肉体存在的,几千年来至今,所有人“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劳动。”[8]弱势群体如若自我否定于“弱势”的标签,而逃避能够维持其生存的劳动,便是对自身存在前提的剥离,唯有先“动起来”,“在对自身生活有用之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9]通过劳动,参与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创造出劳动产品,才能满足其自身的生理结构与机能,基本生存虽然不是人之全部,但却是生命本原性追求与原初动力,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弱势群体实现幸福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弱势群体作为特殊的异质性存在,或有身体残缺、或有能力不足,但只要仍有部分可行性能力尚存,就有从事劳动的可能,便有实现幸福的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言,“有人用手工作,有人用脑工作,有的人从事工程师、工艺师等,有的人则当监工……或做简单的辅助工。”[10]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因个体特征而差异巨大,因而劳动关乎各尽其能,弱势群体考量自身尚存的有效能力系统,在符合自己特有属性、志趣专长的劳动领域、范围中,以合适的量、强度与复杂度,从事简单、高级或是混合型劳动活动,充分发挥体力亦或是脑力,合理调配不完整的各部分能力,进行有机组合,进而在适合于自身且能胜任的事业中,独立地进行创造,满足自身生存,成就自己的生活,便彻底摘下了自己头上的“弱势”帽子。比如全身90%重度烧伤的90后小伙匡志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参与电商网络营销,开起十字绣网店,带动20余名残疾人就业,2019年营业额达一千多万。
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中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位社会成员只要付出劳动,就会有合理合法的回报,就能满足基本物质生存,改善精神生活状况。弱势群体认同自身,进而不在乎自身与他人之殊异,大家都是通过实在、诚实的劳动,去满足自身所必需自然生命的物质生存,以及理智生命的精神存活。所有能够愉悦生活、实现幸福的事物,皆为自身劳动付出与创造的结果,弱势群体通过付出辛勤劳动,来满足自身生存,所获得的这种安全感、确定感以及无忧虑感,是其自己赋予自身的,因而更为稳固、持久、扎实。同时,弱势群体的幸福体验与需求的强度,较强势群体相比存在弱的可能,很少或者是极小需求的满足,可能带来较高的幸福成就与体验,这种在劳动过程中,以需求满足的结果形态呈现出的幸福,从根本上否定了“懒汉”式的免费午餐,弱势群体最大限度地自食其力、努力奋斗,不断增强着自身对抗生活苦难的勇气,激发积极投身劳动的动力,使现实幸福成为可能。
(二) “劳以成人”:劳动获致发展
劳动不仅能够满足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其中蕴藏的发展性意蕴则更为深远,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11]劳动创造人、发展人,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人的幸福与人本身一样,不会凝固不变、一劳永逸,它们永远是未完成的形态,正是劳动为其生成、发展与提升提供了现实场域,新时代的中国,“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12]当弱势群体不再在源头上赋予自身“无用”的可鄙标签,自觉走上劳动岗位的时候,他就已将自身置于“发展”的康庄大道上,便不再会消极迷茫、止步不前、自我沉沦,他的特有禀赋、个性特征、志趣专长在劳动中释放、完善、发展,如此弱势群体便赋予了自身以无限的可能性。劳动是弱势群体之能力与情感的自由表现与现实运用,在新时代的自主劳动中弱势群体的能力与情感又得以进一步发展。
首先,弱势群体能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全面发展自己一切能力,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使命与任务。”[13]对于弱势群体来讲,他们身处有限现实,而充分发展自身能力,正是打破束缚在其身上的各种“弱势”枷锁,而追求无限可能,是对人之为人的超越性特殊生命存在的彰显。弱势群体在劳动中获致能力的发展,劳动是一种双向对象化活动,弱势群体按照“人的尺度”将自身目的与意图,锲入对象物中,使其成为满足人之要求、需要的,主体意志对象化的现实产物,由此体验创造性生命的幸福。然而由于弱势群体的能力,在严格意义上存在缺损、有限与不完整,因而在主客体的对象化过程中,或将屈服于对象物的坚硬抵抗与干预,但正是在这种“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对抗、冲击又磨合中,弱势群体反观自身,吸取教训,以长处补短处,考量、进而把握、利用新时代、新常态、新业态下的一切有利资源,使自身的优势技能得以发挥、发展,由此,他们的已有劳动能力不仅不会萎缩,还将在整合、补缺、增优中得以全面有效地提升与发展,进而更加适应于丰富、多变又多样的现实需要,劳动能力发展过程中,体力与智力的结合,实能力与潜能力的应用与激发,由此而来的是求真求善、艺术审美等各方面能力的生成、提升与发展,不满于现存,不止于现有,弱势群体将全面发展的能力进一步运用于劳动之中,拓展、充盈、丰富自身的同时,又予以幸福以全面性和无限空间。
其次,弱势群体情感的发展。人之丰富且充盈的情感,构成了幸福不可或缺的精神之维,马克思认为,完整的人是“具有丰富、全面且深刻感觉的人。”[14]情感方面的缺失,使人即便正处于幸福之中,也根本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更不用说体验、享受进一步创造幸福了,外在的行动方面受情感方面的钳制,进而人的整体发展也将受到阻碍。弱势群体能量小、势力弱,常常表现出自卑、苦闷、麻木甚至是绝望的单向度的消极情感,当弱势群体丧失自信、懈怠消沉、陷入完全的自我否定,他便剥离了自身的精神生命,沦为行尸走肉般的人形空壳,这是极为可怖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自主劳动中,人的“精神本质”[15]才得以完全彰显,弱势群体被自身、外界等一切因素冻结与压抑着的情感渴求与生活欲望,唯有在劳动中才能得以释放,劳动生成着人之积极的情感,复归弱势群体以完整的人之存在。在劳动过程中,弱势群体不断增进着,对广阔天地的认识,并“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6]整个人的世界,在改造劳动对象的过程中,也正形塑着自身主观世界,他们的情感表现维度将愈发全面,既有成为自身命运主宰者的愉悦、高兴与满足,又有发现、创造、欣赏美的欣喜、兴奋与快乐,弱势群体在劳动中生成着多彩丰富的情感体验,积累着各式各样生存智慧,并在重复检验中完善发展,不断剔除禁锢、束缚他们的悲观厌世、扭曲煎熬、麻木不仁、涣散堕落等消极情感,真正成为具有全面且深刻感觉的积极存在。情感左右着弱势群体的认识向度、实践动机与行动取向,“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17]劳动中弱势群体获致的积极情感,使他们更理性、更乐观、更自信,他们有愿景、有期待、有追求、有活力,更能合理审视不利境遇,甚至连遭遇不幸时的哀伤、悲痛与难过等,都不再具有消极意义,它们成为了扭转现实的“助推器”,激发弱势群体进一步投身科学、合理的各项活动,提升现有生活质量,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 “劳以达人”:劳动实现价值
桎梏于“残废之人”“无用之人”之枷锁,感受不到自身价值所在,是弱势群体幸福失落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本质地构成了人之价值的基础与根源。”[18]价值奠基于劳动、创造于劳动、实现于劳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19]
可见,新时代的自主劳动,供予人们直观、确证、实现自身,获致自由生命价值与辉煌的机会,当弱势群体投身积极的自主劳动,便开始剔除自身“无用之人”的便签,重新认识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于劳动中,肯定了自身的个人生命。”[20]在为其所特有的劳动领域中,弱势群体独立的进行创造,找回自身作为价值主体存在的成就感与自尊感,同时,自主劳动中弱势群体与社会建立广泛联系,对自身的社会身份进行重构,通过劳动创造,满足他人需要,在为他服务中重拾信心、重建自信、重识生命意义,不断实现自身社会价值,最终在“人与人关系”层次获致社会性的高层次幸福。
首先,自主劳动中,弱势群体之自我价值得以重拾。马克思认为,“劳动无论就其内容,亦或是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均是人的价值显现过程。”[21]作为“个人之自我实现”[22],自主劳动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讲,均具有自我生命价值再生产的意义,是清晰的自我价值卷入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正面临着,自我生命意义失落的弱势群体而言,自主劳动更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载体,弱势群体在理性、务实地了解自身的基础上,投身适应于其特有生理特征,能够发挥其优势专长技能、支持其自我价值实现的某些劳动领域,诸如“盲人按摩”等等,在弱势群体主导的劳动领域,自主性,亦即自我决定感融入到劳动过程中,他们便能在某种特殊技能的发挥中,体悟建设性本能的乐趣,以及以特有技能满足他人需要的独有满足感,寻找自信的理由,进而建立自我价值。自主劳动的过程,既是弱势群体自身得以合理解释与接纳的过程,又是弱势群体对自身劳动能力与发展程度的自我评价与肯定的过程,更是打破原有枷锁自我改变、丰富与提升,增加存在高度与生命价值厚度,更为自信与自尊的过程。“幸福在于人之自我价值的肯定与提升。”[23]自主劳动使得弱势群体不再“感到自己是不能完成自己使命的社会成员”[24],体悟到自身价值生命存在,便不再自我否定、自怨自艾,而渴望最大限度地释放自身创造性能力技能,实现广泛的价值肯定、尊重与认可,体验自我实现方面的深层次成就感、尊严感。随着弱势群体对自我价值的不断重拾与提升,其幸福程度也将愈发纵深化发展。
其次,弱势群体之社会价值得以确证。“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在社会中实现自己。”[25]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自己为他者的存在……同时,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26]正是在为他人服务的劳动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人之“为他性”以及“利他性”的价值属性得以释放,才能真正实现人之为人的社会价值,达致真正的幸福。“倘若某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或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卓越诗人、大哲人,而他永不会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27]在马克思看来,当人为自己劳动,能动、现实地实现自身二重化时,获得的是一种短时、表层的满足于愉悦,而当人致力于他人需要进行劳动,用自己所创生的劳动产品满足他人,为其服务时,实为以自身劳动产品为横桥(主体——对象物——其他主体),搭建的彼此依赖与需要的社会性幸福,是一种更深层、持久的幸福。当弱势群体投身自主劳动,施展特有专长,满足他人需要时,便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摆脱了自身与外界的疏离感,重拾社会中的自我存在,进而在为他劳动中,直观他人、反观自我,以能动、积极的劳动与其他社会成员建立互惠联系,赢得尊重与赞誉,由此社会身份得以提升,自身价值得以社会的广泛承认与肯定,弱势群体便不再封闭自我,转变对自身的固有“无用”影响,而愈发自信,进而主动融入社会,投身进一步的劳动之中,不断创生出新的、持续增值的人生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那些致力于大多数幸福的人”实乃“最幸福的人”[28]为他人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放大劳动幸福之程度,当弱势群体的劳动,与千百万人其他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他的劳动就是致力于千百万人的幸福,在实现他人幸福的过程中来收获自己的幸福,如此之社会价值与人生幸福便是最高层级的,它能使弱势群体感受自身生命意义之愈发丰满,进而持续激发投身劳动、为己为他,追求、享受美好幸福生活的动力。
三、弱势群体劳动幸福何以实现
人具有社会属性,永远是社会中的人,个人之生存绝不是动物般弱肉强食、末尾淘汰,消极适用于丛林法则,社会的人作为整体性存在,是彼此相关联之集合体,每个个体均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生存密切相联,整体性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29];改观弱势群体过度边缘化的孤独式存在,实现其劳动幸福,离不开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灵活多样的就业参与,以及劳动光荣的文化风尚,政府兜底、企业分担、弱势群体敬业之“三管齐下”,惟其如此,才能系统提升弱势群体的劳动安全感、成就感与价值感,使其在自身内部动力的激发与外部条件保障的双重作用下,虽弱犹安,进而转弱为强,为自身未来发展与价值实现增加确定性,这正是马克思劳动幸福理论现实关照。
(一) 健全劳动保障,巩固弱势群体劳动安全感
我国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为全体人民实现劳动幸福筑起坚固防线,在弱势群体的劳动保障方面更是责无旁贷,政府要健全劳动保障,使得“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30]
首先,政府要以“倾斜性”保障优先,“有劳动机会才有劳动幸福”[31]多方面综合因素致使弱势群体,技能基础薄弱、抵御风险能力弱、心理承受力脆弱,陷入社会、生活与劳动的弱势,如此如若弱势群体追求、实现进而享有劳动的幸福之质与量,要与其他社会成员无差,必然要施以合理适度原则下的特殊倾斜性保障,政府必要的劳动政策倾斜、保护尤为关键,政府应在普通劳动保障标准与弱势群体特殊属性间进行平衡考量,健全有差别、有弹性的弱势群体的劳动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劳动保障的保险系数、覆盖面与针对性,诸如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合理特殊的休息时间、适度的特殊保险与福利、健全的人格尊严保障,通过斟酌弱势群体现实技能留存,进行恰当的劳动生涯设计与管理,为特定弱势群体创设、买入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或施以行政或是经济手段,鼓励企事业单位雇用一定数量的弱势群体,亦或鼓励弱势群体自主创业,为其就业创业,供以合理程度的信贷、税费减免等优惠举措,同时不断畅通弱势群体的劳动诉求表达机制,关注其劳动中的所忧所惑、所意所愿,完善的劳动保障加之温情的情感关怀,能够使得弱势群体在自由、平等、有温度的诚实劳动中,技能得以施展、价值得以实现、情感得以满足、尊严得以保障,获得稳定的劳动安全感,不断提升幸福感。
其次,政府要以“赋能型”保障为主。弱势群体的劳动保障,绝非成就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养懒汉”,而是因劳称义、劳有所获的“育勤人”,因而要超越人道主义之慈爱、同情、怜悯之爱,助人自助、授之以渔,使每一位弱势群体均有通过自主劳动,施展自身才能,获得劳动幸福、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重建、提升弱势群体的之能力首当其冲,政府应以“赋能型”保障,完善弱势群体脑、体的综合应用技能,帮其达致最大限度地自食其力,必须从弱势群体自身实际出发,针对其自身条件之特殊性,开展全方位、立体化、个性化的弱势群体职业技能、劳动思维等方面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与培训,引导弱势群体正视劳动创造,转变劳动观念,激发其投身自主劳动积极作为的动力。政府应联合技能培训类社会机构,创设弱势群体培训与教育基地,以市场需求、企业岗位要求等社会实际需要为导向,设定弱势群体培训目标,创设特色培训项目,制定针对性培训方案,全程监督培训过程,严格考评培训成果,政府购买培训成果,进而切实保障弱势群体劳动能力与技能得以重建与提升,且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因势利导的“赋能型”保障,使弱势群体以特有可行专长技能走上工作岗位,便真正实现了社会机会层面上的有效保障。
(二) 优化就业参与,增强弱势群体劳动成就感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32]企业作为推动弱势群体就业的主力军,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 (就业与职业) 歧视公约》(第111 号公约) 履行消除就业歧视与障碍之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弱势群体更精准、更温心、更便捷的公平就业参与助力:
首先,企业要开放岗位安排。身心等方面的缺陷,致使弱势群体劳动就业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与损害,但残缺并不意味着完全丧失,部分局限性是足以弥补的,弱势群体能够通过人体功能代偿,即通过发挥可行部位感觉与运动能力,实现健康器官优势互补与潜能激发,诸如肢体障碍弱势群体,可从事脑力劳动充分发挥其智力功用,因而企业应关注弱势群体“能干什么”,而不是“不能干什么”;考虑弱势群体能以“特有方式”干什么,而不是所谓的“正常方式”,进而在权衡本企业工种所需的基础上,考量弱势群体与其他健全社会成员的异质性,复合化、差异化、多样化按需设岗。同时广泛公开就业需求信息,以便于弱势群体及时、系统、全面、准确地掌握岗位信息,按自身实际能力技能,积极对需入岗,一些适当的特有岗位,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有能力的企业,也可进行针对弱势群体的公益性岗位安排。诸如企业的呼叫系统,客服中心可向肢体缺陷的弱势群体开放岗位安排,高科技工作中心可考虑具有精细化、耐重复等特征的艾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以开放岗位安排,鼓励帮扶弱势群体入岗,不仅不会阻碍企业利润获取,反而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中,蕴藏着巨大的社会价值,潜在地提升了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声誉与形象,实现社会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其次,企业要灵活就业形式。企业的灵活性就业形式对于增加、促进弱势群体非人就业数量,以及实现弱势群体“更高质量与更充分就业”[33]大有裨益。部分弱势群体由于身体缺陷存在,不方便按时、定点到达现实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因而企业在联系其经营目标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居家就业、派遣就业、远程就业、网络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不仅能够满足弱势群体之特殊性、多样化、多层次性的实际需求,以平等姿态实现工作稳定,提升弱势群体信任感、安全感与归属感,同时灵活的用工安排,对于节省实体场所以及人工成本,提高企业运作效率,也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诸如技能面窄的弱势群体,以居家就业的形式,进行简单包装等零散性工作,企业以上门回收的方式,收回劳动产品,便节省了车间、厂房等实体生产空间费用,对于高学历、有专长技能的弱势群体,通过远程、网络就业,参与产品研发设计、会计出纳等部门,在减少弱势群体活动量的同时,又能充分发挥其技术专长,由此弱势群体“以较高的工作敬业度与组织承诺感,对公司高度认同。”[34]企业以灵活就业形式,优化弱势群体的劳动参与,能够充分展示出企业凝重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回报社会的经营理念,而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对企业的长远运行与未来发展大有裨益。
(三) 弘扬劳动光荣,提升弱势群体劳动价值感
“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35]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对个人来讲,具有生命再生产意义,在劳动中人之主体力量得以确证,价值得以实现,是最高形态的幸福。因此,只有让弱势群体意识到劳动是幸福之源,劳动真正成为了弱势群体之渴望行为,他们才能尊重、崇尚进而热爱劳动,自觉投入其中,追求幸福,实现价值。而此种意识之形成并非自然而然,离不开一定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弱势群体自身的正确劳动价值观树立。
首先,社会要匡正劳动风气,形成劳动光荣的新时代风尚。一个社会的劳动风气,作为劳动者的风向标与精神港湾,绝不允许任何好逸恶劳、投机取巧、坐享其成、少劳多获等任何不正之风的存在,劳动光荣的新时代风尚之形成,离不开劳动领域长期、共时、广泛的塑造与纠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36]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通过多途径、多渠道、多形式对弱势群体劳动模范之典型事迹进行宣传,通过直观、且富有冲击与感染力的先进劳动案例,诸如,90 后残疾小伙靠十字绣年入千万等卓越事例,为其他弱势群体营造感同身受、亲临其境、刻骨铭心之感。“无论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与鼓励”[37]。劳动价值有殊异,劳动分工无贵贱,再简单的劳动坚持做、反复做,也能成就不简单、做成大事。弱势群体在震撼中产生共鸣,自觉意识到自身也能够通过持久而务实的劳动,满足基本生存,获致发展、实现价值。此间随着弱势群体劳动情感认同的不断增进与内化入心,他们的劳动欲望与期待、图强意志与勇气得以激发,真正实现“伸手要”向“自力得”的转化,由此“被动”变“主动”,“输血”变“造血”,“要我劳动”变“我要劳动”,激励着弱势群体以主人翁的姿态,通过辛勤、诚实、平等劳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瓦添砖,不断提升成就感,收获幸福感。
其次,弱势群体自身要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观,自觉爱岗敬业。劳动观是弱势群体对劳动的根本看法,于一定程度上,它直接决定了弱势群体的就业选择、人生格局与价值判断。“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丽的观念。”[38]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中国人民的希冀,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终是短暂、虚假的,脱离诚实的自主劳动,人便无以“自足”更不用说“成己”进而“达人”了,因此,弱势群体要主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公民层面的“敬业”要求,进行自我教育,坚决摒除消极、错误的拜金、享乐、利己劳动观干扰,确立平等、诚实、奉献的劳动观念,进而建立起对自主劳动的正面认知,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取向,
在如此认知与取向下,弱势群体自觉投身劳动、拥护创造,在辛勤、诚实劳动中焕发主动、积极与创造性,自身综合素质、意志品质得以提升的同时,为他人劳动、服务社会又使得弱势群体赢得外界尊重与赞扬,重建自信与自尊,个人生活有了“自足”的安全感,社会生活有了“达人”的价值感,弱势群体的物质、精神与社会生命得以全面满足,由此筑起了扎实的劳动幸福感。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于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着。”[39]那些已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与崇高劳动信仰的弱势群体,要积极传播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在其他弱势群体心中埋下崇尚劳动的种子,带动他们一起投身劳动,改变自身命运,实现人生价值与梦想,由此在整个弱势群体中凝聚起尊重、热爱、崇尚劳动的积极向上正能量,最终“全体人民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