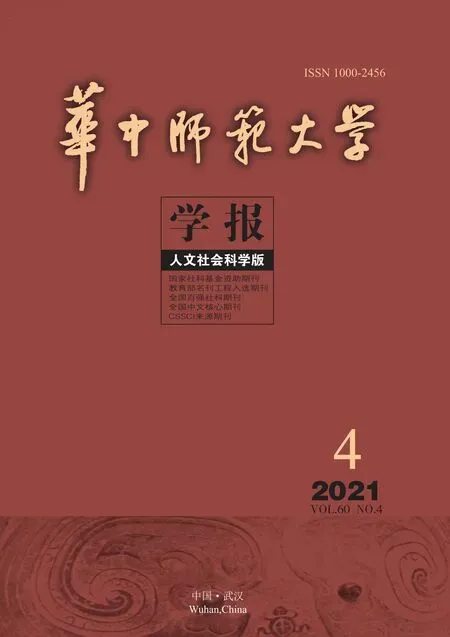人民史观、贯通视野与义理涵养
——张舜徽史学片思
2021-01-06谭徐锋
谭徐锋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9)
张舜徽(1911—1992),幼承庭训,早岁又在长沙、北平从名师硕儒问学,学问博大,重心在于小学与史学,其史学成就与其整个学术研究贯通始终,与时代脉博紧密关联,不可割裂开来,必须综合观之。特拈出三点,试对其史学思想进行分析①。
一、写人民史,为人民写史:从《广文字蒙求》到《中华人民通史》
张舜徽受阶级史观的影响,已有研究者做了梳理②,不过尚待深入。本文要强调的是,张先生好像有一种反王朝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所主张的历史观而行之的人民史观。对于妇女、少数民族、底层百姓的重视,成为他史学研究的主要基调。
张舜徽在1948年12月之前就开始接触阶级史观。他在《广文字蒙求》一书序言中说:“近岁涉览译本新书,对于有关人类起源、阶级分析,略有窥悟。”③这一转变应该是受到国共政局变换的影响,当时双方攻守势易,形势逐渐明朗。
张先生最初开始采用阶级史观的著作也是《广文字蒙求》,第三部分“从古文字中探索远古史实”,开始采信“氏族社会”、“阶级”、“劳动大众创造了人类文明”这些当时的新名词。从远古入手,能为阶级史观找到较好的例证。
1949年后,张舜徽著作中运用阶级史观较为明显的是《中国史论文集》中对于农民起义等问题的描述,系统而深入的著作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④和《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⑤,其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批判火力十足。《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侧重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立论,认为“我国过去旧的历史书籍,浩如烟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来写作的。……淹没了劳动大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更无由认识到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⑥。
《中华人民通史》分为六编,其中师法《史记》《通志》的痕迹较为明显,按照类别撰写,试图以类观通,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介绍清楚,好似《史记》作为当时的通史,《中华人民通史》也试图呈现一个当下的通史。这一通贯的诉求其实是张舜徽早年抱负的晚年实践⑦。他试图为人民写史,认为历史可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对本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以及制度文物、创造发明的成就,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亿万众中的英杰人物,茫然无知,或者早已淡忘了,便自然没有爱国思想,并且不知国之可爱者何在,更谈不上关心国家的兴亡了”⑧,经世致用的关怀相当重,目的在于让人知道国家为什么可爱,进而关心国家命运。
在他看来,此前的很多通史“没有谈到几千年间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以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在历史上,只看到汉族的活动事迹,看不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谈到事物发明时,只强调个别人物的成就,看不到集体创造的伟大”⑨,所以他要为这些被忽视的人发声,《中华人民通史》“社会编”专辟一节“痛苦的妇女”,介绍中国古代妇女所受的痛苦;“人物编”也凸显中国古代妇女的贡献,赞扬文成公主、王昭君、秋瑾、王贞仪、黄道婆的历史影响。
《中华人民通史》扩充了历史叙述的对象,将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都纳入视野,尤其侧重被统治阶级,从内容的广度而言是空前的,也践行了作者的主张。正如评论者所说,“这部书打破了按王朝体系编写通史的传统,它以事物为记载中心,将历史上重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的情况叙述得清楚明白,务求使读者从中得到系统的知识。……结构井然,知识系统,一卷在手,便可获得较为全面的历史知识”⑩。
如果从取得的实际效果而言,则可能会有一些落差。揆诸实际,《中华人民通史》的发行量并不太大,从笔者目前收集的版本来看,是否重印过待考。《中华人民通史》的文字表述方式尽管颇为通俗,但是编排方式却有失琐碎,甚至有些像是名词、人物清单,也没有以人物为中心展开叙述,更多是知识点的叙述,较难收到引人入胜的效果。殊不知一般读者更喜欢顺流直下的时间先后顺序,也更喜欢讲故事与情节化。传播广才能谈得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华人民通史》第一版出版后,大陆久未重版,直到《张舜徽集》出版时收入,似乎并没有达到作者的预期。
从编纂方式而言,近人蔡尚思《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增订本与张先生的书大致类似。而坊间版本近百种、很可能是销量最大的吕思勉《中国通史》采用章节体,上册讲中国文化史,采用典制体;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从民族起源开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因此,就效果而言,以时间为序,以章节体编排,依然是通史性著作(无论通俗与否)的主要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形式。
如果从成书内容而言,《中华人民通史》与张先生此前的著作是有延续与传承的,“创造编”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的相关内容,“学艺编”与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内容有不少部分是重合的。
作者的苦心孤诣值得称道,但是从学术评价的视角观察,通史贵在贯通,而《中华人民通史》或许是为了照顾到普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需要,把“通史”写得很全,却缺乏整体观照,最后写成了“人民历史手册”。为什么缺乏整体观照,可能是由于张舜徽的研究重心在于学术史,对于政治史缺乏专深的研究,而政治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又极重,因此这样的通史撰述难免缺乏深度。
从汉宋兼采的博通路数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宏大叙事,其实有某种相通之处。从贯通的角度讲,张氏未刊稿《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更符合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到其晚年,他似乎放弃了这一叙述方式,而是走向以类观通的路数,反映出他对于时代思潮的反思,与其《中国文献学》的思路是一致的。
张舜徽的史学观很可能有一个不断演变最终回归博通之学的路径。如果悉心观察其早年、中年与晚年的著述,就可以比较清楚。张舜徽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著作,有人专门做了讨论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他80年代的著述,就可以看出其表述方式、编排体例与他40年代的著述更接近,对受时代思潮影响较为明显的相关论述做了扬弃。据其后人讲,《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这本书是我父亲在世时明确表示不准备出版的,说他想表述的观点在《中华人民通史》里已经有叙述了”。其后人所说的确属实,但另一层因缘,可能是《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的意识形态过于激烈,将历史分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历史,侧重批判的一面,第四册题为“受压迫人民的痛苦”,这一非常革命的叙述,可能在作者晚年看来,已经不合时宜,所以表示“不准备出版”。
我们对两书做一对比,发现《中华人民通史》弱化了《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的阶级分析观点,而是着眼于具体史事的呈现,除了时代语境的变迁,更可能是作者的史学观发生变化所致。当然,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张舜徽在《中华人民通史》编述提纲中说:
众所周知,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便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我们在阐明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时,特别是叙述政治制度的沿革、学术思想的盛衰,必须从当时的经济基础去考虑问题。在每类中,都要说明其所以然;而不可孤立地看问题,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加以割裂。这样,才能将历史的真实,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来。
不过越到后面,对此他越有保留。不仅如此,成书于晚年的另一本《中国文献学》,其中的意识形态表述也很少,如果对照此前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等书,就发现有明显的减弱,例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正文开头所引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历史学科的定义被删除了,标题中的“封建社会”等标签也消失了。章太炎自称“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张舜徽史学观念的转变返璞归真,庶几近之。
陈寅恪认为,“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张先生的史学论著,从其去世近三十年来的反响来看,试图有“条理统系”的著作争议较多,而以朴学面目出现的著作反而受到学界的长期推崇,有论者誉之为“祖传秘方”,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二、不畏流俗的学术勇气
学界讨论张舜徽的学术时,对其学术与时代的关联重视不够。其实,张先生对于当时上层的政治、文化主张非常关注,并行之于文。《中国史论文集》开篇就是《从汉字发生、发展、变化的史实,说明今日实行字形简化的必要与可能》,为当时的汉字简化辩护,指出:“中国文字的前途,必然是走拼音的道路。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个中思路,显然是呼应当时北京的文字改革主张。张先生在文中引用了斯大林的相关言论。不过,在赞同斯大林的相关主张的同时,他也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认为由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所引申出来的“语言既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物,不可能突变,文字也自然不可突变”这一说法是“不甚妥贴的”。在当时的语境下,斯大林在中国的声望依然很高,张先生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这一表现无疑是不畏流俗。
对于时人鄙薄的清朝遗老王国维以及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的罗振玉,张先生也不为流俗所扰,着力表彰二人的学术贡献。张先生表彰罗氏的文章可能是1949年至1979年三十年间大陆地区仅有的。他能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对罗氏的学术贡献进行清理,难能可贵。张先生曾利用罗振玉所影印的唐写本《玉篇》,撰成《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可以说是受益于罗氏者,后来还主动为罗振玉文集的出版呼吁,并题写书名。当时大陆地区对于王国维的研究也甚少,如《王国维的思想道路及其死》着重强调王氏“一生所走的政治道路,却是反动的道路”。张舜徽对王氏的表彰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的。当时的阶级斗争观念颇为盛行,为罗振玉、王国维辩护很可能被人所诟病,而张先生依然故我,着力表彰二人的学术贡献,很有道德勇气。
张舜徽平生既不请人给自己的著述写序,也很少给别人的著述写序,主要是为了避免相互标榜之嫌,但有两个人例外,一个是李审言,一个就是罗振玉,张先生曾解释过为什么破例为此二人的著述写序。从二人在当时的名望和处境而言,张先生为其写序,显然无利可图,仅仅是为了表彰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
“文革”中,南方某大学一位正走红的教授来华中师范学院讲学,张舜徽听到中途愤然离席,并说“做人要有良心,做学问也要有良心”。当时,张氏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时常挨批斗,全家蜗居于武昌昙华林澡堂,“澡堂简陋,低矮阴湿,夏天如蒸笼,冬天如冰窖,下雨的时候还四处漏水”,甚至要穿雨靴。要知道,得罪了当时的学术“红人”,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噩运,还不仅仅像表彰罗、王二人那么简单。张先生的愤然离席与愤然发声,会议主持者看在眼里,主讲者也记在心里,无疑只有骨鲠之士才会如此行事。
一赞一弹,看似迥然有别,实则一本学术良知,可谓大义凛然。这本身有着孟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既有学者的学术良心,也有着身为湖南人的耿介性格,还可能有着一直以来的义理涵养的启发,所以才能一触即发。
三、以义理涵养身心:张舜徽的选本及其赠言
纵观中国学术史,有种现象颇为普遍:不少学人在晚年精力衰微之后,会重理旧业,或做摘抄,或编选本,或不再著述而从事讲座。这里面涉及的往往是他们一生衷心系怀的研究领域或关注焦点,无意间透露其心曲。钱穆先生就是如此。钱穆晚年常谈心性等宏大问题,编了《理学六家诗钞》等书,早年热衷理学的学术旨趣又在晚年回归。
张舜徽先生晚年编纂《文献学论著辑要》《经传诸子语选》《清儒论学语录》《清儒论学文选》等书亦属此类。在志在传世的《中华人民通史》之外,不少选本其实有着另一种关怀,诉求依然是精英史观,力求揭示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这里面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经世致用,更有经史润身的诉求。
孟子曾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如何养气,是古代士大夫心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人生出处的大关节。张舜徽对于先贤的嘉言懿行颇为重视:“我们总结前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时,除条理史实外,也还有观摩借鉴的一面。对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进德修业之方,都要认真体认,引归身受。他们好的言论行动,可资学习;缺点错误,可为厉戒。古人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便是这个意思。”对于清儒的治学之道,他提倡“博观约取,择其有裨实用的东西,加以消化,灌注到读书实践中去,受益是很多的”。
张舜徽曾引曾国藩论文语“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无疑是力求将先贤的光明俊伟之言化为一种气象,以便灌沃自身与学者的心田。这里面既有文章之道,更是学问之阶。
张先生的这一努力,体现在其有关学术论著及其历史文选、先贤名言的编纂中,在其日常生活中也见之于行事。张先生将自己所欣赏的先贤格言赠予其子张君和,对他进行鼓励。据张君和回忆:
父亲最希望我们有健全的精神和正直的品德。他曾就“积事久,取经多,则魂魄强”这段话解释说,一个人要有健全的精神,不仅靠自己的积累总结,还要善于学习他人的经验。因此,他常常以前人的嘉言懿行来启发我。我在外地工作时,与父亲通过许多信,他在信中先后给我写过三段话,我始终铭记在心,受益是很大的。
其一是:“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功;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这是《荀子·劝学》里的一段话,是启发我在工作和学习中要克己制胜,埋头苦干。
其二是:“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这是《荀子·非十二子》里的一段话,是督促我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断增长自己的才干和智慧。
其三是泽雅堂主人的话:“风霜之所加,蒲柳先零,而松柏愈茂,岂谓天之有忌于蒲柳也。持我之志与气与屈抑挫折之天相支柱,而徐俟机运之转。机运之遂转,不有得于前必有得于后也;机运之未转,不有得于此犹有得于彼也。……志与气足以御困,则虽朝夕不能自活,此心泰然,所谓困而不失其所也。”这是鼓励我如果遇到困难挫折,内心要坚强,有利的时机与主动的恢复,将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泽雅堂主人施补华本身就是一个遭受过很多挫折的人,最后崭露头角又天不假年,因病去世。张舜徽此处特意以他为例,试图强调人生再困苦,也要“此心泰然”。
除了鼓励其子,张舜徽“本人也是常常藉前贤的言行以自励,他刚强的性格、坚韧的毅力和开阔的胸襟或许与此有关”。张先生七十三岁开始撰写《中华人民通史》,担心年老无法完成,就用唐甄的“我发虽变,我心不变;我齿虽堕,我心不堕。岂惟不变不堕,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人谓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到了暮年,他还常常温绎朱熹所编《小学》中的篇章,并把早年手抄的诸子语录重新工整地誊正合装订成册”。
张舜徽在论及清儒刘台拱的行迹时曾说:“其一生以宋贤之义理涵养身心,而以汉儒之训诂理董经籍,各取所长,不为门户。”这里也可以说是夫子自道。如果将此处的“宋”易为“古”,则可以说是张舜徽早年的学问轨辙,而以义理涵养身心则是其一以贯之并且广为倡导的。
以前贤的嘉言懿行激励自己和后人,是张舜徽深造自得的经验,也是他多年修身的秘诀。这里面其实有理学修身的传统,尽管他在著述中对于儒学沦为官学颇多批评,然而前贤的不少妙语却融入其骨髓。《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专辟一章节录朱熹治学语录,在小引中张先生称其父“博览群书,而案头常置《朱子文集》及《语类》,时时检寻之。尝诲舜徽曰:‘朱子之学,至为博大,非徒义理精深而已’”,后其师也推崇朱子。张舜徽后来于上海购得康熙刻本《朱子语类》及六安涂氏刊本《朱子文集》,“益喜摩挲”,并“撮钞其精粹语,依次存之”。这里面无疑有其父亲的影响,甚至就是所谓讲理学。而这种以先贤义理润身励学的传统,又经由张舜徽传导至其子张君和。
张先生有一幅完白山人邓石如隶书横幅“留冬日之爱”,颇喜爱,后转赠其子。冬日萧瑟,也尝试于其中保存暖意,即先儒所说的“活泼泼地”,可见嘉言懿行对于张舜徽影响至深。
除此之外,张舜徽还不断启用新的书斋名以寄托自己的心志,多表达了他自强不息、老而弥坚的志向。这些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此前很少为人所关注,但确是关系到他的价值取向与志趣情操的重要内容。不可忽略的是,张舜徽在风雨如晦之时依然笔耕不辍,发愤撰写《说文解字约注》,这种学术定力与心境,与其受先贤义理的灌沃当然密切相关。
湖南大儒曾国藩曾被范文澜斥为“汉奸刽子手”。以范文澜在1949年后的学术地位,被他否定的曾国藩,很长时期为人所有意无意地忽略。在张舜徽笔下,《清儒学记》在一句“人们一提到曾国藩,大都深恶痛绝,斥之为‘民族罪人’、‘汉奸刽子手’,对他没有什么好评,这是很自然的”之后,多是表彰曾国藩兵戎之际不忘读书及其散文写作成就与文辞理论。成于暮年的《爱晚庐随笔》对曾国藩更是赞誉有加,其中涉及湘军上层的人物明显多为表彰。
在其心灵深处,张先生始终相信这些先贤的嘉言懿行能够滋润心灵。《爱晚庐随笔》保存的其实依然是精英文化的传统,对于阶级史观所重视的反而关注不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在张舜徽的史学思想中,人民史观与精英史观并非截然对立,在其内心深处,也许对于此前的精英史观是颇为赞许的。张先生出身书香门第,加之湘学诸老的牵引,其思想底色到底如何,值得再思考。
四、余论
夏曾佑曾谈到:“人之处事,有有所为而为之事,有无所为而为之事。有所为而为之事,非其所乐为也,特非此不足以致其乐为者,不得不勉强而为之;无所为而为之事,则本之于天性,不待告教而为者也。……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观察历史对象的天性及其无所为而为之事,就其“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实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此前的史学史、学术史研究过于重视学者的已刊作品,而对学者的未刊作品重视不够;即使关注了所有史学作品,又对其他著作关注不够,不能整体关照,这样就难免有所偏差。相反,应该如同张舜徽先生本人所强调的“读无字书”,才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学者的思想与行迹。从生活史与心灵史的角度观察张舜徽的史学观,其选本的意义得以大大凸显。
研究张舜徽的史学,要注意其高头讲章与淡雅小品的区别,同时也要留意其史学观的前后变化。这里面有着明暗远近的层次感。如果意识到学者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关注张舜徽在家书和子女教育中对于先贤义理的称引并以此为心得,再反观其晚年著作对于古代文化更多一些温情,也许正是其史学思想的底色。
张舜徽的史学有着多条线索,明线是因为1949年前后政局的更迭,大量采信阶级史观、阶级分析法,并在史学撰述中用于实践。暗线是从其幼承庭训开始,对于儒家先贤的义理有深切的体认,而且手抄笔录,置诸座右,其言行与心性为之灌沃,生机勃勃,在非常年代更是为其平添了生机与自信。这两条线索又随着时代的紧张与否有所变化,而在其晚年,则慢慢向暗线复归。重视这些明暗之间的渐变或突变,揭示其中若隐若现的思想层次,是学术史研究的要着。
此前的张舜徽研究有一个倾向,就是分而治之,这样当然可以让相关研究更加细化,但是也会导致缺乏相互观照,无法全面地评价其学术成就。张舜徽研究既要走进张舜徽,也要走出张舜徽,既要走进桂子山,也要走出桂子山,结合当时的语境,进行更深入的考辨。对于张先生这样一位旧学深厚的湖湘学人,我们不能低估旧学在其心目中的价值,要注意到可能存在的历史与价值的离合,在其学术生涯与生活世界中有着复杂呈现。只有多方面地细心考察这些面相,才可能准确理解张舜徽的学术理念。
张舜徽是我所敬重的学术前辈,揄扬之词已经足够多,作为纪念论文,不仅要表彰其学术成就,更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正是张先生最为服膺的清儒章学诚的名言。本文试图对张先生的史学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估,希望能为后世弘扬其学术成就做出一些努力。
致谢:本文的撰述得到了范军教授的鼓励和张门高弟周国林教授、张三夕教授、王余光教授的指点,也与王东杰兄、侯深师姐有所交流。谨此致谢。
注释
①关于张舜徽学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书: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国林主编:《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董恩林主编:《纪念张舜徽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2届年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戴建业主编:《张舜徽学术论著阐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参见刘固盛、王闯:《论张舜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点》,见周国林主编《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周国林、邱亚:《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③见张舜徽:《旧学辑存》(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该序成于1948年12月10日。
④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该书成书于1956年除夕,作者称不到三个月即写成。
⑥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序言》,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
⑦余嘉锡认为郑樵、章学诚考辨不精审,而张舜徽却“推重二人识见卓越,实有过人之处”。见张舜徽:《追忆先师余先生的教人方法》,《霜红轩杂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09页。
⑧⑨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⑩王余光:《史学家的使命——读张舜徽著〈中华人民通史〉》,《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