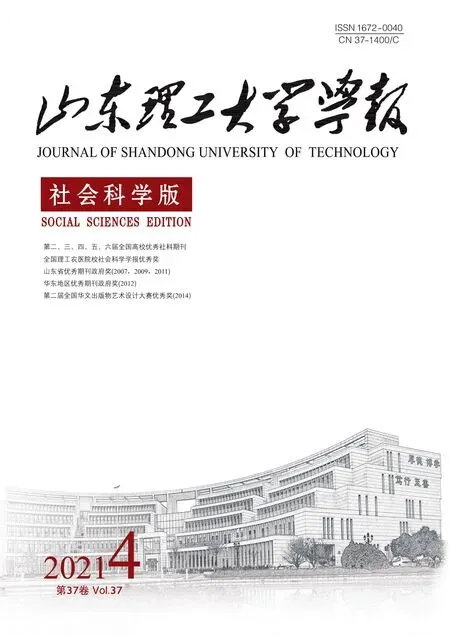汉代园林审美文化嬗变论
2021-01-05周均平
潘 芳,周均平
园林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颇受忽视,园林审美文化研究在学界也鲜有人涉足,而汉代园林更因为其物质实体的“销声匿迹”极少被提及。虽如此,汉代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却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上承秦朝,下启魏晋南北朝,创造了中国园林艺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由此奠定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基础”[1]19。汉代园林审美文化恢宏庞大,跨越两汉绵长的历史,有着自身的嬗变轨迹,这其中也昭示着汉代审美文化的变迁,展现了汉人审美走向自觉的历史逻辑,对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的梳理与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汉代园林审美文化解读
(一)园林与审美文化
园林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它与人融为一体,人于园林中游走、观望、欣赏,捕捉美的光影,追寻美的足迹。相比于其他艺术形态,“园林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是一幅绝妙的实物形态山水画,园林在反映时代文化状况方面有着其他精神艺术形态所没有的优越性”[2]。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园林的发展历史同样悠久绵长,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周维权先生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一书中将中国乃至世界园林的发展分为上古萌芽阶段、古典园林阶段、现代园林阶段和现代园林新发展阶段四个历时性阶段。我们沿用周维权先生的分期和概念,认为中国古典园林是“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人为地开辟山水地貌,结合植物栽培、建筑布置,辅以禽鸟养蓄,从而构成一个以追求视觉景观之美为主的赏心悦目,畅情舒怀的游憩、居住的环境”[1]2。古代君王帝侯圈地为园,在园内建造宫殿房屋以供居住、游憩,圈养禽兽,莳养花草以供狩猎、观赏,开渠引水营造“山川河湖”之美景,布置石刻雕塑来装饰园林,如此环境既蕴涵着特定时代丰富的文化信息,也蕴涵着这一时代独特的审美内涵与审美理念。
审美文化是指“一切体现了人类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从而具有审美性质,可供人们审美观照,情感体验和审美感悟,并可使人们从中得到一种审美愉快的文化”[3]。综合来看,审美文化是某一时代具有审美特性的文化现象或活动及其所蕴涵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观念。审美文化研究既注重感性直观层面的研究,又致力于深层审美理念内涵的挖掘,它以包孕着鲜明文化信息和审美精神的审美现象或审美活动为研究对象,并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以求辨析、展现特定时期审美对象的美学特征和审美理念,从而在多维学科和多重研究方法的烛照下揭示其演变逻辑和发展规律。
(二)汉代园林审美文化
汉代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园林数量众多,形态多样,由此创造了恢宏大气又不失自然美感的园林审美文化。鲁迅曾面对一面汉镜,发出过“遥想汉人多少闳放”的感慨,汉代国力雄厚,国祚延绵,孕育了雄大、闳放、昂扬、厚重的文化风格,培养了汉人质朴、率真、勇敢、刚强的性格。汉代园林艺术也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迅速成长,可以说汉代真正完成了中国古典园林多样形态和基本审美理念的定型,创造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范式,此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与有汉一代一脉相承。
汉代园林兼具多种功能,从经济生产、军事训练、狩猎娱乐到日常起居、观赏游乐,它在满足实用性的基础上,也以直观的形式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精神与审美追求,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文化形态。汉代园林审美文化就是指体现着汉代审美意识与审美追求的园林文化现象,它既包括园林文化所依附的诸如木、石、陶、线条、色彩等具有审美因素的感性直观的物质材料载体,也包括园林所蕴涵的汉人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等理性文化内涵。
从外在感性特征看,汉代园林审美文化形态随历史而变迁,不同的审美文化形态交融变换,并走向多元共存;从深层的理性观念来看,汉代园林审美文化与思想文化发展相交织,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园林审美理念和汉人审美追求。探究汉代园林审美文化嬗变历程,既是对汉代园林的一次全方位的立体呈现,也是对汉代审美文化的充实丰富,更是对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的亲近与认同。
二、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的二维嬗变
汉代造园现象蓬勃发展,创造了丰富庞杂的园林景观。汉代园林审美文化也随历史而变迁,园林审美形态由单一走向多元;园林审美观念也由缥缈的天上逐渐回到现实的人间,沿着汉人审美情趣化的方向不断演变。
(一)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的形态变异
1.皇家园林的沿革
汉代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探究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的形态变异,首先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角度出发。追溯文字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对园林的最初阐释。《说文解字》中对“园”的解释为“所以树果木也”,对“囿”的解释为“禽兽曰囿”,对“圃”的解释为“种菜曰圃”。由此观之,园林的产生源自于古人基本的生存生产需求,这其中少有审美的因子,先民为满足口腹之欲圈地为园、为囿、为圃,在其间进行种植和畜牧,其主要的功能还局限于经济生产功能。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发展,园囿也得以进一步发展变化,园林因而逐步具备了文化功能。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形态是“台”,这是先秦园林的原始形态。“台,观四方而高者也”,台的出现充满了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娱神色彩。纣王的沙丘苑台是史料记载的最早苑囿,纣王在沙丘苑囿内栽种树木,放养禽兽,建造宫馆。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建台的风气兴盛起来,鲁国建有观鱼台、泉台、秦台、临党台等;齐国建有路寝台、大台、长台等;宋国曾建平公台、仪台等;晋国曾建九层台、吹台、宝台等,而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高台建筑莫过于楚之章华台与吴之姑苏台。先秦台榭可看作是皇家园林的雏形,这一时期台榭的建造还只限定在帝王诸侯之家,台的作用也以祭祀通神为主,兼具狩猎和休闲娱乐等功能。
作为国家大型土木工程,皇家园林的建造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它既需要强劲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其搭台,也需要博大而凝聚的政治文化力量为其张目。汉承秦制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强盛稳定的中央集权王朝,政治、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形成了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汉代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博大的文化积累都有力地促进了皇家园林的发展。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支持和“文景之治”的苦心经营,至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达到了鼎盛。一方面,吕后弄权和“七国之乱”先后得以平定,加之颁布实施了“推恩令”,这一时期汉室王朝稳步发展,扰攘汉代百余年的诸侯国问题得以解决,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强化;另一方面,文帝、景帝时期“贱商重农”的策略有所松动,使得“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4]3261,到武帝时“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5]1040。皇家园林也在此时达到鼎盛,武帝广开上林苑,规模空前,所谓“游观侈靡,穷妙极丽”[5]3049;建造建章宫,史称“千门万户”[5]1132。强盛的国力使皇家园林的营建活动更为频繁,通过统计可知武帝时期皇家园林的数量为汉代最盛,其中号称“天下第一苑”的上林苑最具代表性,此外未央宫、建章宫、甘泉宫等规模亦大,并不断得到增益,格局开阔,这既是强盛家国实力的象征,也是汉人开拓精神和恢宏气魄的映射。
东汉初年,因“王莽篡汉”带来社会动乱频仍,导致经济萎靡不振,故三代皇帝均偃武修文以平稳政局,崇尚朴素以恢复经济,最终达到“明章之治”的理想效果。新朝初始定都洛阳,宫苑营造活动大为减少,其营造规模与西汉相比亦大为缩小,不可同日而语。“明章之治”后,汉室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至桓、灵二帝时,汉室朝廷自皇家至贵族大多追求享乐,此时造园活动与此前相比明显增多,形成东汉皇家造园的高峰期。东汉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皇家园林有濯龙园、永安宫、西园、上林苑、广成苑等,这一时期皇家园林规模建制相较于西汉大为萎缩,但园林的主要功能有所转变,由之前的祭祀、狩猎功能转为游乐、观赏功能。
2.私家园林的起步
私家园林的出现,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园林艺术开始走下神圣的皇家殿堂,走入民间。虽然在汉代私家园林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相比于皇家园林它依然如蹒跚学步的孩童,但它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生长潜力使之在后世大放异彩。
而孕育这非凡审美现象的,首先就是这个伟大的时代。“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诸侯”[4]379,汉朝建立之初为安抚诸侯国、稳定统治,曾一度分封宗室。政治权力的高扬激发人的享乐欲望,西汉梁孝王刘武,鲁恭王刘余等藩王都曾在封土内建造宫室园苑。此外,汉代地主小农经济不断发展,至汉武帝时期经济出现大繁荣,一大批坐拥几百万乃至千万的富商迁徙到长安城及其周围,他们买入田地,坐拥山泽,摹仿皇家贵族豪奢的苑囿建造自己的园林。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得到巩固,地主豪强侵占田产,外戚贵族广布园田,私家建园现象一时兴盛。
汉代私家园林主要包括贵族园林和富商私园两部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数梁王菟园、袁广汉私园和梁冀诸园。梁孝王刘武,乃是汉景帝同母弟,深得窦太后喜爱,又因平定七国之乱有功,受赏无数,都城坐落于睢阳,乃天下膏腴之地,得以在此大兴土木,营造宫室。梁孝王所建园林规模庞大,堪与帝苑相媲,有僭越之疑。其园林名曰梁苑,又名菟园、睢园、修竹园,可谓声名远扬,至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仍有“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之名句。武帝时期,茂陵富商袁广汉曾在北邙山下修建园林,规模亦大,开民间造园之先河。据《西京杂记》载,袁广汉后来“获罪没入官产,花木移入上林苑”[6]148,其园中花木被移入皇家园林上林苑,可推测其花木之繁华与珍贵,可想见其园林建制之盛大亦是有僭越礼制之嫌。东汉时期,外戚梁冀乃东汉开国元勋梁统之后,其两妹分别为顺帝、桓帝皇后,顺帝时梁冀官拜大将军,故权倾一时,其为人野蛮放肆,人称“跋扈将军”。这一时期,作为外戚贵族的梁冀侵占山泽、广布田园,与其妻在城外“多拓林苑,禁同王家”[7]1182。
综合来看,汉代私家园林多为皇亲国戚与富商豪贾僭礼所建。一方面,汉代建立了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几百年间虽也有社会动荡,但整体观之,国富民强;同时,汉人对富贵荣华有着炽热的追求,所谓“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如此“耻贫贱而乐富贵”的思想一时兴盛,于是无论是集权势与财产于一身的权臣贵族,还是在庄园经济催生下家财万贯的巨商富豪,都争相仿照皇家园林建设宅院、私园以示身份地位。另一方面,虽然汉代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强化,并以董仲舒新儒学来加强思想领域的教化与控制,但政治的大一统在造就文化领域大融合、大繁荣的同时,也孕育着一种挣脱束缚、走向自觉的审美意识。如此,汉代私家园林虽然格局规模多效仿皇家园林力求宏伟广大,但细究其园内的布置,明显可见山水审美意识已崭露头角。相对于王宫,贵族与富商之家所受到的政治束缚减弱,其所建园林虽也有政治权力的宣示,但文化功能相比于皇家园林得到进一步的显现与提升。
3.士人园林的萌芽
在汉代,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类型基本定型,根据其“所有者”的身份地位我们将其大致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士人园林。综合来看前两者具有共性,它们都是等级特权的某种象征,我们将士人园林划入其中,是因为人“所有”的既可以是实存的物象,也可以是观念中的意象,东汉末期士人对理想居住、游憩环境的文人式建构已经初步显现了士人园林的基本特征与审美趣味,故称之为“士人园林的萌芽”。
士人园林的“出现”与东汉末期隐逸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所谓“士人”的园林,其首要前提便是“士人”这一群体在东汉末期的发展,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是这一时期士人园林萌芽的先决条件。首先,政局动荡致使士人隐居自保。东汉末年,汉室皇帝更换非常频繁,且登基皇帝年纪都相对较小,由此造成皇权旁落、外戚弄权、宦官干政的局面,党锢之祸后,一部分士人对朝廷失去信心,选择远离朝野、隐居山林。其次,道教的抬头促进了隐逸思想的发展。千百年来,“仕”与“隐”是中国士大夫所面临的重要的人生选择,东汉中期以后经学衰落、儒学式微,而道教有所抬头。道教所倡导的以“隐”之态度摆脱统治阶级之束缚的思想切中了这一时期士人们的精神苦痛,极大地促进了士人归隐的风气。再次,庄园经济与隐逸思想的结合促成了士人隐居环境的变化。东汉末年,虽然战乱频仍,但作为一种渐成规模的经济形式,庄园经济依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这种自给自足、带有田园色彩的经济形式与士人隐逸思想相结合,直接促成了士人对美好隐居环境的追求。东汉中期以前,士人“隐居蓬门筚户甚至是岩居穴处仍然是天经地义”[8],刘安《招隐士》所描绘的“桂树丛生兮山之幽”“猿狖群啸兮虎豹嗥”的隐居环境是何等阴森恐怖;而发展至东汉末,张衡《归田赋》与仲长统《乐志论》所描绘的田园环境已然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9]692,“良田广宅,背山临流”[7]1644,可谓一派和谐优美、山清水秀之景象。
东汉末,文人的生命觉悟被逐渐唤醒,不同于西汉时期对家国情势的关心,这一时期的文人将关注的重心转到自身命运上来。“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从隐于金马门到隐于田园、江湖,出现了一批隐遁之士”[10],这其中通过诗文来构建士人园林的代表人物当数张衡和仲长统。张衡因多次上疏却不被朝廷采纳而辞官归隐,政治理想的失落进一步刺激了其归隐田居的趣尚,于是写下著名的《归田赋》,赋中极力描绘自己对隐居环境的想象,表达自己对高洁志向的追求;仲长统一生未仕,作有《乐志论》,渴求“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7]1644的田园居所,理想的田居生活场景在想象中得以构建,主人在此与背山临水的自然环境相亲近,培育良田、种植果园,与家人朋友相欢娱,以此寄托自己的情志,以期获得精神上的超脱。
(二)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的理念发展
审美文化是外在的审美感性形态与内在的审美理念的有机结合。汉代园林在从皇家园林到私家园林再到士人园林的变迁中,也揭示着汉代园林审美的总体理念的发展变化,暗含着汉人审美走向自觉的嬗变轨迹。
1.体象天地
汉室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呼唤着气势宏伟、雄浑壮观的审美情怀;西汉中期以后董仲舒的新儒学登上历史舞台,其“天人感应”的思想进一步延续了中国古代对天地自然的敬畏;而西安和洛阳相对平坦的地势以及理水修缮技术的发展也为皇家园林经纬阴阳、模山范水提供了支持。作为统一大帝国的象征,两汉皇家园林始终以广大的天地宇宙作为摹仿的对象,在宫苑布局与分布上法天象地,在具体的山水配备上也讲求模山范水。
“本来天上的阶级即是人间的阶级,个人在政治上取得了权力,便想在生命上取得自由,意欲成仙,意欲成为人间永远的王”[11]。在人们心目中,上天神圣而崇高,它在空间上趋于无限给人以浩瀚博大之感;“天上的阶级”尊卑分明,星宿的运行井然有序,它神秘莫测给人以神圣崇高之感;“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封建统治者为了取得权力的合法地位无不崇尚天宫,并努力营造与上天相同一的人间秩序。因此,天宫星宿便成为宫苑布局模仿的对象,这在西汉初年高祖一统江山和西汉中期武帝国力极盛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汉代皇家宫室大开大合,正所谓“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9]11。西汉初期兴建的未央宫有“台殿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凡闼凡九十五”[6]3,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宫殿建筑群,其中栉次鳞比的宫殿、台榭围绕着静穆宏伟的前殿呈现众星拱月之势,可谓“地上天宫”;西汉中期武帝扩建上林苑,宫苑繁多,其间驰道相连,布局上也多模仿天地星象,考古发现在西安城西昆明池有牵牛、织女两座石像[12],也充分说明班固所描述的“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9]21并非虚语;“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9]508-509,鲁恭王的灵光殿在建制上亦是与天上星宿相对应。
实际上,西汉帝国仿照天象营建盛大宫苑的现象反映的正是其以规模庞大、格局统一的建筑群落为其强盛国家实力之象征的崭新要求。东汉建都洛阳,在宫室营造上依然是延续西汉的规制建有未央宫与上林苑,但是相比于西汉,国家实力有所下降,因此宫室规模气势都不及西汉。但这一时期,洛阳城和园林的营建思想仍然是延续了西汉时期“法相天地”的规划理念,正如张衡所言,东都洛阳城“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规天矩地,授时顺乡”[9]106。
而在具体的山水配备上,东汉时期的皇家园林较西汉更注重借景自然、错落有致。西汉时期“武帝广开上林……穿昆明池象滇河,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5]3049,中国园林“一池三山”模式由此形成。西汉皇家园林在山水配备上讲求对自然山水的模仿,模山范水、亲近天人、以求升仙,并竭力收集自然资源以囊括天下万物,体现强盛帝国的威严、富庶。至东汉,洛阳城内的永安宫与濯龙园都以水景闻名,濯龙园里清水芙蓉、嬉戏池鱼点缀着各处水泽,永安宫中修竹冬青与清冽的泉水交相辉映,正所谓:“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脩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9]104而位于洛阳城近郊的平乐苑、广成苑、西苑等虽在规模建制上不及西汉时期的苑囿,但却能够巧妙地利用自然山水以创造优美的景致。西汉时期皇家园林“模山范水”以求广大、崇高,以展现帝国壮丽之景,这种看似功利化、政治化的审美追求也意外开出了园林审美的自然之花,至东汉,山水审美进一步发展,继而催生了园林艺术“有若自然”的审美理念。
2.有若自然
西汉武帝时期,商品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富庶商人,民间造园活动由此活跃;而自西汉中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萌芽,至东汉这一经济形式不断发展,贵族豪贾纷纷广占田庄、侵占山泽、结坞自保,进一步催生了汉代私家造园活动。这一时期私家园林在选址和布局上往往依山傍水,在景观设置上也更加追求“自然而然”之美,由此形成了汉代园林“有若自然”的审美理念。
西汉武帝时期,茂陵富商袁广汉在北邙山下建有私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6]148。作为茂陵豪贾,家资殷富,其园林规模亦大,但更引人注意的是袁广汉私园选址在北邙山下,依山傍水,这就为其模仿自然界的山水、岛屿提供了天然地理优势。园林借助自然地理环境“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形成山水波涛的“天然之景”,又“构石为山”形成人工假山,已经显现出时人对自然山水的模仿。
东汉时期,外戚权臣梁冀在洛阳城近郊建有私园。其园林“采土筑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7]1182,梁冀私园采土筑山仿效的是自然界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二崤,这种直接取法真山营造假山的方法完全突破了皇家园林求仙升天的山水模式,一改西汉时期那种对海上仙山、虚妄仙境的塑造,是对自然界客观存在之山水的如实再现。崤山多“峻阜绝涧”,与之相对应,梁冀园中亦有“峭坂”与“深林绝涧”,可以说梁冀私园的营造布局对客观摹仿对象的表现近乎到了一一对应、穷形尽相的程度,其目的便是要使园中假山与真山一样自然、逼真。除此之外,梁园中还广布树木摹仿自然植被,放养禽兽比拟山林间的生灵,这无疑都增强了园林中山水的真实感,从而达到了自然而然、有若自然的审美效果。
汉代私家园林远离皇宫,受到的政治制约和礼制束缚也相对减少,因此更具个人情趣。由西汉向东汉的时代转换,不仅蕴涵着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变化,而且也蕴涵着审美文化的重大变异。自东汉以来社会崇实,不论是衣食起居还是习俗经验,乃至文学艺术,都表现出一种客观实用的社会风尚,汉代园林的审美理念也由崇尚宇宙天象而“体象天地”转变为摹仿客观山水以求“有若自然”,这无疑是对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自此以后,“有若自然”的审美理念始终贯穿中国后世几千年的园林发展史,这背后所折射出来的迷人风景也成为中国园林迥立于世界园林的闪光点。
3.清旷乐志
东汉末的“士人园林”出现了迥异于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审美追求。文人对理想生活环境的想象式建构始于汉魏这一时代的交汇点,士人园林所蕴藏的“清旷乐志”之审美理念也萌生于汉末并在魏晋时期全面绽放。这一审美理念的产生既是政局动荡、时代转换的产物,也是园林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先声。
东汉末年独特的社会现实促进了“人的觉醒”。这一时期政局动荡、民不聊生,思想上儒学式微、经学衰弱、谶纬垮台,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从儒学和谶纬的支配下逐渐解脱出来。两次“党锢之祸”又加速瓦解了士人群体对朝廷的信心,士人将关注的重心由家国天下、社会政局、世俗生活等界域转向内在情绪、个体心理、生命感伤、自有意念等层面,显示出一种从外在之“实”向内在之“真”的朦胧向往和追求[13]。在东汉末期的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清醒的生命意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这一时期文人们更加关注人生现实,认识到人生的短暂与莫测;又发出了“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宵会》)的感慨,进而自我劝谏“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人生缥缈幻灭,不如及时行乐,这是汉末文人对现实人生的留恋、对快意生活的追求。
东汉末年文人的山水审美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与自然山水有着不解之缘,一般认为中国古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经历了神化、比德、比情、畅神的发展历程[14],这是一个审美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过程。神化关系是指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人类无法理解神秘的大自然,认为万物有灵,从而神化自然,对自然抱有崇拜的心理;比德关系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指把自然物同人的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以自然之规律和特点来比附人之情操、道德;比情关系形成于汉代,是把自然现象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以自然之规律和特点来比类人之情感;畅神关系是指把自然山水看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在人对自然的观照中获得情感的愉悦和精神的升华。同样,早在汉代就已经萌生了“畅神”自然审美观[15],至东汉末年山水审美得到进一步的升华,钱钟书先生曾依据仲长统对田居生活的描写认为“山水方滋,当在汉季”[16];当代学者余英时也认为怡情山水成为士大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自仲长统始[17]339。
仲长统因此成为东汉末年士人山水审美意识渐趋独立的标志性人物,而其对山水田园的理想式建构也催生了汉代士人园林萌芽。他终身未仕,“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7]1644。无意于功名利禄,流连于清旷卜居,仲长统在《乐志论》中描绘了一副美妙清旷的山水田园生活图景。肥沃的田地环绕园子,清旷的山脉伏卧窗外,潺潺溪水流经门前,青青竹林遍布四周;出门有舟车代步,居家有佳肴果腹,与自然万物相游戏,与达者智人相往来;弹奏《南方》以逍遥,抛却尘世之束缚,超乎宇宙之外。如此居所,已具备魏晋南北朝士人园林的雏形,园林结构复沓自然,布局在高低俯仰、前后环匝中尽显空间之美感,环境清旷怡人;士人寓居于此,与文人雅士相往来,体悟自然之美,领悟人生之真谛,获得一种乐志怡神的审美体验。
时代的演进总会给艺术增添新的因素。士人遁迹于山林,在矛盾的夹缝中归园田居,同时将自己的意趣与追求熔铸进园林之中,用笔搭建起理想中的田园居所,描绘出园林生活的乐志怡神,形成了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园林的艺术形式,士人园林正是萌芽于如此情势之中,并由此呼唤出园林审美文化的新趋向。自此,士人园林对“清旷乐志”的追求日渐清晰地显现出来,并在魏晋南北朝达到高峰,正如余英时所说,自汉末仲长统以来“流风愈广,故七贤有竹林之游,名士有兰亭之会,其例甚多,盖不胜枚举矣”[17]339。“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矢志不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言其志:“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此种归隐田居、远离朝野的追求可谓与汉末士人如出一辙;而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草药之属,莫不必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18],如此园林,既有清旷优美的环境氛围,又兼备娱目欢心自然之物,已然是将仲长统理想中的田园现实化,士人园林乐志怡神之功能尽览无余。
三、汉代园林审美文化嬗变的意义
(一)汉代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佐证
汉代皇家园林虽然是权力的象征和政治的情感寄托,但我们也无可否认,当一代代帝王走进这恢宏壮丽的上林苑,踏入那庄严肃穆的未央宫,他可能在某个瞬间也会被园林的美,被其中所蕴涵的磅礴气势所感动。这种审美感受虽是与宗教感受和政治感受交织在一起并深受后者支配,但这从政治中走来的审美体验与感受也是不容忽略的。
比较而言,私家园林在布局和景观配置上更倾向于个人化,更加追求有若自然的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权力对审美的干预。而士人园林在理想中的建构已接近纯粹个人化的精神家园,虽没有实体园林的建造,但已经具备明显的个人审美情趣。其空间布局和景观设置的自然之美愈发强烈,个人的喜好得以凸显,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园林的萌芽,也是汉代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佐证。
(二)中国古典园林审美文化沿革的重要范式
作为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园林艺术的面目与前代相比发生着重大变化。先秦时期园林的构成主要包括高大的台观、台榭建筑和人工水体(池沼)、动植物等附属景观,讲求规模上的广大和建制上的恢宏,西汉时期皇家园林发展达到鼎盛,依然是延续先秦园林的审美风范,总体未脱求仙问道与扬我国威的朴素追求。汉代私家园林的出现应该说是为皇家园林向士人园林的过渡搭建起一座桥梁,它的出现意味着园林审美文化开始出现挣脱政治功利和政治需要的倾向,其“有若自然”的审美理念也折射出汉代审美文化由追求虚无之美到探索现实之美的转变。而东汉末期的“士人园林”更是退居到个人,在艺术创作的目的与归宿上始终指向个人的审美情趣和人生况味,士人园林不再追求体象天地的无穷宇宙,而是努力营造清旷乐志的自然环境,士人隅居于此,以求在有限的自然山水和田园林野中得到无限的心灵慰籍与审美快适。
而向后延展,我们可以看到汉代所创造的皇家园林、私家园林与士人园林成为中国园林千百年来的重要范式,汉代多样化的园林形态所孕育出的审美理念在后世中国园林审美中一以贯之,并持续滋养着汉民族的文化品格。此后各代,中国园林艺术始终沿着汉代所形成的三大园林体系而消长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极盛的士人园林大体是在东汉末年士人园林奠定的基础上推衍而成;而盛唐园林兼容并包,在保持汉代皇家园林开放气度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汉代士人园林的情趣化内涵;而随着中国士人的审美趣味由外在走向内心,由宏观走向微观,一直到宋元明清,园林审美也由汉代的“体象天地”“有若自然”“清旷乐志”进一步演变为对“壶中天地”的倾心。
汉代园林审美文化横跨两汉四百余年历史,既有外在审美形态的变迁,也有深层审美理念的变化。从形态变异方面来说,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经历了由皇家园林到私家园林的流变,再到东汉末期士人园林的萌芽;从深层理念来说,汉代园林审美的总体理念不断发展丰富,实现了由“体象天地”到“有若自然”再到“清旷乐志”的递嬗。需要指出的是,三种形态与理念并不存在相互更替的历时性,而是后来者与前者并存,共同丰富了汉代园林审美文化的内容,展现了汉代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历史逻辑,建构起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范式与审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