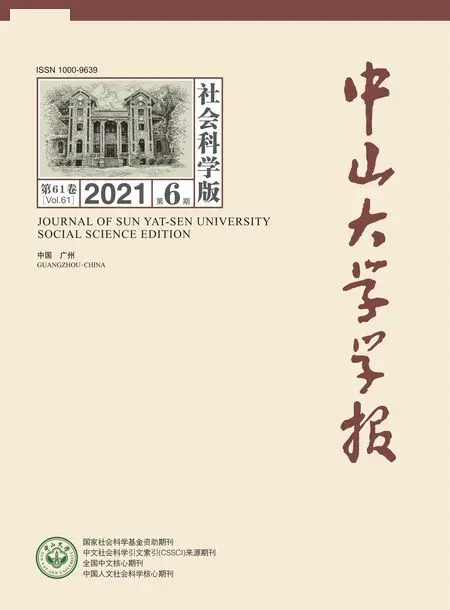西海寻路道术裂?*
——以卫礼贤与黑塞、荣格的思想交谊为中心
2021-01-04叶隽
叶 隽
一、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日耳曼知识精英的教育养成与文化理想:以歌德为中心
钱锺书先生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①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序”第1页。王国维先生谓:“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②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65页。其理相通,真可谓是“两代学人,一般见地”。如果我们将素来关注的中心从本土语境移开,将其落实到宏观世界场域中去,选择一个同属文明进程中重要异国为考察对象,譬如这里的德国,则会别有一番意趣。
当20世纪前期之际,西去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汇为潮流,并成为日后现代中国建设的中流砥柱;但如果我们能以世界为胸襟,则东来的德国人,也一样在追寻着文化资源与发展可能。因“西去取经”问题已为国人普遍关注,本文关注相反的一面,即外人的“东来求法”现象。事实上,近代以来的来华者多半没有如同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那样有明确的学习意识,他们来到中土,更多是出于猎奇、利益与传教等诸多其他因素,譬如本文主要探究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
卫礼贤(Wilhelm,Richard,1873—1930)与荣格(Jung,Carl Gustav,1875—1961)、黑塞(Hesse,Her⁃mann,1877—1962)年纪相若,只略长数岁(2—4岁),基本可算同龄人,将他们都视作日耳曼文化中的精英人物并不为过。作为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生在第二帝国统一不久,亲历过威廉时代的辉煌兴盛(1890—1915年),也算有福之人。可即便幸而无早殇之忧,但在进入威廉以后的1920年代,前期的“有福”却必然会被后期的“忧患”所替代。
1890年代,卫礼贤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黑塞却逃离了毛尔布仑神学校在家自修,而荣格则在瑞士的巴塞尔大学读自然科学与医学。有趣的是,黑塞与瑞士关联亦甚密切①黑塞1904年时与瑞士女子玛利亚·贝诺利结婚,同时移居瑞士。1923年甚至加入瑞士籍,并戏称其乃自己的“第二故乡”。值得指出的是,黑塞1899年曾在瑞士巴塞尔经营书店,而此时荣格正在巴塞尔大学读书。,这且按下不提。少年时代的不同教育养成过程为他们提供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路径。三人虽经历不一,可同样都成为了精英:荣格相对来说比较正统,经由科班出身的学校教育而逐步发展,最后获得博士学位后而开始其学术历程②关于荣格生平,可参见[瑞士]荣格(Jung,Carl Gustav)著,刘国彬等译:《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黑塞则最具叛逆精神,早年辍学,做过各类工作,饱尝社会生活的艰辛和磨难,根本就没有正统的大学学历③关于黑塞生平,参见[德]黑塞:《我的传略》,[德]黑塞著,张佩芬译:《黑塞小说散文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64页。;而卫礼贤的教育得益于教会力量,在神学院受教后开始其传教生涯④关于卫礼贤的一生事迹,可参见其夫人的回忆录,Wilhelm,Salome:Richard Wilhelm-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卫礼贤——中国与欧洲间的精神使者》)。Düsseldorf,Köln: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56;[德]吴素乐(Ballin,Ursula):《卫礼贤——传教士、翻译家和文化诠释者》,[德]马汉茂(Martin,Helmut)等主编,李雪涛等译:《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Chinas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454—487页。。然而殊途同归:他们三人都成为日耳曼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是思想史上无可规避的重要标志;更为有趣之处还在于,三者的相互启迪和发明构成了现代日耳曼文化精英追索真知的“三子星座图”。
对于日耳曼文化传统养成的知识精英而言,《圣经》固然是必不可少的“宝书”,歌德却更是他们倾心向往的圣贤。同样是德国文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黑塞对歌德“景行行止”般的推崇几乎成为一个范式⑤有学者专门将黑塞关于歌德的论述整理成书,参见Hesse,Hermann:Dank an Goethe-Betrachtungen,Rezensionen,Briefemit einem Essay von Reso Karalaschwili(《感谢歌德》)。Frankfurt am Main:Insel Verlag,1975.。他在《感谢歌德》一文中表示:“在所有的德国作家之中,歌德是我最深具谢意,也是我最常尚友、困惑、受启,迫使我想成为其后继者或挑战者的那一位。他不是那位我最爱与最享受的诗人,也不是我最少与之发生冲撞和冲突的诗人,不是这样的,那是这些位:艾辛多夫、让·保尔、荷尔德林、诺瓦利斯、莫里克,还有其他人。但所有这些我所爱的诗人们都不能将我引入深层的问题和重要的伦理冲动,对待他们我不需要斗争和对抗,但在面对歌德时我总是必须进行思想对话和思想斗争。”⑥原文为:Unter allen deutschen Dichtern ist Goethe derjenige,dem ich am meisten verdanke,der mich am meisten beschäftigt,bedrängt,ermuntert,zu Nachfolge oder Widerspruch gezwungen hat.Er ist nicht etwa der Dichter,den ich am meisten geliebt und genossen,gegen den ich die kleinsten Widerstände gehabt habe,o nein,da kämen andere vorher:Eichen⁃dorff,Jean Paul,Hölderlin,Novalis,Mörike und noch manche.Aber keiner dieser geliebten Dichter ist mir je zum tiefen Prob⁃lem und wichtigen sittlichen Anstoßgeworden,mit keinem von ihnen bedurfte ich des Kampfes und der Auseinandersetzung,während ich mit Goethe immer wieder Gedankengespräche und Gedankenkämpfe habe führen müssen.Dank an Goethe(1932),in Hesse,Hermann:Dank an Goethe-Betrachtungen,Rezensionen,Briefe mit einem Essay von Reso Karalaschwili(《感 谢 歌德》)。Frankfurt am Main:Insel Verlag,1975.S.9。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是黑塞应罗曼·罗兰(Rolland,Romain)之邀,为《欧洲》(Europa)杂志的“歌德专号”(Goethenummer)所撰。而荣格不但以其隐然或有“歌德血统”而颇感得意,更是宣称:“我的教父和权威是伟大的歌德本人。”⑦[瑞士]荣格(Jung,Carl Gustav)著,刘国彬等译:《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第78页。至于卫礼贤,他似乎干脆就把歌德视为德国版的孔子,将其与孔子、老子等中国贤哲相提并论,并且能更深一层进行比较:“他(指歌德,笔者注)十分清楚地指出,如果生命的节奏搏动过速的话,本来具有互补性的东西方之间必然会产生对立。直到今天我们才完全清楚,他在这方面不仅超越自己的时代,而且超越后来的历史学家有多么远。”①[德]卫礼贤著,蒋锐编译:《歌德与中国文化》,《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如此看来,作为日耳曼文化规训之典范,歌德的思想观念早已渗入后代精英的骨髓中,任何一代精英人物都很难摆脱其庞大的精神身影。那么我们要追问的自然是:后来者是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精神教父及其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呢?
作为纯正的诗人代表,不论是创作续写还是精神继承,黑塞都相当自觉地沿袭歌德之道,但他显然意识到这样一种精神使命的极端艰巨性,所以非常坦白地承认自身积累与远大目标之间的差距所在。
甫入20世纪,三者已经选择了不同的未来道路:卫礼贤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年(1899年)踏上了异邦的国土(中国的青岛),开始其传教事业;黑塞则同样转移到了异乡(当然是仍有日耳曼文化氛围的瑞士巴塞尔),继续他遍历各行的职业实验,但很快(1903年)就专心致力于其文学创造的终生事业;而荣格选择了苏黎世的一家精神病医院,继续临床学习精神病学,这一选择对他未来志业的形成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我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转折意义对于德国人来说怎么高估也不过分。这三位术业有专攻、身处不同地域的日耳曼知识精英也身不由己、不约而同地卷入其中,甚至有那么一天,彼此的道路会有交叉乃至略微重合。德国人在黑格尔时代是那样的自信,以自己的日耳曼世界作为世界文明的担当者;而经由俾斯麦—威廉二世的铁血手段,在政治层面又催生了何等的自信狂妄。可一旦一战的帷幕落下,他们不得不品尝失败的苦果,在一片废墟的大地上遥望苍凉。如何面对沉痛的教训,如何清理自己的创伤,却是摆在德国人面前,尤其是知识精英面前的重大挑战。卫礼贤、黑塞、荣格等人自然也属于这样一批精英谱系中人。不过在这样一种潮流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其时德国知识界向东转的声音。1920年宗白华刚到德国不久,就由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推崇而重新开始反思自己这代人的文化观:“风行一时两大名著,一部《西方文化的消观》,一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又说“德人对中国文化兴趣颇不浅也”,一月之内就“出了四五部介绍中国文化的书”。这一外来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对自家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所以即便是“实在极尊崇西洋的学术艺术”的时候,宗白华也仍然强调“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②宗白华:《自德见寄书》,林同华主编:《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
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西海寻路”或许不是没有必要,但如何选择路径的开端和切入的时机,则更为重要。如此,我们就不妨选择这种路径发展的交叉处进行观察,因为只有交域的产生,才可能为观念的交锋提供一种更为有效和坚实的共享基础。
二、黑塞与卫礼贤的交谊及其对西方思想史的意义:《玻璃球游戏》的深刻思辨③Hermann Hesse:Das Glasperlenspiel.Vol.1-2.Frankfurt/Main:Suhrkamp Verlag,1971.中译本参见[德]黑塞著,张佩芬译:《玻璃球游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关于黑塞和卫礼贤的关系,曾有论者作过简略的叙述,参见“Hermann Hesse und Richard Wilhelm”,in Hsia,Adrian:Hermann Hesseund China-Darstellung,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黑塞与中国——介绍、资料与评论》)。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4.S.319-323。关于这种关系,还可参见马剑:《“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一位使者”——从黑塞对卫礼贤的评价看中西方文化交流》,王炳钧、冯亚琳主编:《德语学习学术版》2009年第1期。但此文征引不无疏误,需要认真核对。
如果说印度为黑塞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的话,那么中国就为他构架出一个更加陌生化的、带有理想色彩的文化世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黑塞的精神世界里,有一幅绝非单一向度的立体东方知识图景。这对于其思想形成和精神质变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也是我们理解那代德国现代知识精英的必须维度。
据推断,20世纪20年代后期卫礼贤与黑塞有多次相见之缘。如通过二者的共同友人,中国专家莱因哈特(Reinhart,Georg,1877—1955);如1926年12月,在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的相逢①“Hermann Hesse und Richard Wilhelm”,in Hsia,Adrian:Hermann Hesse und China-Darstellung,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黑塞与中国——介绍、资料与评论》).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4.S.319.。但最重要的一次,当在1926年6月,卫礼贤利用到苏黎世(Zürich)讲学的机会,希望与黑塞论交。他通过施密茨、勾德两人分别以口头问候、转达信件等方式,向黑塞致意。黑塞于是在6月4日写了一封道谢信,并表示他在深秋和冬季将重返苏黎世,也许彼时可以见面。他说:“长期以来您对于我是位重要人物,我一直对您敬爱有加。我对中国文化的亲密缘分绝大多数都源于您,在亲近印度文化多年之后,这种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对我而言日益重要。长久以来我就想感谢您,为了您许多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和翻译,特别是您的《老子》《庄子》以及其他种种翻译的典籍感谢您,现在借着这个机会也可以表白了。我们两人有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我在日本的表弟贡德特。我经常为此感到欣喜。”可以说,黑塞是相当真诚的,对于卫礼贤译介中国典籍而给他带来的知识和精神资源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所提及的表弟贡德特(Gundert,Wilhelm,1880—1971)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此君日后将禅宗经典《碧岩录》译成德文,意义重大。但黑塞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我所知不多,我完全生活在圈外,对于当前思想界流行的言论(如凯瑟苓所代表的)我不屑一顾。相反,我与中国之友如莱茵哈德有共同点,我们都与您有缘分。我与苏黎世的心理分析家们也不相投,我觉得,除了荣格,他们大多数和蔼可亲,然而却都是肤浅而适应世道的成功人士,他们的任务完全在于肯定市民意义上的生活,而将其悲剧性的一面压制下去,所以我和他们断了关系。”②《易经》(这里称引自1926年4月6日黑塞给卫礼贤的信,当误),[德]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Michels,Volker)编选,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China:Weisheit des Ostens),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德文为:Von Ihrer heutigen Tätigkeit weißich nicht so sehr viel,ich lebe als Outsider,und habe der aktuellen geistigen Welt(wie sie et⁃wa von Keyserling etc.repräsentiert wird)den Rücken gekehrt.Dagegen finde ich bei China-Freunden wie Reinhart wieder ge⁃meinsame Beziehungen zu Ihnen.Die Zürcher Psychoanalytiker stehen mir ferner,sie scheinen mir mit Ausnahme von Jung alle liebenswerte,aber falche,wohlangepaßte Erfolgsmenschen zu sein,druchdrungen von der Aufgabe,das Leben im bürgerlichen Sinn zu bejahen,und sich um seine Tragik zu drücken.So habe ich auch diese Beziehungen einschlafen lassen.“Hermann Hesse und Richard Wilhelm Zwei Briefe”(两信所署时间分别为1926年6月4日、6月8日),in Hsia,Adrian:Hermann Hesse und China-Darstellung,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黑塞与中国——介绍、资料与评论》)。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4.S.324.凯瑟苓即凯泽林(Keyserling,Count Hermann,1880—1946)。
卫礼贤则表达了更为强烈的和黑塞谋面的愿望,甚至为此作出这样的解释:“请您不要误解我与凯泽林的联系,也不要因为我的‘世界存在’。如果人们像您和我一样去观察世界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双重艺术加以深藏:像您那样存在于寂寞之中以及像我一样存在于世界之中。但我相信我们将彼此理解,我可以向您介绍多位来自古老中国的先贤,譬如庄子及其他,他们完全是非社会的。孔子承受了很多苦难并且对其有很好的理解(比他表现出来的对他的弟子们的表象要好得多)。”③德文为:Lassen Sie sich durch meine Verbindung mit Keyserling nicht irre machen.Und auch nicht durch mein“Welt⁃wesen”.Wenn man die Welt so durchschaut hat wie Sie und ich,so kann man sich auf doppelte Art verbergen:in der Einsam⁃keit,wie Sie und in der-Welt,wie ich.Aber ich glaube wir werden uns verstehen,und ich kann Ihnen aus dem alten China mehrere Herren vorstellen wie Tschungtse u.a.die gänzlich unsozial waren.Meister Kung hat viel unter ihnen zu leiden gehabt und verstand sie nur zu gut.(Besser als er sich seinen Jüngern gegenüber den Anschein gab).卫礼贤1926年6月8日于法兰克福致黑塞函,in Hsia,Adrian:Hermann Hesseund China-Darstellung,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黑塞与中国——介绍、资料与评论》)。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4.S.325-326.可以清楚地看到,卫礼贤如何将中国文化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加以运用的,与德国知识精英的交往,正是在这样一种异国资源的发现中得到展示。有趣的是这里透露出的历史信息,譬如黑塞表明了对凯泽林的不屑态度,而卫礼贤则予以回应,显然也与凯泽林拉开了距离。发掘出这样的细节无疑是有趣而重要的,这涉及德国或欧洲文化语境内部的派系立场分野,即作为感性哲学代表的凯泽林,因其斯拉夫文化背景而享有声名,但却并不被黑塞这样的主流作家和思想家所接受。
其实黑塞熟悉卫礼贤,主要是通过他的德译中国经典:“如今,有一系列的中国古籍翻译出版了,我认为这是当今德国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就是卫礼贤翻译的中国传世经典……译者是一位一辈子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无与伦比,他不仅通晓中文,也通晓德文。中国思想对于当今的欧洲有多么重要,他自己就亲身体验过。这一系列典籍的第一部是耶拿的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我至今忘不了,我当时读《论语》时是如何惊讶,如何似进入童话世界般地欣喜,如何感觉到在陌生的同时又感觉到它是多么正确,似乎是我预想到的,期待的,我感觉到它的宏大庄严。”①[德]黑塞:《卫礼贤的中国译著》(1928年),[德]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Michels,Volker)编选,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China:Weisheit des Ostens),第147—148页。作为在德国甚至日耳曼文化与知识场域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主流作家和思想家,黑塞的青睐与好评,尤其是多篇书评对卫礼贤的德译中国经典作品的推介,对译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支持和激励。但这也只是经典阅读的延伸效应,对于诗人本身而言,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如何拓展自家的知识域和提升思想力。所以,正如黑塞自述,“早就充分探讨了《老子》和《易经》中的东方道路”,而且目的相当明确:“为了能够确切地认识所谓现实的偶然性和可变性。”②[德]黑塞:《我的传略》,[德]黑塞著,张佩芬译:《黑塞小说散文选》,第477页。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对于相当熟悉印度的黑塞来说,东方各主要文化体在他的知识地图中是怎样被定位的?他在何种程度上确定《易经》和《老子》《论语》等知识世界中的东方代表性?其实,这正与黑塞对印度精神世界的理解有关:“印度人所欠缺的方面,比如:贴近生活、精神上要求达到的最高的伦理道德,但又能与感性的日常生活的魅力与游戏和谐融合,在高度的精神性和单纯的生活乐趣间来回游移,这一切在这儿比比可见。如果说印度在苦修和僧侣式的避世中达到至高境界并能触动人心,那么古老中国在精神心灵的培育上所达到的境界足可与之匹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自然与精神、宗教与世俗生活并非敌对的双方,而是意味着友善的对立,二者都能得到自身存在的权利。如果说印度苦修的智慧在其要求上的极端性是青年式的,清教徒式的,那么中国的智慧则是经历丰富因而变得聪明机智者的智慧,懂得幽默,并不因为阅尽沧桑而灰心丧气,也不因聪敏而变得轻浮。”③[德]黑塞:《卫礼贤的中国译著》(1928年),[德]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Michels,Volker)编选,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China:Weisheit des Ostens),第147—148页。德文为:Was jenen Indern gefehlt hatte:die Lebensnähe,die Harmonie einer edlen,zu den höchsten sittlichen Forderungen entschlossenen Geistigkeit mit dem Spiel und Reiz des sinnlichen und alltäglichen Lebens.-das weise hin und Her zwischen hoher Vergeistigung und naivem Lebensbehagen,das alles war hier in Fülle vorhanden.Wenn Indien in der Askese und im mönchischen Weltentsagen Hohes und Rührendes erreicht hatte,so hatte das alte China nicht minder Wunderbares erreicht in der Zucht einer Geistigkeit,für welche Natur und Geist,Religion und All⁃tag nicht feindliche,sondern freundliche Gegensätze bedeuten und beide zu ihrem Rechte kommen.War die indisch-asketische Weisheit jugendlich-puritanisch in ihrer Radikalität des Forderns,so war die Weisheit Chinas die eines erfahrenen,klug gewor⁃denen,des Humors nicht unkundigen Mannes,den die Erfahrung nicht enttäuscht,den die Klugheit nicht frivol gemacht hat.转引自Hsia,Adrian:Hermann Hesseund China-Darstellung,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黑塞与中国——介绍、资料与评论》)。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4.S.52-53。在这里,作为东方文化核心部分的印度、中国文化得到了互补式的呈现,也表现出黑塞作为一个精神寻道者执着不懈地借助不同文化资源,进行精神世界探索的尝试,中国知识世界尤其是古典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表现出更为重要的价值。所谓“德国语言界的精神精英在过去二十年里都被这股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潮碰撞到,在某些激情奔放的思想运动昙花一现又快速趋于消亡的同时,卫礼贤的中国典籍默默地不断增大影响,其重要性日益明显”①[德]黑塞:《卫礼贤的中国译著》(1928年),[德]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Michels,Volker)编选,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China:Weisheit des Ostens),第148页。。
当然,如果仅仅停留在德译汉籍的知识世界里也未免低估了黑塞这样创造性人物的意义,如果我们进入到他创造的文学世界,譬如像《玻璃球游戏》这样的文学文本。正是在这样一个诗思对话的文学世界里,黑塞充分展示了他的东方资源和诗性创造,两者交相融合,虽非浑然一体,但确实展现出创造性的价值来。我们或许更看重《玻璃球游戏》所营构的知识、文学与思想世界,但在黑塞自己看来,这不过是通向东方之路的开端而已,一扇“通向东方之窗”。这意味着东西方之间互动循环的历史“元”轮将被彻底推动起来,首先就该是知识与思想意义上的。
三、荣格与卫礼贤的交谊及其对西方学术史的意义:《太乙金华宗旨与慧命经》的心理启迪②关于荣格和卫礼贤关系的一个讨论,参见方维规:《两个人和两本书——荣格、卫礼贤与两部中国典籍》,《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范劲:《中国符号与荣格的整体性心理学——以荣格的两个“中国”文本为例》,《江汉论坛》2013年第6期;范劲:《〈玻璃球游戏〉、〈易经〉和新浪漫主义理想》,《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3期。
荣格与卫礼贤相识于1922年,在德国智慧学校的大本营——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当时,卫礼贤应凯泽林之邀,在该城的智慧学校(Die Schule der Weisheit)作报告。
虽然直到1904年才进入学界,在苏黎世大学(Universität Zürich)获得精神病学讲师的职位,但由于天分卓异,又得到弗洛伊德(Freud,Sigmund,1856—1939)的大力提拔③关于荣格、弗洛伊德的关系,可参见[美]约翰·克尔(Kerr,John)著,成颢译:《危险方法:荣格、弗洛伊德和一个女病人的真实传奇》(A Most Dangerous Method:the Story of Jung,Freud&Sabina Spielrein),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仅用了六年时间(1910年),35岁的荣格就出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一举成名。但这种“名利兼收”的状况,并未阻挡荣格在学术、思想层面精益求精的追求,甚至不惜为此与昔日恩师弗洛伊德“反目成仇”——仅仅三年之后(1913年)就与弗洛伊德全面分裂,较之当年尼采之反抗瓦格纳“有过之而无不及”。年将不惑的荣格,有长达近十年的时间沉浸于困惑之中,其实,他早年就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犹疑不决,表现出对超越传统知识藩篱征象的趋势。而他对弗洛伊德性理论的质疑,尤其“有把一切理论都建立在两种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上的趋向”(哈特曼语,Hartmann,Heinz)④转引自[奥]弗洛伊德著,廖运范译:《弗洛伊德自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98页。。这是与他的思维方式有根本冲突的,所以,他最终选择以真理为标准,而非私人感情。“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所有我的那些朋友和熟人一个个相继离我而去。我的这本书被宣布为一派胡言。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于是事情就无法挽回了。”⑤[瑞士]荣格(Jung,Carl Gustav)著,刘国彬等译:《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第284—285页。旋即就不得不面对世界大战的挑战,1914—1918年的历史早就在其幻觉中不断出现⑥1913年10月,荣格独自在旅途中“看到一场滔天洪水,覆盖了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低洼地带。从英国到俄国、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都被覆盖了。我看到黄色的滚流、飘浮的瓦砾和成千上万的死亡”。[瑞士]荣格著,林子钧等译:《红书》(Liber Novus),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7页。,即便战争结束之后,也是哀鸿遍野,欧洲没落。所以,从这一背景来看,1922年与卫礼贤结识,对其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为他直接走向中国心灵提供了一座最佳桥梁。1923年,荣格就邀请卫礼贤去瑞士,在苏黎世进行学术讲座。当然,更重要的或许是如何就中国文化经典进行深度交流,以盘活他理想中的中国思想资源。
1922年至1930年与卫礼贤的八年交谊,荣格深受其惠,这使他接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在卫礼贤逝世之际,荣格不惜以崇高的语言来表彰其人:
卫礼贤无愧为一个大师,他不仅超越了他的职业范畴,而且以他的学识关注着人类的命运。他自始至终一直如此。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使他如此彻底地从传教士至欧洲人的狭隘视界中解脱出来呢?事实上,他刚一接触到中国人对于灵魂的神秘看法,就立刻感觉到里面隐藏着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的东西,为此,他放弃了欧洲人的成见,成为这种稀世之宝的代言人。这是容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这是洞察一切的伟大精神,惟其如此,他才能毫无保留地在这种迥然相异的思想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并将自己的种种天赋和才能贡献给这种富有魅力的精神。他既没有丝毫基督徒的悲苦,也没有一点欧洲人的骄横,他的满腔热忱就充分地证实了他这种人所罕有的伟大精神。①[瑞士]荣格:《纪念卫礼贤》,[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通山译:《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41,140—141页。
这并非一般意义的死后哀荣的颂词而已,因为荣格与卫礼贤的学术与思想交往友谊深长,此乃对其精神人格有深度认知和感受后的肺腑之言。荣格最可贵的,是他对卫礼贤这样一种博大胸怀与探索人格的把握,之所以能如此,是他也同属于那种执着于追求真理过程的伟大思想家,故此才能换位思考,产生“理解之同情”:“如果我们都安心于各自的专业范畴,那么,作为汉学家的他(指卫礼贤,笔者注)和作为医生的我恐怕会老死不相往来。然而,我们在超越了学院疆界的人文领域中相遇了。那是我们最初的交往。一道火光跃然而出,点燃了一盏明灯,这已注定要成为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②[瑞士]荣格:《纪念卫礼贤》,[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通山译:《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41,140—141页。确实,日后每每在荣格学术与思想发展的关键时刻,卫礼贤总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灵感,譬如《易经》《慧命经》等都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荣格作为一代精英代表的切身体验。关于他的重要著作《红书》,他曾这样说道:“这本书耗费了我十六载光阴。我的一位炼金术挚友在1930年把我带离它。结尾部分写于1928年卫礼贤送了我一本炼金术专著《金花》之时。在那本书里,我找到了本书内容得以证实之路,我也就不能再继续撰写它了。无知之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如果我没有接收到这原始经验的压倒性力量,它本来可能写进我的书中。在炼金术的帮助下,我终于可以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整体里了。我一直都很清楚,这些经验包含着某种宝贵的东西,因此,除了珍重地记录下它们,我也不知道有任何别的方式了。”③[瑞士]荣格:《跋》(1959年),[瑞士]荣格著,林子钧等译:《红书》(Liber Novus),第472页。这很清楚地表明《红书》和《金花的秘密》之间的精神关联性,也就是在汉籍翻译史和分析心理学之间构筑了一条可能的知识和思想通道。要知道,荣格自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④[瑞士]荣格:《〈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1930年),[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邓小松译:《金花的秘密——中国生命之书》(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A Chinese Book of Life),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1页。,所以他的东方求知就显得格外意义重大,而对中国的深度接触则主要通过卫礼贤的中介而达致。1957年,荣格谈到《红书》:“我跟你谈到过那段岁月,追寻内心图像的那些年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光。其他一切皆发源于此。这本书就始于那时……而包孕一切的神奇开端就在那时候。”⑤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4721654/,下载自2016年10月5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心理学家荣格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阐释内心意象,这使得其对潜意识现象的挖掘成为一种必要的技术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并不回避那种对于神秘主义倾向的选择,譬如他指出:“在我们的基督教文化中,圣灵及圣灵的爱在很久以来就是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追求的……这种原则所代表的情感和本能历史久远,来自于人类生命延续的根源。毋庸置疑,中国的这些概念得自直觉的洞察,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人类精神的本质,就不能没有如此的见地。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概念,因为中国的哲学史告诉我们,中国从没有偏离心性本原的精神体验,因而从来不会过分强调和发展某一单一心理机能而迷失自己。也因此,中国人一直都对现实中与生俱来的矛盾性与两极化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发现相反的两面总是能相互找到平衡——这是高等文化的象征……我不是要贬低具有强大判断能力的西方理智,在这方面东方可以说还很幼稚(这与聪明程度无关)。如果我们能把另一种或者说第三种心灵的功用提升到和我们的理智一样的高度,我们也许会超越东方很多。”①[瑞士]荣格:《〈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1930年),[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邓小松译:《金花的秘密——中国生命之书》(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A Chinese Book of Life),第24—25,30,94,42—43页。这段论述很重要,因为对于基督教的立场回归给我们揭示了那代日耳曼知识精英的基本思考和态度。其实卫礼贤也是如此,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以作为传教士而并未归化一个中国人入教,但这并不代表他对基督教的背叛或不敬。他始终保有内在的强烈的基督教情结,在一战青岛岁月里,支撑他的动力或许就与宗教背景密切有关。在其时,他甚至写了一本《耶稣传》(Jesus,Zügeaussei⁃nem Leben.(Darmstadt:Gesellschaft Hessischer Bücherfreunde,1922),这一切都提醒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和感知卫礼贤的基督教背景。
荣格追问说:“到底什么是个性的完整?对这种完整性的追求是否必要?正是在这时我们来到了自古以来东方人走过的大道上。中国人能找到这条路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加剧人性本有的对立面之冲突,以至于失去两股对立势力之间的联系。这种原始的思维,是是和否之间的紧密无间,而不是非黑即白。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到相对的两股势力之间的碰撞,因此他们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来自于印度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境界。”②[瑞士]荣格:《〈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 心理学评述》(1930年),[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邓 小松译:《金在这里,荣格显然明确表达了对普世元一价值甚至道路的认同:无论东西,都会相融归一,是否黑白,其实都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彼此相融,需寻出第三维的沟通张力来的。更了不起的是,荣格并未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他将其进一步纳入身处的历史语境之中。他显然认同卫礼贤的观念,所以也同样表述道:“欧洲的大炮已经敲开了亚洲的大门,欧洲的科学技术、世俗主义和贪婪已经在中国泛滥,我们已经在政治上占领了东方。”③[瑞士]荣格:《〈太乙金 华宗旨〉的分析心 理学评述》(1930年),[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邓 小松译:《金这当然是一个基本事实,而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对中国,甚至对亚洲的殖民事实,即便是对整个广义的东方世界都是如此。从非洲到拉美再到亚洲,欧洲殖民者的步伐和坚船利炮走遍世界,形成全球化的时代。这就是西方文明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和创伤,是典型的“双面胶”。
在荣格看来,“回光不仅仅是圆形运动,它一方面表示对神圣区域的标识,另一方面表示固定和集中。道开始运行并主导万物,有为转向无为,所有次要的事物都要受制于核心事物。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回光就是‘围绕自己转圈’。这样人格的各方面都被包含在内。这引起了光明与黑暗的两极交替,也就是白天与黑夜的交替。这种回转的运动在激发人类本性中所有的光明和黑暗的力量时有着十分重要的精神含义。这一运动同时激活了内心中所有对立的心理力量。这是通过自我修持而觉悟。一个完美的人的原型概念是一个柏拉图式的人,他圆融无碍而且雌雄同体”④[瑞士]荣格:《〈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1930年),[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邓小松译:《金。这种“道驭万物”的思想其实很符合道家的理念,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且“无为—有为”相互转化,二元关系的“未济—既济”彼此相生,其中关键之“三”已在孕育之中。这里的“雌雄同体”显然不应指具体的生理特征上的,而更应是心理意义层面的“阴阳兼备”。
四、西海寻路路安在:现代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卫礼贤意义
1930年,年未及花甲的卫礼贤早殇,对于德国思想界,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损失。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像卫礼贤那样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汉学家,再也不可能复得一位如卫礼贤这般与中国精英理解亲和的摆渡人,再也不可能有如此深度介入西方主流思想生成之中对于中国文化达到高山流水般知音境界的人物。虽然德国汉学界对卫礼贤的学术评价并不太高,但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卫礼贤的意义应当在一个远为开阔的宏大视域中来审视。
荣格与黑塞的走向东方之路虽然没有终止①当然值得指出的是,黑塞与荣格之间也有密切的思想关联。首先是黑塞对荣格的借鉴,1916—1917年间,黑塞决定在心理分析治疗师约·贝·朗格(Josef Bernhard Lang)那里接受一个疗程的诊治,并与对方进行了非常有趣的对话。由此黑塞对荣格的著作,尤其是所谓“深邃心理学”和下意识力量理论发生了兴趣。荣格的学说对黑塞提出的“内心道路”概念,具有明显的影响,黑塞把“内心道路”看作摆脱生活矛盾的唯一手段。他还在著作中使用了荣格的术语。参见苏联科学院编,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德国近代文学史》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882页。,但他们通往中国的精神航道终究不再可能如以前一般畅通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因为一战导致的重大变化,整个欧洲人产生了彻底的文化自我质疑,德国人更是充满精神上的衰败颓废。个体当西方崩裂之际的痛苦以及黑塞、荣格这代人的整体迷惘与困惑,在卫礼贤的身上因了特殊的时机而凸显得非常明显。荣格对这一问题的捕捉极为细腻而准确: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无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设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时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在此占东方因素的上风。如果这样的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无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之后,我曾试图让他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我说给他的话是:“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
他回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象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呢?”②[瑞士]荣格:《谈理查德·威廉》,[瑞士]荣格(Jung,Carl Gustav)著,刘国彬等译:《回忆·梦·思考——荣格自传》(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第603—604页。理查德·威廉即卫礼贤。
这段文字兼有叙述与分析,很能表现作为心理学家荣格的特点。一方面,数次旁听讲座与提出忠告的事实说明荣格与卫礼贤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诚如他自己所言,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卫礼贤③参见刘耀中、李以洪:《荣格心理学与佛教》,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6页。。另一方面,他揭示出卫礼贤在复归德国文化及学术场域后所表现出的矛盾状况背后的深层文化接受与转换问题。按照人类学的观点,在两种文化传统之间发生矛盾、碰撞乃至冲突,是常态,也是所谓“濡化”与“涵化”的张力,其中蕴含着个体、文化之间的博弈,其实也是相生相就之过程。个体不可能脱离语境和文化母体而存在,文化也不可能不借助个体而实现其实体发展。
在荣格与黑塞这些日耳曼文化主流精英的眼光中,卫礼贤无疑具有对“中国文化”的绝对话语权。在后者看来:“卫礼贤是一位先驱,是一位榜样,他是一位和谐的人物,融合东西方、融合沉思与行动。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几十年里,他深入接触、研究古老中国的智慧思想……他并未忘却或失落他的基督信仰,也未失去他带着施瓦本烙印的德国风格,没有失去或忘却耶稣、柏拉图、歌德……他一步步在促进着两种伟大的理想的融合,在自己身上融合了中国与欧洲、阴与阳、思考与行动、沉思与效用。因此产生了他美好、温婉的教育笔调,比如《易经》中的语言,我们从中听出了歌德与孔夫子的声音。”①[德]黑塞:《一位沟通中国与欧洲的使者》,[德]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Michels,Volker)编选,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China:Weisheit des Ostens),第157—158页。德文为:Er war ein Vorläufer und ein Vorbild,ein Mensch der Harmonie,der Synthese zwischen Ost und West,zwischen Sammlung und Aktivität.Er hat in China,hat im jahrelangen inti⁃men Umgang mit altchinesischer Weisheit und im persönlich-freundschaftlichen Austausch mit der Elite chinesischer Gelehrs⁃amkeit weder sein Christentum noch sein schwäbisch-thüringisch geprägtes Deutschtum,hat weder Jesus noch Plato noch Goethe verloren und vergessen,noch seine gesunde,kraftvolle,abendländische Lust an Wirken und Bilden,er ist keinem An⁃ruf des aktuellen Lebens entzogen,ist weder einem denkerischen noch einemästhetischen Quietismus erlegen,sondern hat,Stufe um Stufe,die Befreundung und Verschmelzung der beiden großen alten Ideale in sich vollzogen,hat China und Europa,Yang und Yin,Denken und Tun,Wirksamkeit und Beschaulichkeit in sich zur Versöhnung gebracht.Daher der Tonfall seiner schönen,sanft belehrenden Sprache,etwa im IGing,aus dem man Goethe und Kung Fu Tse zugleich heraushört,daher der Za⁃uber,den er auf so viele Menschen hohen Ranges in West und Ost geübt hat,daher das so weise wie freundliche,so wache wie schelmische Lächeln seines Gesichtes.“Ein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in Hsia,Adrian:Hermann Hesseund China-Darstellung,Materialien und Interpretation(《黑塞与中国——介绍、资料与评论》)。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4.S.322-323.正是在卫礼贤身上,黑塞看到了二元相融的美丽面相,这当然也是事实。但还有另一份真实,这就是荣格看到的情况,卫礼贤自身也在承受着“一体二魂”之苦,或许这种痛苦只要身在尘世就很难避免。卫礼贤的最根本问题,或许正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聚焦于其一身,所以其承受灵魂分裂痛苦之烈,恐非常人可以理解。一方面,卫礼贤以极为旺盛的精力和理想情怀投入他所热爱的中国文化译介事业和德国的汉学建设,但另一方面,他恐怕也不得不和世俗的攻击贬斥之声作战。正如黑塞也意识到的那样:“好些没有机会像卫礼贤那样亲身体验中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对这位中国官员,这位我们时代最中国化的欧洲人,展开闻所未闻的、极端野蛮的攻击。卫礼贤以他的中国方式微笑着,友善地面对种种不断的误解,静静地进行他伟大的工作,德国评论界还没有意识到他成就的广度和深度,他可以等待,受益于他的工作的将不仅仅是一代人。”②[德]黑塞:《卫礼贤最后的译著》(1930年11月),[德]黑塞著,[德]孚克·米谢尔斯(Michels,Volker)编选,谢莹莹译:《黑塞之中国》(China:Weisheit des Ostens),第151—152页。这种精神分裂之苦,或者思想与行动不得不承受的割裂之苦③吴宓的“二马之喻”或可略作注脚:“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睹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7页。,在荣格、黑塞那里,恐怕都还不能完全理解。当文化相聚相触相撞之际,亦是其化合为新文化和新精神的过程,它绝非简单自然产生,而往往必由此痛苦、艰难的历程而通往真正地创生分娩之路。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译介当然少有可比者,但中国文化毕竟博大精深,其进入德国或西方的路径仍将漫长而曲折,欲以一人之力强为之,未免过于急切而难能,何况还有现实场域的诸多制约,自身身体条件、家庭状况的诸多限制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卫礼贤还是未能参透中国文化的根本和要义所在。与其将希望都落在某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还不如更尝试用观念侨易的长时段眼光来看问题,如此当更能理解和摆正一个个体,即便是再杰出甚至伟大的个体在“人类历史巨链”中的位置。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西方(或具体而言在德国)其时虽已有强烈的认知中国作为异文化资源的意识,但从根本来说,“筑渠引水”的整体语境尚未具备。或者我们尝试从思想史角度考察之,其时欧洲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其“道术之裂”。说到底,科学只是表层之技;大道之寻,才是根本之道。而这个“道”是什么,在现代性的挑战面前,东西方其实都深感惶惑。并非仅是西方知识精英感到困惑,东方知识精英更是痛苦万状。因为后者要面临的,更是直接的家破国亡“烽火连三月”。长久以来,西方有两大根本传统支撑着整个文明社会的运行,即基督教(神学)与希腊文化。但随着科学的兴起,宗教的独尊地位日益受到挑战,甚至被视作现代性与科学的绝对敌人。这尤其表现在知识精英对基督教的基本态度上,如黑塞早年拒绝神学院教育。卫礼贤即便是受了神学教育,且长期以传教士为业,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相信基督教可以归化万方的理念,故才未曾发展一个中国人入教。可以认为,宗教的现代生存方式出了问题,而现代科学的方式也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结果。
落实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欧洲与德国社会历史语境,则是帝国消解与纳粹上台的大势迁变。荣格与黑塞在此似乎略有南辕北辙之意:当黑塞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人道理想,从德国转居瑞士,远离了政治主导的场域,荣格却由瑞士亲近德国,似乎有与纳粹发生关系的可能,其实在思想渊源上确实颇多牵连。
荣格活了86岁,黑塞活了85岁,他们甚至都高寿于歌德(83岁),可以更近地望见“米寿”高龄。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借助上帝赋予他们的天年,在思想的试验场上披荆斩棘,更上层楼。他们最终也没能超越歌德,只是在这条寻道的途中踯躅而行,坚守信念而已。这无疑是极为遗憾的,或许其中缺少的最重要的环节恰恰就是卫礼贤。如果他不是那么早就英年早逝,如果他能与荣格、黑塞继续结伴而行到“向米之龄”,那么多出来的30年光阴一定会是不一样的。还可以有多少的中国智慧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代精英的思想蓄水池呢?并非是因了卫礼贤之逝中国知识资源就枯竭或断流了,但流向的不同和船夫的技巧,确实能决定航向的正确与否和化合程度是否能达到恰到好处之分寸。应该说,卫礼贤凭借其对中国文化资源的优良整合与积极参与,相当成功地介入了德国乃至西方知识语境的文化重构进程。这一点,不仅通过与凯泽林、帕盖特的交往得以体现,也不仅通过对辜鸿铭思想的德译与推广而推波助澜,更重要的是,通过与黑塞、荣格这样处于知识场域中第一流精英人物的交谊,直接推动了思想史的进程。所以,就此而言,他的功用是双向性的:在德国语境中的影响是他的主动介入,在中国语境里的功用则为“无心插柳”。事实上,卫礼贤的思想路径近于“秘索思”一路,有论者甚至认为:“卫礼贤在很多方面都是时代之子。在西方,他跻身于思想家的行列,能与持活力论的杜里舒、生命哲学的鲁道夫·奥伊肯、智慧学派的代表凯瑟林伯爵,特别是荣格相提并论。”①[德]朗宓榭(Lackner,Michael):《卫礼贤:一位“汉化”了的德国翻译家》,[德]朗宓榭著,徐艳主编:《朗宓榭汉学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这段评价很重要,不但将卫礼贤纳入西方思想家的行列,即由边缘而主流,也展现了同时代思想者的群像图。奥伊肯(Eucken,Rudolf,1846—1926)、杜里舒(Driesch,Hans,1867—1941)、凯泽林(Keyserling,Hermann Graf,1880—1946)、荣格、卫礼贤等人确乎构成一条清晰的线索,我们或许还可就这一名单进行补充,譬如潘维茨、帕盖特、奥托等都应视作同谱系中人。这条路径,在我看来,就是“秘索思”的思想史路线,是注重感性、强调信仰、主张直觉的致思路径。
由此我们可以见出,东海入世,其理彰明;而西海寻路,则殊为歧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里,尤其是欧洲,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具体历史背景。自古希腊始,秘索思—逻格斯的二元路径就发生着错综复杂的一元—二元的变换关系,到塞玛的出现则第三维若隐若现,都在规定着后来可能开辟的致思路径。卫礼贤的思路和知识来源,即便仅局限在德国思想史上的中国认知这一路径上,也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特殊的本国思想史源流的。而这种对中国异文化资源的重视和积累,是与日耳曼民族的求知意识和寻道自觉密不可分的。或许还是借用荣格的表述可以更接近一些对原初之道的探寻:“若我要以这个时代的精神来表述,我就会这么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我将要对你们宣布的事。证明对我是多余的,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还有另一种伟大的思维,也就是任何能把握所有当下的深层意义的思维。这个时代的思维只知道实用和价值。”①[瑞士]荣格:《序:来者之路》(1915年),[瑞士]荣格著,林子钧等译:《红书》(Liber Novus),第4,5页。荣格还认为:“这个时代的精神让我想见识超理的高大广阔,却不是它的微小。深层精神却战胜了这种傲慢,我必须像咽下不死药一样,吸收它的微小。它可能会灼烧我的内脏,它的确并不光彩、不算勇敢,甚至低微可笑、让人反感。但是深层精神的钳子紧攫着我,我得喝下这苦杯。”②[瑞士]荣格:《序:来者之路》(1915年),[瑞士]荣格著,林子钧等译:《红书》(Liber Novus),第4,5页。雅斯贝尔斯(Jaspers,Karl,1883—1969)《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书名更能彰显这种时代症候,他在所撰《英译本重印前言》中说:“本书写于1930年。当时我虽然相当了解法西斯主义,但对国家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我还在为书稿的完成而喜悦时,十分震惊地听说国家社会党人在1930年的选举中赢得了最初的胜利……为了阐明那个时代,我利用了仅属于那些岁月的事实材料,因而本书在许多方面都感染了当时的气氛。”③[德]雅斯贝斯著,王德峰译:《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5页。理解介于时代精神和观念侨易过程的平衡点,或许是我们切入那代精英人物西海寻路之迷宫道路的最后锁钥。
“西海寻路道术裂”,或也正反映出西方知识空间的这种迷离和困惑感,正应了斯宾格勒的那本书名《西方的没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许正是“东方的复兴”的某种征兆。阴阳之间总是彼此渗透、相互转化的,在人类文明的这个太极图谱系中,虽然未必就一定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确实有一个交替消长的过程。这或许正是人类文明的自我修复机制在起作用。当以卫礼贤、黑塞、荣格等为代表的现代欧洲知识精英在调和东西的道路上孜孜不倦,以深度探索的方式进入中国、印度等支柱核心体的东方文化之中时,表现出的或许正是那种第三极流力因素的生命力及其作为阴阳鱼的游移可能的冲击力。所以,另一个有待开掘的层面或许更是,“东海问道学力弈”。我们看到在亚洲世界里,无论是泰戈尔、甘地、阿罗频多等的努力,还是辜鸿铭、孙中山、蔡元培等的起落,甚至如冈仓天心、伊藤博文、中江兆民等的跌宕,那是另一幅需待细究的场景了。
人类永远会在无穷的征途之中,对器物、制度、文化等的追索也概莫能外。设若如此,则卫礼贤与黑塞、荣格等因知识和思想交谊而展开的寻路征程,也就不仅属于他们个体,正如同他们所共同尊敬的歌德那样,他们也会意识到:“人类会变得更聪明,更具识别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有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时代如此。我似已预见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上帝不再能从人类身上获得乐趣,那就必然会毁灭一切,求得更生冲创之力。我相信,这一切都已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日,必将开始又一轮新的恢复冲创之力的时代。但距离那刻肯定仍有漫长的时日,我们依旧可在成千上万的年头里在这块可爱的、古老的土地上享受生活,就像现在这样。”④德文原文为:Aber laßdie Menschheit dauern,so lange sie will,es wird ihr nie an Hindernissen fehlen,die ihr zu schaffen machen,und nie an allerlei Not,damit sie ihre Kräfte entwickele.Klüger und einsichtiger wird sie werden,aber bess⁃er,glücklicher und tatkräftiger nicht oder doch nur auf Epochen.Ich sehe die Zeit kommen,wo Gott keine Freude mehr an ihr hat und er abermals alles zusammenschlagen mußzu einer verjüngten Schöpfung.Ich bin gewiß,es ist alles danach angelegt,und es steht in der fernen Zukunft schon Zeit und Stunde fest,wann diese Verjüngungsepoche eintritt.Aber bis dahin hat es si⁃cher noch gute Weile,und wir können noch Jahrtausende und aber Jahrtausende auch auf dieser lieben alten Fläche,wie sie ist,allerlei Spaßhaben.“1828年10月23日谈话,Eckermann,Johann Peter:Gespräche mit Goethe-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1982.S.600.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交流、融汇和再生之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显然至关重要,他们给后来者展示的行路之难、向道之诚,也就有了非同凡响的“范式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