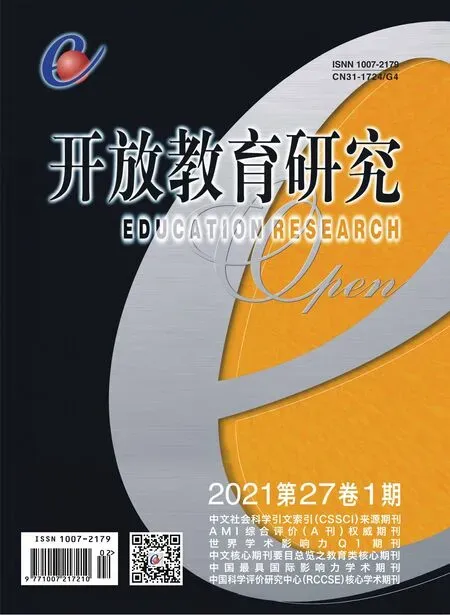远程在场的知识延展与存在收缩
——对在线教育的存在论阐释
2021-01-03张敬威苏慧丽
张敬威 苏慧丽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
在线教育是基于网络技术的教育模式,具有“非真实”与“远程在场”等特点,它通过人工技术对人的自然身体进行数据化的替代性复制,一方面为教育提供超越此在时空的可能,另一方面对现实教育全方位的挤占要求教育必须警惕学生面临存在收缩的危机。
一、知识传播的有条件延展:当远程在场得以可能
随着通信技术与在线教育的发展,教学与学习更具延展性,教学场域的远程在场得以可能。然而,伴随着学生知识的延展,学生在虚拟情境中获取的知识也呈现出片面而断裂的特征。
(一)技术成为身体的延展性工具
在线教育中我们能够通过网络跨越地域的限制实现远程的视频与音频等多维交流,现代化的非自然技术重构了教学的场域,也重新定义了学生在课堂中的身体构成——技术成为身体延展的同时向学生提供着具身经验。学生的身体本身是一种作为经验存在的“活的身体”(corps vecu)①,而在线教育为经验的身体提供了可被感知的延展性工具。工具自诞生伊始便承担起作为身体延展的作用,比如当猩猩想吃树洞中的蚂蚁而手臂又无法够到时,便使用木棍插入洞中将蚂蚁沾出来吃,此时木棍便成为猩猩身体的延展,承担了猩猩手臂的作用。正如海德格尔提出的“锤子”与梅洛-庞蒂提出的“盲人的拐杖”,他们均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成为身体的延展。在线教育为身体提供了更大范围的延展空间,使学生的“视觉”与“听觉”得以延伸。
在线教育为学生提供了远程视听课程内容的可能,也为师生提供了远程在场的技术支持,但是远程在场的存在与交流形式自其出现伊始便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小孩的推断和他的实践思维首先具有实践和感性的性质。感性的禀赋是把小孩和世界连接起来的第一个纽带。实践的感觉器官,主要是鼻和口,是小孩用来评价世界的首要器官。”(马克思,2016)当人成为远程在场的存在,便限制了学生认识世界的部分感官——“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2016),“人的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就是人通过与世界多式多样的关系,全面地表现和确证自己的本质的完满性”(丁学良,1983)。当人被局限在有限维度的虚拟环境中,就成为单一性关系中的一部分,人也不再是全面与完整的人,而成为碎片化世界所规定维度下的人。在这种规定的碎片化世界中,人的认知能够得到一定范围的延展,却导致了认知的整体性与深刻性不足,从而使人知识内化的过程被削弱,出现片面与断裂的特征。
(二)片面而断裂的知识内化
知识的内化往往源于自我的同一性,即我的意志与我的行为的同一性。动作对思想反馈,从而产生一种主客观的互动关联,在认知冲突与顺应中完成内化。知识的内化过程是多感官协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事物因果联系的反馈性结果,因此其产生需要在一个实存完整的真实世界中得到全面且真实的因果性反馈。教学同样适用这一规律。学生对知识的内化需充分调动其官能及其所拥有的经验,在感知与冲突中再思考,在矛盾中完成经验的修正与再认识。
在线教育的弊端有两项:一为反馈的整全性缺失,二为反馈的因果关联性的呈现缺失。在线教育提供了得以延展的界面化图景,使得教育的可视、可听的范围更广延,却削弱了教育的一项重要环节——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学生在界面化操作中获取了少量的界面反馈,对五官与统觉的刺激仅仅来源于界面本身,这样教学就出现了一种对象化的偏移——教学的对象从知识或事件偏移到了界面本身。学生从学习知识或事件转为了对界面的关注,而界面作为知识与信息的载体与表现形态,仅仅呈现了表象化与可视化的内容,人与世界的关系被缩减成人与界面的关系——世界对人的因果性反馈被简化为拟真程序的界面反馈,人开始在被削弱了整全性与因果性关联反馈的界面世界中出现眩晕。
表象内容的大量碎片化呈现使学生的知识掌握出现弥散状态,缺乏因果联系的认知与主客冲突的内化过程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名称”的理解层面,而无法达到“概念”②的掌握程度,也无法形成内在的逻辑掌握。远程在场的学习形态在使学生拥有了更为广博的见识的同时削弱了学生对这种见识内化的过程性训练,以及在思维层面的冲突性认知步骤。碎片且弥散的知识成为学生存储的对象,而非内化理解与应用的对象。
(三)缺乏应用的知识存储
当教育成为一种界面化的存储方式,学生所接触到的知识沦为与经验关联更为遥远的符号,那么学习便成为一种以符号为对象的学习,而符号与世界的联系在学生的感官中消失了。丧失了内涵的符号便沦为符号本身,“知识”也被削减为单纯的“识”③,学生掌握符号对应的概念,却无法联系符号所代表的世界,符号的意义与经验脱节,学生进入符号世界却脱离了现实世界与真实经验。学生沦为了存储的容器,其所掌握的符号关联也成为仅存于虚拟世界呈现的经过教育者筛选后的片面性关联,由此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虚拟的世界成为学生的真实场景。学生通过教育者的训练适应了虚拟的教育场景,而教育者却忘却了虚拟场景仅仅是为呈现现实中某一规律或特征而塑造的场域。虚拟场景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虚拟的因果联系,从而对实存的因果联系进行分析,然而这种虚拟的因果联系与真实世界的经验脱节后,就不再具有对实存因果联系的代表性,使这种虚拟的因果联系丧失了其对真实世界指导的基础。
当学生对知识的存储形式沦为脱节于真实经验的存储,那么知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将会失效。当“形而上”脱离了“形”,那么“上”就丧失了意义。存储本身并不具备主体性价值,作为纯粹的知识载体其仅仅是一种手段或工具。“人是生活在目的的王国中。人是自身目的,不是工具。人是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自由人。人也是自然的立法者。”(康德,2003)真实经验是人作为目的性存在的重要支撑,是人成为自然的立法者的前提。教育作为培养人成为人的实践活动,保障人的知识与经验的关联性、尊重人的完整性与目的性是其基本要义。面对在线教育带来的延展性便利,保障学生的真实体验,是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二、存在的收缩:知识碎片化与弥散化溯因
以存在论视角进行分析,在线教育产生的知识碎片化与弥散化问题、知识与真实经验脱节问题,其内在原因可归结为“存在的收缩”。
(一)空间收缩导致的认知局限
当教育情境从一个可感知的真实场域被缩减为界面化的呈现时,其空间感便消失大半。“如果间隔(intervalle)在突然变为界面(interface)时,变得苗条,‘更加苗条’了,则事物,也就是被感觉到的客体,也同样变得苗条,失去了它们的重量,它们的密度。”(维利里奥,2004)存在的收缩为教育带来两项挑战:一是学生可感知深度的确定,二是教师拟呈现的与学生重点感知的一致性对接。被电子界面分裂呈现的世界投影给予学生一种不能被察觉到的视觉纬,其中唯一的停止成为了当前瞬间的一种类癫痫发作的缺席,电子界面化的呈现给予观看者一种无休止的镜头造成的错觉(维利里奥,2004)。学生在这种错觉中逐渐习惯,将把不在场当作在场,由而产生一种存在论的替代,这种电子界面化的扩张隐匿了空间收缩的同时加剧了人的生存空间的收缩(张一兵,2018)。
当电子化的远程界面承担身体的工具性意义,延展了身体的同时也将身体的感知扁平化了。当学生习惯了电子化学习,将虚拟世界掺杂于真实生活时,相当于被装上了电子化的义肢——数字化世界成了健全的电子化残疾。当身体的延展变得轻而易举,就会削弱主体到客体之间的路程(trajectivite)④,若没有路程,则丧失了人在客观世界中的交融过程,也就意味着感知与经验在进行与反思双重层面的压缩——线上技术带来瞬时性的同时使可感与可思的区间减小,使思想习惯于无法跟随通信的速率而变得麻木与机械,从而产生一场源于路途性丧失导致的人类环境的“景深”⑤的衰变(维利里奥,2004)。路途性的消失直接导致了空间存在的收缩,而空间存在的收缩则直接关涉教育环境的“景深”——学生的感知的深度。
这种精神的缺失正是胡塞尔(1988)所指的“已经没有活生生的体验了……已经把意义抽空了”。而此类空洞却在学生生活与学习中不断重复,成为学生的认知习惯,不断地压缩学生的存在空间与对存在的认知。这种存在认知的压缩在在线教育中变得更为突出,扁平化的内容被快餐式地重复,在教师拟呈现与技术可呈现的双重制约下,学生知识掌握的碎片化与弥散化、认知的空洞化正在加剧。
(二)身体缺席导致的主体冲突
远程在场意味着身体的缺场。尽管技术作为身体的延展,但身体仍然承担作为交往效应的载体。传统教学常常借助非语言符号进行完整与丰富的表达与交流,包括动作、表情、眼神等,并且这一系列符号在不同的时间、场合、人群背景下表露不同的含义。多维共存的交往方式呈现的是一种整体性信息,使人在多维度接受信号的同时对对方进行综合判断。然而,身体的缺席使交流者的交流方式由多维度变成单一或有限维度,表达者尽管在远端仍保持着表情、神态、动作等信号的持续输出,但是它们在传输中都被屏蔽掉了,而接收者仅仅收到了特定维度信息,从而出现教师拟呈现与学生重点感知对接的偏差。
由此学生所处空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冲突:教师的综合形象消失了,学生的身体感却持续在场。学生接收远程在场的虚拟信号时却感受此在真实场域对感官带来的刺激。个体在通信穿越中的碎片化呈现使多维的生物性与物理性存在变为符号性存在,符号进行综合情境表达带来了通信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交流,伴随而至的是感知层面的虚拟与实在相交替的眩晕感(闫旭蕾,2009),此时对学生而言,存在着真实世界与再现世界、主动性与互动性、在场与远程在场之间的多维两重性(维利里奥,2004)。由于主体接收信号的双重性,导致的主体认知判断的双重性,认知的佐证材料由此在感受与接收此在信号的综合变为了此在感受与远程信号的综合,因而出现了直接经验与上手世界的分裂,也衍生“分立出行动的当下能动性和远程行动的互动特征”(张一兵,2018)。
在线教育的工具性意义在此维度中与梅洛-庞蒂所指的“盲人的拐杖”有别。“盲人的拐杖”作为身体的延伸,使盲人的触觉由手延展到拐杖的尽头,然而盲人所处的场域仍然是拐杖所在的真实空间,“此时此地”的条件致使拐杖所接触的实体盲人仍可通过空间内的其他信息加以佐证判断,而在线教育则出现在近乎于“此时”而非“此地”的情况下。当拐杖作为介质承担的作用是以“此地”的延伸综合“此地”的统觉,而在线教育则无法达成这一状态。
(三)情境残缺导致的片面发展
在线教育呈现的是一种定向化的残缺情境,其目的性呈现与教学目标契合度越高,教育的有效度越高。在线教育的特定情境一方面受限于客观载体的技术限制,一方面来自于施教者的片面化给予。当学生仅仅接触施教者所设定的情境,这种定向的残缺情境就构成了学生的全部学习范畴。这种取代了真实空间的虚拟情境设立的目的在于:通过虚拟呈现使学生掌握一种抽象认知,并力图使学生可以通过该认知指导真实世界的实践。若要达成这一目的,需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学生对抽象认知拥有真实的经验基础,使该抽象呈现与现实世界产生确切的关联;其次,一系列虚拟呈现具有逻辑关联,能够通过综合得出具有逻辑性的抽象结论,而非直接呈现结论。
在线教育与人的认知具有相向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技术产生与改进的目的在于为人服务,所以其发展的核心基础是人类信息交流的感官平衡;另一方面,学生接收在线教育会在不断的认识冲突中向已改进的新环境顺从和适应,即技术趋向人性化的同时人性顺应技术性,从而致使一个可预见的教育危机逐渐清晰化:学生在人与技术的特征更为趋近的环境中局限了对存在的认知。在线教育为人提供了一种“物的尺度”——决定了人具有认识活动的可能,而“人的尺度”则超出了“物的尺度”的局限,具有反思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特征(苏慧丽等,2019)。定向的残缺情境会加剧人的定向残缺,人的片面化同样会致使情境的定向残缺。
由于在线教育所呈现的定向残缺情境是现实的片面化映射,在线教育与现实世界具有有待于被充盈的拟真关系。这种拟真关系为教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增大了可教、可呈现的范围,同时也付出了真实性危机的代价,所以在线教育的价值取决于学生对真实世界的把握。实在世界是在线教育的基础与支撑,如果在线教育妄图抛弃在场教育独立进行,就会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前提性。
三、重述“在场”的意义:以此在真实引领彼在虚拟的教育
远程在场的在线教育使学生面临经验与认知断裂的危险,给学生带来存在感知收缩的危机,这就不得不对在线教育的适用情况与适用规定进行批判性思考。在线教育的先天劣势在于真实经验的缺失,由此重述“在场”的意义尤为重要,应以此在真实引领彼在虚拟的教育。
(一)区分现实与虚拟的课堂
在线教育为教师与学生都提供了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这种现象学意义的身体以符号化的形式承担起了主体功能与技术功能的双重任务。施教者的意识在其所在场域生发,其所处的知觉场决定了意识生发的重要源地,而受教者出现一种现象场或 “身势圈”的差异性冲突——他者场域下形成的经验性规律在本土场域中的接受性冲突,由此所传递的仅仅是信息符号本身,而在场域的变换中筛滤掉了体验性与感知性的传递。当学生适应于这种缺乏感知性的符号传递就会出现“可思”与“可感”一致性的削弱,而新的一致性的出现会使学生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当学生习惯于将其知觉现象场中的因果联系归结为虚拟场域中的联系时,其对现实世界的因果判断就会出现偏差与断裂。
当学生将其主观意志与远程在场的能动性反馈结合起来并作为意识指导实践的主要依据,那么学生就会脱离实存世界的因果规则,尽管虚拟条件下部分行为不在此在发生,却仍然需以此在为基础。远程在场是现实在场行为的延伸而非可以独立存在的能动表现,当在线教育无法使学生区分远程在场与在场形成的能动性反馈,就会面临将虚拟操持看作真实行动的危机,进而导致学生对经验真实性的怀疑。
所以在线教育开展的前提是区分现实与虚拟课堂,使教师能够清晰地区分真实与虚拟的教学手段,从而有目的地搭配虚拟与真实的教学手段;使学生能够明晰地认识在线教育的远程性与虚拟性,能够区分虚拟情境的因果关系与真实情境的因果关系的差异,并且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与场域进行差异性应用与实践。这便要求课程设计对虚拟场域与真实场域教学手段的功能性区分与体系性设计,明确区别性的同时挖掘关联性,发挥两种教学手段的比较优势,实现互补效果。
(二)明确虚拟是现实的辅助教学
学生意志与行为的同一性是其行为得以通过虚拟手段延展的基础,这种虚拟手段作为为目的服务的工具,其被关注的重心往往在于目的而非可接受性,仅仅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数字化符号不具备传播意义,因为其丧失了交流的中介功能。这也在根本上决定了在线教育的辅助地位,明确了在线教育的延展性作用与价值的同时规定了其指向与目的。
传统教育早已出现了拟对象的教学方式,尽管受技术的限制缺乏一定的真实性,但仍然可以通过情景构建等方式使学生拥有一定的“沉浸式”体验,其自始至终都被定义为一种使学生获取知识、能力或培养思维的辅助手段。而在线教育由于其沉浸性与真实性的提升,为教学带来了便利性与高效性,使教师与学生在虚拟真实的意识迷思与经验幻象中逐渐忽略了技术被创设伊始的目的。
人类接收的外部信息,约65%通过视觉通道,20%通过听觉通道,10%通过触觉通道,2%通过味觉通道(陈月华,2005)。人作为多感官综合接受体,直接规定了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对人的价值。真实的外界是人的生存环境,人需要在实践中同化、顺应并平衡于外界的客观定在⑥,而虚拟世界作为外界实存的投射自产生伊始就被赋予了服务人类的技术目的。在线教育技术的价值在于能否更契合地反映技术使用者的预期目的,能否更完整、准确地投射真实世界的实存状态,这也就规定了在线教育技术是以真实环境为基础的,是真实世界的投影,其目的在于促进人对实存世界的认识。所以教学应明确拟对象是作为把握真实对象的中介而存在的本质,在线教育是现实教学的辅助。
(三)以真实经验引领虚拟感知
身体技术使我们的肉的形而上学结构具象化并予以扩大,其既是可见他者的又是他者可见的,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镜子( Merleau-Ponty,2007)——即身体具有感知层面的反身性。所以,技术虽然可以设计或创造有利于学习的环境,但不能为学生创造学习,因此不能将经验(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与现象本身混淆起来(拉斐尔·A·卡沃等,2020)。学生对世界的认知源于其对周遭环境的真实感知,这就要求教学要有真实的根源与经验的过程。教学应尊重学生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的认识世界的过程,因而课堂教学要努力还原知识产生、发展的情境,从而使学生学习完成一种类似于探索与发现的过程性复演,在意识、思维与经验层面完成具有因果关系的训练,只有拥有对真实世界经验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能力,才能真实地辨别虚拟的个别所代表的真实的一般。
教学应突出真实经验的归纳性教学与凭借虚拟感知技术的延展性教学的结构性关联,通过真实体验——经验归纳——技术延展等步骤引导学生。真实场域既要引导学生完成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在归纳中使学生认识虚拟与现实、符号与实体、个别与一般的差别,同时加深从场域之定在到意识之运动的因果性关联,核心是在虚拟场域中结合学生对真实经验的归纳基础,使学生拥有更广博的见识与更具延展性的深思。
在线教育有助于将抽象对象具象化、将模糊对象实例化,从而使教学更具情境性与具象性,使学生更易理解。但是,这种“拟对象”的呈现方式易于使学生养成一种仅适合于“拟对象”构成的场域中的思考逻辑。当学生带着这套逻辑方法回归到真实世界时容易出现迷幻与错乱的异方法域问题。教学应使学生在对真实对象的操作体验中,在真实情景的认知冲突中坚定其认识论基础,夯实真实经验在精神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于伟,2017),也就是说,要在保障对真实经验正确把握的基础上以在线教育增强学生的认知,达到以真实经验引领虚拟感知的目的。
[注释]
①“活的身体”指作为身体的经验存在,区别于政治、文化与社会构建而存在的身体。
②2015年6月4日,孙正聿在“东师人文讲坛”讲座中从“名称与概念”层面阐释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理论自觉,指出“概念”与“名称”的内涵区别:“概念”是深入的理解,“名称”仅仅是对字面的认识。
③“知识”的“知”字由“矢”和“口”构成。“矢”指“射箭”,“口”指“说话”,“知”指说话像射箭一样一语中的;“识”字从言从戠,“戠”字本指古代军队的方阵操练:“音”指教官口令声,“戈”指参加操演军人的武器,原指整齐划一的动作,衍生为区别、辨别之意。当学生缺失了基于经验的主体性思考,所能够掌握的便仅仅是认识与辨别的能力。
④此处指存在论意义上的“路程性”的消失,并非常规所指的路程性,而是路程的存在论意义。
⑤“景深”原意是指在摄影机镜头或其他成像器前能够取得清晰图像的成像所测定的被摄物体前后距离范围,维利里奥以此比喻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关联性。
⑥ 定在,是黑格尔的哲学用语。黑格尔把存在作为第一个逻辑概念,但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是纯粹的无。由存在过渡到空无是变异或生成,变易就成为第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即具有质的规定性。这样,存在就成为有特定规定性的存在——定在(参看于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