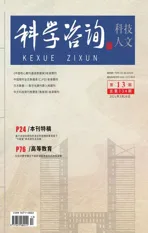太宰治小说《越级申诉》中犹大形象构建
2021-01-02赵月娥
赵月娥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越级申诉》是日本作家太宰治于1940年以《圣经》为素材创作并发表的短篇小说,与《富岳百景》《女生徒》《满愿》《奔跑吧,梅洛斯》等共同构成太宰治中期优秀小说群。该小说采用犹大独白的叙事策略,悲痛地诉说着自己对耶稣的复杂情感,并为自己的卖主行为进行辩护。这篇圣经故事新编式的小说,对原典中的背叛者犹大进行改写,因题材和写作技巧的创新以及深刻的立意获得广泛肯定。国外《越级申诉》研究主要涉及主题研究、意象研究、叙事研究等,而国内有关《越级申诉》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顾杨妹(2013)认为,犹大即作者化身,太宰治是借犹大表达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进行了自我剖析[1];肖书文(2016)指出犹大正是作家的性格形象,认为太宰治幼年经历及对左翼运动的脱离是其创作《越级申诉》的心理原因[2]。上述研究结论大多雷同,对犹大的形象构建与太宰治基督教信仰间的关系未能深度探讨。因此,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析太宰治通过犹大的形象书写所体现的基督教思想。
一、犹大的形象构建
《越级申诉》小说结构主要由犹大独白的若干事件和由此产生的复杂心理活动串联而成。具体来说,小说对犹大形象的构建主要依照时间顺序,从“五饼二鱼”“油膏耶稣”“神殿逐商”“门徒洗脚”“最后晚餐”这五个圣经中代表性事件来完成。
小说以第一人称独白方式讲述故事,犹大自我形象的描述是从他对耶稣过往的控诉中逐渐清晰起来的。犹大认为自己被耶稣“恶意使唤了多次”,在门徒们潦倒到连面包都没有吃的时候,是犹大利用商人的智慧成就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救活了门徒的性命,自己才是完美的奉献者。在情感上,犹大抛弃了父母及赖以生存的土地主动追随耶稣,仅仅因为纯粹地爱着耶稣并且只愿“陪在他身边,听他的声音,望他的身影”。当犹大敏锐地观察到耶稣看玛利亚泛红的脸颊时,便立刻表明自己在男女之事上“从未对女子动过心”,以示自己对耶稣情感的专一性。犹大认为自己对耶稣的爱是纯粹的,在爱的欲望面前他不怕任何刑罚和地狱,是个完全的无私者形象。另外,犹大还认为自己具备一种聪明的现世生活法则,即“对别人低声下气,再踩在别人头上”。耶稣神殿逐商时,犹大不忘嘲讽耶稣和众门徒的愚蠢,认为他们无法掌握世俗的圆滑,一种智慧商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描述小说高潮情节的“门徒洗脚”和“最后晚餐”中,犹大为自己背叛者的形象再次辩护,详细叙述其内心忏悔的挣扎历程,试图证明其卖主行为是可被理解的。
众所周知,第一人称小说创作最大的好处是代入感强,但缺点是视角狭窄。因此,当摒弃第一人称叙事干扰站在读者角度阅读文本时,我们便可发现犹大并非无私、奉献和充满智慧的,反而是一种独占者和利己者的形象。比如,小说中玛利亚与犹大被描写成一种爱情竞争者关系。在油膏耶稣时,犹大认为玛利亚头发擦拭耶稣双脚的行为是“何等诡异”并斥责了玛利亚,并托词香膏可卖三十两银子赒济穷人,但耶稣却表示“不许责骂这位女子”。由此犹大断定耶稣已对玛利亚产生暧昧并承认这是一种来自追求者的“嫉妒”。而门徒狂唱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来迎接耶稣时,这种行为被犹大解读为只是为了从耶稣那捞些好处的功利信仰,因此觉得门徒根本不配获得来自耶稣的庇护和关爱。
又如,在犹大向耶稣表明自己抛弃了双亲与土地选择跟随时,耶稣说道:“彼得和西门,雅各和约翰都是赤贫的渔夫,他们都没有能够安度余生的土地。”可见,耶稣早已洞察犹大的跟随动机从开始就不纯正,犹大抛弃家业的爱是一种小我的爱,是渴望回报的爱,是希望追随能换来反馈的爱。犹大不止一次说耶稣是个“美好的人”,但这种美好只是体现在耶稣曾经对自己温柔与爱护的行为反馈上。而实际上耶稣的美好与爱还具备公义和圣洁的特质,比如耶稣对门徒的呼召具有绝对的主动性,他即便知道犹大是要卖他的人却仍呼召了犹大。耶稣作为信仰层面的绝对权威者和至高者,他所彰显的爱是一种大爱,显然不同于犹大理解的狭义的爱,但犹大并未理解。当其执迷地沉醉于无法获得耶稣独有之爱的挫败感中时,即便他感受到了耶稣的温暖安慰,他的心理表现却是“想放声大哭,只求你懂我的寂寞就够了”。因此,犹大在充满张力的外界环境下逐渐走向自我封闭与孤独,最终恶性循环,固执于追求自己对耶稣的独占之爱。
在某种意义上,犹大并不是把耶稣完全看成他感情上的“爱慕者”,犹大对耶稣的爱一直凌驾于信仰之上,与耶稣及基督教所宣扬的爱大相径庭。犹大在耶稣的神性与世俗性之间感到困惑,他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耶稣会真的复活,他“只相信现世的喜悦,不害怕来生的审判”。耶稣更是一种象征正义和博爱的客观世界,犹大对这个美好向上的世界抱有强烈的憧憬。他始终像一个旁观者在评判着耶稣,把自己的理想、希望、计划都投射在耶稣身上,但又不断意识到耶稣这个美好世界带给自己无限的苦恼。脆弱的神经、强烈的自尊、敏感的猜忌使犹大与这个美好世界格格不入。而对这个客观存在却又无法摆脱的世界,犹大慢慢表现为一种绝望和自私。当发现一切理想都将落空时,犹大给予自己一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离开并出卖耶稣。犹大并非因恨才去告密,反而因为太爱而不得已为之。在他看来,出卖耶稣是对自己爱的行为的最佳诠释,爱与恨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背叛对犹大来说是独占、利己之爱的名义下的正当行为。小说最后一句“我是商人,我是加略人犹大”这句独白,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综上,小说以圣经中五个代表性事件为时间轴,并透过犹大独白式叙述,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从渴望天国、跟随耶稣时的门徒犹大形象,到出卖耶稣,追求自我利益化的商人犹大形象的转变。
二、犹大形象与太宰治基督教思想
《越级申诉》创作于太宰治婚后的第二年。在此之前太宰治的个人感情生活非常丰富,曾与酒吧侍女田部、艺伎小山初代有过轰轰烈烈的殉情经历。而婚后又与女读者山崎富荣产生不伦恋情,最终为了坚守爱情双双投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太宰治除了主动发生过爱情中的“背叛”行为,也曾蒙受过小山与其他男性偷情的“背叛”之耻(后胁迫小山殉情,但因药物剂量不足无果)。这种在太宰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动背叛”和“遭受背叛”的经历,使他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产生一种自我独特的心理认知,太宰治在《我的前半生》中说道:“爱别人首先必须得先爱自己,如果讨厌自己那就理所应当地该去自杀了[3]。”在对“爱”的理解上,太宰治本人与作品中的犹大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个人情感中,背叛他人后自发的省察意识和遭受背叛而触发的反抗意识,太宰治都将其理解为一种爱的表现,而《越级申诉》中犹大出卖耶稣前的内心忏悔和出卖耶稣后的理性辩护行为,与太宰治本人的价值观相当契合。
但要弄清太宰治如何构建《越级申诉》中的犹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考察太宰治与基督教的关系。正如佐古纯一郎(1992)所指,如果无视《圣经》与太宰文学的关联就无法真正读懂太宰小说[4]。太宰治一生接触基督教有三个重要时期,第二时期(1940-1942)太宰治对基督教的接受主要是把《圣经》作为翻案小说的写作素材来使用的。
太宰治熟读《圣经》,但奉行无教会主义,不进教会也未曾受洗。他对耶稣的情感依靠倾向于一种单纯的、个人的追随与爱慕,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与西方基督教信仰是有差别的。随着对《圣经》的深入阅读,基督教思想带给太宰治的安慰与鼓舞作用也发生变化,渐渐成为其矛盾与苦恼的来源。其在《苦恼的年鉴》中写道:“我几乎全部的苦恼,都来源于耶稣基督的‘爱人如爱己’这一难题[5]。”对于太宰治来说,耶稣基督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救世主,只是能够约束自我行为的立法者,基督教精神逐渐被太宰治相对化。太宰治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也深知自己不可能成为耶稣教诲的合格践行者,也不相信对罪的忏悔可以获得耶稣的赦免,其在《风之信》中曾写道:“忏悔并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而是接受上帝的惩罚[6]。”
如此,太宰治对《圣经》的解读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越级申诉》中有三处《圣经》原文引用,其中“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被解读成门徒在缺乏粮食的时候没有办法寻找到食物,如果没有犹大的奉献耶稣早就倒闭荒野。另一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犹大口中变成了一句“彻头彻尾的鬼扯和谎言”。而神殿逐商时耶稣大段的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训斥,被犹大解读为“难以置信”且认为耶稣已经“罪无可赦”。另外,小说中描写的对玛利亚的“嫉妒”与“发怒”、对无法获得耶稣反馈之爱时的“苦闷”等心理行为与《圣经》中爱是“恒久忍耐”“不嫉妒”“不轻易发怒”等教导是完全背离的,在种种独白辩护之下反衬出的犹大形象与圣经中“未经悔改”“假冒伪善”“贪爱钱财”的犹大形象也不相同。作品更多地将犹大行为正当化,并没有显示出作家在神学层面上对犹大“灵死”“身死”“永死”的批判。
同时,透过小说太宰治也通过犹大之眼反思着耶稣。小说通过神殿逐商、逾越节骑驴等一系列事件来展现了耶稣如何在群众中树立起他的权威,这些事件几乎都是直接引用《圣经》。不过,小说并没有选择那些耶稣施行神迹的故事,而是试图以现实的逻辑来解释耶稣的权威,甚至是有意消解耶稣的神性。尤其是写到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时,小说不仅对耶稣的表演性质毫不讳言,也并未说明耶稣骑驴这一行为所包含的宗教意义——弥赛亚以谦卑的姿态降临。相反,小说不无嘲讽地把这一事件描绘成了一出“喜剧”,群众的狂热,耶稣的含泪隐退,犹大的难以置信和彻底破灭。不可否认宗教约束在作家身上仍发挥着作用,致使太宰治尚不敢僭越改写耶稣形象。但另一方面,太宰治又通过犹大视角否认了作为神之子的耶稣。在这里,太宰治与犹大的关系既是统一的又是剥离的,太宰治本人并未否认耶稣“神之子”的地位。他看到了犹大行为的虚妄与危险,却又无法正确想象一个成长于现实社会的“神之子”耶稣,他看到了耶稣的爱给受苦的人们带来真实的安慰,但也怀疑这种安慰是否能转化成坚实的信仰。
因此,《越级申诉》中太宰治透过犹大这一形象的构建,表明了自己理想与信仰间的矛盾和差距。太宰治的《圣经》理解和对基督精神的认同是相对的,片面的、充满个性化的。他将带有自我独特理解的耶稣基督的言行、教诲和思想融入《越级申诉》小说的理念与艺术创作中,透过小说中犹大对卖主行为的独白式控诉,深刻诠释了作家自己对耶稣和《圣经》中爱的理解。
三、结束语
纯粹的文学作品相较宗教著作具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太宰治在《越级申诉》中对犹大的传统形象作了颠覆性的处理,他把犹大的背叛解释为一种对耶稣的特殊之爱。太宰治在信仰上是朴素又艰难的,但困苦犹豫并没有使他彻底抛弃,而是在批评、反思乃至动摇的挣扎中逐渐丰富他对基督教的认知。太宰治这种独特的信仰模式为《越级申诉》的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越级申诉》诠释了爱与恨的情感在纠结与碰撞中产生的艺术效果,体现了作家对爱恨主题的终极人生思考,对犹大形象的重构过程过多呈现出作家自我的宗教伦理观念,而相对缺乏普遍的人文社会思想是该作品的局限所在。
值得指出的是,太宰治的基督教思想不仅仅存在于《越级申诉》这一部小说中。在描述二战后日本颓废国民生活的《斜阳》,以及带有作者青少年自传体色彩的《人间失格》等作品中,均能发现作家独特的宗教情怀。太宰治借此提升了其作品的文学意境,使其作品今天亦保持着历久弥新的鲜活性。如果能将太宰治多个创作阶段的基督意识进行比较,势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他命途多舛的生活经历及整体把握其作品的文学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