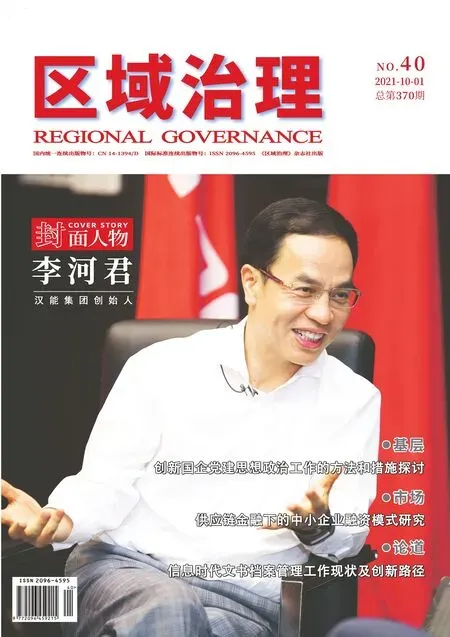婉转腾挪-谈柳琴戏唱腔艺术探讨
2021-01-02山东省滕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孙作建
山东省滕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 孙作建
一、柳琴戏的起源
在日益科学发展的今天,柳琴戏的现状和许多地方戏一样,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这不能说是科学发展造成的因果关系,而是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得更加成熟和各种音乐元素的介入的结果。特别是现在,很多流行音乐已经深埋在当今年轻人的心中。很多人从心底里不愿意接受中国的传统戏曲文化。这也许是中国戏曲文化几千年来发展中遇到的最大危机,因为思想意识对一门艺术的接受远比其他方式更为直接和有效。柳琴戏作为地方戏的典型代表,具有地方戏的独特魅力,其声乐特征和表演形式都发展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中国仍有许多地方戏剧,如淮海戏,逐渐被流行音乐和新的流行元素稀释。因此,保护地方戏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本文所分析的淮海戏灵魂调的介绍能够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毕竟,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就不复存在了。柳琴戏中的“拉魂腔”的起源总的来说有三种,一是与以上所说的相同,山东历城有唐大牛、唐二牛兄弟二人外出逃荒,在海州沭阳一带以卖唱为生,播下了“拉魂腔”的种子。二是在清末道光年间,山东临沂有个姓金的艺人,他把演唱艺术传给邱、黄、桑三个徒弟,他们三人又广收徒弟,从而将“拉魂腔”发扬光大。三是清道光年间,在海州一带有邱、葛、杨三个民间艺人卖唱,从而留下了“拉魂腔”。拉魂腔将主要曲调型抽出,和其他音乐素材重新组合构成新腔,变化异常灵活,并能在“活”的前提下,保持拉魂腔声腔剧种风格的统一。这些骨干音有 此谱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
二、柳琴戏的演唱形式
柳琴戏早期没有什么固定的板式,在演唱上,艺人具有较大自由空间,随心所欲地唱,故称之为“自由调”。在20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柳琴戏的唱腔不定腔、不定谐,演唱时完全是随意性的,演员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任意起唱,并且在演唱中即兴地加以装饰变化,于是,通常称其为“自由调”“怡心调”“怡人调”。顾名思义,就是随心所欲演唱之意。在较早出现的有关拉魂腔唱腔音乐的研究中可见,它的板头并不严格,曲调也没有一定的模式和规律,各个演员在演唱同一个角色和同一个段子时也不一样,这种“自由”演唱的形式成为柳琴戏唱腔(拉魂腔)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唱腔的落音处,女腔通常会有翻高八度的花腔,再有男腔以衬词拖腔为辅助,形成独特的风格。柳琴戏节奏大多以快板为主,多为有板无眼的四一拍,大多节奏明快,还有连续的节奏转变,给人一种欢快活泼的跳跃感,再加上音程跳跃中经常出现和频繁的转调,使柳琴戏的演唱给人一种缤纷多彩又和谐明媚的感觉。
柳琴戏的板式大致可分为慢板、二行板、数板、紧板和五字紧板。慢板通常使用在首句演唱,节奏为一板三眼,通常会转至二行板做一板一眼的演唱;二行板中又有流水板,即有板无眼的演唱结构;在遵守板腔体演唱规律中又有紧板和五字紧板,紧板即以七字句为主的有板无眼的演唱,五字紧板则以在紧板基础上进行字数的减少和节奏的加快;因此可见,在形成板腔体的过程中,柳琴戏并没有严格的上下句规定和音乐节奏变化的细致要求。
柳琴戏的唱腔以徴调式和宫调式为主,曲调有哈弦、起板、导板、连板起、拉腔、射腔、起腔、含腔、平腔、停腔、柔腔、叶里藏花、雷对调、一哟调、老公调、回龙调、垛板、调板、闸板、冒调花腔、四六长腔、男女拉拉腔等。此外还有从民间小调变化而来的过河调、赶脚调、送郎调、补缸调、叠断桥、打牙牌、千金小姐进花园调、小放牛、八段锦、调兵调、叶落金钱等。这些曲调在演唱形式上没有严格的要求,作曲者可以根据艺人的声音特点自由组合,艺人在路演时也可以根据现场气氛进行创作。可以说,柳琴戏在演唱形式上是具有高度的自由性和自我发挥性的。
三、柳琴戏的唱腔特点
特点之一,“自由性”。柳琴戏之所以能够实现唱腔的“自由性”这与其音乐的构成形式有着很大的关系,根本原因来自柳琴戏早期的演出方式,“肘鼓子”作为早期的“乞佬歌”形式中,经常需要结合时事和演出过程来进行二次创作的发挥,为吸引观众所用。加之柳琴戏并没有专业的剧作者出现,所以在唱词的写作和唱腔的创作上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体系,因此在柳琴戏的唱腔中,“自由性”就成了别具风格的特色。柳琴戏的基本曲调是由若干上、下对应的乐句连接组合而成,遵循二、四、六、八句拖腔的规律,这些上下对应的乐句是柳琴戏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它没有固定的曲调名称,上句与下句之间可以自由转换。所以就形成了它的自由性。而在长短句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五字紧板”等特殊的板式以外也没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只要跟板走、跟腔走,不跳出本身板腔体的范围和柳琴戏的演唱规律即可,至于声位和辙韵上,柳琴戏则更不做更多要求,不出格即可。
特点之二,“固定性”。柳琴戏男女唱腔的拖腔是固定的,而两种唱腔最主要的区分在于拖腔方式的不同,男腔拖“啊咦”或“哈咦”,女腔拖“嗯………”。一般而言,男腔下行二度拖腔,浑厚稳重,而女腔上行七度拖腔,则显得欢快跳跃。演员可以将乐句根据自己的演唱习惯和实际情况进行组合。但无论怎样组合,二、四、六、八句后的固定拖腔是一定有的。有了拖腔,大家一听便知这是“拉魂腔”柳琴戏,相反,若丢掉了这个拖腔,柳琴戏就失去了灵魂,也就不能称之为柳琴戏了。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柳琴戏的唱腔特色和规律的源头,在固定的拖腔中体现出柳琴戏本身的程式特点,但依然具有高度的自由性。
特点之三,固定的“花腔多”。在柳琴戏唱腔中,有很多固定的花腔调,并且有着固定的名称,称为专用曲调,老师们们则更习惯称之为“花腔调门”。这些花腔调门虽不是柳琴戏最为本质的唱腔特征,却是丰富唱腔必不可少的条件。它的花腔不下于十几种,最常用的有“含腔”“立腔”“停腔”“哭腔”“扬腔”“四句腔”“撂捱子”“叶里藏花”“老公调”等。这些腔是固定下来的几组乐句,在柳琴戏的演唱过程中,这种“花腔调门”给予了演员自身极大的发挥空间,不同“花腔调门”的运用也是柳琴戏艺术家门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根据曲调和节奏来表现出需要的情感和情景,“花腔调门”将柳琴戏的民俗性质带领到了一个高峰,也将音乐审美提高到了一定境界。
柳琴戏是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流行民间小演唱“拉魂腔”和“肘鼓子”相结合而形成。在没有被称为柳琴戏之前,又称“拉魂腔”,通常称作“拉魂腔”。1953年正式定名为柳琴戏。它形成于清代中叶以后,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接壤交界地区。柳琴戏的来源是以滕州民间小调“拉魂腔”为基础,受当地柳子戏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柳琴戏”的艺术特征概括为演唱、剧本和伴奏三个层面。一是处理“不确定曲调”和“无谱曲调”的自由。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对情节的理解,相对自由地处理歌曲。他们可以随意组合音乐十天,也可以随意处理花腔。即使是一些有经验的灵魂牵引艺术家,也可以通过与音乐家的合作来创作一些新歌。这样,“扯魂调”的演唱,在最后一句“扯魂调”的"前提"下,总是充满了丰富的变化。第二,自由的脚本系统,没有脚本和不定式。由于在20世纪初之前还没有文本形式的剧本,所以拉魂歌剧的曲目更多的是通过口头的方式在艺术家之间传播。因此,唱什么样的歌词往往取决于艺术家的即兴发挥。据刘长春回忆,当她在布家班唱歌时,剧团经常请一个有知识的人给艺人讲剧本,分配谁演什么角色,有时教几个字,有时不教,然后告诉其一个大致的情节。艺术家们唱完教堂的歌词后,他们唱了各种各样的歌。这种提纲剧或屏幕剧的剧本体系给艺术家的表演留下了很大的“空白”,艺术家在不影响剧本主要情节的情况下有很多自由的创作空间。此外,“人偶”和“扬子词案”也是艺术家在创作、记忆和演唱中形成的一种常规模式,广泛应用于传统灵调剧目中。三是弦包络与空腔音乐伴奏方式的自由。灵调伴奏音阶小,数量少,形式比较简单。它主要是为了连接艺术家的歌唱,尚未形成独立的音乐表现特征。
四、柳琴戏唱腔艺术探讨
在戏曲行也中“味道”是一个很难去把控的地方;学戏时,老师会说一个学生唱的没有“味道”;在演出时,观众也会说一个演员的唱没有“味道”,那么柳琴戏的“味道”是什么,它从何处而来,又怎么能够体现?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齐如山先生曾说过,在戏曲表演中要以“技术先行”为准则,因此,想要有“味道”,就要保证艺人在唱腔技艺上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和柳琴戏的唱腔特点,例如柳琴戏的拖腔,一些中青年演员减少了拖腔的使用,原因是其不符合当下市场上的音乐审美,笔者并不赞成这一观点,因为拖腔的丢失是柳琴戏特色的丢失,如果单纯为了音乐审美上简单的愉悦而丢失了柳琴戏本身的特色来追求“味道”的话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创新应该要根据柳琴戏的基本规律,通过传统柳琴戏的唱腔的学习来总结出柳琴戏的“味道”,这其中,技巧是一切的基础。
谈到技巧,笔者深有体会,在2007新编了大型历史剧《墨子与鲁班》中我饰演了鲁班一角色,我在鲁班唱腔的运用上,充分挖掘了柳琴戏“吞”“闪”“切”“磨”等高难度唱腔技巧。所谓“吞”就是板后顿起来唱,这种唱腔的技巧常用于一些排比句唱段,顿起来唱最后来个拖腔上行板,使观众听起来有婉转的感觉,吞板又分快吞和慢吞两种,观众在听完唱腔行腔时,往往都会给以热烈的掌声。所谓“闪”“切”,就是在激情高昂唱腔当中突然停顿截死,然后甩一个非常柔和、动听的拖腔。这种唱腔的运用和处理大部分用在突变和回忆的唱词当中,给人以回味的感觉。所谓的“磨”就是运用演唱者的演唱技巧,充分发挥滑音和波音的作用,使其唱腔委婉、柔和、悦耳、动听,给人以美感。在实践过程中,我充分体会到,要想把柳琴戏唱好,并非是一件易事,要去下很大的力气打磨演唱的技艺,下番真功才有可能见其成效。而且我还体会到,在柳琴戏的演唱过程中,拖腔是一大难题,而恰恰又是它的灵魂所在。除用真嗓之外,还要使假嗓巧妙地糅合进去,使唱腔和拖腔柔和不生硬,才会使柳琴戏更具有“拉魂腔”的特点。将技巧充分掌握以后,融合演员的自身条件,“味道”和流派就会一一出现了。这里以王传亮老师的《回龙传》中王华的代表唱段“听的谯楼打初更”为例,王传亮老师的嗓音条件在柳琴戏演员中为魁首,但依然在高音上有共鸣上的不足,但在《回龙传》这一唱段中,王传亮老师通过对柳琴戏唱腔技巧的把控,婉转腾挪地将其完美呈现,以首句的弱音渐强来带入剧中夜晚初更时分,使观众感到渐入佳境,再通过每句的行腔将柳琴戏的特色精准的呈现,杂糅以符合王传亮老师本身的优缺点,避免过强的共鸣从而脱离角色,最终形成强弱层次分明的呈现方式,既有柳琴戏的特色,也有演员自身艺术总结的“味道”出现。同样,柳琴戏的本质特点,就是艺人具有很大的主观能动创作性。我们再以江苏省柳琴剧团的朱树龙老师为例,相对于王传亮老师,朱树龙老师的共鸣更强,高音更加稳健,但在低音的细致处理上则有不同,因此,在朱树龙老师演唱的剧目《八郎探母》的唱腔处理中,和王传亮老师对比展现出了柳琴戏不同的唱腔处理方法。朱树龙老师充分运用了自身高音共鸣强和稳的特点,在首句即出现高音,通过充满激情的唱腔调动观众的情绪,在唱腔中注重较大的情感起伏表达,弱音中按照柳琴戏的演唱技巧,不做特殊处理,充分发挥演员本身的先天优势,从而展现出柳琴戏的不同味道。流派的纷呈是一个剧种繁荣的表现,这种流派的概念,小到不同艺人的表演特点,大到不同艺术家通过几十年的舞台经验和对自身的总结形成的独特的表演风格,流派会无限提高一个剧种的审美高度和广度。通过对王传亮老师和朱树龙老师的演唱方式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知道,在柳琴戏的唱腔艺术中,技术是极其关键的,无论演员本身有何种风格,也要对柳琴戏基本唱腔技艺的掌握是一切的基本要素,继而从中结合自身的特点总结,才能形成新的柳琴戏的艺术特色,才能结合个人,而有“味道”,这种“味道”是每一个戏曲演员都要追求的东西。
五、结语
本篇文章旨在探讨柳琴戏的唱腔艺术。在当今的柳琴戏剧坛中,唱腔创新是大多数新编戏的基本要素,那么就如何能够创作出好的新唱腔这一问题,笔者作为柳琴戏演员认为,要充分把握基本的柳琴戏技术,在原汁原味的柳琴戏当中进行保留特色的创新,不过分追求单纯的音乐审美的大众化,演员是戏曲演出的中心,创作者要会根据演员的特色和条件进行创作,从而发挥更细致化的作用。在笔者本身的自我审视看来,我在嗓音条件上更偏向于婉转温柔的高音,在以往的演出中总结了自我的特点,克服并且避免了自身的弱项。通过本次对柳琴戏唱腔艺术的探讨,笔者认为,在演出过程中更应该注重柳琴戏高度自由性特点的开发,以及对柳琴戏“花腔调门”的运用手段的熟练对于柳琴戏唱腔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演员也要把握基本的规律和特点。作为优秀戏曲唱腔代表之一的柳琴戏,其承载着社会发展的烙印,因此, 其所体现出的价值并非仅仅是地方戏曲史层面的,更是研究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依据。从柳琴戏的唱腔发展情况来看,其最早遵循着对花鼓调的模仿与演绎方式,传承至今形成了独特的板腔体,可以说,对这一唱腔演变过程的研究,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