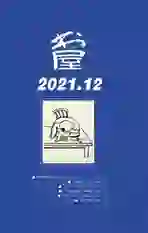乐意做个“情信而辞巧”的歌德派
2021-01-01黄维樑
二十一世纪伊始,我在深圳的福田购置了物业。除掉在香港以外各地读书和教书的约十年岁月不算,这之前我在香港一共居住过三十多年。深圳置业之后,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辗转在香港、台湾、深圳、澳门居住;2016年1月起,我长住深圳;最近为“身份”定位,自称为“香港深圳人”。深圳楼价高,香港更高。楼价负担得起的福田居舍,予我们一家宽敞的作息环境;我的书房得地独大,成为“书厅”。从前在香港的沙田笔耕,笔落纸上,沙沙作响,在“纸田”收获了密密麻麻无数沙粒一样的文字。到了福田后,手笔依旧蒙福,在文学田地上的笔耕仍然丰收,但不久就从笔耕转为键敲了。
粤港澳大湾区有十一个城市,包括香港、深圳、澳门。二十年来,我居住于此三地(此外还有台湾),读书、教书、著述不辍,时而四出讲学或旅游,享受小康或中产的丰足生活。我写作学术论文,也写作不那么学术的文章,或谓散文。在大湾区的三个城市,敲文打字,“键”笔乐记大湾区,以及游踪所及的五湖四海,乐记其生活、旅游和文化。构思酝酿文章,敲文打字时造句谋篇、修饰润色,心力和体力并用,能不有劳苦之感?每当构思有得,佳句神来,文章既成,一时认为可堪自珍,发表后获得知音的点赞,又来了稿费,又有出版社邀请出书;这时啊,劳苦已忘记,或苦尽而甘来,以为文章有价,甚至幻觉是大业是盛事,如此这般想象,岂不快乐?人生的苦与乐,就像《易经》两仪阴阳互抱一样,好在我总是把阳的半环看得丰润一些。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突然,一朵莲花》在1983年出版,此后有《大学小品》(1985)、《我的副产品》(1988)、《黄维樑散文选》(又名《至爱》,1995)、《苹果之香》(2000)、《迎接华年》(2011)。即将出版的这本《大湾区敲打乐》所收,主要是最近十年的文章,以及《迎接华年》与以前散文集缺收的“轶文”与“遗珠”。近年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数量不菲,则另行结集出版。
已出版的散文集,每本的长短文章大都有数十篇。我一向都把文章分门别类,例如《迎接华年》分为六辑:序文、学文、亲文、同文、游文、杂文。除去《自序》不计算,这本《大湾区敲打乐》共收长短文章五十二篇;内容可仿照以上的分类,不过现在只分为三辑:如常生活、文化旅游、师友文章。无论如何,从内容分类看来,我所关注所书写,都是相当杂的,说都是“杂文”并无不可。
《文心雕龙》有《杂文》篇,对杂文的要求,高于现代我们一般所说的杂文。《杂文》开宗明义这样解释:“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龙学家牟世金对原文这样翻译:“聪明才智、博学高雅的人,他们的言辞富有文采,他们的气质充满着才华,所以在写作上赋采抒情,能不断取得各种不同的新成就。”这就类似近世论者所说的“学者散文”了。这种学者散文,就我浅近追踪所及,博通中西的钱锺书可说开其端,我所熟悉的香港旧同事梁锡华、黄国彬接其棒增其华,中间更有余光中“在中国文字风火炉”中炼丹的雄心伟业,其“日新殊致”的风格就更为明显了。我向来所写的散文,知我者爱我者,美称之为学者散文。至精至美的学者散文,我或笔耕或键敲,虽然不能臻至,但心向往之。
《文心雕龙》论文,还有“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的要求,即文学作品要兼重修辞艺术和实质内容,内容方面,刘勰对作家有“顺美匡恶”的期许。是的,无论是诗是文是小说戏剧,言为心声,笔或键的锋利能胜刀剑;对时代社会的人、事、物,或褒或贬,可异常敏锐。当然,也可温柔敦厚,我的为文风格近于后者。
我以“键”笔匡正恶行,比如在本书文章中反对浪费食物、呼吁实践“光盘行动”,比如对某些学生沦为“萧艾”的叹息,乃基于一种菩萨心肠。批评人,我不会说某个城市的人不如狗;宣扬中国文化,我不会说一个章子怡胜过万个孔夫子。文章不猛然出格,作者就难以暴然出名;但我行我素,这方面内子最能理解。
我的文章“顺美”(赞美功德)的比较多。我记叙近观远察种种美好的人、事、物,乐意敲文打字做个“情信而辞巧”的“歌德派”。(敲文打字的敲,也是推敲文字的敲;“情信”之外如要“辞巧”,用词造句当然要加以推敲,“敲”才能“巧”)写文章歌颂理想国?理想国又名“乌托邦”,那就是乌有此邦。尽管并不完美,国家当今确实处于一个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多年来在神州大地或旅游或讲学,在深圳日常生活,我真要发出韩愈所说的“鸣不平”。“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即内心不平静时、激动得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的“强烈感情满溢”时,这就要发出声音了。什么声音?韩愈说可包括“鸣国家之盛”的声音。
本书中,多有我周游列省列市的记述。所见的五湖四海,山与水恢复其青绿,大城小镇换上新装,民众安宁生活丰衣足食以至锦衣玉食,大学校园恢宏其气象,博物馆壮美其收藏,机场巨大而航程安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快递可称“新三高”,“公厕革命”大大成功,“冠疫”(Covid-19,即新冠肺炎疫情)被扫荡社会复常平靖,这真是我们可鸣其盛唱其好的大时代。
二十年前我在深圳置业时,报章喜登深圳获选为国际花园城市的大新闻;而今居住的,是个日新又新、日进步又进步的全国“先行示范区”。对深圳的“现代化”形容,我认为应升格为“现代化+”。如果不外出享受这创新城市之光,在家里,我开卷悦读、“键”笔乐记之余,可观看或“回看”高水平的电视节目如近年的《航拍中国》《典籍里的中国》《清平乐》《觉醒年代》等,可视听5G手机5G覆盖的种种电子信息(包括我的纷繁“微信”),既高清,又可选择高雅。唱好深圳,我仍需努力。本书名为“敲打乐”,性情比较接近古典的我,在大湾区写作,有时真想敲文打字时“浪漫”起来,用力打拍敲击乐器,让编钟木琴大锣定音鼓响起热情的礼颂之曲。歌德笔下的浮士德(Faust),对着美好的当下,渴望时光停留下来。我更贪心,希望美好日子绵绵延长。
有时怀念在澳门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岁月(2012—2014),一家人的平常日子过得真是“都瑞美”。自2020年春天起,香港疫情起伏不定,从深圳到香港,短短的过境通道遭遇长长的时间关闭。我家不辞长做深圳人,但怀想香港的亲友不能面对面相见、面对面碰杯,竟萌生一股淡淡的“乡愁”来了。思念文友,我让想象驰骋,写出《杜甫在香港》这篇文章。在香港,在美国的母校,以及多位师友,与师友的文章,多年来也都在我的忆念中,本书留下了多篇记录。
在美国和欧洲的旅游,和在神州大地一样,我称之为文化旅游,本书也有记述:多瑙河、魔涛河(在布拉格的River Moldau)还有名不见经传的牛津大学适苇河(River Cherwell),诸篇游记中蕴含我的多情。剑桥大学的剑河(康河)名闻遐迩,中华文士连群结队赞美它。去年在“喜马拉雅”偶然听到有人朗读我的《牛津的适苇河》一文,惊喜之余,我把这篇1986年的旧作纳入眼前这本新书,并借此表示“同情弱者”之意,剑河是名气上的强者。
书中文章发表后,我喜得多位雅士知音。近年在《羊城晚报》和《北京晚报》所刊拙文,常获新旧文友如李元洛、陶文鹏、汉闻、郑延国、陈学超、徐志啸、杨全红、李金坤、庄向阳等位点赞,他们中且时赐嘉言,对此我深深致谢。本书的一些篇章以及《迎接华年》与更早的文章或散文集,也屡屡获得各地读者或口碑或撰文鼓励称美,我同样衷心感谢。当然,要感谢的还有大湾区各地以及宝岛台湾的书刊编辑青睐约稿或用稿——其名单有如杜甫诗“感子故意长”那样长;还有“老校长”耄耋的金耀基教授又一次挥墨赐题书名;还有香港文思出版社诸位倾力制作本书;还有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本书出版经费。诸位先生女士,请接受这里无形的五个感谢“表情包”。
编印书刊的成本不菲,本书既获资助,我自己又参与本书的制作以减少成本,乃定下了较为低廉的售价,希望多些爱书人购买本书。本书的文章,随心意之所之而撰写,并非有心意有计划撰写一本讲述大湾区生活与文化的专著。不过,对香港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而言,阅读本书,应可增加对大湾区的认识,增加“国情认识”;观看本书提及的《航拍中国》《典籍里的中国》等有益有趣的精彩电视片,则应是对“国民教育”的一种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