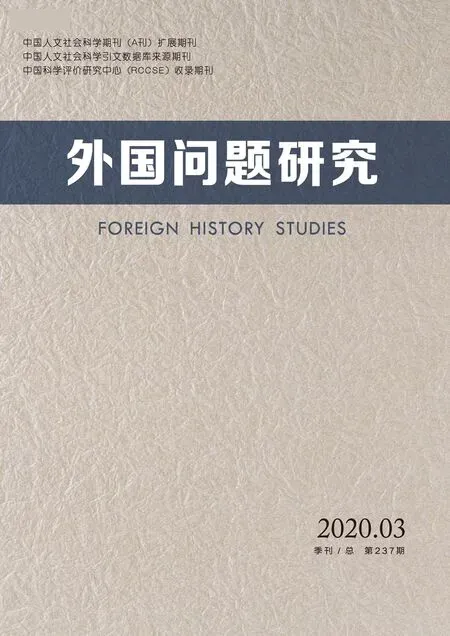托莱多翻译学院:中世纪文化交流的枢纽
2020-12-31谷佳维
谷佳维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自12世纪上半叶开始,持续近两个世纪的西班牙托莱多(Toledo)翻译运动被称为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1)西方世界的翻译运动共出现六次高潮,分别是公元4世纪末罗马翻译希腊文学、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中期的《圣经》翻译、中世纪托莱多翻译运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翻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翻译活动。参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页。在这场以托莱多翻译学院(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为中心的长期、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当中,为数众多的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科学与文学典籍通过阿拉伯文或希伯来文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卡斯蒂利亚语,古典文化得以经由阿拉伯世界重回欧洲,与此同时,阿拉伯文化开始在欧洲广为传播,对随后的文艺复兴与科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刘建军:《阿拉伯文化对欧洲中世纪文化的影响》,《北方论丛》2004年第4期。
有关托莱多翻译运动的探讨始见于法国学者阿玛贝尔·茹尔丹(Amable Jourdain)1819年撰写的著作,(3)Amable Jourdain, Recherches critiques sur l’ge et l’origine des traductions d’Aristote et sur les commentaires grecs ou arabes employe par les docteurs scholastiques, Paris: Joubert, 1843.而“托莱多翻译学院”现象的命名则由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856年完成。(4)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家和作家欧内斯特·勒南在其博士论文中用法语将这一现象命名为“collège de traducteurs”,即“托莱多翻译学院”。参见Ernest Renan, Averro⊇s et l’Averroïsme. Essai historique, Paris: Université, 1852.然而直至现今,这一欧洲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交流事件在西方学术界并未得到充分研究,(5)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Revista de estudios filológicos, No.11, 2006, p.101.现有成果一方面从翻译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具体的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进行梳理,探讨这场翻译运动对西班牙民族语言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6)José S. Gil,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y los colaboradores judíos, Toledo: Instituto Provincial de Investigación y Estudios Toledanos, 1985; Brbara Azaola Piazza,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presente, pasado y futuro,” Idea La Mancha: Revista de Educción de Castilla-La Mancha, No.5, 2007, pp.122-129; Pilar Herriz Oliva, Averroes en la revolución intelectual del siglo XIII. Bases para una reinterpretación de la Modernidad, Murcia: Universidad, 2015.本文将在此基础之上,从语言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角度入手,进一步研究翻译运动对西班牙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的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国外学者通过对托莱多学院的创始人拉蒙德(Raimundo de Sauvetat)大主教及其继任者的研究,明确了翻译学院始终受到基督教会资助和支持的事实,并由此普遍认同了基督教会的参与对于翻译学院的兴起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过度推崇拉蒙德的个人功绩,如欧内斯特·勒南称他是“文化的君主”、马塞利诺·梅南德斯·佩拉约(Marcelino Menéndez Pelayo)称其为“自由思想的守护者”。(7)Marietta Gargatagli, “La historia de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Quaderns. Revista de traducció, No.4, 1999, p.11.本文认为,以上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将托莱多翻译学院的源起简单化,忽视了中世纪西班牙多民族、宗教、文化共存的复杂性。托莱多翻译运动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与南部穆斯林统治下的安达卢斯(Al-ndalus)长期交流与对峙的背景下产生的,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沟通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试图在民族交流与文化传承的历史语境下,对托莱多翻译学院兴起的原因和条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
国内方面,虽然由于一手资料的缺乏等原因,尚未展开针对托莱多翻译学院的专门性研究,但仍有部分学者在综合性研究中充分肯定了翻译学院对阿拉伯文化的传播与欧洲文艺复兴产生的巨大推动力。(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第37—40页;肖丰:《西欧文艺复兴文学中的阿拉伯文化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8年,第36—43页。然而,既然西班牙率先通过翻译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古罗马经典,文艺复兴在西班牙为何兴起较迟?以托莱多翻译学院为缩影,西班牙特殊的宗教与历史文化背景造就的多元文化共生社会面貌如何?本文将论述翻译学院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在研究其在中世纪欧洲文化的融会与复兴中所起的枢纽作用的同时,探索以上问题的答案。
一、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兴起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托莱多翻译学院兴起的直接动力是基督教会的支持,是出于对基督教教义进行重新阐释的需求。(9)Marietta Gargatagli, “La historia de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pp.9-13; Paulo Vélez León, “Sobre la noción, significado e importancia de la escuela de Toledo,” Disputario. Philosophical Reserch Bulletin, Vol.6, No.7, 2017, pp.537-579.12世纪初,西欧封建社会在历经几百年的动荡与发展之后,开始走向稳定,以基督教教堂和封建王公为中心的城市显著发展,商会和手工业行会兴起,出现了与宗教和政治权威相对立的自主精神。(10)王亚平:《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使得基督教内部出现了一股重新阐述教义、建构基督教解释体系的热情。在新的诠释体系之下,人们从关注灵魂被基督拯救转向了关注基督拯救和人自身拯救的统一,人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了讨论的核心问题。新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需要新思想和新理论的介入,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典哲学家的学说就是在这一历史需求中被重新发现的。(11)刘建军:《论12世纪西欧文化复兴运动》,《北方论丛》2003年第6期。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认为上述情况只是翻译学院产生的原因之一。托莱多翻译学院是在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王国针对穆斯林征服者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背景下建立的,它诞生在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除基督教的支持外,具体还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促成。
(一)“收复失地运动”中的民族迁徙、宗教共存与文化交往
公元711—718年,由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控制的、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推翻了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人的政权,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置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建立了以南部城市科尔多瓦(Córdoba)为中心的安达卢斯。(12)安达卢斯(Al-ndalus)可泛指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的区域。随着半岛北部基督教王国“收复失地运动”的展开,安达卢斯的面积不断发生变化。
截至1085年托莱多被基督教王国收复,穆斯林在安达卢斯的统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公元756年,被废黜的倭马亚王室王子阿卜杜·拉赫曼一世(Abd al-Rahman I)拒绝承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权威,(13)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后者的大部分成员遭到屠戮,阿卜杜·拉赫曼一世逃亡西班牙。成为科尔多瓦独立的埃米尔,建立了科尔多瓦酋长国(Emirato de Córdoba),后倭马亚王朝开启;公元929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III)宣告成为第一任科尔多瓦哈里发,科尔多瓦成为哈里发国(Galifato de Córdoba);11世纪早期,后倭马亚王朝解体,安达卢斯分裂为被称作泰法(taifa)的多个穆斯林小王国,其中包括与北部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Reino de Castilla)大面积接壤的托莱多泰法(Taifa de Toledo)。(14)Antonio Arjona Castro, Historia de Córdoba en el Califato Omeya, Córdoba: ALMUZARA, 2010, p.272; Brbara Boloix Gallardo, “La Taifa de Toledo en el siglo XI. Aproximación a sus límites y extensión territorial,” Tulaytula: Revista de la Asociación de Amigos de Toledo Islmico, No.8, 2001, pp.23-57.
与此同时,自8世纪早期,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便不断扩张自身势力,发起了持续七百余年的“收复失地运动”,又称“再征服运动”,基督教与穆斯林的长期对峙造就了民族交往与文化融合不可多得的契机。另一方面,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已经拥有了规模可观的犹太社群,虽然曾受到零星的迫害,但直到1391年的大屠杀及随后被大规模驱逐之前,犹太人长期享有较为开明的宗教与种族政策,(15)雷蒙德·卡尔:《不可能的帝国:西班牙史》,潘诚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第58—59、105—106页。因而,进入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三种民族、宗教与文化的相容并存之地。
伊比利亚半岛的民族交往与文化融合是广泛而深入的。这一现象首先表现为民族的大规模迁徙,以及穆扎赖卜人(mozrabe,即在安达卢斯居住的阿拉伯化的基督徒)、穆德哈尔人(mujédar,即在被基督教王国收复的土地上继续居住的穆斯林)等新族群的诞生。其次,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并不局限于世俗层面,而是同时发生在宗教层面。例如,11世纪的安达卢斯犹太教教士摩西·伊本·伊斯拉(Moses ibn Ezra)曾经记载了自己与一名穆斯林智者的交往:穆斯林智者请伊本·伊斯拉用阿拉伯语诵读《十诫》,伊本·伊斯拉却反过来要求对方先用拉丁文诵读《古兰经》。对方诵读时发觉经文的内容无法完整地传递,原文的美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于是收回了之前的请求。(16)Juan Vernet, Lo que Europa debe al Islam de Espaa, Barcelona: Acantilado, 2006, p.128.这表明在当时的西班牙,不同民族、宗教之间并不是封闭的群体,且在一定程度上能使用多语进行沟通,由此为翻译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二)早期翻译活动的出现
随着伊比利亚半岛各民族之间交流的不断加深,翻译活动的出现成为必然。在托莱多翻译学院建立之前,半岛上基督教王国控制的北方地区就存在着早期的翻译活动。以比利牛斯山区为例,“早在10世纪下半叶和11世纪上半叶,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自由基督教徒便把对阿拉伯文化的兴趣当作一种潮流”。(17)Simón Haik, Las traducciones medievales y su influencia, Madrid: Universidad de Complutense, 1981, p.374.此外,半岛东北部里波尔(Ripoll)的圣玛利亚修道院(Monasterio de Santa María)在10世纪翻译了大量阿拉伯科学文献,至今还有超过250份手稿得以保存;(18)María José Prieto Villanueva, Pensar la ciencia desde la biología. Una visión evolutiva del conocimiento biológico, Barcelona: Publicacioens i Ediciones Universitat Barc, 2017, p.111.在巴塞罗那,1134—1145年,犹太学者亚伯拉罕·巴哈·海以亚(Abraham Bar Hiyya)与来自意大利帝沃利的柏拉图(Platón de Tívoli)共同翻译了阿拉伯数学、天文学和星相学著作;(19)Francisco Lafarga and Luis Pegenaute, 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en Espaa, Salamanca: Editorial AMBOS MUNDOS, 2004, pp.40-41.12世纪上半叶,活跃在半岛北部的翻译家则包括今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地区改宗基督教的犹太医生佩德罗·阿方索(Pedro Alfonso)以及北部图德拉(Tudela)的犹太诗人亚伯拉罕·伊本·埃兹拉(Abraham ben Meir ibn Ezra)。(20)José Antonio G.-Junceda, “La filosofía hispano-rabe y los manuscritos de Toledo. Una meditación sobre el origen de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Anales del Seminario de Historia de la Filosofía, No.3, 1982, p.67.
早期的翻译活动并不局限于和平时期和知识阶层,而是同时出现在战争状态下,并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由于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大规模发生,早在公元10世纪中期,基督教王国的军队便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穆扎赖卜人、犹太人和穆斯林士兵,笔译员和口译员职位因此在军中产生。(21)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p.101.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分裂后,众多的穆斯林泰法国相互冲突,并通过向基督教王国输出黄金获取对方的军事援助,(22)雷蒙德·卡尔:《不可能的帝国:西班牙史》,第69页。安达卢斯与基督教王国的联系由此进一步加深,翻译活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为托莱多翻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三)阿拉伯世界的翻译传统与文化典籍
公元8世纪中期至10世纪末,阿拉伯帝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百年翻译运动”。这场运动的高潮始于公元9世纪上半叶,随着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阿布·阿拔斯·阿卜杜拉·马蒙(Abu Abbas Abd-Allah Al-Mamún)执政时期的到来,集翻译、教育、科学研究、天文观测、图书馆为一体的研究中心“智慧宫”(Bayt al-Hikmah)在巴格达创立,吸引了大批学者前往从事学术活动,为数众多的古希腊哲学与科学典籍被翻译为阿拉伯文与希伯来文,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欧几里得、盖伦等人的经典著作。(23)“百年翻译运动”中,产生的译著包括柏拉图的著作8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9种,希波克拉底的著作10种,盖伦的著作32种,以及《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等千种以上。参见纳忠:《阿拉伯通史 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68页。不仅如此,阿拉伯学者还为上述作品写下大量的注释与评论,(24)希提:《阿拉伯通史 上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62—363页。丰富并深化了原著的内容,可以说,“阿拉伯学者们通过对数世纪作品的翻译,成了文化巨匠。在知识领域里,他们不愧为希腊与波斯文明的真正继承人”。(25)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3页。
因此到中世纪早期,相较于古希腊经典濒临湮没的西欧,阿拉伯世界已具备了可观的文化优势。而正如前文所述,伊比利亚半岛早期翻译活动等文化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也使当时的欧洲学者充分认识到阿拉伯文化的先进性。(26)José Antonio G.-Junceda, “La filosofía hispano-rabe y los manuscritos de Toledo. Una meditación sobre el origen de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p.85.随着安达卢斯的发展,科尔多瓦在10世纪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27)许昌财:《西班牙通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上述阿拉伯、希伯来译本的典籍大量出现在众多皇室、民间藏书馆中,仅第二任科尔多瓦哈里发哈卡姆二世(al-Hakam II)兴建的皇家图书馆藏书量即达400 000余卷,其中不乏珍稀版本,在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学者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除科尔多瓦外,安达卢斯的其他大城市也建有多座知名图书馆,如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a)、阿尔梅里亚(Almería),西部的巴达霍斯(Badajoz),中部的萨拉戈萨(Zaragoza)、托莱多等。(28)马凌云:《中世纪伊斯兰图书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2016年,第71—75页。上述图书馆的藏书对当时渴望寻回古希腊经典的半岛北方基督教国家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29)José S. Gil,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y los colaboradores judíos, p.106.直接促成了大规模翻译运动的诞生。
(四)托莱多的特殊地位
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之所以在12世纪的托莱多兴起,与这座城市特殊的历史、地理、政治与文化地位紧密相关。首先,翻译运动由基督教会和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王室资助,而历史上,托莱多既是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发展的中心,也是行政中心。托莱多位于半岛中部,早在西哥特人统治时期(409—711年)即成为“王国的宗教与政治象征”。(30)José Antonio G.-Junceda, “La filosofía hispano-rabe y los manuscritos de Toledo. Una meditación sobre el origen de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p.70.6世纪至7世纪早期,基督教在此召开了四次托莱多主教会议,其中589年召开的第三次会议结束了半岛的宗教分裂状态,将罗马化的西班牙人口集合在了西哥特人的君主制体制之下,基督教势力增长,政教共治体制形成。(31)雷蒙德·卡尔:《不可能的帝国:西班牙史》,第44—55页。此后,尽管穆斯林统治时期的托莱多长期处于基督教势力以外,但其对于半岛的基督教徒始终具有特殊意义,因而在“收复失地运动”当中,也成为第一座被基督教王国收复的大城市。
其次,受地理位置影响,托莱多长期处于基督教王国与安达卢斯双方势力的交界,民族与文化融合的程度相对较高。8世纪初期,穆斯林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托莱多被纳入安达卢斯的版图,其半岛行政中心的地位也被科尔多瓦取代。1035年,随着后倭马亚王朝的解体,托莱多泰法国(Taifa de Toledo)建立,以托莱多为首府,疆域包含了马德里(Madrid)等当今西班牙中部的若干主要省份。托莱多泰法时期(1035—1085年),一方面,以托莱多的马蒙(Al-Mamún de Toledo)为代表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将已灭亡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原有的大量藏书与手稿收集到了托莱多,其中包括前文提及的哈卡姆二世皇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吸引了北部基督教国家及欧洲其他国家学者的目光;另一方面,统治者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政策,不同族群间相处较为融洽,且推行了保护学者的措施。(32)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p.106; José Antonio G.-Junceda, “La filosofía hispano-rabe y los manuscritos de Toledo. Una meditación sobre el origen de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pp.75-76.
1085年,西班牙北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君主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托莱多(Toledo)。重回基督教统治的托莱多经济迅速发展,财富大量积累,“为精神生活的繁荣提供了绝佳的契机”。(33)Claudio Snchez-Albornoz, El Islam de Espaa y el Occidente, Madrid: Espasa-Calpe, S. A., 1974, pp.190-192.基督教治下的托莱多并未摒弃阿拉伯文化传统,相反还从安达卢斯大规模搜集经典著作,除前文提及的阿拉伯译本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和评注之外,也涵盖了阿拉伯世界的原创作品。与此同时,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托莱多境内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犹太人相处和谐,多元文化氛围进一步增强,为数众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学者也因城中所藏的阿拉伯典籍慕名而来,翻译学院成立的条件至此完全成熟。1130年,托莱多翻译运动在拉蒙德大主教的支持下拉开序幕,此时的托莱多已经成为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一座向所有自基督教西方而来寻找知识的学者敞开大门的城市”。(34)Mariano Brasa Díez, “Métodos y cuestiones filosóficas en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Revista espaola de filosofía medieval, No.4, 1997, p.45.
二、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1125年,法国克吕尼修会修士拉蒙德被任命为托莱多大主教。为了应对基督教教义重新阐释的挑战,他着手成立托莱多翻译学院,利用托莱多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对城中所藏的大量阿拉伯译本的古希腊、古罗马典籍及其评注进行翻译。除此之外,翻译运动也将目光投向部分穆斯林学者的原创作品,有研究显示,这是出于通过深入了解穆斯林思想,在思想层面与其展开较量、并进一步对其进行同化的目的。(35)Henri van Hoof, “Esquisse pour une histoire de la traduction en Espagne,” Hieronymus Complutensis, No.6-7, 1998, p.10; 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p.102.
在组织构成方面,尽管以“学院”为名,但托莱多翻译学院并非研究院或教育机构等实体组织,也无证据显示当时的托莱多存在专门用以进行翻译活动的独立场所。(36)Francisco Lafarga and Luis Pegenaute, 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en Espaa, p.37.事实上,翻译学院的译者组织相当松散,除中心地点托莱多外,受拉蒙德及其继任者们庇护和资助的译者也会前往其他城市从事翻译活动,上述活动同为托莱多翻译运动的组成部分。(37)Claudio Snchez-Albornoz, El Islam de Espaa y el Occidente, p.193.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托莱多翻译学院事实上是不限定场所的翻译共同体,但其内部的确存在教学活动及学术探讨,此类活动由译者之间以个人名义开展,虽然其中并无任何宗教或世俗势力的介入,(38)Francisco Mrquez Villanueva, “In Lingua Tholetana,” in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eds. by J. Samsó, Toledo: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Toledo, 1996, pp.23-24.但在客观上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的族群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12世纪上半叶到13世纪末,托莱多翻译学院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翻译运动在拉蒙德大主教和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资助期间两度达到高峰。下文将通过对以上两次高峰时期的翻译模式、译者来源、翻译内容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翻译学院发展历程中文化交流的具体情况和主要特征。
(一)第一次高峰:拉蒙德大主教时期
拉蒙德于1125年担任托莱多大主教直至去世(1152年),并于1130—1150年兼任卡斯蒂利亚王国大臣。在大主教任期内,拉蒙德开创了托莱多翻译学院并迅速将翻译运动推上高峰,因此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并无足够证据显示拉蒙德对翻译运动的推动作用相较其继任者们更加出众,(39)Marietta Gargatagli, “La historia de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p.11.这一观点从侧面论证了托莱多翻译学院初期的迅速发展是各方面条件互相配合、水到渠成的结果。
拉蒙德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以小组为单位协作进行的。在这一翻译模式下,源语言(即“译出语”,source language)为阿拉伯文及少量的希伯来文,目标语言(即“译入语”,target language)为拉丁文,二者之间借助卡斯蒂利亚语作为中间语言(intermediate language)进行衔接。具体操作时,首先由一名译者将源语言逐词逐句地口头译为卡斯蒂利亚语,这要求该译者能够熟练读写阿拉伯文,并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以便理解原文含义、厘清术语概念,有时还需懂得辨认手稿。因此这一职位通常由受过精英教育的穆斯林或犹太人担任,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犹太哲学家来自塞维利亚的约翰(Juan Hispalense)、犹太医生、天文学家摩西·塞法迪(Moshé Sefardí)等。(40)摩西·塞法迪于1106年改宗基督教,此后又名佩德罗·阿方索(Pedro Alfonso)。参见José María Mills Vallicrosa, “La aportación astronómica de Pedro Alfonso,” Sefarad: Revista de Estudios Hebraicos y Sefardíes, No.1, 1943, p.65.翻译活动的第二个步骤则是由一名精通拉丁文的译者通过听译将卡斯蒂利亚语译成拉丁文,并形成书面文稿,担任这一职位的通常是西班牙本地基督徒或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翻译小组中起主导作用,(41)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pp.108-111.代表人物包括英国人巴斯的阿德拉德(Abalrdo de Bath)、切斯特的罗伯特(Robert de Chester)等,(42)Francisco Lafarga and Luis Pegenaute, 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en Espaa, pp.39-40.而最著名的两位则是意大利翻译家克雷莫纳的杰拉德(Gerardo de Cremona)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库埃利亚尔(Cuéllar)镇的副主教多明戈·贡迪萨尔沃(Domingo Gundisalvo)。(43)Alexander Fidora, Domingo Gundisalvo y la teoría de la ciencia arbigo-aristotélica, Pamplona: EUNSA, 2009.研究显示,在翻译小组当中,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学者联系紧密、合作稳定,例如,多明戈·贡迪萨尔沃与犹太人塞维利亚的约翰之间就保持了长期的协作关系,共同产出了大量翻译成果。(44)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p.111.
拉蒙德时期,翻译成果在题材上以哲学和宗教为最多,这与基督教重新阐释教义的需求紧密相关。哲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尤其是经阿弗罗狄西亚的亚历山大(Alejandro de Afrodisias)、阿维森纳(Avicena,又称伊本·西那Ibn Sina)、法拉比(al-Farabi)等人评注与阐释的版本受到充分重视,译本大量涌现;此外还有肯迪(al-Kindi)、安萨里(Al-Ghazali)等穆斯林哲学家的原创作品以及11世纪安达卢斯犹太哲学家伊本·盖比鲁勒(Ibn Gabirol,又称阿维斯布隆Avicebrón)创作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代表作《生命泉》(FonsVitae)等。在这一时期的哲学翻译中,多明戈·贡迪萨尔沃与塞维利亚的约翰合作的翻译小组贡献最多。而在宗教方面,《可兰经》与希伯来文圣经《旧约》的《诗篇》部分都在这一时期被译成拉丁文。(45)María José Prieto Villanueva, Pensar la ciencia desde la biología. Una visión evolutiva del conocimiento biológico, p.111; Alexander Fidora, Domingo Gundisalvo y la teoría de la ciencia arbigo-aristotélica, p.236.
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12世纪出现了与宗教和政治权威相对立的自主精神,对人本身的关注使得医学、数学、天文学等科学类著作亦引起译者及翻译活动资助人的重视。科学类译著贡献最多的是作品总数超过80部的克雷莫纳的杰拉德,(46)Francisco Lafarga and Luis Pegenaute, 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en Espaa, p.44.他领衔翻译了阿维森纳的《医典》(ElCanondemedicina),波斯数学家花拉子米(Al-Juarismi)的《代数学》(Compendiodeclculoporreintegraciónycomparación),托勒密的数学、天文学专著《天文学大成》(Almagesto)(4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第39页。以及托莱多泰法国天文学家查尔卡利(Azarquiel)编著的《托莱多星表》(Tablastoledanas)等。此外,巴斯的阿德拉德领衔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os),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也在这一时期被译为拉丁文。上述译著对欧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欧洲大学的教科书,如《医典》等,一直沿用至16世纪。(48)María José Prieto Villanueva, Pensar la ciencia desde la biología. Una visión evolutiva del conocimiento biológico, p.111.
小组合作翻译模式的稳定存在一方面从侧面印证了当时的托莱多宽松的民族、宗教与文化政策,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翻译过程中,卡斯蒂利亚语这一中间环节的存在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在这一时期,作为罗曼语族其中一支的卡斯蒂利亚语“尽管已经开始在公共权威的运作中扮演新的显著角色,但地位还远不能与拉丁语相比”,(49)帕特里克·J·格里:《中世纪早期的语言与权利》,刘林海译,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96—100页。因此,翻译运动的目标语言只能定位为拉丁语。卡斯蒂利亚语作为中间语言,此时发展尚不成熟,缺乏专门术语和学术词汇,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拉丁文最终译本出现错漏与缺失,例如《天文学大成》拉丁译本中甚至将大量阿拉伯文术语直接原样保留。(50)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p.112.这一情况在后来的阿方索十世时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二)第二次高峰:阿方索十世时期
拉蒙德大主教去世后,托莱多的翻译活动虽然不复之前的声势,但在其继任者的持续资助之下未曾中断。(51)Mohamed El-Madkouri Maataoui, “Escuelas y técnicas de traducción en la edad media,” p.103.13世纪下半叶,翻译学院受到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的直接支持,翻译运动迎来了第二次高峰。
阿方索十世重视文化传承,在任期间取得多项文化成就,因而有“智者”(el Sabio)之称。由于青年时代长期在安达卢斯征战,有机会较为深入地了解穆斯林文化,并对其极为推崇。1252年,阿方索十世继承王位,此时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不仅合并了半岛北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莱昂(León)王国,还攻占了南部安达卢斯的重镇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Sevilla),(52)雷蒙德·卡尔:《不可能的帝国:西班牙史》,第98—100页。国力趋于强盛,文化上也对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学者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在这一背景下,阿方索十世大力发展托莱多翻译学院,翻译运动自此受到皇室的直接庇护。王庭对译者进行直接选派,针对翻译手稿开展的审阅、校对、排版、注释等工作也相应出现,(53)Brbara Azaola Piazza,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presente, pasado y futuro,” p.126.翻译学院的组织因而更为严密,翻译质量也有所提升。除此以外,本文认为,与拉蒙德大主教时期相比,阿方索十世时期的翻译运动呈现出以下两点显著的变化:
首先是翻译活动逐渐向平民化、世俗化过渡。这一变化一方面体现在翻译题材的选择上,另一方面反映在目标语言的变化上。在题材的选择上,虽然这一时期阿斯托尔加(Astorga)主教、德国人赫尔曼(Hermn el Alemn)翻译了12世纪安达卢斯哲学家阿威罗伊(Averreos,又称伊本·鲁士德Ibn Rushd)的大量著作,犹太教经典《塔木德》(Talmud)以及神秘哲学“卡巴拉”的相关典籍翻译工作也在这一阶段进行,(54)Francisco Lafarga and Luis Pegenaute, 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en Espaa, pp.54-55.但哲学与宗教题材已经不再如拉蒙德时期一般占据主要地位,与此相应的是天文、占星、数学、化学、物理等众多实用学科的著作被重视起来、大量译介,不仅如此,民间故事、百科知识等与世俗生活联系紧密的题材也受到了关注。例如,阿方索十世即位前便命人翻译了阿拉伯故事集《卡里莱和笛木乃》(CalilaeDimna);(55)宗笑飞:《阿尔—安达鲁斯寓言——中世纪东西方文学之交的一个维度》,《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3期。同一时期,犹太学者犹大·本·摩西·哈科恩(Judah ben Moshe ha-Kohen)领衔翻译了在托莱多发现的360个刻在石碑上的配图故事,并以《石刻》(Lapidario)命名,该书被认为是一部涵盖物理、医药、星象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著作。(56)Francisco Lafarga and Luis Pegenaute, Historia de la traducción en Espaa, p.56.
另一方面,翻译的目标语言从拉丁语到卡斯蒂利亚语的转变使得翻译运动的平民化和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阿方索十世重视卡斯蒂利亚语的发展,多次要求确保将卡斯蒂利亚语作为翻译的目标语言。(57)Carlos Alvar Ezquerra, “Épica y lírica romnticas en el último cuarto de siglo XIII,” in La literatura en la época de Sancho IV, eds. by José Manuel Lucía Megías and Carlos Alvar Ezquerra, Alcal de Henares: Servicio d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Alcal, 1996, pp.13-24.与此相应地,懂得多种语言的单一译者在这一时期逐渐取代了二人合作的翻译小组,其中以改宗犹太人译者的表现最为突出,产生了拉比·扎格·德·苏胡尔门萨(Rabí Zag de Sujurmenza)、托莱多的亚伯拉罕(Abraham de Toledo)、伊萨克·本·希德(Isaac ben Sid)等代表人物。(58)Brbara Azaola Piazza, “La escuela de traductores de Toledo presente, pasado y futuro,” pp.126-127.目标语言的转变简化了翻译的步骤,使得原文的表述更为精准地得到保留,与此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卡斯蒂利亚语的学术化,加速了民族语言的发展成熟。
阿方索十世时期托莱多翻译学院呈现的第二个显著变化是原创作品的出现。翻译学院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因此在开展翻译活动之余也成为学者间交流合作的平台。在阿方索十世的倡导下,托莱多翻译学院多次召集学者合作撰书,题材涉及天文、历史、生活百科等多个领域。例如,1263—1272年,包括犹大·本·摩西·哈科恩、伊萨克·本·希德等人在内的天文学家团队在查尔卡利所撰《托莱多星表》的基础之上编写了《阿方索星表》(Tablasalfonsíes),对两个世纪后哥白尼学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9)Julio Valdeón Baruque, Alfonso X el Sabio. La forja de la Espaa moderna, Madrid: Ediciones Temas de Hoy, 2003, pp.172-177.同一时期,由犹太学者、穆斯林学者、卡斯蒂利亚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教士共同编纂的天文学百科全书《天文学智慧集》(Librosdelsaberdeastronomía)问世,全书共16章,虽然部分译自阿拉伯语和阿拉姆语的相关著作,但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原创章节。(60)Carlos Alvar Ezquerra, “Épica y lírica romnticas en el último cuarto de siglo XIII,” pp.13-24.此外,关于象棋、纸牌等游戏的著作《游戏之书》(Librodelosjuegos)也是这一时期知名的原创作品。(61)María José Prieto Villanueva, Pensar la ciencia desde la biología. Una visión evolutiva del conocimiento biológico, p.112.
13世纪末,随着阿方索十世统治的结束,托莱多翻译运动逐渐落下帷幕。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的托莱多翻译学院在持续促进文化西渐的同时,翻译的领域不断拓展,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合作持续加深,且随着卡斯蒂利亚语作为目标语言的提出,译作在民众当中的普及程度大幅提升,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愈加深入。而翻译运动后期原创作品的大量问世,则是民族交流达到相当程度的体现,是文化融合产生的新成果。
三、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影响
历经近两个世纪发展的托莱多翻译学院沟通了东西方文明,在中世纪的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作为中世纪宗教共存、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事例,托莱多翻译运动为西欧打通了连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通道,且凭借该文化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桥梁作用,使得以上知识与学术成果的作用迅速蔓延至整个西欧。我们将对托莱多翻译运动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更大的范围内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分析。
(一)民族语言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语言是共同体的标志之一。语言既表达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建立,也有助于推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62)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6—231页。托来多翻译运动后期,卡斯蒂利亚语成为翻译的目标语言,借助翻译运动的推动作用,阿方索十世积极推行语言的标准化,1235年,宣布托莱多当地用语为“西班牙语的标准”,规定卡斯蒂利亚语在行政领域代替拉丁语使用,成为政府的工作语言。(63)Hans-Josef Niederehe, Die Sprachauffassung Alfons des Weisen: Studien zur Sprach-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Niemeyer, 1975, pp.98-100.
随着民族语言的兴起,1270—1284年,阿方索十世以翻译学院为依托,组织编纂了的《西班牙编年通史》(EstoriadeEspaa),第一次全面记载了由圣经时代至其父费尔南多三世(Fernando III)统治时期的西班牙历史。(64)Inés Fernndez-ordóez, “La estoria de Espaa: creación y evolución,” nsula: revista de letras y ciencias humanas, No.563, 1993, p.2.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这一以卡斯蒂利亚语编写西班牙通史的工作,意在将这一成果作为一种构架民族身份的方式向大众普及。根据其对“语言共同体”(sprachgemeinschaft)的阐释,语言不仅表达或反映了共同体凝聚意识,且是建构或重构共同体的手段,(65)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第8、137页。因此,翻译运动促成的卡斯蒂利亚民族语言的成熟为西班牙民族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此后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15世纪晚期,西班牙语进入了语言标准化的新阶段。1492年,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德·内夫里哈(Antonio de Nebrija)编写了《卡斯蒂利亚语语法》(Gramticacastellana),这是欧洲第一部用民族语言刊印的语法书。内夫里哈在序言中将著作献给刚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的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 la Católica),并写道:“语言一直与帝国相伴随”。(66)Ramón Menéndez Pidal, “La lengua en tiemp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Cuadernos Hispanoamericanos, No.13, 1950, pp.9-24.将语言比作帝国或与帝国相联系, 是当时西班牙语著作的普遍主题,一些作家甚至将语言比作军旗的追随者,描写语言跟随军旗前进的想象。(67)Guillerno L. Guitarte “La dimensión imperial del espaol en la obra de Aldrete”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Spain, eds. by Antonio Quilis and Hans-Juergen Niedereh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6, pp.129-181.值得注意的是,1492年对于西班牙人意义重大:在这一年,“收复失地运动”完成;卡斯蒂利亚王国与阿拉贡王国的合并使西班牙成为统一的实体;哥伦布向美洲出发,揭开了帝国兴盛的序幕。在这一背景下,成熟的卡斯蒂利亚语成为一个大帝国的语言,成为高涨的民族归属(nationality)重要的载体之一。(6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步》,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融合
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由基督教徒、穆斯林与犹太人长期共享,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兴起正是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发展也离不开各民族学者的通力协作。另一方面,翻译学院的繁荣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的族群之间进行跨文化沟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这一文化现象本身即可视为中世纪西班牙宗教共存、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如前文所述,穆斯林与犹太译者在拉维德时期的小组翻译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阿方索十世时期,犹太人更在众多译者、学者之中充当主力。数据显示,13世纪的托莱多生活着约350个犹太家庭,这一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数量约为8万,其中半数居于卡斯蒂利亚境内。在“收复失地运动”中,卡斯蒂利亚王室与穆斯林以及犹太人多次签订协议,保障与其和谐相处。例如,1085年攻占托莱多后,王室便规定“穆斯林可选择离开或留在托莱多,其人身与财产安全皆受保护。穆斯林继续拥有对托莱多清真寺的所有权……”;而阿方索六世于1090颁布的《基督徒与犹太人法规》(CartainterChristianosetJudaeos)则写明犹太人具有同基督徒相等的追讨债务的权利,犹太法官与基督法官权利等同,且犹太人的誓词具有完全的合法性。(69)Yitzhak Ba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Christian Spain, Vol.I, Jerusalem: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2, pp.49, 193; Joseph Peréz, Los judíos en Espaa, Madrid: Marcial Pons, Ediciones de Historia, 2005, pp.52-53; Howard M. Sachar, Farewell Espaa: The World of the Sephardim Remember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43.
由此可见,托莱多翻译学院存在时期,卡斯蒂利亚王国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的宽容社会。而上述宗教宽容与文化共生之所以会在14、15世纪走向反面,通过翻译运动的目的便可窥一二。翻译运动之所以将目光投向穆斯林学者的原创作品,其中便有通过深入了解穆斯林思想,在思想层面与其展开较量、对其进行同化的目的;犹太学者的参与也是出于利用其语言优势解决翻译工作复杂性的需求。正如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所言:“在这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当局,不论是伊斯兰教的还是基督教的,都会采取能获得支配地位的措施。宗教或文化上的少数族裔会因为它们的技艺而被利用,而在其他方面则被死死地踩在脚下。”(70)雷蒙德·卡尔:《不可能的帝国:西班牙史》,第83页。由此可见,多元文化共生之所以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现实需要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在复杂社会中实现和平的手段”。(71)Chirs Lowney, A Vanished World: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Medieval Spa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25.而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基督教王国势力日增,宗教与文化宽容逐渐失去其必要性与实用性,因此,通过考虑宗教少数群体的需求来保障和平与利益的政策也随之走向了终结。
然而,多元文化共生与融合带来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首先,在人种方面,尽管发生过驱逐运动,但染色体研究显示,现代伊比利亚人的基因中有10.6%的北非阿拉伯人血统及19.8%的犹太人血统。(72)Santos Ramírez and Grupo Gea-Clío, “Luces y sombras en la convivencia de las tres culturas: judías, musulmana y cristinana durante la Edad Media en la península ibérica,” January 8, 2008, https://leer.es/recursos/comprender/-/asset_publisher/yu6Je5CpDgK3/content/luces-y-sombras-en-la-convivencia-de-las-tres-culturas-judia-musulmana-y-cristiana-durante-la-edad-media-en-la-peninsula-iberica-santos-ramirez/, 访问时间:2020年1月8日。其次,在语言方面,成百上千的阿拉伯语单词进入了卡斯蒂利亚语,使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73)杰里米·布莱克:《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高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5页。同时受翻译运动影响,卡斯蒂利亚语从拉丁语、希伯来语中都借用了大量词汇,因此被该国16世纪学者胡安·德·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称为“混合语言”,(74)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第172页。其丰富性得到大幅提升。此外,穆斯林的建筑风格、饮食与生活习惯等在当今的伊比利亚半岛依然得到传承。因此可以说,中世纪不同文化群体的交流与融合共同塑造了西班牙。
综上所述,尽管中世纪西班牙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没能持续存在,但这一文化现象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同享的社会”应有的面貌。(75)Chirs Lowney, A Vanished World: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Medieval Spain, p.14.甚至有学者指出,“现代公民政治中的所谓融合主义,正是承接自过去的西班牙”。(76)杰里米·布莱克:《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第67页。在全球化发展的当今,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世纪的西班牙或可为我们提供借鉴。
(三)人文主义的兴起
凭借托莱多翻译学院产出的成果,西班牙率先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古罗马经典,然而该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却肇始较迟,且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与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区不同的宗教背景及历史文化语境有关。一方面,14、15世纪起,西班牙人对血统的“纯正性”愈发重视,黑死病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激起了基督徒对穆德哈尔人与犹太人更深的恨意,(77)杰里米·布莱克:《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第62页。狂热的迫害情绪催生了宗教法庭,犹太人与穆斯林遭到驱逐,“由于追求绝对的信仰统一,西班牙的文化和物质发展进入死气沉沉的状态”;(78)Henry Charles Lea, “Ferrand Martinez and the Massacres of 1391,”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No.2, 1896, p.209.另一方面,持续七百余年的“收复失地运动”令基督教国家消耗了巨大的人力、财力, 随后又走上探索美洲殖民地的道路,也使文艺复兴的到来受到阻滞。此外,西班牙的封建势力强大,君主专制制度未能对新兴资产阶级采取保护和奖掖的态度,同时城市发展缓慢,因此与城邦兴起、贸易繁盛的意大利相比,人文主义缺乏发展的土壤。
尽管在西班牙国内传播受阻,托莱多翻译运动的成果却在更大的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译运动带来的文化西渐引领了中世纪西欧对哲学、宗教、科学、理性、自然、世俗生活等多个方面的重新认识与深入探索。在此基础上,以天文学、数学、医学为代表的科学思想的出现,以生活百科、通俗小说为代表的世俗意识的崛起,连同带有东方阐释烙印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经典的重现一道,共同促成了新的基督教阐释体系的诞生。翻译运动激发的注重科学精神、关注现世人生等观念与后来的人文主义思想高度契合,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文艺复兴不仅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是对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多元异质文化进行吸收、借鉴的结果。因此,这一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彰显了多元文化的贡献。
综上所述,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兴起是伊比利亚半岛民族交往和文化融合的结果,其繁荣发展也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的族群之间进行跨文化沟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成果更是连通了东西方文明,促进了人文主义的诞生。以托莱多翻译学院这一文化现象为缩影,中世纪西班牙宗教宽容、民族融合与跨文化交流的社会景象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