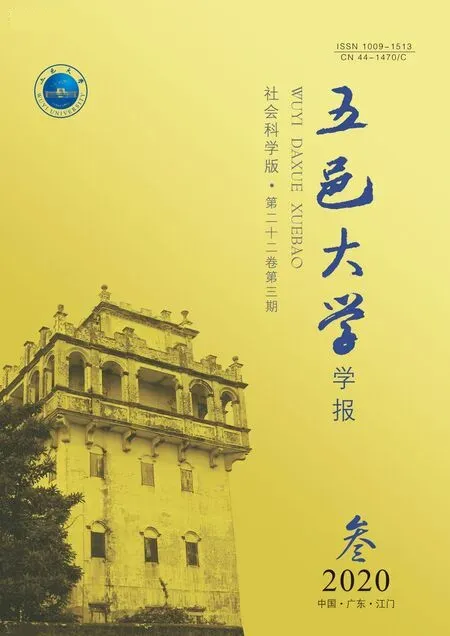《资本论》中劳动范畴的三重关系属性
2020-12-30尚小华杨红英
尚小华,杨红英
(1.五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2.韶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资本论》(第一卷)从商品范畴出发,依据原创性的抽象劳动理论,展开了对资本的批判,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史上关于劳动批判理论的制高点。全面准确深入解读劳动范畴,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资本逻辑的出发点和理解《资本论》。《资本论》揭示了诸物中蕴含的关系性要素——抽象物(劳动、价值、资本),并指出这些要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史性演变及相互作用。《资本论》(第一卷)通过对历史上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人和物的各种功能性表象的揭示,透视出这些表象背后的关系属性及关系属性对关系物的作用,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8的关系性论域。本文所谓的关系属性,即透过物与物的自然关系,揭露出其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解开资本主义的人和物的抽象化存在,及资本所具有的幽灵般的对象性的根源。
一、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内涵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32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最顽固的理论堡垒,只有粉碎其术语的意识形态外衣,才能真正探索到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没有明确地把表现为创造性价值的劳动和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相区别,更加没有分析到抽象劳动的存在。我们认为,劳动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物质性、生产性的实践活动,在具体劳动的意义上构成人类的生存条件。然而,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同时具有了抽象劳动的真实存在属性,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物的存在方式。
第一,作为形成商品交换关系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范畴涉及对于劳动范畴的形而上学理解,是理解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关键。《资本论(第一卷)》以原始的物物交换这一社会现象出发,提出并批判地证明了商品中包含了劳动的二重性原理。通过劳动二重性原理,《资本论(第一卷)》确认了作为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存在、作为价值的抽象劳动的存在,以及作为抽象劳动的人与人的社会性关系的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社会的生产表现为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整个情况出现了颠倒——社会生产的目的则表现资本自我牟利。在一个以商品交换为生产目的的社会形态中,商品交换本质上就在于抽掉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自然差别,以一定的量的比例进行交换。这种交换的依据就在于不同的商品都作为同质化的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结晶——抽象劳动而存在。可见,抽象劳动范畴的存在前提是商品交换关系的存在。
第二,抽象劳动推动了社会关系的互认。马克思用1件上衣=20码麻布为例,分析了存在于具体劳动中的抽象劳动的形成过程。这两种商品的具体劳动直接来自不同的社会分工,是彼此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生产者的劳动结果。具体劳动体现了生产者和自然物之间的物质的改造关系和能量的变换关系。因此,商品具体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是一切物质财富存在的基本源泉。然而,商品交换的神奇就在于,彼此异质的物质财富承载的是同质的、不可捉摸的、生产者彼此的社会关系互认的价值对象性。
作为日常直观的自然形式的产品物化为价值物的根据就在于生产者各自存在的抽象劳动,即由抽象劳动形成的价值成为交换的根据。生产者在彼此交换劳动产品的同时也就完成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换。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的抽象劳动的互认和社会形式劳动的出现,当且仅当“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1]95——即资产阶级的时代,这种劳动的社会化关系才能全面地被揭示出来。可见,抽象劳动范畴承载的是社会关系的互认。
第三,抽象劳动的历史性关系存在。价值实体体现了商品的社会关系本质,是商品之所以成为自身的根据和秘密。然而,价值却连任何一个自然的原子都不具有,那么,价值实体的存在只能依靠人类的抽象力才能加以发现。单纯的上衣,在没有交换前,其内含的劳动仅仅作为抽象价值而存在,缺少自身的对象性。在上衣和麻布交换的过程中,不同商品的劳动得到了互认,不同的具体劳动化为了一般人类劳动进行比较,按一定比例进行等价交换。在等价交换过程中,上衣的对象性与上衣本身的自然形式完全不同,呈现为和麻布同性质的价值属性,麻布就是物体化的价值和价值的载体。商品的价值物象化在商品的自然属性中,只有依赖交换并在交换中才能被揭示和把握。“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1]66上衣在取得了与自身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后,麻布就成为了其价值对象性的承载物,宛如上帝的羔羊承载了基督徒的羊性一样。
随着历史的演变,商品世界的相对价值形式最终在货币商品出现后获得了客观的固定性,所有商品内含的抽象劳动都通过金银体现自身的客观存在。离开了特定时代下的平等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者的抽象劳动无法对象化为价值实体,价值实体无法对象化在有用物上,有用物也无法取得社会关系的存在形式。在看似平常无奇的物物交换中,所有生产者的劳动都取得了相同的抽象劳动的特殊关系性存在,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1]88。由于抽象劳动的确立,商品成为价值实体的存在,成为了交换关系附体的关系性存在物。商品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不是纯粹的思维的产物,而是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具有独特的社会效力,其直接表征了特定的历史关系——产品不作为生产者自己的直接生存资料进行生产——的存在。
二、活劳动的创造性关系演绎
商品不是永恒的自然现象,同理,活劳动也是历史关系演变的结果。活劳动即工人所拥有的分批分次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劳动力商品。
第一,自由买卖关系的吊诡。从个人到劳动力商品的演变转化是一个历史现象。只有在资本主义因素下,个人才作为劳动力商品,拥有了交换的自由和平等。一旦在商品交换领域中确立了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劳动者在表现为物理生命的永恒自然个体的同时,又表现为劳动力商品体——可以自由、平等地出卖自身的同时,又不得不出卖自身、不平等地生产出更大价值的矛盾关系体。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就在于:作为劳动力商品,劳动力价值在交换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劳动者身体中形成,但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交换之后才得到显现,即“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和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使用价值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商品”[1]202。这种分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际表现为劳动力获得的支付报酬通常滞后于劳动力的被消费,因此,实际上就是工人冒着物理生命灭失的风险给资本家以信贷。拖欠工资和大量工人赊购生活资料的现象就是这种信贷风险的表现。
第二,从市场买卖关系到车间物化关系。《资本论》分析到,劳动者假如一次性全部卖光自身的劳动力,那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转化为自身成为商品。因此,劳动力商品维持自身的必要条件还包括分批分次地出卖自身的劳动能力。此时,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出现了:工人作为自然生命的个体,其生命是连续不断的,必须依靠源源不断的一定量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资料以维持自身和后代个体的物理生命。但是,维持其生命存续的条件却是分批分次的,因此就存在断供的风险——失业。
走进资本主义生产的车间,我们就从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进入到强弱分明的统治关系。因为在车间里面,工人肉体所拥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作为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存在。资本家使用劳动力的过程和消费任何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仅仅把劳动力视为一个他付钱购买的死的商品,一个像酵母一样的会发酵的商品。“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1]216-217这样一来,在劳动力的买卖过程中,作为物理生命的工人个体褪去了劳动以外的任何属性,仅仅成为商品意义上的价值存在,用来和资本家的货币进行交换。
第三,活劳动的人格化。活劳动的首要意义就是指依附在生命体内、能够补偿自身价值的工人个体所拥有的体力和脑力。一方面,活劳动使得过去劳动的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在新产品上得以保存和延续,即保存原有的资本价值,使得资本家投入的各种要素在新商品上存活;另一方面,活劳动的活也在于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工资后,从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转换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即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在资本家组织的生产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对作为使用价值物存在的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将会创造出比劳动力商品价值更大的价值。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工人则成为人格化的劳动,这是双方在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存在本性和实际状况,也是双方的真实实体。“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产物。”[2]活劳动依赖于客观的雇佣关系的存在,并成为雇佣关系存在的明证。
机器、商品、货币、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不但不再是活劳动借以确认自身本质力量的、有目的的生产手段和材料,反而成为了对活劳动提出要求并强制活劳动的主体性存在,仿佛这些死劳动是在借助活动来确认自身本质力量,“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1]359可见,如果我们从自然客体角度来定义死劳动和活劳动,就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完成了从社会主体性角度的颠倒,死劳动成为主动的压迫性劳动,活劳动成为受动的被压迫的劳动。
三、死劳动的剥削关系本质
死劳动即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关系的物化。《资本论》对资本对死劳动的贪婪做了生动的比喻,它指出,资本作为自然状态上的货币和生产资料形式的无生命的死劳动,由于剥削关系的存在,导致它成了拥有生命的、主动的吸血鬼。
第一,货币流通关系的奥妙。作为死劳动的资本主要以货币的形式存在,“资本按其概念来说是货币。”[3]229货币在简单流通过程中,作为衡量商品双方抽象劳动价值大小的等价关系和作为交换得以顺利进行的媒介关系而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流通的形式从简单商品流通转变为社会关系性的货币流通——生产者和消费者实现了彼此社会关系的互认。在货币流通中,从货币出发,经过商品物,再返回货币。货币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和终点,同时追求抽象财富的货币也成了生产的目的。“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1]140由此,货币开始具有了独特的魔力,一切产品只有依赖货币才能表现出自身的价值,才能成为商品。货币流通导致货币成为了现实的神灵,不过是资本统治关系的化身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货币表现。货币拜物教是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1]93。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通过货币流通过程实现了自身地位的跃升和整个社会关系的互认。
第二,对剩余劳动的强制占有关系。资本充满了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具有依赖活劳动、不停吮吸活劳动的关系属性。资本在不断增殖自身的同时还创造了一种假象,即资本是通过等价交换购买到活劳动的,因此,“它的无偿部分似乎必然不是产生于劳动,而是产生于资本,而且不是产生于可变资本部分,而是产生于全部资本。”[4]我们只有透过这种假象,通过分析资本的商品形式、货币形式等存在形式才能看到:资本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代言人,而资本家又是资本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占有的不过是超出活劳动价值的剩余劳动的积累。
马克思认为,追求剩余劳动的前提条件就是交换价值在一个社会形态中占优势地位——即资本化的社会。资本为了不断占有剩余劳动,必然会无休止地对活劳动进行榨取。这种榨取的形式和古代社会对金银的追求存在类似之处,即存在过度劳动现象。资本“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1]297。在贪婪的剥削关系的统治下,剩余劳动成为了资本追逐的无限目的,这种贪婪突破了道德界限,也突破了生命体的界限。这种贪婪除了导致工人成为抽象的胃以外,还将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都卷入了服务于交换价值的逐利旋涡。由此可见,资本本质上就是一种对剩余劳动的强制占有关系。由于这种强制占有关系的存在,剩余劳动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更多的资本,加固了资本的地位和力量。
第三,死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忽视了劳动范畴的历史属性,更加忽略了劳动背后的社会关系的差异性,因而无法从整体联系的高度洞察范畴的辩证关系存在。在这种非关系性的分析视角下,“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214“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5]死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关系表现为主客关系和主体性的颠倒。我们只有把握到资本主义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性关系存在,才能避免将资本看作生产工具式的非历史、非关系性的抽象的分析视角。资本借助雇佣关系,通过对活劳动力商品的购买,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延长工作日等方式对活劳动进行无休止地消费,进而贪婪地占有剩余劳动,将形式上平等的雇佣关系转变为实质上不平等的剥削关系。
商品价值形成的过程中,同时也客观存在一个体现了剥削关系的价值增殖的过程。在剥削的过程中,活劳动不仅要补偿资本购买活劳动而支付的价值部分并因此要进行必要劳动,还要被迫完成工作日规定内的法定劳动时间,甚至是高强度、超过法定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因此,活劳动的存在形式不仅表现为苟活,而且表现为“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作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1]381。所谓苟活,即在形式表现为死劳动的资本的统治下工人出现了“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1]311等苟且维生的生命退化现象,同时还表现为生产过程中被要求延长工作日、提升劳动强度等一系列规定导致的身心压迫。
四、劳动范畴三重关系属性的时代启示
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所有劳动被抽象为雇佣劳动。”[6]无论是活劳动还是死劳动,都成为了抽象劳动。这种抽象性劳动存在的具体表现就是劳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取工资,进而导致了劳动者状态的被动化、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简单化和机械化,以及劳动目的的货币化。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资本力量的独裁和劳动者的生命丰富性的丧失。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资本力量日益强大导致的忽视劳动者权益的极端剥削化倾向。只有加强对资本统治劳动的本性认知,我们才能通过适当的政策和制度引导资本、节制资本,使得资本为劳动服务、为劳动者服务。在当前特殊的疫情防控时期,我们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在此前提的保证之下有序开展复工复出活动,这正体现了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敬畏,体现了对资本的节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总之,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激活资本对财富创造的有利因素,最大化资本对助推科技发展的客观效应,实现资本关系的为我化存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联合体性质的生产关系,保持劳动者对资本的主人翁态度,这样活劳动的创造积极性一定能够更加充分地释放出来,劳动者的美好生活就一定能加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