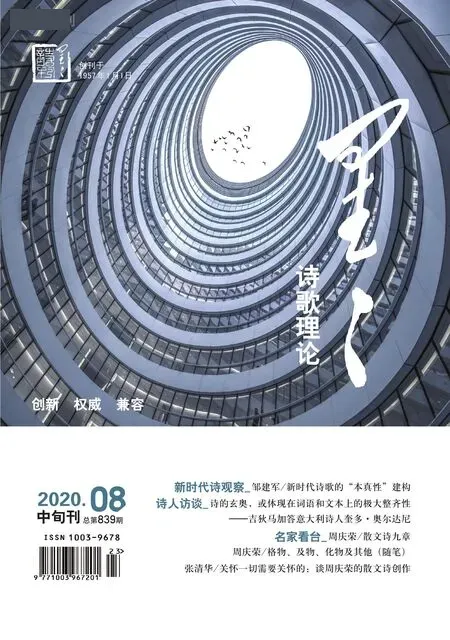可视的世界,不可视的神秘——读费尔南多·佩索阿《我在审视无法看见的事物》
2020-12-30远人
远 人
我在审视无法看见的事物。
天就要黑了,
我所渴望的一切,
受阻于墙壁。
天空巨大;
我能感觉到上方的树木;
现在,随便一阵风,
树叶都会颤动。
一切都在彼岸——
一切,包括我的思想,都在那边。
没有一根晃动的树枝
能将天空变得渺小。
我的睡眠和我的生命
融合。我毫无
感觉;也不悲哀。
但我终究是一个悲哀的东西。
(杨子 译)
从古至今,没有哪个成名的诗人或作家不在为读者提供与众不同的文本。所谓与众不同,就是其作品呈现出一种观察生活和世界的独特视角。葡萄牙后期象征主义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的诗歌的确给我们意外的观察角度,我们不仅看到这一观察的结果,还看到佩索阿独特的观察方式。从他的方式中还能发现,我们原本以为熟悉的世界竟然出现了意外的陌生感。
不知这首短短的《我在审视无法看见的事物》是不是佩索阿的代表作,我只是在阅读中发现,这首诗展现的视角很难在另外一个诗人笔下出现。现代派诗歌从庞德开始,全力针对“物”的出现和刻画,那些现代派诗人们无不在意象中寻找簇新的表达。我们不应忽略,有意象,就意味着可视。进言之,庞德以降的现代派诗人,无不在可视上下功夫。佩索阿看似反其道而行之,实则从写作开始,佩索阿就以冥思的方式进入自己对世界的探求。在他那些公认为代表作的长诗《牧羊人》《烟草店》等作品中,我们就领教了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诗人如何将双眼转向冥思的领域。冥思并不可视,佩索阿令人意外的是他将不可视转化为语言的可视。这是一种全新的角度。没有自己的角度,一个诗人很难为世人瞩目。
这首诗开宗明义,题目和第一行就明确告诉读者,“我在审视无法看见的事物”。“无法看见”就是面对了不可视。世上有不可视的事物吗?当然有,既然事物有可视的,当然就有不可视的。二者的区别是,可视的事物我们能明确地指认,不可视的则不可指认,甚至会怀疑它的真实存在。事实上,佩索阿每日不间断的冥思就是不可视的一种。没有人能目睹另一个人的心理,所有人的思想、念头及感觉都需要用种种手段表现出来之后,才能由不可视转化为可视。但这时的可视也仅仅是语言或其他手段完成后的可视,所以我们在佩索阿诗中读到的,依然是不可视。
追求不可视和表示不可视是两个有所交叉的领域。佩索阿要的就是这一交叉,所以,我们从这首诗的第二行开始,就时时撞见可视的代表如天空和墙壁。天空可视,墙壁可视,在佩索阿的冥思依附下,我们又觉得这些可视物充满难以言说的象征。在常人那里,天黑就是天黑,在佩索阿这里,则不仅关乎自然,还关乎内心,所以他笔下的天黑有种神秘意味,因为“无法看见的事物”正伴随天黑而来;当墙壁在常人眼里不过是一堵人工建筑时,在佩索阿那里,它的作用却是遮挡了“无法看见的事物”。这种极具逻辑的表述在读者那里造成信服。没有信服感的诗歌谈不上是诗歌。正是信服存在,我们才愿意跟随佩索阿的诗行往下走。
不可视的事物是因人的感觉而来,所以,佩索阿感觉黑夜的“天空巨大”,感觉天空里充满“上方的树木”。我们能够体会,“树木”是佩索阿的白天所见,现在这些可见的成为不可见的,这种自然转化在他的表述下即刻变得神秘起来。“现在,随便一阵风,/树叶都会颤动”,同样是白天的可视现象,当它们成为不可视之后,对佩索阿的感觉就造成极度的敏感,所以我们发现,佩索阿越是将简单的事物纳入感觉的领域,这些存在反而会变成感觉的游离,佩索阿又偏偏用无比肯定的诗句表现这一游离,这就使可视与不可视成为相互撕裂的两种事物。没有极度的敏感,佩索阿就进入不了这一相互撕开的空间。所以,当事物永远是事物之时,佩索阿已经发现了事物深处蕴含的神秘和不可视的部分。
对佩索阿来说,他能将可视的转变成不可视的,是因为他将感觉指向了存在之外的“彼岸”和“思想”。这恰恰是人类最渴望探索的领域。当他确认“一切……都在那边”时,佩索阿就已自觉地进入个人的哲思。诗歌厌恶哲理,因为哲理不乏说教的意味,但诗歌从不拒绝哲思,诗歌本身蕴含“思”的存在。和庞德们的意象相比,佩索阿的哲思表现当然更具难度。我们不能说佩索阿在发展诗歌。诗歌本身不可能发展,诗歌只可能在某个维度上展开深入。佩索阿的维度不同于庞德,也不同于大多数现代派诗人,这既是他的生活所致,也是他心灵的触动所致。人最被什么触动,就会形成什么维度。佩索阿的生活谈不上波澜壮阔,所以他将全部行为赋予在心灵的感受之上。在他那里,我们发现一个写作者的内在视野究竟能打开得多宽。从现实到冥思,从阁楼到宇宙,是佩索阿毕生所走的思想之路,所以常人不太常用的“思想”一词,在佩索阿那里随处可见。对一个诗人来说,越囿于现实,越易展开冥思;越是生活单调,越易展开渴望。二者驱使佩索阿不断地进入内心。内心的无尽对应了佩索阿渴望的无尽。对任何人来说,内心的渴望正是最大的不可视。
我们总说认识自己才认识世界,反过来说,认识世界的,也必然是认识自己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佩索阿在诗中写了多少和世界有关的可视事物,最终仍将目光转向内心,实际上,也不是他在最后才将目光转向自己,而是一开始就从自己出发。他太知道自己,所以也太知道世界。所谓世界,决非是表面认识的那样,人有内在,世界也有,正是太多不可视的事物才构成世界的真实内在。人最终能不能认识世界的内在?这恰恰是佩索阿在哲思下掩藏的思考。他知道世界有内在,却无法破译那些内在。个人太渺小,哪怕一代代名震八方的思想家,也在那些不可破译的内在面前束手无策。只是思想家未必有诗人的感性。所以,“不悲哀”的佩索阿仍感到“自己终究是一个悲哀的东西”,这不是他个人的悖论,而是世界本身的悖论。佩索阿令人敬佩之处,也就是他指出并承担了既属于人,也属于世界本身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