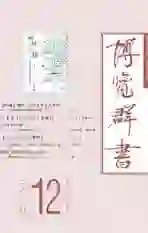在暗淡的外表下
2020-12-28李璐
李璐

按照惯例,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诺贝尔文学奖揭晓,这次,瑞典学院将2020年的奖项颁给美国桂冠诗人露易丝·格丽克,获奖理由是“她那无可辩驳的诗意的声音,通过朴素的美让个体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国内读者对于露易丝·格丽克并不熟悉,她的作品的中文译本只有文景出版社的柳向阳翻译的《月光的合金》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以及台湾宝瓶出版的陈育虹翻译的《野鸢尾》。
诗人生平
从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和《纽约时报》第一时间发布的消息中可以得知,露易丝·格丽克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现居马塞诸塞州剑桥市,是一名诗人也是耶鲁大学的一名英语教授。格丽克是继1996年波兰作家维斯瓦娃·辛波丝卡之后第一位获得该奖的女诗人,也是继2016年鲍勃·迪伦之后第一个获得该奖的美国人。她在美国现代诗坛是经典一般的存在,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十数部诗集和一部散文集,是2003年至2004年的美国桂冠诗人,曾获全国图书评论家奖、普利策诗歌奖、兰南文学奖、博林艮诗歌奖、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创作实力毋庸置疑。
格丽克生于纽约一个匈牙利裔犹太家庭,她的母亲就读于著名的卫斯理学院,父亲经商,保障了格丽克稳定优渥的生活。格丽克在一次题为《诗人之教育》的演讲中回忆道,母亲对于孩子展现的创造性天赋一直鼓励:
姐姐和我在每一种天赋上都得到了鼓励。如果我们哼个不停,我们就上音乐课;如果蹦蹦跳跳,就去学跳舞。诸如此类。我母亲念书给我们听,然后很早就教我们开始念书。我还不到三岁,就已经熟悉希腊神话了。
青春期时的格丽克饱受厌食症、失眠和抑郁的困扰。在她出生前,她的姐姐,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就因厌食症离开人世。似乎某种神秘的关联性,格丽克在青春期中期也出现厌食的症状,甚至严重到辍学接受心理治疗。在治疗期间,格丽克参加了莎拉·劳伦斯学院的诗歌课(1962)和哥伦比亚大学通识教育学院的诗歌研讨班(1963-1968),师从美国德高望重的桂冠诗人斯坦利·库尼兹(1905-2006)。如果说心理分析帮助格丽克实现内省,那么写诗则将这种过程形象化,两者互相促进,为格丽克战胜心理疾病提供了重要帮助。
创作初期——后自白派的心理分析
格丽克的诗歌主题聚焦于爱欲、生死、孤独、信仰、毁灭和存在等具体又根本的问题,“经常像是宣言或论断,不容置疑”。加之其文字简洁直白,锋芒毕现,颇有一种神谕的质朴与威严。格丽克的直白恰恰是对于练字的专业,并不以文字的玄虚来烘托主题的高深,而是专注于捕捉日常经验中的启示与顿悟,开拓出一种深邃神秘的境界。被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称为当今美国最纯粹、最有成就的抒情诗人,格丽克早期的诗歌风格也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语言的锤炼。格丽克的写作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美国正处在私人化写作盛行的时期,东部的自白派以坦白的方式揭示诗人的私人生活和内心活动,以一种心理现实层面的自白,探究和追寻自我,实现诗歌的拯救作用。格丽克诗集的中文译者柳向阳认为从美国诗歌的传统来看,格丽克的早期作品就受其影响,更准确地说,她是后自白派;自白派沦陷于抑郁症,她则战胜了心理疾病,超越了自白派,超越了自己。《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中评价,格丽克自第二部诗集《下降的形象》(Descending Figure)开始将自传性材料写入她凄凉的口语抒情诗里。这正代表了诗人的学徒时期,以自我为轴心抒发对于爱与性的渴望与犹疑。在这一阶段,童年家庭生活中的姐妹之情、母女关系、亲人离世都成为其写作素材。正如她在《自传》一诗中写道:“我有一套爱的哲学,宗教的哲学,都是基于早年在家里的经验。”格丽克善于把握人心隐微之处,这与她接受心理治疗时学习心理分析关系密切,心理分析教会了她“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正如她在诗歌《不可信的说话者》中表达:
不要听我说话;我的心已碎。
我看什么都不客观。
我了解自己;我已学会像精神病医生那样倾听。
当我说得激情四溢,
那是我最不可信的时候。
这种对于自身情绪的剖析,无疑让人关注其作品的自传性,但这恰恰是诗人极力摆脱的。在她看来,自己的创作之所以取材于个人生活,不是因为它们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范式。
创作中期——古希腊的诗歌面具
格丽克在创作中期开始转向寓言修辞,展现了向古希腊传统的回归。其中以《阿基里斯的胜利》(1985)为代表,该诗集因古典神话和《圣经》典故的插入,个人色彩被冲淡,于是作家在表现欲望、自由、权力等主题时,更加直白,毫不遮掩。在《阿基里斯的胜利》中,她描写陷入悲痛中的阿基里斯,“他已经是个死去的人,死于/会爱的那部分/会死的那部分”。然而,诗歌不是在表达神祗们的情绪,而是对个人精神生活和外部社会生活的反映,神祗成为格丽克表达自己的安全代理人。就像丹尼尔·莫里斯指出的,“格丽克用神话人物作为伪装,创造了具有公众意义的个人叙事”。这也是译者柳向阳反复强调的——古希腊传统是格丽克的诗歌面具。
格丽克诗歌的另一个特点是整体性,作家赵松在访谈中说道:“她的所有诗歌,即便你抹掉时间、打乱编排,依然能看到一种整体性和生长性。”因此,欣赏她的诗歌,要从整体中去感受,“她的诗歌不是一棵树,不是十棵树或一百棵树,而是衍生出了一整片丛林”。这而这,也正是格丽克有意为之,在她看来,“学会组织一本書,让一叠诗成为一张弓、一句锋利的言论,让人既兴奋又压抑。”早期五部诗集的最后一部 《阿勒山》(Ararat)就是“组诗体”的首次尝试,也是由此开始,格丽克成为一位“必读”的诗人,每部诗集都可看作一首精巧编织的长诗或一部组诗。
格丽克趋向成熟的代表作是获普列策奖的诗集 《野鸢尾》(Wild Iris),这也是诗人最广为流传的诗集。与之前作品中嵌套的神话典故不同,诗人化身为花草、“季节之灵”“时光之灵” “万物之灵”,体验万物经历的生命考验和蓬勃喷涌的生命力。野鸢尾在冬季过后,从地底破土而出,湛蓝的花朵是新生命的力量,如同经历灵魂的再生:
你,如今不記得
从另一个世界到来的跋涉,?
我告诉你我又能讲话了:一切
从遗忘中返回的,返回?
去发现一个声音:?
从我生命的核心,涌起?
巨大的喷泉,湛蓝色?
投影在蔚蓝的海水上。
在《野鸢尾》打造的寓言体系中,场景是花园,人物是上帝、园丁和自然,通过彼此的对话和借位思考,展现了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考,而采用这样的结构方式是“20世纪末诗歌书写所冒的风险,但格丽克赢得了赌注 ”。
巅峰期——内化的自省
晚近的格丽克又回复了神话原型传统与自白诗的结合,只是与早期依靠敏感通灵的直觉推动不同,诗人对于诗歌的把控更熟练,开始将外宣的情感内化淬炼。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被学界公认为其创作力巅峰之作的诗集《阿弗尔诺》(Averno,2006),讲述了珀尔塞福涅被劫为冥后,在冥界与尘世往返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格丽克并不是从传统的女权主义视角一味指责冥王哈迪斯以爱之名行使伤害,而是以清冷的语气客观审视双方。在《漂泊者珀尔塞福涅》 一诗中,她对珀尔塞福涅加以讽刺:
珀尔塞福涅正在地狱里过性生活。
不像我们其他人,她并不知道?
冬天什么样,她只知道?
冬天是因她而产生。
在格丽克看来,女性身份并不意味着接受性别差异的观念,艺术不应受制于观念的差异,而应在揭示差异的过程中“变得更有趣、更微妙”。“艺术之梦不是去宣示已知的东西,而是去照亮被隐藏的东西,那通往被隐藏世界的小径并没有被意志标示出来”。诗集中的18首诗歌,“以相互关联的复杂形象、一再出现的角色、重叠的主题,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集合,但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失于为整体而言说”。格丽克继续从神话原型中发掘与现世感知的关联性,用来对抗孤独、遗忘、记忆枯竭、情爱腐蚀以及精神毁灭的负面情绪。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总结:格丽克不是一个在痛苦面前退缩的人;如果你想要肤浅的谈话或轻飘飘的讽刺,那么格丽克的诗歌就不适合你。可以说,诗人在后期的诗歌中,通过神话镜像的剖析将自我的存在状态逐渐显露,从而实现了自我认知。
格丽克的折桂在专业人士看来理所当然,她是一个经典化的诗人,持续高产且获奖无数,作品更是经常出现在教材和选本里。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情感的外部投射,格丽克总能以清晰准确的遣词造句表现她对于世界的玄学思考。她的诗集构建出整个世界,扩大了诗歌对于读者情绪的唤起作用。应该说,诺奖的颁奖词对于她风格的把握无比精准,格丽克的语言朴素,接近口语和普通语法,对于节奏和短语的把控力卓绝,独立准确,并足够反映本质;她将主体经验在诗歌话语中反复重塑,恪守从多角度呈现问题的诗学理念。她的获奖,让诗歌爱好者们高呼胜利,在话题引领资本的出版市场,也许能带领大众通过其诗歌暗淡的外表欣赏其下掩映着的沉沦世界的诗性之美。
(作者系山西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