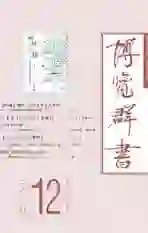评《为敌人正名:在南非成为人》
2020-12-28胡忠青
胡忠青

扎克斯·穆达(Zakes Mda,1948-),又名扎内穆拉·基齐托·加蒂尼·穆达(Zanemvula Kizito Gatyeni Mda),是南非著名的黑人剧作家和小说家。在承袭南非英语文学批判现实的这一创作指向的同时,穆达摈弃了主流作家的精英叙事传统,转而致力于表现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其立足民间的文学创作,不仅使他成为同时代最受欢迎的南非英语文学作家,也使他成为南非文学史上最受关注的黑人作家之一。
2017年,七十高龄的穆达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论文集《为敌人正名:在南非成为人》(Justify the Enemy: Becoming Human in South Africa)(以下简称《为敌人正名》)。该文集收录了穆达在各个时期的论文、公共演讲和媒体访谈等非文学作品,涉及穆达对文学创作、文化传承和社会问题等多方面的论述。通过这部文集,穆达不仅向读者阐释了一名作家对于创作艺术的思考,而且身体力行地向读者展示了作家在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对创作艺术的内部探索
在穆达的小说中,魔幻与现实交织,想象与真实并存。欧美有些文学评论者习惯地将其小说归类为“魔幻现实主义”,并认为他的小说是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对此标签,穆达极为反感。他强调,他的魔幻叙事是非洲口头传统的现代延续,是非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魔幻与现实结合的叙事方式赋予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英雄们神奇的力量。正是这些不遵循现实主义和理性路线的神奇元素赋予非洲口头传统独特的魅力。
口头传统不仅启发了穆达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且成为他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小太阳》(Little Suns,2015)、《红色之心》(The Heart of Redness,2000)和《祖鲁人在纽约》(The Zulus of New York,2019)等故事所依仗的正是人民反抗殖民统治者的历史传说。在穆达看来,有两种创作历史小说的方法:一种是重写过去,保持对历史的尊重;另一种是改造过去,颠覆历史记录。历史是胜利者的故事,是统治精英将自己统治合法化的官方叙事。而历史小说是质疑和挑战霸权主义历史叙事的有效工具。其目的是将那些此前被边缘化的历史叙事拉向中心。所以,穆达总是站在人民立场,从底层民众的视角重新解释历史。然而,他并没有取材于档案资料,而是将口述历史融入到文本中,使其成为讲故事的手段,让读者通过虚构的人物来体验历史,反思历史对自身产生的影响。具体到个人历史的书写,穆达反对迎合西方读者期待心理,在自传中放大个人苦难的做法。他认为,自传作者要做的是如实呈现自己的过往,而不是有意以半虚构的方式塑造一种典型的非洲经历,以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所以,在回忆录《时有虚空:一个局外人的回忆录》(Sometimes There Is a Void: Memoirs of an Outsider,2011)中,穆达坦白了自己不堪的过往,也如实呈现了南非的社会现实。因为过去的经历,才塑造了当下的自己。

与此同时,穆达极为注重小说中地理景观的书写。他的小说创作总是始于一个真实的地点,而不是故事。对他来说,树木,岩石,青草和河流等地理景观是记忆的储存地,因为环境因素决定了角色的情感,也决定了他们的认同感。所以,在每一部小说中,穆达都注重塑造不同的地理景观,通过地理景观揭示底层百姓的生存困境和自我救赎能力。《唤鲸人》(The Whale Caller,2005)、《后裔》(Cion,2007)和《埃塞镇的圣母》 (The Madonna of Excelsior,2002)等小說的创作都源于地理景观的激发。尤其是在小说《埃塞镇的圣母》中,穆达创造性地以语象叙事的方式,将自由州广阔的地理景观引入小说,颠覆了黑人被排除在非洲景观之外的白人书写模式。这种由地理景观进入故事的写法,具有极大挑战性,却给予穆达充分的创作自由。
穆达对地理环境的倚重,并不仅仅在于地理叙事在表现社会整体性与全面性的同时,帮助提升小说的主题意蕴。其更为深层的根源在于,穆达试图通过地理书写缓解非洲人与自然地理日益疏离的焦虑。南非的种族主义统治将包括黑人在内的有色人种限制在荒凉贫瘠的边缘地区。这种地理空间的划分与限制,使得黑人们在内心深处认为自然地理是原始的、落后的,也导致黑人把对白人的痛恨延伸到后隔离时期政府为保护南非自然生态所做的努力。黑人们普遍认为,后隔离时期的政府更关心环境保护,而不是黑人大众的生活。所以,大部分黑人往往对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保护采取敌对立场。部分黑人读者甚至认为穆达的地理书写是“白人的事情”。对此,穆达并不气恼,他认为,“问题不在于黑人们不关心环境,而在于环境正义的论述并没有以一种直接相关的方式来构建他们的生活”。所以,穆达在小说中始终以一种与百姓生活相关的方式来书写地理,展示人性如何与自然相互依存。
作为一名剧作家,穆达始终秉持“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戏剧创作原则。为此,他经常带领自己的学生深入边远地区感受底层民众的生活,并为他们演出戏剧。不仅如此,他还邀请农民参与戏剧创作,引导农民通过戏剧表现自己的生活,反思社会问题。所以,他始终认为,戏剧的最高境界是“观众也是演员”。
对社会现实的内省与外察
1997年,穆达给时任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以自己回归南非求职受挫的经历为例,表达了自己对南非政府系统任人唯亲现象的担忧。因为这种权力腐败已经严重阻碍了民主国家的发展。他认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是黑人赋权运动,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黑人赋权运动只是将少数与政治有关系的人变成了“革命新贵”,众多的黑人革命者和被排除在权力体系之外。底层黑人也被排除在社区的规划与发展计划之外。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存在的问题是,曾经作恶的人在坦白自己的罪行后,继续逍遥法外,受害者却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补偿,只能背负着过去的伤痛继续挣扎。而且,统治阶层关注的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和解,却忘记了黑人之间也迫切需要和解。曾经的种族主义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严重破坏了不同族裔,不同部落黑人之间的团结。黑人内部的分裂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国家发展。
政府系统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攀升,犯罪频发,艾滋病泛滥。乱象丛生的社会催生出两个更为根深蒂固的问题:炫耀性消费和即时满足。很多黑人用昂贵的服装,奢华的派对,华丽的婚礼和时髦的葬礼来补偿内心的自卑情结。而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大量黑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导致犯罪率的进一步攀升。同时,这两种疾病助长了南非黑人的仇外情绪。所以,穆达认为,唯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才能让深陷其中的黑人真正觉醒,奋发向上,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实现自给自足。然而,长期的殖民统治历史,致使南非形成了依赖外来力量发展自己的习惯。政府将发展“交付”与外围国家。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被否定了。而这种“交付”的概念造成并加强了人民的依赖心理。穆达将这种病态的“依赖”概括为“非洲病”。所以,穆达认为,南非政府和企业界以牺牲黑人大众利益的代价为新殖民主义资本铺路。正是黑人自己使新殖民主义成为可能。
然而,包括穆达在内的南非知识分子们对南非现存问题的反思与批判,招致部分黑人统治精英的抵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黑人不应该批评黑人,否则就是授白人以柄。而穆达则认为,敢于监督和批判政府,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大众媒体必须发挥监督作用。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应该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穆达也是始终将对南非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愤世嫉俗者。在自己的大半生中,他见证了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始末,深切感受到了新南非的建立为南非人民,尤其是黑人们的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空前数量的黑人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到了国家提供的电力和清洁的水;独立的大众媒体和强大的公民社会的有效制衡帮助深化了南非的民主;独立于政府的司法体系使南非的人權法案逐渐完善。这些都是新南非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越来越多锐意进取的年轻人,投身于新南非的文化和经济建设。作为泛非主义者,穆达关注的是整个非洲。他极力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对“非洲”和“非非洲”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否定了黑人文化的活力和多样性。非洲身份是一种正处于重新形成,重新定义过程中的身份,需要从地缘政治身份,即那些与非洲有着共同历史、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人的角度来考量。
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作为作家,穆达研究文学创作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创作来反映现实;作为南非国民,穆达积极发现南非社会存在的问题,并为南非的政治文化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穆达对南非建设的参与并不仅限于笔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例如,他开办作家讲习班,向年轻作家传授写作经验;开办创意写作坊,指导爱好文学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从事文学创作,并帮助他们将作品转化成文化产品;为农村贫困人口寻找致富途径等。所以,穆达也是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穆达一方面鼓励新一代的艺术家打破种族隔离主题的束缚,创新写作模式,将国际风格与非洲传统相结合。另一方面,穆达也提醒他们,白人与黑人互为存在,互为影响。种族主义统治历史曾经形塑着作家的创作,也将继续影响着当下的文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即使是描写一个敌人,也要让他充满人性,也即作家要在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要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小说中的人物,而不是在分析他们的错误行为时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所以,在之后的小说创作中,穆达始终坚持辩证书写小说人物。不仅如此,穆达还将这种平等理念延伸到了人与非人类关系的建构。在他的笔下,自然万物皆有灵,是与人平等的存在。他告诫年轻作家,作家应该把自己想象成小说人物,赋予他们人格,并以相同的方式构想非人类的存在。这种以同理心看待与描绘敌人与非人类的态度,既是穆达的创作态度,也是他的人生态度。所以,他传授给青年作家的知识既是写作技巧,也是人生哲理。
穆达注重从自然环境中汲取创作灵感。但是他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仅仅是索取。他总是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回馈大自然。在一次外出采风的历程中,一座开满野花的大山给了穆达愉悦的视觉享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的贫瘠和乡村空间女性化问题。由此,穆达本能地想到一个问题:如何让这座山美的更有价值。为此,穆达自费学习养蜂课程,积极帮助当地村民开办养蜂合作社,引导当地村民合理利用这座山上的自然资源。养蜂事业在为当地村民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帮助当地留守妇女走向独立。这种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经历也激发了穆达的创作灵感。例如,在小说《艾克莎修的圣母》(The Madonna of Excelsior, 2002)中,养蜂成为主人公尼基自我救赎,改善人际关系的途径。所以,穆达将自己的小说视为“公共行动文学”,即社区行动主义与文学创作共生关系的结晶。为此,穆达呼吁南非的政府系统,以及有能力的企业等,应该像他的养蜂合作社,以及柏科基金会正在开展的乡村帮扶计划一样,在全国范围开展“领养乡村运动” ,建立社区发展项目,通过基层改造社会。
至此,我们有必要回头重读一下该论文集的标题:“为敌人正名:在南非成为人”。通过对书中收录论文的解读,我们不难看出,“为敌人正名”,意指在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去辩证看待一个人及其所作所为,哪怕他曾经是你的敌人。在此过程中,人们要反思,他人的行为与自身存在的关系,自己在他人成为其人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种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正是后隔离时期南非民众以及南非统治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建设中应该秉持有的态度。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和实现被惨痛历史扭曲的人性,“在南非成为人”。如何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穆达通过这部文集给出了答案。在他看来,敢于正视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敢于批判性传承非洲的传统文化,南非,乃至非洲才能走上和谐发展的道路。
严格来讲,穆达的这部文集并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集。因为其中有多篇原发表于各种非学术杂志的社会评论文章。穆达另有其他一些研究戏剧与小说创作的论文并未被收录在这部文集中。但是,这部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已经充分展现了穆达身份的多样性。作为一名作家,穆达专注于文学创作,积极探索文学创作的内在机理,体现了作家敏锐的感知力与创造力;作为一位普通公民,穆达将作为南非公民的内在体验与流散知识分子的外在审视相结合,深度剖析南非现实,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穆达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帮助他人,参与社区建设,体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在回忆录中,穆达不止一次提及说,他时时感受到一种局外人的痛苦,一种虚空。从论文集《为敌人正名》中,我们或许能一窥究竟。他的虚空,他的痛苦更多是来自于他对社会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悟,以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力感。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评论家们既批评他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太过“鲁莽”,又称赞他的写作“引人入胜,大胆无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