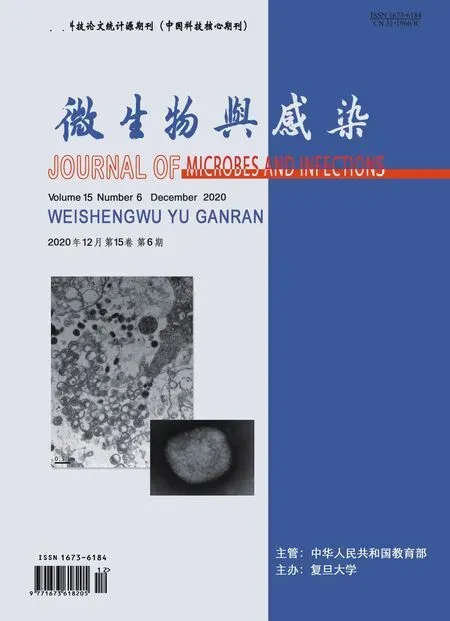肠道菌群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肝病的研究进展
2020-12-28徐文心张欣欣
徐文心,张欣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临床病毒研究室,上海 200025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有2.57亿人口患有慢性HBV感染,其中88.7万人因乙型肝炎(简称乙肝)并发症而死亡[1]。乙肝可引起急性或慢性肝病,约15%~40%的慢性感染者会发展成肝硬化、肝功能衰竭或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2]。
人体的肠道微生物群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参与了机体代谢、免疫等各种生理过程。随着对肠道微生态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gut microbiota, GM)失调与多种疾病[如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抑郁症、2型糖尿病、炎症性肠病、结直肠癌等]的发生和发展相关[3-6]。本文从HBV感染者的GM改变入手,简要阐述GM与HBV感染相关肝病的研究进展。
1 GM概述
人体体表和体腔存在大量微生物群,它们定植于口腔、皮肤、胃肠道等,与其生存的微环境共同构成人体的微生态系统。肠道微生态系统非常复杂,且很重要,被认为是被遗忘的人体“器官”。GM是其核心成分,与肠黏膜上皮组织和免疫系统共同组成肠黏膜屏障,以阻止微生物侵入和消灭有害物质[7]。
GM在维持人体健康和预防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破坏宿主与GM之间的平衡会引起一系列病理改变。肠道和肝脏起源于同一胚层,两者间存在解剖和功能上的联系,即肠-肝轴。门静脉系统是连接两者的“超级高速公路”,肠道中的GM及其代谢产物可作为抗原信号经此到达肝脏,诱导炎症反应并调节免疫细胞的活化,而肝脏可通过分泌胆汁等物质进入肠腔来影响肠道功能[8-9]。因此,监测GM变化可能对HBV相关疾病的严重度和预后具有指导和预测作用。
2 GM与HBV感染相关肝病的关联
目前,肠-肝轴的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肝病发病机制研究中,约20%~70%的慢性肝病患者会发生GM失调,其失调的严重程度与肝损伤程度显著相关[10-11]。已有研究表明GM的变化可能在诱导和促进HBV感染相关肝病的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1 GM与CHB
近年来,GM和HBV感染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两者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一方面,乙肝患者肝功能受损,胆汁分泌和白蛋白合成减少,引起肠壁水肿,影响肠道血供和蠕动,从而造成肠黏膜屏障损坏、通透性增加。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会导致细菌及其代谢产物易位、GM组成和功能改变(有益菌数量减少、定植抗力下降、致病菌过度增长等);另一方面,肠黏膜屏障和GM的改变会引起患者体内有害物质和炎性因子释放增多,致使内毒素血症发生和局部炎症反应增强,进一步加重肝脏损伤。此外,宿主免疫应答被认为是乙肝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有研究显示,肝细胞的损伤不仅源于HBV入侵引起的细胞免疫应答,还包括GM失调产生的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 PAMP)所诱发的自然免疫应答。PAMP经门静脉进入肝脏,通过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被人体免疫细胞识别,引起一系列免疫应答并释放各种细胞因子 [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等],通过激活免疫应答直接或间接抑制HBV的复制并造成肝细胞损伤。例如,Pan等分析了急性乙肝或CHB肝衰竭患者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水平的动态变化,发现LPS水平有明显的异常分布。在疾病进展期和高峰期其动态变化与MELD-Na评分相关,提示LPS可引起继发性肝损伤[12]。研究表明CHB患者体内革兰阴性菌过度生长会导致血清LPS水平升高,LPS与TLR4相互作用并介导信号转导通路,形成骨髓分化因子2(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2,MD-2)-TLR4受体复合物[13]。该复合物与MyD88结合,激活一系列细胞激酶,活化的激酶进一步激活转录因子,导致促炎因子增多和肝坏死[14]。LPS还可通过激活肝星状细胞上调趋化因子和黏附分子的表达诱导肝损伤。
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探究GM的多样性与HBV相关肝病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CHB患者与健康受试者相比表现出明显的GM数量和比例改变。例如,一项针对中国患者的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无症状HBV携带者、CHB患者和失代偿性HBV感染肝硬化组患者的普拉梭菌、肠球菌和肠杆菌显著增加,而双歧杆菌和乳酸菌明显减少;同时,后3组的总胆汁酸水平显著降低而SIgA和TNF-α浓度升高,促使人体内环境构建新的肠道微生态平衡。此外,4组间双歧杆菌/肠杆菌比值差异显著(P<0.01),CHB患者和失代偿性HBV感染肝硬化患者的比值明显低于其他两组,这表明HBV相关的疾病进展与GM失调程度呈正相关[15]。Wang等通过对肠道细菌16S rRNA测序和血清学检测,对比研究了Child-Pugh评分较低的CHB患者和健康人的GM情况,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数据显示CHB患者的OTU124(韦荣球菌属)、OTU55(嗜血杆菌属)、OTU38和OTU224(链球菌属)与宿主的肝功能指数以及包括苯丙氨酸和酪氨酸在内的10种血清代谢产物具有高度相关性,即在发生严重肝损伤前,CHB患者的GM结构已发生改变,说明GM结构的变化可能在慢性HBV感染中起到了致病作用,GM或可成为CHB的潜在治疗靶点和诊断标志[16]。
当然,在动物模型中也发现GM参与CHB的发展。Chou等揭示了幼鼠(6周龄)在GM建立之前,已普遍存在依赖TLR4途径的HBV免疫耐受通路,并且成年小鼠GM的成熟会刺激肝脏免疫的发生,导致小鼠体内的HBV被快速清除,表明GM在HBV免疫中起着关键作用[17]。在最近一项研究中,Zhu等对比分析了急性或慢性HBV感染小鼠模型和健康小鼠中GM组成的动态变化,并检测了小鼠结肠中特定免疫分子的表达。结果显示, HBV感染小鼠中,OTU计数和香农-韦弗(Shannon-Weaver)指数等GM组成的变化明显延迟。健康小鼠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的比率是稳定的,而在HBV感染小鼠中观察到了明显的动态变化。此外,急性HBV感染小鼠结肠中γ干扰素(interferon γ, IFN-γ)和细胞程式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 PD-L1)的表达出现早期上调,而慢性HBV感染小鼠PD-L1的表达上调较晚。这些数据表明,HBV的感染可能会阻碍GM的发展[18]。
2.2 GM与乙肝肝硬化
虽然目前抗病毒治疗对慢性HBV感染具有显著疗效,但由于各种原因,CHB发展为肝硬化、肝功能衰竭或HCC的进程似乎难以完全避免。在这一进程中, GM组成改变与肝硬化的严重程度互为因果关系,其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CHB向肝纤维化或肝衰竭的转化过程[15,19-20]。
Wei等比较了乙肝肝硬化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粪便中微生物群群落及其代谢范围的变化。结果显示,与健康组相比,肝硬化患者的GM中拟杆菌水平较低(4%vs. 53%),变形杆菌水平较高(43%vs. 4%)[21]。Wu等探究了173例中国患者肠道乳酸菌的多样性,包括HBV感染相关肝硬化(LC)组患者、因乙肝肝硬化而接受肝移植(LT)组患者和健康志愿者。与对照组相比,LC和LT组患者的肠道乳酸菌多样性和乳酸杆菌组成的复杂性降低,主要表现在两组的鼠李糖乳杆菌数量显著减少,发酵乳杆菌频率降低[22]。肝硬化患者常出现肠道通透性过高现象,即所谓的“肠漏症”,这种肠屏障功能障碍被认为是肝硬化几种并发症的重要致病因素。因此,乙肝肝硬化患者的GM改变可能会更加明显,患者并发症的风险进一步增加。
2.3 肠道菌群与HCC
一直认为HCC是由炎症过程触发的,但是CHB与肝硬化和HCC之间的具体机制仍未完全阐明。在HCC的发生和发展中常伴有内毒素血症和继发性感染,而GM失衡可引起患者内毒素生成增多,同时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 GM可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3]。
潜在的革兰阴性致病菌过度生长(特别是大肠埃希菌数量的显著增加)及血液中LPS水平升高,都与HCC的发生有关[24]。另有一项研究显示,不仅是菌群的种类不同,HCC患者的GM与健康对照组之间在微生物代谢、铁的转运和能量产生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25]。Yu等在HCC动物模型中证实,从二乙基亚硝胺给药前4 d到注射后21 d,用多黏菌素B和新霉素(对大多数肠道革兰阴性菌具有杀菌作用)对大鼠进行治疗,HCC结节的数量和大小明显减小[26]。与之相似,Dapito等指出在长期慢性肝脏损伤、炎症和纤维化情况下,GM产生的LPS对TLR4的激活促进了HCC的发生,包括调节其快速增殖、促使肝细胞有丝分裂表皮调节素的表达和抑制细胞凋亡[27]。但是,考虑到HCC患者病史长,常合并多种疾病,GM失调的变化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分辨其与HCC患者预后之间的具体关联将是研究的一大难点。
3 HBV感染的GM调节
近年来,对GM的相关研究为乙肝相关肝病的治疗提供了新思路,GM的调节治疗越来越被重视,通过益生菌或粪便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来调节GM的组成和功能,可能会改善GM失调并提高乙肝患者的预后。
3.1 益生菌
补充益生菌有助于恢复肠道微生态的平衡、修复肠道屏障和调节免疫功能。Mazagova首次描述了益生菌群在维持肝脏稳态和慢性肝损伤小鼠模型中预防肝脏纤维化方面的有益作用[28]。复合益生菌可改善慢性肝病患者GM的异常状态并减轻慢性炎症反应,但短期治疗对调节肠道通透性或改善肝功能无明显作用[29-30]。Liu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肝硬化患者应用益生菌后大肠埃希菌数目减少,GM失调的症状改善[31]。
在肝病患者发生GM失调后,益生菌有助于人体重构一个健康、复杂的微生物群。然而,由于人体肠道中存在数万亿个细菌,作为益生菌而接种的细菌数量可能不足以取代原有发生失调的细菌。虽然益生菌似乎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治疗制剂,但仍需更多的研究来判断其有效性。
3.2 FMT
FMT是将来自健康供体的粪便悬浮液经处理后导入患者肠道内,以重建肠道微生态系统。FMT被认为是调节GM的一种有前途的治疗方法,已显示在多种疾病(如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神经性厌食症、多发性硬化症等)中发挥作用[32-33]。FMT可能的作用机制包括调节GM组成、加强肠屏障功能、抑制病原体等。
作为一种新型治疗方法,已有实验表明FMT在乙肝治疗方面可能是有效的。在动物实验方面,Wang等发现,肝性脑病大鼠模型中FMT对肠黏膜屏障功能的改变比益生菌具有更好的作用[16]。在临床试验方面,对18名CHB患者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FMT对乙肝e抗原阳性的CHB患者,特别是长期治疗后仍无法停止口服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具有一定疗效[34]。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易受感染的肝病患者来说,FMT治疗的安全性尚不明确,这类患者通常会使用免疫抑制剂,因此有发生菌血症的风险。另外,针对不同疾病,FMT的最佳给药途径、治疗时间和反应的持久性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数据予以确认。
4 结语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GM的改化可能在诱导和促进HBV相关肝病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对CHB患者GM失调的了解不断增加,调节GM似乎是有潜力的治疗方法,但该领域的可用数据仍然非常有限,需要更多的大规模、更深入的研究来揭示GM与HBV相关疾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具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