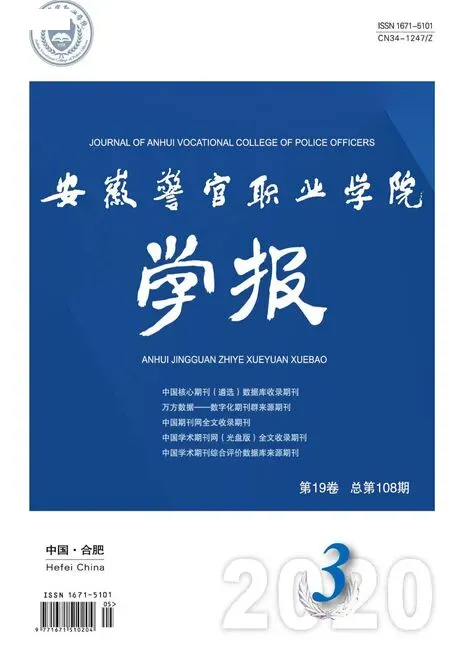从形式与内容看黔东南侗族习惯法的变迁
2020-12-28杨鸿雁
杨鸿雁
(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属于我国侗族占比较多的区域,相应的,它也是我国侗族文化保存相对完整的区域,被称为“全国侗族原生文化的中心”。[1]独特的历史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有的组织形式——款,而在款组织中达成的缔约、盟誓则被称为款约,在侗族悠久的历史中,款约起到了维护秩序、惩治犯罪、加强款与款之间经济发展等重要作用。 黔东南侗族地区款以及款与款之间的发展都由款约来约束, 故此在漫长的历史里起着维护与制约侗族地区诸事的款约的结合被称为款约法。
《侗族习惯法研究》一书中提到“侗族,由于聚居内陆、山地,历史上无政权、无文字的特点,决定了侗族习惯法独特的立约形式、 原则和程序。 ”[2]不同层次的款组织都会通过聚款立约的形式制定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款约法,如《侗款》中约法款部分就是针对刑事制定的习惯法,其六面阴、六面阳等条款至今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形式的变迁
黔东南侗族习惯法形式上的变迁有两个特点,一是从不成文走向成文,二是逐渐被村规民约所吸收。
(一)从不成文到成文
侗族约法最初的表现形式是以栽岩的方式勒石定规,即用无字的石头代表合款所约之法,若犯法则在该石上划痕,以儆效尤,这样的方法与中华历史上无文字所以结绳记事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但无文字不代表没有语言,人们不能写字,但是能说能唱。 侗族是一个乐于歌唱的民族, 在汉文字未进入该地区时,就有讲款人负责念款,传播和重申约法,哪怕在汉文化传入该地区后, 念款活动也始终贯穿和陪伴着侗族习惯法的发展。
侗族习惯法从不成文到成文的变迁可以从两个表现形式入手分析, 一个是上文提到过以汉字记录的书面记载文本——款书, 另一个是极具侗族特色的石头法的变迁。 以汉字记录侗语的款书有几种具体形式:一是以同音字或拟音词记录侗语发音,此种方法最为普遍常见;二是以汉字将侗语语义记下,该种方法阅读时需要翻译成侗语;三是用结合汉字,又并非出于汉字的另创土字记录,该种方法比较少见。汉字传入后侗民开始用以上几种方法记录款约,此种方法与款碑同步进行,即是说,款书既有从前无文字时口诵的款约内容, 也有汉字传入后刻于碑上的款约,与碑拓类似。如果说款书是侗族成文习惯法从无到有的直接证明, 那么款碑则是见证其一路成长的有力证据。与无文字时的岩规不同,侗族碑刻所记内容种类繁多, 当时汉文化的深入与侗民与官府的联系使得碑刻有了除款约和乡规民约外的其他内容,如官府法令、告示牌与官府禁约,目的是让百姓知晓政府法令, 便于管理,“但更多的是侗族款组织的大量‘款约’,它由过去的口头传承变成汉字刻碑加以记载。 ”[3]以碑刻形式存在的侗族习惯法能得到较好的保存。
(二)逐渐被村规民约吸收
这里所说的黔东南侗族地方的村规民约,是与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照搬同一模式、只留形式毫无实质内容也无实际效用的村规民约区分开来的规约,是作用于侗族地区,带有地方自治性质的民间款约。 它伊始出现于20 世纪70 年代末的南侗地区。 随着时代变迁,款组织退出历史舞台,村规民约应运而生,最初的村规民约只是单独的特殊公约,如《防火公约》,这类公约同从前的款约一样也是立于鼓楼等村民集中地,只是从石刻变成了木牌。 如黔东南报京公社报京大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商定颁布的《信地新规》,即是为了维护治安,保护集体利益而由寨老和队干部商订的四个村子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20 世纪80 年代后, 黔东南偏远侗族地区的治安不好,屡有乱象发生,这与当时国家法尚未深入而款组织又无力维持致使款约法失去效用有关。为了维护治安,侗民们依据先民的经验,吸取早先款约中的些许内容创立了自治管理的村规民约。 这类规约一般用汉字写在纸上并发放给村民或制成木牌张贴在鼓楼寨门等地,除了涵盖从前规约中的内容外,还囊括了生产、生活、思想、道德等诸多方面。 这种村规民约极具特点的是它不仅结合了当地民族习惯,还以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参照, 这类规约至今仍然在侗族村寨有效用。 如锦屏县南部三个自然村寨于2007 年联合制定的“村规民约”。[2]234
村规民约与侗族习惯法的关系同样是研究重点之一。可以肯定的是,本文所述的村规民约与传统的侗族习惯法之间既有相通点,也有不同点。从性质来看, 它们都是具有强制性的民间自治且民主的地方性规约, 不论是以款约形式呈现的侗族习惯法还是村规民约,都是一经制定人们必须遵守,如若违反则将受到公众惩处;从内容上看,村规民约继承了良善的侗族习惯法内容,这与当地传统思想有关。在历史发展中侗民已经习惯了有款无官的管理思想, 继承侗族习惯法又融合国家法的村规民约是最好的侗族地区的自治制度。
不同点是,从制定形式来看,传统的侗族习惯法是由款首组织村民集会,通过集体商议制定出来的,且往往伴随着严谨的宗教仪式。 而村规民约的制定形式则不同,它虽然吸收了款约的内容,但是大多是由乡政府或村委会商议制定的, 更多时候它体现的是旧时的规约与国家情况的融合。 而二者的执行主体也不同,前者由款首商议执行,后者由行政管理人员一方或与地方权威联合执行。
二、内容的变迁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出现而偷盗现象严重的时期,侗族先民需要一个维护私有制和个体利益的行为准则,款组织和款约法便是这样诞生的,而这一时期款约法的内容是以防盗和治盗内容为主,当国家总体发展,汉文化传入侗族地区后,该地受官府及封建思想影响,盗窃现象总体减少而出现了其它矛盾后,习惯法的内容开始从治盗转向治安,即维护官府和侗乡的关系,大量的款碑资料表明侗族款约法的内容仍多是针对贼盗犯罪,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如此。[2]240本文将黔东南侗族习惯法内容上的变迁从民事与刑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民事方面
侗族地区多山多树,自古侗民便有保护林木的意识。 林木既能用于生活建造,又有商业价值,清朝时期清水江流域木材的运输贸易便是一大证明。 除此之外,一些林木还具有宗教意义,如风水树观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学村所制定的《加学乡规民约》着重规定了林木保护, 如乱砍滥伐者罚77 斤肉,家养动物破坏幼苗的罚33 斤肉等内容。 榕江县以榕树为名,自1999 年起,榕江县便展开护树行动,积极栽种、保护林木,该活动展开后口寨村的老人们便主动响应保护林木,更在2006 年发起倡议,有组织有规模的进行环境维护和榕树保护,提出“种树留绿”的口号。 在黔东南侗族地区,不仅生态保护的传统民事习惯法得以保留, 其他关于生产、生活、婚姻、家庭、继承等民事行为的规定仍约束着人们今天的日常生活。 这些规定也很好的保留在了如今村寨的村规民约中。
(二)刑事方面
在侗族习惯法中关于刑事类的处罚并不少,而今天侗族习惯法的规范体系中的村规民约很少涉及该方面。 这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旧时的侗族习惯法中的罚则由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组成, 其中一些刑罚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是残忍的,如活埋、水淹等,1757 年即乾隆二十二年,黎平竹坪等十三个侗寨联款制定了款约并刻款禁为记,其中就有“如有盗窃,拿货查实者,通历众寨,绑捆款上,立即打死。 ”的记载,紧接着是“一不许赴官;二不许动凶;三不许隐匿抗违。 如有三条查一,同治罪”的内容,[2]242可见当时刑罚之严厉与刑不报官的原则。2009 年的一天,该地十多个村寨的寨老再度齐聚于此地并以该“款禁”为思考制定了新的规约—《和谐共约》,其内容是倡导侗寨团结、和谐发展, 净化了两百多年前同立于此地之款禁立即打死的血腥。 “具体来看,传统款约对一些犯罪的惩罚较为严厉,多为生命刑和自由刑,而在现在的村规民约中,其内容一般不涉及生命刑,反而是财产刑和名誉性有所增加。”[4]新中国成立后,黔东南侗族地区的罚则主要保留了以下几种:喊寨,一种羞辱刑, 即当事人在寨内鸣锣叫喊自己所犯的错事,如失手防火等行为等,这样的惩罚方式既使当事人感到羞愧, 也警醒了其他人不要犯同类错误;罚款,罚款有罚酒肉与罚款两种方式,在今天,罚款成为了侗族习惯法中罚则的主要方式;开除寨籍,代表着不被众人接纳,是一种羞辱刑,在群众中流传着“宁愿被国家判刑三年,也不远被隔一天” 的说法;[2]40除了以上几类罚则外, 还有抄家、放炮、洗脸等种种罚则。 不论如何,黔东南侗族地区传统习惯法中种种残忍的酷刑早已不再适用,对于杀人等重大事件也都是移交公安机关,不会自行处理,所留下的罚则多为轻省羞辱性质的,可以说对罪犯的处治是从野蛮到文明、 从体治到心治的方向发展。[5]
三、侗族习惯法的现代应用
黔东南侗族地区的法治发展从来没有脱离本土,它始终带有民族特性。 除此之外,传统的民族习惯法能够根植于这块土地并培养出乐天质朴的侗族人民绝不是偶然的, 吸收良善的习惯法却有其要。 如在生态环境方面的观念就与我国当前发展的眼光相合,以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不可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体现在法制方面是我国“生态法庭”的建立与环境保护法的实施与不断完善。[6]侗族的生态法观念让这个民族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侗族也因为独特的生态环境发展出了无数独特的民族文化。 侗族地区的生态保护观念从来没有隔断, 无论是传统的生态习惯法还是今天的村规民约, 都体现了其独特且延续至今的生态理念,值得在今日提倡,值得当前我国的生态法治建设借鉴思考。
除此之外,在婚姻习惯法方面也有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 黎平是典型的侗族聚居地,具有十分丰富的侗族文化和历史,也是侗族大歌发扬之地,在黎平县岩洞乡盛行着这样一种习俗: 凡是年轻夫妻因感情破裂打算离婚的, 会请自己最信任的老人去对方父母家中说明, 老人和对方父母在说明过程中会代替己方年轻人做自我批评, 这样的结果一般是双方重归于好, 倘若并未重归于好双方父母也能很理智的接受子女离婚的事实, 这时如若是男方要求离婚, 他会去山里打一担柴火放于女方家中离去,过程中不卸肩上的扁担,如若是女方则是挑一桶水放入男方家中,同样不卸扁担,以这样的方式完成离婚,堪称理智和谐,不卸扁担的意义是虽然双方离婚,但自己身为婿(媳)对老人该尽的孝心还没有尽完,以后有需要可随时帮忙。这样有来有往, 文明温暖的离婚习俗有利于社会和睦发展,也利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 这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快节奏不无关系, 但是离婚不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破裂的理由。 岩洞乡的离婚习俗淳朴融洽,值得我们思考。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天柱县甘溪村世代为侗族居住, 但该村早已没有了习惯法约束的影子, 只有一些观念体现在了该村村规民约里。2014 年,该村推行了合约食堂制度,旨在遏制该地兴办酒席,铺张浪费之风,合约食堂制度是该侗乡法制发展的直接证明, 侗族本没有的合约这一概念, 其背后与习惯法的联系以及该制度的有效推行既能有效研究传统习惯法, 也能为国家法制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四、小结
尽管侗族地区的款组织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但侗族习惯法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村规民约的方式继承了下来。 的确,良好的能够促进发展的制度应当保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考传统侗族习惯法很有必要。 过去残忍、严苛的刑事习惯法逐渐褪去, 侗乡中的耻辱刑却总能很好的发生作用。乐于歌唱的侗族以侗歌调解纠纷的方式恰如早先的念款活动,发展到今日,这样的方式仍然能够很好的解决纠纷,十分值得有同类民族底蕴的地区借鉴参考。 贵州是一片多民族的土地,而黔东南则是这片土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本文以侗族习惯法的形式与内容变迁为研究探索了黔东南这片宝藏之地。侗族是一个神秘的民族,独特的条件创造了独特的组织形式——款, 而独特的组织形式又衍生出了许多值得研究的内容, 本文仅以法人类学为视角对该地区该民族进行探查, 该地仍然等待着更多学者去发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