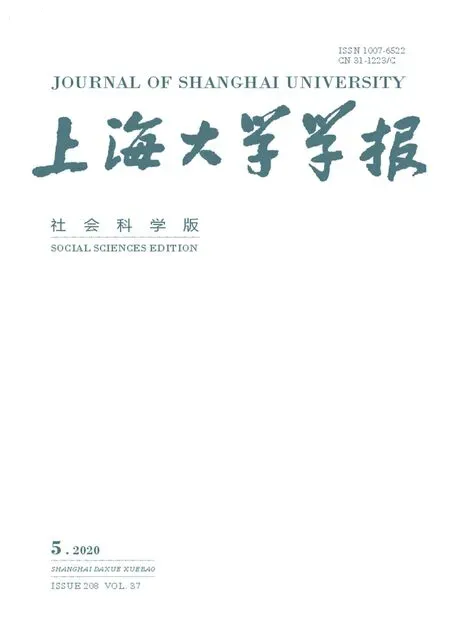中国传记电影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反思
2020-12-28储双月
储 双 月
(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北京100029)
传记电影,熠熠生辉、光彩照人。这是一种描叙真实人物的个性及生平事迹的影片,它建基于事实之上又略有升华。因此,它的审美价值、历史意义、心理功能和教育作用,是无与伦比的。传记电影恪守事实的真实,具有历史属性。它可以是历史电影的一个分支,但又不同于历史电影,因为它关注的是人物的个性。传记电影“不是这种鸟瞰式俯视而抓其经脉,而是特写式聚焦。焦点始终对着孕育意蕴的细节——传记事实和自传事实。翻覆如云的情感、变幻莫测的心理、大难临头的危机都被一一剪辑制作”,然后展现给观众的“是一部个性历程的电影”。[1]真实是传记之本。胡适指出:“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2]虽然以人物为原型,但是没有出现真实姓名的电影不能算作传记电影。
传记电影在英美影坛一直非常活跃,而且长期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备受英美电影人、观众和奥斯卡金像奖的青睐。2019 年,传记电影《绿皮书》《波西米亚狂想曲》《宠儿》获得奥斯卡金像奖,获得提名的《黑色党徒》《副总统》也是传记电影。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传记电影在中国当下影坛不仅创作数量较少,而且鲜有精品出现,成为高冷和小众类型。中国传记电影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英美国家。
一、20世纪中国传记电影的三次创作风潮
中国传记故事片创作最早可追溯到《闫瑞生》(1921),该片在剧作上“追求电影故事与生活实事的酷似”,[3]使用形似原型人物的非职业演员扮演,人物造型和表演力求显得真实可信。影片致力于追求真实性的意识使其与传记电影“纪实传真”的精神相通,初具传记电影的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古装电影拍摄潮流兴盛,激烈的商业竞争又催生了一些历史电影的出现。其中,《朱洪武》(1927)、《杨贵妃》(1927)是根据史实改编的传记电影,注重发掘人的价值,拓宽了表现的题材。这些传记电影中的人物、事件在历史中有迹可循,创作者的制作态度较为认真,服装、化妆、道具、布景均较为讲究,尽量符合人物身份和剧情发展,耗费的资金成本较高,客观上扭转了中国早期电影的欧化倾向,促进了中国传记电影的民族化发展。
传记电影创作的第一次风潮出现于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上海“孤岛”时期,电影创作者们选取讲述那些反抗黑暗统治、跟邪恶势力斗争和保家卫国的历史人物事迹,在乱世国难中表达对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的建构与坚守。《貂蝉》(1938)、《木兰从军》(1939)、《武则天》(1939)、《葛 嫩娘》(1939)、《西施》(1940)、《岳飞尽忠报国》(1940)、《苏 武 牧 羊》(1940)、《梁 红 玉》(1940)、《李香君》(1940)、《香妃》(1940)、《孔夫子》(1940)、《洪宣娇》(1941)等影片就是在这种乱世背景下创制的,颂扬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情操,抒发了壮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的评论认为,“花木兰代父从军,果然足以启发妇女们英勇的情绪,而梁红玉击鼓退金兵,也是以拨动着现代妇女前进的心弦”。[4]这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影片给时代以积极的影响。其中,《武则天》和《孔夫子》已经自觉地重新塑造人物的个性,努力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宋人修的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的罪状归结为三条:一是在李治死后私生活荒淫无耻;二是篡夺李唐政权,改国号为周;三是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乱捕乱杀。后来的稗史小说、林语堂的《武则天正传》、宋之的话剧《武则天》都把她作为一个异类加以排斥、批判和谴责。编剧柯灵认为:“史料与传说提供的只是一副没有血肉的骨架,一个被形容得残暴阴险、淫荡无比的女性。”[5]234他勘定剧本的思想重心:“是一个被压迫女性对环境的反抗与报复。但驱使她行动的是人类的本性,而不是经过澄滤和磨炼的、清醒的政治意图。我不想把她写成一个宏图卓识、澄清天下的女政治家。”[5]235柯灵着力剪裁、缝补、点染,用了许多对照和烘托,结果使得“武则天的骄横狠毒过于刺目”,[5]236而背景则模糊不清。《孔夫子》以春秋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一生事迹、学说和人格为主要内容,意在扫除几千年来的积尘,还孔子一个本来面目。影片参考《论语》《礼记》《史记》《春秋》等史料,主要从“杏坛讲学”“夹谷会盟”“子见南子”“周游列国”“孔子归鲁”等历史事件来塑造孔子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正气凛然、孤独高远的形象。全片多次出现对“乱臣贼子”的批判,呼吁“诛尽奸乱兮逐豺狼”,贯穿着一股矫正天下的刚正之气,整体庄严而肃穆,让人心生敬意。这是一部成熟且深刻而真实的传记电影,对历史事实、传记事实的阐释带有历史意识,并且起到针砭时弊、批评世俗、激浊扬清、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传记电影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成为处理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样式,出现了第二次创作风潮。《中华女儿》(1949)根据八女投江的史实改编,开启了缅怀革命英烈、弘扬爱国精神的新篇章。《刘胡兰》(1950)、《赵一曼》(1950)、《上饶集中营》(1950)、《董存瑞》(1955)、《狼牙山五壮士》(1958)、《雷锋》(1964)、《白求恩大夫》(1965)等纪念性传记影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要以革命英雄和英雄模范人物为效仿的榜样,全身心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武训传》(1950)批判运动告诉文艺界: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影片描写的中心人物,一定要创作有教益的、描写为本民族争光即引以为荣的人物。在力求使传记电影具有思想性、真实性和人民性基础之上,追求艺术手段上的新鲜感和独创性。当然,这也意味着绝不可以任意解释或歪曲农民革命战争等历史事件,要认识并反映真正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进程的方向。1953 年10 月1 日,中央电影局制定并下发了《1954—1957 年电影故事片主题、题材提示草案》(简称《草案》)。《草案》就古代和近代历史与相关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主题、题材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提示:“ 1.表现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描写农民革命的领袖的传记,描写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们强大的反抗精神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显示出农民革命对于推动历史前进所发挥的积极作用;2.表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描写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和英雄的行为。例如:岳飞、戚继光、林则徐、秋瑾等等;3.表现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描写他们的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人民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与反动势力战斗不懈的高贵品质。例如:屈原、杜甫、鲁迅、聂耳、冼星海、詹天佑、李时珍等等。”[6]《草案》对传记电影的言说范围做了详尽的规划,尤其是落实到古代史、近代史上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身上。这就严格限定了传记题材的表现对象和描写内容,带来电影创作上必然的束手束脚。
在上述《草案》的指导和规范化监管之下,“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几部反映古代历史和近代历史题材并寻找历史先进人物的影片,如《宋景诗》(1955)、《李时珍》(1956)、《林则徐》(1958)、《聂耳》(1959)。《宋景诗》是为了让当时被批为“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武训传》学习先进典型、树立正确历史观、价值观而拍摄的。影片为此不惜美化和粉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投降和镇压农民起义等史实,以渲染和拔高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作用和教育意义。这些传记电影叙述历史人物的重要社会活动及其历史功绩,避而不谈历史人物的私生活、爱情故事。既不着力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也不揭示和反映他们受到历史局限的内心斗争。为了使情节完整、结构严谨、主题清晰、思想性明确,电影创作者们进行了推测和虚构,组合搭配历史事件,贯穿着一条进步的新事物与反动的、衰亡的旧事物之间斗争的主线,让观众从新旧势力斗争中找到把握正确方向的历史英雄的典型形象。在此逻辑指导之下,历史人物性格特征选择的原则服从于对社会历史活动建构的重要性,历史事件选择的原则服从于对历史进程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进入新时期,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人的个性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电影艺术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日益加强,从而涌现出了第三次传记电影创作风潮。这批描写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并发挥其推动历史进步作用的历史名人的传记电影上映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为了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端正思想路线,新时期的电影创作者们不仅将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的功勋业绩和生平故事搬上银幕,还将曾遭受“四人帮”打击、迫害或挤压的中共领袖人物和高级将领在革命年代的光辉业绩予以歌颂,如《拔哥的故事》(1979)、《吉鸿昌》(1979)、《曙光》(1979)、《元帅之死》(1980)、《刑场上的婚礼》(1980)、《血沃中华》(1980)、《梅岭星火》(1982)、《贺龙军长(1983)、《陈赓蒙难》(1984)、《陈 赓 脱 险》(1984)、《夏 明 翰》(1985)、《少年彭德怀》(1985)、《彭大将军》(1988)、《叱咤香洲叶剑英》(1990)、《青年刘伯承》(1996)、《故园秋色》(1998)等。《毛泽东和他的儿子》(1991)、《周恩来》(1991)、《毛泽东的故事》(1992)、《刘少奇的四十四天》(1992)展现了日常生活化、平民化的中共领袖人物为国家安危、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在人民史观视野里,默默无闻的广大人民群众及其历史活动被史无前例地突出和观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全面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群众是历史行动的主体,拥有历史的主体地位,这种从阶级身份出发判断历史作用的思维逻辑使得以往备受推崇的古圣先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仁人志士等在1949 年以后的传记电影中几乎销声匿迹。到了新时期,电影创作者开始选择那些不被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历史人物作为影片观照的主角来进行历史叙事,如《李清照》(1981)、《毕昇》(1981)、《革命军中马前卒》(1981)、《知音》(1981)、《秋瑾》(1983)、《廖仲恺》(1983)、《张衡》(1983)、《谭 嗣同》(1984)。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逐渐形成,社会开始以开放、包容、博大的胸怀接受历史人物和解释中国历史,如《孙中山》(1986)、《成吉思汗》(1986)、《非常大总统》(1986)、《直奉大战——冯 玉 祥 在1924》(1986)、《张 骞》(1997)、《国歌》(1999)、《我的1919》(1999)。这些被压抑的历史人物或被遮蔽的历史事件,作为“被遗忘的存在”或“历史创伤的在场”而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历史叙事中得以敞亮和聚焦。也就是说,电影创作者采取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种历史眼光,即弱化政治历史维度的意义来还原中国历史人物,通过对人物在历史情境中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和内心活动进行描写从而来表现人物性格品质,这就使得中国传记电影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高度。传记电影中的传主身份已不严格限定在杰出人物身上,而从著名人物转变到知名人物,再聚焦到女性人物身上,甚至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末代皇后》(1986)、《两宫皇太后》(1987)、《最后一个皇妃》(1988)、《杨贵妃》(1992)、《画魂》(1994)展现了女性作为生命个体与历史车轮的同向转动或反向转动,有些女性命运在滚滚红尘裹挟中渐行渐远,有些则抵挡住了名利纠缠而没有迷失。《一代妖后》(1989)、《川岛芳子》(1989)、《大太监李莲英》(1991)是当时备受争议的排异性传记片,这些电影将在情感和认知上具有较强排他性的反面历史人物作为传主,讲述了人性在黑暗的现实、沉重的历史中是怎样沉沦的。《焦裕禄》(1990)、《蒋筑英》(1993)、《孔繁森》(1995)、《离开雷锋的日子》(1997)作为英雄模范人物和楷模的传记电影,将苦情伦理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民大众的社会化素质、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提高热爱祖国和勤恳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21世纪中国传记电影创作的现状追踪分析
传主的身份决定着传记电影的主题,也决定着拥有怎样的观众群。传记电影根据传主身份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纪念性传记,以此来铸造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先驱、领袖和将帅人物的纪念碑,让观众产生缅怀和崇敬之情,如《相伴永远》(2000)、《毛泽东与斯诺》(2000)、《毛泽东在1925》(2001)、《邓小平》(2002)、《毛泽东去安源》(2003)、《我的法兰西岁月》(2004)、《风起云涌》(2004)、《邓小平·1928》(2004)、《和 平 将 军 陶 峙 岳》(2009)、《竞雄女侠秋瑾》(2011)、《百年情书》(2011)、《秋之白华》(2011)、《第一大总统》(2011)、《刘伯承市长》(2012)、《周恩来的四个昼夜》(2013)、《出山》(2018)、《周恩来回延安》(2019)。《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平·1928》《竞雄女侠秋瑾》《百年情书》《秋之白华》《第一大总统》纷纷转向青春片、爱情片、动作片、惊险片等商业类型片寻找突破口;《邓小平·1928》《竞雄女侠秋瑾》《百年情书》《第一大总统》还渲染了惊心动魄的武打和战斗场面。这些影片讲述了硝烟弥漫的动乱年代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革命先驱们不管血雨腥风的惨烈,依然展现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同志情谊。《相伴永远》《竞雄女侠秋瑾》《百年情书》《秋之白华》《第一大总统》皆采取在大时代中正面描写传主的恋爱婚姻、家庭亲情等私人生活,给人以真实的情感触动和浪漫的激情,让人感受到生命在大地上存在的回响,清新而亲切。《相伴永远》以李富春和蔡畅之间坚贞专一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两位地位相当、经历相似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跌宕起伏的政治人生和高尚情操。这些影片都有一根浓浓的情感红线穿行于政治人物的革命活动和人生历程之中,突出表现历史洪流中他们的人格力量和道德精神。
《毛泽东与斯诺》《毛泽东在1925》《毛泽东去安源》《我的法兰西岁月》《邓小平·1928》《刘伯承市长》《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出山》《周恩来回延安》作为专题式传记片,截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的一段人生经历或相关联的某一历史事件,将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高尚精神作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充满个性色彩的革命历程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上述影片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伯承作为领袖、将帅的感召力,在于他们对那个自己还在其中扮演着角色的时代,作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评判。他们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直接改变或者说是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传主的个人在历史的艰难行进过程中是起积极作用的,在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印记。无论是20 世纪上半叶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或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都与21 世纪的当下拉开了距离,“我们就要从阶级和集体中把个人突现出来,‘恢复’出来,以刻画他们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历程”。[7]这些传记电影不仅突显了革命潮流或历史进程中人物的的精神境界和革命情怀,而且强调了影片的历史高度和思想深度。
第二类是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医学家、民族英雄等历史名人传记片,这些影片大多祛除了宣教色彩,专注于人物命运的刻画。传主不是投身于新兴政权成为御用神话,而是尽情展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实现过程,依靠才华横溢或卓越功勋立足于世,如《王勃之死》(2000)、《英雄郑成功》(2000)、《刘天华》(2000)、《詹天佑》(2001)、《真心》(2001)、《鲁迅》(2005)、《一轮明月》(2005)、《吴清源》(2006)、《梅兰芳》(2008)、《邓稼先》(2009)、《袁隆平》(2009)、《一代大儒孙诒让》(2009)、《孔子》(2010)、《吴大观》(2011)、《画圣》(2012)、《钱学森》(2012)、《萧红》(2012)、《柳如是》(2012)、《天之恩赐》(2012)、《黄金时代》(2014)、《启功》(2015)、《穿过硝烟的歌声》(2015)、《大唐玄奘》(2016)、《冼夫人之浩气英风》(2017)、《皇甫谧》(2018)、《河间圣手》(2018)。他们都是在文学、艺术、国学、教育、科学、医学、军事、国防等领域很有建树、有成就的知名人物。孔子、鲁迅、萧红、柳如是、梅兰芳等人的人生历程中有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突围,能让人触摸到他们的惶恐和焦虑;邓稼先、钱学森等其他名人、伟人一生都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没有彷徨,没有内心矛盾。如果让他们重新选择,仍然会走原来的路,国家因有这样的人才而荣幸。《孔子》《鲁迅》《王勃之死》《一代大儒孙诒让》《一轮明月》《梅兰芳》《萧红》《黄金时代》展现了传主卓尔不群的意志和起伏跌宕的命运遭际,尽显幽独超逸的丰姿、高洁淡远的趣味与傲岸的形象,凸显了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风骨、气质和智慧。《钱学森》有心拍成流传千古的鸿篇巨制,而且具有显而易见的动机诉求和矛盾冲突,但因有家人和后人门生健在,思想受到束缚,放不开手脚,敏感的地方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下去,导致只是浮光掠影地涉及一下,没能很好地解答观众心中的疑惑。前半段钱学森在美国被幽禁最终得以争取到机会回国拍得惊心动魄,而在后半段“文革”时期的遭遇稍显简略或一笔带过,没有切中要害。因而,人物形象显得有些扁平,没有触及传主内在深处的思想洗礼或灵魂审判。相比较而言,《邓稼先》并不避讳传主的“文革”遭遇,而且增加了其在美国工作的好友杨振宁的对比线索,使事件内容更加集中完整、充实饱满,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与历史认识价值。
第三类是把传主当作人民公仆来学习的英雄、模范、先进典型人物传记片,这类纪念性传记电影带有鲜明的宣教色彩,如《郑培民》(2004)、《张思德》(2004)、《生死牛玉儒》(2005)、《任长霞》(2005)、《大爱如天》(2007)、《吴运铎》(2011)、《杨善洲》(2011)、《郭明义》(2011)、《吴仁宝》(2012)、《神探亨特张》(2012)、《警察日记》(2013)、《为了这片土地》(2015)、《仁医胡佩兰》(2016)、《南哥》(2017)、《李司法的冬暖夏凉》(2017)、《苏庆亮》(2018)、《李保国》(2018)、《文朝荣》(2018)、《黄大年》(2018)、《李学生》(2018)、《天慕》(2018)。这些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人物都具有身先士卒、不甘示弱的优秀品格,有敢于和困难进行顽强拼搏的毅力,把坚贞不屈的性格应用于工作,甚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上述影片建立了求真务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了体现勇担当、善担当、乐担当的鲜明导向。这类纪念性传记电影充满中国特色政治伦理的味道,彰显出传主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善,亦即传主的政治行为在各种场合中都要求符合伦理道德。作为主旋律影片,这类传记电影提倡践行党员干部清醒自觉的政治伦理意识,是为了维系当下社会政治的道德性和秩序性。然而,由于创作者没有把传主当作普通人的肖像画来描绘,没有把影片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拉开一定的距离,重叠太广,细节雷同太多,致使观众无法进入审美的世界。正因为急于让观众产生崇敬型认同,而好人好事型故事情节恰恰又难以让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所以最终落落寡合。
三、问题与对策:中国传记电影创作的出路
优秀的传记电影往往将记事描述和论断阐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叙述和阐释之间把握好分寸感和平衡点。传主的生平事迹不能是五脏俱全式罗列,否则就显得拖沓、干瘪,让人感受不到血肉的饱满和生命的气息;阐释也不能过于汪洋恣意,否则就让论断和识见压倒了事实,即言过其实,不能让人信服。
第一,重思想表达轻娱乐、观赏、艺术,致使一些纪念性传记电影因缺乏看点和想象力而失去观众,没有社会效益。当前英模传记电影仍然“存在着移植英模原型、简单复制生活的缺憾,对英模人物的命运典型化、艺术化地刻画不力,塑造艺术形象的力度不够,以及创作上的投机心理”。[8]英模传记电影、领袖将帅传记电影是纪念性传记电影的常见样式。纪念性传记电影的主题表达不能过于直白浅露,欠缺广阔的联想空间。当前纪念性传记电影大多不被主流观众和市场认可,原因在于纪念性传记电影牢记要为传主树立纪念碑的使命,这种“歌颂体”作品往往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局面。纪念性传记电影要在当下主流观众群体中产生吸引力,不仅仅要寻求普遍的历史因果规律,还要对存在于历史领域中的特殊事物作出艺术性把握,并就历史领域中分辨出来的特殊性特征作出判断。以此观之,创作者的使命除了在历史政治视野里揭示普遍性的历史因果规律之外,还要聚焦于事实的特殊性层面,这样观众才能把握传记电影的本质特征,进而明白长期以来困惑创作者的根本问题。因此,不能受功利主义影响,只注重宣教功能而轻视传记电影的商业属性和艺术属性。纪念性传记电影如果仅仅通过歌颂并塑造民族英雄和模范人物,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那么就会沦为歌功颂德的工具,成为简单的宣传品,离观众越来越远了。因此,务必更新创作观念,勇于面向市场,不以政府扶持为倚靠,正确处理政治与商业、艺术之间的关系。
第二,传记电影是“人的专史”,因此传记电影不能沦为“历史大事记”,还要正确阐释创作者对传主的理性认识。“人物”是“材料”,是手段,历史和时代才是终极目的。观众观看传主命运的跌宕起伏、情感世界的百转千回,是为了从传主的人生经历中获得人生经验的感悟、人类智慧的积累。这些都需要创作者在对人物的演绎或对传主的层层剥笋过程中提供真知灼见。创作者揭示那段历史领域内的现象和事件,是为了不能与已逝的历史保持“同样的永恒的缄默”,而是从中获取一些慰藉、忠告和帮助。人们如若从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中获取力量,就足以完成所有社会的文明发展和文明进程所赋予的任务,足以对历史的错误进行有效的控制。在现代进程中反观混沌状态的历史领域,是为了拨开弥漫于混沌状态的历史领域中的雾霭,以便反思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同时,还为现实社会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概念或曰理性精神,以便人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命运,为历史赋予意义并且指明方向。这就是创作者借助电影这一现代媒介手段,对其所理解的历史世界或现实处境进行一种艺术化表达。
第三,传主是创作者客观冷静的观察对象,创作者不能与传主的情感紧紧捆绑在一起,致使创造者本人的历史在场性削弱了电影文本的审美场。因此,不能把传主拔高为神,而是应该把传主当作普通人的肖像画来描绘,兼顾个人性与生活中的戏剧性。《孔子》《梅兰芳》《大唐玄奘》等认同性传记电影没有仅仅着眼于建立崇敬型认同,而是让观众产生体验型认同。观众与传主的生活世界已经拉开了距离,没有重叠,这样就极易让观众进入传主审美的世界。关键在于要把人的本性浓缩到肖像画里,着力突出人物性格和精神气质,写出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这样才能契合观众的审美偏好。观众想要看到的不是简单的、实实在在的一棵树,而是要欣赏到具有审美距离的一幅画或作品。
第四,传主背后的时代不着痕迹或似有似无,这也是传记电影创作的误区。观众观看传记电影,除了了解传主个性之外,还希望能够审视历史中的人性,回顾一个时代的印记。由“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帮助观众认识传主所处的时代或政治历史背景,其目的不是强调人的不可认知性,而是凸显认识传主的有效途径。通过认识外在的客观世界,来更好地认识传主内在的主观世界。因此,传记电影不能仅仅拘囿于讲述传主的生活经历、精神境界,还要提炼出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将信息准确地传递给观众以帮助观众认识复杂的环境和事物。传主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传主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传记电影的一经一纬。只有详细地把传主与时代、传主与他人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阐释明白,通过一经一纬、一横一纵的记述,才能勾画出传主的整体轮廓、精神气质和动态发展趋势。事实上,这是健康的现实主义传统,就是要真实而准确地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选择那些最有特色的事件和最为典型的人物特征来描述,达到个人命运与时代风潮的契合。
第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思想作祟,封建思想、传统道德观念、政治意识形态成为长期以来束缚中国人思想心性的樊篱和桎梏,从而拘囿了传主和题材选择的自由。因有传主政治身份尊卑的忌讳,与英美传记电影相比较,中国传记电影的传主选择非常单一,思想禁锢,束手束脚。革命英雄、领袖将帅、英雄模范作为“完人”常常成为传记电影的座上宾,捎带一些孔子、玄奘、鲁迅、梅兰芳、李叔同、萧红等历史文化名人,反面人物和具有争议性的非正面人物很少被立传。传记电影时常成为“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电影”“历史片”“献礼片”“好人好事片”的代名词,在类型电影中没有像英美传记电影那样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之地。长此以往,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不稳脚跟,更谈不上走出国门。突破狭隘的题材意识,树立正确的类型观念,与其他类型进行融合是当前传记电影创作的重要出路。《孔子》《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英雄郑成功》与战争类型相融合,《竞雄女侠秋瑾》《邓小平·1928》与动作类型相融合,为影片增添了很多戏剧性张力、趣味性和神秘感。这些影片都率先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探索。
传记电影只有敢于甩掉政府扶持的拐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要承载过多的宣教功能,正确把握和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及政治性与商业性、艺术性的关系,有机地融入其他类型因子,坚持中国特色与世界眼光的原则,高点定位,才能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传记电影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