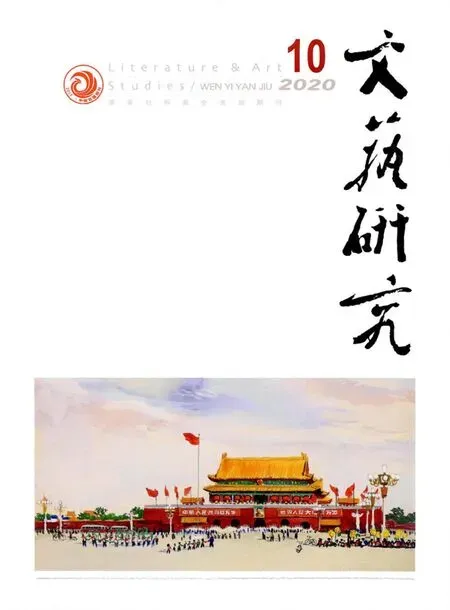删改与重述: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异文和时代感
2020-12-28谷曙光
谷曙光
新中国建立以来,文艺界名人回忆录汗牛充栋,但以谈艺为主、拥有众多海内外版本、产生持久影响的,非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莫属。
《舞台生活四十年》作为梅兰芳最重要的著作,侧重谈艺论剧,漫言演剧生涯,道尽梨园沧桑,书写了一位艺术大师在大时代艺术活动中的跌宕起伏。该书共分三集,约计50万字。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中,像该书所经历的出版情况——先后辗转七八家出版社,有平明、人民文学、中国戏剧、团结、东方、新星等诸多版本,又被收入新旧两种《梅兰芳全集》——实属罕见。再加上多种香港、台湾地区的版本以及苏联的海外版本,情况更加复杂①。统计该书的版本,竟有19种之多(不包括重印)。约略言之,七十年间,该书经历了《文汇报》连载(首度连载)、平明出版社初次成书(第一、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版(第一、二集成为定本)、《戏剧报》连载(二度连载)、中国戏剧出版社新修订版(纪念梅兰芳逝世一周年)、苏联版(唯一的外文版)、香港首推第三集(书商创意)、香港率先将三集合刊(书商汇编)、台湾版(大幅删削)、中国戏剧出版社第三集(整理者定本)、中国戏剧出版社合集(三集合编定本)、新《梅兰芳全集》校勘版等重要的出版节点,真可谓一波三折,充满传奇色彩②。
当然,如果这些版本前后基本一致,算是重印也就罢了,实际情况却是每个版本都有不同,文字、图片或增或减,书内异文折射着重述历史的企图,透露出或浓或淡的意识形态意味。版本变迁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③。各版本的“操盘手”,都在各自的时空背景下对此书进行处理,“笔则笔,削则削”④,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删改无非是为了应对具体时空下重塑梅兰芳形象的需要。作为一部“谈艺录”,《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众多版本显示出丰富的研究信息和价值,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针对该书各版本的异文、叙事策略以及时代感进行研讨的文章。
一、异文:修订和删芟
(一)中国内地诸版本的增删修订
由许姬传、许源来、朱家溍等整理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在中国内地有多个版本,经历了许姬传等人的多次修改。概言之,较大规模的修订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文汇报》最初连载的基础上,经修改后结集,交平明社出版;第二次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重版时对平明版进行了增删修订;第三次是中国戏剧出版社在出版第三集时对之前报刊连载内容做出修改。傅谨在新版《梅兰芳全集》前言中表示:“这部书(《舞台生活四十年》——引者注)尤其前两集的版本相当复杂,其中或大或小的不同,部分固然是由于史料订正所致,但是也有相当部分改动,并不见得都与史实有关。”⑤这一说法启人思考。
细细推究中国内地诸版本的修订,很能体现记录、编订者的想法。有的是把原来意思不够显豁的地方略加修饰,使之明了;有的是把似是而非、表述有错讹或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予以订正;有的是删去一些谬误或与主题关系不大的细枝末节;还有的则是增加了一些谈论表演艺术的细节和分析。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改动是对一些略显敏感、棱角鲜明的地方予以加工润色,尽量使之平和,使之对梅兰芳形象的塑造具有正面意义。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曾与谭鑫培打过对台。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竟对晚年的伶界大王构成挑战,这是梅兰芳早年的一段重要经历,属于“过关斩将”的荣耀之事⑥。然则,《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是如何写谭鑫培的呢?从平明版开始,各版都有“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一节,专门写谭鑫培晚年一次演《四郎探母》时因嗓音失润而半途终场的事件。后来经过一个多月休养,谭鑫培再演《四郎探母》,精彩万分,找回了面子。这个段落写出了谭鑫培对艺术、对观众的认真负责。但如果比照最早《文汇报》上的连载,就会发现两个标题完全不同,连载时的标题为“前辈的好胜”,侧重写谭鑫培的好胜心。《文汇报》连载和平明版里都有大段的按语。按语中言:
老谭嗓子突然哑了,我们都替他着急,这出戏唱到完,他也就得着两个彩声。一个是用假嗓音唱的那一句“叫小番”的嘎调,一个是被擒时那个“吊毛”身段。可是德建堂的六郎,拼命要彩。池座里的观众,对他这种乘人之危、有损戏德的举动都表示不满。有人甚至于大着嗓子说:“我们是来听谭鑫培,谁听你呀!”《过关》一场,照例每一个国舅要唱两句,他们那天现编了四句词儿“我看此人好面善,过关的人儿像老谭……嗓子坏了唱戏难上难”。戏台上是不能出问题的,拿老谭的盛名,尚且一点不客气的照样讽刺他。⑦
这是梅兰芳的表兄、也是老友言简斋的一段口述,说得绘声绘色,远非幸灾乐祸,今日视之,亦是难得的梨园掌故。不过,以中国传统美德而言,小辈自不宜多谈前辈之“走麦城”的经历,况且谭、梅之间曾有龃龉,此段尤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忌。梅兰芳、许姬传都是用心细密之人,难免顾虑,怕有损谭鑫培的名声。因此,到人民文学版,这段口述就被删去了,标题也改为“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潘伯鹰指出:“前后四十年中,人事变迁,在今日追叙,自不免有甚难下笔之处,而许君措语深得含茹之妙,遂能履险如夷,因难见巧,尤不可及也。”⑧这是深知甘苦之言。《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叙述分寸感好,秉持过犹不及的宗旨,颇得中庸之道。写谭鑫培一节屡次修改,就属“履险如夷,因难见巧”之笔。
其实,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戒坛寺”一节里,梅兰芳终究还是对早年与谭鑫培打对台表达了歉意。他说:
他(谭鑫培——引者注)在晚年,是不常出台的了。我正在壮年,唱的日子多得很。当他偶然露几天,我不应该顺着俞振庭的意思,用新戏老戏夹着唱的新花样,来跟他打对台的……后来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他那边座儿不好,我还是咄咄逼人,不肯让步,使这位久享盛名的老艺人,在快要结束他的舞台生活以前,还遇到这样的一个不痛快。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今天承认这件事是我年轻无知,做得冒失了。⑨
时至今日,还有人说谭、梅从未打过对台,或两人不是对手,但《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这段梅兰芳谦恭的“自供状”倒成为最好的明证。这一段显示出梅兰芳的谦逊和反思精神。其实,如何把略显尴尬、难以下笔的人和事,放到合适位置来写,既娓娓道来,又不露臧否,这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考验。这种在书中不同地方多处用笔来描摹同一人,颇得太史公刻画人物之“旁见侧出”笔法。
梅兰芳一生的竞争对手众多,欲算计甚至陷害他的人,也并非没有。《文汇报》的连载中就记录了梅兰芳早年的伙伴、也是竞争者王蕙芳在演出中“阴”他的一个细节⑩。请看这样一段描述:
有一次我跟俞振庭、王蕙芳合演《长坂坡》。原定我的糜夫人,蕙芳的甘夫人。临时蕙芳开我的玩笑,先抢着“喜神”不肯放,他也扮上了糜夫人(台上的假孩子,内行叫做喜神)。这甘夫人的词儿,我根本就不会。虽然很简单,马上就要上场,哪里有时间“钻锅”呢?我正在着急,俞五老板(俞振庭行五)过来安慰我说:“不要紧,我来给你说。”结果是上一场说一场地对付过去的,这在我一生演出当中,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了。⑪
民初有“兰蕙齐芳”的说法。王蕙芳比梅兰芳年龄略长,起初气焰甚炽,“辫帅”张勋极捧之,但后来在竞争中渐渐落败。事隔几十年,梅兰芳把这一事情说得平平淡淡,不显痕迹,但这岂是玩笑,应该说险些酿成舞台事故。但此段后来成书时被删去了,这很能显示梅兰芳的隐忍和温厚。再有,梅兰芳数十年间见过和交往过各类人物,其中不乏国家首脑、党派领袖、各界头面人物,但他在书中从未挟名人以自重、自夸,也未见有意贬低谁、挖苦谁。这是梅兰芳写作回忆录定下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美德的体现。
不必讳言,历次大陆版的修订增删,都有一大宗旨,那就是维护梅兰芳的正面形象,彰显其敦厚品行。有些细微的改动,看似不经意,却是出于精心安排。中国戏剧版《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有“与杨小楼合作时期”一章,当初在《戏剧艺术论丛》连载时的标题为“我与杨小楼合作”,其中“《五花洞》”一节谈到一次堂会上演出《六五花洞》的情形,当时梅兰芳和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王幼卿六名旦演真假潘金莲。连载时有“民国十六年军阀张宗昌叫堂会,地点在奉天会馆(即现在的西单剧场)”⑫的字样。及至成书,此句被删去了。标题也改为“荒诞的《六五花洞》”,显然是想表达批判之意。盖北洋军阀张宗昌臭名昭著,谈梅兰芳早年给他唱堂会很是不妥,不妨隐去其事。《文汇报》连载时还有一节“两个堂会”,成书后也整节删去了。毕竟是回忆早年阔佬、军阀办堂会的经过,不宜多谈。但今日视之,梅兰芳的这些活动倒都是难得的梨园掌故,何况里面还有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的重要史实,删去实在可惜⑬。许姬传等人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凡任何有可能对梅兰芳的美誉产生不良影响之处,哪怕一丝一毫,都会仔细斟酌,不惜删改。
在“新武汉”一章,人民文学版也有删节。最早《文汇报》连载和平明版均有这样一段记载:“从六月五日起梅先生在汉演出的程序,是这样预定的:(1)五日与六日是优待工人,在人民剧院再度登台,表演两场。(2)七日至九日是四野文化部的晚会。(3)十日是中南局的晚会。(4)十一日至十三日是去武昌表演三场,因为武汉有一江之隔,对岸的观众,晚上回去不方便,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梅先生的演出的原故。(5)十四至十五日是为了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在民众乐园与中南京剧工作团联合演出两场。(6)十六日的白天是招待武汉全体戏曲工作者的观摩演出。”⑭人民文学版为何删去此段?大约是因为其中详列了梅兰芳剧团为军队和政府的招待演出场次,略显忌讳。其实,1949年后,梅兰芳剧团每到一地,少不了给当地政府和驻军演出,有时内部招待、观摩的场次还超过公演。人民文学版的删改是为了彰显梅兰芳走群众路线、与工农兵同乐的时代精神。
“焚券”与“赎当”,是有关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两段重要经历。《文汇报》连载和平明版均记载有误。人民文学版修正了错误,改动较大。这属于订讹传信一类。比较细碎的与舞台生活关系不大者,人民文学版亦删去了一些。譬如《文汇报》连载和平明版都用较多篇幅谈种植牵牛花的步骤及要领,人民文学版对之加以删削,此一删削使相关章节显得更加精炼。后来的中国戏剧版承袭之。还有一些生动但未必可靠的梨园轶闻,或考订不精的剧学小问题,报纸连载时有,后来成书时删去了。再有,如平明版中的“满清时代”,人民文学版改成“前清时代”。“满清”带有贬义,于是改成不带情感色彩的“前清”。
(二)香港版、台湾版的剪芟和漏改
香港版第一、二集,系内地平明版的翻版,不足为奇。香港版第三集,值得关注。“文革”中,香港出版人自发地为梅兰芳编辑散见的谈艺稿件,后汇总成第三集出版。香港版的章节设置自出机杼,特别是有的小标题,如“八部天龙金光闪”“大王要吃活人肉”,起得很俏皮,花了心血。香港版还有一个附录,收录了多篇梅兰芳去世后的悼念文字。遗憾的是,因南北睽隔,内地又处动荡时期,资料难查,致使该版编辑难免疏漏。比如刊登在北京《戏剧报》1959年第7—9期上的“吉祥园初演《散花》”“武戏文唱、文戏武唱”“在上海重演《散花》”三节,就未能收人。值得一提的是,该版第三集对“文革”后许姬传等人重编第三集或有一定的反哺作用。
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所有版本中,台湾里仁书局版(下称“台湾版”)剪芟程度最大,显然是为了该书能在台湾顺利面世,而不至遭到查处或禁毁。
台湾版的底本应该是香港版,书名改作“舞台生涯”,署名“梅兰芳述”。内容是摘录梅兰芳本人有关生平和艺术的谈话,许姬传在该版中彻底消失。细细检视一番,中国大陆诸版每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有一些穿插点缀和生活细节的说明文字,台湾版则全部删去。梅兰芳和许姬传的对话,类似“过场戏”的部分,亦删去。中国大陆诸版的梅兰芳前记和许姬传的编写说明在台湾版里也不见踪影。原来第一章“远东饭店的谈话”,在台湾版中只摘出其中三小段,改称“前言”,篇幅仅半面。一些标题亦有或大或小的改动。因这一版删节过多,有些地方只好再补加上若干字句,以便上下衔接。
台湾版改动的原则:只准讲古,不能谈今。凡涉及1949年后梅兰芳的演剧、经历、行踪等,不惜删削改动,从而把对梅兰芳的活动情形的叙述基本限制在1949年之前。
举例细言之。中国大陆诸版第一集里的“枪挑穆天王”一节,台湾版做了大段删节。此节写1950年12月17日,梅兰芳在北京大众剧场贴演《穆柯寨》,连演《枪挑穆天王》。梅兰芳偌大年纪,连演两出,自是辛苦,但他表示:“你就看前天这样大的雪,观众在半夜里站在雪地里排着班买票,他们对我的这种热情,使我听了能不感动吗?像今天两出戏并着唱,我承认是很累的。可是明天到了台上,想起他们买票的辛苦艰难,我又得把全副精神提起来,认真工作,让他们看了,都能获得满足。要不然我也太对不住他们了。”⑮这种显示新时代、新气象、新精神状态的文字,台湾版自然会因为忌讳而删除。
又如“关于四喜班”一节,中国大陆诸版开头几段写1950年梅兰芳剧团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住利顺德饭店,旁及看门老者今昔感慨等细节,台湾版都一一删去了。“游园惊梦”一节关于“迤逗”读音的讨论以及养猫的插曲,亦被删削。1949年之后梅兰芳演《惊梦》的变化,被删除。《思凡》一节,写到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典礼,被改写。台湾版还删改了一些细节,如改“北京”为“北平”,改公元纪年与民国纪年并用为民国纪年等。
台湾版的大量删翦一定程度上伤筋动骨,造成体例杂乱。“杨三绝艺”一节,中国大陆诸版以较大篇幅引述了萧长华回忆“同光十三绝”之一的杨鸣玉精彩技艺的谈话,绘影绘声,读之如身临剧场。这本来极有价值,但因不是梅兰芳的自述,台湾版删去了,令人殊觉可惜,于是标题也显得无的放矢。后面谈“喜(富)连成”科班的部分,又有萧长华的大段叙述,这次倒保留下来,估计是该版编辑人员意识到,若再删的话,已经无法弥补内容的缺失。台湾版前后体例不一,删削随意,有时令人无所适从。
(三)改好与改坏
上面重点谈了中国内地诸版和香港、台湾地区两个版本的编辑删改情况。有意思的是,其中有改好之例,也有改坏之处,不可一概而论。
《宇宙锋》是梅派戏里少数具有反封建意识的名剧,其中赵女的抗争精神在传统戏中较为少见,也颇为符合1949年后“戏改”提出的文艺标准。此剧是梅兰芳着意经营的代表作,他对其心得极深,于是写入书中,细加分析。到人民文学版,更增加了谈表演、舞台调度的按语,对先前不够深入的地方也予以加强。增添的部分,突出了梅兰芳在表演方面的独到匠心,特别在一些要紧的有创造性的身段和唱念上,重笔加以阐发和强调,以便让读者更好地领会梅派名剧的精妙之处。这种对表演艺术的细腻分析,非常有价值,属于越改越好之例。书中对梅派名剧《贵妃醉酒》的解读,也同样精雕细刻。
从报纸连载到平明社初次成书,再到人民文学版、中国戏剧版先后修订,总体来说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编改过程。当然也有改得不够理想的地方,如写养牵牛花一节。当日梅兰芳家中举办品花大会,汇聚了京城一些顶级艺术家,堪称高端艺术沙龙。《文汇报》连载记录了罗瘿公的《牵牛花赋》,这是难得的出自名士的文字,不过到平明版竟删去了。到人民文学版,又删去下面一段文字:
我们请来评判的外客,常有很知名的书画家、文学家,如齐白石、罗瘿公、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汪蔼士……他们欣赏完了,有时看得高兴,就拿起笔来,有的对花写照,有的吟诗作赋,那大半天的雅聚里面,不定要留下多少有趣的墨迹呢。他们欣赏的牵牛花,看完就萎谢了,可是乘兴留下来的作品,直到今天我们拿出来看了,还是可以欣赏不已的。我记得罗先生还做过一首记载我们养牵牛花的诗:“谁移萼生花,置之盆盎生。寻丈屈尺寸,部别乃异名。栽制恃人力,定非花之情。虽曰非花情,坐阅百态更。粲粲之数子,汲汲各有营。果然花时节,能各以异争。开轩灿行列,洗琖要客评。向日纷弄色,巡檐媚相迎。斯会今则创,岛国有图径。栽培吾不敏,见此心怦怦。”⑯
这段回忆虽然与戏曲无关,但却属艺苑珍闻一类,从中既可看出梅兰芳社交圈中人的深厚文化底蕴,又可增加文章的文化品位和可读性,还记录了名士罗瘿公的诗作,如此鲜活的艺坛掌故,无论因何种原因删去,其实都是不明智的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成功之处,突出表现在历史现场和鲜灵活泼的细节记录方面。有时删去细节,就失去了原有生动的韵味,文章也显得干瘪了。如写梅兰芳与杨小楼首演《霸王别姬》,中国戏剧版第三集有这样一段话:
这场大武戏完了之后,杨老板下来双手轻快地掭了盔头,对我说:“兰芳,我累啦,今天咱们就打住吧。”我说:“大叔!咱们出的报纸是一天演完,要是半中腰打住,咱们可就成了谎报纸啦。我知道您累了,这场戏打得太多了,好在这下边就是文的了,您对付着还是唱完了吧,以后再慢慢改,这个戏还是太大。”当时他没有加可否,接着说了一声:“还勒上吧。”我赶紧陪笑说:“您再歇会儿,还有功夫哪。”正说着就听见管事李春林大声说:“来啦!来啦!虞姬!虞姬!”我看杨老板又戴上盔头,我才放下心出去,总算一天把戏唱完了。⑱
《霸王别姬》是经典名剧,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打磨的过程。最初戏太长,场子松散,武打又多,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上面这段在《戏剧艺术论丛》连载时,在“当时他没有加可否”后,其实还有几句话:“跟包的已经把一块热气腾腾的毛巾盖在他头顶上了。他就着小壶喝了一口茶,又点上纸烟抽了两口,把头上的热毛巾拿下来……”⑲中国戏剧版第三集把这几句话删去了。这几句属于细节描摹,再现后台场景,杨小楼的人物情态极生动,这样的删翦实在可惜。还有,“报纸”“谎报纸”在连载时是“报子”“谎报子”,“报子”乃口语,指“戏报子”,即旧时戏单海报,一字之差,改得却欠妥,造成了讹误。
又如,“《金山寺》”一节,于《戏剧艺术论丛》连载时,有一句话:“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已经千锤百炼的传统戏,如果改动,要特别慎重,千万不可草率。”⑳此句到中国戏剧版第三集推出时删去了,这亦堪玩味。梅兰芳一贯敬畏传统,艺术上主张“移步不换形”,但1949年之后“创新”受到更多的强调。梅兰芳的这句话虽无问题,但在某些人眼里就有“保守”之嫌疑,显得“碍眼”。笔者推测,此句的删除,未必是许姬传的意思,或许是出自出版社的“顾虑”。在笔者看来,自是保留为宜。
再如中国戏剧版第三集“与陈彦衡谈创造新腔”一节,记梅兰芳之谈话:“在民国初年,新腔之风虽未盛行,但我排演新戏时,总想琢磨些新颖动听的腔调,加强表现剧中的人物。”㉑这段话中的“加强表现剧中的人物”一句,倒像是1949年后的流行说法。其实,在“文革”前《戏剧报》连载时,原文为“给座儿换换耳音”㉒。两相比较,显出很大的不同。梅兰芳的原话是口语而非书面语,有一种身临谈话现场的亲切感,于细微处见精神。改了,失去了特有的京味儿,神采顿失。
《文汇报》连载时,未分章节,有两级标题,有的小标题生动贴切,显得很俏皮,很有味道。后来结集出版,要分出章节,于是重新加工,对原来的小标题施以斧斤,有些原本很好的标题没有保留下来。如“撇下了可爱可怜的孤儿”“举世闻名的乐人——梅雨田”“前辈的风义”“一个意外的收获”“两只大老虎”“三个阔问官”“一个紧张的镜头”“好戏登场以前”“一碗白木耳的代价”“名士在‘夷场’”“白帽与兵营”“谭鑫培的‘绝唱’——《洪羊洞》”等等。
二、“《穆桂英》”一章的消失
新版《梅兰芳全集》编辑时,搜集了多种版本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通过比较后发现,当年发表在《戏剧报》(1958年第19、20期)上的“《穆桂英》”一章,后来未能收入中国戏剧版第三集。整章删除,实属罕见。新版《梅兰芳全集》编辑团队曾提出此问题,并在小范围内讨论过,大家认为此一做法“似有深意”,但又不得确解。为何删去“《穆桂英》”一章,俨然成为梅兰芳研究中的一桩公案。其实,香港版第三集和台湾版对该章倒是都有收录。下面笔者就这一问题谈谈一己之见。
笔者认为,梅兰芳当年在《戏剧报》上发表“《穆桂英》”一章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1958年,正是“大跃进”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当时所提出的让工业和农业在短期内大幅增产(即“跃进”)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规律,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浮夸风弥漫全国㉓。为了完成新时代的新任务,宣传工作极为重要,要紧跟形势,大力宣传,推出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和杰出人物,树立榜样,鼓励全国人民大干快上。
“《穆桂英》”一章,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推出的。选择这个题目,显然看重的是穆桂英作为古代女英雄智勇双全的典型,可以成为鼓舞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极佳形象。这一写作是否有高层授意,不得而知,但当时鼓励戏剧界代表人物多写文章配合时代需要,是大势所趋,梅兰芳自然会成为其中的不二人选。这么说并非没有根据。在《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有“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一章,篇幅颇长。其实,梅兰芳和余叔岩虽合作多年,但关系并不融洽。那么,梅兰芳为何要浓墨重笔专写余叔岩呢?原来,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齐燕铭曾有此建议。齐燕铭希望梅兰芳写一个先天条件不佳、后天苦练成功的艺人形象,以激励新中国的青年演员。梅兰芳、许姬传经过斟酌,选择了余叔岩㉔。此外,《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最后一章末尾的按语谈道:“当梅先生在世的时候,每逢有突击性的写作任务,常常是排除其他事情,全力以赴把一篇完成。”㉕“突击性的写作任务”一语,也足以说明问题。梅兰芳那样的大名家,谁能给他布置这种任务呢?答案只能是来自高层,也更多是政治任务。在笔者看来,“《穆桂英》”一章应该就是为了完成这类“突击性的写作任务”所交的一份作业。
梅兰芳写穆桂英是合适的。梅兰芳擅演古代各类型女性,有关穆桂英的题材也算得上梅兰芳的拿手戏。通过写古代女英雄激励广大的劳动群众,岂不是一个好主意?梅兰芳直白地在此文中写道:“在大跃进声中,各个战线上出现了不少今天的穆桂英,我觉得戏曲舞台上不仅要演宋代的穆桂英来鼓舞观众,而且剧作家应该写出比《穆柯寨》更好的喜剧,来歌颂今天无数的穆桂英式的女英雄、女模范,演员们应该在舞台上演出更新更美的女英雄、女模范,来教育鼓舞今天新时代的观众。”㉖可见,撰写此文的用意极为显豁。文章的内核是讲古,但预设的意图却是比今。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一借古喻今让文章的格调更显激昂,若与《舞台生活四十年》其他章节放在一起,因其叙事策略游离于整部书之外,读来确有不甚和谐之感。
“《穆桂英》”一章未被收入中国戏剧版,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之前中国内地诸版第一集中其他章节在内容上有重合的嫌疑。考察中国戏剧版第三集的其他章节,“《奇双会》”一章写梅兰芳第三次入双庆社;“从绘画谈到《天女散花》”一章谈绘画与舞台艺术;“《童女斩蛇》”一章讲梅兰芳上演的最后一出时装新戏;“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与杨小楼合作时期”“《霸王别姬》的编演”“承华社时期”数章,皆是以梅兰芳的舞台生涯为中心,其中由顺着他个人艺术经历的一条暗线贯穿。而“《穆桂英》”一章,只是单纯地谈梅兰芳扮演穆桂英的剧目,缺少与其他章节贯穿的线索和逻辑。再有,中国戏剧版第一集第十章“一个重要的关键”中,已经有了关于穆桂英的“穆柯寨”和“枪挑穆天王”两节。故从整部书的结构、内容、逻辑性、整体性等方面考虑,不收“《穆桂英》”一章是精于安排文章架构的明智之举。这应该是出于整理者许姬传的决定。当然,许姬传还是敝帚自珍,他后来终究将此文收入其《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书。
附记一笔,台湾版虽收入“《穆桂英》”一章,但删削很多。台湾版编者需要拿捏分寸,转变叙事策略,亦不容易。中国大陆与台湾,处于不同的历史氛围,有着截然不同的现实需要,对“《穆桂英》”一章的处理恰成鲜明对照。2016年新版《梅兰芳全集》中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恢复“《穆桂英》”一章,为重新审视这一历史问题提供了契机。
三、叙述的双线与单线
中国内地诸版《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二集,以许姬传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大量引用梅兰芳的谈话,并加上双引号;而第三集则完全不同,第一人称叙述者换成梅兰芳本人,文字不再加双引号,且将许姬传隐去。叙述视角和口吻前后的改变,成为《舞台生活四十年》全书体例前后不同的一大表征。为何会有如此改变?许姬传自言,“第三集的体例略有变动。梅先生主张以戏为单位,语气改为第一人称”㉗。须知,第一、二集出版后大获好评,到出第三集,体例却发生了较大改变,这显然不同寻常。
在中国内地诸版第一、二集中,主体部分是梅兰芳的谈话,许姬传仅是穿针引线的人物。虽然大段引用梅兰芳的谈话,署名也是“梅兰芳述、许姬传记”,但梅兰芳的谈话却不是第一人称,一路看下去,确实显得有点“怪”。许姬传的第一人称,虽未到喧宾夺主的地步,但也令人感觉过于突出了。有人议论,这种叙事视角实际上置许姬传于重要地位,他本人作为此书的整理者这样处理,似有自高身价的嫌疑。
笔者倒不这么看。《舞台生活四十年》属于“口述史”一类,许姬传是这一访谈的设计者、引话者和对谈者。如果从头至尾只是梅兰芳的自述,有些地方就不容易处理,有的话甚至不宜也不能写进书中。有许姬传的对话穿插其中,某些地方再加上按语,就显得游刃有余。那些不适合由梅兰芳本人说出的话,也能顺理成章地表达出来。如果只是梅兰芳一人“单打一”,那就只能是一条线。许姬传的存在,对此书有侧面烘托的意义。双线并进,是一种叙述策略,亦让中国内地版第一、二集显得更为圆通周到。有无许姬传,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内地版第三集为何又隐去许姬传?或许已有人提醒许姬传要“低调”,反感他在书中反复出现,“恶紫夺朱”,于是许姬传不得已干脆隐去自己,以免闲话。
闲话确实有,但恐怕还不是《舞台生活四十年》叙述视角转换的深层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戏剧报》重启连载的时间是在“反右”之后,此时谨言慎行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内地版第一、二集里谈了许多早年间的人和事,如何拿捏分寸,颇费心机。旧时的人和事,不宜多谈,免出纰漏,才是上策。单纯谈戏,更多突出艺术一面,相对容易处理。这恐怕才是由第一、二集以人与事为主转变成第三集以戏为主的内在原因。相对而言,多谈旧年人和事,许姬传这条线的作用就大一些,双线显得游刃裕如;谈戏为主,许姬传在书中的存在价值就小了,改成单线亦无妨。
此外,还存在一个联合署名的问题。“文革”后中国戏剧版第三集的署名是许姬传和朱家溍两人㉘,也即中国内地版第三集有朱家溍较多的劳绩。因此,在叙述时就不能只用许姬传作为第一人称,否则会有忽视其他整理者作用的嫌疑。再者,“文革”后重新整理第三集时,许姬传年老多病,已无精力再对如第一、二集那样进行细致修订了。中国戏剧版第三集最后的“承华社时期”一章,实际上是一篇“未完稿”,许姬传甚至把未完成部分的简略提纲也附上了,看起来与全书很不协调,足证他已力不从心。
香港版和中国内地诸版一样,第一、二集以许姬传为第一人称,第三集以梅兰芳为第一人称。至于台湾版,编辑时就已经处理了叙事视角转变的问题,即在香港版基础上把梅兰芳的大量叙述摘录出来,隐去许姬传,等于是把第一人称由许姬传改为梅兰芳,体例上与后出的中国戏剧版第三集相一致,这或许是台湾版经删改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历次版本透出的时代感
《舞台生活四十年》历次版本的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时代感存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是该书主要的辗转之地,三地时空不同,表现亦异。
《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于1950年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待整理成书出版后,梅兰芳因演出等各种事务繁忙,连载暂停了几年。但该书好评如潮、影响巨大,外界也对继续连载抱有普遍期待。其实,梅兰芳、许姬传私下里并没有中断口述和记录,只是需要一定程度的积累。这件事迁延到1958年,开始由《戏剧报》接手发表梅兰芳回忆的新内容。为何不是《文汇报》而改由《戏剧报》继续连载呢?据《文汇报》老报人谢蔚明说:“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文汇报》冲击很大,《四十年》第三集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报》约稿连载。”㉙谢蔚明一度任《文汇报》驻京记者,亦算是《舞台生活四十年》成文发表的有功之臣,在搜集资料、拍摄照片等方面助力甚多。他的话值得重视。《文汇报》在当时曾被最高领导人公开点名批评,《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发表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措辞相当严厉㉚。在这一语境下,继续在《文汇报》上连载梅兰芳的回忆文章,显然已不合适。当然,从《文汇报》转到《戏剧报》,还不止这一方面的原因。《文汇报》毕竟是一家上海的报纸,而以梅兰芳当时的地位,他的回忆文章理应由中央一级的全国性报刊登载,起码应是戏剧界最重要的专业刊物登载。考虑到梅兰芳本人当时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由该协会主办的《戏剧报》连载,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一章,是梅兰芳逝世后在香港《文汇报》连载刊登出来的,这颇为出人意料㉛。截至1962年,新一轮连载已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报刊刊登多篇,此外,“1919年梅先生赴日本演出——第一次在国外演中国戏曲”“梅兰芳、杨小楼合组崇林社”“承华社时期”等几章也基本写就㉜。此时,许姬传等人也已着手整理誊清,拟推出第三集。谁知形势发生了令人难以预料的变化。1964年之后,剧坛上出现了传统戏从受冷落到逐渐被禁演、现代戏大行其道的局面,受其影响,已编好的书稿因专谈梨园往事和传统戏,不能不陷入出版困境;再加上“文革”时期,尽管梅兰芳已经离世,但仍遭批判,被诬蔑为“阻拦京剧革命的顽石和恶虎”㉝,显然,形势已使《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的出版不再可能。还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是,第三集誊清稿在“文革”期间丢失了。后来重新整理第三集时,一是利用了之前报刊上连载的内容,二是“梅兰芳、杨小楼合组崇林社”“承华社时期”两章,使用了“文革”前留在梅夫人福芝芳那里而侥幸保存下来的稿子。至于遗失的赴日演出一章,则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不过,香港《文汇报》连载为第三集率先在香港出版提供了可能。香港天行书店自主把内地《戏剧报》和香港《文汇报》上新发表的内容收集起来,汇聚成第三集推出。略感可惜的是,香港版第三集既未标注具体的出版年月,更不知何人为主事者。笔者经过多年考证,终于在香港已故作家萧铜的《京华探访记》里查到蛛丝马迹。萧铜是香港版《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的策划者之一。此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还有以沈苇窗为代表的一批资深剧评家,笔者猜测第三集的结集或与沈苇窗等人亦有关系,于是去查沈氏主编的香港早年著名杂志《大人》,发现了一条关于出版日期的线索。在1971年3月出版的《大人》第11期上,有《〈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外编》一文,据文前按语,可大致推知第三集的出版时间在1970年末至1971年3月之间。至此,香港版第三集的编者和出版日期,都有了眉目。这一集的推出,既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说明当时的香港文化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存文脉传承的重要作用。
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诸版本中,台湾版迟至1979年才得以面世,其中亦不乏明显的时代原因。众所周知,台湾“戒严”时期限制言论自由,图书出版禁锢亦烈。20世纪50年代,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大陆的名作家,其著作在台湾都属查禁之列。鲁迅、郭沫若更不用说。推而言之,梅兰芳作为中国大陆当时最著名的戏曲艺人,其书在台湾一时不能出版,也在意料之中。
《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价值显而易见。台湾书商在“戒严”后期图书出版审查有所松动的情况下,终将《舞台生活四十年》改头换面,删削后推出,台湾戏剧界和普通民众也终于得见此一佳作㉞。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版书前特意增加了《关于梅兰芳》一文。由于彼时两岸对峙,遂令此文之叙述带有特殊的意味。如云:
梅氏为人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以是遂能博采内外两行之建议,而有出人之成就,然亦不免失之过于温顺,以至神州变色之后,为匪役使,以近耳顺之年,犹须贡献其“剩余价值”,老境堪怜矣……㉟
此种荒诞的表述,今日读之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不过,不如此表述的话,其书难以在台湾出版也是实情。
再往细处说,台湾版还有精装和平装之分,内容亦存不同。平装本所载《关于梅兰芳》一文,与上引精装本文字小异,如改“梅氏”为“梅先生”,再就是“然亦不免失之过于温顺”以下被删去了。由此推断,精装本印制在前,平装本印制在后。印平装本时,“戒严”时期已过,少了一些政治上的忌讳。仅从《关于梅兰芳》一文中“梅氏”和“梅先生”称呼的差异,即显示出台湾对梅兰芳态度的变化,也能看出微妙的时代意识的变化。
比照中国大陆版和台湾版的具体内容,差别最大的,是写武汉的一章。原来平明版第二集第六章,标题是“新武汉”,内容包括第五次到汉口、楚剧、汉剧、后台的两件事情、《抗金兵》、离汉之前、老艺人的爱国热情等七部分;台湾版则大为删节压缩,章节标题改称“武汉”,去掉“新”字,具体内容则只有汉口的几次演出、《抗金兵》、春合社三部分,其中春合社部分还是从平明版第二集第七章移过来的。对此章大加删削的原因不言自明,在政权“新旧”之间。中国大陆版凸显1949年后武汉的“新气象”、演剧的“新面貌”、艺人的“新生活”,而台湾版恰恰要“去新”“除新”“删新”。这是台湾版删削的基本原则。
概言之,台湾版由于改动较大、删芟随意,遂令该书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版的文献史料价值。但恰恰因为翦削大且多,时代痕迹明显,又让此版呈现出最特殊的面貌,从而具备了另一种特殊的历史价值。真实与想像、隐喻与重塑,都在其中得以体现,个中意味,一言难尽。
在《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上述多地诸版本之外,1963年,苏联推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俄文版。虽然当时中苏已在多领域存在矛盾,但是民间文化交流尚未关上大门。梅兰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联系两国的文化符号和特殊纽带。梅兰芳1935年曾访苏演出,取得巨大成功。应该说,他在苏联文化界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也是该书俄文版推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 语
参与《舞台生活四十年》编辑成书的人物众多。《文汇报》连载的策划者是柯灵,操盘手是黄裳㊱,梅兰芳当然是最重要的当事者,也是口述者,文字加工则以许姬传、许源来、朱家溍三人为主。在“二许一朱”中,又以许姬传出力最多。至于参与该书编辑的“梅党”,人数更多,如“梅党”中的几位元老“巨头”冯耿光、吴震修、李释戡等,都隐在幕后。关于“二许一朱”及诸多“梅党”的各自作用,许姬传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一文中有较详确的说明,可参阅。
《舞台生活四十年》历经多次删改修订,版本多种多样,总体来看,中国内地平明版是基础,流传最广;香港和台湾地区版则可视为衍生品。在中国内地诸版中,第一、二集相对圆满,而晚近出版的中国戏剧版第三集则因刻意求好和束缚较多,整体反不如早出的两集挥洒自如。不过,众多版本对名伶形象的呈现和重塑、异文的隐喻意味、多地版本显示的时代感等,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学者、书法家潘伯鹰当年致信《文汇报》总编徐铸成,盛赞连载之事和许姬传云:“此乃今日罕见之佳著,不仅以资料之名贵见长,不仅以多载梨园故实见长,其布置之用心与措词之方雅,皆足见许君经营之妙。”㊲此亦堪称《舞台生活四十年》之定评。
一部艺术大师“谈艺录”的版本变迁背后,有着复杂的时代因素。不同时空,表现各异,有可能是正向的,亦有可能是逆向的,两者都值得细细考量。“删改”与“重述”,从这两个关键词分析《舞台生活四十年》,既指向文本形式的改写,又试图从这一文字改写中捕捉时代的痕迹,在廓清历史迷雾、还原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发掘文字删改背后的社会意识和历史逻辑。
一个可以引申的话题是,如果说该书在梅兰芳生前的修改,是得到了他本人的默许,那么为什么在梅兰芳故世后,他的文章还会被随意更改?难道更改者觉得他们有权这样做并安之若素吗?当然,这背后存在复杂的时代因素或某种不得已的苦衷。我们需要以一种“理解之同情”细细考量,有时亦难苛责更改者。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版《梅兰芳全集》所收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不仅未改,还有意识地为读者提供了原版复原和校勘对比的渠道。改或不改的背后,其实透露出了更多值得关注和探讨的学术意涵。
① 许姬传撰有《〈舞台生活四十年〉日文版序》(《许姬传艺坛漫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0页),可知其书曾有翻成日文的动议,惜无下文。
② 此处是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版本的概述。更详细的情况,参见拙文:《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版本考》(《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十余年来,笔者在海内外费心搜求,终于将《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所有版本蒐集齐全,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的文献基础。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傅谨主编新版《梅兰芳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联合出版)推出。新版全集收录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不但以“文革”后的中国戏剧版为底本,与其他一些版本做了细致的校勘,还独具匠心地印出最早的《文汇报》连载的全部文本。此一对《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收入处理,成为新版全集的一大亮点,充分凸显了编者的学术意识和理论思考。排比众版,做出校勘,尤为难能可贵,这恰恰是2000年版《梅兰芳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所欠缺的。但新版《梅兰芳全集》也有遗憾,即未能关注香港和台湾地区及国外版本。
③ 此处借用已故学者张晖语。张晖《追寻古典文学的意义》云:“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南方都市报》2013年3月24日“张晖纪念特刊”)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版本和异文,就是要探究并发掘其变迁背后所呈现出的时代感。此一理念宗旨,贯穿本文的始终。
④ 《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44页。
⑤ 傅谨:《前言》,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9页。
⑥ 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梅兰芳》里,第一部分演绎早年梅兰芳如何脱颖而出,重点拍了梅兰芳与前辈艺人“十三燕”的竞争与合作。此“十三燕”即影射谭鑫培,意在表现与谭鑫培的合作与竞争,在梅兰芳早期的舞台生涯中是多么重要。
⑦⑮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一集,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第222—223页,第156页。本文称“平明版”。“平明版”与“《文汇报》连载”相比,略有删节。
⑧ 转引自许姬传:《〈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许姬传、许源来:《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277页。
⑨⑭⑯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第12页,第263页,第117页。
⑩ 《文汇报》连载(1950年12月27日)时,有“急中生智”一节,但后来成书改为“《儿女英雄传》”,且把王蕙芳“阴”梅兰芳的一段删去了。
⑪ 梅兰芳述、许姬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文汇报》1950年12月27日。
⑫⑳ 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朱家溍整理:《我和杨小楼合作(上)》,《戏剧艺术论丛》第二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第42页。
⑬ 梅兰芳、程砚秋关系微妙,虽有师徒名分,但后来并称“四大名旦”(另两人为尚小云、荀慧生)。删去拜师情节,亦有斟酌,并非偶然。
⑰ 罗瘿公的诗较长,有二十余句,梅兰芳不可能随口吟出,故肯定系记录者整理文稿时添加。因此,如删去罗诗,尚情有可原,但前面叙述雅集,确不应删。
⑱㉑㉕ 梅兰芳述,许姬传、朱家溍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第103页,第242页。
⑲ 梅兰芳口述,许姬传、朱家溍整理:《我和杨小楼合作(下)》,《戏剧艺术论丛》第三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㉒梅兰芳:《〈童女斩蛇〉——〈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连载》,《戏剧报》1962年第12期。
㉓ 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309页;高放:《序言》,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㉔ 参见许姬传:《〈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82—283页。
㉖ 梅兰芳:《穆桂英》,《戏剧报》1958年第20期。
㉗㊲ 许姬传:《〈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82页,第277页。
㉘ 1981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封面署名,许姬传记,但扉页却是许姬传、朱家溍记,有差别。
㉙谢蔚明:《旁证柯灵黄裳笔墨官司——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面世经过》,《世纪行》2000年第11期。
㉚ 参见《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1949年6月—1966年5月)第四章“沉重的1957年”,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135页。
㉛ “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一章,“文革”后出版第三集时增补甚多。盖最初香港《文汇报》连载的篇幅有限,及收入第三集,就把一些当时采访的“口述历史”增补进来,多方印证,极有文献价值。
㉜ 这三章的名字根据许姬传、朱家溍整理的《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后记》,但赴日演出一章后遗失,而“梅兰芳、杨小楼合组崇林社”一章在“文革”后整理出书时,被分成两章。
㉝“文革”期间批判梅兰芳的宣传册和文章,就有此类标题,如《阻拦京剧革命的顽石和恶虎——梅兰芳必须批判》(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批判材料之六),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等1967年11月翻印。
㉞ 台湾版推出后,不久即脱销,又有再版。可证此书在台湾亦有一定销路。参见许姬传:《〈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后》,《忆艺术大师梅兰芳》,第287页。
㉟ 梅兰芳述:《舞台生涯》,台湾里仁书局1979年版,第2页。此为精装本之叙述,后出之平装本与此不同。
㊱ 柯灵、黄裳原为同事,上下级关系,皆是《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功臣。但两人后交恶,《舞台生活四十年》竟为导火索。参见柯灵:《想起梅兰芳》(《读书》1994年第6期);黄裳:《关于〈饯梅兰芳〉》(《黄裳文集·春夜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