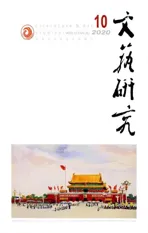从个人关切到社会关怀
——论吴敬梓的人格升华与创作转向
2020-12-28陈庆
陈 庆
“五四”以来的吴敬梓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集中于吴敬梓的生平考察和《儒林外史》的文本解读、版本整理、本事发掘,胡适、陈美林、李汉秋等贡献尤大①。近年来,吴敬梓的诗文也受到较多关注,李汉秋、项东升《吴敬梓集系年校注》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②。以上研究虽成绩斐然,但仍有继续拓展、深化的空间。比如,吴敬梓的创作生涯,可大体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诗文为主,后期以《儒林外史》为主,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他在诗文中的人格形象和在《儒林外史》中寄寓的人格理想有何显著差异?其创作转向与人格升华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具体作品和具体事实,如吴敬梓的诗文、《儒林外史》《诗说》和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等,单独来看,都有不少学者关注③,但综论作家人格与创作的全面、系统的宏观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拟就吴敬梓的人格升华与创作转向的内、外因缘展开系统论述,以期深化对吴敬梓及其创作的研究。
一、诗文:弥漫着科举失利的挫折感
纵观吴敬梓一生,其前期的首要关切是科举功名。其诗文或写亲情,或写友情,或写游历,情感和题材是多方面的,难以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涉及功名富贵和个人身世,通常充满科举失利的挫折感。
吴敬梓现存可以系年的诗文,包括赋4篇、诗137首、词47首,共188篇。赋止于三十三岁(1733)所作《移家赋》,词止于三十九岁(1739)所作《内家娇》,诗止于四十岁(1740)所作《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均为前期作品。其中与家族的科举辉煌和个人的科举经历有关的,多达五十余篇。一部分泛写人生沦落、知音难遇,如《小桥旅夜》:“早岁艰危集,穷途涕泪横。苍茫去乡国,无事不伤情。”《送别曹明湖》:“人生知遇真难得,挥手别君泪沾臆。”《金缕曲·七月初五朱草衣五十初度》:“天意也怜吾辈在,且休忧尘世无相识。”一部分聚焦于科举鼎盛的家族历史,顺便提到个人寥落及由此带来的愧悔之痛,如《遗园四首》之四:“风雨飘摇久,柴门挂薜萝。青云悲往事,白雪按新歌。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可怜贫贱日,只是畏人多。”《酬青然兄》:“明发念先人,不寐涕汍澜。况当明圣代,敢忘振羽翰?”一部分侧重书写与博学鸿词科相关联的知遇之恩和未能奋飞的痛苦,如《送学士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昔岁彤廷诏,曾令蓬户窥。不才尘荐牍,授简写新诗。坐待官厨饫,吟看日晷移。几回瞻謦欬,再拜奉师资。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曹跃舟留宿南轩》:“感恩望霄汉,相顾叹蹉跎。”上述三类作品,对科举失利的挫折感只是点到为止,并未展开。
除此之外,这五十余篇诗词中,另有十余篇集中抒写科举失利的挫折感,表达了吴敬梓的个人关切。下面试以时间为序略加考察。
1730年,吴敬梓三十岁。是年除夕,作组词《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八首。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后悔自己因一时愤激而放浪形骸,竟然成了全椒一带公认的败家子,如之三:“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年少何人,肥马轻裘笑我贫。 买山而隐,魂梦不随溪谷稳。又到江南,客况穷愁两不堪。”另一方面,痛感举业无成,有负于科举鼎盛的家世、辛勤养育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如之五:“哀哀吾父,九载乘箕天上去。弓冶箕裘,手捧遗经血泪流。 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牛眠,何日泷冈共一阡?”之六:“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买得厨娘,消尽衣边荀令香。 愁来览镜,憔悴二毛生两鬓。欲觅良缘,谁唤江郎一觉眠。”
据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可知,吴敬梓在父亲去世之后,曾遭遇一场来自家族内部的财产纷争,赖刘翁等人相助,才终于平息。涉世未深的吴敬梓因此变得愤世嫉俗,故意把家产不当回事,过上了情色无度的生活。先是卖田,后是卖房,以致家产所剩无几。所谓“昔年游冶,淮水钟山朝复夜”(《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二),“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写的就是这段令他愧悔万分的经历。
全椒吴氏是当地声名赫赫的科举世家,即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所云:“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④这样一个家世背景,既给吴敬梓带来了作为世家子弟的荣耀,也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他比常人更加渴望经由科举而飞黄腾达,因为这不仅是个人前程所系,也是家族声名所系。无奈科举功名是不能继承的,没有哪个家族可保子子孙孙科举顺遂。不幸的是,吴敬梓在十八岁考上秀才后,一直未能跨过乡试的门槛,即所谓“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身为故乡人所不齿的败家子,无颜继续待在全椒,吴敬梓打起了迁居南京的主意。
1733年,吴敬梓三十三岁。他在迁居南京之后,痛定思痛,作了生平最有分量的一篇赋——《移家赋》。该赋写作当始于1733年,至1734年初才最终定稿。此赋将“身辞乡关”“迁居南京”视为他人生中最为耻辱的一次逃亡:“余家世于淮南,乃流播于江关,枯鱼穷鸟,不可问天,布衣韦带,虚此盛齿,寄恨无穷,端忧讵止?”吴敬梓之所以如此悲怆,是因为迁居南京有辱门庭。如果功名显赫,春风得意地去外地做官,他不仅不会懊丧,反倒还应该兴高采烈。
中国古代,诗和赋常用于抒发分量厚重的情感。诗中代表如阮籍《咏怀》、杜甫《秋兴》,赋的代表如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和《别赋》、庾信《哀江南赋》,都因感情厚重和表达考究传诵不衰。吴敬梓将其移家南京,比拟为陆机入洛:一个是不得已离开了故乡,一个是不得已离开了故国。他科举失利的挫折感和身为败家子的心酸,在《移家赋》中有充分表达。
1734年年底,吴敬梓写《乳燕飞·甲寅除夕》一词。与《移家赋》相比,这首词较为平实、直白:“令节穷愁里,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风雪打窗寒彻骨,冰结秦淮之水。自昨岁移居住此。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捧卮酒,泪痕滓。 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谷贻孙子。倘博将来椎牛祭,总难酬罔极恩深矣。也略解,此时耻。”俗话说“三十而立”,吴敬梓已过而立之年,却依然只是生员,一个年纪老大的秀才。他把取得科场功名视为对父母最大的尽孝,但功名富贵却又总是与他无缘。
这首词还提到了“他乡留滞”,“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说的是他“昨岁”从故乡全椒移家南京一事。也是在这一年,他还作了另外两首词,抒发的同样是作为“不孝”之人的愧疚感。一首是《满江红》(雀化虹藏),下阕有云:“岂合在,他乡住?岂合被,虚名误?盼故山榛莽,先人丘墓。已负耦耕邻父约,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一首是《琐窗寒·忆山居》,其中提到:“撇却家山,紫翠丹青如画。想泼醅春酒正浓,绿杨村店鸡豚社。几多时,北叟南邻,定盼余归也。”杨得意曾把司马相如推荐给汉武帝,司马相如的人生从此海阔天空。吴敬梓也对自己的辞章颇为自信,希望遇见杨得意那样的人。吴敬梓确信,要是有人把自己推荐给今上,他也必然不同凡响。只是这样的机遇迟迟未能降临,吴敬梓因此心灰意冷;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因为功名不遂而愈发强烈。
1736年除夕,吴敬梓作《丙辰除夕述怀》一诗:“回思一年事,栖栖为形役。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厄。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愬愬。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严霜覆我檐,木介声槭槭。短歌与长叹,搔首以终夕。”这首诗关联着一个重大事件:乾隆元年(1736)三月,清廷再开博学鸿词科,三十六岁的吴敬梓预试合格,获得安徽巡抚赵国麟的正式荐举,却又因病未能参加廷试。博学鸿词科是常科之外的特科,旨在选拔那些辞章或者学术特别优异的人。困顿中的吴敬梓,有幸获得考试资格,真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这次机遇的因病错失,令他深为懊恼。司马相如的《封禅书》,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都是历史上的朝廷“大制作”。有能力写这种“大制作”的人,正是博学鸿词科所要搜揽的。吴敬梓因病不能赴试,他把这一困境比拟为飞鸟困在网罗之中。
1739年,吴敬梓三十九岁。这一年生日,他写《内家娇·生日作》一词:“行年三十九,悬弧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垄;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 行吟憔悴久,灵氛告:须历吉日将行。拟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见重华协帝,陈词敷衽;有娀佚女,弭节扬灵。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关键词仍是“富贵”与“功名”,但情绪较为复杂。所谓“难求富贵”“休说功名”,是说他试图放弃对此的眷恋,却又依旧不能断然舍弃。行将踏进不惑之年的他,在确定未来人生走向时,不免有几分犹疑、困惑。
综上所述,吴敬梓人生前期的诗文,凡涉及功名富贵的,通常表现出急切的渴慕之情或求而不得的焦虑痛苦。吴敬梓的个人关切,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与上述诗文中的吴敬梓有别,《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这个以吴敬梓本人为原型的人物,在对待科举功名的态度上,与之恰好形成对照。例如,乾隆元年,吴敬梓因病未能参加廷试,那种失落和懊丧之情,在诗文中溢于言表。而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却是故意装病,以生病为借口拒绝参加考试。辞试成功,杜少卿分外高兴,说:“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⑤这样一个杜少卿,折射出的是写作《儒林外史》时的吴敬梓,而不是前期诗文中的那个吴敬梓。
二、“词科”反思:从个人关切到社会关怀
促使吴敬梓对科举制度展开深入反省的,是乾隆元年举办的博学鸿词科,史称“丙辰词科”;而与《儒林外史》写作相伴随的《诗经》研究,则进一步提升了吴敬梓的人格境界,有助于《儒林外史》内涵的深化。
吴敬梓是丙辰词科的亲历者,也一度对之寄予厚望。他现存的四篇赋中,有三篇与之有关:《继明照四方赋》是乾隆元年作的学院取博学鸿词试帖,《正声感人赋》是乾隆元年作的抚院取博学鸿词试帖,《拟献朝会赋》可能是为督院试或更高一级的考试预拟的赋作。现存的诗中,有三首与丙辰词科有关,分别是学院取博学鸿词试帖《赋得敦俗劝农桑》、抚院取博学鸿词试帖《赋得云近蓬莱常五色》、督院取博学鸿词试帖《赋得秘殿崔嵬拂彩霓》。在应博学鸿词试之前,吴敬梓耗费巨大心力写了《移家赋》,意在证明他确有写朝廷“大制作”的才能。然而,丙辰词科的实际情形与吴敬梓的设想大相径庭。
清廷一共举办了两次博学鸿词科,一次在康熙十八年(1679),史称“己未词科”;一次即乾隆元年的丙辰词科。两次性质虽然说来相同,而情势实大有不同。己未词科是在“三藩之乱”平定在即、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的背景下举行的,其动因有三:其一,明清易代,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动荡,急需笼络隐逸之士以营造升平气象;其二,此前为筹军饷,捐纳得官者甚众,官场混乱,需要选拔人品清高的士人以孚众望;其三,为数不少的奇才异能之士,未能经由常科选拔出来,有必要借特科加以弥补。所以,无论是决策者康熙还是各级官吏,都郑重其事,全力以赴。从录取结果看,一等20名,二等30名,一时名儒硕彦,网罗殆尽;其中秀水(今浙江嘉兴)朱彝尊、无锡(今属江苏)严绳孙、富平(今属陕西)李因笃、吴江(今属江苏)潘耒,皆以布衣入选,时称“四大布衣”⑥。丙辰词科距己未词科已五十余年。第一道开科谕旨颁于雍正十一年(1733),响应者寥寥。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即位,再加申谕,各级官员才按部就班地启动了保荐程序。与己未词科相较,丙辰词科阅卷严苛,录取比例低,任职状况也大为逊色。己未科与试者143人,录取50人;丙辰科与试人数更多,却仅录取19人。己未科取中者,进士授编修,已官卿贰、部曹、参政、参议者授侍讲,其他授检讨;丙辰科取中者,一等授编修,二等举人、进士授检讨,其他授庶吉士,散馆任职,竟有改主事、知县者。丙辰科落选的人中,长于经史的有桑调元、顾栋高、程廷祚、沈彤、牛运震、沈炳震等,长于辞章的有胡天游、刘大鹏、沈德潜、厉鹗、袁枚等,足以引发士林的失望和惊诧。
丙辰科与己未科的差异何以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于:朝廷已不需要像康熙十八年那样笼络人才。三藩之乱平定已久,台湾也已收复,天下一统,臣民服帖,哪里用得着大规模地破格搜罗人才。当吴敬梓从族兄吴檠那里得悉了丙辰词科的诸多内幕时,他有过幸未与试的窃喜,更多的是对与试者的同情和对朝廷动机的质疑,并把这种质疑从特科逐渐延伸到了常科。
这一时期,吴敬梓先后作《伤李秀才》《贫女行二首》《美女篇》等诗,是考察其心迹的一手资料。《伤李秀才》诗序云:“丙辰三月,余应博学鸿词科,与桐城江若度、宣城梅淑伊、宁国李岑淼同受知于赵大中丞。余以病辞,而三君入都。李君试毕,卒于都下。赋此伤之。”诗的第一句是“扶病驱驰京辇游”,可见李岑淼与吴敬梓一样,廷试前都生了病。吴敬梓因病而未赴试,曾不免沮丧;李岑淼带病赴试,足见他对这次机遇的珍惜。当李岑淼病死于都下的消息传来,吴敬梓伤心地写下了这首诗,并由此对读书人的境遇有了一种超越自身的观察和思考。
挚友程廷祚的铩羽而归对吴敬梓的触动尤为巨大。程廷祚别号绵庄,是《儒林外史》中庄绍光的原型。程晋芳《绵庄先生墓志铭》说:
盖自国初黄梨洲、顾亭林两先生殁后百有余年,大儒统绪几绝,继之者惟先生。然久试场屋,辄不利。雍正十三年举博学鸿词科,安徽巡抚王公鋐以先生应诏。乾隆元年至京师,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门下,属密友达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试不用,归江宁,时年四十有五。⑦
程晋芳把程廷祚与黄宗羲、顾炎武等清初大儒相提并论,或稍有拔高之嫌,但程廷祚无疑是雍、乾年间首屈一指的经学家。至于落选原因,拒不接受权要的延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诸多一流学者或一流辞章家也同样名落孙山。博学鸿词科的举办,从理论上说,旨在弥补常科只认试卷不认人的弊端,而丙辰词科将那么多名流一股脑刷掉,可见当局并没有选拔人才的诚意。特科也好,常科也好,科举考试的主导权都在体制一方而不在士子一方;天下士子,数十年寒窗苦读,以求一第,而掌控体制的人对此未必在意。
面对天下士子局促于体制之下的卑微地位,吴敬梓深感痛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个建议:读书人不必热衷于功名富贵,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人格的独立和相应的尊严。他这一时期写的《美女篇》《贫女行二首》,都用比兴手法表达了这一主旨。《美女篇》云:“夷光与修明,艳色天下殊。一朝入吴宫,权与人主俱。不妒比《螽斯》,妙选聘名姝。红楼富家女,芳年春华敷。头上何所有?木难间珊瑚。身上何所有?金缕绣罗襦。佩间何所有?环珥皆瑶瑜。足下何所有?龙缟覆氍毹。歌舞君不顾,低头独长吁。遂疑入宫嫉,无乃此言诬。何若汉皋女,丽服佩两珠。独赠郑交甫,奇缘千载无。”《美女篇》异乎寻常之处,在于否定了“入宫见嫉”的习惯说法。“富家女”的失意,不是因他人嫉妒,而是因为她不该进入那个圈子;一旦进入那个圈子,就成了仰人鼻息的被选择者,就仿佛渴望录取的应试者一样。要获得尊严,就应像汉皋游女一样:她和郑交甫之间,不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而是互相吸引、互相爱慕的关系。吴敬梓为天下士子给出的这个建议,是以不追逐功名富贵为前提的。他同时还写了《贫女行二首》:“蓬鬓荆钗暗自羞,嘉时曾以礼相求。自缘薄命辞征币,那敢逢人怨蹇修?”“阿姊居然贾佩兰,踏歌连臂曲初残。归来细说深宫事,村女如何敢正看!”乐于做村女或贫女,也是看淡功名富贵的意思。
经历了丙辰词科后的痛苦思考,吴敬梓终于在四十岁左右(1740)开始了《儒林外史》的写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写《诗说》——一本研究《诗经》的著作。据李汉秋研究,吴敬梓开始撰写《诗说》的时间,当不晚于乾隆辛酉(1741)⑧,依据有二:一是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云:“辛酉、壬戌间,延至余家,与研诗赋。”⑨一是蒋宗海《吴文木〈诗说〉序》云:“程舍人鱼门言先生作《诗说》时,尝主其家,忽夜悟《凯风》诗旨,即援笔书之,亟呼鱼门共质,因与剧论达旦。”⑩据此,吴敬梓动笔写《儒林外史》不久,即开始了《诗经》研究。
吴敬梓以《诗经》研究作为晚年的安身立命之处,并不是想做一个经学家,而是想经由对《诗经》的体悟,找回原始儒家的气象和真谛。这个寻找和体悟的过程,潜在地影响了《儒林外史》的写作。或者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作和《诗经》研究,有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启发的关系。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吴敬梓的人格不断升华,《儒林外史》的内涵也逐渐深化。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诗说》中有《鸡鸣》一则,对《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一诗作了如下解读:
朱子读《女曰鸡鸣》之诗,曰:“此诗意思甚好,读之有不知使人手舞足蹈者。”诸儒所解亦甚多,究未得此诗之妙在何处。窃意此士乃乐天知命而又化及闺房者也。人惟功名富贵之念热于中,则夙兴夜寐,忽然而慷慨自许,忽焉而潦倒自伤。凡琴瑟樽罍,衣裳弓缴,无一而非导欲增悲之具。妻子化之,五花诰、七香车,时时结想于梦魂中,蒿簪綦缟,亦复自顾而伤怀矣。故王章牛衣之泣,泣其贫也,所以终不免于刑戮。即伯鸾之妻制隐者之服,犹欲立隐之名也。此士与女,岂惟忘其贫,亦未尝有意于隐。遇凫雁则弋,有酒则饮,御琴瑟则乐,有朋友则相赠。士绝无他日显扬之语以骄其妻,女亦无他日富贵之想以责其夫。悠游暇日,乐有余闲。此惟三代太和宇宙时,民间或不乏此。而郑当淫靡贪乱之世,乃有此修身齐家之君子,故诗人述其夫妇之私言,佩诸管弦,便可使威凤翱翔而游鱼出听也。比户尽如此士女,倘所谓风动时雍者矣。其所关于人心政治者,岂细故哉!
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曾认定《女曰鸡鸣》是“贤夫妇相警戒之词”⑪:夫妻二人互相勉励,以期于世有补。吴敬梓却断言,诗中的这一对夫妇,安贫乐道,绝无功名富贵之念。在他看来,所谓于世有补,不过是热衷于功名富贵的另一种说法。
并非偶合,《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将《诗说》对《女曰鸡鸣》的新解融入到了小说情节之中。几位朋友谈及《女曰鸡鸣》,杜少卿说了自己的新解:“但凡士君子横了一个做官的念头在心里,便先要骄傲妻子。妻子想做夫人,想不到手,便事事不遂心,吵闹起来。你看这夫妇两个,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弹琴饮酒,知命乐天。这便是三代以上修身齐家之君子。这个前人也不曾说过。”⑫杜少卿的话,其实是把《诗说》的意思用口语更浅白地表达了出来。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谈他关于《女曰鸡鸣》的新见,主要不是为了展开学术讨论,而是从儒家经典中为无意于功名富贵的杜少卿夫妇和庄绍光夫妇寻找依据。杜少卿辞掉朝廷徵辟,隐居南京,换了汲汲富贵的人,岂能忍受得了?但杜少卿和他的妻子却过得十分惬意。庄绍光辞爵还家,隐居玄武湖,他的生活如同一首清澈的小诗:闲着无事,便斟一杯酒,拿出杜少卿作的《诗说》,叫娘子坐在旁边,念给他听;念到有趣处,吃一大杯,彼此大笑⑬。这两对夫妇,正是吴敬梓所赞许的“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的“修身齐家之君子”。
又如,孔子曾在《论语》中这样表彰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⑭孔子赞美泰伯的让德,而吴敬梓所推崇的《儒林外史》中的人物虞育德,正是践行这种让德的典范。他的人品如此之高,学问如此之好,担任的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闲职。难得的是,虞育德并不因此而抱怨,而是乐天知命,努力发挥人格表率作用。
吴敬梓《诗说》中的《简兮》一篇,谈怀才不遇的士君子何以自处,与《儒林外史》的虞育德形象,正好形成呼应关系:
余反复《简兮》之诗,而叹硕人之所见浅也。“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鸿飞冥冥,弋人何篡”,何必以仕为?即不得已而仕,抱关击柝可矣,孰迫之而伶官?既俯首于伶官,即当安于籥翟之役,必曲折引申以自明其所思于庸夫耳目之前,谁其听之耶?《卞和论》云:“兰生幽谷,不以无人不芳;玉产深山,不以无工不良。雕之琢之,取以为器,人之乐,非玉之幸也。和既以玉刖矣,以玉殉可也,以玉隐可也,必涕泣涟洏以自明其为玉,何其愚也!”观此,可为诗人进一解。
《诗经·邶风》中的《简兮》一诗,东汉郑玄和南宋朱熹的解读大体相近,认为乃贤人时值卫之衰世,怀才不遇,仕为伶官,乃以自誉而实自嘲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人品之高⑮。而吴敬梓认为,一个安贫乐道的贤人,何必在世俗社会洗刷自己?何必在意世俗社会的荣辱毁誉?当然,对造成“贤者”怀才不遇的体制,吴敬梓是有批评的,而且批评得极为尖锐。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吴敬梓的《诗经》研究和《儒林外史》写作,虽然一是学术研究,一是小说创作,但却相得益彰。吴敬梓从原始儒家那里获得了安身立命的勇气和底气,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的水准也得到了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社会关怀在《儒林外史》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儒林外史》:社会关怀的集中表达
吴敬梓在人生后期潜心从事《儒林外史》的创作,其人格升华与创作转向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他对科举制度的不满不再是基于个人失意,而是着眼于这一制度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后果:科举制度让太多的读书人挤在一条独木桥上,浪费了大量人力资源,在把许多读书人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的同时,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崇拜功名富贵的心理。
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但诋父兄专制举”句下自注引了吴敬梓的两句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⑯吴敬梓的这一质询意味深长。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曾如此评价唐代的科举制:“唐代的科举制度,实在亦有毛病。姑举一端言之,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唐代前后三百年,因政权之开放,参加考试者愈来愈多,于是政府中遂设有员外官,有候补官,所谓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⑰所谓“专储制举才”,是说人才集中于科举一途,人才的积压和浪费即由此造成。
科举制在带来求官人数持续膨胀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读书人的困顿。所有的读书人都以做官为目标,而做不上官的一定是大多数,部分读书人不免陷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儒林外史》中的老秀才倪霜峰就是此例。他生了六个儿子,一个死了,四个因为没有吃用卖到了他州外府,最小的一个也因为生活无着出继给经营戏班的鲍文卿;他本人则靠修补乐器为生。谈起人生的潦倒,倪霜峰感慨地说:“我从二十岁上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儿女又多,只得借这手艺糊口,原是没奈何的事。”⑱在《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吴敬梓写了四个市井奇人,都是读书人:一个会写字的,叫季遐年,寄食于僧寺;一个围棋下得好,叫王太,卖火纸筒子为生;一个画的画好,叫盖宽,开茶馆为生;一个琴弹得好,叫荆元,做裁缝为生。他们对考试做官都没有兴趣。有人问荆元:“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荆元答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⑲这表明,吴敬梓确已有几分近代意识:在应考做官之外,读书人不妨另谋生路;不是不读书,而是不把做官当成读书的唯一目标。
《儒林外史》充分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科举挤压了真儒的生存空间,无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虞博士是《儒林外史》中的“第一人”⑳,他在体制内被边缘化,不是因为人品不好,而是因为人品太好。五十岁的他中了进士,“那知这些进士,也有五十岁的,也有六十岁的,履历上多写的不是实在年纪。只有他写的是实在年庚,五十岁。天子看见,说道:‘这虞育德年纪老了,着他去做一个闲官罢。’当下就补了南京的国子监博士。”㉑科举时代的履历,有实年与官年之别:实年就是真实年龄,官年就是填在表上的年龄,通常比实年要小。诚信的人吃亏,弄虚作假的占便宜,这并非个别情况,虞博士只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而已。
第四十六回,唐二棒棰向虞华轩请教一个荒唐的问题:“我前科侥幸,我有一个嫡侄,他在凤阳府里住,也和我同榜中了,又是同榜,又是同门。他自从中了,不曾到县里来,而今来祭祖。他昨日来拜我,是‘门年愚侄’的帖子,我如今回拜他,可该用个‘门年愚叔’?”㉒余大先生听说了这事,气得两颊紫涨,愤怒地反问道:“请问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紧,是科名要紧?”“既知是祖父要紧,如何才中了个举人,便丢了天属之亲,叔侄们认起同年同门来?”㉓在科名和“天属之亲”之间,五河县人把科名看得更重;其骨子里是对富贵的看重,所以回目用了“五河县势利熏心”来形容。科举考试有一个理论上的目的,即引导考生研读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的规训为人处事,但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势利之风。
吴敬梓早期对八股文的憎恶与他个人的功名不遂直接相关,但《儒林外史》对八股文的调侃则超越了个人关切。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说吴敬梓“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缘此,所遇益穷”㉔。程晋芳所描述的,是处于人生前期的吴敬梓。《儒林外史》同样不恭维八股文,但考虑问题的角度迥然不同。小说中写了两个翰林:高翰林和鲁翰林。翰林理所当然是八股文写作的顶尖高手,这两位翰林最得意的也是就八股文发表高论。第十一回中,鲁翰林这样谈论八股文的妙用:“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㉕八股文是讲究起承转合的,因而要注意思路的贯通;八股文是讲究对仗等修辞技巧的,因而与诗赋有相通之处。由此着眼,鲁翰林的话自有依据。但是他把八股文说得如此神乎其神,却正是所谓不可向迩的“翰林气”。第四十九回,高翰林这样谈论“揣摩”的妙用:“‘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了。小弟乡试的那三篇拙作,没有一句话是杜撰,字字都是有来历的,所以才得侥幸。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甚么官了!”㉖考场上的八股文,顺应风气的,得中的几率往往更高。努力随着风气的变化调整写作风格,就是所谓长于“揣摩”。所以,高翰林的话,从应试的角度看自有合理性。但一个身居庙堂、理当兼济天下的人,却仅仅以擅长考试“揣摩”高视阔步,不也甚为可鄙吗?《儒林外史》这一类描写,延续了前期吴敬梓“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的一面,但就《儒林外史》整体而言,这些描写又是后期吴敬梓社会关切的体现。
《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比照前期那个愤世嫉俗的吴敬梓写了一个虞华轩,而以后期吴敬梓的眼光对他做出了评价:
话说虞华轩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岁上,就是个神童。后来经史子集之书,无一样不曾熟读,无一样不讲究,无一样不通彻。到了二十多岁,学问成了,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头就知到尾,文章也是枚、马,诗赋也是李、杜。况且他曾祖是尚书,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无奈他虽有这一肚子学问,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虞华轩生在这恶俗地方,又守着几亩田园,跑不到别处去,因此就激而为怒。他父亲太守公是个清官,当初在任上时,过些清苦日子。虞华轩在家,省吃俭用,积起几两银子。此时太守公告老在家,不管家务。虞华轩每年苦积下几两银子,便叫兴贩田地的人家来,说要买田、买房子。讲的差不多,又臭骂那些人一顿,不买,以此开心。一县的人都说他有些痰气,到底贪图他几两银子,所以来亲热他。㉗
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是吴敬梓的自况,其实这里的虞华轩,和“一朝愤激谋作达”㉘的青年吴敬梓之间,也有一种对应关系:五河就是全椒;虞华轩的家世背景,与吴敬梓的家世背景大致相合;而虞华轩的人品、学问,同样是比照吴敬梓来设定的。被视为败家子的吴敬梓,对全椒耿耿于怀:如果不是这个“恶俗地方”,他怎么会“激而为怒”、落得“去年卖田今卖宅”㉙的境地呢?吴敬梓偶尔会借《儒林外史》的写作洗刷自己的败家子形象,这样一种动机,不必曲为隐讳。但《儒林外史》对虞华轩的愤世嫉俗并未一味喝彩,而是在与虞博士、庄绍光等人的对比中,表明并不赞成他的为人处世。向虞博士、庄绍光认同,而不是向虞华轩认同,这是后期吴敬梓社会关怀的表现。
综上所述,写作《儒林外史》时的吴敬梓,与前期的诗文作者吴敬梓,确有巨大的人格差异。作为一个科举时代的失意者,吴敬梓曾经为此而焦虑,而愤怒,并将这种挫折感倾泻在他的诗文之中。但在《儒林外史》的写作中,支配他的已不再是个人关切,他以一个在野儒者的视角,观察和描述他所熟悉的读书人的生活,真正做到了“以公心讽世”㉚,他的《儒林外史》因而具有了不朽的价值。
① 胡适分别于1920年、1922年撰写了《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此外,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均为相关领域的扛鼎之作。
② 李汉秋、项东升:《吴敬梓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本文所引吴敬梓诗文均据此本,为避繁琐,仅随文注明篇名。
③ 相关论著,参见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张国风:《儒林外史的人间》,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朱万曙:《诗人吴敬梓》,《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陈文新:《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
④⑦⑨⑩⑯㉔㉘㉙ 李汉秋编著:《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第140页,第11页,第31页,第15页,第11页,第3页,第3页。
⑤⑫⑱⑲㉑㉒㉓㉕㉖㉗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96页,第400—401页,第298—299页,第628页,第422页,第533—534页,第534页,第139页,第563—564页,第539—540页。
⑥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07页。
⑧ 参见《吴敬梓集系年校注》,第479页。
⑪ 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页。
⑬ 对这一情节的分析,参见陈文新:《吴敬梓的情怀与哲思》,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11—212页。
⑭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8页。
⑮ 参见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194页;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4页。
⑰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58页。
⑳ 《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卧闲草堂评语,《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第292页。
㉚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