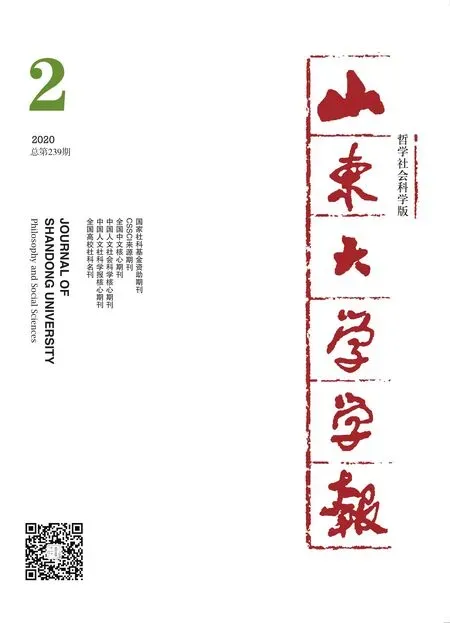晚清民国《礼记·儒行》的再经典化及其意义诠释
2020-12-28蔡杰
蔡 杰
从经典诠释史上看,《礼记·儒行》在宋明时期受到理学家的质疑,却获得晚清民国学者的普遍推崇。前后二者相映成趣,堪称儒学史上的一段公案。事实上,《儒行》不仅仅是文本可靠性的问题,还关乎儒家对“儒”的自我认知,应该说后者才是《儒行》受到质疑或推崇的本质原因。学界对宋儒质疑《儒行》的问题已有一定的关注,而对晚清民国学者推崇《儒行》现象的研究,在儒学史上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一、质疑《儒行》:理学的冲击与明清的突破
《儒行》是不是孔子之言?我们一般会将这一质疑追溯到北宋李觏,不过唐代来鹄也明确提到过对《儒行》的否定。来鹄观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实际问题而发,认为世俗观念中的儒士(文士)无用,儒书(言书)无用。来鹄主张孔子观念中的“儒”没有限制性的标准,因而《论语》所谓“君子儒”“小人儒”,《儒行》的“十五儒”都不是孔子之言(1)来鹄:《儒义说》,《全唐文新编》(第4部第3册),周绍良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9972页。。可以这么理解,来鹄对《儒行》的否定,是在唐代佛老盛行而儒学没落的大背景下,对儒家“五经”的实用性产生的质疑,从而波及《儒行》。所以能够确定的是,来鹄此说并不是专为《儒行》的义理而发,这与后世理学视域中的宋儒观点是有较大差别的。
由此,若将对《儒行》的质疑追溯到北宋李觏,也没有根本性的错误。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儒行》一直都是权威文本,即便是到了北宋初年,朝廷仍以《儒行》与《中庸》《大学》一同颁赐近臣以及新第举人、进士,说明《儒行》仍是受到官方认可的。但是随着北宋理学的兴起,李觏、 二程、 吕大临等纷纷质疑《儒行》文本(2)李觏提出:“《儒行》非孔子之言也,盖战国时豪士所以高世之节耳。……考一篇之内,虽时与圣人合,而称说多过,其施于父子、兄弟、夫妇,若家,若国,若天下,粹美之道则无见矣。”(见《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页。)二程认为《儒行》“煞害义理,恰限《易》便只洁静精微了却,《诗》便只温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儒行》之篇,此书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见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4、177、1201页。)其弟子吕大临也跟着说:“此篇之说,有夸大胜人之气,少雍容深厚之风,窃意末世儒者将以自尊其教,谓‘孔子言之’,殊可疑。”(见吕大临等著,陈俊民辑校:《儒行第四十一》,《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60页。)。其观点无非是认为《儒行》具有夸大矜张之气, 不是温柔敦厚或洁静精微的风格。在宋儒眼中,儒者的气质应当是温柔、雍容、敦厚、精微的,由此他们质疑《儒行》不是孔子之言,而是战国豪士的言论。
从思想内容上看,《儒行》偏重于讲述儒者的实践力行,不太符合宋儒好谈性理的品味。所以分析《儒行》受宋儒质疑的原因,可概括为两点:一方面,在宋儒的时代需要本体心性上的理论建构,所以《周易》和《中庸》一类的文献是受欢迎的,而《儒行》则相对不受待见;另一方面,宋代整体的风格守柔,他们对汉学不仅仅是不满于汉学的注经方法,也不满于汉学的思想主张和性情特点。所以宋儒对汉代一些刚毅的儒者也就有一定偏见,《儒行》处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受到质疑反而是情理之中。
在官方层面,至南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朝廷仍欲颁赐新晋进士《儒行》《中庸》,而颇有功于南宋朝纲文化建制的高闶上疏劝止(3)见《宋史·高闶传》。此事应在高宗绍兴五年,非在元年。《宋史·高闶传》载“绍兴元年,以上舍选赐进士第。执政荐之,召为秘书省正字。时将赐新进士《儒行》《中庸》篇,闶奏《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庶几学者得知圣学渊源,而不惑于他说,从之”,说的是高闶在绍兴元年为进士,而召为秘书省正字已是后来的事。根据有相关记载,此事应在高宗绍兴五年九月二十二日,高闶上奏疏:“《儒行》虽间与圣人之意合,而其词类战国纵横之学,盖汉儒杂记,决非圣人格言。”(见楼钥:《攻愧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32页。)。高闶的理由基本上沿袭北宋诸儒的观点,直接将《儒行》排除在圣学之外,认为这是孔门异说。自此,对《儒行》的质疑上升到官方,此后再无颁赐《儒行》的事例,《儒行》的政治地位无复谈起(4)清代陈澧也曾对这一历史事件做过评述:“《宋史·张泊传》云‘太宗令以《儒行》刻于服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玉海》卷五十五亦载此事,又载‘祥符二年,复以《儒行》赐亲民厘务文臣其幕职州县官使臣赐敕令崇文院摹印送閤门辞日给之,又载‘绍兴十八年,御书《儒行》赐进士王佐等’。宋时重《儒行》如此,《宋史·高闶传》云‘时将赐进士《儒行》《中庸》篇,闶奏《儒行》词说不醇,请止赐《中庸》’,盖至是而讥议《儒行》之说,上达于人主矣。”(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清光绪刻本,第9页。)。
由于程朱理学后来成为显学,《儒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在晚清之前,历代儒者大部分是因袭宋儒旧说。对《儒行》的质疑,在宋明理学的学术氛围中几成定论。但是宋元明清的七八百年之间也有极个别的声音,肯定《儒行》是圣人之言,并试图重建《儒行》的权威经典地位,此人就是晚明黄道周。黄道周在重整明朝司经局时,作《儒行集传》一书进呈于皇帝,并拟为太子讲授。黄道周的《儒行集传》是古代现存唯一一部单篇别行的《儒行》诠释著作,其开篇即为《儒行》与“儒”正名,论证《儒行》符合孔子思想,此书所蕴含的经学价值是巨大的,也是《儒行》诠释所绕不开的经典之作(5)关于黄道周《儒行集传》的诠释方法与义理思想,参见林庆彰《黄道周的〈儒行集传〉及其时代意义》,《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增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或拙文《成德与举贤——晚明黄道周对〈儒行〉篇的独到诠释》(未刊稿),本文在此不再详细展开。。
除了黄道周作《儒行集传》对《儒行》的正面肯定之外,清初李二曲也有间接肯定与赞赏《儒行》的言论。李二曲说:“士人儒服儒言,咸名曰儒,抑知儒之所以为儒,原自有在也。夫儒服儒言,未必真儒,行儒之行,始为真儒,则《儒行》不可以不之监也。是篇杂在《礼记》,兹谨表岀,以式同志。懿德之好,人有同然,诚因观生感,因感生奋,躬体力践,有儒之实,斯儒服儒言无媿儒之名矣。”(6)李二曲:《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0页。李二曲虽然没有批判宋儒的观点以及论证《儒行》文本的可靠性,但是他的观点有一层潜在的意思,就是认为《儒行》记载了真儒的行为,而这种行为恰恰能够决定真儒的本质,是相对于儒服、儒言、儒名等外在形式而言的。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李二曲认为《儒行》体现的是真儒,并且他也提出《儒行》是“粹语至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是孔子之言,但可以看出李二曲对《儒行》的态度是比较肯定的(7)李二曲相对肯定《礼记》中多篇语录的经典地位,他说:“子云‘不学礼,无以立’,则《礼》为初学入德之门,不可以不先之者也。中间虽多汉儒附会,然《曲礼》《檀弓》《学记》《表记》《坊记》《儒行》《乐记》等篇,多粹语至论,宜日读一过以薰心。”(见李二曲:《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5页。)。
在宋明理学浓厚的思想氛围下,像黄道周、李二曲这样极个别的声音,也仅是出现在明末清初时期解构理学的思潮当中;总体而言,宋元明清时期对《儒行》还是以质疑为主。譬如四库馆臣在提要中对黄道周《儒行集传》的评价,其实也隐含着宋儒式的质疑:“《儒行》,先儒讥其不纯,以为非孔子之言,以其词气近于矜张,非中和气象。道周负气敢言,以直节清德见重一时,故独有取于此篇。”(8)纪昀等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研究所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70页。这里所谓“先儒”无疑是指李觏、二程、吕大临、高闶之徒。在提要中,四库馆臣并没有对《儒行》文本的是非做出判断,反而说黄道周挑选《儒行》作注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即因为自身的气节德行。清儒将《儒行集传》的成书原因归结于黄道周的“负气敢言”,而没有对宋儒观点进行评价,可以认为四库馆臣是默认宋儒旧说的。
即便是明末清初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质疑《儒行》的声音仍然是占主流。譬如与黄道周、李二曲同时代的王夫之就持宋儒旧说,认为《儒行》“词旨夸诞,略与东方朔、扬雄俳谐之言相似。……盖于《戴记》四十九篇之中独具疵戾,而不足与五经之教相为并列”(9)王夫之:《礼记章句》,《船山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457页。。比宋儒更为刻薄,王夫之将《儒行》视为《礼记》中的唯一瑕疵,并认为此是汉代人所作,而非宋儒所质疑的战国儒士。到了清代陆奎勋比王夫之更进一步,提出《礼记》中多篇均为汉儒所作:“《戴记》中《表记》《缁衣》之属,孰非汉儒所推衍者?何独于《儒行》而疑之?”(10)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九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0页。更有甚者,姚际恒认为《儒行》本于老庄之意,是效仿《庄子》而作(11)姚际恒提出:“战国之时,墨子常非儒,故后之儒士作为此篇以尊儒,而名《儒行》,然依倣《庄子·田子方》篇鲁哀公与庄子论儒服之说为发端,实原本于老庄之意,宜其篇中所言,轻世肆志,迂阔陂僻,鲜有合于圣人之道也。夫庄子非哀公之世,所言寓言十九,此亦甚明,安可本之为说?辑《礼》者但以其名尊儒而收之,岂不误与?”(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九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0页。)。姚氏之说堪称新奇,他实际上是从文本写法的角度,去界定该文本义理思想的归属;具体而言,是将《儒行》判定为符合《庄子》文本的写法,由此推论出《儒行》属于道家。在辞章层面上讨论义理的问题,这种论证方法显然不足以成立。从文本辞章角度上看,姚说有一定的突破性,但在思想义理层面上并没有比宋儒更加高明。
至此,我们可以离析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从宋儒到清儒的诠释中,《儒行》与孔子、孔门七十子及战国儒者、汉儒的关系问题,已经逐渐浮现出来;二、入清之后,从王夫之到姚际恒的《儒行》判断,距离宋儒越来越远,其观点也越来越离谱,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在这种新奇之说当中,似乎已经蕴含着最终进行反思与批驳的种子。
二、经典再确立:儒学思想的博大精深
从儒家经典诠释的角度,当我们看到晚清民国学者对《儒行》的推崇现象时,通过仔细研究会发现,自宋儒的质疑至晚清的推崇之间,其实有一个逐渐演变的内在过程。这一演变过程的内在理路很是值得注意,因为晚清时期对《儒行》的推崇,并不仅仅是当时的外在因素一蹴而就的。
在明末清初时期的理学面临解构之后,晚清学者对《儒行》的肯定,可以追溯到清学的治学风格当中。清学的特点是反对宋学而推崇汉学,那么如此学术风格也开始决定了清儒对《儒行》的改观。较早在《儒行》问题上反对宋学的有李光地的胞弟李光坡,李光坡略小于李二曲,他虽然没有全面批判宋学,但是在《儒行》的问题上已十分明确地提出质疑宋儒旧说的观点。对宋儒旧说的一连串反问,正是告诫世人为学须切身体察,方能立论,万万不可盲从旧说、人云亦云(12)李光坡:《礼记述注》卷二十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18页。。李光坡对《儒行》的观点,一方面体现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实学特点,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清代质疑宋儒旧说的先河。结合黄道周与李二曲对《儒行》的肯定的历史事件,可以判断,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的兴起源自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以及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思。李光坡的质疑与反思在百年后的清学全面兴盛之际,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乾嘉学派”的朴学大师孔广森。
孔广森是赞同《儒行》不合中庸思想的,这一点与宋儒并无二致;他对《儒行》的肯定,主要是建立在对宋学的强烈批判上面(13)孔广森:《礼学卮言》卷五,清顨轩孔氏所著书本,第13、14页。。孔广森等一批朴学家推崇汉学,批判宋学,对二者的态度极其鲜明,所以宋儒所反对的,孔广森则相应地作出辩护。那么,对孔广森这段话的理解,就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儒行》的正面辩护,二是对宋儒的强烈批判。其一,孔广森认为至上之圣人的思想才是中庸,而《儒行》讲的是一般儒者贤人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儒行》纵然不是儒家最高的精神体现,但也是符合儒门宗旨的。其二,比较于圣人的中庸思想,孔广森认为三代与两汉贤者是过之,而宋儒是不及,这就说明过之者所做工夫已经到位,而不及者所做工夫尚且不足,于是得出结论:宋儒远远不如三代与两汉的贤者(14)孔广森对宋儒的批判可谓不留余力,“东汉士君子于《儒行》,多有其一节,宋以后人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貌为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葸,识见浅近,遂至去凡人间不以寸。若乃贤者之过,能俯而就固善己,不能俯而就则其过必日甚,其过日甚则其高世必愈远,其制行必愈难,虽不合乎圣人,不犹足以矫厉风俗乎哉?”(见孔广森:《礼学卮言》卷五,清顨轩孔氏所著书本,第十四页。)孔氏此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清初之后儒学世俗化的发展态势,孔广森试图借助《儒行》以此矫正世风。。
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孔广森对《儒行》的论证,其实是基于扬汉反宋的立场,亦即只是附带性地肯定了《儒行》。他认为《儒行》并不符合圣人的中庸思想,这一观点其实仍未突破宋儒旧说,比于晚明黄道周的视野与见识是远远不如的,比之李二曲的观点亦有所不及。但李光坡与孔广森对《儒行》在认识上的突破,可以作为宋儒的质疑至晚清的推崇之间的过渡形态。
李光坡与孔广森等人的观点再进一步,就接近于晚清时期对《儒行》的肯定态度。如果说孔广森处理的是《儒行》与汉儒的关系问题,那么晚清的文廷式、廖平等人则开始着手处理《儒行》与孔门七十子及战国儒者的关系问题,亦即把《儒行》的作者推进到战国儒者,将其内容所记录的言行确定为孔门七十子。文廷式的思想可以溯源到其师陈澧,陈澧提出《儒行》对先秦时期儒风的整肃大有助益,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世风大变,诸子争鸣,百家林立,于是有了道、墨、名、法与儒的派别,“儒”是当时世人用来定义孟荀这一派的,所以陈澧其实是指出了《儒行》与战国儒者具有密切关系(15)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清光绪刻本,第10页。。值得注意的是,陈澧此说与宋儒的战国儒士所作说,其实并无二致,但是由于《儒行》在宋元明清的认识发展中,其所受到的质疑愈演愈烈,所以陈澧的观点是一种往源头逐步回溯过程中的可靠选择,——因为很难在过度质疑的学术环境中,一蹴而就地认定《儒行》就是孔子所作,——所以笔者认为陈澧对《儒行》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这是与宋儒不同的地方。
作为陈澧的弟子,文廷式的思想受到其师的影响比较明显,在《儒行》的问题上继承了其师陈澧的观点,并将其进一步明朗化。文廷式的论述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点:一、《儒行》并非孔子之言,而是战国儒者托名于孔子而作,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战国时期百家林立,其他学派攻击儒家,战国儒者以此作出回应;二、《儒行》的内容记录的是孔门七十子的行为,体现了孔子教化的广博多样性,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以孔门七十子多样化的行为,来整肃儒风,确立儒家学派的标准(16)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十三,民国三十二年刻本,第19页。。文廷式也正是据此批判宋儒见识的狭隘单一,因为宋儒只是将儒家风格归为中庸,不知孔子的教化其实是十分广博多样的。
文廷式的观点在晚清学者中很有代表性,与其几乎同时的廖平也持类似观点。廖平指出“‘哀公问曰敢问儒行’至‘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下分十六门,韩子云‘儒分为八’,此其倍数”,其说从数的角度出发,论证《儒行》十六儒正是记录“儒分为八”的孔门七十子的言行,其实是处理了《儒行》与孔门七十子的关系问题(17)廖平:《礼记识》,《廖平全集》(五),舒大刚、杨世文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54页。文廷式与廖平的观点,比于现代学者所主张的《儒行》属于漆雕氏一派,可谓更为高明,因为《儒行》的内容丰富,并不止刚毅勇猛的风格,所以其涵括的孔门言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能仅限于漆雕氏一派。持《儒行》属于漆雕氏一派的说法的代表人物有蒙文通、郭沫若等人,其说应是从文廷式、廖平等人的观点发展出来的。蒙文通相对谨慎地提出“《儒行》一篇,凡十七义,而合乎游侠之事,十有一焉,得不谓为漆雕氏之儒之所传乎?”(见蒙文通:《先秦诸子与理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4页。)蒙文通只是认为《儒行》是漆雕氏一派所传,并不是说《儒行》是漆雕氏所作,而郭沫若进一步提出:“《礼记》有《儒行》盛称儒者之刚毅特立,或许也就是这一派儒者(按:漆雕氏之儒)的典籍。”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第二卷《历史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9页。)从人物关系上看,廖平是蒙文通的老师,郭沫若与蒙文通有密切的交集,彼此之间的思想见解应该有相互的影响。。
如果说孔广森处理的是《儒行》与汉儒的关系问题,文廷式、廖平等人处理的是《儒行》与孔门七十子及战国儒者的关系问题,那么最终重新确立《儒行》经典地位的是康有为,是他解决了《儒行》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在晚清时期,康有为率先将《儒行》定为孔子的教理,并批判宋儒的见识狭隘,不识圣人思想的博大精深:
此篇是孔子为其教所定之行,如佛之有百法明门,禅之有百丈法规。考后汉人行谊,皆与之合,而程子讥为汉儒之说,此不知孔子教术之大者也。如‘儒有上不臣天子’,樊英实行之,而朱子以为行之大过矣。人性万品而以一律限之,自谓析理于秋毫,岂知圣人之理广博无量,不可以一端尽哉?(18)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姜义华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4页。
虽然文廷式也将《儒行》与孔教关联起来,但是康有为更进一步将《儒行》确定为孔子所作,视为孔教的行为规范。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所以在其教化之下,孔门弟子们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气质,因为弟子们很难全盘继承圣人的思想,所以多样化的弟子们正好体现了圣人思想的广博性。在晚清儒者看来,宋儒的见识褊狭单一,这是宋儒所自称的“纯”,而宋儒所认定的杂质在晚清儒者看来,其实都可以纳入到孔子的思想当中,因为像康有为就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甚至是无所不包的。并且,康有为还特别看重《儒行》,认为“能传孔子之学者,《戴记》《中庸》《大学》《王制》《礼运》《儒行》”,在此基础上,康有为甚至提出以《儒行》《大学》《礼运》《中庸》四篇代替宋儒的“四书”(19)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姜义华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3页。康有为的“新四书”提议,是其1910年致梁启超的信中提出的,见《康有为全集》第九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晚清民国时期《儒行》受到普遍推崇的现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有一个逐步演进的内在过程,最终才重新确立起《儒行》的经典地位。
三、时代的诉求:对儒门刚猛气节的青睐
在《儒行》的经典权威性重新确立之后,后续的《儒行》诠释还有两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在特殊时代的诉求当中,对儒门刚猛气节的推崇,这是《儒行》在晚清民国时期受到格外青睐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对《儒行》的诠释过度侧重于刚猛气节的阐发,后续儒者对此做了重订,使《儒行》的诠释回归儒门正旨。
与康有为类似,章太炎晚年也提出自己的“新四书”观,即提倡《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四篇(20)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的“新四书”中仍有《中庸》,而章太炎的“新四书”已经排除了《中庸》,这与他反对宋儒的柔退而提倡刚毅侠气具有重要关系,这一点下文会再进行展开。。章太炎还主张《大学》要与《儒行》放在一起读,理由是“若缺少刚气,即《孝经》《大学》所说完全做到,犹不足以自立。……《儒行》言人事,《大学》言修齐治平之道”(21)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再后来,熊十力也十分重视《儒行》,同样主张《大学》与《儒行》一起读,因为“《大学》《儒行》二篇皆贯穿群经,而撮其要最,详其条贯,揭其宗旨,博大宏深,盖皆以简少之文,而摄无量义也。……经旨广博,《大学》为之总括,三纲八目,范围天地,乾坤可毁,此理不易。续述《儒行》,皆人生之至正至常,不可不力践者”(22)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7页。。章氏和熊氏都看中《大学》的讲义理、《儒行》的重实践,这两篇的内容恰好形成一种互补关系,相辅相成。当然,章太炎的《儒行》观与熊十力不尽相同,章太炎的思想具有强烈的革命性,而熊十力的《儒行》观可能会更加接近儒门正旨,二者可视为后续《儒行》诠释发展的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
章太炎对《儒行》的推崇,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影响很大,乃至在整个经学史上也会具有一定意义,这也是后来陈柱与熊十力等在《儒行》诠释中格外看重章太炎观点的原因,并分别对其有针对性的讨论或批评。章太炎认为“《儒行》所说十五儒,大抵艰苦卓绝,奋厉慷慨。儒专守柔,即生许多弊病”,他所看重的其实是《儒行》特有的刚猛侠气(23)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在晚清民国时节,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许多进步思想家试图通过提倡刚毅、勇猛、进取等价值观念,改变国民的软弱麻木的奴性,这是晚清民国时期《儒行》受到普遍推崇的时代原因。例如张灏曾指出梁启超对现代国民的人格理想“已经掺杂了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权利、冒险进取、尚武、生利分利等”;再如梁漱溟甚至提出“刚之一义可以统括孔子全部哲学”,可谓惊世之语(24)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3页。。不过在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中,能够培养国民刚毅气节的方法并不仅限于儒家的《儒行》,像墨家学派也带有一股侠气,于是有孙诒让撰《墨子闲诂》欲补救国民之萎靡,但是章太炎认为墨家思想的宗教性过于浓厚,担心最终会酿成西方那样的宗教战争,所以章太炎舍《墨子》而提倡《儒行》(25)章太炎对孙诒让撰《墨子闲诂》一书有深刻的洞见,在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孙诒让的救世方案的不可靠性,他说:“近人病儒者之柔,欲以墨子之道矫之,孙仲容先生首撰《墨子闲诂》以为倡,初意欲施之于用,养成风气,补救萎靡。不意后人专注力于经上下、《经说》上下论理学上之研究,致孙氏辈一番救世之心,湮没不彰。然使墨子之说果行,尊天明鬼,使人迷信,充其极,造成宗教上之强国,一如摩哈默德之天方,则宗教之争,必难幸免。欧洲十字军之祸,行且见之东方。且近人智过往昔,天志压人,未必乐从。以故孙氏辈救世之心,固可敬佩,而揭橥号召,亦未必尽善也。窃以为与其提倡墨子,不如提倡《儒行》。《儒行》讲解明白,养成惯习,六国任侠之风、两汉高尚之行,不难见之于今。转弱为强,当可立致。即有流弊,亦不过造成几个危害不甚重大之暴人,较之宗教战争,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也。”见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27页。。
国难当头,章太炎以革命者的姿态倡导激进、狂热、壮烈的精神意志。在他提炼出《儒行》有“高隐”和“任侠”两种品质之后,便主张“高隐”不必用,而独取“任侠”之风。章太炎指出:
周濂溪、程明道开宋朝一代学风,《儒林》《道学》二传,鲜有奇节伟行之士,一遇危难,亦不能尽力抵抗,较之东汉,相去甚远。大概《儒行》一篇,无高远玄奥之语,其精神汉人均能做到。高隐一流,非所宜于今日,而任侠之风,非提倡不可也。(26)章太炎:《〈儒行〉要旨》,原载《国学商兑》一九三三年第一卷第一期,本文自《章太炎讲国学》,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章太炎对宋儒的柔退性格提出了强烈批评,因为宋儒一味地重视儒家的中庸精神,而丧失刚毅勇猛之气。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不能再空谈高远玄奥的性理,而是迫切需要奇节伟行、刚毅勇猛之士,所以章太炎认为柔退性格十分不适合于晚清民国时期,这也是他提出的“新四书”说将《中庸》这一篇经典排除在外的根本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章太炎在此对宋儒的批判,与清代李光坡、孔广森等人对宋学的批判有一定区别,晚清民国学者对《儒行》的诠释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其诠释宗旨带有鲜明且深刻的时代诉求。

至此,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在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经典诠释与现实诉求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具体而言,章太炎等人所需要的只是《儒行》的刚毅勇猛之气,但《儒行》的思想内容并不只是激进的、狂热的、壮烈的精神意志,而是总体上体现为原始儒家所重视的力行求仁的品质。也就是说,《儒行》并不是章太炎的目的,只是他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墨家思想去除所谓宗教性,章太炎同样会青睐之。所以能够断定,章太炎的目的并非以儒家思想救世。从《儒行》的诠释角度看,宋儒只看到《儒行》的勇猛刚气,晚明黄道周较为全面地看到了《儒行》求仁行仁的本质,而章太炎对《儒行》的理解其实与宋儒并无二致,其区别只是在于宋儒反对刚猛,而章太炎赞赏刚猛。因此,可以说章太炎对《儒行》的理解与体会,实际上并没有比宋儒更为深入,只是立场与态度刚好相反而已,这也是熊十力对章太炎的观点提出批评的地方。
四、重订与回归:坚守纯正的儒门要旨
如果说《儒行》在晚清民国时期受到普遍推崇,是因为其思想内容含有较为独特的刚猛之气,那么从《儒行》的诠释角度上看,过度侧重于刚猛气节的义理阐发,则很容易流于表面,甚至会导致过度诠释。笔者认为,章太炎对《儒行》的推崇与阐发就有这方面的缺陷,而熊十力即提出批评:
章炳麟谓《儒行》坚苦慷慨,大抵高隐、任侠二种。若然,则枯槁与尚气者皆能之,何足为儒?何可语于圣神参赞位育之盛?圣神者,孟子云“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细玩《儒行》,证其如是。夫百行一本于仁,自立身而推之辅世,细行不堕,大行不滞,如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及不临深,不加少,同弗与,异弗非等,此是参赞位育本领,何滞碍之有?其迹间有似于隐与侠,要不可谓《儒行》止乎此也。夫《儒行》大矣,章氏何足以知之?……近时章太炎嫉士习卑污,颇思提倡《儒行》,然只以高隐、任侠二种视之,则其窥《儒行》亦太浅矣。(28)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熊十力对章太炎的《儒行》诠释颇不以为然,因为章太炎对《儒行》只提炼出“高隐”和“任侠”两种品质,这就严重偏离了《儒行》的力行求仁之旨。仁是儒门本旨,儒者的一切行为均是本于仁、发于仁,以仁作为其背后的意志起点与行为动机,而不只是体现为表面上的“高隐”和“任侠”两种气质,所以熊十力批评章太炎对《儒行》理解太浅。笼统而言,熊氏与章氏之所以理解有差异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革命派与保守派的区别。熊十力不像章太炎那么激进,相形之下,我们可以将熊氏视为保守派。虽然熊十力提倡《儒行》的初衷与章太炎相同,都是为了救世,但是二者取法不同,熊氏较为保守,章氏十分激进,这就决定了章太炎更加关注现实社会的迫切需求,而熊十力则坚持《儒行》的完整大义,确守儒门正旨,具有较为坚定的儒家立场。其实这也体现了在面对相同时代问题时,不同思想家所选择的不同救治方法。
就《儒行》诠释的具体问题来看,后续学者的理解要比章太炎等人相对准确与保守。除了熊十力之外,刘咸炘作《〈儒行〉本义》,其中就《儒行》的刚与柔的问题专门做了辩论:
夫十七条中,语义多复,是固丁宁之态,故不可以十七种严分也。约言其义,则为刚柔二端,刚者强而有为,柔者静而有守。是二者不可以偏,偏则入于杂流而非儒。儒之为字从需,需有二义:一以人言世所需也,士为四民之首,所谓以道得民也,此篇所以反覆明之有用也;一以己言难进之义也,《易》曰“需不进也”,此篇所以反覆明儒之非干禄也。(29)刘咸炘:《〈儒行〉本义》,《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刘咸炘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刘咸炘反对将《儒行》十七条语录看作孔门的十五或十六种行为,认为十七条语录是一个完整体系,不可分割,体现了圣人思想的整体性与综合性(30)刘咸炘还进一步明确地解释说:“后之学者,不睹圣人之全,亦鲜不窃窃以此为怪也。知毁之之说,而后知孔子之所以为言矣。……孔子之行即儒行也,哀公岂不知之?而有是问者,盖闻毁儒之言而不能无惑也。故孔子举十七义以明之,非儒有十七种也,反复交互以完其义耳。”(见刘咸炘:《〈儒行〉本义》,《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7页。)。这一观点可以当成是对晚清时期文廷式、廖平等人的回应与纠正,其潜在的意思即是将《儒行》视为孔子之言。第二层含义就是专为刚柔问题而发,可以当成是对章太炎等人的回应与纠正。刘咸炘主张《儒行》是刚柔并济的,不宜偏于章太炎的“刚”,也不可偏于宋儒的“柔”,刚柔并济的主张其实反而更能准确地展现儒家的中庸思想。所以刘咸炘没有像章太炎那样放弃《中庸》,他重新将《中庸》视为儒门宗旨,提出“儒者之道,莫备于《中庸》”,其实这就是刚柔兼顾的体现。
当然,熊十力、刘咸炘等人并不只是在学术层面探讨《儒行》的义理思想,他们同样紧紧结合着时代中的现实问题。熊十力提倡《儒行》的动机也是为了救治晚清民国时期的国民性,他一方面就《儒行》文本的历史问题,对宋儒的性格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又针对现实中的世风问题,指出“吾国民元以来,党人如敦《儒行》,则不至以私欲比党而祸国。行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友道固然。今之党人犹当循斯纪。民国以来,党祸至烈,使《儒行》修明,当不至此”(31)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熊十力对宋代风气的批判比较独特,他说:“宋承五季衰乱,天下无生人之气,太宗思提倡《儒行》,诚有所感而然。但学风之激厉,端赖在野大儒以身作则,君主以虚文相奖,收效有限。而北宋诸老先生,竟未有表章《儒行》者,程伊川且甚排斥之,《遗书》卷十七云:‘《儒行》之篇全无义理,如后世游说之士所谓夸大之说,观孔子平日语言,有如是者否?’伊川为宋学宗师,其斥《儒行》如此,宜乎?理学末流,貌为中庸,而志行畏葸,识见浅近,且陷于乡愿,而不自觉其恶也。今世衰俗弊,有过五季,贪污、淫靡、庸暗、污贱、浮诳、险猜、毫无人纪,吾为此惧,爰述《儒行》。”熊十力注意到了宋代之前的五代问题,认为宋代理学末流所导致的世风之弊,有其内在的历史原因,这一洞见在《儒行》的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突破性。。应该看到,在经典诠释史上,为《儒行》做过辩护的学者基本都注意到了宋儒的问题,这是《儒行》诠释所绕不开的学术性质疑,但他们同时也都试图借重《儒行》以救世。从熊十力的观点来看,他甚至注意到了友道与结党的问题。以此为例,《儒行》主张仁义忠信高于世俗政治,“党人”如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即便身处政治当中,同样怀抱有一颗超越世俗政治之心,亦即在政治党争之上犹有一个更高的仁义忠信所在。这其实也是黄道周在《儒行集传》中所着重阐论并且要向崇祯皇帝表明心志的,因为友道与结党的问题恰好与晚明时期的君臣关系、黄道周自身的政治经历息息相关,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色彩与现实指向。所以如果说章太炎的革命者姿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不尽相符,那么熊十力对《儒行》的提倡则相对接近晚明黄道周,更加契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关切。
更为吊诡的是,熊十力提倡《儒行》的一个重要动机,也是来自晚明时代的问题。晚明黄道周重视《儒行》力行求仁的品质,有一大原因是出于反思与救治阳明后学的流弊,因而倡导力行实行的实学精神,这几乎是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家们的共同呼声。但是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演变为后来的乾嘉朴学,已养成笃实的学风,到了熊十力却还在批评三百年前的阳明后学狂禅的流弊(32)熊十力指出:“两宋理学,大抵不脱迂谨,末流遂入乡愿。近人诋程、朱诸师为乡愿,此无忌惮之谈。但理学末流诚不佳,明儒变宋,则阳明子雄才伟行,独开一代之风。然末流不免为狂禅,或气矜之雄,卒以误国。阳明教人,忽略学问与知识,其弊宜至此也。《儒行》首重夙夜强学以待问,又曰博学不穷,曰博学知服,阳明却不甚注意及此,故不能无流弊。宋明诸儒本无晚周儒者气象,宜其不解《儒行》也。”见熊十力:《读经示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因而有研究者称“熊氏为后人称述的性格,正与四库馆臣所言黄道周‘负气敢言’的性格遥相唱和”,其实可以更进一步地说,熊十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晚明黄道周对《儒行》的诠释。应该说,熊十力等人对《儒行》的诠释更加切合儒门正旨,是对晚清民国时期偏重刚猛气质的一种反拨。

此外,还有唐文治的弟子陈柱也效仿黄道周《儒行集传》作《儒行集解》,其自序云:“黄石斋先生《儒行传》历举古之贤士,最足廉顽立儒,唯所引过于繁,转令学者未易卒读,故今特约之。嗟乎!今之学者能以是为式,则贪鄙无耻之风可除,而民族之复兴其庶几可望乎。”(35)陈柱:《儒行集解》,《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4期。陈柱《儒行集解》的内容主要是集郑玄注、黄道周传及其师唐文治的解释,其中尤以取用黄道周《儒行集传》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唐文治与陈柱师徒均意识到《儒行》具有救治人心之大用。晚清民国之际,现代性对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构成极大冲击,人心逐于权力与器物,丧失了对人伦与政治的更高价值追求,而《儒行》中所蕴含的仁义忠信的价值理念得到挖掘。而如此对《儒行》之义理思想的理解与把握,则是那些只执其刚毅之气的观点所远不及的。可见,后续这一批学者相对于激进的章太炎等人而言,会更加看重《儒行》经典的本旨,将《儒行》的诠释拉回儒家思想的正轨,表现为一种保守传统的态势。
综上所述,在重新确立《儒行》的经典地位之后,晚清民国学者由于特定时代的迫切需要,极力地推崇《儒行》的刚猛气节,但一定程度上因过度侧重而有失原旨;后续的《儒行》诠释者则对此进行批评与纠正,试图将《儒行》的诠释拉回纯正的儒家思想当中,体现了坚守儒门正旨的保守性。总之,晚清民国时期对《儒行》的推崇,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包含着近现代以来儒者对“儒”的自我认知,以及这一批儒者在面对时代问题时所提出的不同救世主张。即便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晚清民国时期的时代问题并未获得完满解决,《儒行》对于救治世弊人心的巨大功用,或许可以继续不断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