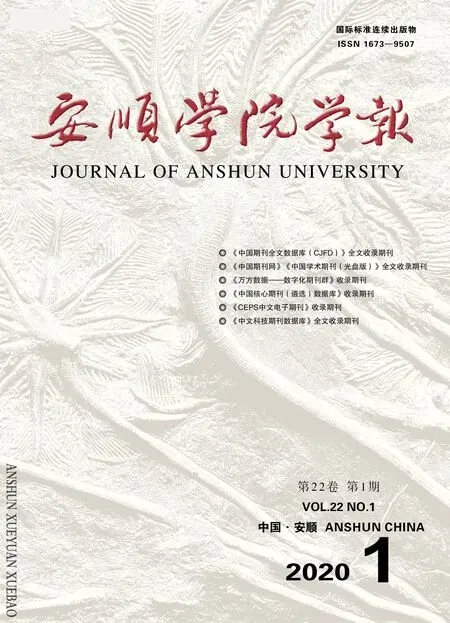屯堡村社教育的基本内涵及社会特征
——基于普定县号营村“农村社区教育体系”的考察
2020-12-27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安顺学院旅游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一、乡村学校教育的制度性缺陷
在近代,洋务派孜孜以求通过“考求洋务”来实现富民和强国之目的,但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这一理念才得以广泛实践并延伸到村落社会。其主要表征是清朝政府颁布法令,要求地方社会兴办新式学校教育。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王朝国家体制消亡,与之同步消亡的还有“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体制。从而,在村落社会中发展新式学校教育的合法性制度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在为底层民众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也为村落社会的自主治理培育人才。在后续的实践过程中,乡村学校教育的目的不断变化。随着国家介入程度的逐步加深,乡村学校教育已发展成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平台。在当前工业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学校教育已逐渐成为为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加快现代化步伐培育人才的重要平台。
乡村学校教育,作为一种以村落社会为基本依托的教育形态,为村落发展和村庄治理培育人才是其应有的基本内涵。但是从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已从最初的“甜蜜恩爱”演变为当前的“渐行渐远”。此种变迁轨迹,彰显出国家对乡村学校教育的定位囿于时代背景的社会特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通过制定不同的乡村学校教育制度来实现其治理社会的基本诉求。鉴于本文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为村落发展和村庄治理服务而撰写的基本定位,因而此处所论述的乡村学校教育的制度性缺陷,基本建立在当前我国乡村学校教育的实践之上。
(一)“强国家、弱社会”特征显著
现代乡村学校教育自进入中国之后一百多年的实践过程,始终彰显出显著的“强国家、弱社会”特征。清朝末年,洋务派成员希冀以推行新学教育为切入点,试图于社会狂澜中挽救清末乱局。此种意义上的乡村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国家自我觉醒的产物”[1]。辛亥革命之后,“当权者重视借助教育的力量来维护其统治,教育投入有所增加,教育体制日臻完善,国民政府竭力加强对教育的控制,把教育作为‘以党治国’和‘三民主义治国’的工具,以达到维护其一党专制统治的目的。”[2]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在国家主义的导向下,乡村教育发展成为国家政治意志贯彻落实的战略内容。”[3]自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的轨道后,“乡村教育受到经济主导的国家主义逻辑驱使,发展主义成为教育发展的政策核心信仰。”[4]“从1993年开始,在推进‘两基’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这个国家首次实施的大型教育工程中,大力推进中小学布局调整,减少校数,扩大规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实现布局合理、结构优化……”[5]。有研究者发现,乡村学校布局上移的趋势还在继续,其“如同一座飞岛悬浮在乡村社区之外”[6]。
从上述内容中发现,座落于村落社会中的乡村学校教育,其“强国家、弱社会”特征主要表征为:作为“国家”代言人的社会精英,始终在乡村学校教育场域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他们主导乡村学校教育的制度设计和发展轨迹,而“村落社会”与“平民”,则一直被动接受来自他们安排和设计的教育内容。对于这种情况,从1919年开始,就有学者①站在“村落社会”和“平民”的立场,指出乡村学校教育的不足和缺陷,并为其开出诸多“药方”,如提出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改善乡村办学条件、改革教育内容(编写校本教材、教学内容中融入地方性知识)等。即使如此,乡村学校教育场域中“国家”与“村落社会”、“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没有化约,相反,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乡村学校教育呈现出“内卷化”的发展趋势。
(二)乡村学校教育的内容单一
在现代学校教育出现之前,私塾承担着为村落社会传承文化的基本职能。“私塾是由民间个体创办的承担基本文化传承的一种教育机构,它诞生于乡土社会中社会组织的需要,是一种具有本土文化适应性的教育组织形式,并且历史悠久。”[7]私塾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其在传递基本儒家文化知识外,还将乡规民约、民俗礼仪、生存智慧和生计实践等融入到教学内容中。私塾教育提供的这些教学内容,是村落社会中的民众及其祖先在与自然环境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并借助日常生活的传递和传播平台赋予其显著的地方性。因而,那些接受私塾教育的村民,即使未能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他们既不会在社会意义上与村落中的乡规民约、民俗礼仪产生隔阂和断裂,也不会在生理意义上与村落中的生存智慧、生计实践出现不适和障碍。
而当前广泛盛行的在洋学(或官学、学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学校教育,不仅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且主要是为工业社会服务的。首先,“工业社会‘要求劳动分工要有流动性,陌生人之间要持续、经常和直接地进行交流,共享一种标准的习惯用语和必要时用书面形式传递的精确意思’”[8]。其次,工业社会的基本逻辑是线性发展。存在于这两方面社会背景下的乡村学校教育,其教学内容的设计和安排自然是以满足工业社会需要为基本原则的。因为它从本质上要求原先生活于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只有接受现代学校教育之后,才能进入到工业社会中,并按照其基本规则和节奏生活于其中。对“榜上有名”者来说,当他们与工业社会/城市产生紧密的关联之后,相应地也就远离了农业社会/农村。但内蕴于现代学校教育中的淘汰性选拔制度,必然会“制造”出一批“榜上无名”者。对他们而言,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接受的知识和技能,不仅未能成为他们在工业社会/城市中谋取一席生存空间的垫脚石,反而可能会成为重新返回农业社会/农村的壁垒。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乡村学校教育对农业社会/农村的负外部性效应非常显著。
相关研究指出,产生于两种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乡村学校教育,是一种冲突与竞争的关系。[9]在他们较长时期的拉锯中,主要由村落社会提供的具有显著农业社会属性的私塾教育,虽然将“弱者的武器”之功效发挥到极致,仍敌不过国家治理框架中的教育行政手段,不仅严重挤压私塾教育存续的社会空间,而且在乡村学校教育的内容安排上逐渐偏离村落社会的实际需求轨道。
(三)国家教育制度设计理念与实践过程的偏离
自新式学校教育进入我国以来,其制度设计一直秉持“上下一致”“城乡一体”的基本理念。试图在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内容安排、教学方式等方面实现城乡之间无差别对待的诉求。但是在进入到现代社会时,随着工业化建设不断推进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之间的发展堕距不断增大,学术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城乡二元体制。此种体制之于乡村学校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农村劳动力资源大量吸入城市中。“推拉理论”彰显出,城乡之间在就业机会、经济收益方面的等级差异,导致农村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会主动进入城市。即便如此,但由于对知识、技能掌握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明显逊色于城市民众。再加上制度性排斥和教育成本的增加,导致他们的儿女只能在乡村中接受学校教育。第二,教育资源、教育机会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配置。实践过程中的这两方面表现,一方面由于人群的大量流出,导致以村落社会为主要依托的乡村教育失去人文氛围和精神支持,如村落社会与乡村学校空间隔离、“留守儿童”厌学情绪高涨等;另一方面,即使国家在制度层面为乡村学校教育设计相应内容,但由于这种安排是建立在城乡一体基础之上的,从而使得乡村学校中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适应增强。换句话说,能满足城市学生需求的学校教育制度设计,未必是乡村学生所需要的。同样,相对城市学生而言,乡村学生更需要优质教育资源和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但囿于城乡二元体制,乡村学生的诉求不仅未能实现,更导致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异。国家教育制度设计理念与实践过程的偏离现象,实质上是整个社会在城乡一体化的幌子下,人为地在城乡之间制造出的教育鸿沟。
二、号营村的时空背景
就当前的行政区划来看,号营村隶属普定县马官镇,东接下坝村、中坝村,西界六谷,南连马堡,北抵贾官村,与山脚村、荷包村接壤。其地理位置(东经105°40′,北纬26°13′)总体位于贵州省中部,东距省会贵阳市90多公里,距安顺市22公里、普定县城10公里、距马官镇政府所在地仅1公里。 相关研究发现,号营村是典型的屯堡村庄,“既处于交通线上,又属于‘西门屯堡’范畴。”[10]对号营村社会属性的此种学术意义上的概略性论述,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号营村提供了如下三条路径。
首先,乡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孙兆霞等人在《屯堡乡民社会》中提出乡村精英、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三种内源性资源是屯堡文化在长时段“变”与“不变”之间自主选择的社会基底。“乡村精英在村庄生活中发挥主导、引领作用;民间组织承担起村庄内部事务的操作和协调;社会舆论对村庄事务起监督和评判的作用。”[11]质言之,由乡村精英、民间组织和社会舆论共同构建出的村庄公共空间和自组织机制是号营村最基本的社会内涵。
其次,“交通线”的地域分工。“交通线屯堡村寨的区位,使其在屯堡族群生产分工中主要承担贸易和副业生产的功能。”[12]号营村所处的屯堡区域,地势相对平坦、稻田面积相对可观是其主要特征。“据统计,在1981年田土包产到户时,号营村耕地总面积1118亩,按照当时村庄仅500人左右的人口规模计算,人均耕地2亩多。虽然后来村庄人口不断增加,但仍超出中国大多数村庄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截至2015年,全村在村人口1967人,人均耕地为0.57亩。”[13]但囿于喀斯特地貌和“地表水贵如油,地下水滚滚流”的水文景观,导致其以农业耕作为主要内涵的生计之途遭遇到一定的困境,尤其是稻田式生计景观的遭遇更为明显。
最后,“西门屯堡”的文化底蕴。“西门屯堡”本是以地理方位为区域划分标准的结果,但是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看,号营村的村民数量的确不多,但却是由四十多个姓氏的村民共同构成。这些因不同原因、通过不同途径在不同时段来到号营村的民众,在生计资源相对紧张的社会空间中长期和谐共处,不仅彰显出号营村的平权结构,赋予号营村底蕴深厚的民俗文化;而且表征出与“东门屯堡”的结构性差异。
三、屯堡村社教育的基本内涵
号营村作为典型的屯堡村庄,既具有乡民社会的共性特征,也有显著的个性特征。具有此种社会属性的号营村,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建构并延续至今的教育形态,被学术界称为屯堡村社教育②。
(一)屯堡村社教育是一种“农村社区教育体系”
乡村教育或乡村学校教育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点,著作数量不胜枚举,但切入点和现实关怀各有不同。村社教育是一种与乡村教育或乡村学校教育有显著差异的教育形态,当前学术界较少涉及。在《屯堡村社教育》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是一种由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构成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
鉴于村社教育的构成要素是基于号营村“教育立村”的长时段实践而概括和提炼的事实。为此,本文关于村社教育各构成要素的内涵分析和论述,都秉承“立足于号营村,但又不完全局限于号营村”的原则。
生计教育,即是指以主要生计方式为依托,将村民与土地、市场关系变化而促使生计渠道拓展、生计能力提升以及覆盖人群扩大的过程。通过田野调查得知,蔬菜种植、小建筑包工和经商贸易是号营村村民的三种主要生计方式。就号营村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三种生计方式与教育的勾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造就有根生计。号营村村民生计方式的最显著特征,即是以区域内民众的实际需求为切入点,通过村落文化规约而成的技能传递机制,在与外部互动过程中实现既增加经济收入又提升生计能力的目的。其次,为号营村的学校教育提供经济基础和精神支持。号营村有根生计在回应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农民能力建设被忽视等问题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村庄“空心化”、家庭“空巢化”问题对村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此看来,由于生计方式的“有根性”特征,使得号营村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谋取到足够多的生计资源,在为其子女接受学校教育提供足额资金的同时,还能给予其足够的情感慰藉,更为关键的是可以参与或配合在村落内部实施的有关学校教育的活动等。最后,为学校教育中的失意者提供情感归属和谋生之道。
号营村的礼制教育,主要借助村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牌坊、家谱以及公共活动等,在将国家礼制传递到村落社会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将其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从而建构新的礼制规范。这种礼制传递和建构的过程,其教育内涵主要在两个层面得以彰显:第一,在再生产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实现规范全体村民行为举止的目的。如牌坊设立的程序规范与旌表功能、家谱扬善隐恶的功能以及公共活动的精神群像的引导作用等。“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乡村治理过程,这是村落社区运用国家礼制规范来实现礼制教育和乡村秩序再生产的基本机制。”[14]第二,消弭科层制乡村学校教育的诉求与乡村社会生产生活之间的隔阂。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语境中展开,且作为现代科层制教育体系中重要一环的乡村学校教育,其制度设计、教材制定和内容安排,皆是以适应现代城市社会中的生产、生活为基本诉求,而与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隔阂。号营村的学校教育布局在礼制规范与情感温度的村落社会中,可在一定程度上消弭这种隔阂。
号营村的习俗教育,指盛行于村落社会中的民间风俗习惯在人的精神成长中扮演“襁褓”角色的过程。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积淀和传承而成,是这种民间风俗习惯的显著特征。它之于教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为村民个体与村落社会的情感牵连提供社会基底。第二,为乡村学校教育提供活态传承的文化资源。号营村在建构“农村社区教育体系”过程中,诸多因升学、工作、经商等因素已离开村庄多年的民众,仍竭力从物质和精神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研究发现,这与他们自小受号营村浓郁的民间风俗习惯熏陶有关。中国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在离乡42年之后,仍对家乡的风俗习惯记忆颇深,并且坚定地认为自己后来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喜好与之紧密相关。“我儿时看这‘地戏’,不但获得了一些历史知识,而且深受它的爱国主义精神感染。我后来很爱看京剧《李陵碑》,至今仍喜欢听余叔岩所唱杨老令公黄昏时分依营门等他的送信搬兵求救的儿子七郎归来的那一段唱腔,……。这是同我儿时在号营看‘地戏’分不开的。回想当年乡亲父老们演出这‘地戏’,也确有一种威武雄壮的阳刚之气,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5]正是基于号营村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精神记忆”,从而使得刘纲纪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积极支持家乡的学校教育。在号营村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了解到,号营村外出的普通民众皆是如此,不仅在情感上与号营村难舍难分,而且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支持号营村的建设,在号营村的学校教育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号营村的学校教育是指以乡村学校为载体,但与村落社会紧密关联的教育形态。就号营村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乡村学校”在不同历史时段中有不同的表征形式,即1949年前的家庭私塾和1949年后的乡村学校。无论是哪一种形态,都与国家紧密相关。其次,村落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关联则表现为:1949年以前,私塾完全由号营村内的民众建立并主导;1949年以后,地方政府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下,不仅将学校建立在村落社会内,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允许村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学校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及教学过程中的监督和协调等方面工作。如20世纪80年代村民集资建校。
总而言之,号营村学校教育的实践过程,不仅有国家教育体制的宏观调控,也有村落社会的强力参与。国家教育体制之于号营村学校教育的意义和影响,有目共睹,此处不赘述。而号营村落社会之于其学校教育的意义和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适时地在经济、物质方面给予支持;第二,通过谐调学校教师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在村落社会中培育重视教育的氛围;第三,在物质、精神方面给予优秀学生以奖励,不仅有助于营造积极向学的氛围,而且有助于学生家乡情怀的养成。如果将国家教育体制中的升学率视为制度性产出的话,那么村落社会在参与过程中造就的产出则属于非制度性产出,它主要表现为村民的个人成长、家乡情怀的养成以及村落教育景观的型塑等方面。通过田野调查得知,号营村的学校教育在制度性产出和非制度性产出两方面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二)屯堡村社教育的各组成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整体地看,构成号营村“农村社区教育体系”的四方面要素,就其在工业化背景下之于村落社会的意义和影响而言,具有同等重要的结构性地位,缺一不可。
生计教育回应的是当前农村产业结构的问题。即此种教育形态,通过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多样化村民的谋生渠道,并且在此过程中提升其谋生技能,使得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谋取到足够多的生计资源,从而缓解村庄“空心化”、家庭“空巢化”程度。
礼制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乡村治理过程,这是村落社会运用国家礼制规范来实现礼制教育与乡村秩序再生产的基本机制。它很明显地回应了农村社区与传统文化断裂、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强国家、弱社会”等问题。
习俗教育是一种培育、传承民间风俗习惯的过程,这是村落社会在着力培育习俗教育资源的同时,大力提倡民俗文化结构性活态传承的自组织机制。既回应了当前工业化背景下农村社区与传统文化断裂的问题,又可以借此培育村民对村落社会的文化记忆和情感依恋,还可以使村落社会获取经济利益或社会声誉。
学校教育表征的是村庄与国家、乡村和城市、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号营村学校教育的制度性产出和非制度性产出,“彰显出号营村不希望将号营小学办成一座专门培养小学毕业生的工厂,或者说是不希望将其办成一个为城市培养人才的基地,而更多的是希望将其办成有助于号营村未来长远发展的文化中心。”[16]号营村学校教育的实践过程和产出,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管理部分对撤并乡村学校这一举动进行反思,而且有助于整个社会思考学校教育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之于农民的正向价值和意义。
上述以号营村“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为基础论述的各种教育形态之于村落社会的积极意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各种教育的最终产出。当我们将这种产出置入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教育体制中时,发现尚未有社会公认的指标体系对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的实践过程和最终产出进行测量。即使是学校教育,虽然制度性产出可以通过“升学率”这一指标来测量,但非制度性产出同样无法测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的产出都属于非制度性产出。但是在号营村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数据和资料彰显出,这三种教育形态的产出对其学校教育的制度性产出和非制度性产出均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并且学校教育的产出又为另外三种教育也同样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质言之,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教育体制中,屯堡村社教育的各组成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即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的产出是通过学校教育的制度性产出来彰显的,同时这种制度性产出又为生计教育、礼制教育、习俗教育的构建与延续提供物化平台和精神源泉。
四、屯堡村社教育的社会特征
产生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对立,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既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也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中蹒跚前行的乡村学校教育,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只是暂时的,一方面,它将随着社会体制的不断健全而逐渐消弭;另一方面,它将随着村落社会的主体性、能动性不断增强而逐渐化约。鉴于本文着意彰显村落社会与乡村学校教育相互成就的基本定位,因而,此处将着重从村落社会主体性、能动性的角度论述屯堡村社教育的社会特征。
(一)主体能动性凸显
以社区教育体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村社教育,不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更是研究的切入点和载体。此项研究的初衷并非是要从面上将其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性收获进行复制性推广,而是要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观照下,深入认识和理解号营村的结构性特征和内生性资源。
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无论是民国时期以侯氏家族为主举办的私塾教育,还是20世纪80年代由村支两委主导的集资办学举动,都彰显出类同的发展路径。即都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段中,村落社会在乡村学校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号营村之所以能在特殊的历史时段中,不仅参与到乡村学校教育实践过程中,而且在参与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其村落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及蕴于其中的内生性资源紧密相关。
首先,号营村存在一种以“人的社会本性”为主要内涵的结构性特征。就号营村的实际情况而言,这种“人的社会本性”不仅表现为村民普遍性的认识到教育之于村民个人和村落整体的积极意义,而且表现为村民乐于在某一人群或组织的带领下参与到有助于教育的行动过程中。其次,乡民社会中的内生性资源促使村民愿意参与到此种行动中。乡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分别为:村庄公共空间和自组织机制。简单地说,这两方面基本内涵其实就是蕴藏在其社会深处的内生性资源。正是因为上述两方面因素,不仅造就了号营村以侯氏家族、村支两委为代表的村落社会共同助力乡村教育的社会景观,而且提高了号营村在长期主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从制度层面成功争取更多教育资源、教育机会的可能性。更为关键的是,将这种从制度层面向国家争取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无意识举动化约到其“人的社会本性”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说,号营村中的“人的社会本性”,其实就是一种积极参与乡村教育的主体能动性。而乡民社会的属性特征赋予其公共空间和自组织机制,则是促生、彰显号营村村民主体能动性的文化资源。总而言之,蕴藏在屯堡村落社会中的主体能动性是村社教育建构并得以延续的主要载体。
(二)多元化的教育内容
以“农村社区教育体系”为基本内涵的屯堡村社教育,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国家教育制度统筹安排的乡村学校教育;其二,村落社会自主组织实施的非学校教育,主要包括生计教育、礼制教育和习俗教育三种类型。乡村学校教育的内容构成,旨在为乡村学生日后在城乡二元框架下顺利参与到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提供各种技能性知识。从当前教育制度的基本内涵来看,在此种教育内容支配下的乡村学校教育,其教育产出主要通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城市化、工业化的实际需求而组织的选拔性考试来衡量。既然是选拔性考试,肯定就有“榜上有名”者与“榜上无名”者之分。同一场考试,导致两种不同的人生。成功学意义上的人生评价,不属本文的论述范畴。本文意在论述这两种人群在经历过选拔性考试之后与村落社会的关系问题。
就“榜上有名”者而言,他们作为选拔性考试中的“胜出者”,自然就此在身体意义上离开村落社会,即不再占用村落社会的生存空间和生计资源。但是他们在精神方面与村落社会仍紧密相连。通过在号营村的田野调查得知,发生在村落社会中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或公益性文化活动、公共性社会活动等,他们仍然会积极参与其中。村落社会中的风俗习惯和礼制规范是促使他们参与其中的深层文化资源。而他们对于这些风俗习惯和礼制规范的习得、掌握,主要来自于由村落社会自主组织实施的礼制教育和习俗教育。
而那些“榜上无名”者,即便作为选拔性考试中的被“淘汰者”,但他们所依存的村落社会并未抛弃他们。一方面,享受与“榜上有名”者同等的待遇,即村落社会为他们提供同样的礼制教育和习俗教育;另一方面,还额外为他们增加生计教育。经受过这三种教育的洗礼之后,这些“榜上无名”者,不仅能在精神方面顺利融入到村落社会中,严格按照村落社会的应有内涵铺陈自身的生活。而且能在经济方面探寻出一条在地化兼业型生计之路,即有根生计。
正是由于屯堡村社教育所提供的多元化教育内容,使得生活其中的民众,不仅能在乡村学校教育资源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在城乡二元对立框架中顺利通过选拔性考试融入到城市化、工业化体系之中,而且仍能在精神方面找寻到回得去的故乡。即便是那些未能通过选拔性考试的“榜上无名”者,也能在生计教育的支撑下做到“脚下有路”。这两类人群,“不管他们在后续的人生道路上取得的成就如何,他们始终都应该具有一种对村庄有感情、对职业有操守的超越个人、家庭利益的人文精神。”[17]从这个角度来看,促使人社会化成长是村社教育的基本目标。
注 释:
①余家菊是中国较早关注乡村教育问题的学者,他于1919年在《中华教育界》刊物上发表《乡村教育危机论》一文,论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中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严格来说,村落社会中并无教育。由此之后,中国社会中关于乡村教育的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逐渐增多。无论是哪一方面,都秉承一个基本原则:为村落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且更能满足(或符合)村落民众生产、生活需求的教育资源。其实现途径主要有二:第一,呼吁国家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其二,倡议从事文化运动或嗜爱平民精神者主动为村落社会提供教育。
②屯堡村社教育,作为学术概念,首见于陈斌、张定贵、吕燕平等人所撰的《屯堡村社教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出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