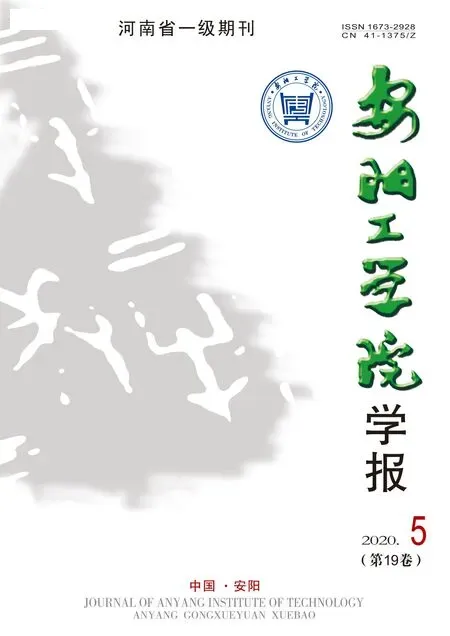网络空间秩序混乱型寻衅滋事罪能否成立
2020-12-26刘子良
刘子良
(郑州大学法学院,郑州450000)
我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八亿多人,接入方式以移动互联为主。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时代,出现了许多基于互联网的新型违法犯罪方式。本文认为,根据犯罪对象和犯罪手段的不同可以将网络犯罪行为分为以下三种:①以互联网信息系统为犯罪对象的行为,如《刑法》第286条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②以互联网为犯罪手段或载体的行为,如刑法第287条规定的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其他犯罪行为;③以网络空间秩序的混乱为要件的行为,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信息解释》)中规定的犯罪行为。当前理论界对前两种类型的网络信息犯罪并无较大争议,理论观点趋于一致。但对2013年“两高”《信息解释》第5条第2款“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示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的规定,在理论界引起较大争议。学界对网络空间公共场所的定义和公共秩序的概念莫衷一是,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本文将针对网络空间秩序混乱型寻衅滋事罪提出个人观点。
一、将网络空间定义为公共场所是否妥当
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处罚范围的合理性和国民具有预测的可能性,条文概念的不明确将会导致处罚范围的不明确,使国民无法预测条文的处罚界限,无法指引自身的行为,规避风险。如刑法第293条将寻衅滋事罪分为四种情形,前两项是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第三项是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行为,第四项则是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有学者认为,从四种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属性来看,前三项的侵犯对象均为具体法益、个人法益,第四项侵犯的则是抽象法益、社会法益,缺乏可操作性,应当废止该罪名[1]。本文也认为,将刑法保护的法益概括为抽象性和社会性并不妥当,这既无利于法益的保护,又违反了法条明确性原则,甚至会导致不具有可罚性的行为沦为处罚对象,使得刑法成为“恶法”。法益有着清晰明确的内涵与外延,条文处罚范围有着明确的界限,所以如果将第四项所保护的法益定义为保护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在公共场所自由出入、自由活动的个人法益则应是妥当的。
那么将网络空间定义为公共场所是否妥当呢?学界对此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①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从字面意思来看,公共场所是给社会公众提供社会活动的不特定场所的总和,是不特定人出入进行社会活动的空间,将剧院与网络空间同等看待并无差异。以淫秽物品为例,刑法第367条仅将其列为书刊、影片、录像录音带以及图片等其他类型,那么电子文档、手机短信也可视为淫秽物品[2],况且虚拟与现实只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或存在形态,并不改变物质的性质,加之法律具有滞后性和有限性,无法要求条文语言完全概括出所有行为方式。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将信息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便是合理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亦有学者认为将网络空间定义为公共场所并没有超出公共场所的“定义范围”,况且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保护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将网络空间定义为公共场所,完全符合保护公共秩序的立法目的,并没有超出国民预测的可能性,符合一般人的理性认知,其潜在的意蕴在于对“公共场所”的探索性解释,是传统刑法和罪名体系在网络空间适用的延伸。②持否定说的学者则主要从解释方法出发得出结论。持类推解释观点的学者认为将“网络空间”归类为“公共场所”属于类推解释,使得法益的内涵范围超出原有范围,有违法理[4]。持体系解释观点的学者认为从刑法条文体系出发,网络空间所涉及的公共秩序无法与刑法条文所规定的公共场所秩序相契合,使得寻衅滋事罪的刑罚规制范围远远超出了刑法第六章第一节的“扰乱公共秩序罪”[5],并且与两高之前所颁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条文与理念不相符[6]。
本文赞同否定说观点,认为肯定说的结论还存在着某种致命缺陷。首先,若以肯定说来看,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亦可构成危险驾驶罪,因为将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与将电动自行车解释为机动车如出一辙。毫无疑问,这属于类推解释。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三要素法”是:①多数人明显能够看出;②多数人需努力才能看出;③多数人明显无法看出。当两个概念满足①②时,即为扩大解释;若满足③时,则为类推解释[7]。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一般人角度为出发点来区分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办法是伪命题。其次,目的解释要求解释刑法条文时应立足于条文设立的目的和法条保护的对象。但以目的解释作为其进行扩大解释乃至类推解释的幌子是不恰当的。
在本文看来,所谓立于一般人的角度其实均是立于解释者的个人角度,其实质也是一种“主观解释”。立法法对法律的制定过程有着明确的程序规定,但对于司法解释则并无具体的程序予以规制,司法解释在颁布实施前“两高”并不会向广大人民群众征集意见,那么其所谓的“一般人立场”便是伪命题。避免类推解释的最佳方法便是采取体系解释,在法律体系内找寻解释的依据,要比追逐时代精神、保护目的和一般人立场等更具有权威性。所有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特定的价值观念和立法目的为目的,在相关法条中找寻立法者的价值立场和立法目的,比采用其他途径更安全,有较高的国民可预测性。再者立法者追求法条的整体实践,适用了某一法律规范便是适用了整个法律体系。立足于刑法体系,并无法将信息网络空间解释为公共场所。首先,“两高”于2013年7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将公共场所的范围解释为车站、商场、码头、展览会、机场、运动场、医院、公园等场所,这便意味着公共场所仅是现实场所。其次,《刑法》第291条之一的第一款是编造虚假信息在现实社会传播,第二款是编造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传播,立法者将两者做了明确的区分,并没有将二者视为一体。那么这便意味着基于保护目的和时代发展的目的解释和扩大解释是无法成立的。由此来看对于公共场所采用形式解释比实质解释更为妥当。
二、公共秩序与公共场所秩序是否等同
《信息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寻衅滋事罪第四款论处,而《刑法》第293条第四款规定的是“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尽管公共秩序与公共场所秩序仅字面上的“毫厘之差”,但在实质意义上却“失之千里”。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的关系,理论界尽管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普遍认为“公共秩序”是抽象的一级概念,是一种社会状态,或是一种社会公德、习俗风尚,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赖以生存的社会状态;而“公共场所秩序”则是具体的二级概念,指人们可以在车站、商场、机场、电影院等场所自由出入来往,遵守场所秩序,维护自身、他人和场所的合法利益,如《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所规定的几种情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仅限于公共场所秩序混乱是不恰当的,应该将道德秩序包括在公共秩序之内[8]。笔者认为,公共场所秩序属于公共秩序的范畴,但绝不能把道德秩序纳入公共场所秩序的保护范畴。
首先,公共秩序显然是公共场所秩序的上位概念,如《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为“扰乱公共秩序罪”,其中所保护的秩序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保护广义的“国家管理秩序”,如现实生活的妨害公务罪和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以及信息网络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第二类保护“经济秩序”如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罪;第三类保护“公共场所秩序”,如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第四类保护“道德秩序”,如聚众淫乱罪和侮辱尸体罪。不仅如此,该节还包括了其他在社会生活中所能遇到的具体内容。显而易见,公共秩序不仅包括公共场所秩序,还包括居民赖以生活的其他社会利益,因此将《信息解释》的公共场所秩序上升至公共秩序,显然有扩大刑罚处罚范围之嫌。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认为处罚信息网络的造谣传谣和起哄闹事行为是妥当的,但公共秩序与公共场所秩序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退一步来说,若我们将网络空间视为公共场所,那么网络空间与公共秩序仍然是不对等的两种概念。本文认为,按照此种解释思路来看,其无疑扩大了法条的字面含义,超出了国民预测的可能性,严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其次,持支持观点的一些学者将两者解释为一种概念,那么试问:这种解释结论公平吗?不以刑法体系、条文相关性和内心的公平正义为指导,即使偶尔得出合理的结论,那也仅是巧合罢了[9]。在解释《刑法》条文时,不仅要依据法条的立法目的,也要注重法条与法条之间的衔接性和协调性,更要立足于罪刑法定原则。那么既然《刑法》第293条第四款已经对刑法第六章第一节进行了限制,《信息解释》作为下阶的司法解释便不能将网络空间的传谣造谣和起哄闹事行为的后果定义为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否则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律适用的范围,有法律拟制之嫌。也有学者认为尽管在网络空间起哄闹事没有造成网络空间“公共场所秩序混乱”,但“破坏了社会秩序”,这是在第四款范围内的类比推理,显然符合寻衅滋事罪第四款的规定。然而这是更明显的类推解释。
三、何种秩序的混乱
2013年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的秦某某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被称为网络诽谤第一案。被告人秦某某注册多个网络账号,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编造“温州动车事故外籍乘客天价赔偿”“某名人具有德国国籍”等虚假信息并大肆传播,引发了众多网友评论转发,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判决书来看,秦某某的网络造谣行为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的主要原因是造成了现实生活空间的社会秩序混乱,而非造成了网络空间秩序的混乱①。又如,2018年河南某县发生的常某殴打老师案②,被告人常某在道路上拦截并殴打老师,后将视频上传至网络,引发了众多网民的转载与评论。判决书认为,常某拦截殴打老师,并录制视频进行传播,破坏了社会道德和公序良俗,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
首先,尽管两者的具体案情不同,时间跨度较大,但两者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均以信息的转载量和评论量作为判断网络秩序是否混乱的标准。有学者认为判断起哄闹事行为是否造成网络秩序严重混乱,应当以《信息解释》第二条(一)“……实际被点击、浏览的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作为标准,其有利于量刑标准化[10]。今日的互联网进入了以“流量为王”、“数据说话”的时代,尤以“微博热搜”为首,例如重庆公交车坠河案起初媒体报道均是强调对向而来的女司机越道行驶,导致公交车躲闪不及而坠河。紧接着,众多网民在媒体博文下起哄评论辱骂女司机并要求其偿命,其中部分“楼中楼”评论更是达到了上千条,后重庆警方通报该女司机无过错,是公交车司机自行行为导致的坠河。据女司机家属称其精神压力巨大,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那么以此来看,每位跟帖量达到500以上的网友均已经构成了《信息解释》第2条(一)所规定的标准,新闻媒体在没有核实真实具体情况下发布不实新闻也应当承担责任。显然,以点赞、转载次数作为标准是不妥当的,并不能真实的反映网络公共秩序的混乱程度。互联网作为表达言论的平台,不同意见进行交流与碰撞是很正常的表现,有学者认为在网络空间进行“刷帖”、“霸屏”、“灌水”等行为就意味着网络秩序严重混乱,那么单纯的网络秩序混乱,并没有侵害公民的人身、民主、财产等权利,又怎么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呢?即便承认存在网络“语言暴力”,但也不能将“言语暴力”与“肢体暴力”相提并论[11]。
其次,统观当前理论界的观点,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信息网络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处罚依据是造成了现实中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即便主张“双层论”“同等论”的学者,其处罚的立场从实质上来看也是基于现实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
再者,从各地各级人民法院所判处的网络寻衅滋事犯罪来看,其判决依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络秩序严重混乱,另一类是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但从案件事实来看,二者实质上并无任何区别,其形式都是“在网络上散播言论,在现实中又有实质危害行为”。
行文至此,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信息网络秩序混乱是一个伪命题,无论是从互联网的虚拟性、平面性和互动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公共秩序等其他角度来看,单纯的网络信息散布行为是不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唯有侵害结果发生在现实空间才能予以规制。
四、网络型犯罪行为如何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必然会就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刑法适用产生不同的观点。2013年的《信息解释》尽管饱受学界争议,但它却实实在在地给违法者敲响了警钟。在网络立法尚不完善的时代,如何规制网络型犯罪行为?有学者主张全国人大进行立法解释,有学者主张全国人大予以专门立法。笔者认为,并不能单独依靠立法来解决所有问题。
首先,对于以互联网信息系统为犯罪对象的行为,仍然按照刑法条文的明确规定予以定罪处罚。其次,对于以互联网作为犯罪手段或载体的行为,其实只不过是传统犯罪行为通过另一种渠道的表现,“换汤不换药”,对于此类行为可以秉持“裁掉多余”的立场,依然按照传统条文予以处罚,并没有必要再进行立法,比如网络诈骗,同理,对《刑法》第287条应当视为注意性条款。最后,对于以网络秩序的混乱为要件的行为,应当正确区分网络秩序混乱和现实社会秩序混乱,在微博、微信、贴吧等网络平台进行的起哄闹事行为并没有实质意义。某些单纯的网络诈骗,例如制造灾难谣言进行诈捐行为,即便是分文未得,但已造成严重的网络秩序混乱,此时若按照寻衅滋事罪处置,其刑罚可能会超过业已骗取大量财物的诈骗罪,这样的结果显然令人匪夷所思。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行为所造成的侵害与现实行为所造成的侵害两者是否相当呢?在本文看来,网络行为的处罚应当明显轻于现实行为的处罚。《刑法》第291条之一的第一款规定投放虚假物质或编造虚假信息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最高刑是五年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最低刑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款规定在网络上传播的,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刑是七年有期徒刑。那么由此来看,立法者认为网络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明显低于现实行为的危害后果的。因此,《信息解释》第5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欠妥当的,对于通过网络进行寻衅滋事的行为处罚力度应当低于刑法第293条的处罚规定。
总而言之,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尽管互联网已经深度融入人们的生活,但将网络空间秩序解释为公共秩序,仍然令人感到费解。在互联网时代,无论采用何种解释方法,都不能超过法律用语的应有含义,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更不能违背国民预测可能性。在当前“重管理,轻保护”的互联网法治思维背景下,网络空间秩序混乱性寻衅滋事罪仍不能成立。
注释
①(2013)朝刑初字第2584号刑事判决书。
①(2019)豫0324刑初43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