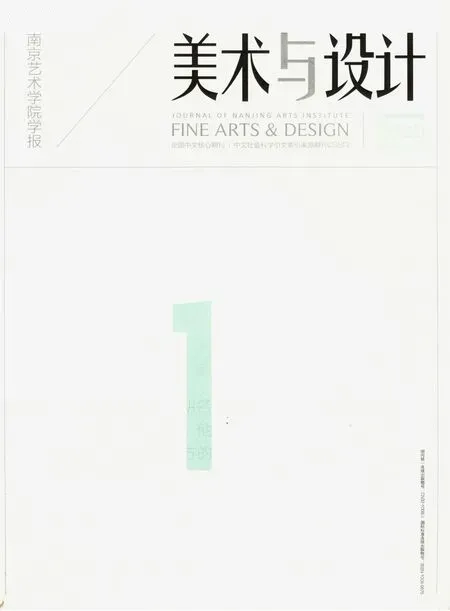20 世纪上半叶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2020-12-25曹院生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241
曹院生(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241)
1937 年,朱希祖撰写《余杭章先生行状》如是说“余杭章太炎先生又以文字、历史为国性所托,自亡命日本时已陶铸弟子,民国既建,各大学国文、历史教授大都为章门弟子,迄今不下七八传,而亦弥布全域,大学、中学靡不有其踪迹。”[1]章太炎及其章门弟子是中国近现代史中一个重要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皆有着突出的专业成就与社会影响力。然而,以这个群体为核心的新式文人在书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一直没有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点。
与旧式文人康有为相比较,在书法理论研究方面章太炎似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在叙述20世纪中国书法学术史的时候,如果忽略了章太炎及其弟子,以及章氏同侪对书法的推进,可能20 世纪书法史的书写将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关注以章太炎及其弟子与同侪为核心的新式文人群体的书法研究成为必要,以期他们在书法史的叙述中获得一个客观的定位。下面将从一些零零碎碎的资料中梳理出这些新式文人在碑学运动的背景下对书法的学习与理解,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对碑学的交流相互肯定而结合在一起形成共同体,又是如何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他们所确立的碑学规范。
一、章太炎的碑学思想
20 世纪初的新式文人是指以章太炎、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为核心的文人群体,而相对的旧式文人是指以翁同龢、沈曾植、郑孝胥、罗振玉、康有为等满清遗老为核心的文人群体。章太炎作为新式文人的核心人物,他学术政见基本上与康有为相左,如对经学的理解、孔教的态度、革命的选择等方面,章太炎也似乎总把康有为当做靶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尤其是经学理论。章太炎立足于古文经学而康有为立根于今文经学,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皆已超出汉、清二代的今古文。
首先,章太炎宗法秦汉碑版和魏晋法帖等“古学”,并非一味地尊碑抑帖。章太炎对康有为“借经术以文饰其争论”的行为不以为然,同样对康有为倡导北碑反对帖学的主张也不认同,这与两者对待经学的理解分歧有关。章太炎立足于古文经学,又是俞樾的弟子,而俞樾又师阮元。阮元撰写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他在《南北书派论》中指出,北碑“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不出锋,犹如汉隶”,大力倡导碑学以救帖学日渐靡弱之弊。所以从师承而言,章太炎也是碑学中人,但是他对康有为倡北碑反帖学颇为不满。他宗法秦汉碑版与魏晋法帖等“古学”,并有自己的见解:“然而规摹碑版,非倜傥有识之士心知其意者,则视摹法帖为尤难。其必以浅深辨坚鋊,以丹墨校肥瘦,以横卓通运用,然后可与昔人竞力耳。世之论碑版者,徵存缺于一字之内,分明暗于数书之间,非不能详审,而大体不存焉。故差足以辨真偏,而不足以别妍蚩。自大兴翁氏专求形似,体貌愈真,精彩愈远,笔无己出,见诮诸城。后之习者,笔益蹇省,乃至模写泐痕,增之字内。一画分为数起,一磔殊为数段,尤复上诬秦相,下诋右军,则终为事法帖者所诮已。”[2]章太炎认为,学习碑版比学习法帖更难,因为碑版经过书丹、雕刻后所呈现的形神特征与书写者在纸上所呈现的形神面貌完全是两样,更不用说碑版经过风化破损后的状态,对于学习者而言更是盲人摸象。这种规摹碑版简直就是“上诬秦相,下诋右军”,自然也就会为师法魏晋帖学者所讥笑。当然,如果规摹碑版者能够从法帖的角度出发,认知碑版也是可以学的,“其必以浅深辨坚鋊,以丹墨校肥瘦,以横卓通运用,然后可与昔人竞力耳”,这充分体现了章太炎作为一个碑学者对待碑学的辩证认识,而不像康有为那么偏激。同时,他对翻模失真的法帖也不主张学习,自然也不会因为翻刻而失真的法帖存在而否定魏晋法帖。章太炎这种深究的客观态度与其根基扎实的古文经学研究一脉相承,他反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妄言“微言大义”,而推崇“学问本来就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3]。
当然,章太炎推崇魏晋帖学与其文学思想有关,他看重魏晋文学长于持论的特点,从玄言妙理上取得共鸣。他说:“夫持论之难,不在出入风议,臧否人群,独持理议礼为剧。出入风议,臧否人群,文士所优为也;持理议礼,非擅其学莫能至。”[4]可见,保存清远风骨之本是太炎先生魏晋情结的一个基点。“这样,文章与学术相通而化合,辨名析理的魏晋文深契民国初叶的文化生态,精通学理、富有论战效果的魏晋之文便成为革命派舆论宣传的重要武器。”[5]
其次,基于经学研究衍及而成的碑学研究。扬州学派的经学研究由于衍及与书法相关的小学、史学、金石等方面,于是立刻反映到书法理论上来。作为古文字学家,章太炎强调书写者必须“字法准确”,且立足于“六书”与“形”“声”“义”三者的统一。他说:“唐人不识古文,所作篆书,劣等字匠。……北宋以还,钟鼎渐渐发现。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6]章氏说,自宋至清对于钟鼎文字大家都望文生义,而忘记了作为“六书”基础的声韵与训诂之学,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对于习书之人,首先要明白,“字法准确”,此乃第一要义。为此,习书者必须通文字之学,兼习声韵与训诂,而声韵训诂则有赖于传授,“设无传授,何从而知之乎!”[6]60虽说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书家成为一个文字学家,但是对于“小学”之学还是要具备一定的常识,不然真会贻笑大方。
由此可见,章太炎对于碑学书法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把钟鼎文、金文以及他所排斥的甲骨文研究从“小学”中剔出归之于“以资欣赏”的艺术设想,显然与一种现代性的艺术研究有些格格不入,这是不是与他背后藏着一个罗振玉的阴影有关不得而知,但是“章氏一生学术政见,多视康有为如大敌”,[7]而罗振玉与康有为皆为改良派的核心人物,是章太炎的“死对头”。另一方面,章太炎对于碑版法帖的收藏、临摹与鉴定有浓厚的兴趣,尽管没有写成大部头的理论专著,但他晚年所写的一系列短文、通信等,无不闪现出他对书法的一些真知灼见。所以对他所谓的“不习金石刻画”之说要一分为二的理解,对于那些有刻画痕迹、湮隳斑驳的碑版他当然不会临习,至于那些字口清晰、形神兼备的秦汉碑版他怎么会不认真临习呢!
新式文人的“文人字”是一种特有的书法现象。它没有不为法所囿,更无馆阁体的板滞之气,而是呈现出一片自然流露的清新之气和张扬的个性。在尚用的书写中无意于佳乃佳,但又不失书法意识的觉醒。这些新式文人常常以独具个性的艺术风格从事各种场合的书写,并进行书法交流。章太炎作为一个文人,它们有着一般文人同质的表现方法,同时他又是一位书家,对书法意蕴的主动追求有着明确的审美价值取向。自然而然,他对篆书的研习与创作情有独钟。他不仅以篆书作板书讲课,而且给钱玄同写信居然也用篆书。他的书法尚碑,且为大家所追捧,章门弟子经常不失时机地向他求字。1932 年,章太炎到北平避难,章门弟子与师欢聚。周作人亦设家宴款待章师与同门:“五月十五日,下午天行来,共磨墨以待,托幼渔以汽车迓太炎先生来,玄同逷先兼士平伯亦来,在院中照一相,又乞书条幅一纸,系陶渊明《饮酒》之十八,‘子云性嗜酒’云云也。晚饭用日本料理生鱼片等五品,绍兴菜三品,外加常馔,十时半仍以汽车由玄同送太炎先生回去。”[8]师生相聚甚是怡乐。
沙孟海在其《章太炎自题墓碑和有关手迹》中说:“章先生是一代朴学大师,初不以书法出名。往年我写《章太炎篆书千字文前言》,分析三百年来篆书凡有四派:钱坫、孙星衍是古文字学旧派,邓石如、吴昌硕是书家派,吴大澂、罗振玉是古文字学新派,章太炎则是古文字学别派。章先生的篆书,结法用笔与后来出土的战国墨书竹简和铜器刻款多有暗合之处,自成一家面目。《终制》一篇,体势在篆楷之间,更多近似近年新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至于自题墓碑五字,隶楷参半,又成一格,略似吴《谷朗碑》。”[9]在此沙孟海将章太炎视为篆书大家,而且将其与钱坫、孙星衍、邓石如、吴昌硕、吴大澂、罗振玉等人相提并论,并且指出,他是“古文字学别派”。这个“古文字别派”的“别”字体现出章太炎碑学的包容性,他的篆书既与“战国墨书竹简和铜器刻款”暗合,又近似“近年新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还“略似吴《谷朗碑》”,这就是他有别于康有为之处。
一句话,章太炎的书法思想源自古文经学,崇尚“古学”,即秦汉碑版与魏晋法帖;另一方面,胎息阮元、俞樾碑学思想,尊尚“碑学”。由于他的书学研究由经学研究衍生而出,自然缺乏研究的系统性,所以其书法创作也只局限于篆书方面的成就。然而,作为近现代书法史上的意义,章太炎的书法并不只是体现在他个人书法研究的成就,而是体现出他对其弟子及同侪的书学思想的影响。
二、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的形成
章太炎怀疑现代学堂存在“眼学”的弊端,所以选择古代收徒“从游”的方式。他曾四次开门课徒,讲授国学,其中第一次是1908 年在日本东京开课,从游者有朱希祖、黄侃、钱玄同、鲁迅等人,后来成为北大某籍某系的章门弟子大多从这开始。章氏也会与他的同侪及弟子从古文字学出发,讨论书法问题,其中不乏围绕着碑学而展开的讨论。
1923 年,章太炎研究三体石经,撰《新出三体石经考》,在《华国月刊》第一卷一期至四期连载。他说:“《新出三体石经》以为邯郸淳‘书独步汉魏,尝写壁经,而弟子迻以入石,其笔法渊茂,弟子所不能至,故云转失淳法,非谓字体有失也。邕在汉立一字石经,淳从后开三字石经’,邯郸淳与蔡邕‘篆法同师,而年亦相若’。”[10]在此章太炎明确指出,石经古文为邯郸淳所写,而《正始石经》乃其弟子迻书上石,非邯郸淳所作,就像《熹平石经》只因为蔡邕有其规画且曾书丹过而将其归于蔡邕所书,并指出,邯郸淳与蔡邕“篆法同师”。由此可见,章氏对书法关注的中心议题依然是“尚古”与“法”,不过其以古法为标准进行思考的背后,包含了一个自愿放弃主观的诠释权的内涵,是一种缺乏主体意识的表现。
据载,章太炎“又有《与黄季刚书》,原书无年月,也谈石经,并答黄侃‘所问《鲁论》异字’,以为‘唯高子弑齐君,最为难了。崔抒弑光明见《春秋》,坦然明白。鲁学者,不应不见而遽改崔为高,恐亦古文真本如是’。”[10]426黄侃,字季刚,章太炎的大弟子,有“天王”之称,文字学家。章氏在信中和黄侃从文字学的角度讨论《三体石经》,并进行辨伪。据清代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四所载:“乾嘉钜卿魁士,相率为形声训诂之学,几乎人肆篆籀,家耽《苍》《雅》矣。诹经榷史而外,或考尊彝,或访碑谒,又渐而搜及古专,谓可以印证朴学也。”由此可见,像章太炎及其弟子黄侃、汪东等国学大师虽不以书法名世,却“几乎人肆篆籀”,写得一手好字。黄侃能篆能隶,可行可楷,而且对《急就章》极有研究,曾编有《急就章编画》。
1929 年10月17日,章氏《致汪东书》,就是一封专门谈论书法笔法问题的书信,言及自用单钩执笔法临习《天发神谶碑》之事。“寻源溯流”一直是章氏研究的初心。单钩执笔法是一种古老的执笔方法,与后来沈尹默提倡的“五指执笔法”大相径庭,章氏自认为寻到了写篆隶执笔法的正脉,并因“今人殊鲜为之”而自得。接下来章氏又说:“《天发神谶碑》此间原有摄影本,但此亦与重摩者无甚高下。欲睹其真,然后快意求之,当亦不能甚急也”。由此可知,章氏对于原拓真本的重视程度,即使是面对当时极为难得的珂罗版的《天发神谶碑》,也锱铢必较。
再说章太炎对鲁迅的书学影响。“如果说,鲁迅后来在辑佚、校勘、考证、目录等方面的功力,研究古文字及金石碑刻,书法之崇尚汉魏风骨,与清学有一定关系的话,其中介当为章太炎。章太炎讲授‘小学’‘金石学’‘文字学’‘说文解字’等等,鲁迅深受其益,且章太炎的治学方法更为鲁迅所运用。”[11]鲁迅毕生以抄录、辑校古代典籍、碑刻为乐事。他从日本回国以后大量收藏碑刻拓片,其中不乏清末民初金石大家陈介祺、端方、马衡等曾经收藏过的拓片。据统计他收藏的汉碑拓片有一百三十多种,经过他抄录和校勘的有一百多种;魏晋南北朝墓志有三百多种,经其抄录并校勘的有一百九十二种。如用古文、小篆、隶书抄写了《三体石经尚书残字》,他还抄写了《曹全碑》,并对其作了详细的记录。他用楷书抄写《曹全碑并背阴》但隶意甚浓。和章太炎一样,鲁迅对碑刻拓片的收藏和抄录皆缘于治学的兴趣。他发现王兰泉《金石萃编》有许多错误,想写一个可信的定本;他重订《寰宇贞石图》时,第一册目录上第一份著录就是《石鼓文》,且将其断代为周代,并在题下注云:“十字,在京师国子监。”[12]他在致曹聚文的信中曾谈到想编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由于精力与财力的不足,没有如愿。
鲁迅抄录古碑并非书法临帖,但他依照碑刻拓片双钩摹写碑文进行校勘的方式又是书法临摹学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双钩摹写可以让临习者准确地把握运笔过程中的笔法、单字结构,进而深入理解其神采,所以大量收藏与抄录活动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还提高了他的书写功力,改变了他的审美趣味,提升了他的艺术境界。
除了与其弟子交流以外,章太炎还与其同侪一起讨论研究。《新出三体石经考》刊发后,章太炎《与于右任论三体石经书》,章氏以为:“石经非邯郸原笔,《书势》已有其文,然既云‘转失淳法’,则明其追本于淳,若绝不相系者,又何失法之有?《书势》之作,所以穷究篆法,而非辨章六书,篆书用笔不如淳,则以为转失淳法,故其下言‘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言笔势微伤于锐也,岂谓形体点画之间有所讹误乎?朴安因是疑三体石经文字不正,失邯郸、许氏字旨之素,则未寻《书势》大旨也。”[10]426于右任是一位碑学大家,信中章氏告诉于右任,《书势》中说得很清楚,“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蝌蚪之名,遂效其形”[13],并指出胡安因未寻《书势》大旨。
1923 年12月4日,章氏《与张伯英书》云:“石经之出,不知者以为碑版赏玩,吾辈读之,觉其裨益经义,在两汉传注以上。盖传注传本,已将文字辗转变易,石经则正本也。”[10]426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认为,石经“裨益经义,在两汉传注以上”乃为“正本”,这才是石经的价值所在,并不仅仅是一般人所谓的赏玩之物。
章氏对于一些诸如石经之类的出土碑版,并不仅仅限于对它们进行赏玩,而是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考证。他在书法上的意义则是为研究者提供对古代碑版进行甄别的依据,使得碑学研究获得一个很切实的事实起点。不可否认,“章太炎对于书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又是不可小觑的。也正是他在有意无意中书法研究的关注与论述,都能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书法这门传统意义上的‘小道’与当时以及此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的主流学术界、思想界之间的对话。”[14]
民国前后有一些以旧的治学方法进行书法研究的学者,他们从文字学、考据学的角度对一些出土碑版的作者、年代、版本、卷次以及文字的异同进行研究,并根据石刻损泐情况分别考订翻刻与原刻,拓本新旧等区别,为碑版赏玩提供最有权威的资料。我们无法排除这些研究在书法理论中的主要地位,如果没有这些研究的存在,民国书法理论就找不到一个有异于前贤的新起点。
同理,如果没有新式文人的这些关于碑学的交流,我们也难以觉察到,有一股新型的碑学力量在暗流涌动,它不同于旧式文人的那个碑学群体,而是一个以章太炎、黄侃、汪东、朱希祖、钱玄同、鲁迅、周作人,以及于右任、张伯英等为核心的新式文人碑学群体,即沙孟海所谓的“古文字学别派”,这个别派中的新式文人在交流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因志同道合而形成了另一个碑学共同体。
在这个碑学共同体中,他们遵守一个相互肯定的规范:一,书写的篆字以《说文解字》为准,就像顾廷龙评章太炎篆书所言:“余维先生所作篆书,以说文为主,首采初文,并用本字,多从古文间代弍字,偶及金文,亦取通假,而不依新附。”[15]二,临摹的对象以秦汉至魏晋间的新近出土的碑版为佳,如篆隶相参的《天发神谶碑》,正始中所刻的《三体石经》,有古文有篆隶,篆文则严正有格,古文则旖旎舒展。三,这是一种立足于文字学、考据学的书法理论研究,它的“骑墙性”研究特点有别于此前的书法理论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有待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碑学规范,毕竟它不是从书法本体而构建的书法规范。
三、钱玄同、沈尹默等新式文人对碑学规范的发展
随着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的不断发展与壮大,以及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在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社会影响力,共同体成员在日常书写与交流中对书法这门学科获得了一个新的认知。他们开始从书法本体出发系统地研习书法,从书法史的角度讨论书法,并在规范的指导下,运用规范这个工具解决规范内的正当问题,如“执笔”与“笔法”等具体问题。
第一,壮大了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
日本留学归来的沈尹默,从杭州到北大,经营了一个以章太炎门生为核心的社交圈,经常对碑学问题进行交流,壮大了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
1913 年2月,沈尹默被误以为是章太炎的学生而应聘到北京大学预科教中国历史,①据沈尹默《我和北大》中记载:“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自好硬着头皮,掛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见郦千明编著《沈尹默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 年版,第20 页。并成为为北大炙手可热的人物。接着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黄侃等章太炎弟子也陆续进入北大教书。沈尹默因为是沈兼士的哥哥,又被人误以为是太炎门生,那些比他晚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自然也就将其视为“自己人”,在北大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太炎门下一员。1917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公布专任教员名单中,章太炎的学生就有不少,如黄侃、朱希祖、马叙伦、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等等(《北京大学日刊》1917 年11月30日)。而当这些人相继进入北大后,他们代表了一种新文化力量。他们以北大为中心,不断地交流和传播新式文人碑学思想。
第二,从书法本体出发系统地研习碑学。
对碑学进行系统的研习,沈尹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沈尹默虽然不是章太炎的学生,但他对碑学曾用功甚勤,他与章门弟子过从甚密,或多或少会受到章太炎书学思想的影响。1909 年,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其俗在骨”[16],沈尹默“遂取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部分细加研读,并在习字中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笔蘸淡墨临写汉碑”[16]144-145。他之所以没有研读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或许就与章太炎的碑学思想有关,但他又发展了章太炎的碑学规范,从书法的本体出发不仅研习秦汉篆隶,还系统地研习北碑。据沈尹默自述:“一九一三年到了北京,始一意临学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爨宝子碑》《爨龙颜碑》《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尤其爱写《张猛龙碑》,但着意于画平竖直,遂取《大代华岳庙碑》,刻意临摹,每作一横,辄屏住气力,横成始敢畅意呼吸,继续行之,几达三四年之久。嗣后得元魏新出土碑碣,如《元显儁》《元彦》诸志,都所爱临。《敬使君》《苏孝慈》则在陕南时即临写过,但不专耳。在这期间,除写信外,不常以行书应人请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为得要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17]沈尹默不遗余力地研习北碑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脱去以前行草书所沾染上的俗气。“脱去俗气”是书法美学的要求,不是文字学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说,沈尹默是在站在书法学的角度系统地研习碑学,这是对章太炎所确立的新式文人碑学规范进行了发展。当然,沈尹默对新出土的《元显儁》《元彦》诸志也情有独钟,这些新出土的碑版字口清晰,研习者可以更确切地理解书丹者的笔意,章太炎也觉得此类碑版可以用来临习。
在此期间,对碑学的讨论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碑学爱好者相互肯定而实现艺术精神一致的过程。1912 年10月15日,据《钱玄同日记》记载:“午后访尹默,出石印完白隶楷三种,隶书浑厚茂密极矣,楷书学齐朝,与董洪达造像如出一人。又隶书一种,有礼器県阁气息。盖完白隶楷实为第一,篆实逊之,行草则仅能成逸品而已。包慎伯、康有为皆推崇过当也。”[18]钱玄同、沈尹默作为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不仅可以共享规范,而且还要利用规范这门工具探讨规范内的正当问题,一方面是为了不断地检验规范,发展和完善规范,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共同体成员对规范的信仰,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
还是这一天,钱玄同访沈尹默出示邓石如隶楷作品同观,16日又和马裕藻在沈尹默家同观石印缩本钱坫书联,钱玄同赞其“瘦硬,变化极矣”[18]11。17日又记:“《邓完白隶楷三种》,有正出版,楷书瘦劲,绝类北齐之董洪达造像。隶书二种,一瘦一肥者。顽伯隶书类然瘦者吾谓似礼器,尹默谓是学《曹全碑》阴,吾实未取遽信。”[18]11对于邓石如楷隶的取法问题,钱玄同与沈尹默的观点不同,这也是碑学规范系统内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规范发展完善的前提。此类材料在钱玄同日记里比比皆是,说明他们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碑学问题,而且从他们讨论的问题及观点分歧可以看出,他们对碑学已经有了一个系统的认知。
第三,从书法史的角度讨论书法。
他们讨论的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出土的秦汉碑版,而是从李斯扩展到李阳冰,再到邓石如等篆隶大家,从书法史的角度讨论碑学的发展得失。如11月2日,沈尹默就和来访的钱玄同讨论李阳冰的篆书。《钱玄同日记》记载:“十时顷至尹默家中,复与默辨阳冰篆书之高下。余夙谓学篆不外两种,求古则以《石鼓》为正宗,参以钟鼎文,否则以专汉篆如《少室》《开母》,孔林坛坟、鲁王墓前石人题字、吴天玺《纪功》《封禅国山》及碑额之类。斯相石刻久已不存,今所见者,即徐铉临本,亦复枣木屡翻,全非真相。阳冰自谓斯翁以后直至小生,而如城隍庙碑等,专以瘦硬取胜,实不足道。此固非余一人之私言。而尹默则颇尊信阳冰。吾谓阳冰自谓直接斯相,其语太誇,完白自谓不如阳冰,则太自贬,皆不得因其自道而信之。完白篆体虽为清世第一,而以隶笔从容作篆,较之阳冰之矫揉造作,实足胜之也。尹默论书,吾素所倾佩,唯过尊阳冰,则期期以为不可也。”[18]12钱玄同的观点非常明确,学习篆书有两条路,一是取法高古的石鼓文,二是学习汉碑碑额的篆书等,这一点钱玄同与章太炎的崇尚高古的观点颇为相似。他并不认为李阳冰的篆书得到了李斯“高古”的精奥,反而觉得邓石如的篆书比李阳冰的写得好,因为邓石如用隶书笔意作篆书的从容之态胜过李阳冰的矫揉造作,对此沈尹默不敢苟同。虽然观点有分歧,但是他们对问题的分析维度却是史学维度,他们研究书法是从书法史的维度认识书法中的问题。此处钱玄同将章氏的史学精神灵活运用到了书法上来。章氏弟子朱希祖述本师功绩曾经如是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19]清末民初的古今之辨将中西问题转化为古今问题,此后现代学术转型进人“以史为本”时代,而章太炎正是这一转化过程中的转捩点,从而为“以史为本”的现代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章氏培养了很多弟子,各成名家,故章氏之后,史学遂为众学之本。1917 年12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创立,后来马衡和刘季平在此期间分别讲授了《隶书之源流及变迁》和《篆隶之沿革》等带有“书法史学”研究性质的演讲。
第四,讨论书法中的“执笔”“笔法”等具体而正当的问题。沈尹默在北大书法研究社还做过关于笔法的演讲,此前他就与教钱玄同讨论过执笔法。1912年10月27日的《钱玄同日记》记载:“为尹默书窗纸四大张。……今则作寸以上字可悬腕,悬肘。此盖因执笔法近稍改正,盖尹默教我也。”[20]沈尹默的“五指执笔法”与其“笔笔中锋”的笔法理论一脉相承。然而,在邓石如的问题上,他俩的矛盾焦点就在于以何种笔法作篆。沈尹默提倡在书写过程中,不管什么书体都要“笔笔中锋”,更何况“笔笔中锋”是篆书的基本笔法;钱玄同则认为,邓石如用略带绞转的隶书笔法所作的篆书从容又有变化,仪态万千且不矫揉造作,自然令人可喜。钱玄同还说他平时非常佩服沈尹默对书法的认识,但是对于这一点他坚信自己是对的。12月8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十时至尹默处,见石印《完白山人》《温公家仪》,末有赵撝叔一跋,谓山人以隶笔作隶,实胜少温。此予向持此论者,尹默则不谓然。余谓西汉之隶是篆笔作隶,今日作篆,自当以隶笔为之。”[18]14由此可见,在对待书法创新问题上,钱玄同比沈尹默更懂得变通。
那么,沈尹默为什么又固执己见提倡笔笔中锋呢?只要将沈尹默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去思考,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章太炎注重“溯源”“崇古”,而石鼓文介于古文和篆书之间,上集大篆之成下启小篆之河,它的基本笔法就是笔笔中锋,可见,沈尹默的“笔笔中锋”的要求有明显的时代性。而过于强调“笔笔中锋”就是墨守成规,是一种偏执。章太炎的碑学思想里就反对康有为偏执地崇尚北碑的观点。倡导碑学是时代的要求,但不一定要成为反对帖学的目的。站在崇古的立场,他也倡导碑学,但他并没有非此即彼地反对帖学,然而沈尹默为了脱去“俗气”崇尚“高古”强调“笔笔中锋”确实有点顽冥不化的偏执,是对规范的恪守,这也是他与钱玄同存在分歧的根本。
根据规范的创新机制,在某一规范的指导下解决规范内的正当问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必要的张力,甚至可能出现危机。在规范的指导下危机解决了,就会实现对规范的精炼与完善;危机解决不了,规范就会失灵,从而被另一个新规范所代替。在精炼与完善规范的过程中,不断进取的人会立于规范发展的潮头,而恪守规范的人将会远离规范而被抛弃,或改宗到另一个规范;在创新规范的过程中,共同体中的成员也将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主动创新的人会构建新的规范,而恪守规范者将会越来越远离共同体核心而变得冥顽不化。后来的沈尹默就是因为恪守碑学规范,未能获得长足的发展而改宗到了帖学规范;钱玄同因为缺乏坚守和创新,拿起了钢笔逃离了书法;鲁迅不断创新规范而皈依到了碑帖结合的规范,诚如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所言:“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21]
限于篇幅,我们不必列举太多的史料来阐述这个共同体成员对规范的发展问题,一句话,沈尹默、钱玄同、黄侃、马叙伦、周作人、沈兼士、马裕藻、马衡、蔡元培、陈独秀、刘季平等人,壮大了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并且立足于书法本体,从书法史的角度讨论碑学规范内的正当问题,完善和发展了碑学规范。
四、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的贡献
在碑学的规范和指导下,新式文人不仅进行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精炼和完善碑学规范,还组织社团开展讲座指导和培养书法人才,利用展览和评阅建立交流平台,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以及投身于艺术市场,获得市场份额,扩大社会影响。
首先是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
1917 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提倡“美育代宗教”,同年12月21日,蔡元培支持北大设立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由学生杨提生,罗常培、俞士镇、刘之墉、薛样绥、马志恒、祁仲鸿、董成等人发起,公推薛祥绥、杨提生为执事,请马衡、沈尹默、刘季平三位先生为导师,并草拟了简章:凡属本校本、预各科学生,均得为本社社员;聘请教师数人,指点途径,评骘成绩;学校备储各种碑帖于图书馆,备众观览(《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10月23日)。
书法活动开始以社团的形式在大学里开展,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建设。不过,书法社团的出现并不是现代书法的特有现象,自宋元以来就有各种书画社团活动,明末清初复社、几社的发展也给书画爱好者提供了组建书画社团的新思路,并产生了各种书画流派,如董其昌所主导的松江画派等,只不过这些社团及其活动并不具备现代艺术社团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松江画派的文人雅集也很频繁,虽然他们也常常围绕着“南北宗论”进行绘画讨论,但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沟通与交流,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质。正如陈振濂所说:“古代文人雅士结社是一种松散的雅集,而不是有宗旨、有特定艺术追求的组织化手段,它几乎没有什么集团性格。”[22]民国初期的书画金石家们一时还无法彻底改变这种性格,但有一点值得可圈可点,那就是他们已经有意识地跨越一般的文人雅集的层次,而自觉地进入一种具有集团性格的艺术活动,如1900年,由高邕之、李叔同、任伯年等人组织的上海书画公会。它已逐渐摆脱一般的雅集形式而转向具有现代社会组织意义的“公会”形式,开启了一种新型的社团组织性质。这种社团活动方式的风行,有效地改变了书画金石家们个体活动的性质。同时,研究社的一些书法教学、比赛及展览活动等皆以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方式呈现,以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取而代之以往的个人艺术活动形式,从而凸显出书法艺术组织的社会性。
为了便于社员学习,研究社购置了不少碑帖。“校长允为本社购置碑帖,当请马叔平先生开列碑版名目,沈尹默、钱玄同二先生开列草书碑帖名目。校长阅后,即托马先生随时购买碑帖。现在已购多种,正在裱装。碑版、草书名目排列极有统系,有益学者。今录于后,以供参考焉。”(《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2月22日)蔡元培乃北大校长,同意购买一些碑帖以供社员学习之用,特地让马衡开列碑版名目,沈尹默、钱玄同则开列草书碑帖名目。马衡是一位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且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所以对于碑版的选择他是权威。不仅如此,碑版、草书名目排列极有统系,足见北京大学是从专业的角度重视书法研究社的建设。
研究社还编印学习资料和开展书法作品的观览活动。1918 年2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集会一览表(二月念五——三月三日)》,预告当晚十九时,马衡、刘三、沈尹默三位先生在文科第一教室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2月25日)。3月25日,沈尹默假文科第一教室开第二次讲演会,为学生讲演用笔方法,并和钱玄同一起为学生编辑和油印《书法拾遗》资料(《北京大学日刊》1918 年3月20日)。1919 年1月21日晚7 点,书法研究社假文科事务室开第一次谈话会,请刘季平、马叔平、沈尹默三位先生莅临,后来马先生因有事未到。沈尹默讲书法大要,与社员探讨了很多书法问题,然后与刘季平到研究社观览社员所习书法(《北京大学日刊》,1919 年1月25日)。根据以上材料可知:一,研究社不定期地举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和讨论,对碑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指导;二,对学生书法展览作品进行评阅,是创作实践方向的指导;三,虽然《书法拾遗》已佚失,但可以推知它的内容无非是一些书法学习的指南与资料,或者是研究的成果与心得等。
如上所述,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的创立,虽说它没有被贴上“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的标签,但是碑学运动的盛行以及这些负责书法研究社的教授们是如此地热衷于碑学研究,自然有一种导向作用。据现有材料记载,沈尹默在研究会的第一次活动中和其他两位导师一起做过演讲,然后号召研究会成员捐赠各种碑帖等事务,后来沈尹默在书法研究社做了关于用笔方法的演讲,马衡和刘季平在此期间分别讲授了《隶书之源流及变迁》和《篆隶之沿革》等带有历史研究性的演讲。从其讲授内容来看皆在碑学研究的范畴之内,这就为碑学规范的推广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为碑学共同体的壮大发展产生了规模化效应,在社会上制造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声势,很容易由此影响到全国。此后,马衡的《金石学》、马叙伦的《石屋余渖》与《石屋续渖》,以及沈尹默的许多书学理论文章都是这个共同体的理论研究成果。总之,研究社的讲演会、谈话会、书法观览以及《书法拾遗》不仅为研究者及其后学提供了碑学研究的规范与指南,还实现了研究成果的共享与交流,也足现了这个书法社团社会性的价值与意义。
其次,积极参与和推动艺术市场的繁荣。
民国时期的艺术市场比较繁荣,尤以上海为最,如王一亭赞助吴昌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沈尹默、钱玄同等人对此也比较积极主动,马叙伦在其《石屋续渖》中,心情如此复杂地说:“上海有《活报》者,谓:‘王福广篆隶等描花,沈尹默富商撑腰脊。’……尹默书功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尹默年必展览其书一次,收入巨万,谓之‘富商撑腰’亦不诬。”[23]沈尹默每年必展其书是民国后期的事情,而热衷于与富商的联系是他进入艺术市场一贯使用的手段。1912 年10月18日,《钱玄同日记》载曰:“晨起即偕而、默诸人赴坚匏别墅”[18]11。10月20日,“晨得兄书,属偕而、默诸人往坚匏。阅《朱舜水先生集》及关于舜水纪念会之书。”[18]111913 年1月19日,“晨偕不庵至坚匏。今日不庵宴兄,嘱而翁、关氏二兄弟、沈氏三兄弟及冷僧作陪,宾主皆相知熟人,谈甚欢。”[18]17坚匏别墅位于杭州西湖北山街,也称小莲庄、小刘庄、占地十七亩,房屋数十间,依山畔水,回廊环绕,曲径通幽,集聚江南风格,乃湖州巨商刘锦藻1903 年所筑的别业。刘锦藻34 岁中进士,后辞官回浙江经商,在南浔办电灯公司,杭州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创办浙江兴业银行。那时的刘锦藻就喜欢结交当时的文人吴昌硕、王国维、柳亚子等,并邀请他们在他的净香诗窟里喝茶吟诗,当然这些文人也愿意与这样的儒商结交。从钱玄同的日记可知,沈尹默、钱玄同等人也在刘锦藻邀请之列。自古以来,文人与巨贾结交,文人希望获得巨贾的赞助,而巨贾既可沽名钓誉博得一个好名声,又可获得经济利益。
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他们还努力寻求艺术市场的拓展,如利用报刊媒体刊登书法润例广告。1917 年7月,沈尹默还与刘三在《南社》第二十集刊登书法润例广告。《沈尹默、江南刘三书例》:“堂幅每幅银四元,五尺以外六元,横幅同例。单条每条银二元,五尺以外三元。楹联每对银二元,五尺以外三元。扇面每柄银一元。堂扁招牌每字银一元,二尺以外二元,三尺以外四元。碑志寿屏另议。屏联来文加倍,泥金加半。磨墨费加十之一,笔资先惠。通讯收件处上海华泾、北京北京大学,一月回件。”[18]17沈尹默确实是时代的弄潮儿,其行事总是立于潮头之上,这种运用新媒体刊登书法润例广告就是鲜明的例证,以及他后来利用媒体对其书法展览的报道与宣传,包括通过展览作品的方式,皆是为了扩大声誉与市场,足见沈尹默对艺术市场的敏锐。虽然他不是先例,却不失为一个先行者。1925 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封里刊登《章太炎书例》:“篆联:七尺至八尺,三十元……行联:七尺至八尺,二十四元……篆中堂:一丈,六十元……篆屏幅:一丈,二十四元……碑志篆额手卷册叶另议。磨墨费一成,先润后作,一月取件。”[10]469在民国时期利用报刊刊登书法润例见多不怪,这也是适应和推动艺术市场繁荣的一个主要手段,也是艺术市场繁荣的一个新的起点,是艺术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识。清末民初,绘画展览崭露头角,书法作品偶尔掺和其中展出,随着沈尹默等人的积极参与,书法展览获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市场,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繁荣了艺术市场。
结 论
在这个新式文人共同体中,章太炎、汪东、黄侃、马裕藻、鲁迅、马衡、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可以说都是书法家,然而他们大多数人都不曾以书法家名世。书法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桩文人余事,然而他们通过对碑学的讨论与研究,形成了一个新式文人碑学共同体,从而确立了新式文人碑学规范。在规范的指导下,钱玄同、沈尹默、马衡等人都对此规范进行了发展与完善,并且吸引了大量的后学参与其中,壮大了研究队伍,获得了丰硕成果,扩大了社会影响。这些共同体成员与晚清遗老不同,他们是新式文人,所以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反映出一种新旧文化邅递的关系。随着旧式文人的离世,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到了民国中后期,这种新旧文化的对比转变成了新文化群中学者与艺术家(如黄宾虹、柳亚子、齐白石等)两个群体间的对比。所以,这些新式文人在20 世纪书法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