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动力学:历史溯源、理论演进与研究前景
2020-12-25向安玲
向安玲,沈 阳,何 静
一、引言
舆论(public opinion)作为一个独立的合成术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段然,2019),通常指公众普遍持有的观念、看法、判断或情绪(Schmeller,2009),它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且与公众事件相关(Holcombe,1923;Dewey,1927),是社会群体关于自我、他人、自身需求、目标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图景及行动指南(Lippmann,1946)。从狭义层面而言,舆论是指在消除个体意见差异的情况下,多数人对于社会问题形成的共同意见,也即大部分群众针对特定重要公众问题的共有态度、感觉和观点(Minar,1960),强调的是意见一致性;广义上的舆论则是社会上众多意见集合而来的特定合量(Gault,1923),强调的是意见的加总。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层面的舆论,都包含个人意见和公众意见之间的交互影响。从舆论学研究角度出发,研究者更多关注狭义层面的舆论(刘建明等,2009),也即更加关注共识(consensus)的形成而非意见的纷争。在舆论形成过程中,个体会综合评估群体中其他人的初始观点及其观点的迭代变化情况,并据此调整个人观点,最终群体内就特定议题达成共识,也即由个体意见转化为公众意见(Degroot,1974)。所以舆论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融合的过程,个体根据群体间意见的相近性不断调整自己的意见,众多意见相互碰撞、影响,使得舆论处于持续演变的状态(Lorenz,2007)。
舆论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跨学科研究议题。以传播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学等为主的人文社会学科更多地通过质化研究,立足于社会现象洞察与案例分析,来探讨舆论演变的原因、阶段、规律和调节机制。这些学科认为舆论演变包括混沌、众意分化、意见组合与主流民意形成等阶段,演变进程受到“社会变迁动力”和“共同利益动力”的影响(刘建明,2014)。限于相关因素的模糊性、不可控性和测量难度,人文社会学科对舆论演变的探讨多停留在理论层面,较少涉及对演变过程的量化推演。目前传播学领域对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的批评报道与舆论监督、网络媒体与网络舆论、公共领域与舆论场、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等方面(潘佳宝、喻国明,2017),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和外部视角探讨舆论与媒介之间的交互关系与社会影响,而忽视了从内部视角去探讨舆论本身的演化规律、趋势和内外动因。通过多维影响因子和量化推演去反映舆论形成和变化的动态过程,对于进一步洞察受众认知模式与媒介信息解码模式、把握群体内部交互影响与媒介宣传引导效果、探索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交织影响下的舆论演化趋势而言具备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包括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等在内的理工学科就开始关注舆论的形成和演变模型,学者们通过大量数学模型构建和仿真测算去描述、解释和分析舆论演变过程,并结合实际现象去挖掘规律、预测走势,逐步发展形成舆论动力学(opinion dynamics)。舆论动力学的概念由美国学者芬克豪瑟(G.Ray Funkhouser)正式提出,认为舆论演变是在社会各种力量交互作用下的结果,通过动力学模型可揭示舆论演变的内外动因(Funkhouser,1973)。与传统动力学不同的是,舆论动力学的研究对象是在大众社会普遍无序条件下的信息传播和观点演化规律,旨在探讨一个初始无序的舆论分布如何通过大量具有内在联系的个体互动和外部信息干预最终形成有序分布,也即揭示舆论生成与演变的内外动因。国内外传播学学者对舆论动力学的探讨和应用较少,在量化模型应用上也存在较大局限性。而自然科学研究者对舆论的探讨往往缺乏对其概念内涵和社会学机制的深入挖掘,导致相关动力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现实脱节,模型在实践层面的指导价值较弱。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舆论动力学相关经典模型进行回顾,结合传播学相关理论,对影响舆论生成和演变的相关因素进行梳理,一方面为舆论动力学量化建模提供指标依据,另一方面为传播学领域的舆论研究提供方法参考,基于交叉学科视角促进舆论动力学的发展和应用。
二、历史溯源:舆论动力学经典模型
1956年,French(1956)引入代理人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ABM)来研究个体在社会网络交互中如何应用社会权力去对他人施加影响,该模型也是舆论动力学后续模型的基础(Anderson &Ye,2019)。French模型假设群体中每个人的意见[xi(t)]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个体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其他人的意见来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群体中不同人对个体观点的影响程度都不同(权重wij),通过加权汇总的简单离散数学模型可对个体观点的形成过程进行描述,即式(1):
xi(t)=wilx1(t-1)+wi2x2(t-1)+…+xinxn(t-1)
(式1)
其中,xi(t)是个体i在t时刻的意见,wij是个体j对个体i意见的影响程度。也就是说,个体i在t时刻的意见,是由他自己在上一时刻的意见及群体中其他成员在上一时刻的意见(假设个体i知晓其他人意见)所共同决定的。而影响程度高低则涉及个体i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关系邻近度、信任度、身份地位、观点说服力等因素,这些因素有待从社会科学视角出发予以进一步阐释。
1959年,Harary(1959)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验证了French模型,奠定了使用数学建模方法研究社会舆论演变的基础。1974年,DeGroot(1974)在French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共识”的形成机制展开了探讨,他采用德尔菲(Delphi)法,即反馈匿名函询法,对专家意见进行反复征询,并提出平均化更新的方法来促成意见达成一致。在French Jr.提出的式(1)基础上,DeGroot指出随着时间的变化除了个体的观点xi(t)会发生变化,观点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wij也会发生变化,即wij(t+1)与前一时刻t的xi(t)和xj(t)相关。French Jr.和DeGroot两人的模型被合称为French-DeGroot模型,该模型奠定了舆论动力学的核心思想,即社会网络中的所有个体的意见在相互影响下经动态调整达成一致、形成共识,也即形成前文提及的狭义层面的舆论。后续无论是基于社会物理学还是基于复杂网络的舆论动力学研究大多以French-DeGroot模型中的社会网络关系作为基础。
以French-DeGroot模型为主的舆论动力学模式在探讨观点演进与共识形成的过程中更加关注群体间的影响,与“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论颇有相似之处。而个体在很多议题上除了会部分参考其他人的意见,也会出于利益、认知逻辑等因素坚持自己的最初看法。也就是说,个体意见的形成取决于两部分关键因素,一个是个体自己的初始意见(initial opinion),一个是群体影响——这也是Friedkin-Johnsen模型(Friedkin &Johnsen,1990)的核心观点。在式(1)的基础上,我们根据Friedkin-Johnsen模型可得到式(2):
xi(t+1)=g1xi(t0)+(1-g1){wi1x1(t)+wi2x2(t)+…+winxn(t)}
(式2)
其中,gi是个体i最开始的观点对其后续观点的影响程度,也即个体i固守己见的程度;(1-gi)则代表其他人对个体i观点的影响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很多仅限于仿真探讨的舆论动力学模型,Friedkin-Johnsen模型已被大量实证研究验证(Friedkin &Johnsen,2011;Childress &Friedkin,2012;Friedkin et al.,2016;Friedkin &Bullo,2017;Parsegov et al.,2017)。这一系列研究都表明,针对不同议题,舆论形成受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呈现出差异性,而要了解这种内外因素的深层结构,则需要从传播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视角来加以探索。
总的来看,基于数学建模的French-DeGroot模型和Friedkin-Johnsen模型奠定了舆论动力学研究的基础框架。但限于数学模型的抽象性,往往这类模型只能用于小规模群体分析,国外相关应用也主要集中在陪审团、政府内阁和公司董事会中的舆论共识和群体决策研究中(Anderson,2015)。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舆论规模越来越大、交互关系越来越复杂,French-DeGroot和Friedkin-Johnsen模型不再适用,于是面向大规模网络(large scale network)的舆论动力学模型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包括物理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等在内的学科成为新晋研究阵营。
三、理论演进:跨学科视角与模型迭代
虽然舆论动力学的核心理论模型发源于数学领域,但舆论本身的演化动力受到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大众媒介等多方面的影响,关联多个学科领域。舆论动力学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动力学研究,其包含了大量不可测量的心理、情绪、意识形态要素。对舆论动力学的研究需要通过人文社科来挖掘舆论形成和演化的要素,通过数学模型构建因素间的逻辑关联,再通过物理学领域的复杂网络理论来进行仿真和推演,最后再回归到社会科学领域对推演结果进行解读。舆论形成和演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涉及来自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领域的理论支撑,应用自然科学领域的动力学去探索舆论演化内外因素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一) 物理学视角:从磁吸模型到复杂网络研究
相比于数学领域对舆论共识形成的关注,物理学更关注个体意见的改变和由此带来的最终舆论状态。换言之,物理学视角下的舆论动力学侧重于广义层面的舆论。个体意见在相互影响下不断演进,最终可能达成共识、极化、多元分散等多种状态,这也更符合当下舆论场的真实生态。这类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模型也促进了社会物理学的发展。在社会物理学驱动下舆论动力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包括一维媒介模型、二维媒介模型、小世界模型、无标度媒介模型等分析模型相继诞生(潘则宇,2017)。
一维媒介模型主要以Sznajd模型为主(Sznajd-Weron &Sznajd,2000)。Sznajd模型假定:1)群体中的个体在讨论某一个议题时只能选择同意或拒绝两种观点。2)个体观点只受到与其相邻的个体的影响。3)个体间的交互呈线性模式,且当两个相邻个体(Si和Si+1)观点一致时,才能说服其邻近个体(Si-1和Si+2)也持有相同观点;反之,如果两个相邻个体观点不一致,则其邻近个体(Si-1和Si+2)保持原有观点。这种“邻近效应”放在人际传播领域也同样具备研究价值。
Stauffer et al.(2000)将一维Sznajd 模型拓展为多维媒介研究,认为个体会征询所有邻居的意见并取其算术平均值来决定自己的观点。Krause-Hegselmann模型(Hegselmann &Krause,2002)在此基础上对同质性观点进行了进一步探索,认为个体会基于信任界限(bounded confidence)选择和自己意见相似的人交互,而且每一次交互后他们的观点会更加接近,随着时间推移和交互的深入,舆论场会逐步聚集成不同的小群体(cluster),群体内的人具备相似观点,群体之间则存在差异性。根据意见群体的分布,我们可以把最终形成的舆论状态分为三种:共识状态、两极化状态、多元化状态。
Elgazzar(2001)在Sznajd模型基础上,应用小世界网络模型来探讨舆论演进动力,认为舆论网络中的每个节点以一定概率与其他节点进行随机连接,通过调整网络中的传播节点数量、连接概率和传播半径,可以实现小世界舆论网络模型的构建。结合舆论传播的现实情境,不同舆论议题的民生相关度、普及度和内在热度决定了其传播节点规模和传播半径,节点属性及其间的社交网络关系则决定了连接概率和舆论扩张速率。
近年来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舆论演化仿真成为舆论动力学研究的热点(任立肖等,2014),包括元胞自动机模型、投票者模型、多数决定模型、有界信任模型、CODA模型等都被应用到舆论演化分析中(任立肖等,2014)。但相比于统计物理学模型的相对简单性和可控性,现实社会网络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往往很难通过建模仿真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在这种背景下,更加抽象和复杂的社会物理学成为舆论动力学的研究路径之一。
(二) 社会物理学视角:舆论形成、扩散与趋稳动力
18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首次提出“社会物理学”(sociophysics)这一概念,指出“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延伸,提出通过“社会静力学”去研究社会结构和通过“社会动力学”去研究社会发展的创新思路(牛文元,2010)。包括牛文元、刘建明、刘怡君等在内的国内学者对于社会物理学在舆论演化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讨,衍生出了一系列交叉学科理论,为舆论动力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
1.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舆论生成机制
社会燃烧理论将自然界的燃烧现象和社会失序动乱现象进行类比,认为燃烧的三个基本条件(“燃烧物质”“助燃剂”“点火温度”)可以用来解释社会失序与动乱发生。将自然燃烧过程用以解释舆论的生成,可以把多元议论、见解、诉求视作“燃烧物质”,观点的分层和交互可以理解为“助燃剂”,突发事件和意见领袖言论则往往扮演着“点火温度”的角色(刘怡君、牛文元,2008)。从这个角度出发,多元观点、流通交互和突发事件(包括重要言论等)是舆论生成的三大必要条件,其中异质化的观点是舆论生成的基础物质,观点与观点间的碰撞与连接是舆论生成的必要路径,突发事件或关键性言论往往是舆论形成的引爆点。当作为燃烧物质的异质化观点越来越多时,舆论往往处于潜伏期;而当同质化观点开始聚集,交互越来越频繁时,舆论逐渐升温;直到某一个事件爆发,最终点燃了舆论并开始传播扩散。
2.基于社会激波理论的舆论演变机制
激波理论用来解释高速运动中气体受到强烈压缩后产生的强压缩波(即激波)。在激波形成过程中,速度、温度、压强等迅速变化,通过测量相关物理量的变化情况可以判断激波的波动情况。社会激波理论常用来解释具有波动性、流动性的社会现象,诸如人流、车流拥堵中的速度、密度变化(刘怡君、牛文元,2008)。“舆论波”往往是民心波动的表层意识再现,由舆论中心向外振荡起伏地扩散,呈现出上下起伏的波动状态(刘建明,1990)。基于社会激波理论探讨舆论演化,可以把多元观点看做流动的气体分子,观点产生的速度越快、密集度越高、情绪温度越高,以及媒体、涉事人及相关管理部门的施压越大,则舆论振荡越大,尤其是外界的刺激(衍生事件、信息公开、相关言论等)往往会引起舆论的高涨、激化或冲突,对舆论波动曲线起到引导性作用。外界对舆论演化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从众”“从上”“从理”“从利”四个维度(刘怡君等,2013)。
3.基于社会行为熵理论的舆论反转机制
“熵”是热力学中的概念,用以度量体系内的混乱程度。社会行为熵主要用以解释个体组成群体的行为,认为人类自发追寻“最小努力”“熵最小”“心理平衡”“情商共鸣”“社会取向倒U型”和“自我例外”原则,其中“心理平衡”与“情商共鸣”可用以解释意见领袖的形成(刘怡君、牛文元,2008)。舆论中的信息熵越大,舆论发展的不确定性往往越大,出现反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尤其是在后真相时代,相较于客观事实,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的信息往往会对舆论产生更大影响(胡泳,2017)。而社会行为熵理论可用来解释情绪化信息的生成,进一步对舆论演化及反转提供社会物理学层面的解释。
(三) 社会心理学视角:舆论演变的内在驱动因素
社会心理学研究普遍认为舆论形成是个体意见转化为公共意志的过程,或者是个人感知周围意见并被卷入(involved)群体意见的过程(张志安、晏齐宏,2019)。个人将社会环境作为参照框架用以解释新信息,社会交互环境是影响个体心理和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Sherif,1967)。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影响理论(social impact theory),个体受到社会压力时会改变自身态度和行为以趋向占优势群体的意见,造成包括从众、服从、社会助长与社会惰化、群体极化与群体思维等常见社会现象。经典舆论动力学模型多是基于社会影响理论构建,通过个体对群体意见的感知、判断、决策来进行建模和仿真,认为舆论形成是一种基于群体心理运作机制和交互行为的社会化过程,即个体基于对自身固有观点[xi(t0)]、群体观点影响[wijxij(t)]、情景的感知来调整自身的观点和决策,最终形成舆论共识。
Nowak et al.(1990)基于社会影响理论,对舆论动力学中的“观点”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从个人态度(private attitude)到公开发表观点(public opinion)的转化受到了多种外界因素引导。Hlyst et al.(2001)梳理了社会影响理论对舆论形成的三种影响机制和相应的动力学模型,包括:1)具有强领导的有限群组和元胞自动机模型;2)基于“社会温度”动态变化的演化模型;3)将个体视为通过通信场相互作用的主动布朗粒子模型。在舆论的社会影响机制中,少数“狂热分子”(zealots)往往会对舆论的演化方向起关键作用(Verma et al.,2014)。Jędrzejewski &Sznajd-Weron(2018)进一步考虑了“记忆”对个体判断和社会影响程度的干扰作用,对基于代理人基模型的舆论动力学理论进行了优化。
鉴于舆论演化环境和交互网络的复杂性与隐匿性,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演化动力分析日趋重要。尤其是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研究者基于社交媒体数据洞察个体潜在意图并展开行为预测,从信息获取到态度改变再到决策行为的全过程开始被数据渗透,这也为舆论动力学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 传播学视角:舆论演变的媒介驱动因素
相比于对舆论动力学理论模型的优化和迭代,传播学者更倾向借鉴舆论动力学相关理论思想和方法路径,针对舆论传播现象进行质化分析和实证探索,探讨媒介在舆论传播中发挥的驱动性作用。该部分相关文献量较少,证明传播学领域对舆论动力学的应用尚处起步阶段。
国外学者侧重于从政治传播、媒介效果和受众研究视角探讨舆论动力学模型,尤其是政治传播中舆论共识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Vliegenthart et al.(2008)发现新闻媒体基于利益和冲突两大框架去影响舆论演变,并指出新闻内容可作为舆论动力学中的一个变量用以预测共识的形成和政治传播效果。de Vreese &Boomgaarden(2006)基于Zaller的舆论动力学模型发现,在信息单向流动的情境下,媒体对政治成熟度较低的个体具备显著影响,而人际沟通对政治成熟度较高的个体产生显著影响;在信息双向流动情境下,媒体对舆论的影响作用有限。此外,传播网络中“狂热分子”的存在会加剧舆论场的两极分化,给民主政治带来了极大挑战(Leeper,2014)。机器人或“狂热分子”如何试图在社交网络中干扰传播、破坏选举进程,成为近年来舆论动力学关注的新热点(Anderson &Ye,2019)。
部分学者将舆论动力学模型引入媒介效果研究中,Quattrociocchi et al.(2014)引入基于复杂网络的舆论动力学模型,针对信息系统中不同媒介的规模和交互模式对舆论演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指出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竞争性和差异性共同打造了一个适应多元异质文化的稳定舆论环境。有研究基于舆论动力学模型和社会影响理论探讨大众媒介在跨文化互动过程中的作用,指出跨文化交互中群体舆论演化存在全局同质化、局部同质化和无序化三种阶段,大众媒介是推动群体观点和秩序结构演变的重要参数(Gonzlez-Avella et al.,2012)。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对传统舆论动力学模型提出优化路径。Althaus &Coe(2011)指出社会认同过程是舆论演变的主要动力。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当一个人所处的情境激活了储存在他长期记忆中的社会知识时,他的观点才会发生变化。Shi &Johansson(2013)基于动力学模型探讨了公共随机网络上共识的形成机制,认为传播网络中的节点之间随机建立吸引、排斥或忽略关系,共识形成需要一个特定的吸引水平,而极化的形成也需要一个特定的排斥水平。Wai et al.(2016)将DeGroot模型中的舆论节点分为顽固和非顽固节点,提出一种“社会雷达”方法来估计不同类型节点对其邻居的相对信任度,并认为当顽固节点足够多,以至于能影响多个非顽固节点时,整个舆论网络结构将被颠覆。除了个体观点的“顽固程度”,个人情绪唤醒程度也是舆论动力学模型运转的一个关键要素(Sobkowicz,2012)。从舆论演变外在动力来看,媒介环境、群体影响、历史情境等都是影响舆论形成和演变路径的重要因素;从内在动力来看,个体身份认同、知识背景、情绪状态等则是影响其观点改变和共识形成的关键变量。这些内外动力因素都值得从传播学视角来进一步解构分析。
国内传播学学者对舆论动力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主要集中在危机传播、谣言传播、政治传播、品牌口碑传播和意见领袖发掘等领域。危机传播是舆论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应用领域,国内学者侧重于关注危机事件中舆论的潜在演化方向及带来的舆情风险,并指出需要基于动力学模型推演结果进行舆论引导和风险防范。研究发现在突发性群体事件中,随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强,舆论领袖对普通个体的引导力会有所减弱,个体会呈现出更强烈的从众行为(赵奕奕,2014)。在危机传播的实践过程中,新闻发言人需要根据舆论动力学模型对大众的潜在反馈进行评估,因此开拓舆论动力学的更广阔疆域也成为传播学的一大责任(董立人,2010)。杨科、李英(2020)基于舆论动力学理论探讨了维权事件中的观点扩散机制,发现危机严重程度和企业努力程度不仅会影响维权舆论达到稳态的时间,也会影响达到稳态时参与的个体数量;而维权群体本身的网络关系和个体影响力只会影响到舆论演进时间,基本不会影响稳态时的参与个体规模。纪忠慧(2009)基于舆论动力学研究框架,论证了美国权力精英通过定义和解释外部实践、制造新闻、修辞舆论等策略,实现了对舆论中的个体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双重潜在支配。
总体而言,国内传播学领域对舆论动力学的探索还处于浅尝辄止阶段,多基于动力学研究范式挖掘舆论生成与演化的媒介要素,缺乏对模型的进一步迭代与实证应用。如何充分挖掘媒介在舆论生成与演进中的驱动性作用,是传播学视角下舆论动力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研究前景:舆论的真实性与逻辑性探讨
舆论动力学历经60年发展,在理论框架、算法模型、实证测算方面不断拓展、迭代,尤其是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让舆论场的混杂性、不可控性、演化速度进一步提升,传统的舆论动力学理论正在遭遇新的挑战。一方面,从舆论演变的内在因素而言,在社交媒体开放式、跨圈层、流量驱动的传播特征影响与利益相关群体的压力制衡下,个体的私人想法与公开表达之间的差异被进一步拉大,舆论的真实性愈发模糊。尤其是在人机混合传播背景下,“机器人水军”的出现增强了传播网络的可操控性,对网络节点和网络结构的逐层影响进一步影响了舆论演变的整体方向。另一方面,从舆论演变的外在因素来看,跨平台、跨时空、跨议题的舆论网络成为趋势,群体之间的交互不再局限于同一网络结构中,跨平台之间的交互和共振使得舆论网络的异质性、融合性提升,同一个现实主体在跨平台网络中可能扮演着多个传播节点,且呈现出差异化的交互网络和影响路径。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议题不再遵循线性演进,多个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使得其舆论演变也会相互影响,舆论动力学模型不再针对单一议题和单一传播网络,更多地需要面向混合议题和混合网络去进行逻辑发现和舆论推演。总体而言,观点的私人性与公共性、议题的逻辑关联性、传播情境的动态可变性、机器人和狂热分子对舆论的操控性等成为舆论动力学在当下以及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Anderson &Ye,2019)。
1.从显性观点到隐性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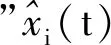
虽然国外学者已经开始探索显性观点和隐性观点的特征与差异,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的转化关系上,对于其间的转化机制、调节因素、控制因素并未做过多探讨,如何将传播学领域的“沉默的螺旋”“两级传播”等理论融合到舆论动力学模型中,值得做进一步探索。
2.从单一议题到混合议题
根据经典舆论动力学模型,个体会对自己及他人观点产生的影响力进行评估(self-appraisal),并以此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调整自己的观点。但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生产和舆论演进的速度往往快于个体进行自我评估的速度,所以常常在个体完成评估之前舆论就达成了共识(Anderson &Ye,2019),且舆论又进入新一轮的博弈与演化中。尤其是在后真相时代,碎片化信息、情绪化传播、衍生议题所造成的反转新闻事件屡现,在舆论演化过程中焦点常常会发生变化,传播网络也从单一议题主导转变成混合议题主导。传统舆论动力学模型并不能有效解释混合议题网络上的舆论演变,混合议题网络中个体观点除了受其自我评估与群体观点影响之外,不同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于个体观点演化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包括顺承、因果、转折、条件、并发等在内的事理关系直接关系到舆论观点的形成和演化,如何将事理图谱应用到舆论动力学理论框架中,是社交媒体环境下需要探讨的新问题。
3.从单一网络到混合网络
融媒体时代用户的复杂需求只有在多域和多平台中才能得到满足,跨平台行为使得面向单一传播网络的分析常常面临数据高稀疏度、海量动态、多元异构和意图复杂等挑战(蒋朦,2015),如何桥接多元异构的舆论网络成为动力学模型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个体而言,在不同平台上的社交网络关系、传播影响力甚至是传播行为倾向都存在一定差异,在同一个议题中个体在不同平台上的观点表达和群体交互影响不尽相同但又交叉影响,跨平台的信息传播和交互影响往往容易被忽略。已有研究表明,极端言论在不同平台之间的传播是一站式的、去中心化的、无标度性的,也即极端言论网络在某一平台遭受打击后可以一次性地传播到另一个平台,并迅速地重新布线和自我修复(Johnson et al.,2019)。单一平台上的舆论演进不能独立于其他平台去进行考虑,跨平台之间的群体交互和信息流通已成为舆论形成和演化的常态条件。
4.从人人交互到人机混合传播
智媒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逐渐替代人更有效地进行信息筛选、生产、传播,促使舆论形成的基础和内核发生变化,对社会主流舆论产生本质性影响(高宪春,2019)。这当中最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人机混合传播(man-machine communication),尤其是以“机器人水军”为主的智能化传播主体的介入。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在其2014年颁布的报告中指出,全球至少有超过2300万活跃社交媒体账号由“机器人”运行,“机器人水军”已经对全球重要政治活动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赵爽、冯浩宸,2017)。在人机混合传播网络中,除了人本身,大量机器化的节点对意识和意志进行有意图的表达与病毒式传播。这种动机明确、操作隐蔽、混淆性强、可控性强的传播网络极大地冲击了传统舆论动力学的核心理念。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舆论”的内涵、思考媒介伦理的价值、洞察“虚假舆论”的规律,对“人”的意识形态和观点的研究也需逐步拓展到对“机器”的意识形态及观点的挖掘。如何通过舆论动力学理论模型去发现“异常节点”也有待做进一步探索。
从传统媒体时代的中小规模网络,到互联网时代的复杂网络,到社交媒体时代的跨平台混合网络,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混合传播网络,媒介技术成为舆论动力学理论发展和演进的外在驱动要素,也成为舆论动力学模型需要关注的关键变量。如何从传播学视角、融合跨学科知识对舆论动力学理论进行拓展和应用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机器博弈的网络信息传播安全多准则动态管控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ZDA329)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