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绪:无悔的扶贫教育人生
2020-12-25安文军
安文军
中国农业大学
张文绪,1934年出生,湖南龙山人,土家族,水稻专家、水稻史学家,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曾在世界一流农业研究机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六五”及“七五”期间,担任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主持人,研究成果曾获得1986年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科研事业最盛的时候,毅然响应国家扶贫号召,赴湘西武陵山区,参与创办武陵大学并长期担任校长,为湘西地区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成绩显著。1990年获得农业部扶贫先进工作者称号。退休后,老骥伏枥,在中国稻作农业考古研究方面卓有建树,是20世纪90年代玉蟾岩古栽培稻的主要发现者之一。同时,在书法领域开创里耶秦简书法,别成一家。
1986年,张文绪培育的旱稻新品种“秦爱”获得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当时的他是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学校的科研骨干,中国遗传育种领域的佼佼者。那时,他与同是西南农学院毕业的学长袁隆平有着近乎相同的人生轨迹:同样在少年时代矢志学农;同样在六七十年代的艰苦环境下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水稻育种研究;1980到1982年,他们又同在世界一流的农业研究机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访问交流、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他们一直延续着大学时代结下的友谊,志同道合,都怀着强烈的科技兴国的梦想。
当年的张文绪风华正茂,在学生的眼里,是一位梳着大背头,风度翩翩,平易近人,业务过硬,前途无量的教授。在“六五”“七五”期间,他连续担任国家攻关课题的项目主持人,选育的旱稻新品种在北方地区推广种植已达百万亩。他有自己的实验室和科研团队,是全国最高农业学府中极具发展前景的学者之一。学长兼好友袁隆平就是他的榜样,虽然他们一个做籼型稻,一个做粳型稻,但通过育种解决中国人的饭碗问题,这个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当时,他们在水稻育种的问题上经常交流、共勉。袁隆平每次从湖南到北京办事,都会到张文绪家中做客,聊天叙旧,进行科研业务上的探讨。而一次意外的选择,却令张文绪走向了另一条人生道路。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甚至比做科研时更多,然而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被人淡忘,让他的亲人、朋友和昔日的同事、学生每每谈及都深感惋惜。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大多读过柳青的《创业史》,也知道“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但张文绪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且一生无怨无悔。
改变人生的选择
1986年,是中国扶贫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5月14日,由田纪云副总理主持的指导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的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从此,中国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正式拉开大幕。在此前的1984年,中央就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也正式颁布。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对贫困问题就有了明确的认知和特别的关注。专门性扶贫政策的出台与专门的国家级扶贫机构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扶贫工作从原来的“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根本转变。
当时,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农村部),是后来人所熟知的国务院扶贫办的前身。由于中国贫困地区基本上是以农业为主的区域,而且最贫困的群体都在农村,农牧渔业部领导深感责任重大,格外重视专项扶贫工作,在1986年年初就下发了《关于安排开展山区、贫困地区开发研究、建立示范区的通知》。作为当时归口农牧渔业部的重点高校,张文绪任教的北京农业大学也第一时间接到了通知,接受扶贫任务。从此,张文绪迎来了其人生的转折点。
1986年春季刚开学,张文绪被学校主管科研和推广工作的副校长靳晋请到了办公室,谈话的内容不是育种的新进展、科研项目和奖项申报,而是扶贫开发。没有过多的寒暄,靳晋直接而坦诚地告诉他,扶贫是中央和国务院新的战略部署,部里承担了武陵山区的扶贫开发工作,而地处武陵山区腹地的湘西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扶贫片区。靳晋以征询的口吻对他说:“学校想请你去管湘西扶贫的事情,你愿不愿意干?你是业务骨干,而且又是湘西人,学校觉得你很合适。”
张文绪1934年出生在湘西凤凰古城,在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里耶镇度过了童年时光。但是,自1946年小学毕业离开湘西到重庆之后,他已经有40年没有回去过了。面对靳晋期待的目光,那一刻,张文绪内心发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但短暂的犹豫过后,他还是答应了。
此时的张文绪,正是科研业务起势的时候,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两年访学经历让他对水稻遗传育种前沿有了清晰的把握。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历经8年,随着农业科技研究进入快车道,张文绪在国内的研究也已经有了坚实基础和拿得出手的重要成果,踌躇满志的他正一心想要在中国的稻作农业领域搞出点大成就来。
那年,张文绪刚刚50出头。在当时,50岁就当上教授,50岁就荣获科技大奖,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人生发展最顺、风头最盛的时候,再奋斗十年,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是完全可能的。但潜藏在心底多年的家乡情结,还是让他做出了选择。他想回去看看,想用自己的所学为久别的家乡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当年4月,由学校党委书记周鹏程带队,张文绪和学校的另一位干部一起赴湘西进行调研。这次调研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全部时间都是在与自治州领导探讨、协商如何参与地方扶贫的具体方案中度过,张文绪甚至都没来得及回里耶老家去看看。然而,短暂的调研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结果,学校将参与扶贫工作的重点确定为协助筹建武陵大学农林牧系,明确以通过教育扶贫的方式培养山区需要的农业科技人才,张文绪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而这个时候,武陵大学还只是画出来的一张蓝图,除了校址确定设在风景秀丽的大庸市(后来的张家界市)之外,连一间办公的房子都还没有。

20世纪70年代末,在稻田中工作的张文绪
“少小离家老大回”
同年7月,张文绪安顿好学校的实验室工作,并给刚招来的研究生孙传清(继承张文绪的学术衣钵,成为中国著名水稻育种专家)布置了学习任务之后,他第二次返回湘西开展深入的扶贫调研。这一次,他是带队者,队员包括农学、园艺、食品加工、畜牧、兽医、土化和农经等院系的8位老师。思想“前卫”、研究生一毕业就是摄影“发烧友”的张文绪,还特别请学校派了3位电教中心的摄像师随行,他想借这个机会给家乡留下影像的记录。
张文绪几乎走遍了整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桑植、永顺、花垣、吉首……一个县一个县地走,一个村一个村地看。从12岁离开湘西,他就一直生活在城市,重庆、北京,出国、回国,中学、大学、研究生,然后工作。在他心里,家乡既遥远陌生又美好亲切,他甚至曾一厢情愿地认为家乡的山村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都在发展进步,和他离开时应该是完全两个模样。然而,调研的结果完全打破了他对家乡抱持的所有美好想象。他亲眼目睹了武陵山区封闭而落后的现实,亲身感受到湘西人一如他离开时的贫困境遇,他的内心被强烈地震撼了。

1981年,张文绪(左二)在菲律宾与他的合作导师、国际水稻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植物遗传学专家张德慈先生(中)合影
在这里,有一个叫八面山的村庄。其中的一家有三个兄弟,父亲是一位转业军人。父亲用自己的转业费给家里盖了半边瓦房(另半边是草房),才勉强给大儿子娶了媳妇。父亲去世后,两个弟弟因为没钱无法结婚。哥哥死后,三弟续娶了大他十几岁的嫂子,而二哥则打了一辈子光棍。当地有一句话:“山上的姑娘,好看的进了城,一般的下了坪,不三不四的嫁给当地人。”张文绪在调研中亲耳听到这个故事,亲眼看到这个事实。二哥仍住在半边草房里,只有一张床,上面铺着稻草,一床被子,还是村里救济的。当地政府曾资助了他们一些钱,买了两头小猪,养大了卖点钱,生活才稍微好一点。但是政府也不可能每年都给他们救济。两个壮劳力,就在贫困中年复一年地煎熬着。村子不通电,不通公路,更谈不上有电话,几乎是与外面隔绝的。一次县里开会,要求这个乡派个代表参加,然而乡里收到通知的那天,会议已经结束了,因为送通知的人要走山路、走好多天才能送到。
张文绪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穷。父亲务农没有地、做生意又没本钱,仅依仗着认识几个字,有时候代人写信,有时候干些杂活,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哪里能挣钱就到哪里;母亲也只是在每年收获季节从舅舅家背回来一点柑橘换些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家里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由于父母为了挣钱东奔西走,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哥哥出生不久便夭折,而刚出生还没满月的他被放在背篓里,留给勉强有口饭吃的爷爷奶奶,父母则继续四处漂泊讨生活,几乎很少回来看他。但是张文绪是幸运的,两位老人虽然过得清苦,但坚持认为读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等他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他们就从牙缝里省出两升米,送他到里耶小学读书。他跟随学校远足活动参观了一个驻扎在村落屯田的军队,这里的人都是抗战前线退下来的老兵,他们种玉米、种白薯、养猪、养羊、养牛,自食其力、衣食无忧,因为有武装,当地的土匪也不敢侵扰他们。这在年幼的张文绪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觉得那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与平时看到的满街乞讨者、多数村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屋不遮风雨”的苦难生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爷爷在他小学毕业后也去世了,奶奶历经千辛万苦带着他去投奔远嫁到重庆的姑妈。在姑妈的帮助下,他上了中学。1952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填报的志愿都是农学专业。他的想法很简单、也很朴素,就是要种好多好多的粮食,让大家都有饭吃。这是他在幼年时就形成的对美好生活最纯朴的向往。
时隔40年,当张文绪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现实景象与往昔记忆叠合在一起,大大的问号出现在他脑海里:已经有了翻天变化的中国为什么还有这么穷的地方?而且还是自己的家乡,怎么摆脱贫穷?那一刻,张文绪坚定了投入扶贫事业的决心。他说:“促使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并无悔坚持下去的初始动力,是家乡情结,是对家乡人的情感。这是比任何外在力量都强大的力量,是任何理论都讲不清楚的。就是这个情结,这份感情,在心里发挥作用。就好像必须要这样选择,回到家乡,到武陵山区,为贫困的人民做点事情,不做就不对。”
这次调研过后,张文绪开始写文稿、做编导,将拍摄的影像资料编成一部纪录片,并起了一个很诗意的名字:《湘西漫步》。其中,与湘西优美的风景构成巨大反差的是湘西地区的贫困状貌,以及村民老乡们穷苦的无以温饱的现实。湘西人面对苦难的坦然从容、内心对美好生活的执着渴望,以及那些看不到希望沉重而忧伤的目光,深深地刺痛着张文绪的内心。纪录片的字里行间、画里画外,也深藏着张文绪深切的情感和神圣的责任。这也成为他将人生中最宝贵的8年时光投入扶贫事业的动力源泉和鞭策力量。
此后,张文绪开始了在武陵山区湘西州的定点专项扶贫工作。在《北京农业大学校史(1949-1987)》中这样叙述那段历史:“从此开始了长时期的以大庸市武陵大学为基地的湘西科技扶贫工作。”“师生发挥自己的科技专长,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武陵山区的大学梦
建设武陵大学(现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农林牧系是张文绪在湘西扶贫工作的重点。大学的筹办对于当时的武陵山区是一件大事,也是国家为改变武陵山贫困面貌的两大项目之一(另一个项目是大庸机场建设)。
建设武陵大学是时任中纪委书记李昌最早提出来的。他与张文绪一样是湘西人,毕业于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同时也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在抗战的烽火中参加革命,并多次与胡耀邦协同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是晋察冀第四纵队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任书记处书记。1953年,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李昌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70年代中期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在共和国的教育界、科技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应该说,几乎每一位从湘西走出的人,都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情感。1984年,国家划定了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武陵山区赫然在列。当年年底,已过古稀之年的李昌不顾舟车劳顿,在时任湖南省省长熊清泉的陪同下考察湘西20多天,并写出《关于尽快改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贫穷落后状况的意见》上报中央。在他看来,落后的文化教育是制约湘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而人才又是改变落后局面的重要前提。于是,他提出创办武陵大学,希望能够通过教育扶贫,培养人才,带动这里的扶贫工作。
在贫困山区创办一所大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张文绪来到湘西之前,武陵大学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建,但直到他第二次调研后的1986年秋天,武陵大学才正式搭建起工作班子。班子成员主要来自哈工大、国防科大退下来的老领导,其中搭配的自治州干部对办学并不很懂。这样,新加入工作的张文绪虽然只是农林牧系的系主任,因为“年富力强”,经常协助校长张真谋划和解决建校的种种难题,陪着这位已经66岁的前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在北京、长沙、湘西和办学地来回奔波,跑手续、协调工作,为学校招聘老师和工作人员。这些杂事、琐事虽然对刚刚创建的学校来说很重要,但总是与他想象的系主任工作完全两样,没有教室、没有实验室、没有学生,也根本谈不上他所熟悉的教学、培训之类的工作。之前和他一起来山区调研的老师们陆续离开回到学校,只有他一个人坚持留下来继续工作着,他甚至一度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动摇和怀疑。但在湘西办大学、培养技术人才、让贫困山区的人们真正脱离贫困的梦想,以及在山区调研时目睹到的家乡人的困苦生活,总是在夜深人静时闪回在脑海中,让他又重新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天上掉下“校长帽”
一年多的时间,在纷乱与忙碌中很快过去了,武陵大学也渐渐有了些模样。教学楼、宿舍楼、餐厅先后建了起来,省教委也特批了试招生的指标。正当张文绪准备喘口气,回归系主任的本职工作时,校长的“官帽”却意外地落到了他的头上。
1988年年初的一天,他到州里办事,遇到了时任湘西州委书记的杨正午(后来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老远就对他说:“老张啊,你一步登天了!”杨正午是张文绪的里耶老乡,还是低他几级的小学校友,因扶贫工作他们经常打交道,也时不时开个玩笑。但这次不是玩笑,武陵大学董事会决定让张文绪担任校长。老骥伏枥的张真校长因为身体不好,一坐车就会头晕呕吐,实在无法在山区道路上颠簸,只能向老领导李昌辞职。关于继任人选,李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文绪。事后,李昌向张文绪解释选择他的原因:一、他是湘西人,对家乡有感情;二、他是大学教授,比较熟悉大学运行的模式,这个以扶贫为目的的山区大学也需要农业科技方面的专家做掌舵人;三、他比较年轻,比其他两位候选的老同志身体好,能扛得住折腾。就这样,张文绪从农林牧系系主任变成了校长。
当时张文绪并没有意识到武陵大学的校长究竟是多高的职位。过了很久,他才从地方干部的口中得知,这个校长是副州级(副局级)干部。做了半辈子书生的他,竟然成了家乡人眼里可以和州领导平起平坐的“官”,这让他在震惊之余,更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他自己从来没有认为、也没把这个校长当作“官”,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服务于家乡人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文绪这个武陵大学校长,是湘西州从北京农业大学借来的,他的人事关系始终在农大。领导也常开玩笑说,州里是打了张“借条”的。退休后,他的身份仍然只是农大的教授,没有享受任何级别待遇。当了校长的张文绪,后路就真断了。一所初创大学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决策处理,他再也不可能像其他扶贫的老师一样,在不放弃科研主业的同时兼职做扶贫工作了。张文绪停招了农大的研究生,交了农大实验室和办公室的钥匙,原来的科研团队也各奔前程。1988年年初,他的人生完全转向了扶贫工作,彻底走上了扎根武陵山区建大学、培养人才、推广农业科技服务湘西发展的道路。

1988年,张文绪(右)和李昌先生(中)等在武陵大学合影
1988年秋,武陵大学开始正式招生。因为条件艰苦,作为校长的张文绪只能安身在新建招待所的一间客房,一床、一桌、一椅、一个脸盆架,就是校长宿舍的全部,还经常兼有办公室、会议室功能,很多学校的大事都是在这里议定的。在李昌的帮助下,国科大、哈工大的教师纷纷受聘来到武陵大学任教,张文绪也从北京农业大学聘任了一批各个领域的农业专家来武陵大学兼职。在他的努力下,先后有10多所高校的干部和专家被聘来参与管理和教学工作。武陵大学办学非常扎实,山区招来的学生们也格外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机会,学习非常用心、刻苦。省里统考时,学生成绩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排名靠前,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就此开创了一个不错的办学局面。
张文绪在担任武陵大学校长的6年多时间里,将学校逐渐引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1994年,是他任期的最后一年,武陵大学也顺利通过国家教委的合格验收,成为国家承认的大学,获得了正式办学“户口”。其时的武陵大学,已经拥有了10个教学系部,10余个大专、中专和成人函授专业,培养了2000余名各类专业人才。
武陵大学的建立源于扶贫,它的办学目标就是为改变武陵山区的落后面貌和培养扶贫科技人才。基于此,张文绪提出“面向山区、面向贫困地区、面向少数民族地区”的办学方针,并在办学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贯彻,毕业生们也成为湘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实现了办学的初衷。同时,张文绪致力于把武陵大学办成一个农业科技推广和扶贫社会服务的中转站、枢纽线。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北京农业大学等院校的很多本科生、研究生、青年教工都来过武陵大学,到湘西实习、考察、调研,进行社会实践和技术推广。教育扶贫带动科技扶贫,对湘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虽然事务繁忙的张文绪很少有机会与大家一起到乡村做具体扶贫工作,但很多事情都由他统管、协调。比如他曾争取农业部的帮扶经费,把几位北农大的老师和学生引荐到龙山县一个典型的土家族村落——坡脚村,指导当地村民发展养兔经济,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后来还成为农业部在湘西的两个扶贫示范点之一。可以说,当时湘西扶贫过程中的很多实用农业技术,都是通过张文绪和武陵大学引进湘西地区的。
机缘把张文绪推到了武陵大学校长的位置上,他便用了全副的精力来把它做好。
工作是一种幸福
张文绪当上校长不久,学校是采用边建设、边招生的方式,但由于基建经费经常不到位,事业拨款又严重不足,经常会出现无米下炊的窘境,甚至工资发放都有困难。面对心怀扶贫事业而抛家舍业到山区任教的老师们,面对刚刚招来的希望通过知识改变人生的学生们,张文绪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之前只需要关心科研成果而无需担心科研经费的他,现在身兼校长的重任,就必须去找钱,否则刚有起色的学校就可能无法办下去。于是,他放下教授的尊严,四处募捐,不断向州长汇报,找省里领导,终于从银行获得了一笔贷款,度过了难关。
困难之后是惊喜。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所贫困山区的新建大学竟然得到了一个高达9.31亿日元的“日本无偿资金合作项目”,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近乎天方夜谭的事。在这件事情上,李昌与第一任校长张真居功甚伟。早在大学筹建之初,李昌与张真便了解到外经贸部有这样一个项目,为此他们付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到外经贸部去游说,并在张文绪任校长前基本达成了意向。这个项目从确定到落地,其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期间的冷暖辛甘,只有张文绪知道。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烦恼”的幸福,要把这个近6000万元的项目经费落实到位,并分摊到各个环节中需要更加繁复的工作。实际上,项目资助主要是以日方援助先进教学和科研仪器设备为主,为此中央和省里先后追加了数百万的配套资金,需要统筹协调的事情千头万绪。期间,从日方确定援助意向、接待经贸部领导与日方专家考察,到项目具体方案设计、论证以及与日方反复沟通、商谈、招标等,再到把仪器运回学校、建设配套实验室、安装调试等等,每一项工作都需要他全力应对。直到1990年项目实施基本规划协议签订后,他又带领大家夜以继日地干了两年才最终安装调试完成。这是他担任校长期间完成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正是这个项目经费的合理运用,才让武陵大学最终度过难关,并取得不俗的办学业绩。
武陵大学在张文绪的带领和努力下,短短几年就用日本援助的科研设备建成22个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室。当时湖南省很多老牌大学都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和现代化的实验室,湖南农大校长曾羡慕地对张文绪说:“老张啊,你现在可是我们湖南省高校中的大富翁啊!”在张文绪的规划和领导下,武陵大学利用这些条件,顺利开办了多个技术性较强的专业。事实也证明,这批设备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批人才基本留在当地工作,在湘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文绪作为武陵大学的校长,席不暇暖,几乎忙成了一个陀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从大庸市武陵大学所在地到省会长沙,得坐一整天的汽车,而且多是山路,颠簸得非常厉害,路上非常危险。有一个下雨天,他乘坐的汽车差一点滑下山崖,幸亏司机经验丰富,才避免了车祸发生。那个时候,从长沙到北京,坐火车也得一天一夜。算上换车的时间,他从武陵大学跑一趟北京,基本上得三天以上,而他每年得往返好几次。
对于张文绪来说,在武陵大学的几年中,他心心念念都是办学的事情和项目的进度问题,想赶快让武陵大学发展起来。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山区人民、家乡父老的期望,对得起自己头上的“校长帽”。那几年,张文绪也是幸福的,做他认为值得的事,做他情感上深度认可的事情,再忙再苦再累,他都觉得工作就是一种幸福!

1990年,中日合作项目实施基本规划协议签字仪式(前排右签字者为张文绪)
人生无悔做扶贫
1994年,60岁的张文绪正式退休。就像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当时,李昌希望他继续留下来,湘西州的州长也找到他说:“干得好好的,别到点就退啊,再干一届吧!”但他还是很坚定地退了下来,就像他当年义无反顾地到湘西做扶贫工作一样。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挚烈,但在内心里张文绪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介书生,做校长,安排协调那些复杂的工作、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不是他所擅长的,也不符合他的本性。8年间,他觉得扶贫工作是国家的需要,是湘西的父老乡亲的需要,因为纯粹的自然情感,凭着满腔的热情,就抛开一切尽了自己的全力去做,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甚至做成了他最初想都没想过的事,他很知足。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人生总要有选择、有进退、有得失,最无悔的人生源于遵从内心的召唤,该做就做,该走就走。退休时,面对别人的挽留,张文绪说:“我觉得,够了。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的能力就这么大,能把这件事情办成了,我的这段人生就非常圆满了。再做下去之后可能就过犹不及了。”顺心遂性而为,这一点张文绪显然和陶渊明形成了某种心灵呼应。但他对曾经案牍劳形的校长经历、奔波繁乱的扶贫过往并不感到后悔。“遗憾、宽慰、不后悔。”这七个字,就是张文绪在退休后对自己扶贫生涯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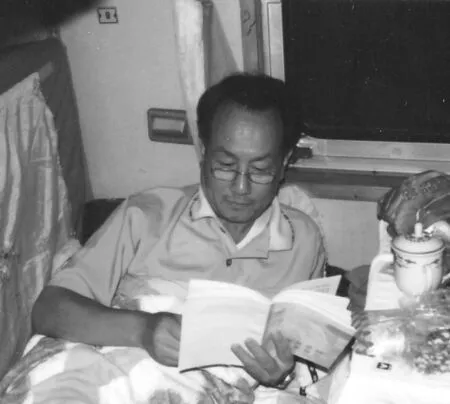
1988年,张文绪在返京的火车上读书
对他而言,“遗憾”是自己青少年阶段就怀有的科学报国主义的理想未能实现,他做农业科学家的道路因为自己的扶贫选择而戛然而止。退休后,每当他在新闻中看到学长袁隆平的水稻育种又有新的突破时,他既钦佩,又羡慕,那也曾是他的人生理想,而且也有实现的机会和可能。但他始终为自己舍弃了科研业务去做扶贫工作、建设武陵大学感到值得。因为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当地的发展注入知识的、科技的力量,湘西地区摆脱贫困和发展进步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只要他重返湘西,就时常能遇到叫他老校长的学生,听到他们对地方发展作出的贡献,这使他深感“宽慰”。统计资料表明,到张文绪退休时,整个湘西自治州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显著提高,粮食产量也上了新台阶,基本解决了该地区的缺粮问题,社会风貌也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些变化,总体上和农业部和北京农业大学对这一地区的定点扶贫有很大关联,也包含着张文绪的一份重要功劳。

1998年,退休后的张文绪在练习书法
张文绪所做的事,固然只是我们国家伟大扶贫事业中的一个阶段、一个局部,但新中国成立70余年间,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在脱贫扶贫的事业中,让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彻底解决温饱、迈向小康,让人民有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不就是由一个又一个像张文绪这样的平凡而伟大的人去完成的吗?
时至今日,有着崭新面貌和富足生活的湘西,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文绪觉得,自己有幸在正值做事的年龄,参与了国家的扶贫事业,作了些贡献,他感到很幸运,也很欣慰,虽然科研事业中断了,对他个人来说难免有些许遗憾,不过他从来没有后悔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都是特殊年代下个人的使命,我并不感到后悔。因为人生不在于你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而是在于你做了没有,只要踏踏实实做了就会有成绩,你就不会感到后悔。”
余晖未了余音袅
退休后的张文绪回到北京,时间变得充裕、自由了。然而他在享受“读书、写字、做闲事”的新人生阶段的同时,内心中依然牵挂着中国的扶贫事业和粮食问题。
原来的水稻育种研究已经中断了8年之久,不可能继续做科研工作了,但他很快就找到了另外一种与水稻结缘的方式。1995年,他收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家荣所长的邀请,希望他能参加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考古发掘,张文绪欣然接受了这次邀请。没想到这次发掘竟然发现了一万年前的古栽培稻,不仅震惊了农业考古界,也改写了世界农业文明的历史。玉蟾岩遗址在1996年和2001年分别被评为199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作为玉蟾岩遗址考古的主要参与者和“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命名者之一,张文绪充分利用自己水稻育种研究的生物学方法,科学地、无可辩驳地向世界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最早的起源地。他亲手测定的古栽培稻为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样本。
农业考古由此成为张文绪做得最多的“闲事”,而且一干又是十几年。没有论文的压力,也不用自己主持项目,不被功与名所累,只是凭着对水稻的一腔热爱。他一有机会就跟着考古队一起去挖掘现场观察、记录、研究,回来后就见缝插针地利用学校的先进实验设备测定,并把得到的数据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出来。前前后后,他与考古所的同仁们联合署名发表了30余篇论文,成为知名水稻史专家。通过10余年的辛苦钻研,张文绪完成了全国26个遗址点的稻作遗存的科学测定和研究,他开辟的古稻研究的生物学新方法,突破了传统考古观念的束缚,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同时他也多次参加国际学界的水稻会议,在国内外学术界第一次揭示出中国史前古稻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化序列。
可以说,张文绪在农业考古尤其是稻作农业史的研究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过他早期在水稻遗传育种上的成就。他用“上善若水”来比喻自己的考古经历,“至柔、不争、向下”,不求荣利、包容宽厚,以轻松的心态做闲事,张文绪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不愧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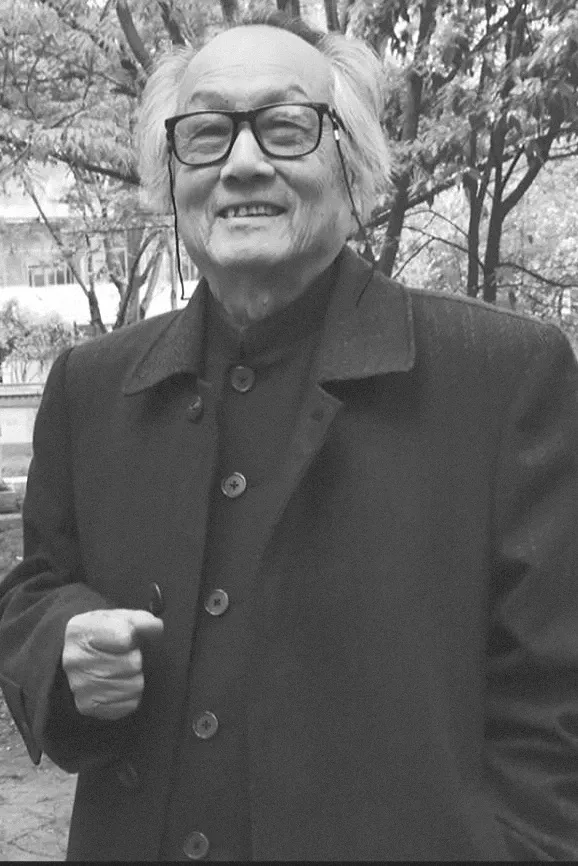
张文绪先生近照
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学长袁隆平曾应邀到学校“名家论坛”做报告,会后,专门约了张文绪吃饭,两位老友聊得非常愉快,没有人知道他们都谈了什么,每当有人问及,张文绪都会说:“谈的都是闲事。”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耄耋之年的张文绪,仍在乐此不疲地做事,但一切都只是“闲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