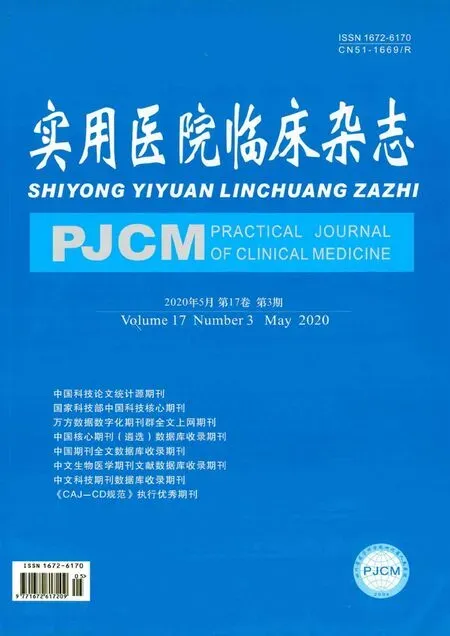真实世界研究方法在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研究中的应用
2020-12-24刘锦平
林 鹭,刘锦平,2△
(1.遵义医科大学,贵州 遵义 563000;2.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四川 成都 610072)
真实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RWS)通过对各种医疗活动产生的真实世界数据处理后进行研究、分析,更真实的反映实际诊疗环境中与疾病相关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等情况[1,2]。随着《21世纪治愈法案》的颁布,人们关注的重点再次聚焦于医疗RWS[3]。乳腺肿瘤学领域RWS报道逐渐增多。内分泌治疗作为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主要治疗方式[4,5],拥有许多RWS报道,并且多集中于近年来出现的新型药物,如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CDK4/6i)和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抑制剂(mTORi)。对于经典的雌激素受体下调剂(SERD)和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仅有部分RWS报道。这些RWS回答了在临床实践中药物的应用方式、有效性及安全性等问题。
1 CDK4/6i
Palbociclib作为首个CDK4/6i,已通过临床试验[6,7]证实了其有效性,并被批准在一二线与其他内分泌药物联用应用于HR(+)/HER2(-)(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ABC/MBC(进展期乳腺癌/转移性乳腺癌)患者[8]。临床实践证据对该药进行评价的RWS陆续出现。2018年Taylor-Stokes[9]等在美国首次进行RWS,对Palbociclib的临床应用方式及实际临床有效性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在两组(AI组或FUL组)人群中,药物应用的起始时间不同。对于药物剂量而言,两组人群中大多数能依从并维持推荐剂量,仅有少数人群需要调整剂量,且调整剂量的降幅及次数均较少。AI组客观缓解(OR)为79.5%,12个月无进展生存(PFS)率为84.1%、总生存(OS)率为95.1%;24个月PFS率为64.3%、OS率为90.1%。FUL组OR为74.0%,12个月PFS率为79.8%、12个月OS率为87.9%。由于药物联用批准时间原因,12个月以后PFS率和OS率无法获得。
该临床实践并未完全依从于临床试验中Palbociclib的起始剂量(125 mg/d)要求,这可能与实际临床中有一定比例的(16.7%)表现状态较差(ECOG评分:2或3)的患者,而临床试验中人群不足有关。对于这类患者临床医生更倾向于使用更保守的药物剂量,这也解释了临床实践中更低于临床试验[6,7]的剂量调整率。该药物证实了在临床实践中Palbociclib与AI或FUL联用在PFS及OS方面的良好疗效,但遗憾的是尚未对调整剂量原因及调整剂量是否影响药物有效性进行探究。次年,来自阿根廷的研究[10]给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与美国人群获益相当的12个月PFS率(85%)提示了在不同国家人群中Palbociclib药物疗效具有一致性,但因阿根廷研究药物上市时间原因,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数据对此加以验证。此两项RWS首次反映了不同国家Palbociclib联合AI或FUL在实际临床中药物使用及剂量调整情况,并提供了有效性的现实证据,但均未对调整剂量是否影响药物的有效性进行探究。
2019年来自Bui[11]及Wilkie[12]等的RWS表明在一二线临床治疗中,为了控制不良事件(AEs)发生,Palbociclib均存在不同类型的给药调整(剂量减少、周期延迟及剂量中断),研究结果显示:临床实践中PFS未受到剂量减少的影响(P=0.77),并且与临床试验相比获益相当[11,12]。此外研究者指出临床实践中PFS值略高于临床试验(11.0个月及9.5个月),这可能与临床实践中药物使用周期延迟而非剂量减少有关[12]。针对Palbociclib带来的以中性粒细胞减少为主的AEs,基于全血细胞计数监测AEs的发生至关重要[13,14]。对此爱尔兰[13]及美国[14]两地进行的RWS提出,在了解药物临床使用情况的同时,对Palbociclib每次使用时及前两周期使用后第14天进行全血细胞计数监测有利于更安全的使用药物。基于美国医保数据库的大样本(n=1242)RWS[15]显示,多数患者在早期治疗中会经历Palbociclib的剂量改变(剂量中断:63.5%~80.9%;剂量减少:1.9%~33.7%),而剂量变化引起的药物重复、药物丢弃会导致可观的经济成本浪费。
2 mTORi
非甾体芳香化酶抑制剂(NSAIs)对于绝经后HR(+)/HER2(-)MBC患者常为一线治疗用药,但在产生耐药后缺乏后续的治疗药物。mTORi依维莫司(EVE)作为一种新型靶向药物,已被临床试验证实对于NSAIs治疗失败患者,与依西美坦(EXE)联用比化疗可显著延长生存期[16]。但临床实践有效性的证据有限,为了明确这一问题,Li[17]等对371例HR(+)/HER2(-)NSAIs耐药后的 MBC患者进行RWS。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总人群,接受EVE组比化疗组平均年龄更大,MBC侵袭性更少。对临床实践疗效分析并且根据基线特征调整后,EVE组患者的TOT(治疗时间)、PFS及OS均长于化疗组。此项较大样本的临床实践研究中EVE组包含治疗方式较多(单用、联用内分泌药物、联用化疗药物),虽未对不同治疗方式进行单独亚组分析,但该RWS仍提示对于MBC患者NSAIs一线治疗失败后,基于EVE的治疗方式相较于化疗有更好的临床获益。
新型靶向药物相对于化疗的有效性、安全性证据对临床药物选择很重要,但遗憾的是上述RWS并未对EVE的安全性数据进行报道。两项来自意大利的多中心RWS[18,19]对此进行了回答,Riccardi[18]等提出在MBC患者中,EVE联合EXE对内分泌敏感的患者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有效且安全的治疗选择,该方案导致的AEs多为G1或G2级,在临床实践中有良好的耐受性,且少有患者(5.7%)因毒性中止治疗。Ciccarese等[19]提出在ABC 患者中,较高的EVE剂量(10 mg及5 mg)能引起患者的不耐受,而剂量不同对疗效并无影响。另一项来源于中国[20]的小样本RWS(n=75),首次在我国人群中证实EVE和内分泌药物联用的临床有效性,并且提出药物导致的AEs发生情况与临床试验类似,临床医师对重度口腔炎等AEs采取预防措施,从而降低了AEs发生率。
另外关于MBC患者单药使用EVE的临床实践提示,对于肝转移患者,EVE单用比内分泌单药治疗或单用化疗更有效[21]。对于NSAIS耐药后患者,EVE比FUL更能延长PFS(HR=0.71,P=0.045)[22]。通过回顾性索赔数据库的大样本RWS[23](n=925)提出,基于EVE的疗法比化学疗法能显著降低医疗服务成本,并且占用更少的医疗资源。
3 SERM
相关文献报道单侧乳腺癌确诊后10年内对侧乳腺癌(CBC)的累计发生率约为5%,并且提出ER(+)乳腺癌发病率增加将引起CBC发生风险增加。虽然临床试验已证明他莫昔芬(TAM)和AI能降低CBC的风险,但对于现实世界中治疗关联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尚不明确[24]。为了回答这一问题,2017年来自美国[25]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对乳腺癌患者选择TAM和AI治疗与CBC风险关系进行RWS。研究纳入了7541例单侧原发性浸润性乳腺癌患者,对药物持续使用时间以及使用后停药时间发生CBC的风险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当前使用及曾经使用TAM其CBC风险均随TAM治疗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在当前使用者中RR=0.76,使用4年后RR=0.34。在曾经使用患者中,TAM停用5年以上RR=0.85,虽然保护作用稍弱,但仍旧存在。亚组分析中,ER(+)人群中 TAM治疗持续时间增加能明显降低CBC风险(RR=0.68),这种保护作用对停药人群仍适用(<3年:RR=0.79;3-5年:RR=0.83)。并且通过对CBC累计发病率的评估分析发现,在ER(+)的乳腺癌患者中,持续服用TAM 4年以上,能预防 10年内3%人群及15年内4%人群发生CBC。但在ER(-)人群中并不存在这种保护作用(RR=1.97)。此外,对未使用TAM但接受了AI的患者研究发现,AI治疗也能降低CBC风险(RR=0.48),但因数据量较少,未能更详细的评估风险内容。该临床实践基于真实诊疗环境的大样本队列研究提出TAM使用能对CBC产生持久性保护,并且与使用持续时间正相关。此外也证实这种保护作用存在于ER(+)人群而非ER(-)人群。为临床使用TAM提供了真实世界数据支持。
4 SERD
FUL作为一类SERD,广泛用于ER(+)ABC患者,而对于这类患者进行生存风险评估能影响后续治疗选择,但少有基于大型数据库的生存危险因素报道[26]。2019年Kawaguchi等[27]基于Safari试验的RWS,纳入2011年11月25日至2014年12月31日开始进行FUL治疗的1031患者,通过收集临床预后数据,对影响OS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总人群中位年龄为60岁,中位OS为7年。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年龄越小、FUL使用越早、FUL持续使用越长(3年) 、既往未使用姑息性化疗以及 PgR阴性均与OS延长相关。此外,单因素分析中组织学或核分级越低也与OS越长相关,但在接受FUL一线治疗人群中,内脏转移和HER2状态不影响OS。在亚组分析中,较低的组织学或核分级的患者与较长的OS显著相关,复发性转移患者的DFI(无病间隔)与OS无关。通过这项基于大规模回顾性临床试验后续的RWS证实了更年轻、FUL使用时间更长、组织学或核分级更低、既往未进行姑息性化疗与OS延长正相关。并提出在临床实践中医师倾向于对内分泌耐药及预后不良的患者选择姑息化疗,这或许能对未选择姑息化疗患者有更长的OS进行解释。同时,实际诊疗中医师术后积极随访以及完善的医保覆盖能带来比临床试验更长的OS(3~5年)[28]。不同的是,临床试验[29]提出较长的DFI和无内脏转移与ABC中较长的OS呈正相关,但这些因素在临床实践中被证实与OS无关。
综上所述,不同于既往规范的试验性研究为内分泌治疗提供证据,日益增多的临床实践研究为我们提供现实诊疗证据,让研究者在了解到内分泌干预方式的临床实际应用情况同时,对其药物使用的有效性、安全性进行验证,也在临床试验研究基础上进行研究结果补充,从而为临床决策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支持。不过虽然现阶段研究者对乳腺癌内分泌治疗的RWS广泛关注,但仍有部分内分泌药物如卵巢去势类药物及AI类药物则鲜有RWS报道。相信未来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加入,通过对高质量的临床病例信息进行更高效的提取、分析和总结,最终为乳腺癌内分泌干预方式的标准化、个体化选择提供更科学的指导[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