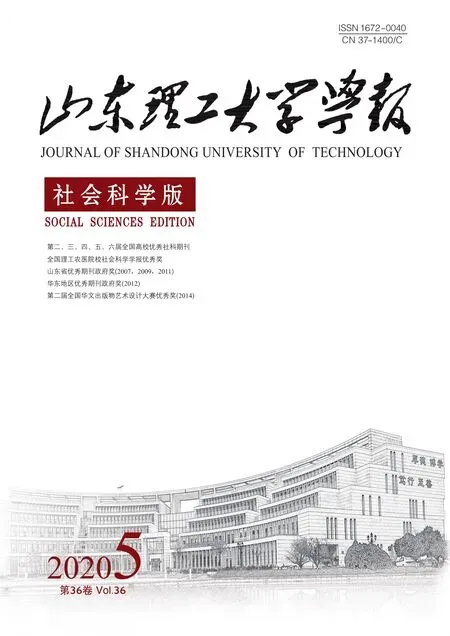梅兰芳京剧艺术在美国的接受
2020-12-24李庆本李彤炜
李庆本,李彤炜
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第一次被西方主流观众大规模地审视与讨论,也代表梅兰芳和他的京剧艺术开始走上世界舞台,走进中西戏剧交流、碰撞与建构的视野中。谢柏梁曾说,“真正使中国戏剧连贯而全面地推向世界,并使比较戏剧研究与演出实践相与遇合的大家,还得要数梅兰芳博士”[1]。
从纵向的京剧发展历程来看,梅兰芳不仅“把京剧艺术的发展推到一个高峰期,也是我国戏曲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2]。他继承“新三鼎甲”部分遗风,又开拓了自己全新的梅派艺术,唱腔、舞技、音乐等方面都达到高超水平。再加上他本人力求创新,愿意尝试与改变,如他改进乐器、编排“时装新戏”与“古装新戏”,让旦角艺术异军突起等,均为中国京剧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响力也在当时的中国可见一斑,谈京剧是绕不开梅兰芳的。由于梅兰芳个人在京剧艺术发展史甚至戏曲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他的跨国演出就更具代表性与深远意义。
从横向的跨文化传播、交流来看,梅兰芳1930年访美跨越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空间界限、以种族为基础的文化界限,把舞台变为中西戏剧与文化碰撞、汇聚的场所,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一次经典案例。梅兰芳成功访美,不仅让京剧艺术在世界艺术版图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更使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光彩;西方主流社会也开始关注并了解、接触中国艺术与文化。
一、美国普通观众对梅兰芳演出的反应
赴美演出前,梅兰芳虽在国内拥有相当高的艺术地位,也在赴日演出的好评中收获自信,但由于当时中美双方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即彼时传统文化在中国国内大受冲击,中国知识分子、媒体对京剧艺术也大加挞伐,故美方并不十分看好此次访美。在这种情形下,梅兰芳排除种种干扰,毅然于1930年1月18日离沪启程,于2月8日到达纽约,开启美国之旅。他的演出剧目有:《汾河湾》《青石山》《贞娥刺虎》《贵妃醉酒》《芦花荡》《打渔杀家》《霸王别姬》等,还有舞蹈,如“羽舞”“杯盘舞”“剑舞”。
《汾河湾》是梅兰芳在纽约演出的重要剧目之一,为了让名字更直观,其被翻译为《可疑的鞋子》。据当时的一些报纸记载,当剧目表演到回家后的薛仁贵看到妻子柳迎春床下有双男性鞋子这一细节时,薛仁贵表现出疑窦丛生、满腹狐疑的情态,这时候观众的反应是——很多美国人笑了[3]。这说明美国观众看懂了剧情,才会在关键时刻产生相应的反应。有一位老太太对梅兰芳说,“你生得这样好看,薛仁贵一定非常爱你,他赔礼的时候,就是你再多一会儿不理他,他一定想法子来央告你,你往后最好不要轻轻儿的就回心转意答应了他!——非难难他不可”[4]108;还有观众看完后说,“当柳迎春生气,她丈夫陪罪告饶的时候,她又想答应,又想为难他,又恐怕太激烈了对不起他,并且恐怕二人若因此真伤了感情也不好,所以虽然在气头上,就赶紧应允了。这种心情,同美国女子真是一样。梅先生并不是女子,怎么能把女子的心事揣摩得这样到家呢!”[5]。
《刺虎》一剧深受美国观众喜欢,它本为昆曲《铁冠图》的一折,描述的是前明朝宫女费贞娥为报家国之仇,假扮公主与李自成结婚,意图行刺他。但李自成将费贞娥赐予了自己的虎将李固,剧中费贞娥在与李固的新婚之夜,假意与他饮酒,将他灌醉,然后把李固刺死,自己也随之自杀身亡。当剧情表演到费贞娥穿着新娘服饰,在李固酒醉拔剑向他刺去时,观众席上有很大的“啊……”的惊呼声传来。观众反应激烈,“有人跳起来叫好,男观众使劲跺地板,女观众擦眼泪,唏嘘之声不绝于耳。《刺虎》的反响是最热烈的,他们都在这里赖着不走,同时没命地鼓掌”[5]。一位老太太说,“费贞娥替他的皇帝报仇,思想真是高超,令人佩服。看她当着一只虎的面就笑,一背脸就恨,以那么年轻可爱的小姑娘竟有这么大的心事,又悲伤他的皇帝,又要敷衍他最恨的仇人,她那心里不晓得多难受呢!梅君也真能做到家!”[4]108
还有观众讲到《贵妃醉酒》,“《贵妃醉酒》让我好气,皇帝约会在一处饮酒,等人家把地方打扫干净了,酒菜也预备齐了,可皇帝找别人去了,杨贵妃怎么能不难过呢?”[4]109
观众的反应与评论基于对剧目剧情内容的理解,他们跟随剧情的发展,容易沉浸在一些情节中,为人物角色发声。梅兰芳在谢幕时激动地说,“谢谢亲爱的美国观众,谢谢你们的爱护和理解,你们看懂了我的戏”[5]。停留在剧情理解上的评论与态度,是接触与欣赏一门艺术后最直观、也是最表层的反应。
很多普通观众总结梅兰芳扮演的女性形象,将这些女性形象和中国整体女性形象相联系,并同自己以前认知的中国女性进行对比。“以前听说:中国女子不做什么事,整天只是在家里伺候她丈夫。一看梅先生的戏,才知中国女子有本领、有道德的极多。比如:柳迎春是那样地能吃苦,却又那样能宽容别人;费贞娥是那样忠烈、有计谋;花木兰小小年纪竟能大战沙场;廉锦枫又是那样地孝,竟敢潜入深海,为母亲摸参。我们看戏的人都爱死了她们”[6];还有人说,“《打渔杀家》里的肖桂英是那样孝顺、勇敢,帮着她爹爹办事,还尽量服侍、安慰爹爹。由此可知,从前所听的话,都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梅先生”[6]。
梅兰芳在不同京剧剧目中塑造的不同人物角色,使美国观众对中国女性形象有了更深的认知与思考。从观众的话中,我们明晓,在大多数美国人的认知里,中国女性自身没有多少独立性,只是一味听从父兄、服从丈夫,完全是依附性的社会角色。而梅兰芳的费贞娥、柳迎春、肖桂英在他们眼中展示了中国女性身上赋含的真实品格,她们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有充沛的情感表现,丰富了中国女性在美国观众心中的整体形象。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还能发现艺术传播的更大力量,即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帮助改变他民族对本民族的误解与偏见,重塑他民族对本民族的认知。
普通观众在理解剧情内容的基础上,还直观地看到了梅兰芳舞蹈动作所呈现出的“美”。“我看了几回戏,总没看见你的手,看了《打渔杀家》,才见到了!我简直没见过这么美的手!我盼望你以后演戏务必穿短袖,好让你那美丽的手永远露在外面”[4]109。手势是梅兰芳表演艺术中的一大特点,他在表现程式化的动作与舞蹈时,都会运用特定的手势,再加上他本人手指纤长,被观众所注意理所应当。“梅兰芳的手所展现的美态被美国人津津乐道,一时成为女孩子们爱慕的对象,她们入迷最深的是他的手指,诸如‘摊手’‘敲手’‘剑诀手’‘翻指’‘横指’,都成了她们模拟的对象。电车上、课堂上、工厂里、舞场上,所有女孩子的手都以模仿梅兰芳的手为荣”[3]。甚至有人评价梅兰芳的手,“那是手指吗?不是,是一朵绽放的莲花”[3]。梅兰芳本人的姿态也备受青睐,有观众一直关注梅兰芳的扮相、动作,惊叹于东方艺术中竟有如此美丽、优雅的女性扮相。
综上所述,美国普通观众对梅兰芳的接受,还只集中在对基本剧情的探讨与理解之上,他们遵循的是美国固有的现实主义戏剧的观看模式,以情节为主。我们发现,让普通观众看懂剧情对梅兰芳的成功有很大意义。观众同时接受到一些中国京剧艺术与美国戏剧艺术的不同艺术特点,即中国京剧艺术注重对美、意境的呈现。
美国普通观众不仅有外在感官上的审美欣赏与认知,他们能够欣赏并喜欢梅兰芳京剧艺术,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看懂与理解剧情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情感共鸣。
齐如山的《梅兰芳游美记》提到《刺虎》一剧最受欢迎,“‘叫帘’竟到了15次,这种情形在美国并不多见”。一位旅居巴黎的老画家在梅兰芳演出期间正好在纽约办展览,他非常希望能够为梅兰芳做一张画像,画的就是他最喜欢的一幅《刺虎》戏装像[7]。斯达克·杨的两篇长篇评论中,几近通篇都没有脱离《刺虎》一剧,“我最爱看《刺虎》……我拿他来举例是因为它是梅兰芳目前上演的剧中最完整而令人赞叹的节目,比起那出关于一只鞋的戏,在表演上较少自由灵活或轻松感,而在风格上却更为壮丽严谨。费贞娥是个宫女,代替公主嫁给虎将……结尾是她用宝剑自刎,倒地而亡。我激动得浑身发抖,怪就怪在这种激动比我多半能从任何对死亡和恐惧仅是摄影般的描绘所感受到的那种激动强烈得多,而同时又显得更朦胧、更纯净”[8]。戈赫·沃伦认为,《刺虎》是伟大的悲剧表演,“表现了一个女人天然的恐怖,她支撑着自己去做一个英雄杀手,看着敌人的血和身体,最终只能选择自杀”(1)George C.Warr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30(5).参见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
他们为什么可以在《刺虎》中找到共鸣点并异常感动,而相反,梅兰芳一开始演出过的《晴雯撕扇》就反响平平以至于此剧目后来被删除呢?其实,关于《刺虎》一剧在美国备受好评,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悲剧情节的吸引力。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悲剧的六个组成部分中,情节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悲剧定义中强调的是戏剧行动。悲剧要力图使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使感情得到宣泄,通过“眼泪、唏嘘、紧张”使痛感转化为快感。《刺虎》一剧在美国深受欢迎,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亚里士多德认为使观众形成怜悯和恐惧的心理状态,在于“发现”和“突转”。拿《俄狄浦斯王》来说,科索沃斯的王子俄狄浦斯成年之后,听神说他会杀父娶母,因此逃离科索沃斯,在前往忒拜的路上,因争路杀死一个老人,后猜中人面狮身谜语成为国王,然后娶了王后。当他的身世一步步浮出水面时,“突转”来了。所有冲突随即爆发,俄狄浦斯自己刺瞎双眼,外出流浪,悲剧性的结局势不可挡,更凝结着之前剧情中所有的情节推进,好比急流、瀑布奔腾而下,人们就在这凝聚的“突转”中感受到了一吐为快、直抒胸臆的痛快淋漓之感。《刺虎》一剧就具备“发现”与“突转”的特征,费贞娥是一名宫女,身背国仇家恨,她假扮成公主欲嫁给李自成,意欲随后趁机杀死李自成以报仇。但事情并不能遂她心愿,她被李自成赐予了自己的“虎将”李固,这让费贞娥无奈、惆怅,剧情的“突转”就来自于费贞娥与李固结婚。但“突转”并未结束,之后费贞娥下定决心刺死李固。于是在新婚之夜,她开始了一系列“表演”。她假意殷勤,故意灌醉李固,下一层“突转”也在此刻爆发,不知情的李固被费贞娥灌醉,随后被其用剑刺死。本以为李固死后,这层突转结束后剧情走向会回归平静,但之后的结局也具有“突转性”。只是一介女流之费贞娥自己走上绝路,她以为大仇已报,只能自杀。至此,剧情完全结束。《刺虎》一剧紧缩凝重的爆发力产生的戏剧效果,与《俄狄浦斯王》动人心魄的情节、结果有不谋而合之处。它迎合了西方观众的口味,是因为它不同于许多其他情节起伏小、冲突矛盾少的中国戏曲,而有着如同《赵氏孤儿》一般为家国复仇强烈之恨的中式剧情,更多饱含的是一个弱女子没能杀死李自成的痛感、最后除掉李固的快感以及无奈自杀的深切悲哀。该剧不仅带给观众家国之情,更有作为一名女性身上背负的沉重与女性本身柔弱之间的冲突。这部剧呼应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一个人在舍生取义决定中的痛彻心扉与无限崇高是通过“发现”与“突转”的剧情实现的。
其次《刺虎》与西方悲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有契合之处。《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和赫克托耳为国大战,普罗米修斯为保护人类免遭厄运而被宙斯折磨,这些都属于悲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而中国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建立在伦理文化对英雄人物的羁绊和精神驯化中的,《汉宫秋》的王昭君在国家危难之际孤身入藩,随时准备牺牲个人性命以维护国家利益;《赵氏孤儿》的程婴为报答赵朔恩情牺牲自己儿子救出孤儿。主人公表现出了为伦理和谐与道德完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费贞娥的报仇与自杀也是这样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她为了国恨家仇,必行此举。西方比较喜欢以高举的利剑去开辟继续往前的道路,《刺虎》表现的是一个女人的强烈的战斗精神。
再次《刺虎》激起了美国观众的崇高感。布拉雷德在《论崇高》里讲过,崇高的产生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否定,人们似乎感到压抑、困惑、震惊,好像有什么无法接受、理解、抗拒的东西在起作用。接着是肯定阶段,那时那崇高的事物无可阻挡地进入人们的想象和情感,不自觉地,被打破了自己平日的局限,而飞向崇高的事物。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极痛苦地杀死了两个儿子,《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主人公是家族仇恨的祭品,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韩厥、程婴等人为救孤儿不惜献身,关汉卿的《窦娥冤》成了丑恶势力的牺牲品。梅兰芳的《霸王别姬》中虞姬痛苦地自杀,《刺虎》中费贞娥也在复仇完毕后同样痛苦自杀,所以也就引起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怜悯与恐惧”。中国戏曲艺术追求的不是“怜悯”与“恐惧”,而是在一定的情感节度里给观众心灵的抚慰和情感的稀释。那么怜悯与恐惧是什么,亚里士多德曾说,“怜悯是由不应当遭受的厄运的人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9]。人之所以产生怜悯是因为悲剧主人公是无辜的人,之所以产生恐惧是因为悲剧主人公是同我们一样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博马舍在其剧作《欧仁妮》的序言《论严肃戏剧》中阐述过,若对一出悲剧中的人产生感情,原因可能不是因为这些人物是帝王、英雄,而仅仅因为他们与我们同在,都可能是不幸的人。真正的内心兴趣,真实的感情与无奈是在人与人之间产生的,而不是人与帝王之间。我们看《刺虎》中的女主人公费贞娥,为什么她的角色是一位宫女,而不是真正的公主。这样的安排设计就是让费贞娥的身份与每一个普通人的社会角色相似,本是一个极为平凡的女子却只能这样无奈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与命运,在中国人看来,她的死符合道德伦理的回归;而在美国人看来,或许她的死就是她自我选择下注定的命运。
美国观众在对《刺虎》的审美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东西,而一件艺术品越是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表达出人类存在的普世价值,便越具有更高的本质符号价值。跨文化理解要面对文化差异性,更要找到进一步跨越文化差异性的方法与途径,找到人类共同生存的价值追求。梅兰芳在美国演出之所以获得极其热烈的反响,首先是因为其与美国文化存在相通之处,产生了共同与普遍的作为人类共同生存境遇的东西。
二、文化学人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接受
梅兰芳访美演出引发了美国文化学人的广泛关注,他们包括戏剧评论者、学者、文艺界的艺术家、剧作者等。笔者收集梳理了发表于报纸、期刊和著作中的相关文章,借此分析美国文化学人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接受情况。美国普通观众从梅兰芳表演中看到的是情节的共鸣,外在的身体扮相美、姿态美,剧评人、学者的关注焦点却与普通观众并不完全一致。
第一,美国评论界对梅兰芳京剧艺术的评价与反映,最常使用的词语莫过于“古老”与“异域”。“古老”代表时间上的遥远,历史悠久;而“异域”代表空间上的阻隔,距离遥远。梅兰芳在纽约首演后,2月17日美国的多篇评论文章中都有此观点。两篇文章中用了“ancient”一词,其他文章使用“old”或者“ripeness”来表达传统、古老的含义。玛丽·沃特金斯在文章《梅兰芳吸引了最多的关注》中说:“他的演出超出了西方观众的经验和理解,这门古老与精妙的艺术……”[10]阿瑟·卢尔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中谈到“这种完美的艺术,充满异域风情,可以在整个晚上吸引美国观众”(2)Arther Ruhl.New York Herald-Tribune,1930(2).参见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纽约晚报》称,“这是东方最精致和复杂的艺术”(3)Gilbert Seldes.New York Evening Graphic,1930(2).参见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他们认为,象征遥远的古老、异域的东方京剧艺术也代表着神秘与好奇。
还有评论者认为,“古老”的京剧艺术有深厚的传统根基,代表一种成熟的、永恒的艺术形式,对比之下,本国戏剧毫无历史可言。显然,这个来自中国传统根基的艺术形式,在一些评论者眼中并不是野蛮、幼稚与低级的。评论者使用“finished”一词来陈述此观点,剧评家罗伯特·里特尔在《纽约世界》中说,“看梅兰芳的戏剧,就像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古老的、仙境的世界……我们自己的装扮、动作就像是来源于昨天”(4)Robert Little.New York World,1930(2).参见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文艺评论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纽约时报》中说,“梅兰芳的表演,犹如中国古瓷瓶或挂毯那样优美雅致,……你还会依稀觉得自己不是在与瞬息即逝的感觉相接触,而是与那经过几个世纪千锤百炼而取得的奇特而成熟的经验相接触……它在一些地方像古老的神话一样永恒、和谐”(5)Brooks Atkins.New York Times,1930(2).参见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江棘认为,1930年的阿特金森好像并不自信于成年人一定有资格去训斥、管教与开导这些所谓的“稚童”。《奥尔巴尼报》称,“尽管梅先生的艺术遵循着一种古老的模式,但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6)Gilbert Swan.Albany Press,1930(3).参见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
第二,剧评人、学者不仅仅关注外在的姿态、扮相“美”,更关注梅兰芳本人的艺术表演才能。他们能观察到梅兰芳表演中的诸多细节。“他的嗓音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媒介,表达了柔和、响亮而富有戏剧性的音色;他控制肌肉的能力基于舞蹈和杂技的训练;面部表情准确提炼到中国优秀雕像中所见到的谨严而纯净的地步;两只眼睛比一般中国人的稍大些而极富表情;两只受过严格训练的手十分纤细,能在传统和复杂的动作中灵活地应用”[5]。吉尔伯特·赛尔迪斯认为,“他有卓越的身体素质,能轻松掌控身躯,眼睛和手很灵活,将自己沉浸在角色中,呈现了一场完整的表演”(7)Gilbert Seldes.New York Evening Graphic,1930(2).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约翰·梅森布朗在《纽约晚邮报》中指出“梅的假音抑扬顿挫,手势与身躯富有准确性,眼睛富有敏感性”(8)John Mason Brown.New York Evening Post,1930(2).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Tientsin,1935.。惠特尼·博尔顿认为,“梅兰芳的表演在优雅、动作、舞蹈与面部表情上接近完美”(9)Whitney Bolton.New York Morning Telegraph.1930(2).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Tientsin,1935.。罗伯特·里特尔认为“梅兰芳集演员-歌唱家-舞蹈家为一体”(10)Robert Little. New York World.1930(2).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评论家们从京剧表演中看到了表演者融歌唱、舞蹈、表演于一体,并发现京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这种中国艺术未必包容人类一切经验在内,但作为戏剧艺术却是完整的,意思是说它寄去了这种特殊艺术的一切手段,包括了表演,道白,歌唱,音乐,广泛意义上的舞蹈,形象化的舞台装置,最后还包括观众在内”[10]。
第三,剧评人、学者从梅兰芳表演中洞察到,中国京剧艺术只服从于艺术性的目的。他们对比当时正在西方盛行的现实主义戏剧,现实主义戏剧的主旨在于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反映生活本质,批判现实。而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戏剧似乎对现实生活并不感兴趣,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故事大多数来自中国古代的王侯将相、民间生活,服饰、舞蹈等也与现代生活并不相同,均来自于中国古代。“目前这次演出成为一次大事并且值得我们重视,主要是因为它纯洁而完整,远远超过任何西方戏剧中的东西……这种中国戏剧的纯洁性在于他所运用的一切手段——动作,面部表情,声音,速度,道白,故事,场所等等——绝对服从于艺术性的目的,所以结出来的果实本身便是一个完全合乎理想的统一体,一种艺术品,绝不会让人错当作现实”[8]。这是斯达克·杨的一段评述,他在文章中使用了“pure”一词,梅绍武将其翻译成“纯洁的艺术”,但笔者认为斯达克·杨想要表达的是纯艺术,即完全不受现实等其他条件制约的艺术形式,强调作品的主观性,只服从于艺术性的目的。
艺术家、创作者不像剧评者一样,综合、整体地感知这门艺术的美学原则、艺术形式,他们更多地是站在自己创作的领域与角度去欣赏梅兰芳的表演。舞蹈家们更关注舞蹈,剧作家更关注戏剧表现形式,他们倾向于从细节着眼,观察梅兰芳表演中是否有与自己创作相通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以借鉴。这是创作者们在审美过程中独有的特性。
舞蹈家从梅兰芳京剧艺术中看到了更多舞蹈表现的细节,诸如动作、装饰,还会联想到自身的舞蹈创作。玛丽.瓦特金斯是一位舞蹈演员,她的文章《梅兰芳吸引了最多关注》发表于《舞蹈杂志》,“梅兰芳是中国最顶尖的演员和舞蹈家……但我只想谈论这出戏里《青山》的舞蹈与《霸王别姬》的剑舞。第一场舞由好几个人完成,他们都参与到身体像狐狸般柔软的美丽女性的表演中。在这场假装决斗的舞蹈带来了高超的技巧把控,年轻男人将两个流苏装饰的魔杖玩儿的那样好,使观众们震惊……应该说,我们的权威是肖恩先生,他早期就在中国见过梅兰芳,通过特殊的表演学习过梅兰芳先生的艺术,他应完全承担起对中国舞蹈的介绍。然而,他是很成功的,今天梅兰芳的表演证实了肖恩先生的地位”[10]。威廉·波利索是一位杰出的美国舞蹈家,他认为梅兰芳的舞蹈比西方舞蹈高级,“他的表情极富魅力,可以熟练运用一系列舞蹈规则与传统,绝对放弃了独创性”。
尤金·奥尼尔也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他在观看后称,“原来‘旁白’这一手法在中国戏剧中已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洛杉矶考察报》1930年5月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听见“旁白”》,“尤金·奥尼尔创造了当代戏剧的狂热,他介绍的旁白和奇怪的插曲,中国伟大的演员梅兰芳解释道,这种阐明情节的手法,作为京剧的主要组成要素之一,早已存在几百年的历史了”(11)“Asides”Heard in China for hundred of years.Los Angeles(California) Examiner,1930(5).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多次观看梅兰芳表演的美国独角戏大师露丝·德雷珀女士说,“当初我创‘独角戏’的时候,就拿定主意不用背景……这次看了中国戏,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国戏早就完全用这个法子”。
梅兰芳1930年的跨文化表演,在美国文化学人的眼里,已经演变为内在审美。我们不能将早期美国土地上出现的中国剧团与梅兰芳此次演出进行比较,梅兰芳的表演走进了美国的主流观众,如同文学作品被翻译一样,获得了被理解、被审美、被阐释的权利。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解读者都是基于自己的前理解来理解文本、创作,必然会发生意义的变迁,只要不是知识型的错误,对意义的多重理解都是应该的,也是必然。而这个阐释的价值与可以被探究的意义就在于,它蕴含了多重理解的可能性,所以,对于阐释是否正确并不重要,我们可以试着探讨为什么这样阐释,以及阐释背后的意义。
美国文化学人看到了中国京剧艺术的一大重要特征——程式性,不仅如此,他们对程式化风格的认知很接近其本质特点。程式化动作来源于现实生活。“这种中国戏剧,就跟任何其他戏剧一样,总是跟基于相似性,跟基于我们所见到的人民生活和我们所观察或向往的世界的真实情况,甚至它的程式规范也主要是场所或活动的是实际情况予以风格化的典型”[8]。它没有照搬现实,而是现实世界的提炼、升华与变形。“自然界里的一片叶子、一束花朵、一只鸟、一只手、一件斗篷,都被观察得极为准确精致,同时我们也对它们所具有特征的细节所呈现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色彩缤纷的标志感到惊奇”[8]。程式风格可以自由表达无数思想感情,促进观众想象力的萌发。斯达克·杨认为,“程式并不等于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创新中进行美的创造……程式规范中有细致真实的细节,梅兰芳反而受到的约束更少,表现更自由”[8]。约翰·梅森布朗在《纽约晚邮报》的短评中说,程式化风格“在情感表现的选择上是无限的”(12)John Mason Brown.New York Evening Post,1930(2).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Tientsin,1935.。戈赫·沃伦在《旧金山纪事报》中称,“梅兰芳的力量超越了这种来自于百年实践的程式化风格的限制,能够更灵活、柔韧地掌握,自由表达”(13)George C.Warren. 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30(5).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布鲁克斯·阿特金逊说:“你也许会一时痛苦地想到,我们自己的戏剧形式尽管非常鲜明,却显得僵硬刻板,在想象力方面从来没有像京剧那样驰骋自由。”(14)Brooks Atkins.New York Times,1930(2).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程式性特征能够表现形式美。斯金南在《联邦》中说,“除了新颖、好奇之外,梅兰芳的成功归功于两件事:有着深厚传统根基的艺术可以传达人类普遍的情感;几分钟的完美表现是一种极具规律性的美”(15)R.D.Skinnen.Commonweal,1930(3).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威廉·波利索说,“梅兰芳的姿势、水袖等表达策略以及人物角色中的人性美都是‘美’的内涵”。
戏曲表演程式化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物体与景象,是对生活化动作的抽象式表现,可以表现不同含义、故事、情景、人物,表达不同思想感情,激发观众想象力。虽然具有一定规范,但演员能在熟练运用的基础上灵活性、创造性地发挥,达到不同艺术效果。美国评论家们从梅兰芳京剧表演中抓到了京剧、甚至是中国戏曲程式化风格的本质,这是难能可贵的。
许多剧评者还将程式化风格与西方象征主义联系起来。象征主义是20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反现实主义戏剧原则,象征主义相信戏剧不应当上演世俗的、日常的活动,而应表演存在的神秘和人类精神的无限品质。象征主义提倡用符号性的图像而非具体的行动与观众交流,通过一些暗示性的语言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世界连接起来。特点是采用象征、暗示、隐喻等表现手法,否定真实,强调直觉与幻想。戏剧目标不是说一个故事而是营造氛围和情绪[11]。
美国评论者认为,京剧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戏剧有相同点,即程式化的虚拟性动作具有暗示性,而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也是象征、暗示、隐喻。玛丽·瓦特金斯说,梅兰芳的表演“将技巧熟练、优美机敏的舞蹈融合在象征主义的表现中,近于完美”[10]。斯达克·杨说:“至于其中许多程式规范和象征,我发现它们像文字一样具有象征性——字除非你认识,否则当然不解其意——都由于它们的含义和联想而使其本身趋于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例如弯身进门,某些时刻由于感情激动而用袖遮脸,这些象征性物件——装饰性的马鞭、尘拂和行头的某些部分——我发现一旦为了取得完整效果而要求精确就出现惊人的精确。” 程式化表演代表思想、动作、客观物、语言、声音,在他眼里,这是一种象征化的符号。阿瑟·卢尔认为“中国古老的文化在这种形式主义中走的更远,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表面上看到了什么,而是这些程式化中表现的姿态与手势暗示与隐藏着怎样的感情与动机”(16)Arther Ruhl. New York Herald-Tribune,1930(2).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盖尔·波登1930年4月1日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中国演员赢得了公主剧院的赞美》,“程式化表演风格可以轻易表现角色,而写实主义为了跨越角色却在进行过度表演;梅兰芳的声音、动作、细节都是一种暗示;‘像是去寻找一幅美丽的画’,让你更欣赏东方艺术”(17)Gail Borden. Chinese Actor Wins Approval at Princess Theatre.Chicago Daily Tribute.1930(4).出自 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1930年5月14日《加州河滨新闻报》的一篇文章称,“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舞台上发展到如此成熟的地步”(18)Riverside(California)Enterprise,1930(4).出自P. C. Chang.Mei Lan-Fang in America:Reviews and Criticisms[M]. Tientsin,1935.。
我们认为,将京剧的程式化与西方象征主义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恰当的。这是明显的跨文化“误读”。当时也有美国评论者看到了梅兰芳京剧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区别,例如,斯金南就明确地指出:中国戏曲传递的是普遍的动作与情感元素,而象征主义在“不同物体表达更多含义、更多思想感情方面走的更远”。斯金南发现,西方象征主义由于情景的不同,一种物体可以在不同情境下表达多种不同的含义,而中国戏剧的程式化风格从真实的模仿中提炼,一种物体大多只能表达一种含义,例如,马鞭只能代表前面有马的存在,象征主义却可以随时变换。
然而,大多美国文化学者的确是基于他们的文化“前理解”,通过西方象征主义来理解中国京剧的程式化的。他们对梅兰芳京剧艺术,往往会基于本国文化艺术的立场来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由于这种审美判断融合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元素,便很容易成为“第三种文化空间”,就往往会使欣赏者脱离本民族文化的束缚,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化空间进行审美观照,从而形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跨文化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