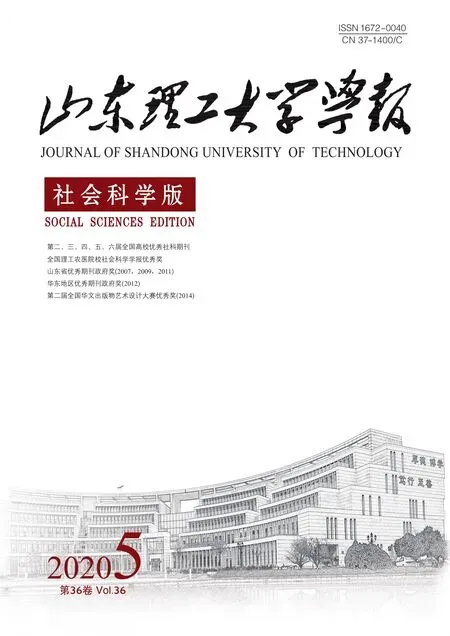论李煜词的美学品格
——“神秀”
2020-12-24张玉霞
张玉霞,马 健
一
李煜是南唐末代国君,著名词人,世称李后主,与其父李璟在词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后世有不少人称其为“词帝”,对他的创作给予了高度认可。李煜早期的词作受花间词派的影响较大,因为生活环境的缘故,其早期作品还未能摆脱花间词派那种题材狭小、意象繁多、富丽华美的特征,多描写宫廷宴乐歌舞、男欢女爱等内容。虽词作整体形象生动,却不及后期词的“真”与“神秀”。历代对其词作的讨论,也多以他后期作品为主,重点剖析他后期的词作,进而说明他这一时期作品中的“神秀”特质。“神秀”作为其作品中的一个美学特征,主要从王国维的观点中衍生而来。我们不仅将它看作是一种文学特征,更要把“神秀”扩展到美学的范畴,继而将“神秀”看作是李煜作品的一个重要美学品格、美学特质,从美学的角度去探究他作品内部的艺术特色。以往学者对李煜的研究大都停留在文本分析、意象阐释方面,对他的美学研究还有所不足,未曾深入挖掘其作品内部的美学特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1]14。这是对李煜整体词作的凝练概括,集中体现了其词的特点。可以看出,“句秀”是表面化的,仅是语言的秀丽,未见风骨,无法触及美学的实质。相对而言,韦词的“骨秀”,虽更有内在的美感,却不见骨力,与文学中本质的内美还是有一段距离。和李煜的词作相比,他们的作品仍有着美学上的局限,囿于作品中“形”与“质”的体现,很难达到“神秀”这一美学范畴。“神秀”在王国维这里并不是严格上的美学定义,而是指词的神韵悠长,也有重性情的“内美”之意。这里主要还是从境界上体现李后主词的意韵,他并没有将“神秀”特意作为美学上的一个概念提出来。与王国维不同,我们把“神秀”从一般的含义中抽离出来,从美学的角度赋予它一定的美学意义,以此来从不同的角度论证“神秀”这一美学品格。
词本就是情感的汪洋,各种情感都能从词中体现出来。李煜在词作中吟咏性情,恰恰是对“质”的彰显,以“质”来显“形”,从而在本体论上来实现“神秀”。张戎在《岁寒堂诗话》中有引刘勰的两句话:“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因为刘勰的这一篇是残篇,后世很难去考据其真伪,我们大抵可认为这算是他对“隐”“秀”的基本规定。很显然,“秀”在这里是一个美学范畴,一般指“审美意象的鲜明生动、直接可感的性质”[2]227。清代的冯班还说道:“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这一观点与刘勰的意思比较吻合。从李煜的《清平乐》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词作中“秀”的特征,生动可感,这也是“神秀”的一个方面: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从全词来看,整首词的基调比较低沉,上下片中寥寥数字尽显作者忧思难尽之情,意蕴深长,一“梅”一“雁”两个意象将离恨情愁形象地表现在眼前。前者主人公心乱如麻,触景生情,后者又假借了鸿雁传书的典故,描绘了离恨之苦。其中“梅”“雁”这两个意象是生动而富有灵性的,这种“活生生”的意象本身就拥有了“秀”的特点,在整篇作品中它就能传达出寂凉的氛围。词的上下两部分层层递进,结句水到渠成地运用比喻,生动形象,以别致的意象诉说离恨的绵绵无尽,作者的情感溢满胸怀,似江水滔滔不绝。唐圭璋有云:“即景生情,妙在无一字一句之雕琢,纯是自然流露,丰神秀绝。”[3]叶嘉莹认为李煜写词时情感的表达是“全无反省与节制的任纵”[4],可见李煜词中的“神秀”之韵浑然天成,同情感一般直接可触。这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也是其词作中“神秀”品格在字里行间的显现,是一种如流水般自然而然地溢出。这种极简而有韵味的表达十分难得。
当然,“神秀”并非没有边界,它也是有其美学界限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中有言:“雕削取巧,虽美非秀也”[5],也就是说华丽辞藻的堆砌并不是真正“状溢目前”的“神秀”,而且仅仅是形式化的东西,往往只是“雕削”。相反,像“明月照积雪”“长河落日圆”之类,指定不是形式上的堆叠,从中我们可以对“神秀”的范围有一个适当的把握和基本的认知准线。如果是形式上的冗杂很难说它具有美学特征。以文学作品来说,需要有语言上的基本表达,太过形式化的文字反而会消磨作品的文学性,甚至无法成为真正的作品。对“神秀”而言,首先,形式化或机械化的语言无法展现其特征;其次,需要作品中的意象通过语言有诗性的显现,这样才能去进一步探讨文学中的美学意义。因此,只有作品中有文学性可言,我们才可以去界定美的范畴,去划定“神秀”在作品中的表现力。
叶朗曾说:“刘勰提出的‘隐’‘秀’这对范畴,则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了‘意’和‘象’的关系,‘意’应该‘隐’,‘象’应该‘秀’,‘意’在‘象’中,‘隐’在‘秀’中。”[2]229也就是说“象”与“秀”是密不可分的,“象”是与“形”“神”相关联的,并非是我们所认为的“情”“理”范畴。如果从“内容”与“形式”方面来说,这里的“象”是侧重于形式的,而非内容的实质。对“象”的把握,可以帮助我们从偏重“形”与“神”两方面对“神秀”加以认知。
有了对“神秀”美学范畴的基本界定,我们可以从“形”“神”的角度更好地解读李煜作品中的“神秀”。比如从其《相见欢》中可见一斑: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这首词中的“形”十分凝练,月与梧桐相互掩映,寥寥数字就将物象中的意味表达得恰到好处。即便是没有下片情感的抒发,景中的情感也早已传递出来,这种情感的溢出是非常自然而美妙的。这首词中只有几个动作描写,却能够传神达意,字字精妙。下片借助“丝”来喻作“离愁”更将词人心中的“神”透过凄婉孤寂之情得以表现。
可见,“神秀”这一特质在李煜的词作中犹如血液一般无声无息地流淌。纳兰性德在论著中曾提到“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这也算是对李煜词作中“神”与“韵”的关照,是“神秀”的一种委婉的表达。在“形”“神”之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后主作品中的“内美”,不论从哪一方面,都能通过吟咏性情巧妙地实现丰神情韵的特质。从其他角度来说,这也是从本体论出发,对“神秀”的关照。
二
除了以吟咏性情,用“质”表“形”,在“形”“神”之间来展现“神秀”,从“韵”入手,借助“平淡”“灵动”而“奇美”的审美风格也可以探索李煜作品中“神秀”的美学特质。历来不少人认为唐诗以风胜,宋词以韵胜,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美学观点,是学界公认的一类说法。确实,宋诗在诗风之上没能出其右,在词的领域却开辟了与唐诗不同的创作道路。我们说唐代前期的诗风飘逸、奔放,后期的诗风则有所转变,有了雄浑、深沉之感。毫不夸张地说,在诗的领域,唐代的诗人已经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宋代的作家为了避开高峰,从词的方向扩展了不一样的世界,而李煜便是词的开拓者之一。从李煜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韵”是略胜于“风”的,正是“韵”的显现,使其作品中的“神秀”品格更加完满。明代胡应麟曾说李煜的词为“宋人一代开山祖”,可见其词作的风韵神貌对宋代词人影响不小。清代的冯旭则更加直接指出了李煜对后世的影响,他说:“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可以说,李煜父子二人的创作为宋代词风开了先气,这也说明了他们父子二人在词史上的重要性。
“韵”最早是乐曲中的概念,一般指声韵。魏晋时期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气韵生动”的美学概念。在这里“韵”有人物所表现的情调与个性的意思,不仅仅是声律上的说法,但谢赫所言的“韵”大都体现在绘画之中。到了宋代,范温否定了前人所说的“不俗之谓韵”“潇洒之谓韵”“生动之谓韵”等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有余意之谓韵”即要求审美意象要有余意,还要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受当时社会风潮与时事政治的影响,宋韵“它不仅指一种艺术态度,而是指一种人生态度;它不仅是艺术,而且是生活,是艺术与生活的统一。它既不是入世的,又不是出世的,而是审美的,是审美的艺术与审美的人生的有机统一”[6]。可见,此时“韵”已是涉及众多艺术门类的美学概念,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它与生活也有了美的关联,而且它的美学外延仍旧在拓展。
“韵”虽在宋词中有集中的体现,但在李煜的词作中却早已见端倪,从其作品的韵味中我们可以窥见“神秀”的特质。李煜的词作能够韵中见情,既体现了作品的“真”,又不乏“秀”的表达,更是从“神韵”向“神秀”的一种溢出。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言:“空中荡漾,最是词家妙诀。”[7]114他指出词要传神写意,表现出不尽之意,留有余味,这与范温的观点颇为相似,我们可以在李煜的《虞美人》中体会这种余意。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整体来看,全词的语言凝练、优美、清新,然而在语言的明净之下,蕴含的却是无尽的风韵情愁。尤其是词的结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以看作是“画龙点睛”之语,富有感染力与象征性的比喻使全词的情感意蕴延绵不绝。作品中李煜怀念故国,以过去的生活为起点,又以过去的存在为结尾。由问起,以答结语,最后一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虽然没有直抒胸臆,但借江水来指向愁苦之情,没有比这更贴切的了。全词用景含情,以情染景,情景交融,浑然天成,充分把情感的力度与深度表现了出来。此外,词的意蕴也得以在景中抒发,比起唐代诗人的风姿神貌,李煜这首词的美学韵味得到了放大。他将词人的情调与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行文增添了悠长的意蕴,从而也将作品中的“神秀”通过韵美表达了出来。
李煜词的“韵”味对宋代词人影响较大。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曾言:“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7]118,这里说的大概就是从唐“风”到宋“韵”的一种转变,而这种转变恰恰可以更好地说明李煜作品中“神秀”的风貌。这种开风气的变调,让李煜的词作更有了意韵上的拓展,也为后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式。经由词的“韵美”,李煜词作中的“神秀”在审美理想中得以向“美”靠拢,从而达到一种极为空明灵动的境界,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三
李煜的词作除了词情和词韵上的特征,在意境上他的作品也为后代词人树立了典范。秦观、周邦彦等人都有受其作品的影响,词的意境在李煜手中得以延伸,进而丰富了“神秀”的表现形式。在词中,意境的完成则是由“吟咏性情”与“韵美”所共同营造的澄静、空灵的审美意境来实现的,这也让李煜作品中的“神秀”具有了最本质的美学高度与内涵。
关于意境的理论早在《文心雕龙》以及《诗品》中已经有所体现,盛唐之后意境理论全面形成。王昌龄在其《诗格》中首次说明了“意境”的概念。他认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和意境,并进一步指出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是对意境最初的探究。随后姣然对意境又有了进一步推进,提出了诸如“缘境不尽曰情”“文外之旨”“取境”等重要理论,全面发展了意境这一理论。此后刘禹锡还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观点,晚唐司空图对这一观点作了延伸,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进一步拓广了意境研究的边界。到了清代,叶燮则在他的《原诗》中,把意境阐释为“含蓄无垠”“言在此而意在彼”。而关于“意境”说的集大成者则是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开篇中就有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1]3对词的高下,他提出了以境界作为最高的衡量标准,契合了五代、北宋词的美学发展脉络。
这里所说的意境主要是作品中“情”与“景”的有机统一,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作品本身能够产生悠长的意蕴,尽显文学中的“神秀”特质。李煜的词作除了体现这一点,他还通过“吟咏性情”与“韵美”所共同营造的澄静、空灵的审美意境来实现“神秀”这一美学品格。纵观李煜前后期的词作,其作品中的意境转变显而易见,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论李煜:“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8]我想李煜的佛学思想对其意境的变化也会有所影响。例如他词中有“梵宫百尺同云护,渐白满苍苔路”,在这里佛家的影响清晰可见。佛学思想为李煜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无论从内容和思想上都使他的作品有了意境上的一个转向。这种变化合情合理,也为其词作增添了新的质料,新的表现方式。
对李煜词作中意境的论说,还是王国维论述得最为贴切。他指出:“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1]15,也就是说李煜词的内容、风格先后有了变化,这也让他的词有了更多余味,更能“言长”。总体来看,唐五代和宋代词人的作品要么“有句无篇”要么“有篇无句”,这种矛盾在李煜身上有了很大改观,达到了“有篇有句”。一直到宋代也仅仅是苏轼、秦观、辛弃疾等几人有这样的成就。不仅如此,李煜为了扩大词的表现力,还借助了诗歌中的手法,以诗入词。不论是“新瓶装旧酒”法还是“夺胎换骨”法,无论是意象的沿用,还是诗境入词,都在李煜这里有了新的形式,这使其词作增添了余韵悠长的意境。
关于李煜作品中的意蕴,叶嘉莹曾有论述:“他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不是外延的,而是一种内展的。他的内心有一个敏感的诗心,像是一池春水,你只要向它投下一块石头,不需要多,只要打在水的中心,只要有一点触动它的内心,它的水波就自然向外扩散展开出去,自然就扩充到一个绝大的意境。”[9]李煜内心世界的丰盈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感和体悟,使他的心境有了拓展。我们可以从李煜的《虞美人》中看出这种意境: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整体来看,这首词基调低沉,情与景相互交融,透露出作者无尽的哀苦与悲恸之情。上阙中无论是梦还是现实,都充满了凄苦之感,仿佛是一支回荡天际的哀歌。词中作者的认知不是通过外延获得,而是借由自己的飘零身世,向内探求,词中所展现的意境也有了延伸。全词我们不见抒发悲愤的词语,然而借助意象的表达,如冷雨的寂寥,流水落花的易逝,却把词人的亡国之痛、内心之伤,形象化地传递出来,使读者的心灵深受触动,言无尽之意,达余韵悠扬之感。
可见,在情与景的交织中,词的意境得到了开拓,有了悲壮之感,深痛之情,让“神秀”也在词作中得以丰盈,意蕴有所绵长。此外,像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等词句无不蕴含绵绵意味。意境的发掘与阐释,使李煜的词作境界开阔,有了更多可描述的空间。这一变化也让他作品中的“意”与“境”获得了新的身份,这种新质也催生了其作品中的“神秀”品格,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广的表现力。
四
前面,我们有提及“神秀”除了在李煜词的风韵上有显现,在其意境中也有形式和内容的延伸。此外,某种意义上“神秀”还是赤子之心的真性情所具有的“内美”,是“敛”而“秀”的,与当时花间词的辞藻艳丽、色彩华美有着本质的区别。正是这种“真”的内美,使李煜的词作在内质上有了与前人明显不同的特质。李煜的词作是工而秀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提到:“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1]17可以看到除了“秀”的本质,李煜词之“真”也是其词作受后世欢迎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方面来说,“神秀”亦是真性情的“内美”,正是李煜作品中的这些美学表现,让他的词也更具有“神秀”的特质,韵味悠长。
文学中的“真”作为一个美学原则历来就被重视,中国古典美学除了关注“美”与“善”的统一,还强调“美”与“真”的统一。以先秦为例,老子和庄子都强调“真”,在这里“真”是“道”,是“自然”,这与我们所说的真性情的“内美”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老子和庄子强调的“真”是质朴无华、自然而然的状态,我们所说的李煜的“真”,是与“美”相统一,从美的蕴藉中表现“神秀”的特质。到了王充这里,开始强调“美”与“真”的统一,其意旨是抵抗“虚妄”,王充在文中还特意主张“真美”反对“虚美”,他始终坚持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崇尚朴实的审美态度。
这里所说的“真”不属于哲学的范畴,而是作为美学范畴提出来的。“真”大致包含了两种意思,一是“主观情感之真而不伪”,二是“反应对象之真而不妄”,王充的观念侧重于第二点。从王充的《论衡》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事真、情真、理真[10]。这与王国维所言的“神韵”所体现的真性情的“内美”是吻合的,也可以说是“情真为美”的体现,而这种“真美”恰恰是“神秀”的彰显。我们所言的“真”更多的是情感之真,赤诚之心,是在对象之真中自然地融汇了情感之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煜的作品中窥见,其词作中所流露出的“内美”也是“神秀”的一个方面。比如其《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一词: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首词是李煜被囚禁后所作。借助暮春之景,作者抒发了人生失意的无限怅恨之情,此番情感是发自内心,是生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之中,真真切切。整体看来,这首词明白晓畅,既没有粉饰装扮,也没有刻意雕琢之意,更像是水到渠成之作,特别是下阙,字字见真情。
首句以“林花”肇始,作者并未言说是何林何花,一笔而过,凸显的是春红的谢落。后面一句“太匆匆”可谓是神来之言,既有作者的无奈之心,又有些许的埋怨之情。下面作者以“胭脂泪”起,一个“泪”字,生动传神。在这里,胭脂泪并非其一般的概念意义,而是代指林花着雨后鲜艳的色彩,作者用“泪”而不用“湿”字,使下片的语言一下子活了过来。此作品以林花始,而这寒雨也让胭脂模样的花留下了“泪”,或许李煜曾读过杜甫的“林花着雨胭脂湿”,受其启发有了此番灵感。后面一句“相留醉”更是神来之笔,短短数字,将作者心中的忧苦尽露。此醉不是迷恋,而是对再见遥遥无期的麻醉,字字包含李煜的真情实意。可见其作品中处处流露着真性情,无处不体现出真情之下的“内美”,而恰恰是这种真美彰显了其作品中的“神秀”品格。最后,李后主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结语,实为暗喻,相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言,似乎意味更深,笔致也转高了一层。对于作者来说,人生漫漫,故国之失的悔恨无穷无尽,像无情的东逝之水,不舍昼夜,淘尽个人的伤悲。
可以看到,李煜的这首词作中饱含了其真挚之感,虽然多为借景抒情之句,却在对象之真中融入了情感的真实。正是这种“情”的真实感,使作品自然有了内化的美感,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内容之中的美。这种美恰好体现了其作品中的“神秀”特质,与“句秀”“骨秀”这类形式上的风格不同,“神秀”在这里早已有了美的内涵,美的风貌,美的意味。
总体来说,将“神秀”作为美学品格提出来,一是丰富了王国维所提出的这一文学特征的内涵,二是赋予了“神秀”美学的范畴。从不同的方面论证其在李煜作品中的体现,以此坐实了“神秀”在李煜词作中的独特风格,让这一风格有了美学上的外延与内涵。我们从吟咏性情出发,以本体论的角度阐释了李煜作品中的“神秀”特征。进而在词韵中,发现了其作品里的“灵动”“平淡”,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把“神秀”推向了美的内在层面。在对“意境”的探讨中,“吟咏性情”与“韵美”的交融,使得李煜词作中的“神秀”特质具有了美学的特质和表现力。此外,对其作品中“真”的挖掘,是对“质”的一种延伸,以此来丰富“神秀”的内蕴,让它成为李煜作品中独有的美学品格。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对李煜作品的研究关照了词的内在表现、美学内容,完成了一次美学上的剖析与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