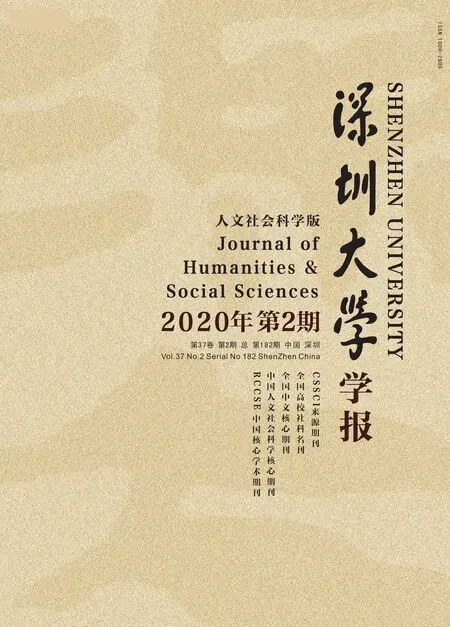诗乐疏离与《蟋蟀》文本阐释的开放性
2020-12-22曹胜高李申曦
曹胜高,李申曦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自清华简《耆夜》出,因其所载的《蟋蟀》与传世文本《诗经·唐风·蟋蟀》相近,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周公歌咏的《蟋蟀》,与传世文本的关系如何?其何以被收入《唐风》?得到学界的诸多阐释①。《诗经》国风本为风土之音,其分类的依据在于音官风土[1](P43)。周公所歌的《蟋蟀》,之所以被收入《唐风》之中,当与其所使用的音乐有极大关系。季札观乐时言《唐风》出于陶唐氏,故周公所歌的《蟋蟀》极有可能是用陶唐氏之乐作为曲调,后被整理入《唐风》。孔子也曾以“陶唐之乐”解释传世本《蟋蟀》,兼顾了此诗的乐义。如若从音乐的角度辨析周公所歌《蟋蟀》的曲调特点,观察其如何作为《唐风》曲调的代表,我们便能从音乐的角度理解国风的编成机制。进而辨析《蟋蟀》题旨如何因乐义而被确定,还可以理解乐坏之后,乐义失传,对其题旨的解读如何从乐义阐释转向诗义阐释,由此考察《蟋蟀》题旨变动的内在轨迹。将《蟋蟀》作为一个标本,观察《诗经》文本与音乐脱离的过程中,不再固守乐义,使得诗义的阐释缺少了礼乐的内在规定而形成阐释开放性。
一、乐歌《蟋蟀》的生成及其原初义
《蟋蟀》的文本,一是传世本《唐风》首篇《蟋蟀》[2](P361);二是清华简 《耆夜》 所录周公所歌[3](P150),整理者亦定名为《蟋蟀》。从文本来看,二者的关联只存在4 种可能:其一,传世本《蟋蟀》与简本《蟋蟀》为相互平行的文本系统,各自流传。二者皆以蟋蟀起兴,内容相似而无关联。其二,传世本《蟋蟀》为简本《蟋蟀》的基础,二者在不同地区流传中形成了文本的差异。其三,传世本《蟋蟀》在先,简本《蟋蟀》为晚出之仿作,是后世学者对周公事迹追述而形成的衍生文本。其四,简本《蟋蟀》为源,经过乐官整理之后,被收入《唐风》,形成了传世本《蟋蟀》。我们可以通过文本比对,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从篇章结构来看,传世本与简本均为三章,都采用重章叠唱的形式,每章首句皆以“蟋蟀”起兴。从语言和句式来看,二者高度相似②。简本第二章所言的“蟋蟀在席”及第三章所言的“蟋蟀在舒”,传世本皆作“蟋蟀在堂”。“席”,为筵席,在堂中。“舒”,释读为“序”[2](P155)。《尔雅·释宫》云:“东西墙谓之序。”[4](P2597)比席更靠内。这样来看,简文兴辞具体而形象,传世本的兴辞则更统一。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及《豳风·七月》对物候的描写,简本的堂、席、舒的变化,体现了周人对物候的详细体察。《豳风·七月》曾言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3](P391),也是以蟋蟀进入房内,指代时间流逝,天气渐冷。《七月》作于周部族居豳期间,词句古朴,简本《蟋蟀》的铺陈近于《七月》,而传世本则以“蟋蟀在堂”一以贯之,显然简本更接近于早期叙述,其保留的当为原始文本。
简本中的“不喜”,即“不乐”;“今我不乐”与传世本“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句相应,传世本更加整齐。简本“毋已大乐(康)”,即传世本的“无已大康”;简本的“康乐而毋荒”,与传世本“好乐无荒”相通,传世本的句式更加整饬。二者文末均以 “良士”收尾,体现出内容的一致性,而传世本的“瞿瞿”“蹶蹶”是对“良士之方”“良士之惧”更为具象化的描述,显示出传世本要比简本的文辞更为精致,当是经过进一步整理之后的文本系统。此外,简本中的句式,与《诗经》早期文本的用词更为相似,如“岁矞云莫”,见于《小雅·小明》“岁聿云莫”[3](P464);“不喜不乐”,与 《周颂·清庙》“不显不承” 的结构相同[3](P583)。可以看出简本《蟋蟀》并非简单的后世造作,当是保存了《蟋蟀》更为原始的文本形态。
如果确定简本在先,还要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简本并非出于后世造作,而是对口传历史的记录,其形成虽晚,而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则流传甚早。后世创作,常常是根据其知识系统对前代的历史故事或者传闻进行更为详细的解释。对口传历史的记录,则是后世根据前世流传下来的口传史实或传说进行文本写定。二者形成的文本常常相似,但文本制作的用意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文本创作,是按照后代人的理解或想象对过往历史事件、传说系统进行再创造,其立足点在于创造性的想象,即便形成历史性的文本,其凿空的成分是文本建构的基础。而文本写定,则是遵照历史的真实和传说的本义,对前代流传的史料、事实或掌故进行更为忠实的记录,其忠实于历史征实是文本写定的关键。如果简本《蟋蟀》为战国学者的文本创作,其必然符合如下前提:一是作者非常熟悉《诗经》,其中提到周公歌《蟋蟀》的文本,其兴辞、内容和主题与传世本《蟋蟀》高度相似,显然作者读过《唐风·蟋蟀》,并根据传世本进行了复古或者拟古的处理,使之更合乎古意。二是作者还要创作出传世本《诗经》所没有的文本《乐乐旨酒》《鞧乘》《赑赑》《明明上帝》等诗,以此完成《耆夜》作为历史故事的叙述。而在战国时期,《诗经》 已经编订且广泛被士大夫引诗赋诗,此时极少有新的逸诗出现,表明《诗经》已经定本,并为时人熟悉。在饮酒作诗的礼乐机制已经崩坏的情况下,《耆夜》作者再造四篇传世本《诗经》之外的乐歌来叙说历史事件,既不合乎作古的用意,又难以为时人所信服,从这个角度来说,简本《蟋蟀》不当为晚出的拟作,而只能是某一口传历史系统的遗留。
这一口传历史系统,清晰地呈现了周初的歌诗的创作机制,使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管窥歌诗的乐义。而且能够从这一标本中观察出《蟋蟀》被改编而收入到《唐风》的整理过程。简本《蟋蟀》文本简古,传世本《蟋蟀》句式整饬,语义简明,显然是乐官系统的整理[5](P8)。而且简本用韵疏,今本用韵较密者,可知乐官整理意在使之更合于大型乐奏的伴奏,故简本保留了更为原始的乐歌形态[6](P4249)。《耆夜》记载了周公创作《蟋蟀》的历史场景: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鞧乘》……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 《赑赑》……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走舟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2](P150)
武王伐耆凯旋而归,在文王太庙举行饮至礼。周公作为执礼者,有感蟋蟀降于堂上,遂作歌《蟋蟀》。其以蟋蟀为兴辞,来抒写“岁矞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之感。在时光易逝的语境中,周公发出了“日月其迈,从朝及夕”的时间流逝感,体会到时不我待的急迫,勉励士大夫不要安逸享受,不要荒废职事。其中的“良士之惧”,是全诗的情感基调,也成为周人“恐惧修省”的传统[7](P62)。《尚书·吕刑》 言:“朕言多惧”,伪孔传:“戒惧者,以儆戒之也。”[8](P251)“惧”为“戒惧”,体现了周初王室成员的警惕戒备之心。《蟋蟀》 每章结句的 “毋已大乐(康)”“康乐而毋荒,惟良士之惧”,正是在战胜耆国的饮至礼上,周公提醒王室成员勿溺于安乐,要时刻保有忧惧之心。
周王室的惊惧之心,既来自于其对天命的敬畏,也来自于对殷商衰败的借鉴。在周人看来,殷商的衰败是殷纣王嗜酒败德、荒淫逸乐所致。《尚书·酒诰》言:“后嗣王酣身……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8](P207)商王耽酒怠政,纵乐不息,最终招致民怨,天降灾祸。周初文献中多次载周公告诫周王室成员不要豫逸享乐。《尚书·无逸》:“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8](P222),以殷王湎酒失德而亡国告诫成王要引以为戒。在伐耆得胜而返进行庆功的饮至礼上,周公再次生出警惕之心,与武王、召公、毕公等王室成员相互勉励,不忘王季、周文王以来的“翦商”之志[9](P37),牢记天命,再接再厉。周公作为饮至礼的主持者,担负着劝酒祝诵的职责③。武王作歌言“乐乐旨酒”“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嘉爵速饮,后爵乃复”,主导着饮至礼的程序,言成功凯旋的快乐。周公歌“王有旨酒”“既醉又侑”“万寿亡疆”时,为酬祝之辞,在饮至时劝大家尽欢[2](P150),是出于饮至礼的礼节。在饮至礼即将结束时而歌《蟋蟀》,则在提醒王室成员在得胜时仍要保有警惧,牢记翦商的使命。
清华简《耆夜》作为战国写定的文本,更接近于忠实口传历史而写定的文本而不是造作的文本。也就是说,《耆夜》中所载的《蟋蟀》,更接近于周初饮至礼上周公所歌咏的歌辞,是传世本《蟋蟀》的祖本。其所体现的最为原初义,是周公勉励周王室成员,要戒骄戒躁,在胜利之后保持清醒,以忧惧之心面对胜耆之后的伐商事业。
二、《蟋蟀》编入《唐风》及其乐义的偏移
周公所作《蟋蟀》为何会收入《唐风》,李学勤先生认为诗因戡黎而作,便在附近的唐地流传而成为当地的诗歌[10]。贾海生曾推断《蟋蟀》本为王朝乐歌,后来将之赐予晋国而编入《唐风》[11](P4)。这是就乐歌形成之后进行的推断,尚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如果诗因戡黎所作而流传于唐地,那么为何其余四篇诗作没有收入《唐风》呢?如果《蟋蟀》被赐给晋国而编入《唐风》,为何要以此篇赐予晋而其余四篇则散逸了呢?国风是按照音乐以乐归类,其之所以编入《唐风》,要从音乐曲调中寻求答案。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唐风》首篇的《蟋蟀》,是以陶唐氏之乐演奏的。现存文献中对《唐风》的音声特点进行评价的,是季札观周乐时所言: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唐》,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12](P42006-2007)
季札聘鲁观乐,乐工为之歌《唐》。季札听歌之后,根据所歌音乐的曲调、声情、旋律和配器中体现出来风格进行评论,侧重于乐之德义。《周礼·春官·大司乐》言:“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13](P787)德蕴合于乐,教乐学乐的关键,便是体会乐中之德。就道德而言,乐中之德为德义;就音乐而言,乐德合一,便是乐义。《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之言:“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12](P1822)诗义、文义与乐义、礼义相辅相成,皆是德义的体现。诗、书见诸文本而礼、乐付诸行动,因此观乐便要观其乐义,感知其中蕴含的乐德。
《左传》载季札观乐之后,对其中蕴含的德义逐一进行阐释,其对《唐风》的德义评价有二:一是认为《唐风》中体现了陶唐氏的遗风,这是对包括《蟋蟀》在内的《唐风》音乐特征的总体观感。二是认为《唐风》中体现的德义,是陶唐氏先民遗留下来的德行。其所言的“忧之远”,是对《蟋蟀》文本中“忧惧”主题的感知:即简本的“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传世本的“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也就是说季札从音乐中听出了其中蕴含的深沉的忧思,但他认为是来自陶唐氏。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听出的是“陶唐氏之遗民”,听出了《唐风》为陶唐氏遗民所歌。《史记·吴太伯世家》则载为“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14](P1452),则意味着季札听出了是陶唐氏之乐。季札听《唐风》与“陶唐氏”联系起来,在于唐风体现了鲜明的陶唐氏的音乐风格。陶唐氏之乐为尧时音乐的遗留。司马迁曾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14](P45)尧之后世以陶唐为号,其民为陶唐氏遗民,其乐为陶唐氏之乐。《国语·晋语》载范宣子之言:“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15](P453-454)陶唐氏在尧时最为鼎盛,后世部分部族仍以陶唐氏为号:“帝尧之后为陶唐氏。后有刘累,能畜龙,孔甲赐姓为御龙,以更豕韦之后。至周为唐杜氏。”[16](P423)季札闻歌《唐风》而知陶唐氏遗风,表明首篇《蟋蟀》是以陶唐氏之乐为曲调。
从考古文献来看,陶寺遗址出土有磐、鼓等乐器,体现了陶唐氏所居区域的音乐繁荣[17](P313)。从文献记载来看,陶唐氏之乐形成于帝尧之时。《吕氏春秋·古乐》 言陶唐氏作乐舞以调整阴阳:“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者,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18](P119)阴气过盛,民气郁滞,作乐舞激发阳气,疏导阴气,使之平衡。又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革各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18](P125-126)帝尧时期音乐的繁盛,体现了陶唐氏等部族丰富而高超的音乐创作能力。
周人尊夏为正,《史记·周本纪》 载周之先祖弃封于尧舜时期:
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14](P112)
周部族以后稷为先祖,其早期所用祀社之乐,便是继承土鼓苇籥。《周礼·春官·籥章》:“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气。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13](P801)社为周部族祭祀土地之主,其祀社所用的乐器,乃上古之遗留[19]。《礼记·明堂位》言:“土鼓蕢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20](P1491)伪孔传曾言:“唐,帝尧也,姓伊耆氏。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号陶唐氏。”[8](P113)土鼓、蕢桴、苇籥为伊耆氏之乐器,为陶唐氏所继承,并在周代社祀中得到延续。周伊耆氏、陶唐氏所用土鼓豳籥进行社祀的《七月》,便出自《豳风》。按照季札的说法《豳风》体现着“周公之东”的事迹[21],也就是说,周初制礼作乐的周公,非常精通、熟悉陶唐氏之乐。
“耆”即“黎”,《史记·周本纪》载“明年,败耆国”,《正义》云:“即黎国也。”[14](P8118)《史记·宋微子世家》又载“灭阝九国”,《集解》徐广言:“阝九音耆。”《史记索隐》:“阝九音耆,耆即黎也。”[14](P1607-1608)《毛诗正义》言:“《殷传》云:‘西伯得四友献宝,免于虎口而克耆。《大传》曰:‘得三子献宝,纣释文王,而出伐黎。’其言既同,则黎、耆一物,是文王伐犬夷之后乃被囚,得释乃伐耆也。”[3](P503)因此,《耆夜》记载当为伐黎凯旋而举行的饮至礼。
《吕氏春秋·慎大》言:“封帝尧之后于黎。”[18](P356)黎为尧后之封地,尧后又称陶唐氏,居于黎地之民,即季札所言的“陶唐之遗民”。其流行陶唐之乐,即司马迁所言的“陶唐氏之遗风”。在毕公伐黎成功的饮至礼上,周公以饮至之主的身份在宴饮将尽时,以黎地流行的陶唐氏乐调作歌《蟋蟀》以慰劳毕公,勉励将士们再接再厉。此曲使用的正是陶唐氏之乐的曲调,因而当季札听乐工歌《唐风》,立刻感知到陶唐氏之遗民。
《唐风》采用的是陶唐氏之乐,流行于尧的后代所居的区域。叔虞封地,以封于陶唐而得名。《史记·晋世家》载:“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称唐叔虞。”[14](P1635)唐之得名,在于其本为陶唐氏所居,以陶唐氏遗民为主。皇甫谧言:“帝尧氏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又徙晋阳,今太原县是也……及为天子,都平阳,《诗》于风为唐国……叔虞封焉,更名唐。”[22](P12)叔虞受封的唐,正是唐风流行的区域,即《史记》所谓的“陶唐氏之遗风”。由此来看,国风的命名,并非按照封国的区域,而是按照音乐流行的区域来划分。重要邦国流行的主要曲调,作为邦风、国风的命名。陶唐氏之遗风为《唐风》,周族居豳所用之乐是为《豳风》。即便邶、鄘并入卫国、郐并入郑而国不复存在,作为音声特点的邶风、鄘风、郐风依然流行于卫、郑,故后世并未废弃《邶风》《鄘风》,东周依然保留有《郐风》,就在于其为音声分类而非诸侯封国之别。
周公制礼作乐时,以《唐风》分类,在于相关乐歌为陶唐之乐,即曲调、声情、旋律、配器继承了自伊耆氏、陶唐氏而来的音乐风格,是为陶唐氏之土风[1](P51)。周公所作《蟋蟀》为《唐风》首篇,当是陶唐乐的代表作。由此来看,简本《蟋蟀》为周公用陶唐之乐演唱的歌辞,意在提醒众人勿纵酒康乐,周公当是《蟋蟀》的创作者。其所用音声为黎地流行的陶唐之乐,叔虞封唐,黎隶属之,陶唐之乐是为唐风。后依照音乐编风,将《蟋蟀》进行整理,使其句式整饬,更合乎钟鼓演奏,加密了韵脚,以便于合乐而歌,录入《唐风》,是为传世本《蟋蟀》。
季札称其中蕴含的“何忧之远也”,正是听到了《蟋蟀》中蕴含的忧惧之思,但季札所言的忧思,为陶唐氏之乐中的忧思,而没有将之视为周公的忧思。如果不是简本《蟋蟀》的出土和《耆夜》的叙述,我们会与季札一样,认为《蟋蟀》所体现的是陶唐氏的忧思,而不知其本出于周公之忧。从这个意义上说,季札所言的“陶唐氏之遗风”,又言之为“何忧之远”时,《蟋蟀》已经失去了原初之义而形成了二次阐释,是忽略了歌诗的生成背景而单就乐义进行的阐释。
三、诗、乐疏离与《蟋蟀》的文本阐释
季札聘鲁观乐,以乐义观察《蟋蟀》的德义,是诗、乐一体情形下对乐歌的整体理解。但在不歌而诵的赋诗语境下,诗的乐义便被剥离之后,按照断章取义的方式,径取文本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有赋诗语境中对《蟋蟀》的阐释: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观七子之志。”……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12](P1997)
《汉书·艺文志》 言:“不歌而诵谓之赋。”[23](P1755)赋诗是剥离诗歌音乐属性之外对文本本身的重新理解,是对诗义的直接采用。《礼记·乐记》曾言及二者的分别:“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20](P1536)观诗侧重理解其中蕴含的文本义,即观察这些文本所蕴含的对于群体价值的理解与实现程度[24](P60)。听歌,主要感知歌的曲调、声情、旋律和配器之中蕴含的乐象、乐义、乐德、乐情。季札观乐中对《蟋蟀》的理解,是基于音声特点来阐释乐义。印段赋《蟋蟀》时,则脱离了乐义而直接使用其文本义。也就是说,赋诗者和听诗者,即便能够歌《蟋蟀》,在赋诗过程中也不再关注于其音声,而通过文本义来观察、揣摩彼此的用意。因此,印段赋《蟋蟀》时,义取诗文“康乐而毋荒”“毋以大康”等句,表达自己不溺康乐、不忘戒惧之志。赵孟听后,评其能保家安民、乐而不荒。二人在赋用《蟋蟀》时,通过诗的文本义传达彼此的用意。在这样的背景下,《蟋蟀》的乐义被剥离,剩下的只有诗的文本义。
我们还可以通过孔子对《蟋蟀》的阐释来观察诗乐疏离过程中的诗义的调整:
《蟋蟀》,知难。[25](P5236)
孔子读诗……喟然而叹曰:“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26](P54)
上博竹简《孔子诗论》和《孔丛子·记义》中载孔子两次谈论《蟋蟀》。一是认为知难,一是称赞陶唐氏俭德。从表面来看,二者似乎毫不相关,实则出于孔子对诗篇不同维度的理解。《孔子诗论》载孔子读《蟋蟀》而“知难”,难,李零校读为“戁”,即惶恐、惭愧之意[27](P20),是从《蟋蟀》中读到了惶恐、警惧之意。《耆夜》言周公作《蟋蟀》劝醒在场者毋耽酒乐,要保持警惧。可见其中戒惧之意,不在于音声,而在于《蟋蟀》文本,孔子的“知难”之论是就《诗》的文本义进行的阐释。《记义》 中孔子谓 “陶唐氏俭德之大”,当是从《蟋蟀》的音声特征中体会到乐义。孔子曾弦歌诗三百,订正诗乐④,《蟋蟀》作为《唐风》首篇,最能体现陶唐氏之乐的音声质朴、节奏单调。《淮南子·精神训》 载尧之俭德言:“尧朴桷不斲,素题不枅。……尧粝粢之饭,藜藿之羹。”[28](P531-533)认为尧之俭德,在于不以耳目之欲繁身、常忧己之重任。这恰恰是《蟋蟀》“毋已大康”“惟良士之惧”所体现出来的忧惧,但孔子以“俭德”论《蟋蟀》题旨,既关注到《蟋蟀》的乐义,更关注于《蟋蟀》的文本义。
季札观乐、印段赋诗、孔子论诗时,《蟋蟀》的乐义与文本义都流传于世,季札从乐义论《蟋蟀》所体现的陶唐氏之德,印段则从文本义用《蟋蟀》的忧惧,分别体现出诗乐合一与疏离状态下对《蟋蟀》题旨理解的侧重与取舍。孔子既从文本义论及《蟋蟀》所体现的戒惧之难,又能从乐义体会到陶唐氏之俭,说明诗乐一体状态与诗乐疏离状态下,对诗的解读会出现一定的偏移。在诗乐尚存的时代,这种偏移尚且存在,当周乐散逸之后,《诗经》只剩下文本时,对《蟋蟀》的解读便只能依托文本义,或因袭前代的解释而进行附会,或干脆抛开乐义而就文本义进行解读,甚至不惜带上望文生义的理解。
汉儒对《蟋蟀》题旨的阐释,便抛开乐义而关注于文本义。昭帝时期的盐铁辩论中曾提及此诗: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生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自古有之,非独于此。”[29](P43)
大夫与文学就推行均输政策展开激烈论争,文学认为“利在自惜,富在俭力趋时”,统治者应“禁溢利,节漏费”,爱惜财物,按时耕种方可自足,节省不必要的开支,百姓便会专心务农,衣食无缺[29](P42-43)。《蟋蟀》作为论政的依据,其题旨便被重新进行了阐释。原先依附于乐义的“陶唐氏之乐”的相关阐释被忽略,而选择了诗的文本义。孔子论《蟋蟀》时所体现“陶唐之俭”则被放大,偏移为诗的本文义,用作对当下社会风气的某种讽刺,被赋予了“刺俭”的含义。这样,诗的创作意图由此被解读为针对节俭固陋而作,原本劝勉王室成员牢记职责、勿过度享乐的题旨则被转化为讽刺时人不知节俭。
在这样的偏移中,《蟋蟀》的题旨便与倡导节俭联系了起来,被汉儒视为刺诗。班固言:“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23](P1648-1649)季札观乐,于《唐风》之中听到的是陶唐氏乐调,从土鼓、苇籥的配器中感受到“陶唐氏遗民”依然保留着尧时的简朴,进行了赞美。班固则由唐地风俗论起,意指君子思虑深重,有陶唐氏遗风,而小人无度,俭啬固陋,不仅《蟋蟀》被解读为过度节俭的讽刺,连季札观乐的阐释,也成为对汉儒“刺俭”说的背书。
在汉儒眼中,《蟋蟀》被视为刺俭德名篇,《毛诗序》甚至将其置于历史故事中,对其创作的用意进行阐释:“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虞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3](P361)认为这首诗作的用意在于刺晋僖公,诗人闵其节俭不合礼制而作。由此阐释,便认为唐地物产匮乏,生活简朴,唐风中蕴含的刺俭之意,正是尧时俭约风气的遗留。李学勤先生根据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发掘的青铜礼器,考证出历史上的晋僖公是位沉溺田狩与美味的豪奢贵族,并非节俭固陋之人[5](P8-9)。他认定《毛序》解说不但与晋侯品行相悖,而且也不符合清华简所载《蟋蟀》所作的本事,将原本赞美陶唐遗民俭约的《蟋蟀》,误读为讽刺俭约而要求按照礼制奢华的诗篇。这种误读的产生,是剥离了诗的乐义而对文本义的望文生义,忽略了诗形成时期的礼乐用意,只就诗的文本义进行解读。有时甚至不惜采用“以意逆志”的方式,就诗的文本义入手,对诗歌的创作过程进行强行说解,如《毛诗序》的刺俭说,便是在不能违背孔子对《蟋蟀》“俭德”的说解中,而按照刺诗的认知对《蟋蟀》的题旨和文本义进行勉强的解读。
《毛诗序》“忧深思远,俭而用礼,有尧之遗风”之语,皆源自季札、孔子对《蟋蟀》的评价。其附会之处在于,季、孔二人原是就陶唐氏之乐来谈论《蟋蟀》的乐义,方有思深、俭德之论。而毛序形成的时代,与诗相配之乐已经消亡,汉儒无法从乐义讨论诗义,前代学者对乐德、乐义的阐释,又不能轻易违背,只能从文本义来讨论乐义,不得不把孔子对乐义的理解附会到文本义的解读之中,试图形成自圆其说的阐释。如《蟋蟀》首四句,《郑笺》云:“岁时之侯,是时农功毕,君可以自乐矣。今不自乐,日月且过去,不复暇为之,谓十二月当复命农计耦耕事。”[3](P361)按《豳风·七月》对于农事的记载,“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3](P392)岁末闲暇之时,相聚饮宴合乎礼制。郑玄认为蟋蟀九月在堂,为岁末之候,农功已毕,当为晏乐之时,晋僖公却俭朴得不行飨燕,过于节俭也不合礼制,这便要讽刺。汉儒认为《蟋蟀》的作者作诗的意图是讽刺晋僖公,其中的“无以大康,职思其居”,被解释为无甚康乐,常思己所居之事,与简本《蟋蟀》的原初义正好相反。《孔疏》:“戒僖公,君若好乐,无得太好之”,进一步将之解读为劝诫僖公勿要过于康乐。“好乐无荒,良士瞿瞿”,《郑笺》:“君之好乐,不当至于废乱政事,当如善士,瞿瞿然顾礼义也。”认为是作者提醒晋僖公当如良士享乐有度[3](P361)。这样一来,汉儒便为《蟋蟀》设想了一个忧思深远、有尧时遗风的作诗者,其忧国忧民且知书达理,见晋僖公俭朴,认为俭朴也不合礼,转而讽刺他要合乎礼制地奢华起来。
由此可见,脱离了乐义只剩下文本义的诗篇,在汉儒的阐释中变成了可以被无穷假设、无边想象的开放文本,可以按照解读者的需要进行文本的阐释和历史的附会。如孔颖达疏《蟋蟀》,详细阐释了不言晋而命名为《唐风》的缘由。欧阳修《诗本义》、范处义《诗补传》也在想尽一切办法维护“俭不中礼”的阐释。严粲甚至在《诗缉》中说:“僖公之病在于鄙陋局促,而无深远之虑,此诗欲开广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不敢违《毛传》《郑笺》和《孔疏》设定的经义,而不得不强为说解[30](P2537-2538)。
没有了礼乐机制作为背景,《诗经》文本很容易被剥离其乐义,进行望文生义的解读,与诗之原初义、乐义渐行渐远,最终陷入莫衷一是的阐释困境之中。如徐文靖在《管城硕记》认为诗人欲使僖公崇俭,方作诗戒其不俭之行,其中的“无已太康”“瞿瞿”“休休”等词句便是提醒晋君务行节俭,与《毛诗》传笺正好相反⑤。顾镇《虞东学诗》一反成说,认为《蟋蟀》是刺僖公过于逸乐,荒于国政。牟庭《诗切》将之解读为刺晋之大夫专思逐利之事,无暇燕乐宾客,也是绕着刺诗的说法兜圈子。朱熹觉得《毛传》《郑笺》太牵强,将《蟋蟀》阐释为唐地民风勤俭淳厚,百姓闲暇饮宴时,互相劝诫之作[31](P87-88)。沈万钶跳出了刺俭的窠臼,直接体悟,将之解读为言圣人勤勉自励[30](P2538-2539)。叶适认为诗人作《蟋蟀》,意在奉劝君子知乐而毋荒,又回到了对诗文本义的直接解读中[32](P68)。这些说法,一反毛诗的阐释,正是出于对毛诗刺俭说的不满,而自立新解。但不幸的是,由于忽略了季札观乐、孔子言诗时的乐义,这些阐释只能就文本义进行阐发,因文本训诂而断以己意,形成了漫无边际的解读,其阐释也因此呈现出无边的开放性,只有能够自圆其说,便可以形成对《蟋蟀》的一家之言。
由此来看,简本《蟋蟀》出现之前,汉儒的解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经学说解,我们即便有所怀疑,惜无证据可资辨析,不得不屈为说解而求通脱。幸运的是,清华简《耆夜》为我们提供了《蟋蟀》创作的历史语境,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洞察幽微的孔镜,来观察《蟋蟀》的原初义。进而将之作为标本,分析其如何在原初义失去之后,如何形成自足的乐义,并得以被阐释。由此进一步观察其在乐义剥离的过程中,如何在赋诗、引诗的背景中被附加了更多的现实关切,成为可以被无穷阐释的开放文本。
注:
①学界关于两《蟋蟀》之关系,或以为今本《蟋蟀》由简本《蟋蟀》演变而成,参见李学勤:《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中国文化》2011年第 1 期;贾海生、钱建芳:《周公所作〈蟋蟀〉因何被编入〈诗经·唐风〉之中》,《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 4 期;黄怀信:《清华简〈蟋蟀〉与今本〈蟋蟀〉对比研究》,《诗经研究丛刊》第二十三辑;孔德凌:《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异同考论》,《北方论丛》2015年第 1 期等。或以为今本《蟋蟀》在先,简本晚出。参见刘成群:《清华简〈耆夜〉〈蟋蟀〉诗献疑》,《学术论坛》2010年第 6 期;刘光胜:《清华简〈耆夜〉考论》,《中州学刊》2011年第 1 期;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江汉考古》2011年第 2期。苗江磊:《由清华简〈赤鹄〉〈耆夜〉看战国叙事散文中的拟托创作》,《华侨大学学报》2018年第 5 期等。或以为两《蟋蟀》为子本,有共同的来源,如张三夕:《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为同题创作》,2016年第2期;李锐:《清华简〈耆夜〉续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 期等。
②据孔德凌统计,今本《蟋蟀》与简本《蟋蟀》文字重合比率高达62.5%,语句相同或相近的诗句比例有46%。参见孔德凌:《清华简〈蟋蟀〉与〈唐风·蟋蟀〉异同考论——兼论清华简〈蟋蟀〉的主题》,《北方论丛》,2015年第1 期。
③《耆夜》中“夜”古音为“舍”,“夜爵”即饮至之“舍爵”。关于饮至礼,《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杜预注言:“舍爵,置爵也。”指师返告庙后合群臣饮酒。《孔丛子·问军礼》也说:“用备乐,飨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焉,谓之饮至”。参见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 152 页。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桓公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43 页。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 421 页。
④《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 1936-1937页。
⑤徐文靖在《管城硕记》中言:“诗意乃刺其不俭,非刺俭也。向使既俭矣,而又戒之曰‘无已太康’,何哉?又《尔雅》‘瞿瞿、休休,俭也’,则诗意欲其崇俭可知。”参见徐文靖:《管城硕记》,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