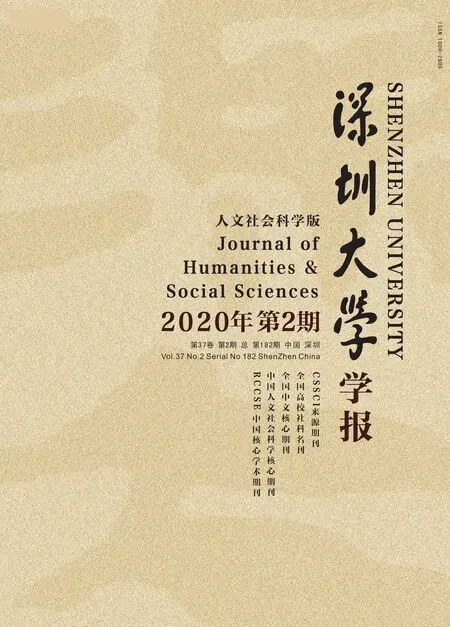作为文化的美剧:主流类型、工业、意识形态
2020-12-22常江,田浩
常 江,田 浩
(1.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2.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91)
一、引 言
美剧是美国电视剧的简称,但它其实是一个“中国制造”的概念,是美国某些类型的电视节目被中国本土的主流电视文化认知改造的结果。在美国电视业中,“剧”的概念相当淡薄。与“电视剧”含义最接近的英语表述是TV series,其字面意思是“电视系列节目”,通常指成系列、以集(episode)和季(season)为单位播出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的集群,但这类节目未必是虚构的叙事性内容。因此,不仅我们观念中的“剧”属于TV series,其他具有类似播出模式的节目如某些脱口秀(talk show)也属于TV series。作为相对晚出现的视听叙事艺术,电视剧的发展受到其所在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深远影响,并未如戏剧和电影一样形成世界通行的程式[1]。即使在中国,电视剧之所以被命名为“电视剧”,也有着极大的历史偶然性[2]。因此,本文所探讨的“美剧”,其实是美国电视系列节目中的两个最具全球流通性、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子类型:电视喜剧(TV comedy)和电视戏剧(TV drama)。至于影响力日益衰微的肥皂剧(soap opera)和不甚主流的迷你剧(mini series)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此外,考虑到整个美国电视行业近年来出现的新结构趋势,本文也将代表性流媒体网络平台 (主要包括 Netflix、Hulu、Am-azon等)播出的剧集纳入考察范围。
美剧毫无疑问是美国最强势的文化输出品之一,美剧之风靡全球甚至被很多批评者视为美国文化强权的一个重要表征,尽管“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始终伴随着争议[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1974年和1985年发布了两个关于全球电视节目流动情况的调查报告,其结果显示,尽管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全球电视节目的市场结构始终保持着“单向街”(one-way street)的特征,即主要由美国流向他国[4]。除极少数区域性特例外(如韩剧在东亚文化圈的流行以及拉美电视肥皂剧的短暂崛起),这一结构至今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5]。中国曾在改革开放初期频繁引进美剧以弥补本国制作力量的不足,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节目审批的日趋严格,美剧开始主要通过盗版DVD 渠道和民间字幕组的译介工作在中国传播。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和中美两国知识产权交易机制的不断完善,电视的观看渠道日趋多元化、透明化,美剧在中国青年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减,对美剧的消费行为亦极大地影响着中国观众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6]。因此,对美剧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的考察,就不仅是电视业内的行业议题,更是中国当下语境下可令我们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深刻社会议题。
立足于文化研究以及更宏观的批判文化理论的视野,本文尝试从主流类型、生产体制和意识形态3 个维度呈现并阐释美剧文化的深层肌理。在此基础之上,论文探讨美剧文化传播的理论化路径及美剧在全球传播中积累的经验借鉴。
二、美剧主流类型:从固化到液化
美国电视节目在诞生初期大量借鉴当时已相当成熟的电影类型体系,并十分注重戏剧性和冲突性元素的使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两种成熟且相对固定的节目类型——电视喜剧和电视戏剧——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聚集了海量的忠实观众。
电视喜剧最初脱胎于幽默的剧场表演,这种表演融脱口秀、杂耍、音乐于一体,配合现场观众的掌声和笑声,往往能够营造出十分热烈的氛围,产生强大的感染力。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电视业将诞生于英国的一种带有鲜明剧场感的叙事类电视喜剧引进播出,开始了本土的创作和生产,这就是美国电视喜剧最重要的一类:情景喜剧(sitcom)。情景喜剧在形态上有4 个显著的特征:每一集剧情相对独立的系列式叙事、多机位拍摄、以密集的对话和笑料推动情节发展、将来自录制现场的观众笑声纳入播出以营造幽默的氛围。其中,录制现场的观众笑声成为情景喜剧最重要的标志,即使是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在节目录制现场设观众席的情景喜剧,也会在后期加入笑声音轨(laugh track)来追求这种形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情景喜剧长盛不衰,在其影响力巅峰的80~90年代,四大电视网收视率最高、盈利最可观的节目均为情景喜剧。全国广播公司(NBC)于1994~2004年间播出的情景喜剧《老友记》(Friends)的 6 位主演,至今仍跻身全美身价最高的电视演员之列,足见该剧在当时创造的巨大收益[7]。
一般而言,1 集电视网情景喜剧的时间不长于30 分钟,也就是电视编排的一个档位。至于其具体的长度,则视乎电视网的广告售卖情况。随着电视媒体的日趋强势和电视广告业的日趋发达,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单集情景喜剧的时间大约从28 分钟缩短到22 分钟,这不仅体现了广告业作为美国商业电视支柱性收入来源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对情景喜剧的叙事结构产生影响——创作者不得不在比以往更短的时间里制造冲突、抖出笑料,叙事线程变短,故事涉入社会议题的层次变浅[8]。这一创作要求进一步强化了语言和对话在情节推动上的重要性。在世纪之交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不少作品,如《人人都爱雷蒙德》(Everybody Loves R-aymond,1996~2995)、《宋飞正传》(Seinfeld,1989~1998)、《威尔与格蕾丝》(Will and Grace,1998~2006,2017-)等,都具有相似的快节奏、浅剧情、以演员为中心的创作倾向。当然,在不播放广告的付费有线电视频道(如HBO)和网络平台(如Netflix、Hulu、Amazon 等),单集电视喜剧的时间一直保持在30 分钟左右。
在近15年里,情景喜剧在形式上有了较大的革新,越来越多的作品不再使用现场观众笑声,拍摄方法也改为手持摄像机的单机拍摄,以这种形式拍出的情景喜剧被称为“伪纪录片”(mockumentary),即通过一种模仿纪录片的“原生态”的严肃手段,去呈现荒诞不经的喜剧情节,以巨大的反差吸引观众。目前,伪纪录片式的新型情景喜剧俨然已成主流,近年来出现了《摩登家庭》(Modern Family,2009~)、《副总统》(Veep,2012~2019)、《办公室》(The Office,2005~2013)等成功作品;但包含笑声音轨的传统情景喜剧也仍不断有佳作问世,如《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2007~2019)和《极品老妈》(Mom,2013-)等。值得注意的是,新型的情景喜剧在调性上已不完全是幽默和搞笑的,而是融合了一些电视戏剧的色彩,这体现了美剧两种主流类型的部分融合[9]。
至于电视戏剧,则是一种比电视喜剧子类型更加丰富、文化光谱也更加多元的节目模式。与电视喜剧相比,电视戏剧与剧情类电影在叙事结构和文化气质上更加接近:一方面,比较语言的锤炼,电视戏剧更加重视对情节和人物的塑造;另一方面,比较主题上的娱乐性和轻浅化,电视戏剧往往更专注于挖掘在形式上更加严肃和深刻的社会主题。在某种程度上,电视戏剧实际上是古老的西方戏剧艺术的当代媒介化形式,它在诸多方面继承了舞台戏剧、戏剧电影和广播戏剧的传统,也融入了电视媒介诸多的特征,比如对冲突性的格外强调。因此,比起其他类型的戏剧,电视戏剧更加注重对警匪(crime drama)和法政(legal & political drama)两个子类型的深耕,概因两者包蕴的冲突性元素最为丰沛。这两种子类型的剧集也为美国电视戏剧贡献了数量最庞大、影响力也最深远的精品[10],前者代表如《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1990-)和《犯罪现场调查》(CSI: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2000-)成为两个行销全球的系列(franchise);后者代表如《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1999~2006)、《纸牌屋》(House of Cards,2013~2018)、《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2009~2016)等,均在美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此外,一些对社会和人性问题有深入挖掘的电视戏剧作品在近年来颇受瞩目,它们往往赢得超出电视领域影响力的荣誉,成为更独特的文化精品,如《广告狂人》(Mad Men,2007~2015)、《绝命毒师》(Breaking Bad,2008~2013)等。这表明较之电视喜剧,电视戏剧往往有更大的叙事和表现空间在更加多元的标准体系内去追求文化和历史价值。
在形式上,电视戏剧也与电视喜剧有较大的差异。通常,单集电视网戏剧往往占据两个播出档位,也就是1 个小时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1 集电视戏剧的时间长度往往可达45 分钟左右,是传统情景喜剧的两倍,这显然更有利于冲突的营造和人物的塑造。而付费有线电视频道和网络平台的戏剧作品则往往有单集1 小时的容量。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播出时间甚至可以更长。如Netflix 的热门作品《西部世界》(Westworld,2016-) 的第一季第 10 集就长达90 分钟,几乎相当于一部叙事电影的容量。
尽管长期以来,“电视喜剧—电视戏剧”的“二分法”构成了我们对主流美剧类型化体系的理解,但随着播出渠道和电视文化的融合趋势的加剧,这套原本高度固化的类型体系在近年来呈现出显著的液化趋势。一方面,电视喜剧和电视戏剧在主题和类型上开始不再泾渭分明,电视戏剧的热门题材如政治,也开始成为电视喜剧深耕的领域,如HBO推出的广受好评的《副总统》,就借助对一位女性政治家(历任国会议员、副总统和总统)的从政经历的戏谑性表现,讽刺美国政治体制,影射特朗普政府的荒诞行径。另一方面,电视喜剧也越来越重视对完整、自洽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对剧情冲突的营造,以使情节和人物更加丰满立体,突破了传统情景喜剧较为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代表性的作品如近两年广受好评的《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The Marvelous Mrs.Maisel,2017-)等。但总体来说,融合的趋势是喜剧的戏剧化,即主流电视喜剧通过对各种戏剧元素的改造和吸纳,以实现对自身文化深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①。因此,传统电视喜剧的衰落是美国主流电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趋势,以至于主流电视评论界提出了“电视喜剧的未来必然是喜剧和戏剧的融合”的结论[1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电视喜剧在形态和叙事上受电视播出方式和产业模式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一旦整个电视业的生态因技术和经济原因发生改变,电视喜剧所受的冲击也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类型液化的趋势并不是电视文化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内部、外部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建构的产物。电视节目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社会现实的想象性建构[12],必须置于所处的宏大产业和意识形态结构之中加以解释。对于美国的电视文化来说,历史悠久、合法性根基深厚的商营电视体制和商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理解美剧及其文化的重要依据。
三、美剧工业:强势的平台与虚拟的问题域
从体制和组织的视角来看,美国电视节目的本质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其通过对特定的成长路径、人物关系、价值体系和社会形态的宣扬,实现对于主流美式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维护[13]。在操作层面,美国的电视产业形成了高度商业化体制、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以及以季播制为主要特色的内容生产机制,这3 方面的特征不断强化电视作为美国社会主流文化最稳定的承载物和维护者的角色——通过向观众提供成本高昂、娱乐性强、价值中庸的节目,美国电视文化的面貌始终呈现为一种“精致的通俗”和“世故的纯真”[14]。
作为美国电视节目及其文化的代表,美剧的生产和传播自然也有着牢固的工业基础,这种工业基础主要体现在2 个方面:第一,广告售卖和付费观看作为生产收益的来源,通过以订购制为主的生产方式,主导及制约着美剧形态和内容的发展革新过程;第二,立足美国、放眼世界的电视传播格局始终追求消弭观众在接受时可能面对的文化障碍,为美剧的有效传播设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
我们首先来看盈利模式对美剧内容生产的影响。目前,主流的美剧生产模式是订购制,播出平台从创意阶段开始,即介入制片公司对一部剧的制作过程,并将这一过程贯穿至该剧制播的始终。简而言之,制作公司从有了对一部剧的创意那一刻起,就要与目标平台进行沟通,既寻求合作的可能性,也要听取平台的意见,对大纲、剧情、人物关系、人事安排(尤其是演员人选)做出必要的修改。即使如此,在制作公司林立的好莱坞,也大约只有5%的创意(在电视行业被称为pitch)能够最终进入试播集(pilot)的制作阶段。同样,在播出过程中,如果观众反响不好,平台也可以做出终止采购、不再续订的决定[15]。在美剧行业,通常将制作公司按照平台的要求对剧本做出反复修改的过程称作“development hell”,意指这一过程之痛苦异常。不难发现,订购制强调的是播出平台在电视剧生产过程中的话语权。而相对于多如牛毛的好莱坞制片公司,全国性美剧播出平台始终保持极为有限的数量,维系相对平衡的寡头垄断格局。通过订购制,制作公司之间的竞争长期处于高度白热化的状态,这确保了只有那些最符合平台需求的创意和制作,才能够最终播出。
目前,主流的美剧播出平台依盈利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电视网(TV network),以5大全国性电视网为代表,面向普通大众,以收视率(ratings)为依据,通过售卖广告获取利润。这是美国商营电视体制下最常见的产业模型,本文不再赘述。第二类是付费平台,主要包括传统电视频道HBO、FX 等,我们也可将 Netflix、Hulu 和 Amazon 等付费流媒体网站归入其中,这类平台通过直接向观众(订户)收费的方式盈利,与西欧公营电视有相似之处(但订阅费收取完全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广告很少或干脆不播广告,这也就决定了一部剧的忠实观众人数(loyal viewership)成为评估传播效果的核心指标,收视率不再有意义。有些流媒体网站甚至会一次性放出整整一季的内容以迅速获取社会影响力,这也与电视网必须要通过维系固定的周播和季播以“拉长”一部剧的生命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增大广告收益的策略形成对比。值得一提的是,付费平台播出的剧集往往比电视网剧集更具文化深度和社会批判力。这是由3 个原因造成的:付费平台在诸多领域不受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内容规制约束②;无插播广告的播出模式使单集信息容量更大;有经济条件付费的观众往往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因此,近年来颇有一些讨论认为付费看剧的模式将成为美国电视行业的未来[16]。
然而,无论采用哪种盈利模式,剧集播出平台都以观众的娱乐需求和文化喜好为生命线,因而收视数据相对于任何其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指标,都对一部剧的存在方式有着最终的裁量权。表面上看,美剧工业机制赋予了观众很大的权力,但实际上,这一机制强化了平台的话语权,与电视播出市场的寡头垄断结构互为给养。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电视剧,美剧的平台烙印是最明显的,播出机构是美剧真正的主宰者,一如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指出的,表面上自足、自治的大众审美,其实不过是电视网制造的一种自主性的假象,是一种粗鄙的民主思想对审美领域的暴力征服[17]。播出平台向观众提供极为有限的选择,这些选择在赋予电视观众文化自主的想象的同时,也默然不语地将其他不符合工业逻辑的选择排除在外。
至于美剧“立足美国、放眼世界”的传播格局,则是上述美剧工业模式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美国国内种族构成复杂、生活方式多元的现状,决定了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美剧必须采取 “最大公约数”式的传播策略,以弥合分歧、掩盖矛盾为主要外在形式,这种形式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剧畅行全球的重要依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以《豪门恩怨》(Dallas,1978~1991)、《老友记》(Friends)、《24 小时》(24,2001~2010)、《生活大爆炸》、《绝命毒师》(Breaking Bad)和《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2011~2019)为代表的具有极强全球流通性的美剧,其文化旨趣大多是脱离美国社会现实的,或以一个并不存在的伪社会问题去引导人们展开对人性的思考,或通过营造文化和谐的大都会乌托邦以掩盖大都会其实是种族和阶级矛盾最尖锐之地的事实,或干脆遁入想象的世界。它们所提供的是一种面向全球中产阶级(global middle class)的文化想象,在大多数时候会被理解为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不仅仅是美国)问题的文本解决方案。因此,在美剧的传播经验里,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法则其实是有着独特的工业基础的,这个工业基础决定了根植于美国社会土壤、展现社会矛盾冲突的现实主义作品始终不会成为主流,美剧在内容生产上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冒犯”(no offense)。借助精细化、高概念的制作技术和符号手段,美剧实际上构造出了一个虚拟的“问题域”(problematic)[18],从问题的提出本身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再到观众通过对这一方案的消费所获得的精神满足,都缺少实实在在的社会根基。美剧逃避真正的社会现实问题,这在近年来不断受到学术界和评论界的批评。比如美国《新墨西哥法律评论》曾经专门出版过一期特刊,讨论《绝命毒师》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文化的种种误用,并声称应当将这部剧作为法学院的教学案例[19]。而评论家Noel Murray 也曾指出,《生活大爆炸》的走红并非因为它反映了极客(geek)群体的某种真实的状况,而是它的创作者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个群体身份的全球性,以及其中蕴藏的市场潜力[20]。
当然,这不是说美剧作为一种工业化产品,在文化上完全受制于其产业逻辑。事实上,通过对美国国内矛盾的回避,美剧获得了一种全球流通性,并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观众带来了不同的文化想象,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实现了跨文化赋权,这种对话是有益处的。只不过由于美国电视产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强大地位,美剧的这一传播格局便难免带有了单向的、灌输性的色彩。对美剧的文化属性的探讨,必须要结合其独特的工业背景,否则就必然会得出偏颇的结论。
四、美剧意识形态:去激进化
对于美剧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学者们大多持有批判的态度,一种常见的话语是:作为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美剧始终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承载物和鼓吹者存在的[21]。通过精美的符号包装和伪装的隐喻体系,美剧向世界传递经过美化的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并宣扬一种虚假的社会批判意识[22]。这些判断当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将分析止步于此,不对美剧达成上述目标的话语编织方式进行深入的分析,我们对美剧的意识形态意图的理解,也只能是一知半解。事实上,在70 多年的历史里,美剧早已围绕特定的意识形态意图形成了一系列叙事和表现上的成规,这些成规往往在与各种生产要素的互动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并在某些时候为另类的解读实践预留空间。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美剧的意识形态传播是充分利用一种带有跨域、跨文化色彩的意义协商空间得以实现的,这一意义协商空间并不是美剧自己开拓或营造的,而是一种历史和政治的产物,是在全球化、后殖民、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时而彼此融合、时而相互抵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被塑造出来的。在20世纪,经由英语通俗小说、好莱坞电影、IP 化的动漫产业以及美国电视剧和综艺节目等一系列媒介文本形式,这一意义协商空间不断被巩固和扩大,其内部的话语构成则体现为一种关于“现代的”生活方式的知识,这种权力话语,用斯皮瓦克的话来说,就是“将不幸的自然化,再将这种自然化浪漫化”[23]。例如,不少针对美国情景喜剧的研究都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其剧情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浪漫化,包括对性别差异的掩饰、对既存全球种族秩序和劳动分工的合理化,以及对阶层固化现象的巩固[24]。我们不能将这种再现策略简单解释为 “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因为这被观众广泛应用于解读实践的话语空间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一个全球性的结构性问题,即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一种全面的保守化。美剧扮演的意识形态角色的本质乃是“去激进化”,即消弭革命的需求,将进步界定为一种渐进式的改良,想象一种非对抗性的全球社会秩序。
其次,美剧的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接合(articulate)不同的思潮和话语,在策略上维系其去激进化特征的稳定性。例如,在 20世纪 70~80年代,美国情景喜剧在叙事上往往带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以不同方式解构关于社会和家庭制度的各种主流话语,通过一种近乎超现实主义的表达,不断瓦解60年代反传统运动在社会共识中存留的芥蒂,令观众以犬儒主义的态度来回避对真正的社会变革的参与,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情景喜剧《一家大小》(All in the Family,1971~1979);而这一时期的剧情片则致力于传达一种高度稳定、高度整合的社会文化想象,几乎不触及具体的社会问题,虚构性和叙事性都很强,逃避主义色彩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则是风靡全球的《豪门恩怨》。而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化观念深入人心,在情景喜剧中,大都会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开始取代中产阶级的近郊小镇,以及抽离具体时空符号特征的“非地域”,如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成为美剧故事主要的发生地,以隔绝真正的“生活和生活方式”[25],各种类型和题材的电视剧不断通过对超越阶层、性别和种族的友情的塑造,来假想一个人人平等的全球性的社会,这一时期的美剧由于在符号形式上更具全球性色彩而集体性地赢得世界影响力,如HBO 的《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1998~2004)和 ABC 的《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2005~)等。而这一时期的剧情片则越来越致力于打造一套 “伪现实主义”话语,不断通过人造的怀旧氛围和“西部想象”去“揭示”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广泛存在的“问题”,正如很多人对 《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1999~2006)和《纸牌屋》(House of Cards,2013~2018)的批评中所指出的那样[26]。简而言之,美国的电视喜剧和电视戏剧不断通过对社会问题予以讽刺(satirize)和戏剧化(dramatize)的方式,解构了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和严肃性。美剧在意识形态上的“去激进化”功能同样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美剧的“去激进化”意识形态功能并非长期持续、稳定地践行,而是不断受到各种新出现的社会因素的挑战,因此另类的内容和另类的解读实践始终不乏生存空间。全球电视行业在数字化转型和互联网分发领域的革新为电视剧在意识形态上的突破带来了新的契机[27]。例如,以Netflix、Hulu 和Amazon 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不但在播出机制上打破了传统电视行业的诸多成规,在文化上也借助以私人化接受为特点的订阅模式实现了诸多突破。很多新的电视剧(或网络剧)由于不需要取悦一般意义上的“大众”而逐渐抛弃传统美剧“不冒犯”的原则,开始刻意追求收视审美体验中的疏离感甚至不适感,以传递带有实验色彩的观念,如 Hulu 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2017~)对反乌托邦的描摹,以及 Netflix 的《爱、死亡与机器人》(Love,Death & Robots,2019) 对各种“反电视”元素的使用等,都值得我们进行理论化的考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旧的惯例当然会保持惯性,但数字技术对电视行业的冲击带来的显然不止是符号或叙事层面的断裂,更有可能是一种文化范式的颠覆。
五、结论与讨论:美剧文化的经验借鉴
前文归纳了美剧文化的三个基本属性:主流类型上的液化倾向、工业生产上的平台主导体制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去激进化”策略。这3 种基本属性决定了美剧作为一种文化所必然具备的全球流通性。通过类型和内容上的“最大公约数”原则并借助在历史中形成的全球流行文化的协商空间,美剧拥有强大的跨文化传播的能力;以平台为主导的工业体系确保美剧行业得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盈利策略,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保持文化和品位的稳定性;“去激进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将美剧包装成一种温和的、只拥有表面效度的“现代文化”的媒介样本,在最大程度上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兼容。
对于中国的电视剧行业而言,美剧在全球传播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值得批判性参考。
一方面,尽管美剧的主流类型、生产体制和意识形态传统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政治成因,但整个美剧行业自始至终坚持建立自身独特的制片、审美和文化标准体系的努力,这是我们理解美剧时不可忽视的能动性因素。在经济和政治因素之外,美国电视业长期保持着锐利的自我批判传统,各主流奖项(尤其是艾美奖和金球奖)也致力于树立自身独立、权威的形象,为电视的专业话语在行业生态塑造的角色中保持一席之地。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电视从业者群体的一种职业自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即使在结构性因素难以被个体努力改变的情况下,美国电视行业仍长期将“品质电视”(quality TV)作为一种通行的标准,努力协调商业利益和节目品质之间的关系而非一味让后者屈从于前者[28]。这种对于品质的坚持将在传播的过程中有效地作用于观众的微观心理层面,产生直接的吸引力[29]。
另一方面,在对电视剧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划时,美剧带来的重要启发是应更多着眼于规划电视剧的意识形态角色(ideological role),而非直接呈现特定的、结晶化(crystalized)的意识形态本身。从构成本身来看,美剧的意识形态光谱是十分多元的,但这种多元性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角色设定,那就是“去激进化”。这当然与美国社会在种族、文化和宗教上的多元性有关,却也必然是美国工业文化在一个世纪的全球传播经验中形成的一种自觉的策略。在中国电视行业的生产实践中,无论将电视剧作为国家话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期望将其打造为旨在赢得价值认同的商业产品,明确一种适宜的意识形态策略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研究美剧的目的不仅在于理解这种具有全球流通性的文化产品本身,更在于对其经验进行归纳和评析,为本土的文化传播实践所用。尤其是,在我们努力构建文化“巧实力”,力图通过多元叙事手段和媒介渠道“讲好中国故事”的当下,美剧的文化建设与传播策略具有独特的借鉴意义。文化形象的塑造和文化价值的传达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从内容生产到产业模式、再到意识形态塑造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我们回归媒介内容生产机制的历史,立足于媒介传播经验的全球比较,尊重价值生成与接受的一般规律,做出既有理论考量、又适应当下全球传播语境的制度设计。具体而言,对于中国电视剧的“出海”实践来说,从美剧为我们提供的经验出发,如何探索出一种日常化的、后结构的(post-structural)跨文化传播策略,是决定这一文化样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巧实力”、承担“讲好中国故事”职能的关键所在。所谓日常化,就是寓文化、政治价值元素于商业的、流行的叙事形式之中,积极融入并参与由电视剧所代表的全球性“温和的现代文化”样板的塑造;所谓后结构,则意指在电视剧的生产和传播中,我们须不断反思客观存在的中西方文化差异在现行传播结构中制造的二元对立思维,并立足于呈现电视剧叙事和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容纳多元文化元素的电视剧话语体系。总而言之,电视剧的娱乐、教育和对外传播功能完全可以通过适宜的表达手段和机制设计实现有机协调。
正如我们对美剧的理解必须要回归美剧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样,以美剧为参照物反思中国电视剧的现状和问题也必须回归自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之日起的全部历史经验和行业规律,这项工作有待更多的研究者探索、完成。
注:
①需要将这种趋势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风靡一时的“戏喜剧”(dramedy)区分开来。作为一种混杂的电视节目类型,戏喜剧从未在主流电视文化体系里获得显著地位。
②这一状况的主要法理依据在于付费有线频道和流媒体网站使用商业电缆而非作为公共资源的无线频谱传递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