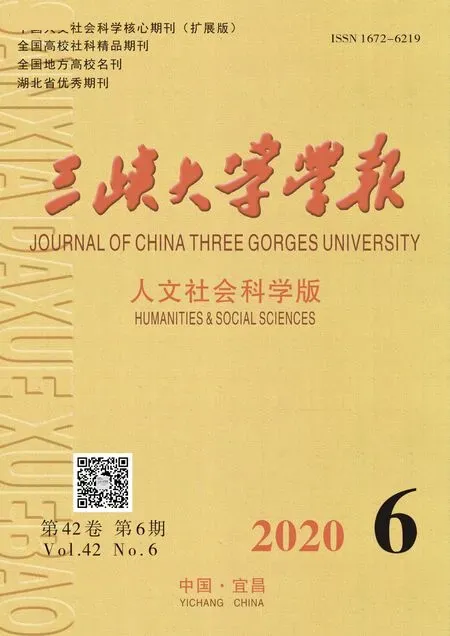浅析新媒体元素对当代舞蹈创作与传播的影响
2020-12-20薛芸芸
薛芸芸
(三峡大学 艺术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20世纪末以来“新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等领域。新媒体具有“高度的交互性、自主参与性、共享全球化、受众个性化、内容多元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等时代特征。”[1]其对人体感官体验的拓宽吸引着各行各业“探险家”们对这项新技术不断进行探索与尝试。艺术领域亦是如此,艺术创作上旧有的艺术观点被不断地打破、重构,新的创作方式层出不穷;在艺术传播上常会在几种不同的媒介之间穿梭,并自由结合,或者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将传统艺术媒介进行重写。
舞蹈艺术作为以视觉为主的审美形式深受影响,以西方现代派舞蹈家为首的艺术工作者对传统舞蹈进行大胆解构,使逐渐僵化的单一审美范式被重新审视并加以修正。同时,众多视觉艺术参与其中,通过相互启迪、相互影响,推动当代舞蹈多元发展,产生更为多元化的艺术主题,将身体、身份、时间、场所、科学等话题纳入舞蹈艺术的讨论范畴。本文拟从新媒体技术发展与舞蹈视觉机制转变的视角,探讨新媒体发展中哲学思潮、社会视觉、传播途径等的改变对当代舞蹈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以期对当代舞蹈在创作及传播中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复杂性转变做出一些梳理。
一、新媒体在舞蹈艺术中的哲思
1.视觉经验不再“唯一”
在新媒介被广泛使用之前,我们偶尔也会对视觉经验带来的信息产生怀疑,而在此之后,“我们已无法再断言”成为确定的事实。当互联网新媒体、移动终端媒体、数字媒体不断渗入人们的生活时,快速变换、消失的视觉经验早已打破几乎所有建立在稳定知识结构之上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某些技术上的手段,通过新媒体重现历史,改变现实,视觉丧失了它最重要的可信度,而随之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知识也变得不再可靠。这也见证了康德在其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预见到的问题“依据经验概念的综合统一,可能是完全偶然的,要是那些经验概念不是建立在统一的先验基础之上的话。不然,现象将会大量涌入心灵……由于缺少与普遍自然律一致的联系,知识与其对象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将会崩溃。”[2]
20世纪新的视觉经验中,“没有任何持久的经验”成为唯一能持久持续下去的特征。这对以视觉呈现为主要审美形式和传播形式的舞蹈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艺术最初的表达为模仿及真实再现,若呈现的不再是真实的,那么它将如何再与观众产生共鸣?
新媒体对视觉的发问将舞蹈艺术从历史的固化中解脱,并将其引入到更现代性的问题中去。对于康德的忧虑,哲学界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叔本华以“意志”替代康德的“先验统一”,以非理性主义认为每个人“自身不是别的,只是意志,他的意志活动独立存在,而且只有在他每一时刻的个别活动中才需要特殊的决定。”[3]将个体感官信息引向整体直觉感受,无论器官如何,其所有的意识融会贯通则会成为一种律令。美国心理学家史坦利·霍尔则给出了悲观的预期,认为不可靠的感知只会带来分崩离析的知觉综合。到底如何才是有效的经验被哲学界反复讨论,在这其中,詹姆斯和格林博格则更倾向于“联想主义”,“他俩都认为任何感觉,不管看上去多么重要,总是记忆、欲望、意志、期待及当下经验的一种混合”[4]。美学理论在身体与感觉、知觉之间不断讨论,这也在不同方面影响了艺术家对于身体、时间、破碎与整体等方面的思考。
2.单一叙事转向联想主义
在视觉经验已经无效的当下,模糊的感官认识、无序的时间逻辑、抽象的身体表达给予了艺术家更大的展现空间,这也促进了西方现代舞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例如新先锋派舞蹈家摩斯·肯宁汉与作曲家约翰·凯奇、视觉艺术家罗伯特·劳申伯格共同组成了“追求混合效应、跨越时间的多媒体表演艺术创作‘铁三角’。”[5]受黑山学院派影响,摩斯·肯宁汉认为单纯的舞蹈动作本身便具有存在的意义,并极力打破舞蹈艺术与日常单一线性叙事思维的惯性,他开始尝试通过电脑对舞者姿态随机抽签的“机遇编舞法”进行舞蹈编排,新媒体技术介入的新时空效果呈现出偶然性的舞蹈编排,呈现出非人力操作所为的逻辑线索。如《旅行日志》《多重虚构》等作品,呈现出将情感因素摒除在外的纯动作舞蹈,这种偶发性、交互性创作也为舞蹈编排打开一条新的创作思路。
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舞蹈编排引入了新媒体技术,追求混合效应,从而导致视觉机制发生变化。知觉被悬置于线性时间及单个感官之上,促进舞蹈艺术家追求用更为抽象的肢体语言蒙太奇的手法来展现他们想要呈现给观众的“真实表达”。对新思潮的解读与新媒体的运用为舞蹈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舞蹈成为宣泄内心情感的一种语言。舞蹈的创作目的从呈现发生了什么逐渐转变为表达了什么,知觉散布于或者分散于任何必要的综合之外,传统表演中无法呈现的舞蹈演员的眼神、细微的肢体表情可以通过大屏幕呈现,细节与综合感官在当代舞蹈中和谐共处,大量的新媒体表演艺术实验也为新媒体舞蹈创作提供了大量灵感与素材,“梦幻”般的新媒体舞蹈也为舞蹈艺术的创作及传播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二、数字技术对舞蹈创作的影响
在实践领域,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让观众习惯了一种新的视觉知识方式。互联网媒体、移动媒体以及数字媒体的大量使用将跨越主题和边界的资讯展现在受众面前的同时,也将种种相关联的技术巧妙地置于一个“没有等级结构的约束性和单一性的情况”[6]下,在联想主义视觉审美下的新媒体舞蹈艺术不仅仅需要通过肢体语言,更要借助灯光、空间、影像、音效甚至与嗅觉相关的艺术装置等技术手段对作品进行更多层次阐释,这也使深度媒体化的当代舞蹈在创作当中具有了一些传统舞蹈创作所没有的特征。
1.数字化舞蹈作品的创作
摩斯·肯宁汉带给舞蹈的启示不仅仅在编舞逻辑上给予了后人灵感,也在舞蹈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结合上开创了先河。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利用软件“虚拟现实”成为了可能,这项技术也被运用在舞蹈创作的构思即呈现上。在舞蹈的编排上,编舞人员可以运用三维人物模型进行编排、演示,甚至加入想要呈现出的舞台、灯光效果对作品整体效果进行演示,加速、便捷化各项环节的呈现,而在这过程中甚至不需要舞者参与其中,也使得舞蹈编排这一环节更加独立、专业。这项技术的逐渐深入,也促使虚拟电子舞蹈从现实舞蹈创作中的一个环节逐渐成为一项具有艺术审美效果的完整作品。通过3D软件的细致刻画及动态捕捉技术对舞者动作细枝末节的捕捉,电脑可以完美地在虚拟空间中呈现舞者想要表达出的情感,让舞者实现舞动的身体到思考的身体的跨越之后,拥有了数字化的身体,再次弱化了物理空间及肢体技巧对舞蹈呈现的障碍。
2.数字化舞蹈作品的呈现
在传统舞台表演中,舞台由面向观众的三面墙所组成的剧场组成,而当代舞蹈在创作及表演中在新媒体技术的辅助下不断地向有限的空间和叙事发起挑战。新媒体舞蹈将互动媒体、声音、光效、舞蹈甚至舞蹈装置进行有机结合,多元的组合将舞蹈以更为立体的形式呈现。大屏幕的实时影像及预制影像中电影技巧的运用为观者提供更具引导性的观看体验,呈现出传统舞蹈舞台所难以展现的对多维度时空的局限及身体细节,通过舞蹈影像形成的新的时空线索丰富舞蹈作品内容,揭示作品内涵,让视觉的角度不单单停留在“四面墙”内,叙事也不仅仅在一条时间线中。
数字技术在舞蹈中呈现的多元的交互方式也为现代舞蹈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审美范式。如2012年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在春晚的一场《雀之恋》将数字技术与舞蹈艺术相融合,给全国的电视观众们带来了无比惊艳的视觉审美。灯光、音响、全息三维技术等技术手段的巧妙运用,让花鸟、山水、蝴蝶、星辰等景观在舞台上栩栩如生,所营造的幻境让虚拟与现实产生碰撞,瞬间就将观众带入到舞蹈所要描述的故事背景中去。在作品尾声时,舞者与电子背景屏中正在开屏的孔雀尾羽所营造的梦幻华美的氛围也将舞蹈推入高潮,浸入式互动舞蹈将舞者心中只可意会之境以视觉形式淋漓尽致地进行呈现。在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日渐成熟的当下,舞蹈作品与观众更深入的交流形式也在逐渐成型。除了增强舞台作品张力外,观众通过触摸感应、距离感应等可互动的形式,可以完全参与进舞蹈创作表演中,在浸入式的艺术体验里完成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技术的进步在改变舞蹈自身语言和逻辑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观看者对于舞蹈的认识,这对推动舞蹈艺术回归大众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3.数字化舞蹈影像的诞生
舞蹈影像在现场空间中大放异彩的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在屏幕舞台甚至是传统舞台上成为独立艺术形式的可能。早期舞蹈影像大多作为辅助舞蹈作品的工具,用以记录、传播学习,拍摄角度及剪辑手段以还原舞蹈为主。而随着新媒体舞台对舞蹈影像更加细致化的要求,加强肢体表现力,增强影视文本叙事为主的舞蹈电影开始逐渐成型。作为舞蹈与电影艺术深度交叉的复合型艺术形式,将舞蹈从三维艺术转化为二维艺术的同时,将更多的媒体艺术元素与舞蹈本身进行有机结合,蒙太奇的视觉手法让光影、空间、肢体都成为讲故事的手段,镜头语言让我们的观看稳步地跟随着画面逻辑。新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的信息传播便利也让数字化舞蹈影像成为可以让更多观众所接触到的艺术形式。
在舞蹈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对于舞蹈影像的成功探索当属成立于1986年的英国DV8肢体剧场。其“DV8”名称的由来,一方面DV是video dance的简称,即舞蹈+影像;另一方面DV8的发音近似deviate,而被赋予了反常、背离、不同寻常等寓意。该舞团将夸张、幽默的肢体动作和影像技术相结合,赋予舞蹈艺术一个全新呈现和鉴赏方式,堪称舞蹈艺术与影像技术完美结合的先驱,其代表作有1986年的《My Sex,Our Dance》;1989年的《Dead Dreams of Monochrome Men》;1993年的《MSM》;1997年的《Bound to Please》;2005年的《Just For Show》。
这种独立的新兴艺术形式更适于呈现关于时空、意识等哲学问题,并且在其表现手法中侧重雕塑、空间、装置艺术等辅助手段,以视觉艺术与观念艺术的创作思维对作品进行阐释。如法国格勒诺布尔国立编舞中心艺术总监Yoann Bourgeois的作品《梦都去哪儿了》,选择在阿维尼翁新城以他常用的阶梯作为道具进行拍摄,作品中不同人种、性别、肤色的人围绕阶梯不断上下攀爬,作品充分利用录像艺术作品的创作技巧,使用片段反复回放的剪辑创造出从阶梯高处坠落、上升的画面,镜头中间穿插天空、焦躁、绝望与追寻,在往复的跌落与复原中,作者试图充满诗意的简述手法带我们一起思考“梦”的意义。数字化技术在拓宽舞蹈范畴的同时,也逐渐弱化了舞者个人与作品的关系,它所富含的包容性让新媒体环境下的舞蹈不再拥有固定模式,一切皆成为可能。
三、新媒体元素在舞蹈传播中的影响
1.消失的边界——数字影像催生舞蹈新场域
更大的自由度促成了更多复合和交叉。以舞蹈影像为主的舞剧、剧场、电影、动画、游戏、软件、装置、实景演出等层出不穷,观众欣赏舞蹈艺术作品的场域也不再局限于舞剧院,他的选择呈现出多种可能。多种综合艺术门类已难分彼此,除去在艺术节(展览)、电影节(展览)、舞蹈影像节(展览)等艺术盛宴中舞蹈作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出现之外,产品广告、综艺选秀、主题游戏、专业APP等娱乐化、商业化的主题中舞蹈也深度融合其中,步入大众的生活。
2.圈子的泛延——移动终端媒体助力舞蹈传播
随着Yotube、Twitter等社交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以及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日益普及,“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明星”。组织机构或公民个人通过网络途径对外发布信息的时代已然到来,“信息时代大众传播的类型化,使得受众理论从传统的‘传者本位论’向‘受众本位论’转移。”[7]高效的个体移动传播平台犹如一个自带磁石的核心,对舞者或者艺术机构感兴趣的用户只需要通过关键词搜索、话题推荐等,便能搜寻出与他们相关甚至是本人所发布的信息,通过留言、私信等形式也可与相同爱好者进行交流。这种互动方式也极大地提升了艺术家或机构与观众的粘性。相应地,机构或个人发布的作品预告、视频宣传、活动信息、个人观点等咨询的传播效应也可能以几何级的效应进行传播,从而吸引更多核心受众人群。而某些话题、热点或核心受众人员的转发、评论也在逐步地扩大圈子的边缘。人们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终端传播平台将生活、娱乐与艺术进行有机结合,机构或舞者个人不再神秘的令人难以接近,舞蹈核心圈子不断地向外泛化。
3.层级的交织——融合媒体中的复合化传播
新媒体的融合不仅表现在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也表现在各个传播媒介之间的融合。在融媒介时代,以网络为中心的传播渠道的复合化对舞蹈艺术传播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想要得到舞蹈相关的任何讯息,网络也许是首要选择,音频、图片、文字信息、视频让舞蹈爱好者可以全方位了解想要的资讯。相应地,专业舞蹈视频与综艺性舞蹈节目也被放在同一场域中进行讨论。舞蹈艺术,从曾经仅以少数艺术精英的人际环境传播方式过渡到当下娱乐化、大众化的融合媒体复合化传播,舞蹈艺术的传播与交流从未如此的自由。
四、结语
在新媒体环境下,舞蹈艺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深度融合的倾向在拓宽舞蹈艺术表演领域的“繁荣”的同时,也在从各个角度消减“舞蹈”本体的意义。深度媒体化的舞蹈将舞蹈家肢体由舞动着的身体逐步以虚拟的数字化的身体替代,用于呈现作品的舞台也由现场空间向屏幕舞台、虚拟现实舞台甚至走向赛博舞台,肢体艺术逐步数字化的过程,舞蹈也被无情地去中心化。皮娜·鲍什作为“舞蹈剧场”的确立者,新媒体艺术的先锋,也在晚期的一次采访中对舞蹈本体与舞台效果的重要性中两难选择(舞蹈动作本体和舞蹈效果呈现)。避免对“舞蹈”过度制造或过度分析的讨论也逐渐展开,对于新媒体元素下当代舞蹈的发展中“弱”化的舞蹈究竟是舞蹈发展的未来还是仅仅昙花一现等问题,有待业内人士展开长期、深入地调查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