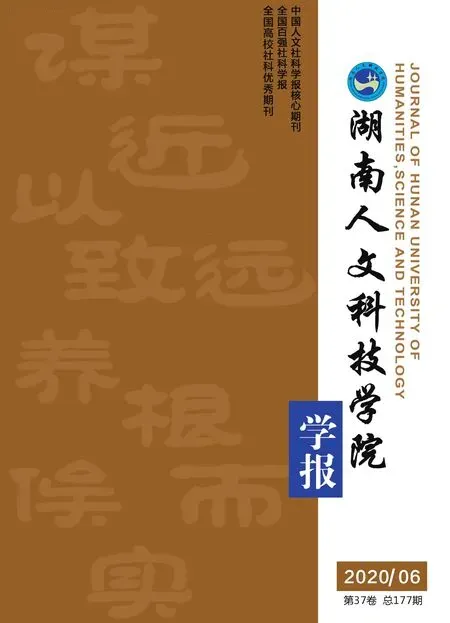再论曾国藩道德领导
2020-12-19周海生
周海生
(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市情研究中心,江苏 淮安 223005)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1]。论者曾在《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刊文指出过,近代重要历史人物曾国藩治术中蕴含道德领导力因素。其具体体现在,注重以“仁”“礼”等价值观统领军队;以“朴实有农夫土气”“忠义血性”为标准,遴选湘军成员;营造道德基础上以“彼此相顾”为目标的运转机制和以质朴为特征的军队风格;以道德判断为依据辨是非、“兴举劾”。用伦理学概念谱系观照晚清政治人物曾国藩“思维世界”中的道德理性和“历史世界”中的领导实践,还可以看到理性和实践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这一运动过程呈现出道德理论知识与道德实践行动合一、个人道德记忆与家庭道德记忆合一、道德软性约束与道德硬性约束合一的特征。危机时期,人们比平常岁月更不能容忍从政人员的道德缺失,也不能容忍用道德理由当做怠政、乱政的借口。再论曾国藩的道德领导,从中寻求伦理鉴示,将有助于了解危机中从政者的伦理轨迹,进而提升从政者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曾国藩道德领导是道德理论知识与道德实践行动合一的过程
(一)曾国藩开展道德认知
价值体系建立的前提和基础是进行道德认知,获得道德知识。曾国藩道德知识从哪里来?不言而喻,成长经历中的生活环境、质朴乡风、艰难生活、长辈的言传身教是道德认知的基础和来源,自然给曾国藩的价值观打上烙印,使其获得初步的、尚未系统化的道德知识。求学和交游经历也增进了曾国藩的道德认知。曾国藩幼年受教于父亲曾麟书,后来曾就读于家乡的涟滨书院和省城的岳麓书院。湖南经世致用学风通过书院,特别是岳麓书院厚植于曾国藩思想之中。青年时期曾国藩还先后结识刘蓉、郭嵩焘、陈源衮、何桂珍、何绍基、吴嘉宾、吴廷栋、窦垿、冯树堂、邵懿辰、刘传莹等人。有志好友相互间的箴劝让曾国藩颇为受益。
尤为重要的是,科举经历是曾国藩获得和储备道德知识的通道和过程,促成其道德知识的体系化。
始于隋唐时期的以进士科为核心的科举制度,到了清代已经相当完备,这一体现就是信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的文官选拔史,就是信度(不同考试条件下考试结果的一致性)、公平性和效度(考试结果、分析、应用与考试初衷的一致性)之间互相争斗的历史。在这一斗争中,信度和公平性渐渐占据上风。选拔的方法、过程、结果越来越可靠,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公平”,但在效度上,即通过考试为王朝治理选贤任能上来说,“选拔出来的文官也越来越与贤能脱节”的问题始终存在[2]。清代科举体制是一金字塔结构,大致可分初、中、高三级。初级主要是“秀才”试;中级是乡试,三年一比,考取后成为举人;高级是会试,在乡试次年举行,中式为进士,之后还有殿试、朝考,优异者选入翰林院。明清朝政治惯例,非进士不得为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内阁。且明清政体中无宰相,入阁成大学士即被世人视为宰相,因而翰林的社会声望和期望值都极高。曾国藩是“两榜”正途出身,从秀才到登乡试桂榜、会试杏榜,进而为翰林。科考过程也是其道德内化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有关。
就内容而言,清代科举总体沿袭前朝,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稳定实行。这一期间,乡试、会试均进行三场考试,且内容一致,即:首场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八股文3道与试帖诗1道,次场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八股文5道,末场策论5道[3]。自元代后,四书在科举考试中地位超过五经,四书只用南宋大思想家朱熹的经义注解,五经也主要采用朱熹等人的解释。朱熹是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之集大成者,由朱熹为主建构的程朱理学通过科举制度成为明清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官方也刻意用理学学说进行社会控制和整合。任何一个投身科举的人,从最初受学到获取功名,长年累月要不断背诵四书五经等经典,更要不断理解领会朱熹等所做的权威性、排他性经义解释。这是几乎每个士子的知识来源和知识结构。“乡会试所考察的知识内容对于清代读书人群体最为重要,故尤其能够影响到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储备”[4]。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伦理道德本位的,程朱学说更是道德至上的哲学体系。因此,这样的“阅读世界”和“知识储备”必然包括道德知识的阅读和储备。
就形式而言,前文所说的科举制度信度不断提高,体现在以八股程式对取士的唯一性和决定性上。明清时代以八股文应试已发展成文化形态,其要点有两大端:体裁用排偶句式,视角仿古圣先贤。任何学子在长期应考训练和考试中,都要以先哲语气立言,要用皇家认定的权威经义立论,要用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机械格套行文。这不啻是一种角色扮演,即以道德先贤视角和儒家学说来看待世界和分析问题。这种考试形式显然预设,掌握大量道德知识便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且不说这种预设在明清两代演生出多少出科举中人悲喜剧,但经过经年累月的背诵、练习,道德知识、价值观念终究可以内化到士子的主观世界中,儒家理念滋润心灵的作用是无可否认的。
曾国藩也是在科考一般性规律下成长的。曾国藩9岁“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5]10。 15岁在父亲私塾中“受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5]14。三度参加会试,最后一次会试中式,殿试和朝考顺利,得中翰林。朝考中曾国藩所作策文题为《顺性命之理论》。从文本看,28岁的曾国藩完全是以宋明理学的价值框架和概念观点,如“性”“命”“理”“气”“仁”“义”“礼”“智”等看待和分析世界了[5]26。由于前述诸种原因,特别是科考的漫长准备,曾国藩初步建构起儒家化的价值体系。这也是曾国藩能够进行道德领导的基础条件。
(二)曾国藩力行道德稽核
拥有体系化的道德知识、建构起价值体系,只表明是主观世界里的拥有,只是过有道德的生活的必要条件,并不必然保证就能正确地践行道德,或践行正确的道德。儒家成圣成贤学说是完整价值链,既要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还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伦理学话语中,道德稽核意指道德主体主动用道德理念、道德标准验证、称量行为,属于理论指导实践范畴。
曾国藩道德稽核的起点是接受理学修身方法,标志是立志做圣贤。1840年,曾国藩成为翰林官之后,有数年处于人生坐标调适期。考察曾氏这一时期日记,基本是酬答、交游之类活动。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路径在哪里,一直萦绕心头。最初他定位在成为一名皇家文学侍从。进京为翰林初期,他曾内心独白,要抖擞精神,为家庭惜福,“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6] 41。“时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分门记录”[7]47,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治学的广博。1841和1842年,他先后拜访以修习理学而著名的唐鉴和倭仁。前者向曾国藩开示“检身之要,读书之法”,教其以《朱子全书》为宗,从事义理之学等。此番受教对曾国藩大概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作用,“听之,昭然若发蒙也”[6]92。次年,他继续行走在追求理学的道路上。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紧……又教余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6]113。理学家倭仁向曾国藩授以理学“研幾”独家心得,强调“内省”,讲求时刻对照朱熹等先贤确定的义理道德标准,检查、审视主观念头和客观行迹,且将之与修齐治平联系起来。倭仁还要求曾氏以类似“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方法写心灵日记,并交其本人批改。此后数年内,曾国藩以虔诚心态、机械方法、严厉态度游于理学修身门径。每日里将几乎近于琐碎的行为、近乎瞬间的念头放在道德标准的探照灯、显微镜之下,以此来稽核道德。多半因初习理学修身之法,曾国藩道德稽核有时甚至到了荒唐、苛求的地步,此时期他的状态,要不就进退失据,要不就坐立不安,要不就患得患失。“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语。”[7]47自此,曾国藩终身未辍体察反省、拷问道德的习惯。人生定位在此时也得到清晰确认,就是立志做圣贤。其“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一语[8]34,显示人生新坐标已定、大格局已展。
(三)曾国藩践履道德反思
随着曾国藩领导实践的逐渐展开,其道德理性活动场景拓展到治事、治军、求才等方面。要使领导活动顺利推展,原来只适应处理个人内心关系的道德稽核逐渐被更多实践面向和基于情境思考的道德反思取代。道德反思对道德稽核不是否定,而是包涵和覆盖;从认识论而言,是在道德稽核基础上不断调较、丰富并修正道德理念、再指导实践的运动过程,是整改落实,是再认识、再实践,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就发生学而论,是由道德知识、道德稽核、领导实践、人生志向共同作用催生的一个过程。
放在长时段历史文化视野里,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相比,曾国藩道德反思呈现的特点在于经历过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1857年3月,曾国藩接到父亲去世噩耗,未等朝廷指示发回,便将军务交托他人,赶回家乡奔丧。此后备受“守制”与“夺情”道德两难的煎熬[9]。乡居守礼岁月,村里面也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这一年家乡画风是这样的:他的大儿媳在黄金堂难产去世;大儿媳的母亲也在此辞世。他的弟媳妇、曾国荃夫人正处怀孕期间,难免觉得宅子不洁,便请巫师上门“禳祓”。在家守制的曾国藩,本来情绪、身体均一直不佳,偶而有一次白天睡觉,正赶上巫师开展工作,便怒不可遏大发脾气,大概是连巫师带弟媳一同训斥了。一同从江西回家守孝的曾国荃估计脸上挂不住,便从黄金堂迁居他处[10]。伤心事、糟心事如此之多,更迫使曾国藩不断反思,特别聚焦在“我为什么会在领导过程中如此失败”问题上。“每念数年在外,愆尤丛集。官事私事,不乏未了之局,死者生者,犹多愧负之言。”[11]592结论也有了。“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8]326备经煎熬的时期也是砥砺的时期,再次复出的曾国藩在道德反思上遂实现质变。其好友欧阳兆熊评论,曾国藩治术历经“程朱”到“申韩”再到“黄老”的转变,故“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12]。
此质变有二个体现,道德不断升华和体系日臻完备。
道德升华,是道德认识和思考达到的层次和境界,是高度。1862年5月,曾国藩“静中细思”,时间、空间、知识、世事相对于人生的有限来说是无限的,因此,“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之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13]280当时的曾国藩领导情境,大端有:清廷以东南半壁与太平军交战的军务尽委之于曾国藩,其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已是湘军重要将领并将进军金陵城下,其部下、同乡左宗棠领一支湘军进攻浙江,淮军已成并由其部下兼年家子李鸿章率至上海,以两江总督身份开始与西方诸强交涉事务,一纸奏折可以决定军务省份封疆大员去留荣辱,要为直接和间接指挥的数十万军队筹粮、筹饷、筹战争物资。反思的重点是什么呢?道德方面,自身坚持用坚韧、退让、谦虚、举贤来克服品德缺陷、成就更高的道德。
1863年3月,“在轿中,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此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巨寇方张,大难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13]389直接在道德和领导中踱步思量,将领悟出的圣人之道与事功相联,大体展示出其道德反思已走向对标圣贤、追寻圣境之路。
道德体系日臻完备,指的是道德认识和思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是深度。曾国藩曾先后提出“八德”体系,先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14];后改成“勤俭刚明忠恕谦浑”,指出此为人生八种品德,前四者对己,后四者对人[15]415。还在不同场合对“八德”内容予以阐释,并以“八德”当做行动指南。
道德认知对应道德有无,道德稽核对应道德对错,道德反思对应道德损益。还原到具体生活场景中,肯定不是由此及彼的线形过程,但在抽象层次上,则体现为思维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过程,首先是对知识化道德的肯定,然后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过程中对道德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稽核、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础上道德理念更加理性化了,然后再施诸于客观活动,这时候已经是否定之否定了。“在经过了形而上学思维之后,人类对经验现实的回归绝对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带着批判性的回归”[16]。
二、个人道德记忆与家庭道德记忆的合一
在伦理学看来,“家”和“家庭”都是伦理实体,各自承载着伦理精神。前者折射的主要是人与物的伦理关系,伦理意义在于它的工具价值,即在提供生存空间的同时提供人之所以为人应有的安全感、尊严感和高贵感,伦理精神是“爱物”。后者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意义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并由此生发人类社会其他伦理价值,伦理精神是“爱亲人”[17]。家和家庭的持续发展是人类不言而喻的价值。家庭伦理建构之后,家庭道德也相应产生。随着家庭伦理和道德的发展,精神文化形态的家训家风也发展起来。家庭伦理道德是家训家风的价值基础和生成空间,家训家风是家庭伦理道德的表达方式和体现形式。就社会一般性而言,家训家风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和精神,进行历史传承。就家庭特殊性而言,那些为家庭兴旺、家远绵长奋斗的人们,会将家训家风当作精神财富进行历史传递。家训家风就是家庭道德记忆的具象存在形式,其实质是可以在家庭里传播和传承的家庭道德记忆。按伦理学,道德记忆是人类记忆活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人类道德生活经历在其脑海中留下的印记或印象;主要包括道德风俗和习惯、道德原则和规范、道德思想和精神、道德实践和行为等。个体道德记忆是关于个人道德生活经历的记忆,家庭道德记忆是关于家庭道德生活经历的记忆[18]。
曾国藩的家训家风一向为后人称道。随着曾国藩科举的成功,特别是后期创建湘军、恢复东南社会秩序、主导自强运动等领导活动的展开,曾国藩对家训家风家运日益重视,主要是在其创造和努力下,曾氏家族成员也参与进来,共同维系和推动曾氏家训家风,从而体现为个人道德记忆和集体道德记忆密切互动的运动过程,其中曾国藩个人道德记忆是主要的决定方面。从领导力就是影响力角度说,曾国藩营造家风,实质上是以个人道德记忆去建构家庭道德记忆,也是一种领导活动。
(一)曾国藩勾勒先辈家风,回溯早期家庭道德记忆
先人们的家庭道德生活深刻地影响着曾国藩。曾国藩先祖辈务农为生,他们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家训家规,但并不意味没有道德生活。其先辈,特别是其祖父治家实践对曾国藩个人道德记忆影响很大。“(我家)累世力农,至我王考星冈府君(祖父)乃大以不学为耻,讲求礼制,宾接文士。……其责府君(父)也尤峻……府君则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19]。这已是曾国藩晚年的记述,依然侧重叙写先辈生活的道德意蕴,可知对曾国藩道德刻写之作用深远。曾国藩道德领导行为上也有先辈留下的印迹,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曾国藩晚年曾与密友交谈称:家里向来贫穷,在祖父操持下才有勉强能维持生计的微薄产业;即使中翰林做京官后,祖父仍然告诉父亲,家中照旧生活,不要他资助家中财物,所以“吾闻讯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20]1107。
曾国藩也注重将对先辈的记忆向家庭成员传递。如关于祖父的道德教诲,他向弟弟们回忆:他至今都记得,进京为官前请祖父训话,祖父教育他不要骄傲;如今,弟弟们也要遵守祖父昔日教诲[8]256。关于母亲,他也多从品格特征处回忆,“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15]115。
曾国藩总结提炼早期家庭道德生活。曾家先人的道德生活是自在自为状态的,但还不是一种理论自觉。将先辈们分散的有道德意含的语言和行为提炼成体系的工作是由曾国藩完成的。曾国藩祖父对整个曾氏家族贡献比较大,曾国藩对家庭早期道德生活的思考就聚焦在祖父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提炼成“八宝三不信”家规体系。“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8]594。祖父的风范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对自己的概括仍觉得不完善,后来还提出升级版“八好六恼”。“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此八好六恼,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15]468。
(二)曾国藩营造家风,建构家庭道德记忆
2012版《曾国藩全集》收录曾国藩于1840年入京为官至1871年所写共1485封家书。在主要写给弟、子的信中,关于治家、兴家、做事、做人的思考和要求随处可见。曾国藩领导过程与治家过程相始终,其特点在于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即注重从理论层次探讨家庭道德记忆,丰富家风思想内涵;个人以身作则,注重提出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推进举措,并有严格的过程管理和绩效考核。
他重点帮扶对象是四个弟弟中的四弟国潢和九弟国荃,因为另外两个弟弟均过早在战场去世。除了平常书信交流反复叮嘱为人治家之道,兄弟见面时也会深度探讨家庭道德记忆内涵。在军务倥偬之际,仍“夜与沅弟(曾国荃)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愿与沅弟共勉。沅弟亦深领此言。谓欲培植家远,须从此七者致力也”[6]435。1868年,曾国潢千里迢迢从乡间赶至金陵,兄弟十年未见,既享喜悦之情,更多深度交谈。“酉初与澄弟(曾国潢)谈,直至二更三点,说话极多,疲甚。中讲《孟子》中也养不中一章,弟深能领会,殊有和乐且湛之趣。”[21]102行将北上任直隶总督之际,曾国藩怀着未知今生能否再相见的伤感,提笔对四弟作近千字临别赠言,劝其保持“清、俭、明、慎、恕、静”[19]472-474。尽管数日前还“闻有狎邪之游,心实忧之。老年昆弟,不欲遽责之”[21]104。
全面管理对象则是自己的两子五女,其中重点是儿子。比之现代父母,曾国藩也不遑多让,动辄以“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进行对比式教育。长子曾纪泽第一次婚姻娶曾任云贵总督的贺长龄之女。曾国藩信中称:你看陈伯伯家儿子多优秀,可你却贪图安逸;正值你成家的时候,全家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8]291另外,“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之起居,合家之琐事,学堂之功课,均须详载,切切此谕。”[8]291数年后,贺氏去世,曾纪泽第二次婚姻娶后来曾任陕西巡抚的刘蓉之女。曾国藩为其梳理家庭道德记忆,“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因此,“尔即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余生平坐无恒之弊……用为内耻。……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8]453-454。这封长信中从曾家祖辈一路说下来,着重指明祖先的道德生活及对自己的影响,再阐明父子各自的优缺点,明确曾纪泽成立新家庭后的努力方向。不啻是家庭道德记忆的路线图。
(三)曾氏家族共铸家庭道德记忆、维系家风
仅有曾国藩个人的努力,道德记忆只能在个人框架内生长。经过曾国藩经历累月不懈努力,曾氏族人或主动、或被动也致力于营造家风,铸成家庭道德记忆。兄弟和衷共济、妯娌相互关心、晚辈抵足而眠的画面屡见曾氏家人笔端。
家庭道德记忆要靠族中人共同参与,但不是所有人对家风的理解、参与的态度、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其中以曾国荃变化最为典型。曾国荃在41岁时就已任浙江巡抚,统领五万湘军夺取太平天国都城金陵。正踌躇满志之时,曾国藩劝其激流勇退。曾国荃虽长期受曾国藩的教诲熏陶,但对他“花未全开月未圆”“上场当念下场时”之类对立统一的哲学和盈科后进的智慧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对其兄建议更啧有烦言。“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之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20]1110。经过回乡年月的积淀、思考,国荃再出任湖北巡抚,但在领导实践过程中却连遭重大挫败。曾国藩为帮助其弟度过难关,提升道德韧劲,遂将自己专属的个人道德记忆拿出来分享,说起生平遭逢的“四堑”:科考时曾被挂牌批评,做京官时被众多高官排斥,初领湘军时被湖南官场排挤,在江西征战时被官绅嘲弄戏弄。“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弟力守悔字硬字两诀,以求挽回……”[15]488。曾国荃逐渐感悟到其兄促进家庭道德记忆的见识高远,向其兄表示,“(以前)以为(自己)本领甚足,今乃知全是运气,毫无本事。……又以一家而论,亦已近炎炎之势,趁此时弟尚可稍冷一步,冀以久延世泽”[22]。日后,曾国荃从负有饕餮之名,真正进入到与其兄共同维系家风、构筑家庭道德记忆之中。
曾国藩的子女是其刻写道德记忆的主要对象,自然是恪守家训、延续家风的主力军,传承家庭道德记忆的主体。他们也用行为证明了这一点。曾国藩对儿子曾如此期待,“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8]373。前文也提到,曾国藩对曾纪泽有“早起、有恒、持重”的要求。后来长子曾纪泽成长为晚清外交家,凭借持重、稳慎、周密的特点,与西方诸强周旋,并争回部分领土权益。次子曾纪鸿投身数学且有精深造诣。当可视作是对曾国藩教诲与期许的恪守和实现,对家族道德记忆的参与。
曾氏后人身处繁华,仍旧躬行勤俭谦慎的道德生活。多年后,曾国藩五女曾纪芬回忆起曾家儿女当年在两江总督府,按照父亲所定作息时间表和课程表,一起生活的情景,曾家后人共同促成家庭道德记忆的画面跃然而出。
早饭后 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食事
己午刻 纺花或绩麻 衣事
中饭后 做针黹刺绣之类 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 做男鞋女鞋或缝衣 粗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右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8]107
曾国藩后来还在此单后添上四句话。“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21]60就像为家庭道德记忆篆刻一枚印章。
三、道德软性约束与道德硬性约束的合一
曾国藩领导实践过程中,有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6]442按其领导经历,“带勇”不仅指率领湘军士兵,也当指与人打交道、带队伍、培育人才等。“仁”及“礼”都是儒家核心道德理念,“用恩”及“用威”意指领导方法上的柔性和刚性。基于道德具有规范人行为的性质及功能,“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即是道德的软约束和硬约束。硬性约束是对软性约束的保障和补充,是“高压线”;软性约束是硬性约束的道义屏障和精神牵引,是“冲刺线”。没有硬性约束,软性约束就可能流于“义理”之学的空谈和玄学的“凿空”;没有软性约束,硬性约束就可能坠向法家的酷烈。在曾国藩的领导实践中,这二者也是合一的。
(一)道德软性约束
“用恩莫如仁”意味着“仁”是“用恩”的主要途径方法,即称“恩”就主要是教诲、激励、给与等隐性和柔性手段来引导人的行为,道德软性约束即由此生发。
“仁”字一词,在曾国藩语境里,当指自己的道德发展与别人的道德发展、自己的事业发展与别人的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的问题。其核心要义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外在特征是“恕”[6]442。 “求仁”极其重要,既与儒家宇宙观、本体论相联,又是儒家“成已”“成物”“成人”的根本路径。曾国藩晚年作“日课四条”专论“求仁则人悦”。“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15]546-548“用恩求仁”理念下,是家庭关系、家庭结构向人际关系、组织结构的延伸和复制,家长就是军官、长官、师长,子弟就是士兵、员工、学生,领导的追随者就是子弟学生。如此则每一层级的领导者都负有让追随者获得发展的义务。
曾国藩用“仁”突出体现之一,是对抚恤、封典赏赐和保举等事务极为重视和谨慎,尽量做到公平。
抚恤是对伤者、逝者的补偿和慰藉,封典赏赐是封建君主给予的荣誉,保举则是请求君主予以官衔和官职。其实质是兑现“仁”。湘军每野战胜,或夺回城市,几乎必定即刻奏请保举、请求抚恤、申请封赏[23]。曾国藩曾思考过保举的人数比例问题,称“各营请奖,此间批定之案,每百人中,多者准保十四人递减至八人不等,然终嫌其太滥。……近年每百人保二十人者,几成常套。弟去年思挽回一二,批定极多不准过十四人。”[24]必定保举,是为了让冲锋陷阵的将士得到回报,是体现“仁”。确定额度,是为了让“仁”的物质化和精神化显得稀缺而有价值。即刻奏请,是彰显领导者对在一线辛劳的重视;拖沓意味着对基层工作的轻视。必定、即刻和限额,在曾国藩处也就有了伦理意味。
曾国藩用“仁”突出体现之二,是不断在领导活动中对部下进行道德灌输和熏陶。
为什么要灌输道德?曾国藩治军之初,官民矛盾、军民矛盾早已非常尖锐。在此领导情境下,“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1]200
无论是指挥湘军、领导淮军,还是总督两江,曾国藩总把与部下谈心谈话、书信交流、批阅禀件当作主要的领导方法。其内容除了部署工作、学术切磋外,更多的是道德上的勉励劝诫。其日记、批牍、作品包括他人的回忆,尽多如此之语,兹举代表性数例。
1861年,湘军攻下一直在太平军掌握之中的安徽省城安庆,任两江总督一年多的曾国藩总算有了稳定且相对安全的办公场所。驻节安庆伊始,曾国藩即定章程:地方官员,要做到治署内以端本、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俭朴以养廉;军队官员,要做到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从;办事人员,要做到习勤劳以尽职、崇俭约以养廉、勤学问以广才、戒傲惰以正俗;地方士绅,要做到保愚懦以庇乡、崇廉让以奉公、禁大言以务实、扩才识以待用[19]444-449。对于领导过程中主要涉及的各类官员,提出分门别类的要求,这些要求包含的主要是品德、作风因素。1864年,湘军攻占金陵,曾国藩驻进两江总督官署,即作官箴,并悬挂于驻节地。“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19]100。1869年任直隶总督后,再对同僚作道德劝勉。“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19]102。从事科举时受过的排偶诗赋训练也有了用武之地。
(二)道德硬性约束
“用威莫如礼”意味着“礼”是“用威”的主要途径方法。即称“威”就要有暴力、惩戒等做后盾制约人的行为,是一种硬性约束。
曾国藩曾论述何谓“礼”“古之君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9]410。“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6]442。一般而论,曾国藩认为“礼”有两层内涵,“道 ”层次上的道德精神和“器”层次上的制度理性。在曾国藩开展领导实践角度上,“礼”是具有“辨等明威”功能的规矩、礼仪、规范等实体性制度,故是一种“礼”制,其有若干特征。
其一,道德标准和要求融入选人用人机制。
对于士兵,“募格,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9]406对于军官,曾国藩也有品格要求。“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25]。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11]215-216湘军早期名将罗泽南就是在这种选人机制中脱颖而出的。其“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26]。
其二,道德价值意蕴贯穿指挥运转机制。
选士兵和军官解决的是选什么人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选、怎么组织的问题。“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27]。此外还有取保制度、军饷发放制度、后勤保障制度等。有逐级挑选,指挥命令可以一以贯之;有“口粮”发放,就有凝聚和服从。再加以另外一条特别紧要的规定:如统带营官伤亡,或士兵溃逃过多,则取消番号。几者相合,组织内成员甚至组织间的情义也产生了。这也是湘军“败必相救”的伦理底色。
其三,包涵道德内容的训练机制。人员选好,架构搭好,还要解决能不能打、能不能长期打赢的问题。训练机制是湘军战斗力的独到之处。曾国藩创湘军之初就重视训练。合成建制后必须训练数月方能上战场成为湘军成例。独到之处体现在“训”有伦理道德指向。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营官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19]446。家庭成员间的道德义务和关系模式几乎原样复制到组织中,并且更制度化了,从而约束性也更强。
民国年代,曾国藩外孙聂云台发出如许感慨:相比之下,后世湘军名门家运要好过淮军名门,重视读书的军功世家子弟要比只知积聚财富的军功世家子弟优秀,“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28]。曾国藩构建家庭道德记忆、孜孜不倦用道德教诲湘军将士,多年后在湘军、淮军各名门家族命运盛衰比较中显出了效果。
曾国藩道德领导有其历史局限性,不能脱离其身处的“历史世界”而拔高其“思维世界”。在伦理学理论视野下,曾国藩道德之领导和领导之道德有着求“真”求“善”的因素,更包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汲取,因而也有价值合理性。基于此,上述诸论在以下方面给现代人以启示:没有道德和伦理的领导实践,是道德虚无主义;不顾实践和没有立场的道德,是唯道德论和道德至上主义;动辄强调领导情境决定领导行为,是道德机会主义;不在现实世界和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答案、一味向历史回归是道德复古主义和封闭主义;离开家庭家风而谈道德领导,是道德空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