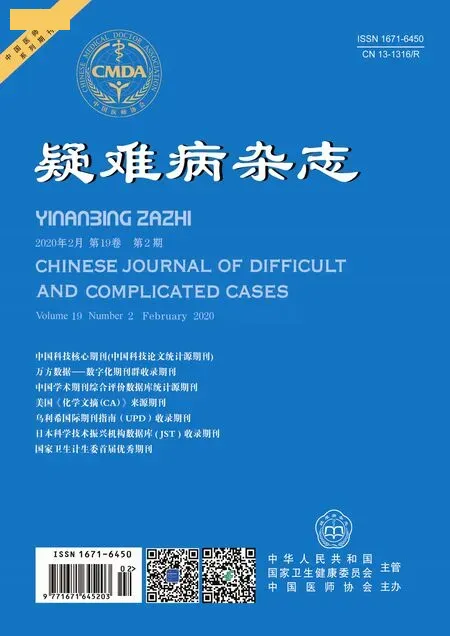肿瘤炎性微环境及其对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抑制的研究进展
2020-12-17刘丽荣刘译鸿综述张海波审校
刘丽荣,刘译鸿综述 张海波审校
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Virchow提出肿瘤起源于慢性炎性反应这一假说,并提出肿瘤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肿瘤中存在大量的白细胞,为炎性反应在肿瘤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目前普遍认为慢性炎性反应可以增加罹患肿瘤的危险性,大约25%成人肿瘤由慢性炎性反应引起。因此,炎性反应被称为“癌症的第七大特征”。现在大量的试验和临床证据发现炎性反应应答和它们在肿瘤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关系。肿瘤细胞、特异的免疫细胞各亚型、间质细胞之间动态联系对肿瘤发展有着关键性作用,而以此作为肿瘤治疗的靶点有着潜在的重大意义。
1 肿瘤炎性微环境
目前认为癌症其中一个特征是伴有慢性炎性反应,而肿瘤相关的炎性反应又将促进慢性炎性组织向肿瘤组织转化,并维持已发展肿瘤的疾病进展[1]。流行病学证据证实,由于持续感染(如乙型或丙型肝炎病毒、人类乳头瘤病毒)或无菌炎性反应(吸烟、石棉)引起的慢性炎性状态都与肿瘤负荷有关;相反,通过药物抑制炎性细胞及其信号转导通路,或通过实验系统中的基因消融,均可降低肿瘤的发生率和进展程度[1-2]。炎性反应的主要来源是先天免疫细胞,即存在于肿瘤微环境中的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s, TAMs),此为先天免疫细胞介导的炎性反应外在发生途径;并且肿瘤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和反应性介质也是其中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异常遗传所导致的原癌基因的激活或抑癌基因的失活,此为癌基因和癌细胞介导的内在途径[1-2]。通常情况下,这2种途径在肿瘤炎性微环境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共同作用。例如,共同特征是产生IL-1、TNF、IL-6类原发性炎性细胞因子,以及激活 NF-κB和STAT3 等炎性反应的主要调节转录因子,并产生其他介质,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和酶,通过增加肿瘤部位白细胞的募集进一步刺激炎性反应。因此,当炎性反应级联激活时,会建立一个前馈回路,其中产生可导致组织损伤的反应因子,同时刺激组织再生。此外,持续暴露于活性氧和活性氮(ROS、RNS)可诱导恶性细胞的表观遗传改变、抑制DNA修复机制、积累DNA 突变,最终有利于转化细胞的增殖潜能[3-4]。
肿瘤微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失调的部位,即使是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等正常细胞也会受到肿瘤细胞及其分泌物的严重影响。在肿瘤组织中,结缔组织支架结构、细胞外基质成分和蛋白水解酶与正常组织相差很大,越来越多研究提示它们是肿瘤进展和转移的主要参与者,以及与免疫细胞一起构建炎性反应微环境[5-6]。
肿瘤微环境中炎性反应信号的持续激活是随着组织稳态和结构破坏的侵袭进展而产生的。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来源的细胞应激分子、凋亡或坏死物质的释放代表了引发巨噬细胞刺激和M2 极化的另一个因素,用于组织修复激活和成纤维细胞募集[7-9]。慢性炎性反应与葡萄糖浓度、缺氧、iNOS、趋化因子(例如CCL2)和TGFβ的改变,协同成纤维细胞募集和纤维化过程激活,这是一种常见的病理生理变化[10-11]。这些变化也可以在肿瘤微环境及其组织重构的渐进结构中发现,遵循伪伤口愈合程序[12-13]。
组织的硬化有助于改变上皮细胞行为,诱导上皮细胞向间质的转变,并通过与整合素的相互作用,刺激促进细胞运动的细胞骨架变化。 即使是ECM储存的TGFβ 也可以被释放,与M2样TAMs合作进一步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和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促纤维化激活[14]。
肿瘤病灶中的免疫细胞来源于血液循环。在新发展的肿瘤中,单核细胞第一个到达并且分化成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通常构成最丰富的免疫群体。其中T细胞为主的适应性免疫细胞也被分化形成。具有抗肿瘤细胞毒性的活化T细胞会普遍存在于表达免疫系统“可见”抗原肽的免疫原性肿瘤中,最终破坏肿瘤细胞或限制其进展侵袭。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已成型的肿瘤会强制反抗,抑制环境中的抗肿瘤反应[15]。巨噬细胞在适当刺激时原则上会具有细胞毒性,受肿瘤细胞的强烈调节,分化和功能极化为具有肿瘤营养功能的免疫抑制效应物,维持其进展并抑制适应性免疫应答[15]。事实上,强有力的证据强调了肿瘤中高TAMs数量或巨噬细胞相关基因特征与更具侵袭性的疾病和患者预后不良之间的相关性[16 -22]。
2 肿瘤微环境中的炎性因子
随着越来越多关于肿瘤微环境中复杂的炎性反应回路网络的研究,为靶向肿瘤所致炎性反应的新治疗模式奠定了更深厚的基础。长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预防心血管事件的人群比例越来越高,为开展癌症发病率和病死率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机会。在大量的人群研究中发现,阿司匹林的日常使用显著降低了肿瘤发病风险,尤其是结直肠癌;并且在已经发病的肿瘤患者中发现,其能有效地提高患者5年生存率。荟萃分析研究也发现其他腺癌的风险降低,例如受体阳性乳腺癌[23-25]。NSAID抑制COX-2 酶的活性并减少前列腺素的合成。前列腺素是一类脂质介质,参与包括炎性反应等多种不同反应,在肿瘤环境中可能维持肿瘤细胞的存活和血管生成[26]。其他消炎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可能也具有类似的预防潜力,但这些药物被较低比例的受试者使用,而且通常使用时间较短,因此目前暂无对大量人群的观察研究。
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是炎性反应的关键介质,并且存在于肿瘤微环境中,其中它们由肿瘤细胞和基质细胞,尤其是巨噬细胞产生。主要介质是肿瘤坏死因子(TNF)、白细胞介素-6(IL-6)和白细胞介素-1(IL-1),它们会导致不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释放,从而增强炎性反应,并在局部生产部位募集新的免疫细胞。如上所述,这些细胞因子通常通过刺激其增殖或存活及局部组织的侵袭能力,或通过刺激新血管生成的过程来加速肿瘤进展[2,21]。
依据这些理论基础,针对性地抑制炎性细胞因子是合理的,而且临床前研究也证实,在不同的小鼠肿瘤模型中,针对肿瘤所致炎性反应策略有潜在疗效。然而,目前临床研究证据相当有限[27]。在肿瘤学中,抗TNF 单克隆抗体被用于不同类型的癌症治疗,尽管有部分肾细胞癌患者存在一定反应[28],但能维持疾病稳定(SD)的患者比例很小。卵巢癌患者体内能检测到IL-6的抗体,并且部分患者伴有SD[29]。总体而言,这种疗法疗效未能达到期望,可能需要联合常规化疗或其他靶向治疗。
3 TAMs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
TAMs影响肿瘤细胞行为的不同方面。 在机制上,肿瘤中的巨噬细胞和相关骨髓细胞产生生长因子,如表皮生长因子(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这些生长因子直接支持肿瘤细胞在非最佳条件下的增殖和存活[30-31]。TAMs 能维持肿瘤的生长,其机制通常是产生能够调节特定基因、激活细胞凋亡和增殖途径的细胞因子。例如,IL-6 激活 STAT3,后者通过作用于不同因子(cyclin D、Bcl-XL、Bcl-2 和 Mcl-1),达到控制细胞存活[32]。
在肿瘤生长的缺氧微环境中,巨噬细胞在缺氧区域积聚并分泌许多促血管生成因子,包括 VEGF、CXCL8、胎盘生长因子(PlGF)和前动力蛋白(Bv8)[33]。TAMs 还产生几种蛋白水解酶和参与细胞外基质重塑的其他介质,例如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s)和组织蛋白酶。TAMs对细胞外基质的降解有利于肿瘤细胞的局部侵袭,渗透到血管内并分散转移[34]。其他由肿瘤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0和TGFβ,具有强烈的免疫抑制作用,并抑制T淋巴细胞的抗肿瘤细胞毒性[35-36]。同时,TGFβ能维持 M2样TAMs,刺激成纤维细胞生成和沉积胶原。产生的纤维化可能是常规细胞运输的进一步障碍,同时也限制了氧和药物渗透到肿瘤组织中,因此针对抑制TGFβ治疗的研究正在开展[37]。
淋巴管生成在肿瘤淋巴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TAMs 产生的VEGF-C 和VEGF-D 被认为在诱导淋巴管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胆囊癌模型中,Yang 等[38]发现TAMs 通过表达VEGF-C和VEGF-D 诱导淋巴管生成和肿瘤淋巴管转移;使用可溶性的VEGFR-3 阻断VEGF-C/D,以及使用氯磷酸盐脂质体清除TAMs,能明显减缓上述进程。
肿瘤上皮间质转化(EMT)是极化的上皮细胞转变成间充质样细胞的过程。在转换过程中,细胞表面上皮标志物如E-钙黏蛋白、桥粒斑蛋白等表达下调,而间质标志物如N-钙黏蛋白、波形蛋白等表达上调,使其丧失了细胞间的黏附力和顶端—基部的极性,促进肿瘤的进展和转移。TAMs表达的TGF-β1 能激活TGF-β 信号通路,依靠Smad 依赖性或Smad 非依赖性2种信号途径诱导EMT。TGF-β1 分泌后可通过自分泌的方式发挥作用,激活TGF-β 通路,形成正反馈,维持正在进行EMT 转化的肿瘤细胞的间充质特性。TAMs来源的IL-6借助TGF-β 通路参与EMT,IL-8 则通过Jak2/STAT3/Snail信号通路促进EMT[39-40]。
TAMs 还可以表达 PD-1的配体PD-L1,这种途径是抑制免疫系统适应性的最重要途径之一[41]。此外,TAMs通过形成淋巴细胞浸润的成分发挥其抑制作用:它们产生趋化因子(例如 CCL17,CCL22),其募集调节性T细胞和Th2淋巴细胞,导致对肿瘤细胞失去细胞毒性能力,并负性影响Th-1 介导的反应。
4 抑制TAMs的相关治疗
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治疗现在已成为越来越多肿瘤患者的既定治疗方法。临床研究已经验证有效的靶点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PD-1和PD-L1[42]。浸润肿瘤微环境的巨噬细胞可以表达PD-1配体(PD-L1和PD-L2),以及 CTLA-4 配体(B7-1和B7-2)[43-44]。因此,抗检查点阻断的免疫疗法也可能影响巨噬细胞,无论是通过直接抑制配体分子,或通过激活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ntibody-dependent cellular cytotoxicity, ADCC)杀伤CTLA-4阳性和PD-1阳性的T淋巴细胞。在临床前模型中,表达FcγR的巨噬细胞对于清除肿瘤中CTLA-4和抗体包被的T 细胞至关重要[45]。
动物模型和临床试验显示针对TAM的治疗,包括清除TAM、TAM的再极化及提高TAM的抗原递呈功能等手段,不仅具有单独的抗肿瘤作用,而且还和免疫检查点等免疫治疗手段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肿瘤细胞糖酵解和缺氧是抗肿瘤治疗失败的主要因素,TAM清除剂和免疫检查点抗体联用可以增强免疫检查点抗体的抗肿瘤效率。Jeong 等[46]在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中表明,TAM 可以分泌TNF-α 促进肿瘤细胞的糖酵解,而TAM 中增加的AMP 活化蛋白激酶(AMP-activatedprotein kinase,AMPK)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激活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gamma coactivator 1-alpha,PPARGC1α)会导致肿瘤缺氧。应用氯磷酸盐清除TAM能够消除肿瘤的有氧糖酵解和使缺氧、需氧的肿瘤细胞表达PD-L1显著增加、肿瘤中T 细胞浸润增加,从而使原本对PD-L1 抗体不反应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产生了明显的抗肿瘤反应。
ADCC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巨噬细胞和NK细胞介导杀死肿瘤细胞的重要机制。来自临床前模型和临床相关证据的发现表明,ADCC是治疗肿瘤用的单克隆抗体有效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那些针对CD20、HER2和EGFR的单克隆抗体[47]。对接受治疗患者的FcγR基因研究发现了与抗体具有高亲和力结合的多态性。这些基因型的表达与淋巴瘤患者对利妥昔单抗(抗CD20抗体)、结直肠癌患者对西妥昔单抗(抗EGFR抗体)和乳腺癌患者对曲妥珠单抗(抗HER2抗体)的治疗应答增强相关[44]。这表明TAMs在单克隆抗体的临床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
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GBM)是一种致命的高度侵袭性恶性脑肿瘤,目前已发现TAM 和小胶质细胞是肿瘤微环境中促进肿瘤的主要细胞,阻断SIRPα-CD47信号能够诱导TAM 和小胶质细胞对肿瘤细胞的吞噬作用,此方法对包括GBM 在内的各种脑肿瘤有效[48]。
5 展望
肿瘤的持续治疗不仅需要针对增殖的肿瘤细胞,还需要针对整个肿瘤微环境。由于有充分证据证明慢性炎性反应会促进肿瘤进展并抑制免疫抗肿瘤反应,因此肿瘤所致炎性反应是需要针对的目标。一些抑制炎性细胞因子或设计用于靶向肿瘤中巨噬细胞的药物制剂已经在实验中显示出一定效果,其中TAMs通过VEGF-A在肿瘤血管、淋巴管及EMT进程的各个阶段发挥着作用,已成为抗肿瘤靶向药物研究的重要靶标。这些药物的早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一些患者确实获得了显著的临床效益,能保证一定的疾病稳定(SD)和较长的无进展生存期(PFS),药物不良反应适中且可控。这些结果相当重要,为联合化疗或其他疗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