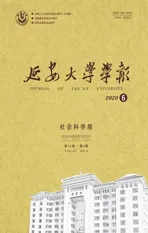道家哲学的生态智慧
——以疫病灾难为视角
2020-12-16魏微
魏 微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爆发与流行已经成为了国人乃至世界的集体记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属于疫病的一种。一般而言,疫病指发生在人及动植物身上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疾病,它由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引发,并在生物活动中得到广泛传播,触发疫病灾难。疫病灾难并非生命个体安危与健康的单向度问题,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命与环境的关系、人类社会秩序与机制、价值观念与精神理念等方方面面的集结镜像,渗透人类几乎全部的生存境遇,可以说,疫病灾难关乎生命的全方位存在状态,是生态危机的集中表现。
蒙培元曾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哲学是“生”的哲学,(1)参见蒙培元《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6-13页。旨在说明中国哲学体现着浓郁的“生生”精神,富含扎实的生命透悟与生态智慧。道家以“道”为理论渊薮,眷注人与自然的关联,也瞩目于自然之中的人类社会及人类个体的存在状态,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态视域,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深刻的探讨。如曾繁仁认为老庄思想体现着古典生态存在论,(2)参见曾繁仁《老庄道家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新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第5-11页。又如史密斯·休斯顿认为道家、道教“看待、思考自然事物的方式可以衍生出一种简单和柔顺的生态伦理精神”。[1]因此,本文尝试以疫病灾难为视角,探寻道家思想在自然、社会、个人维度的生态智慧,以期为生命关怀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一、“有人,天也”:人与自然同源共生
疫病灾难为生命带来严重创伤,是生命灾难,是有生命的生物所承受的灾难。《庄子·山木》曰:“有人,天也。”[2]614在道家看来,人无论如何敞显生命的进程与意义,都要禀赋自然生命,无法背离自身的生物身份。道家生态视域下,疫病灾难迫使人认清自身的自然生命基础,反思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予人敬畏生命与敬畏自然的警醒,启发人领会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本质存在状态与和谐共生的一致生存诉求。
第一,道家警醒人正视自己的自然生命与生物身份,认清人是自然之组成的客观事实。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人的生存与发展极大程度地依存于、依赖于、受制于自然,人很容易感受到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也能对人作为自然生命体与自然规律载体的身份有所体察与认同。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从原始时期将自身生机视为自然的“恩赐”,到了解并利用自然以谋求生命存续与价值实现,人类的生存能力与生存机会基本得到总体的提升,却也越来越倾向于将自身游离在自然之外。工业革命以降,人类以征服者、主宰者的身姿雄踞地球、播撒野心,借助科技与机械的力量对自然进行了无度的征伐与掠夺,俨然在视自然为人类世界的“他者”之际,也磨灭了自身本就作为自然存在者的事实。而在信息技术与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人类更经历着基于互联网而交流形成的“赛博空间”对生活的渗透。在这一新兴生态域里,自然世界在由人类赋义的符号传达过程中几乎完全丧失了自身的话语权,人类则占据了信息世界的制霸地位。此情此境下,人类过度的自我意识遮蔽了作为人生存之基本的自然性,人沉醉于文明演进下人类智慧与能力的光辉,而常常忽视了身为自然生命的有限与脆弱。
《庄子·大宗师》曰:“死生,命也。”[2]220在道家的生态视域中,无论上古的神人、真人、至人如何餐风饮露,飘逸若仙,凡尘俗世中的普通人总是有生有死的,应承着生而为人的本来命运。用现代生物学的话语来说,也即人始终是有机生命体,是千千万万生物种类中的一员,无论人类文明演进到何种地步,人都避免不了生老病死的生命历程,这一点与花草树木、游鱼飞鸟等其他自然生命本质无二。疫病灾难正是一个残酷却也有力的使人反躬自省的契机,它迫人认清自身秉承天然的自然生命及因此必然承受的有限性,也戳破了人盲目自大的虚幻泡沫,教人不要沉醉于文明的楼宇,而忘却了血肉之躯与生命源流的自然归属。
第二,引发疫病的微生物往往寄生在野生动物身上,通过人的捕食行为传播给人类,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传染,构成人与其他自然生物的两相其害。而道家对人提出的不与自然生物互相伤害的要求,便在此成为了毫不过时的忠告,其中敬畏生命与敬畏自然的理念也无疑是始终响彻人类文明的警钟。
如埃伦菲尔德所说,生物“在大自然中长期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不可怀疑的继续存在权利”,[3]动植物与人的继续存在的权利同样应被肯定。但不得不承认,人若想维持生存,延续生命,就必须以将部分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转化为自身生存资源为条件,简单地说,就是要以部分其他生物为食,且有必要地占据一定的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因此,人类由依靠采集与渔猎转向发展农耕与畜牧,以保障自身稳定获取生存资料,保持人类需求与自然供给之间的平衡。然而,无论是2003年流行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还是甚嚣尘上的新冠肺炎,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同野生动物的关系处理不当脱不了干系。尽管人类已经驯养、驯化、杂交了专供人食用的作物与牲畜,但仍有个别人出于对金钱的滥欲、对安全性的无知、对刺激的追求,捕杀与食用野生动物,将病毒带入人类群体,酿成无可挽回的疫病灾难。
基于道家的生态视域,这种与自然相互伤害导致的灾祸本该被杜绝。《庄子·知北游》曰:“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2]674在道家看来,人在自然中能够拥有的最安适的生存处境莫过于“处物不伤”,一是不伤害自然生物,二是人不被自然生物伤害。这是一个相互的、双向的原则,但细究起来,终归要落在人自身的行为规范上,即人应先做到不伤害自然,才能不被自然伤害,或者说,不被自己伤害。就如人不捕食野生动物,便不会被野生动物携带的细菌或病毒感染。道家生态视域下不伤害自然生物的要求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不应伤害自然万物的存在,不应破坏物种多样性与多元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2]288人也不应按照自己的意志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强行改变自然生物的形状、习性与本性,让其他自然生物陷入无谓的痛苦,“如果一个存在物能够感受苦乐,那么拒绝关心它的苦乐就没有道德上的合理性”。[4]道家人与自然互不相伤的原则下,潜藏的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对自然的敬畏,一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敬畏生命、生命的休戚与共是世界中的大事”,[5]它包括对人类生命的珍重、对其他生物生命的爱惜、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仰赖和对自然规律的深沉尊敬,它发乎于现实的生存实践,反应着人类朴素的求生愿望,应作为人类关照自身生存与生态和谐的警钟,长鸣不绝。
第三,鉴于疫病灾难为人与自然中的其他物类都带来了严峻生存危机的事实,我们必须意识到,人并不能单方面无度地滥施破坏,从大自然中攫取利益,人与自然环境及环境之中的其他生灵根本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即是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道家生态视域下,人与自然环境和其他自然生命同出于“道”,整体性存在方式是人生存状态与生命展开的必然图景,可为生命共同体理念提供哲学层面的支持。
人与人之外的自然生命及自然环境来自何处?道家从形而上的高度做出了回答——“道”。“道”是道家哲学中的生成本原与存在本体,道家为“道”赋予了“天地根”[6]80的崇高意义,继而,“道”生万物就成了道家关于宇宙根源、世界由来、万物存在的关键命题。换言之,道家生态视域中,日月星辰、山川湖海等自然环境乃至宇宙环境皆由“道”而生,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也都来源于“道”,栖息于生态世界中的人自不例外。在此基础上,道家对“道”生万物的生成机制也做出阐释。《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6]225《庄子·田子方》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2]630“道”的创生是一个由少至多、由精至繁的运动,其中,交互、合作、和合发挥着重要作用,使生态世界具有极大程度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道家对形而上之“道”作为生态世界终极源头的笃定及其关于生成与存在的系统化预设,昭示着人与自然、生物与环境始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开启了人类看待自然、界定自然、体验自然的立体视角,即不仅视自然万物为物质性的事物,更将自然理解为在人类的生存演进与身份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伙伴,甚至是自身的重要构成,使人对与自身同根同源的其他自然生命和自然环境的关怀内化为人存在的必然基底。这也在思辨的层面确证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作为生命存在形式的现实性,引导人们领会人与自然共生共适、美美与共的有机整体生命观、生态观、世界观,寄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美好愿景。
总之,面对疫病灾难,道家生态思想警示我们认清自身无可更改也不容逃避的自然存在者身份,对生命与自然怀有诚挚的敬畏,保障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更要秉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调节好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生存涉及的最基本关系,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二、“常善救人,故无弃人”:人类命运与共
疫病不分种族,灾难没有国界。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同根共源,而人类社会作为被自然世界包孕着的群体,人与人之间生命的平等、隔阂的消弭、对立的瓦解及合作的促成便也同样是道家生态视域下的应有之义。如《老子·二十七章》所言:“常善救人,故无弃人”,[6]169人类共同承受疫病灾难及其表征的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痛楚,也共同承担挽救彼此生命与走出困境的责任。
首先,疫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殃者众,相应的治疗方案就要充分考虑到每个人接受治疗的几率,而道家的生命平等理念正代表着一种人道主义立场,引导我们在危机中看到生命的内在价值与平等关系。
《老子·五章》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6]74客观规律不讲感情,自然没有人的意志,发乎于人类的道德规范并不适用于客观自然。正如病毒侵害生命体,攻击免疫系统,并非怀有歹心,存有恶念,只是自身的生存机制使然,自然的客观规律使然,只要生物条件合适,找到适宜自身生存的宿主,病毒就会无意识也无差别地侵害生命。道家认为,尽管自然有着它“无情”的一面,人却可以依循大“道”,做到平等待人,平等地挽救生命。《庄子·秋水》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2]512“以道观之”就是从生存的根源之处看待生命,“以道观之”时,生命统合于共同的源头,得以彰显以自身存在为目的内在价值。“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2]68生命的纷繁与差异都由“道”统通,美与丑掸去他者以己为度量的审视目光只还原为存在本身,好与坏不必在取舍间被急于划上分界,价值判断不再以某一功用、某一观念、某一人为标准,生命的内在价值通过回归“道”以其自身之“在”为平等的唯一条件。换言之,道家根植于“道”,从内在价值的角度出发引导人把握更原初、更深沉层次的生命平等价值观念。
其次,疫病灾难不仅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区域,防控疫病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任务,道家的社会生态理念强调社会整体的和谐维系,注重各司其职的责任履践方式,是贯通古今的对人际与国际协作互助、同风雨、共担当的呼告。
人类栖居于同一个地球,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与流行事关所有人生命的根基以及生活的秩序。因此,防控疫病与处理生态危机就不只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区域的事情,而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责任。这一过程中,道家非常注重社会内部的协调互助。《老子·五十七章》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6]83道家视野中有圣人、诸侯、士、百姓等诸多社会角色,圣人、侯王的职责是施无为之治,百姓的职责是恬静生活。道家先贤属意的并非等级的划分与权势的分配,而是每个人基于其所处位置、所在境遇里承担自身所要担负起的那一份责任,所要维系的秩序,这启示我们在灾难危机面前以各施所长、协调配合,促进守望相助的合理化、有序化推进。
最后,新冠肺炎的全球性防控工作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向严峻疫区实施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道家的社会生态理念强调环境公正,引导我们看到疫病灾难与生态危机下人类扶贫援弱、同舟共济的道德光辉与实践精粹。
《老子·七十七章》曰:“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6]334生态系统本拥有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自我调节能力,但人类却常常枉顾这一规律,造成生物资源利用集权化、生态环境保护片面化等不公正的现象。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一面在经济发展中将生态环境危机转嫁给充当国际工厂的发展中国家,一面又将生态环境破坏归咎于它们的生产水平与生产方式,更是加剧了环境不公正的问题。《老子·三十二章》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6]188在道家看来,天地养育与自然造化都是客观存在与客观发生的,不以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物种的福祉唯命是从。因此,人也应平等地拥有自然环境栖居的资格、自然资源利用的权利、自然体验徜徉的机会。据此以观,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分享与成果共享都应保持敞开的姿态,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也应实现无障碍运转,人类若要谋求长远存续,就必然要在文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道路上扶助弱小,维护环境公正,持守人间道义。
概言之,无论是生态危机,还是作为生态危机集中表现的疫病灾难,都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道家基于“道”的本原特性提供了生命平等的基本看法和社会协作的朴素要求,道家对环境公正的有力倡导也帮助我们看清疫病灾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写照,绵延人类风雨同担、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恳切呼告。
三、“我命在我”:个人健康积极追求
一般而言,疫病的感染几率与人平常的生命健康状态也即个人生态息息相关,个人生态越有活力,被感染几率越低。“我命在我不在天”是道家道教极力主张的把握生命主动权的经典态度,虽然生老病死是每个生命个体都要经历的客观事实,但是个人生态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自己手中。在道家看来,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发挥人的主体性,主动把握生机,争取长生久视。1989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做出了新的定义,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道家对个人生命健康也给出了以身、心、性为主要剖面的整体性积极建议。
在物质性、生理性的身体方面,道家告诫人应自绝于险境,锻炼形躯,适度养生。《老子·十三章》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6]108人有物质性的身体作为生命载体,才会受到包括疫病在内的种种祸患困扰,这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事实。道家认识到身体对生命存在的关键作用——人的身体是其自然生命存有的现实基础与直接表征。《老子·十章》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6]93因此,道家希望人能如婴儿一般,拥有血气精专而富有生命活力、生存潜力的身体。而在道家看来,人要保有生命活力、生存潜力,首要的就在于明白并履践“后其身而身先”[6]83的要义,了解个人所处的情境,不先将自己置于险地。如在疫病灾难中,自觉做好卫生防护措施、居家隔离、疫区隔离就是不以身犯险的表现。并且,道家对躯体锻炼予以肯定。生理机能夯实与否虽然禀赋天生,受限于种种客观因素,但也在极大程度上受主观因素影响,道家认为,人有能力也有必要采取如“吐故纳新”“熊经鸟申”[2]476等积极主动的健身举措,增强身体素质。同时,道家主张适度养生,指出对身体无度的供养不仅无益于生命健康,反会带来负担,是害生之举。《老子·十二章》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6]104在道家看来,养生的关窍并不在于吸纳与摄取,而在于自我克制、自我节律、自我管理,在于维护生理机能的总体平衡。
在心理健康方面,道家认为虚心和乐也是人应致力涵养的心灵生态。疫病灾难及生态危机中,人们可能因生存的困缚、情势的紧急和矛盾的集中而产生慌乱、消沉、激愤等负面情绪,甚至造成极端情绪的爆发与外溢,引发过激行为,反而为疫病防治与生态危机处理带来不必要的阻力。在道家看来,这是人强持“成心”[2]56的缘故。道家认为心有勘察、认识、辨别等官能,心若是“实”的,被人自身预设的成见、偏见即“成心”填满,就会丧失接应万物的能力,以至于蒙蔽自我,加深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的隔阂,将自身的生命存在与生命体验从生态整体中割裂,也错失了事实在自身处原本呈现的机会。对此,道家认为人应“虚其心”[6]67,抹去心中的刻板印象,摒弃固有偏见,为现实情态与客观事实的呈现留有如实展布的充足空间。《庄子·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2]412道家也鼓励人无论在何种处境、拥有何种遭遇,都去感知与人和谐、与自然和谐的安适愉悦,并将这样的和乐境界内化为自身的心理状态,成为滋养生命的源泉。
在人性品格方面,道家坚信人本性纯白,无论文明如何发展,都应复性真朴,化育平和上善的生态人格。如果说,在儒家看来,人的本性如同一条河流中始终清明的底色,在生命的流淌之际等待着被发觉、被显豁,那么在道家看来,人的本性就如一条河流的澄澈源头,愈在俗世的前行中诉诸功利机巧,则愈浑浊。现代西方文学与哲学的经典之作《鼠疫》里,阿尔贝·加缪用象征主义的手法描述了阿尔及利亚兰城一场鼠疫下人在善恶之间的挣扎,在困境之中的异化,道家语境里,它所演绎的灾异下的人性写照,正是人性于迷离困顿中的走失与污浊。《老子·二十八章》曰:“朴散则为器”,[6]173道家珍视人性的初朴,遗憾人的异化,对人提出“见素抱朴”[6]134的要求,呼吁人缘着“道”的幽微光芒领会自身存在与世界存在在根源处的一致性,基于现实所处的情境,以持守自身的朴性为持护世界良善正义的焦点化方式。深层生态学创始人阿伦·奈斯尝言:“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7]生态视域下,道家引领人体悟大“道”,复归真朴,正是对塑造生态“大我”、培养生态人格的寄望。
合而论之,由疫病灾难对个人健康关乎身体、心灵、精神、意志、价值判断、情感理智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深切感知了个人生态的多元化与复杂性,而道家基于身、心、性为个人生态的修养提出了惠及整体生态世界的建议,启示我们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作用,积极主动地在关照身心健康的过程中持护生机,把握涵养生命活力与培育生态人格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对自然生命的眷注和“道”生万物命题的提出,道家警醒人正视自己的自然生命,认清人与自然于存在层面的相互寓于关系,深刻体悟人与自然是同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在救人不弃的生命平等与环境公正理念下,道家揭示了人类命运与共的生存本质,指出危机之下风雨同担是人类社会长足发展的应有之义;道家对个人生态积极涵养的倡议鼓舞我们充分发扬主体精神,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把握生机,关怀由生理、心灵、精神、价值观念、情感理智有机建构的整全生命健康。道家哲学的生态智慧提供了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认识人类动态生存状态的根源性、整体性视角,有助于破除主客二分、人与自然对立的僵化思维,将珍爱生命与敬畏自然的范围拓展至生命共同体的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