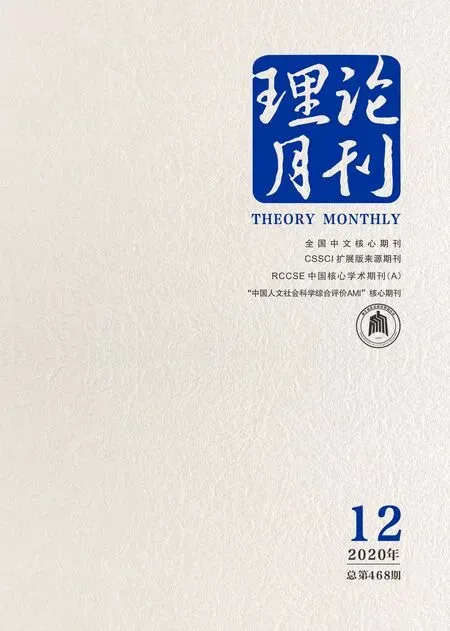数字劳动异化
——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
2020-12-14刘海霞
□刘海霞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他阐述了私有财产的关系,继而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些分析既客观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也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当前的经济情况同马克思时代的经济情况相比要复杂得多,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广泛运用,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出现了。这种劳动形式使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了新的表现。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数字劳动进行概念性界定,然后以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为基础分析数字劳动异化的相关表现,探索数字劳动背景下对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阐释,以期为异化劳动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一、何为数字劳动
目前对于数字劳动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数字劳动的雏形是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Walker Smythe)提出的“受众劳动”[1](p1-27)。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在《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和循环》(Cyber-Marx: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分析了“非物质劳动”主体,努力探求人们如何凭借信息时代新的高科技塑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机器体系与普遍商业化的世界秩序,以及如何辩证地认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新力量[2](p1-2)。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米歇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ir)在《帝国》与《大众》两本书中从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3](p198)出发,揭示出工人阶级转为大众的劳动基础是:工业劳动的霸权地位转向了“非物质劳动” 的霸权地位[4](p75),“非物质劳动”成为信息时代解释社会演进的理解基础。而后,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借用“非物质劳动”的概念,通过互联网上的“免费劳动”对“数字劳动”进行了探索。他认为,数字劳动是一种免费劳动,把文化消费转化成了一种生产性的劳动。这种网络免费劳动包括建立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与邮件列表,以及在MUDS和MOOS上建立虚拟空间等劳动行为。因此,数字劳动者被戏称为“网奴”[5](p34)。为了更形象地理解这种劳动,朱利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提出“玩工”这一概念,并以游戏的改编者付出的劳动为例进行分析。他认为,这种改编劳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也不是单纯的休闲活动。因为改编者作为免费的劳动者,即“玩工”,既不受工资的驱动也不受资本家的控制,但是却被纳入了游戏开发商的生产体系之中,像志愿劳动那样免费为游戏开发商带来了巨额利润[6](p1-8)。泰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认为,与传统劳动相反,随意的数字劳动看起来仅仅是认知剩余(cognitive surplus)①认知剩余,也被称作“认知盈余”,由克莱·舍基(Clay Shirky)提出,指我们在网络上作分享的工作时间,揭示的就是“无组织的时间力量”。的耗费。它没有感觉和外观。因此,数字劳动非常类似于那些不那么明显的、隐晦的传统女性劳动形式,如育儿、家务[7](p12)。福克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数字劳动。他认为,数字劳动不仅包括无偿的互联网使用者的劳动,还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行业整个价值链涉及的各种劳动形式,如富士康工人、硅谷的装配工人、软件工程师等各种劳动者的劳动[8](p7)。
国内学者也对数字劳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主要集中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有些学者表达了对西方学者观点的认同,例如,燕连福、谢芳芳将数字劳动的内涵区分为广义的数字劳动与狭义的数字劳动。广义的数字劳动就是福克斯提出的数字劳动,即整个通信行业价值链上的各种劳动;狭义的数字劳动就是以数字技术为终端的社交媒体的用户的劳动[9](p116-117)。李仙娥对数字劳动概念的界定与福克斯大致相同,她认为数字劳动是指“提供数字媒体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各种生产劳动”[10](p7)。李仙娥和骆晨还将数字劳动分为三类:生产硬件的劳动,如制造商的劳动;生产内容和软件的劳动,如作曲者的劳动;生产性使用者,如生产消费者和演奏者的劳动[11](p4)。黄再胜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观点一致,认为数字劳动是通过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加以协调的一种非物质劳动形态,呈现出个体化、娱乐化和体验化等特征,包括社交媒体平台的无酬劳动、网络平台的微劳动以及网约平台的线上劳动[12]。有的学者对数字劳动进行了重新定义。比如吴欢、卢黎歌认为所谓数字劳动是指以数据信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支撑,囊括工业、农业、经济、知识、信息,存在一定空间,消耗人们时间的数据化、网络化的工作形式[13](p9)。郑吉伟、张真真认为数字劳动是数字劳动者运用劳动力作用于互联网等媒介开展一系列复杂工作的劳动形式,是数字化时代社会生产劳动的具体表现[14](p100)。韩文龙、刘璐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资料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15](p67)。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起初这种新型劳动形式在新闻领域备受关注,并被称为“受众劳动”,主要涉及媒介的使用者。到后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数字劳动”专指在使用互联网时受资本家剥削的劳动者的一种无偿劳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将数字劳动只定义为互联网平台上的非雇佣的无偿数字劳动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学者们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探究数字劳动对社会生产造成的影响。有学者认为:“研究者通过对数字信息技术产业的全球生产进行实证案例分析,指出数字劳动并不仅仅简单地包括数字内容生产的形式,它还包括农业、工业、信息等劳动形式,正是这些劳动形式使数字媒介得以存在和发展。”[16](p2)也就是说,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劳动不仅存在于媒介传播行业,而且存在于其他各种行业。
研究数字劳动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经济背景,即数字经济背景。2016年,我国在《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书》中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7]数字劳动既然是一种劳动形式,那么它也应该符合一般劳动的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8](p208)。“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18](p211)结合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给出如下定义:数字劳动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新的劳动形式,指能够把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劳动对象,把数字信息技术作为劳动资料的劳动者进行的劳动。换言之,数字劳动过程就是指劳动者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对数字化的信息和知识进行加工,从而使自身劳动对象化的过程。而且,数字劳动与工业时代的传统劳动是并存的,更多的情况是两者共同参与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所以,数字劳动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传统劳动的延伸,两者之间存在很深的连续性。但同时数字劳动也表现出了新的形态,即数字化和非物质性的形态。数字劳动形式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研发层面,主要涉及软件与技术研发者;二是内容和应用层面,涉及雇佣关系下的软件与技术的使用者,以及非雇佣关系下的使用者,即无偿数字劳动者(也被称为“产消者”)和零工。软件与技术研发者和雇佣关系下的软件与技术的使用者跟传统劳动者的差别只是在于生产资料的改变,非雇佣关系下的无偿数字劳动者和零工的劳动则是对传统劳动形式的拓展,并使劳动异化有了新的表现。
二、数字劳动异化的表现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阐述是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国民经济学家将有利于资本获利的一切手段理论化,让劳动者认为资本家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合乎人性的,使人变为非现实的、异己的人,甚至“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取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19](p120)。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工人任何超过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都是奢侈的、不可饶恕的。但本质上,劳动是人的特有的对象化活动,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在劳动中不断改造自然、改造自己。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出于自己本性的自愿劳动,在人的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私有制使劳动与劳动者分离开来,使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私有制导致的异化劳动使工人的生活越来越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它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9](p47)。这种异化劳动,使工人感觉到的只有痛苦,使工人的活动仅仅成为谋生的手段,限制了人类自由及本性的发展。
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型劳动形式,处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为资本积累提供新的路径。因此,在私有制占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数字劳动发生异化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依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劳动者从形式隶属资本到实际隶属资本的过程,也是劳动者本身主体地位渐渐丧失的过程。数字劳动拥有一些新的特征,可以使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力量在某些方面有所削弱,但是异化问题仍然没有消失。哈特穆特·罗萨说:“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和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社会关系的人,不必然在物理距离方面也离我们很近,反之亦然。同样的,社会相关性也与空间邻近性脱节开来。”[20](p118)也就是说,当今数字化社会的交往大都是以数据为中介的。但是这种数据中介被网络企业的资本家视为一种垄断性资源,从而产生异化问题。从本质上讲,数字劳动异化与传统劳动异化是一致的,只不过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区别,因此也包含四个方面。
(一)数字劳动商品化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不是问题的真正原因。即便是在当今,一般数据和数字化的中介也并不一定成为异化的根源,最根本的根源仍然需要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寻找[21](p113)。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资本依然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资本逻辑——资本无止境的自行增殖的本性和必然性[22](p93)决定了数字劳动必然会被商品化。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价值增殖的原因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商品是通过工资劳动、面向市场而生产出来的资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永远需要新的市场、新的原料和生产过程、新的更为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或非熟练劳动力”[23](p25-26)。因此在这种条件下,数字劳动注定会走向商品化。数字劳动商品化也就是数字劳动资本化。这跟传统劳动转化为商品并受资本控制没有本质差别。
数字劳动既可以进行物质生产,也可以进行非物质生产,其中最具特点的是雇佣关系之外的无偿数字劳动进行的非物质生产。通常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资本主义表现为:生产的结果就是商品,这种商品可以独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而存在一定的时间,例如与艺术家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马克思认为,这种生产活动是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而且在形式上也没有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恰恰在这些过渡形式中,劳动者所受的剥削最多[3](p417)。反观数字劳动,其在非物质领域的生产结果是数据商品。但是无偿的数字劳动者并没有被资本家雇佣,因此也不会有资本家向他们支付工资。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不符合传统劳动的条件。尽管如此,这种无偿劳动依旧属于劳动范畴。因为这种数字劳动通常是平台用户通过劳动力再生产环节参与到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从而为资本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种劳动者也就是朱利安·库克里奇所说的“玩工”。而且,由于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很多时候是同时进行的,劳动时间与娱乐时间的划分比较困难。因而,对“玩工”的剥削利用的是基于工作时间与娱乐时间区分的丧失[24](p17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劳动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都扩大了。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模糊,使工人原本的个人休闲时间异化为进行资本积累的时间。原本只有雇佣条件下的劳动会发生异化,而在数字劳动时代,非雇佣条件下的无偿劳动也会发生异化。
(二)数字劳动产品异己化
马克思从当时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分析得出:“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9](p47)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9](p47)工人不仅得不到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还要被自己的劳动对象奴役。对于数据的追求是数字技术生产功能的特征。数字劳动作为用户对商业平台的使用,会产生数据商品,拥有平台的企业借此来创造利润。因为,用户“花费在企业平台上的时间是他们无薪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的数字劳动创建了社会关系、利润数据、用户生成的内容和交易数据(浏览行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数据商品,被网络企业销售给了广告客户,让他们选择某些用户群”[24](p157)。数字劳动产生的数据商品并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是企业平台以信用抵押为由用隐私条款获取的。但是这些数据商品被企业平台转卖给广告商,价值最终会在用户观看广告、购买会员以免除广告或者购买广告中的商品时得到实现。所以,数字劳动生产的商品也是一种异己的存在,商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劳动者反而会被商品所奴役。
另外,数字劳动产品中包含的情感、信息、交往等非物质产品,会成为导致“人的心理机制异化的因素”[25](p156)。现代生产依赖于数字技术,互联网信息对人的认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会使人们认识的世界成为一个幻象,而非真实的世界。例如一些社交软件就会诱使人们不断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前提却是人们要完全认可社交网络运行的逻辑,也就是说,“个体确立主体身份的过程就是一个将自身客体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臣服性的过程”[26](p81)。人们一旦认可了这种逻辑,社交网络就可以反过来控制人们的行为,影响人们的意识,从而使人们在网络世界中迷失自我。因此,人的主体性被一点点消磨,最终会按照他人的意志来审视自己的行为。至此,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都已完成。
(三)数字劳动者类本质异化
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证明了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的生产是受肉体需要的支配,其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人可以在不受肉体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且能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在传统的劳动异化理论中,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的原因是劳动者的需要被抽象为一般,使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分离,但是人的生产行为还是有意识地进行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的某些生产行为却很难被劳动者自己发现,更不用说进行有意识生产活动了。
相对于传统劳动,数字劳动的特性包括无偿性和无意识性。当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无偿劳动时,由于其不易被劳动者察觉,因此会被劳动者欣然接受,即使他们受到了剥削。此外,数字劳动是一个模糊了工作时间与娱乐时间之间界限的范畴,数字劳动者根本无法将工作时间与娱乐时间完全分隔开来。或者说,劳动者的全部时间都有可能会转变为工作时间,因此数字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受到的剥削便会加剧。肖尔茨指出,由于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之间隔阂的消失,使得数字劳动具有两个特点,即剥削的诱惑和赋予权力的潜力[7](p2)。剥削的诱惑使类本质发生异化,在此基础上赋予数字资本家的权力则会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异化。
无意识劳动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驱动的“瘾性消费”①“瘾性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用来制造稳定需求的手段,其实质是剥夺人们的选择权,使他们无法选择不去消费那些“过瘾”的商品。。这种消费行为会导致人们变成适应资本逻辑生产体系的“单向度人”[27](p126)。也就是说,在资本逻辑的牵引下,人们的消费习惯会主动跟随资本导向的方式,被资本随意支配。在当今数字网络信息时代,让人们上瘾的不是手机和电脑等硬件,而是这些硬件中包含的内容。因此,互联网公司就会通过手机的用户浏览数据进行定向推送,从而加固这种“瘾性消费”,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
(四)数字劳动异化导致的社会等级分化
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推动着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分工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19](p131)。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着个人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基础。阶级被认为是一种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过程中基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形成的雇佣与被雇佣、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28](p195)。首先从纵向来看,数字劳动依然生产出具有私有制性质的资本家。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关系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使剥削程度加深,剥削范围扩大。前文描述的数字劳动商品化与数字劳动产品异化都说明数字劳动并没有突破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从而也无法逃脱被资本剥削的命运。其次从横向来看,数字劳动的异化使社会在数字经济中呈现等级分化。人的社会活动受数字技术和数字劳动效率的制约,越是熟练掌握数字劳动规律的人,越能够在互联网社会中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进而在“数字等级”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25](p156)。在信息时代,准确的知识成为一种力量,对于那些有机会利用优质信息的个体来说,将网络中的信息从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共享的资源转变为需要专家去伪存真的资源,就可以使他们从中获利。因此就出现了一群利用网络专门从事信息买卖和给出建议的“符号分析家”,或者称之为“数字精英”。这些“符号分析家”从消费者那里获得原始数据,再按照消费者希望的方式处理好信息,然后再将处理过的信息卖回去,由此他们能最大限度地从数字空间中获得好处。赖克(Robert Reich)在其论文中曾这样形容:“高居上层的那些符号分析家在世界范围内是深受欢迎的,他们几乎搞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来自哪里。历史上从来没有人的收入会如此丰厚,而且这种收入是合法的。”[29](p31-42)数字劳动异化形成的等级分化会对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造成不利影响,虽然不会像工业时代劳资对立关系那般激烈,但还是会引起社会不公平现象。
三、数字劳动对异化劳动理论是突破还是加固
数字劳动并没有摆脱被异化的命运,但是由于技术水平以及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的异化有了新表现。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新表现,便可对异化劳动理论作出新的阐释。但数字劳动对异化劳动理论究竟是突破还是加固,还需要进行详细分析。
(一)数字劳动与劳资关系的重构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的实质是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支配,结果是资本对劳动结果即产品的支配[30](p16)。“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9](p56)劳动异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对立与矛盾的激化。但是,数字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对峙状态一方面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加剧。
其一,数字劳动可以给予工人一种“看似自由自主的工作状态”,在数字经济时代,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迫切希望人们采用一种更加方便快捷的工作模式。数字经济为社会生产提供的以信息技术为劳动工具的生产方式,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因此,资本家不会再把关注点放在工作地点和时间的统一性上,而是只要能获得剩余价值即可。劳动者摆脱了机器设备与厂房的控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本家的监督。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象。因为,这种工作状态使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界限模糊化,给资本家为工人安排工作提供便利,其结果是:“数字劳动给人的‘时空自由’会逐步成为资本家的理想安排,形式上给予劳动个体以个性、独立、自控的快感,实质上潜在加剧对工人的剥削,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同时承受同行从业人员的竞争和失业的危机感”[31](p407)。所以说,数字劳动即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自由的工作模式,同样也会成为限制人们自由的一种工作模式。
其二,数字劳动的出现促使新的组织关系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19](p117)。最终,这种异化就表现为“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19](p118-119)。需要的异化,是资本与劳动对立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数字劳动时代,由于互联网技术或数字技术本身蕴含着的共享属性,会形成一些具有共享性和公益性的数字媒介平台。这种数字平台可以无偿满足人们的需要。当然,实际情况并不会这么顺利。资本逻辑扭曲了数字技术的这种共享属性,借用“共享经济”的名号建立了一系列的共享网络平台,使大量的劳动者变成没有任何福利保障的零工,以便节约网络平台企业的成本。因此这种“共享”背后实则是“独享”。
(二)数字劳动与人的主体性复归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到那时,私有制被彻底铲除,生产力高速发展,产品极大丰富,并且人能够充分获得和使用这些产品,实现自身的完全解放和自由发展。对私有财产的铲除,实质上也就是把人们从异化中解放出来。而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剥削工人,而工人为了维持生存,只能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工人自身反而越来越贫穷。但是,马克思说,“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是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19](p125)。也就是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中介,而要消除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并且长期坚持下去。在这里需要强调两点:首先,马克思所说的消除私有财产并没有完全否定私有财产的存在价值,并不是对私有财产的彻底否定。人们只有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与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马克思曾对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严厉的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其看来“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最后,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这个运动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19](p75)。依据马克思的描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把对物质的占有当成人们劳动的目的,它仅仅把劳动当作财富积累的手段,因而它主张把社会物质财富平均分配给每个人,也就是说,把原来的私有财产汇聚到一起,然后重新分配给每个人。但这只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使社会中的每个人的财产都成了私有财产,是私有财产概念的广泛扩散,并没有消除私有财产。
虽然现在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还不能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完全复归,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人的主体性复归的进程被加快,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数字劳动者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信息、知识以及数据等。这些要素多是通过教育或者在互联网交往中获得,而不是全部由资本家所占有。因此,数字劳动者特别是无偿数字劳动者不再受资本的强制控制,对劳动时间、地点甚至是产品形态都具有较高的自主权,且可以按照个性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无偿数字劳动的本意是休闲娱乐,而不是为了生产。从这个层面讲,无偿数字劳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人的类本质的回归。而且,数字劳动产生的情感、关系等非物质产品是构成人类主体性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无偿数字劳动的劳动本意与产生的结果来看,人的主体性呈现回归趋势。
马克思说:“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9](p85-86)因此,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还得发展生产力,通过经济活动等现实的实践活动,在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就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依然需要私有制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言,“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1](p126)因此,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奋斗。
四、余论:争取非异化劳动的可能
马克思全部学说的核心就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性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人参与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通过对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出了资本积累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受到资本的支配而发生异化,使劳动与资本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但是,社会向前发展,在未来社会我们必然要做的就是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劳动解放。
劳动的异化、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但是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3](p208)。而且,“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了这种异化”[3](p208)。因此,马克思说:“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动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3](p185)在资本逻辑下,本来用于解决问题的技术发展似乎带来了更多的经济社会问题。但是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解决问题的特征一直都存在。就像机器抛开它所处的制度环境,可以减轻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缩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这种有利于劳动者的功能却不利于资本家,所以它反而变成了加剧剥削的工具。但是,当“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合适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生产关系”[3](p188)。也就是说,“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作用物”[3](p209)。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数字劳动既可以是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为劳动者挣脱资本枷锁创造条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将作为消费个体的“I”变成生产性、群体性、社会性的“We”,以及如何产生“We”[27](p122)。数字网络能够为发挥劳动者主体地位而服务,例如它可以将用户生产内容转变为工人生成内容,因为“工人”更具有集体性质和社会性质。只要能落实劳动者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在生产决策和剩余价值分配两个环节上,实现数字劳动者的真正民主参与,就有可能会扭转数字技术只为资本服务的局面,使数字化资源成为全民资源,从异化的困境中走出来。然而,理论上的可能性只是一个进行历史分析的维度,代替不了现实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消除数字劳动异化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