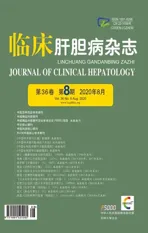原发性肝癌转化治疗研究进展
2020-12-14胡宗强徐源通
江 杰, 胡宗强, 陈 刚, 徐源通, 褚 光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甘美医院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 肝胆外科, 昆明 650000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全球第六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发病率仍在上升,其死亡率为全球恶性肿瘤死亡率第四,我国每年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占全球半数以上[1-2]。《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3]和欧洲肝病学会、美国肝病学会指南[4-5]指出,肝癌的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切除、肝移植、介入治疗、局部消融治疗、放疗、全身治疗等。其中,肝切除术、肝移植是原发性肝癌患者延长生存期甚至获愈的最优选择方案。但其恶性程度高,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及体征,病情进展快,大部分患者发现时已是中晚期,可行手术治疗的病例仅为20%~30%[3]。限制手术的主要因素包括肝内多发病灶或病灶巨大、肝内外转移、癌栓侵及大血管、余肝体积不足、肝功能不全等[6]。
控制肿瘤发展及不可切除性因素、增加手术机会是延长肝癌患者生存时间的关键,也是现阶段肝癌治疗临床研究的热点。但目前仍有很多医生对转化治疗及术前新辅助治疗定义混淆。其中,转化治疗是指不可手术但具有潜在手术性的患者经介入治疗、全身治疗、保肝治疗等治疗手段,控制肿瘤进展甚至降低临床分期,改善肝功能,从而可行手术[7];也指不符合肝移植标准患者经治疗获得移植机会[8]。而术前新辅助治疗是指有手术指征的恶性肿瘤患者,治疗后减小肿瘤,增加R0切除率,降低远处转移和复发率,提高患者的生存期。
目前,转化治疗是中晚期肝癌治疗的研究热点,治疗前评估、治疗方案选择及手术时机评估均为治疗的关键。本文主要针对肿瘤负荷或存在血管侵犯、转移病灶、余肝体积不足的原发性肝癌转化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1 转化治疗相关评估
肝癌病情发展较复杂,常用超声、对比增强CT 及MRI 等影像技术,结合AFP 等肿瘤标志物进行综合评估,评价指标包括肿瘤大小、数目、癌栓位置及AFP水平等,以动态评估肿瘤分期及转化治疗效果,密切监测肿瘤对转化治疗的反应率。多学科诊疗团队(MDT)综合Child-Pugh评分、肿瘤大小、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剩余肝脏体积及远处转移等明确诊断及分期,选择个体化的转化治疗方案,并评估治疗后的手术时机[8-9]。
2 转化治疗方案
2.1 血管性介入治疗
2.1.1 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 TACE通过肝动脉注射化疗药物和栓塞剂至肿瘤营养血管导致肿瘤缺血性坏死,是肝癌非手术治疗的首选标准治疗,常用于术前新辅助治疗、肿瘤降期治疗等,能够有效控制肿瘤进展,为肝切除术及移植术争取更多机会[10]。多项研究[11-12]表明,超米兰标准的肝细胞癌(HCC)患者行TACE治疗,75%的患者成功转化至米兰标准并接受肝移植术,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70%以上,与符合肝移植标准的患者生存率及复发率无明显差异 。在Zhang 等[13]的研究中,831例不可切除性肝癌患者接受TACE治疗 ,共 82 例转化治疗成功(9.87%),43 例接受肝切除术,治疗后手术组的生存率显著高于未手术组。
2.1.2 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 HAIC是通过植入性药盒导管系统有效地将化疗药物作用于肿瘤,反应率较高,全身毒副作用减少,对合并PVTT的HCC疗效明显[14]。HAIC 治疗方案较多,其用药包括5-氟尿嘧啶、顺铂、奥沙利铂等。He 等[15]对79 例不可切除性HCC患者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比较改良FOLFOX化疗方案的HAIC组与TACE组疗效,结果显示HAIC 组客观有效率(52.6% vs 9.8%)、疾病控制率(83.8% vs 52.5%)、可切除性 HCC病例数(10 vs 3)均高于TACE 组。Lee 等[16]回顾性研究中发现103例Child-Pugh A级的晚期HCC患者接受HAIC治疗后,12例行肝切除术,中位生存时间为(37.0±6.6)个月。
介入治疗作为不可切除性HCC转化治疗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病情,使患者获得更多手术机会,但该方法也受肝功能、PVTT、肿瘤大小和数量等影响。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的Ⅱ期临床研究[17]亦证实HAIC具有较高的转化切除率。
2.2 局部消融治疗 肿瘤消融术是早期肝癌的常见治疗手段之一,借助医学影像技术定位,采用化学(乙醇、乙酸等)或物理(射频、微波消融或冷冻消融等)方法直接导致肿瘤坏死,在肝内转移等病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8]。蔡涵晖等[19]对16例难治性肝癌患者行腹腔镜下肝切除术联合射频消融,结果显示术后1年无瘤生存率为100%。李岩[20]对50例多发性肝癌患者进行了分析,发现肝切除联合消融术的并发症发生率较肝切除术低(5.55% vs 32.14%)。随着消融技术的发展,消融治疗常用于肝癌的术前新辅助治疗及手术后复发治疗,也被应用于暂无手术指征的HCC患者转化治疗。多位学者[19-21]的临床实践证明,肝切除联合射频或微波消融治疗在多发性肝癌中具有完全消除肿瘤的临床应用价值。
2.3 放射治疗 放疗是患者等待肝移植期间的一种衔接治疗,也是Ⅲa 、Ⅲb 期肝癌患者获得手术机会的希望。放射治疗包括立体定向放疗、三维适形/调强放疗及放射性粒子植入等。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放疗的照射野精准、大剂量分割照射次数少、局部控制高、不良反应低,使之有效应用于肝脏肿瘤的治疗。Pracht等[22]研究显示,18 例肝癌伴同侧PVTT 的患者经动脉植入钇90微球进行内放射治疗,完全缓解2例,部分缓解13例,肿瘤降级 4例。Assalino等[23]对45例侵犯大血管的HCC进行治疗,其中30例局部放疗后血管浸润完全消退,并成功行肝移植术。近年来,放疗从新辅助治疗、姑息治疗中脱颖而出,能够控制肿瘤负荷、肿瘤体积等。在转化治疗中,放疗对合并血管侵犯的肝癌患者疗效明显,能够达到转化切除治疗、桥接移植治疗等治疗目的。
2.4 系统治疗
在精准医疗的时代背景下,肝癌常伴肝炎、肝硬化等,使得肿瘤分子表型异质性较强,需要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其中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系统化疗在肝癌的个体化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
2.4.1 靶向治疗 药物通常包括多靶点激酶抑制剂、抗血管生成分子靶向药及mTOR信号通路特异性抑制剂等,直接或间接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及侵袭,其中索拉非尼、仑法替尼为晚期无手术指征肝癌的一线分子靶向药物。“SHARP”“GIDEON”等HCC 靶向药物临床试验研究[24]表明,肝癌伴有大血管侵犯、高水平AFP等均可从靶向药物治疗中获益,证明了索拉非尼对不可切除性肝癌的有效性,当病情转化至部分缓解或完全缓解后,再次MDT评估外科干预治疗时机。
2.4.2 免疫治疗 主要是通过减弱肿瘤细胞对免疫细胞识别的抑制作用,或增强宿主免疫系统识别,从而增加机体对肿瘤的免疫攻击及削弱肿瘤的免疫逃逸,其中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受体-1配体抑制剂最具代表性。nivolumab临床试验[25]中,纳入262例晚期HCC患者,治疗期间的整体客观缓解率为15%~20%;Check MATE-040研究结果显示,49例nivolumab治疗病例中,疾病控制率为55.1%。Kaseb等[26]在HCC围手术期辅助免疫治疗的随机临床研究中发现,经nivolumab 和/或ipilimumab治疗后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提示完全缓解为33.3%,明显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并降低了术后复发率。虽然免疫治疗多应用于新辅助治疗,但对转化治疗也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同时,免疫治疗与TACE、消融术、靶向治疗及全身化疗等联合治疗在中晚期肝癌的降期转化治疗中也展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免疫靶点抑制剂对肝移植的不良反应限制了转化治疗的二期手术方案。
2.4.3 系统化疗 传统肝癌化疗药物包括阿霉素、5-氟尿嘧啶、顺铂等,有效率不高,毒副作用大,可重复性差,可能激活HBV复制、加重肝炎肝硬化等不良反应。近年研究发现奥沙利铂具较强的DNA 结合作用,且细胞毒性更强,联合5-氟尿嘧啶具有临床增效效应,对原发性肝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27]。Kaseb等[28]对84例不可切除性HCC患者采用顺铂/IFNα-2b/阿霉素/5-氟尿嘧啶联合治疗方案,其中33%的患者转化治疗成功后行根治性手术。Leung等[29]对50例伴肝内转移的不可切除性HCC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经全身联合化疗后客观有效率为26%,9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后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其组织学检查未发现存活的肿瘤细胞。
随着肝癌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及化疗方案的不断更新,不可手术性肝癌降期转化率明显提高,但有效性和安全性常受肝功能、肿瘤异质性等因素影响。在“精准医疗”模式的推动下,通过联合基因检测等方法能够构建更具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有效地保证转化治疗成功率。
2.5 针对余肝体积不足的治疗
部分中晚期肝癌患者存在术后剩余肝脏体积少、肝脏功能储备不足等情况,此时行肝脏切除术,术后患者可能因肝衰竭死亡。
2.5.1 门静脉栓塞治疗 门静脉栓塞术(preoperative portal vein embolization,PVE)或门静脉结扎(portal vein ligation,PVL)主瘤所在半肝,PVE可使栓塞侧肝脏萎缩、对侧肝脏代偿性肥大,增大术后剩余肝脏体积,提高手术切除率和安全性,使不能直接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相较于肝正常的肝癌患者,慢性肝病的肝癌患者行PVE引起的剩余肝脏体积肥大明显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术后生存预后无明显差异[30]。
2.5.2 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 ALPPS适用于预期残余肝脏体积占标准肝体积不足30%~40%的患者,主要分为结扎门静脉+原位肝劈裂术和肝大部分切除术两大步骤:Ⅰ期,门静脉结扎+原位肝劈裂术,诱导剩余肝脏体积快速增生;Ⅱ期,肝内肿瘤切除术(R0切除),若暂无手术指征,则行TACE 、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张远标等[21]通过经皮微波或射频消融肝实质分隔联合门静脉栓塞计划性肝切除术替代ALPPS治疗,成功转化剩余肝脏体积不足的不可切除性肝癌患者,获得根治性手术机会。但该手术的围手术期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较高,感染和胆漏是ALPPS术后最主要的并发症[3]。
2.6 联合治疗 影响中晚期肝癌患者手术的因素较多,单一治疗存在局限性,结合患者动态复查情况,通过MDT评估并制订个体化的联合治疗方案,如:TACE+靶向治疗/免疫治疗、TACE+PVE、局部放疗+靶向治疗等,待患者转化治疗成功后再次行MDT评估患者病情及肝切除术或肝移植时机,以改善远期预后。
3 结语
近年来,尽管肝癌诊疗技术不断更新,但仍有约 70%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在确诊时已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肝切除术、肝移植依然是改善远期预后甚至治愈的最佳治疗手段。对于不可切除性肝癌,上述治疗方法能够有效地使部分患者成功降期转化,从而获得手术机会。因此,有效的转化治疗为中晚期肝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贡献声明:江杰负责课题设计,资料分析,撰写论文;徐源通、褚光参与修改论文;胡宗强、陈刚负责拟定写作思路,指导撰写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