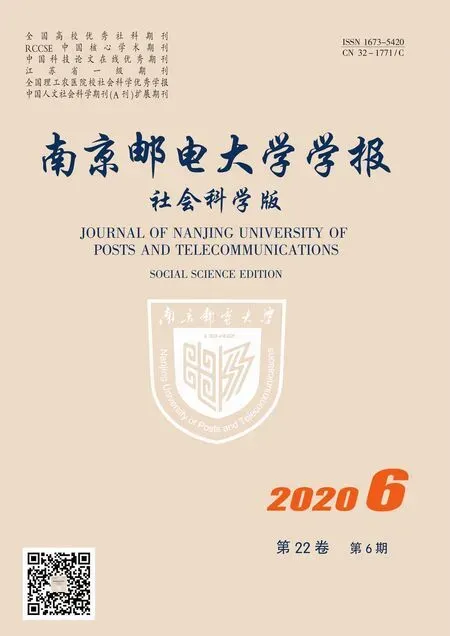从疫情防控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0-12-13李晨涌
李晨涌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自2019年年底开始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重大威胁。如何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共识,事关国家抗“疫”与社会发展稳定的大局,对当前凝聚共识和战胜疫情具有重要意义。
一、逻辑与价值:疫情防控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凝聚民族共识的显性话语,事关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族群众政治认同的大局。面对疫情的全球扩散,无论是基于国家稳定还是民生所需,都需要以一个具有凝聚共识、给予各族人民安全感与归属感的“精神家园”为依托。因而,应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凝聚集体共识、激发民族自强,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战“疫”的重要基础。
(一)有利于为参与疫情防控的主体力量铸牢民族纽带
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这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基础,也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因而,在疫情防控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凸显防控主体的“一体之合”与“多元之和”。
其一,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疫情防控中的“一体之合”。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共同结合成的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而“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1]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存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的过程中,迸发出的救亡图存的“危机感”和守望相助的“革命情”,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蓬勃发展,也促使各民族在交融中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各民族紧密配合、团结协助,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其二,展现出中华民族在疫情防控中的“多元之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长期延续的自在共同体,其深层次结构表现为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而不同”思维意识,其在提供思想支撑的基础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对“多元”的包容、尊重和肯定。这种多元的共时性在民族成分、地域风貌、生存方式、文化信仰等方面有所体现;而多元的历时性则在“历朝历代的版图和政权所表现出的都是多元一体的人群与文化”[2]上可见一斑。其中,多元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实现了一种和谐共生:共时性多元之和,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乃至血缘的融合贯通,打破了阻滞发展的隔阂与梗阻;历时性多元之和,承载了历史朝代所积淀下来的精华,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发展与赓续[2]。因此,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中华民族共同抗“疫”成为历史的选择。疫情所产生的社会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散,共同抗“疫”需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之和”,坚决摒弃狭隘民族主义与大汉族主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汇聚各民族为国家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抗“疫”合力,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疫”。
(二)有利于为凝聚疫情防控的民族共识奠定认同基础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各民族群众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疫情防控需要强化国家认同、深化民族情感、汇聚民族共识。
其一,在疫情防控中以“共识”来维系民族情感、强化国家认同。共同体意识反映了主权国家中各民族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尤其是多民族国家,牢固、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一旦“缺席”,便如同一盘散沙。可见,共同体意识的在场与否,关乎国家的兴盛衰亡。回望历史,长时期的迁徙杂居、民族融合、文化语言吸收糅合等奠定了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基础条件,并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换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所取得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因此,在疫情防控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激发各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强化国家认同,不断深化各民族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民族情感。
其二,在疫情防控中把握“分与合”来改善群际关系、凝聚民族共识。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族裔多元创造了共同体的活力,也带来了异质性的内部张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就存在着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博弈,且会因内外环境不同而产生差异。譬如,离心力一旦超过临界线,便意味着群际关系或民族意识超越一定的界限,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可能会面临被肢解的危险。基于此,“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依托的上位共同体认同意识。因此,面对疫情的严峻形势,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强化“五个认同”(1)2015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首次形成了“五个认同”的表述,即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可以在改善群际关系、汇聚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抗“疫”。
(三)有利于为个人疫情防控的意识归属提供集体依托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个体提供特定的归属感,深化中华民族抗“疫”的集体记忆,在维护共同体利益的基础上更好地“全民抗疫”。
其一,作为“个体对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维护共同体利益为基本遵循。共同体意识是个体在感知自身与他者生存发展基于共性条件的基础上,所呈现的共善价值遵循与能动意愿聚合。也可以说,共同体意识是对“我们曾经是谁、现在是谁以及想要成为谁”的现实回答。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个体对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归属感,所呈现的集体性“比起单独个人的主体性拥有更多的内涵、更广的包容和更大的力量”[4]。疫情中飞沫、接触传染警示个体要保持社交距离,而获取生存生活、医疗防治等保障又强化了个体对他者以及社会的依存,在“远离,还是靠近”的矛盾心理中,体现出个体对集体性的呼唤。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5]491。基于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个体提供特定归属感,使其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与社会为一体的“共在”,进而在做好自身安全防范的同时与共同体成员一起理性抗“疫”,实现“1+1>2”的溢出效应,这不仅是对人的本质为“社会的存在物”的复归,也是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最生动的注脚。
其二,作为“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回应共同体诉求为实践取向。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二者都凸显了中华民族是有着共同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的历史命运共同体。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6],作为一种非排他性的话语表达,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在公共价值诉求上所具有的共通性、互识性和共识性,有助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互惠共赢。随着疫情的暴发,民众正常生活瞬间“熔断”,各民族对疫情防控的公共价值诉求也不断攀升。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来推进疫情防控,从精神、公共安全等方面提供安全保障,积极回应各民族对疫情防控的公共价值诉求,汇聚疫情中各民族群众的抗疫合力,使他们在守望相助中战胜困难、共渡难关。
二、困窘与遮蔽:疫情防控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挑战
回望历史,疫情与疾病的考验从未缺席。而在应对疫情与疾病的同时,中华民族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也得到强化。疫情防控是一场全民“战疫”,疫情中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不仅考验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环境日趋严峻。
(一)疫情中“防控与救治”的短板效应对共同体意识的削弱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7],也使本应充分合作、无缝对接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链条暴露出一些不足,出现了疫情信息获取不对称、少数干部存在形式主义等现实问题,由此产生的短板效应也削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方面,疫情早期对新型病毒性质、传播规律与传染危害性等信息获取的不对称,致使早期疫情防控反应迟缓。对疫情的防控是否及时、救治是否到位,是检验国家卫生治理体系的“试金石”。疫情的暴发、快速传播,暴露出在预警、先期处置、应急能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短板,如医疗资源和医疗技术供给不足等问题,这不仅加剧了疫情暴发早期民众的恐慌心理,也削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疫情防控工作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出”,少数干部在疫情救治中“不作为、不会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马特兰德构建的政策执行“模糊-冲突模型”中,执行情势是影响政策的关键因素。疫情发生后,地方政府亟须以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首,全力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之中。但在实际防控中,个别党员干部在紧急时刻无法发挥“领头雁”作用,导致了实际防控工作开展不全面、政策执行力削弱等,如在疫情严重的黄冈市,当地卫健委主任对疫情“一问三不知”等问题的出现。涉事官员虽被及时处置、免职,但已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人民公仆形象。
(二)疫情中的身份“猜忌与反猜忌”对共同体意识的遮蔽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次突发性、传染性疾病的出现都是对人性和社会成熟度的考验,这其中,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且与个体的生命存续息息相关。疫情当前,正是需要人民群众守望相助的关键时刻,但在身份“猜忌与反猜忌”的博弈中,容易使个人与共同体的离散由隐性转变为显性,这不仅遮蔽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削弱了“共同体感”,也对民族凝聚力构成巨大挑战。
一方面,“邻避冲突”之下的身份“猜忌”对共同体意识的背离。“邻避冲突”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矛盾,表现为一种对自身、家人以及本地区人群健康、安全的风险忧患乃至恐惧而产生的“不要出现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诉求,以及进行情绪化抵抗的现象[8]。这种对风险认知偏颇的做法,也可视为古代“以邻为壑”思维方式的现代延续。毛泽东曾指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9]824。疫情发生后,一些地方为严防死守而采取“一刀切”等较为极端的回避方式;多地区出现了“恐鄂”现象,武汉地区民众在返乡后受到了当地人的歧视、身份“猜忌”,等等。这些“邻避”做法,间接地强化了不同地区民众对地域身份的认知偏颇,也加剧了由地域所产生的心理隔阂。质言之,“邻避冲突”本身作为一种离心力,在妨碍全国各地方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抗疫的同时,也与齐心协力、共克时艰的共同体理念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个人主观隐瞒之下的身份“反猜忌”对共同体意识的遮蔽。人们对于疫情风险的感知因个体经验、利益而发生改变。疫情暴发初期,防控的关键在于对国内疫情重灾区的人口流动监控,以阻断病毒的传播;而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境外确诊病例超过国内且处于不断上升态势,境外输入也成为防控的重点。这其中,少数人选择性地隐瞒个人活动行迹以规避地域身份“猜忌”带来的风险,如国内疫情重灾区群众为顺利返乡而选择隐瞒个人实际旅居行程,境外归国人员为顺利入境而选择故意隐瞒疫情重灾国旅行史、不如实申报健康状况,等等,这对国内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大局。
(三)疫情中的“舆论与对冲”对共同体意识的消解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综合”[10]11。帕斯卡尔认为,“实力,而非舆论,方能称雄世界。然而,舆论却能瓦解实力”[11]。在疫情期间,现实空间的隔离促使网络空间成为舆论信息的“集散场”。而网络空间中舆论的扩散、演化、耦合和转化均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这不仅影响着公众的理性认知与价值判断,也消解着共同体的认同与合力。
一方面,疫情中舆论信息传递出的负面情绪干扰了舆论生态。面对信息超载的网络环境,温伯格将网络视为“可以‘无边界’容纳知识的容器”,而网络化的知识却不再“确定、固定、令人信赖”[12]12。疫情发生以来,充斥网络的舆论以程度夸大、性质负面居多,“各式各样的知识在竞相争取我们的注意力,而每一个选择均有其代价”[13]43。这一“代价”便是无法还原疫情进展的全貌,更易以偏概全地形成对疫情的“整体”认知。这在产生认知偏见和焦虑感的同时,也为疫情防控注入了不稳定因素。同时,官方信息的发布尚难以跳脱“冲击-回应”模式,发布信息相对迟缓,很多舆论话题往往会沦为网络“罗生门”。随着民众关注点的反复更迭,结果就是一个热点迅速掩盖和淘汰另一个热点,在流量的随波逐流中难以得出明确的结果[14]。但这些信息却如“蝴蝶效应”般聚合、传播、蔓延、叠加并不断衍生,迅速将一些负面情绪传递给人民群众,在干扰了疫情期间舆论生态的同时,也会削弱民众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
另一方面,疫情中舆论信息内含非理性导向对社会共识的撕裂。在疫情防控期间,网络民粹主义借由新媒体平台与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潮合流,往往着眼于博噱头、赚卖点,以高调激烈的言辞刷存在感,不但弥散于自媒体和网络评论之中,更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现有体制形成了冲击[15]。在催动舆论信息以自发情绪、激进民意和非理性舆论姿态出场的同时,触发群众性焦虑,更易助推网络舆情外溢到现实空间,引发“涟漪效应”和“落地效应”。可见,疫情中舆论信息所呈现的非理性,势必会加快社会低组织化结构性弊端的暴露速度,进而造成对社会共识的撕裂。这不仅消解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增加了跌入“塔西佗陷阱”的风险。
(四)全球传播时代“疫情与污名化”对共同体意识的冲击
疫情之下,全球传播时代的“信息疫情”来势汹涌,习近平曾借用狄更斯的观点来表达对当今时代的看法,“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16]2。西方媒体在主流叙事中将疫情同中国相联系,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民抗“疫”的共同努力,也冲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话语影响力。
其一,“种族歧视”论。这种言论主要表现为大搞种族歧视,利用疫情“污名化”中国。例如,《华尔街日报》在刊登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中,毫不避讳地将中国人称为“亚洲病夫”;丹麦《日德兰邮报》刊发辱华漫画,将五星红旗上的“五星”恶意修改成冠状病毒的图样等。这种言论将新冠病毒与中国和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不仅是利用种族主义将疫情政治化,更是国际话语权中隐含意识形态霸权的体现。
其二,“双标”论。这种论述主要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譬如,《纽约时报》的“双标”封城报道:在仅隔两周的两个标题中,第一个批评了中国的封城策略对湖北省的影响,认为中国“封城”是“以牺牲人民生计和自由为代价”,而第二个涉及意大利采取的中国式封锁,则赞颂意大利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强调意大利“封城”是“冒着经济风险遏制病毒在欧洲肆虐”。可见,在“双标”论的背后,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看问题的表层驱动,更是服务于西方政治利益的媒体“专业化”的表现。
其三,“国家责任”论。这种叙事将新冠病毒的全球扩散解读为“中国的责任”。譬如,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要求中国政府对早期“不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错误行为”负责;特朗普在推特使用“中国病毒”一词等。沿着这一叙事主线,将责任进一步归向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这一触及深层意识形态与体制之争的归责论辩,已然超出疫情防控甚至一般性政府治理责任层面的政治论辩与斗争,折射出国际政治对立和冲突,这也冲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三、解蔽与建构:后疫情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
恩格斯认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17]665。一场大规模的疫情来袭,不仅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严峻的现实挑战,考验着民族凝聚力,也提升了民族战“疫”力。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在危机中寻找实践契机,将中华民族熔铸为坚不可摧的共同体,在后疫情时代获取更大的发展动力。
(一)以中国共产党对疫情防控的统一领导为政治基础
面对重大突发性疫情,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不仅是对党领导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严峻考验。
第一,以党的统一领导坚定中华民族战“疫”的必胜信心,为战“疫”提供全面的政治保障。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国“一盘棋”,迅速形成“中央、省、市、县、乡、村”六位一体的防控体系,专门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指导组等,推动各级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在此期间,党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规格之高、频次之多,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实属少见。而这一“政治势能”在展现党中央高度负责态度的同时,也是“党的领导在场”的政治位阶体现,赋予了疫情工作更高的政治意义,为中华民族共同战“疫”提供了政治保障。
第二,以党中央的科学决策指明中华民族战“疫”的前进方向,为战“疫”启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面对疫情,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层层联防、级级联控,并通过加强相关部门的统筹协调,对重要物资实行国家统一调度,多措并举保障重点地区医用物资和生活物资供应。如,各省市迅速形成了对口支援湖北疫情的工作机制,实行19省“一省包一市”政策,医护人员、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湖北前线;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到方舱医院改造,快速实现从“人等床”到“床等人”的转变。
(二)以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疫情防控为主体力量
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8]511,这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所具有的磅礴力量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在疫情防控的道路上,与“静”下来的城市相对应的,是“动”起来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不仅汇聚成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也为打赢这场战“疫”提供了力量。
第一,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形成疫情防控的民族“战疫力”。重大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其紧急性、不可预测性难免会出现应急物资短缺、救援人员不足的现象。在政府统一调配的基础上,来自人民群众的物资支援及志愿服务对疫情防控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如捐菜、送菜的河南籍老兵,捐赠蔬果的云南红河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火神山医院建设的贵州雷山县苗族群众张玉星、文静夫妇等,还有“快递、环卫、抗疫物资运输人员不辞劳苦,亿万普通劳动者默默奉献”[19]。可见,人民群众成为疫情防控中的坚实力量,生动诠释了恩格斯的观点:无数个体意志所构成的交叉的力量形成了“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20]462,最终汇聚成了总的合力。这在展现了普通人民担当与大爱的同时,有利于各族人民携手共同抗击疫情,也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第二,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打通疫情防控的“最后一公里”。疫情发生后,人民群众是被保护的群体,也是抗“疫”的主要力量。同时,疫情防控需要在党的组织带领下,快速、有效地构建起区县、街镇、城乡社区等基层防护网络,实现防控范围的全覆盖。而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否,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配合是密切相关的。例如,从武汉的暂时“封闭”到各地对往来人员的摸排,再到戴口罩、勤洗手等疫情防控要求的落实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响应。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是真正的英雄”[21]5。人民群众在这场疫情面前坚持以“小我”服从“大我”、维护“大我”,尽己之力以多样化的方式支持、协助疫情防控工作。正是这种每个成员都对共同体拥有的责任担当护卫了中华民族,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好诠释。
(三)以加强舆论引导为疫情防控的信任支持
“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22]332正确的舆论引导是有效应对重大疫情的必要保障。因此,在疫情中不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不仅有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推进,也有助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信任支持。
第一,统筹权威主流媒体,建立适应全媒体生态的传播格局。卡尔·霍夫兰认为,在信息传播力的影响因素中信源的可信度与权威性是关键所在[23]。因而,要将疫情舆情社情融入全媒体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审视,强化正面宣传;加强主流媒体管控下的网络内容生产和传播,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打造风清正气的网络舆论场。例如,《人民日报》、腾讯、新浪等开设网络实时疫情辟谣专栏,大大缩短了“谣言采集—谣言调查—专业辟谣”过程,以疫情地图动态破解疫情谣言,消解信息壁垒,畅通权威信息发布渠道与平台,以“显政、善治、为民”的姿态汇聚人民防疫合力。
第二,把握舆论引导时效度,阻断公共信任风险的传递链。疫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场舆论战争;疫情防控既是一场全民“战疫”,也是一场全媒“战疫”。疫情之中,舆情引导的关键就在于把民众引导至全局利益上来,齐心协力度过危机。而对舆论风险的及时洞察、准确把握,则是制定应对之策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用好媒介话语权,建立政府与媒体联动的风险预判防控机制,及早发现和识别疫情中舆论风险的苗头,及时预警防范,以充分、扎实的调查数据、事实依据,将舆情关切、公众质疑、深层追问等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争做“第一定义者”,展现负责任形象、为民服务形象。同时,在后疫情时代,要考虑舆论等非疫情风险对国际国内关系的影响,进而做好应对的预案,在讲好中国防“疫”故事的同时,传递客观、正面的中国声音。
(四)以全球抗“疫”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动力赓续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生命健康构成直接威胁的同时,也证明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的荣辱与共。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彰显。
第一,以中华民族抗“疫”之力为“全人类奋战”提供支持与借鉴。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深刻地说明全人类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如何应对关系着全人类共同的命运。疫情发生后,从2020年1月23日开始,武汉封城,仅仅两天后,湖北省封省,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隔离措施,迅速、果断和全力构筑防控线,遏制本国疫情的扩散蔓延,用“中国速度”为全球防疫争取了宝贵时间。对此,谭德塞感叹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24]同时,本着公开、透明、及时、负责的态度,“从2020年1月3日,中国开始定期向世卫组织、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25],将国内疫情防控成果、疫情数据与国际社会共享,以信息正能量传递消除国际恐慌,不仅诠释了“历史应该由事实和真相来书写,而不应被谎言误导污染”[26],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部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整体”的抗“疫”贡献,在彰显中国抗“疫”精神的同时,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支持。
第二,以全球抗“疫”援助之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疫情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其外、独善其身,只有全人类共同携手、团结协作,才能战而胜之[27]。同时,“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28]。因此,在国内疫情总体上已得到控制的基础上,中国克服困难、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工作:“从3月15日至9月6日,总计出口口罩1 515亿只、防护服14亿件、护目镜2.3亿个、呼吸机20.9万台、检测试剂盒4.7亿人份、红外测温仪8 014万件,有力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29]可见,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向世界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共享发展的成果,也意味着共同分担风险、共渡难关,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国际场域的实践体现,而中国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基石。
中华民族在历经坎坷、艰苦奋斗的道路上深知和平与发展来之不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在保障我国各民族稳定发展的同时,为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疫情之下,中华民族以守望相助的人道温情展现出患难与共的团结精神,以坚决果断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向世界展现了危难之中的大国担当。在后疫情时代,我们终将注目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自信地走出富有特色的“既中国又现代化”之路,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