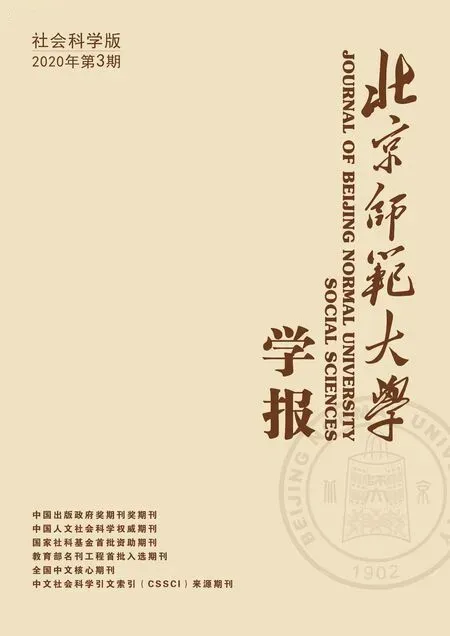谁最早关注、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
2020-12-12张海明
张海明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4)
杨焄教授近作《唐写本〈文心雕龙〉的披露、传播和疑云》(1)杨焄:《唐写本〈文心雕龙〉的披露、传播和疑云》,发表于2018年3月23日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38000。对有关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情况作了较为充分的介绍,读后颇受教益,唯所说“披露”一节,似还多疏漏,甚且讹误,故就闻见所及略作补正,并就教于各位研究《文心雕龙》的同行。
一
杨文认为:“率先对此残卷进行研究的是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他根据另一位汉学家内藤湖南提供的残卷照片,着手撰写《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此说其实由来已久,就笔者所见,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当属王元化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王元化先生选编了《日本〈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一书并为之作序,其中介绍日本有关《文心雕龙》版本研究和校勘时写道:“铃木虎雄是最早校勘唐写本《文心雕龙》的学者,其文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五月。越一月,我国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勘记》(2)赵文本名“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并没有“勘”字。发表于《清华学报》三卷一期。”(3)王元化选编:《日本〈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3页。王先生此语前曾引述釜谷武志之言“当以京都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为嚆矢”(4)釜谷武志彼时为日本京都大学助教,应王元化之请而特意撰写《日本研究文心雕龙简史》,后因与户田晓浩的《文心雕龙小史》重合而割舍,但王序中引用了釜谷氏的某些观点。此处所引,因过于简略而无法确认所说“嚆矢”具体所指,可能是就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勘而言,也可能是就日本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而言(如户田晓浩《小史》只说日本近代最早的研究当推铃木虎雄博士于大正十五年发表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但其所以做出如此判断,主要还是根据铃木虎雄和赵万里二人文章发表时间,铃木在前,赵氏在后(5)笔者检视原书,收入铃木氏文章的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由日本弘文堂大正十五年(1926)5月20日印刷,25日发行;1926年《清华学报》为半年刊,三卷一期刊出时间为该年6月初,准确些说,相差不到半月。,自然以铃木氏为最早。值得一提的是,户田晓浩的《文心雕龙小史》(1976)谈及此问题时说:“日本近代最早的研究当推铃木虎雄博士于大正十五年(1926年)发表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嗣后,铃木博士又于昭和三年(1928年)发表了《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刊记》,两文均对《文心雕龙》的原文校定作出了很大贡献。”(6)王元化选编:《日本〈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25页。户田氏称铃木《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发表于昭和三年不确,昭和三年是其作年,发表则在次年。这里并没有认定铃木氏最早校勘唐写本《文心雕龙》。户田氏此前曾转引过赵万里的文章(7)户田氏曾作《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1968),讨论敦煌本用于校勘《文心雕龙》的资料价值,其中就引述了赵万里有关敦煌本《文心雕龙》抄写年代的意见,并注明赵文原载《清华学报》1926年第三卷第一期,转引自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参见《日本〈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第114、130页。,也许正因为知道赵文发表于1926年三卷一期《清华学报》,却又无法确认该期学报准确的刊行时间,所以其对铃木氏的评价限定在日本学界。
《日本〈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一书出版后,王元化先生的观点遂为学界所接受并形成共识。1995年,杨明照先生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出版,其中由日本学者爱甲宏志执笔介绍“铃木虎雄”的词条写道: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深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室,常人不易见到。后被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抄录带回日本。……铃木虎雄以此校勘《黄叔琳辑注本》,据《敦煌本文心雕龙》作校勘实以铃木虎雄为嚆矢,其后一月则有赵万里之《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发表,更后又有潘重规参照铃木虎雄、赵万里诸家之校勘,著《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对比之下,铃木虎雄之《校勘记》较后出者,不免稍微简略。”(8)杨明照主编:《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320页。不难看出,爱甲宏志所述实参考王元化序言相关文字,同样是由文章刊发时间先后判定其意义。
张少康等人撰写的《文心雕龙研究史》为“近现代日本的《文心雕龙》研究”专设一节,相关介绍也较先前之作详备。兹节录于下:
《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系根据内藤湖南从英国带回来的敦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影片与黄叔琳本《文心雕龙》对比校勘,共校出与黄本不同者计512条,与同年六月赵万里在《清华学报》第二(原文如此,笔者)卷第1期上发表之《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相比,各有其价值。赵校系以唐写本与嘉靖本对校,不同者共计474条。赵记系据其友人容君之校本临写,又据原影本重勘,……显然,铃木虎雄在做校记时当未见到赵校,但其与黄本对校之细,实为后人作进一步之校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对唐写本中的讹误,也据黄本一一指出。应该说铃木虎雄是第一个按唐写本残卷来对通行本《文心雕龙》作校勘的,也基本上把唐写本的优点揭示出来了,引起人们对唐写本的充分重视,应该说是居功至伟,作出了很大贡献的。(9)张少康、汪春泓、陈允锋、陶礼天:《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87页。
作者应该读过赵氏校记,故其叙述颇为具体,只是有些细节略嫌含混。此段文字值得注意者有二:一是其称“铃木虎雄在做校记时当未见到赵校”,此语实隐含了赵校早于铃木氏之作的意味,若如作者后文所言,铃木氏第一个对唐写本残卷进行校勘,则当作“赵万里在做校记时当未见到铃木文”才是。作者如此表述,是否对二人之作孰先孰后难作决断呢?二是认为铃木氏《校勘记》引发研究者对唐写本的关注,居功至伟,不仅有溢美之嫌,而且缺乏必要的证据(详后)。
以上三书在“龙学”界流传甚广,加之编(作)者又都是研究《文心雕龙》的权威,故其观点颇为后来相关文章称引,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对之表示怀疑者。前述杨焄文章虽然肯定“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中国学者赵万里也发表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但还是承认铃木之作在前。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二
张少康《文心雕龙研究史》和杨焄文章都提到一个细节,即赵氏校记所据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得自友人“容君校本”,但都没有对之深究。这其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若能沿波讨源,还原事件真相,当会改变学界先前对此问题的认识。
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正文前有一题记,文字不长,抄录于此:
敦煌所出唐人草书《文心雕龙》残卷,今藏英京博物馆之东方图书室。起《征圣篇》,讫《杂文篇》,《原道篇》存赞曰末十三字,《谐隐篇》仅见篇题,余均亡佚。每页二十行至二十二行不等。卷中渊字,世字,民字,均阙笔,笔势遒劲,盖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西陲所出古卷轴,未能或之先也。据以迻校嘉靖本,其胜处殆不可胜数,又与《太平御览》所引,及黄注本所改辙合,而黄本妄订臆改之处,亦得据以取正,彦和一书传诵于人世者殆遍,然未有如此卷之完善者也。去年冬余既假友人容君校本临写一过,以其有遗漏也,复假原影片重勘之,其见于《御览》者亦附着焉。即以三夕之力,汇录成校记一卷,序而刊之,以质并世之读彦和书者。丙寅花朝日记。(10)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清华学报》,1926年三卷一期。
题记对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和评价,并交代了自己写作校记的过程。但其叙述实在过于简略,所说友人容君究竟为谁?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文心雕龙》残卷又是如何获得?这些问题均付阙如,以至后人只得止步于此。所幸近年来一些新材料的披露,使我们得以对此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2007年雅昌秋季艺术拍卖会上展出了题为“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四种”的拍卖品,乃赵万里“1925年到京拜王国维为师后所辑录传抄的四篇短文”。其中第一种即为赵万里手写本《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此外还有赵氏抄录日本学者度会常珍《仿宋椠本素问校讹》十二页,张文虎《舒艺室续笔》四页,吴梅《奢摩他室曲丛目》十五页三种,拍品最后以十万四千五百元成交,不知落入谁手)。据拍卖方说明:“《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二十七页,原校为东莞容庚所撰,系依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卷子本校明嘉靖刻本,赵万里据以传录一过。此校记未见出版,故虽为重录亦自可珍。”网上展出拍品正好有《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首页,其题记清晰可辨:
英京博物馆藏敦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存《征圣》篇至《杂文》篇,《原道》篇仅见末十三字,《谐隐》篇只存篇题。原本字迹草率,不易审观。乙丑仲秋,假东莞容君希白校本重录一过。万里记。(原文据嘉靖本)(11)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49520293/
如此问题便有了答案:1.赵氏校记所说“友人容君”即容庚,容庚(1894—1983)字希白,广东东莞人,1922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192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翌年转入燕京大学,著名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浙江海宁人,1925年自东南大学毕业后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并任其助教,其与容庚相识及获容氏唐写本《文心雕龙》校本即在此时。2.综合赵氏两篇题记之言,可以肯定,以明嘉靖本为底本校勘唐写本《文心雕龙》者并非赵万里,而是容庚;赵氏之作,先据原照片对容校所引唐写本文字重勘一过,再参照黄叔琳辑注本及《太平御览》所引予以补充,在此基础上作出对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整体评价(12)容氏校记全文虽未得见,但其首页数条已能说明问题。容校先引嘉靖本原文,然后列出唐写本异文,赵校则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如《征圣篇》“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条,容校:“文字无”;赵校:“唐写本无文字。案今本有文字,盖涉上下文而衍,当据删。”又如“以多方举礼”条,容校:“方作文”;赵校:“案黄注本依孙校,改方作文,与唐本正合。”容校、赵校之异同,于此可见一斑。。3.赵氏发表于《清华学报》的校记完成于“丙寅花朝日”亦即1926年3月28日,而容氏校本的完成时间至少在1925年10月之前。
但这还不是最终答案。
赵氏校记于1926年三卷一期《清华学报》刊出后,《清华周刊》第25卷第16期“新闻·杂闻”栏登载了一则未署名的短文,似未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亦抄录于下:
赵万里先生所作唐写本之《文心雕龙》校记,登《清华学报》三卷一号中,其唐写本乃从友人容希白先生处假观移录者也。顷容君此书,乃从其友人黄仲良君假来者,实非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物也。缘黄君此书乃讬友人于伦敦博物馆几经交涉,始得摄影。而黄君于此书用力甚劬,曾校宋本、元本、明本及何义门、顾千里、谭复堂诸人手校本,与类书所引合校全书,业已脱稿,付印有日,并拟将唐本另用珂罗版影印流传。而赵先生因事前未悉此书原委,遽将唐本异同写为校记刊出,良用歉然。想黄君全书出后,于学术界当更有绝大之贡献也。(13)此条文字既无标题,亦无作者,刊于《清华周刊》第25卷第16期第13页“新闻·杂闻”栏,1926年6月11日印行。原文只有逗号,笔者重新标点。
对于考察敦煌唐写本《文心雕龙》在中国的披露和传播来说,这条不知出于谁手的短文无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它不只证实了赵万里校记所说“容君”即容庚,而且交待了容庚校本所据的来源;同时我们也才知道,在容庚之前,已经有人看到从大英博物馆拍摄的唐写本《文心雕龙》照片并据以校勘通行本《文心雕龙》。
这个人就是有“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之称的黄文弼。黄文弼(1893-1966),字仲良,号耀堂,湖北汉川人。1918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1927年作为中方团员加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四次出入新疆,在西北史地和考古研究方面成就卓著。长期以来,提到唐写本《文心雕龙》的校勘,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铃木虎雄、赵万里,而黄文弼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事实上,早在1921年,黄文弼就发表了《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认为古人整理《文心雕龙》方法“多有未备”,提出从校勘、文人小传、文人年表、文章表、辑文、补注、标点符号共七个方面对《文心雕龙》作系统整理。其于校勘一节道:“今将整书重为审校,阙者补之,误者正之,亦整理文心雕龙之首务也。”而具体方法,则是以《太平御览》和《图书集成》为主,旁考各家刻本。显然,黄文弼对《文心雕龙》关注有日,其拟定的整理方法也颇具现代学术意识。黄文弼同时在文中预告:“今与吾友郑君介石(14)即郑奠(1896-1968),字介石,后改为石君,浙江诸暨人,著名语言学家。1915年入北大中文系,师从黄侃、钱玄同,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任教,主要从事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研究。,共谋同整是书,拟定方法,分任进行,期以一年,完全成功。”(15)黄文弼:《整理〈文心雕龙〉方法略说》,1921年11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899期,第2、3版。
当然,在这篇文章中黄文弼并没有提到唐写本《文心雕龙》。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包括日本,还很少有人知道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有一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直到1923年,罗振玉之子罗福苌在《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发表《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其中列有“文心雕龙残:存第二章至第十四章”(16)罗福苌:《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国学季刊》,第1卷第1期,第167页。罗福苌(1895-1921)字君楚,罗振玉次子。早慧,通西夏文、梵文、法文、德文,以西夏学研究见称,惜乎早逝。此文刊发时正文前有罗振玉所作短序,略述罗福苌生平所学,其中提到:“英京书录,乃得之法儒沙畹博士写寄,及临时陈列之目录,见之杂志中者,会最成之。”所说沙畹博士,即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也是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斯坦因考察所得大多经过沙畹整理,故对其情况颇为了解。沙畹曾于1889年、1907年两度来华,在中国生活时间长达5年,1913年因考释斯坦因发现之汉晋木简始与罗振玉有书信往来。,国人这才知道,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件《文心雕龙》的残本。但彼时学界的兴趣更在于敦煌文献中的佛经、变文及俗文学一类,罗文披露的这条信息,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
《国学季刊》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编辑出版,1923年1卷1期是其创刊号,作为国学门编辑所成员的黄文弼应该不会错过罗福苌这篇书目,而他此前开始的对《文心雕龙》的整理工作,无疑使他较常人更为关注任何有关《文心雕龙》版本的信息。所以,当得知大英博物馆藏有《文心雕龙》残卷时,黄文弼便托在英国留学的友人设法翻拍,寄回国内。黄文弼1952年所写《谨述关于〈文心雕龙〉事件的经过》提到此事:“1925年前后,我正校勘《文心雕龙》,听说伦敦博物馆有唐写本《文心雕龙》真迹,系斯坦因在敦煌所劫取的,我就托在伦敦留学的黄建中将该写本晒印影片一份寄我,共有23页,自《征圣》到《杂文》共13篇,黑底白字,黄(建中)并在首页题词,叙述摄晒经过。”(17)见王世民《所谓黄文弼先生藏唐写本〈文心雕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文附录,原载《文物天地》1990年第5期,后收入朱玉麒、王新春编:《黄文弼研究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黄建中(1889-1959),字尧卿,号离明,湖北随县人。1914-191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早于黄文弼一届),毕业后入北京大学哲学门研究所,1921-1925年赴英国剑桥、爱丁堡大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湖北省教育厅长等职,著有《比较伦理学》(1944)。1959年病逝于台湾。其题于照片首页文字如下:
敦煌《文心雕龙》残卷,藏伦敦博物馆之东方图书室。完者自《征圣》至《杂文》,为篇十有三。《原道》篇存赞文,才十三字。《谐隐》篇仅存其目。予尝于馆中据余、黄两家刻本校其异文,善者圈之,疑者乙之,既已裒然成帙矣。今年春,复为友人黄仲良命人影其书,凡二十有二叶,负一而正二,予得其一。唯首叶前十一行,宜在末页,势难易厥位。其字迹模糊者则令重影一纸而附益之。爰识数语于此,邮致仲良,俾便参稽焉。(18)引文据王世民《所谓黄文弼先生藏唐写本〈文心雕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朱玉麒、王新春编:《黄文弼研究论集》,第196页。
虽然没有说明,但黄建中之关注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应该还是因为黄文弼致函所托。从其行文来看,黄建中借阅原件并据以校勘,时间应在1924年岁末,故先云“予尝于”,复云“今年春”。如此,则黄文弼致函亦当在1924年(《谨述》称“1925年前后”,乃凭记忆言其大概),黄建中则于次年春将照片寄回(19)王世民文称“黄建中于当年2月5日将晒印本邮寄黄文弼”,或黄所寄照片题记本有日期,即1925年2月5日。,其后才有黄文弼、容庚、赵万里等人的校勘之作。应该说,容庚、赵万里作校记时,都曾看到黄建中题于照片上的文字并有所吸纳,如赵万里《校记》称“唐人草书《文心雕龙》残卷,今藏英京博物馆之东方图书室”,显然就是得自黄建中题记。
不过,黄建中也不是最早校勘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还有人比他更早。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所附序跋中有近人傅增湘跋一则,原文如下:
诵芬室主人(董康)自英京影印唐人写本《文心雕龙》一卷,自《征圣》至《杂文》,凡十三篇。取此本(天启梅本)校勘,增改殆数百字,均视杨、朱、梅诸人所校为胜。惜《隐秀》篇不存,无以发前人之覆耳。癸亥立夏后三日,藏园居士傅增湘记。(20)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57页。
与前述黄文弼等人情况不同,傅增湘所见唐写本《文心雕龙》得自另一渠道,即董康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拍摄之照片。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著名法学家、藏书家,与傅增湘、缪荃孙及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等人私交甚笃。董康曾于1922年8月-1923年2月间赴欧美考察工商业,顺带去巴黎、伦敦博物馆借阅了数百种敦煌文献,拍摄了六十余种(21)此说首见于内藤湖南《欧洲所见东方学材料》所述,参阅王冀青:《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第30节《内藤虎次郎对斯坦因搜集品的调查与介绍》,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306页。此外史睿、王楠《董康〈敦煌书录〉的初步研究》一文关于董康旅欧考察及拍摄敦煌文献事考辨较详,亦资参考,见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1-604页。,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当为其中之一。大概董康回国后即将此照片借与傅增湘,而傅氏遂与明梅庆生天启二年刻本对校,其校勘文字及跋语也写于该书。癸亥为1923年,该年立夏在5月6日,后三日即5月9日。此书为傅增湘私人藏书,故其跋语鲜为人知,后来捐赠北京图书馆乃得公诸于世(22)傅增湘于1947年将其藏书373部、4300余册捐赠给北平图书馆;1949年去世后,家人又先后捐献给北京图书馆480部、3500余册傅氏遗书。故后人知晓傅氏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杨明照《拾遗》、王利器《校证》均提到傅增湘校唐写本《文心雕龙》事,尽管两书都没有引用傅校,但从唐写本《文心雕龙》校勘史的角度来看,傅增湘所校却因其时间最早,且渠道特殊而值得重视。
至此,有关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在中国披露、传播之史实已基本清楚。
三
回到本文标题所提问题,可以肯定,最早关注、对校唐写本《文心雕龙》的不是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而是中国的傅增湘、黄健中、黄文弼、容庚,甚至赵万里等人。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比铃木虎雄更早知道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存在,更早获得这个珍贵的文本,而且都对之作过校勘。
综合上节所述,可对中国学人利用唐写本《文心雕龙》进行校勘的时间略作排比:1.1923年5月,傅增湘据董康所摄照片与明天启梅本进行对校;2.1924年岁末,黄建中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就原件参照通行本作了简单的校异;3.1925年上半年,黄文弼收到黄建中寄来照片后,开始着手参照多种版本整理校勘《文心雕龙》(23)前引《清华周刊》第25卷第16期短文谓黄文弼校勘《文心雕龙》“业已脱稿,付印有日”,殆非虚语。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所存黄文弼手批《文心雕龙》黄叔琳辑注本卷末注文表明,1926年(丙寅)4月,黄文弼已完成对《文心雕龙》的校勘。;4.稍后容庚从黄文弼处得睹照片(24)黄文弼之所以会将唐写本《文心雕龙》照片交与容庚,或与容庚长于古文字之学相关。残卷字体介于行、草之间,又多简笔,不易辨识,因此黄文弼求助于容庚,而容庚遂有校本之作。赵万里抄录容庚校本题记有云:“原本字迹草率,不易审观”。其时赵氏尚未得见照片,故此语或本容氏描述。,并于1925年10月之前完成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5.容庚将己作校记及黄氏照片转借赵万里,赵氏于1926年初完成《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继而刊发于1926年6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三卷一期。
我们再看日本方面的情况。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并未提及获得唐写本《文心雕龙》的时间,也没有交代该校勘记的完成时间,不过在后来《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之校勘所用书目部分,铃木氏提到敦煌本《文心雕龙》时有一个说明:
燉煌莫高窟出土本。盖系唐末钞本,自原道篇赞尾十三字起,至谐隐第十五篇名止。文学博士内藤虎次郎君自巴里将来。余与黄叔琳本对比,大正十五年五月,既有校勘记之作。今之所引,止其若干条耳。余所称燉本者,即此书也。(25)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收入《支那学研究》,第1编,东京:斯文会,1929年版,第161-162页。另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如果此处所说“大正十五年(1926)五月”是其完稿时间,那么其晚于赵万里校记当无可疑,不易确定的是铃木何时看到内藤湖南带回的唐写本《文心雕龙》。据高田时雄《内藤湖南的敦煌学》(26)高田时雄文章中译本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366页,后收入同氏《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一文介绍,内藤一行于1924年7月6日出发,8月中抵达巴黎,8月25日到伦敦,9月末返回巴黎,12月中去往罗马,12月底自马赛搭乘日本邮轮回国,1925年2月3日抵达神户。内藤曾于10月5日自巴黎致信董康,介绍自己伦敦之行:
法国伯希和、英国适尔士二君,弟皆已见之。见托各书,皆递交讫。勾留伦敦五礼拜,英博物馆所藏石室遗书,除内典未染指外,已睹一百四十余种。……弟嘱适尔士影照四十余种,但有未允照者廿十余种。治要、法令、建初户籍与阁下所录摩尼赞文,并在未允之列,洵不知其何故,为之郁闷累日。(27)高田氏文章引述此信,但不全。本文所引据董康:《董康东游日记》(《书舶庸谭》九卷本),王君南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据此,内藤在大英博物馆看了一百多种佛经以外的敦煌文献,并对其中约二十种拍摄了照片,但未说明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是否包含在内。对于内藤在大英博物馆的收获,铃木虎雄显然并不了解,故其两篇校勘记都以为敦煌本《文心雕龙》乃内藤“自巴里(黎)将来”。在巴黎期间(12月3日),内藤曾致信铃木虎雄,其中写道:“滞留欧洲的时日已经迫近,阅读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仅为三百余种,照片以及旋印照片(rotograph)的数量当为五十余种,其他手写品数十种。其中文学上的新品有之,研究必参考之材料亦有之。因之所需费用陡增,不得已而放弃亚米利加之行程。”(28)内藤致铃木虎雄信原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引文据高田时雄《内藤湖南的敦煌学》。如果后来铃木所得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于其来历没有说明,那内藤此信是否会是导致铃木误判的原因呢?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铃木得自内藤的究竟是照片,还是内藤本人迻录的抄本?铃木校勘记对此亦无说明。前述爱甲宏志介绍铃木虎雄词条称敦煌本《文心雕龙》“后被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抄录带回日本”,未知何据。以内藤本人的汉学修为,辨识文字予以抄录并非难事,何况内藤当时颇窘于经费不足而未能多摄照片,以至于他后来放弃了美国之行。事实上,内藤在英、法两国博物馆都抄录了不少敦煌文献,虽然未见其抄录唐写本《文心雕龙》的记载,但此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不过,铃木校勘记前言既称敦煌本字体为“草书”,且据以断定其出自唐人之手,则其所见必为照片无疑。此外,曾亲阅大英博物馆藏原件的潘重规指出,原件中“偶有误衍误倒自加改正之处,校者不察,则往往致误。如铨赋篇:‘彦伯梗概’,唐本虽作概梗,然已施加乙号,校者以为误,而实不误。祝盟篇:‘故知信不由衷’,唐本亦已乙正,而校者又以为误倒”(29)潘重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版,第3页。。早期所摄照片清晰度欠佳,故据照片对校者皆未能觉察。笔者比对铃木、赵氏两家所校,其误如出一辙,是知铃木校勘所据当与赵氏相同。如果铃木所据果由内藤抄自原件,应该不会出现此种情况。
既然内藤曾自巴黎致信铃木,告知此行拍摄、抄录敦煌文献中不乏“文学上的新品”和“研究必参考之材料”,则从理论上说,内藤归国后,铃木当于第一时间获得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然而据铃木《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绪言》所述,大正乙丑(1925)春他与斯波六郎、吉川幸次郎一起研读校勘《文心雕龙》时,所用版本中并没有敦煌本(30)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绪言》写道:“大正乙丑春,斯波、吉川二子,在大学课以《文心雕龙》,因校诸本,相共读之。二子用功甚力,起余之言不尟。课读所用,以黄叔琳辑注附载纪昀评本,及养素堂板黄氏原本为本,旁及诸书。憾插架单薄,宋元旧刻,概无由窥,虽则明刻,或未及採蓃。”《支那学研究》,第1编,第159页。。这意味着至少在1925年夏季之前,铃木犹未获睹内藤带回的照片。其中原因,或许是内藤需要时间将带回的照片、抄本整理归档,又或许是铃木尚未知晓内藤带回物品中有《文心雕龙》残卷。总之,不论是由于哪种原因,铃木自内藤处获得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时间应该不会太早(31)内藤归国当年曾以“敦煌古书的研究”为题在京都帝国大学做过演讲,次年又写有《欧洲所见东方学材料》一文,发表于《新生》第1卷第1号(1926年5月发行),但似乎都没有提到唐写本《文心雕龙》。要回答铃木何时看到唐写本《文心雕龙》这个问题,恐怕还有待于新的材料。。
以上所述表明,虽然中日学人都是从大英博物馆获得唐写本《文心雕龙》照片,但毕竟分属两个渠道,彼此的研究平行独立,相互之间并不知晓。事实上,直到1928年铃木写作《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时,他并不知道《文镜秘府论》已被杨守敬抄录回国,也不知道中国学者已经利用唐写本《文心雕龙》进行校勘,故云“若夫《文镜秘府论》、燉煌本者,西土学子,固不经见”(32)铃木虎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收入《支那学研究》,第1编,第160页。铃木此处所说“西土学子”指中国学人,以其在日本之西也。。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1929年9月初版时,不但未附铃木同年4月刊出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也不曾提及同氏三年前问世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33)范氏《文心雕龙注》1936年由开明书店重版时始编入铃木《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
除时间上有先后之别外,中日学人对唐写本《文心雕龙》的认识、校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首先,从对唐写本《文心雕龙》的描述来看,赵校题记较铃木更为准确、细致。铃木校记前言只说唐写本《文心雕龙》乃内藤从巴黎带回,其内容起自《原道》篇赞尾,止于《谐隐》篇名,从书体判断恐出自唐代(34)见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前言》,《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京都:弘文堂,1926年版,第979页。;赵氏则明确交代唐写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东方图书室,除内容介绍与铃木相同外,还提到版式(“每页二十行至二十二行不等”),其对抄写时间的考证、判断也较铃木为优。至于对该书价值的认识,则所见略同:铃木称该书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其为《文心雕龙》现存之最早版本,更因为它是一个已知刻本之外的独立系统,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而赵氏亦说,将其与嘉靖本、黄注本及《太平御览》所引对勘,颇能订讹正误,“彦和一书传诵于人世者殆遍,然未有如此卷之完善者也”。
其次,从二人所作校勘来看,赵氏之作较铃木之作更为丰富、完备。为简省计,此处仅以《征圣》篇为例进行比较,以见差异。铃木之作,大多只列异文,少有断语,基本上属于校异一类;赵氏之作则在列出异文的同时,提出己见,并作必要的说明,校异之外,兼顾订讹。如“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条,铃木:“无文字”;赵校:“唐写本无文字。案今本有文字,盖涉上下文而衍,当据删。”又如“变通会适”条,铃木:“会适作适会”。赵校:“会适作适会。案上云抑引随时,与此句相对成文,则以作适会为是,当据唐本乙。”再如“子政论文”条,铃木:“无子政稚圭四字,劝学作窥圣。”赵校:“作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案唐本是也。黄本依杨校,政上补子字,必宗于经句下,补稚圭劝学四字,臆说非是。”(35)引文分别据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第998页;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清华学报》,1926年三卷一期。以上三条,可见二人校勘差异之大概,无怪后来户田晓浩评铃木之作,谓“惜乎详于‘校’而疏于‘勘’”(36)户田晓浩:《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见《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第115页。。
再次,从二人出校条数来看,《征圣》篇赵氏共出校24条,铃木34条,数量上铃木为多。而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二人所据底本不同,铃木所据为黄叔琳辑注本,赵校为嘉靖本,底本原文差异导致出校条数不同。如“以文辞为功”条,铃木出校而赵氏阙如,原因即为黄注本改“立”为“文”,而嘉靖本原文即作“立”。二是某些差异在赵氏看来无须出校,而铃木凡属异文便予以列出,如“無作无”、“睿作叡”、“百作白”之类,铃木出校而赵氏略过。三是由于赵氏粗心未能看出(当然也可能容庚校本即有此误),如“精理为文”句,唐写本作“精精为文”,铃木校曰:“理误作精”,而赵氏失校。虽不能据此以论高下,但至少可以看出铃木校勘态度的认真。此外,铃木之作于异文皆以符号○在旁标示,讹字则以△标示,较赵氏之作清晰醒目,亦可视为其细心之表现。
大概铃木氏之作《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其初衷或如容庚之作校本,目的乃在校异存真,以期为后来全面校勘《文心雕龙》提供一个可资参照的重要版本,所以其校勘便相对简略。在某种意义上说,铃木之作与赵氏校记的差异,恰如容庚校本之于赵氏校记。也正因为如此,后人校勘《文心雕龙》,以为参照的并非铃木所作《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而是其《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即便是校勘唐写本《文心雕龙》的专门之作,如潘重规之《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1970),林其锬、陈凤金之《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1991),也都没有提到铃木氏这部著述。由此说来,铃木虎雄之《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其对日本近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开启意义远大于实际影响,谓之“引起人们对唐写本的充分重视”,“居功至伟”,过矣。
四
平心而论,真正引起人们对唐写本充分重视的,与其说是铃木虎雄之作,不如说是赵万里的校记。
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记》于1926年《清华学报》刊出后,很快就引起学界的注意。1929年,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上、中册由北平文化学社初版时就吸纳了赵氏校记的不少意见。1930年,黄侃因范注而关注唐写本《文心雕龙》,其4月22日日记道:
(胡)小石以所过录赵万里校唐写残本《文心雕龙》起《征圣》,讫《杂文》见示。因誊之纪评黄注本上,至《明诗篇》。……《辨骚篇》:“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向于“菀其鸿裁”句不甚了了。今见唐写本乃是“苑”字,始悟苑、猎对言。言才高之人能全取《楚辞》以为模范,心巧之人亦能于篇中择其艳辞以助文采也。书贵古本,信然。(37)黄侃:《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610页。
胡小石所过录带给黄侃者,应该不是赵万里据照片抄录的《文心雕龙》残本,而是其发表于《清华学报》文章的校记部分,故黄侃将其按篇誊于黄注本上(若是前者,黄侃应该交给黄焯过录全文)。这意味着赵氏校记已在学界产生一定反响,而黄侃之言“书贵古本,信然”,无疑表明他对唐写本价值的充分肯定。又黄侃4月24日日记复云:“属石禅(即潘重规,笔者)寄银(十四圆一角)买内藤还历《支那学论丛》,以其中有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也。”(38)黄侃:《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09、610页。显然,黄侃之所以关注铃木之作,起因实在赵氏校记。胡小石通日语,对日本学界较为熟悉,其先得知铃木氏发表于《支那学论丛》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告知黄侃,并非没有可能。
赵万里之后,利用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以校通行本者,还有孙人和、叶长青、杨明照、王利器等人。
孙人和(1894—1966),字蜀丞,号鹤臞,江苏盐城人,以古籍整理、词学研究见知于世。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例言首条道:“《文心雕龙》以黄叔琳校本为最善,今即依据黄本,再参以孙仲容先生手录顾千里、黄尧圃合校本,谭复堂先生校本,及近人赵君万里校唐人残写本,畏友孙君蜀丞亦助我宏多(孙君所校有唐人残写本、明抄本《太平御览》,及《太平御览》三种),书此识感。”(39)引文据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版《文心雕龙注》,上册,第3页。1936年开明版文字略有不同,主要是增加了铃木虎雄校勘记,另“近人赵君”改为“友人赵君”,“亦助我宏多”改为“尤助我宏多”。与容庚、赵万里侧重对校不同,孙氏之作更近于铃木氏对黄叔琳本《文心雕龙》的校勘,同样是以黄叔琳辑注本为底本,以唐写本及《太平御览》所引为参照。至于所据唐写本,恐亦得自容氏校本(40)据李平《孙人和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校雠辨析与辑佚》(《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七辑)一文辑录,孙校与赵校多有相合,其《征圣》篇“精理为文”条亦未出校,不大可能得自铃木氏校勘记。事实上,铃木氏《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在国内颇不易得,前述黄侃向内山书店求购内藤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即未能如愿。后来张少康等撰写《文心雕龙研究史》(2001)及主编《〈文心雕龙〉资料丛书》(2004),所参照者乃兴膳宏复印自铃木虎雄文集,并非1926年《支那学论丛》所载。,校勘时间则应该是在1926年6月至1929年6月之间。
其余叶长青、杨明照、王利器等人所利用的,应该也是赵氏校记或据黄文弼照片晒制的副本。叶长青所据实为赵氏校记,前述扬焄文章已然指出,此不赘。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关于唐人草书残卷本有云:“原本既不可见,景片亦未入观,爰就沈兼士先生所藏晒蓝本迻录,比对诸本,胜处颇多。吉光片羽,确属可珍。惜见夺异国,不得一睹原迹为恨耳!”(41)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40页。杨氏后来继作《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此段文字有所删改。又杨氏所见沈兼士晒蓝本,效果大概也不甚理想,故其引唐写本出校者远少于赵万里、孙人和所校。杨氏此书虽出版于1958年,但其写作却始于1936年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所说沈兼士先生所藏晒蓝本,同样源自黄文弼照片。盖黄文弼入北大国学门担任助教时及以后数年,主持国学门工作的即是沈兼士,故沈氏有此晒蓝本而为燕京大学研究生杨明照所得见,实不足怪。只是不知此晒蓝本是私人所藏,还是存于北大国学门,可供他人借阅。但无论如何,民国时期学人所见唐写本《文心雕龙》,除个别人(如傅增湘)外,主要还是源自黄文弼所持照片(42)黄侃1934年4月15日日记:“甫欲出游而离明(黄建中号)至,因问彼所影钞敦煌《文心雕龙》”。又19日日记:“借离明敦煌本《文心雕龙》影片廿二纸。”(《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62、963-964页。)黄建中当初所摄照片洗印两份,一份寄给黄文弼,一份自存,故黄侃借阅者与黄文弼、容庚、赵万里等人看到的并无二致。。
当初黄文弼曾对人表示拟将唐本另用珂罗版影印流传,可惜此事一直未见付诸实施。其间原因,或许是因为黄文弼后来兴趣全在西北考古,又或许是因为经费无着,致使黄文弼所持照片终未以其本来面目公诸于世(43)黄文弼1952年所作《谨述关于〈文心雕龙〉事件的经过》提到:“1935年我迁至西安后,曾想把过去根据敦煌唐写本《文心雕龙》照片校稿誊清后出版”,但亦未能如愿。见朱玉麒、王新春编:《黄文弼研究论集》,第201页。。虽然赵氏校记的发表,容氏校本的流传,以及沈氏蓝本的制作,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但毕竟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应该说,即便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北京图书馆购得大英博物馆制作的缩微胶片之后,黄文弼所持唐写本照片仍以其完整性和清晰度具有重要价值(44)大英博物馆首批制作的缩微胶片因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有缺页,户田晓浩、饶宗颐所得胶片皆有此误,北图购入者亦然,但赵万里、铃木校勘所据并无缺漏。,如果当年即将此照片影印刊出,则不仅可释杨明照之憾,且内地学人固不必待饶宗颐、潘重规书出始睹唐写本真容。反观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第一时间即将所录原文全部刊出,为日本汉学界提供了研究的第一手资料。1951年户田晓浩作《〈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补》,所用敦煌本《文心雕龙》即铃木刊于《内藤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之校勘记(45)参见王元化选编:《日本〈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31页。。此中差异,值得深思。
由此想到后来所谓黄文弼私藏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一事。关于此事之来龙去脉,王世民先生文章辨之甚详,然究其原因,恐非仅黄氏本人疏忽大意一端。
从王文介绍的情况来看,此事实导源于1931年9月北平图书馆举办的水灾筹赈图书展览会,当时黄文弼提供了若干西北出土文物作为展品,其中《文选序》残纸被误作“《文心雕龙》写本残卷”予以展出并编入目录,注明“以上西北科学考察团藏书”(46)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5期,1931年10月出版,第105、106页。其“中文残卷”类依次列有文心雕龙写本残卷、毛诗写本残卷、阿梁状辞、比丘尼僧发愿文、至元宝钞、唐张玄章残牒共七种。。这应该就是后来黄文弼私藏《文心雕龙》残卷之说的远因。后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序录介绍校勘所据书目,于“已知有其书而未得征引”条下提到:“前北京大学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某藏唐写本,约长三尺。”(47)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王利器此书乃先前《文心雕龙新书》(1952)增订之作,有关唐写本文字实作于1950年。此语前句当据北图书展目录,故未提及藏者姓名;后句则另有所本,应该是得自前修绠堂伙计李新乾的讹传。至于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版本”节称“抗战前,闻黄君文弼考古西陲,曾获唐写《文心》残卷一幅,长约三尺”(48)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第788页。,则属误记。盖李新乾误将黄文弼所说“二十多张”听成“二尺多长”(49)黄文弼曾语人,自己存有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照片二十多张,因其湖北口音较重而被李新乾听成二尺多长,又讹传为长约三尺。见王世民文及所附黄文弼《谨述》。,事在1947年黄文弼回到北平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之后,故杨明照绝无可能在抗战前便知晓此事。且杨氏1958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校注》并无此条,应是后来据传闻增补。
杨书尚有后文:“惟视为枕中鸿宝,未尝轻以示人,其详无由得知(据说是《隐秀》篇)。”杨氏并未说明此信息得自何人,而王利器则在《我与〈文心雕龙〉》一文中有过解释,称1946年应聘北大教职后,“赵万里先生知余之从事于整理是书也,乃告余曰:‘你的北大同学黄某,藏有敦煌卷子《隐秀》篇。’找到黄某交谈,方知他所收藏的实乃是唐写本《文选序》,而非《文心雕龙·隐秀篇》”(50)王利器:《王利器学述》,王贞琼、王贞一整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若事实果如王氏所说,则有两点令人不解:一是1931年北图书展,赵万里乃主持之人,且赵氏此前又曾校勘唐写本《文心雕龙》,故其对于展品中有“《文心雕龙》写本”之事自当格外留心,不应将展出之《文选序》残纸误作《文心雕龙》残卷,更不应无端认定黄文弼所藏为《隐秀》篇;二是既然王利器当时已面询黄文弼澄清误传,为何在其书中仍保留此则文字,且于50年代初又出面检举?
本文第二节提到1926年6月11日《清华周刊》刊出的一则短文。是文虽未署名,然其所以刊出,当与黄文弼不满于赵万里擅自发表《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有关,故不仅对赵校所据写本来源及黄文弼的研究详加介绍,且特别申明“赵先生因事前未悉此书原委,遽将唐本异同写为校记刊出,良用歉然”。显然,对于不明就里的普通读者来说,此文更像是赵万里的一封公开致歉信。但此文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是否赵氏本人心态的真实反映,却是一个应该追问但又无法证实的问题。如果此文背后隐藏了赵、黄二人之间的一段小小过节,又是否会对后来所谓黄文弼私藏《隐秀》篇传闻产生某种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黄文弼的否认、辩解,无论赵万里还是王利器都不愿相信。赵万里当然知道展出的那片残纸绝非《文心雕龙》,更不会是《隐秀》篇,但他显然怀疑黄文弼还隐藏了某些西北考古所得;王利器笃信赵氏之说,再加上李新乾“二尺多长”的旁证,于是黄文弼私藏《隐秀》篇之说便予以坐实,令其百口莫辩,从50年代到80年代,历30年而不止。黄氏诚有疏忽之失,但事态演变至50年代初多次开会追查,几有牢狱之灾,乃至80年代初重提旧事,以讹传讹,则原因固多,不能完全归因于疏忽二字。
倘若当初黄文弼收到黄建中所寄照片后,即如铃木虎雄之作校勘记将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公诸于世,自然不会再有赵万里作校记之事,也不致招来他人疑其秘而不宣的猜忌;又或者赵万里在发表校记时,对照片来源加以说明并知会黄文弼,使黄建中、黄文弼之贡献得以为世人所知,而黄、赵二人之嫌隙亦可避免。也就是说,所谓黄文弼私藏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与其说是一场由疏忽所导致的误会,不如说是因某些陋习而引发的风波。
以此观之,虽然铃木虎雄校勘唐写本《文心雕龙》在时间上并不领先,但在学术观念、规范方面,滞后的却是中国学人。
五
前述杨焄文章结尾提到,据林其锬《顾廷龙谈〈文心雕龙〉敦煌写本》及《张元济书札》,1946年农历9月28日,张元济曾将若干唐写本《文心雕龙》照片交予顾廷龙,让顾与《四部丛刊》本《文心雕龙》对校。顾廷龙回忆:那敦煌写本是正楷写的,所以校起来很快,一个晚上便校好了。杨文认为,顾廷龙精于版本鉴定,兼擅书艺,绝不可能将那份用草书抄写的残卷误认为正楷。由此可见,在大英博物馆所藏草体唐写本《文心雕龙》之外,还有一份唐人用正楷抄写的《文心雕龙》散落于私人收藏家之手。 这个推测是不大靠得住的。顾廷龙有无可能将那份用草书抄写的残卷误认为正楷我们姑置不论,此说疑点在于:1.张元济给顾廷龙的便条说得很清楚,“今送去唐人写本《文心雕龙》影片四十五张”,而黄建中自伦敦寄给黄文弼的照片共“二十有二叶”(原书双页合为一张),潘重规《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附录照片四十四张(单页),较之张元济送来者仅一张之差。以照片张数论,张元济送来者绝不可能是草书唐写本残卷的后半部分,更不可能是全本。2.退一步说,如果顾廷龙所校确为今传唐写本残卷的后半部分,或另一包含《隐秀》篇全文的写本,那他绝不可能一晚上便校完(当初赵万里校勘曾耗费“三夕之力”,黄侃也用了数日)。更重要的是,如果张元济送来的唐写本《文心雕龙》中《隐秀》篇原文并未散佚,顾廷龙理当予以抄录,公之于世,而不会毫无印象。所以,顾氏所校,极有可能还是英藏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照片。
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康因附逆被判刑入狱,其藏书遂散落社会。张元济所得,会不会是董康1922年底在伦敦拍摄的照片呢?姑记于此,以待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