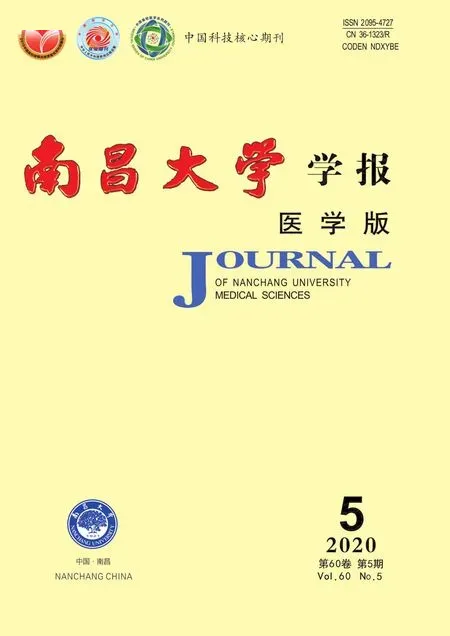新型免疫检查点BTLA在免疫调控及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作用
2020-12-12闵亮亮彭珊珊谭曼曼闵卫平
闵亮亮,彭珊珊,谭曼曼,闵卫平
(1.南昌大学a.药学院; b.免疫与生物治疗研究所; 2.江西省医学科学院中心实验室,南昌 330006)
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是目前肿瘤治疗的研究热点,通过特异性的阻断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抑制通路,恢复T细胞的免疫活性,进而提高机体对肿瘤的抵抗[1-2]。B和T淋巴细胞衰减子(BTLA)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上过表达,通过与配体的结合,抑制T细胞的活性,促进肿瘤逃逸的发生[3-4],因此阻断BTLA信号通路有助于激活T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的功能和活性,抑制肿瘤生长[5]。此外,BTLA在树突状细胞(DCs)的表达还和外周免疫耐受相关,是自身免疫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6]。现就BTLA的分子特征、功能和在不同免疫细胞上介导的免疫调控予以综述。
1 BTLA的分子特征及表达
BTLA(CD272)是位于细胞表面的Ⅰ型糖基化跨膜蛋白,定位于人体3号染色体上的q13.2位点,编码289个氨基酸[7]。2003年首次发现BTLA在活化的Th1细胞上表达[8],随后被证明也表达于B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NK细胞[9]。这表明BTLA不仅参与适应性免疫应答,同时还参与机体天然免疫应答的调控。
BTLA被认为是属于CD28超家族的另一种抑制性受体[10]。与PD-1和CTLA-4相似,BTLA的蛋白结构包括细胞外单个IgV样结构域、跨膜区和胞质区。BTLA的胞质区由3个基序组成:基于免疫受体酪氨酸的抑制基序(ITIM),基于免疫受体酪氨酸的转换基序(ITSM)和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2基序(Grb2)。激活的BTLA通过将含有Src同源性2(SH2)结构域的磷酸酶1和2(SHP-1和SHP-2)募集至ITIM和ITSM基序,导致T细胞受体(TCR)的激活受到抑制[5,8,11]。BTLA通过与配体相互作用诱发一系列的信号传递,参与肿瘤免疫抑制、自身免疫性反应、移植排斥反应等多种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7]。
2 BTLA的配体及其相互作用
BTLA已知的唯一配体是疱疹病毒侵入介质(HVEM),也被称为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14(TNFRSF14),属于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的一员。BTLA/HVEM的相互作用首次证明这两个受体家族之间存在相互联系。HVEM最初被发现在黑色素瘤细胞系中高度表达,肿瘤特异性T细胞的BTLA分子和黑色素瘤细胞的HVEM分子相互作用导致了T细胞的抑制,而应用抗体阻断BTLA可以逆转这种抑制[12]。最近在其他癌症中也发现了HVEM高表达,包括结肠直肠癌、肾癌、肝癌和乳腺癌,同时发现HVEM与患者生存率差以及晚期癌症特征具有正相关性[13-16]。此外,TANG等[14]的研究发现,沉默HVEM基因能够抑制肾癌细胞的增殖,促进肾癌细胞的凋亡,同时在动物实验中发现,HVEM基因的沉默能够显著减缓小鼠的肿瘤生长。
HVEM还存在另外一个配体LIGHT(TNFSF14),HVEM通过与T细胞表面的LIGHT相互作用,促进T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因子的分泌[17]。HVEM与不同配体结合能够产生相反的作用,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BTLA/HVEM通路还是HVEM/LIGHT通路尚无统一定论,还需要大量试验进一步阐明。
3 BTLA/HVEM信号通路机制
在T细胞中的研究发现,BTLA通过与HVEM的N端富半胱氨酸结构域CRD1相互结合后,诱导BTLA胞外ITIM、ITSM、Grb2 3个结构域发生磷酸化[18],ITIM、ITSM结构域的磷酸化可以帮助BTLA招募并激活下游酪氨酸磷酸酶SHP-1和SHP-2,进而抑制依赖蛋白酪氨酸激酶(PTK)的细胞活化,影响T细胞的增殖[19]。Grb2结构域磷酸化后能识别Grb2蛋白,募集PI3K蛋白亚基p85,并刺激PI3K信号传导途径,促进细胞增殖和存活[20]。此外在B细胞中的研究[21]还发现,BTLA与HVEM结合诱导ITIM结构域的磷酸化后,仅导致SHP1募集,减弱B细胞的增殖。并且,BTLA降低了B细胞蛋白酪氨酸激酶Syk的活性,在Syk的下游分子中,B细胞连接蛋白(BLNK)和磷脂酶C2(PLC2)在BTLA信号传导时显示较低的磷酸化水平,这些证据表明BTLA信号激活导致BCR信号转导级联的活性降低。BTLA/HVEM通路的反应机制尚未完全清楚,其激活机制及对下游分子影响的确切机制仍然处于探索中。
4 BTLA介导的免疫反应
4.1 BTLA与T淋巴细胞
BTLA信号已被证明对抗原特异性T细胞有抑制作用。早期研究[22-23]表明BTLA通过与HVEM结合导致T细胞激活减弱,并且BTLA敲除小鼠表现出超敏免疫激活,最近的研究[5,12]发现肿瘤微环境中CD8+细胞BTLA表达上调,同时上调的还有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Tim3)分子,这些免疫抑制分子导致T细胞功能受到抑制,而通过抗体阻断BTLA蛋白可增强肿瘤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根据现有的实验分析,抗PD1/PD-L1的肿瘤免疫治疗仅对部分患者有效,总反应率约为30%[24-25],而同时联用抗BTLA的免疫治疗可以提高对机体肿瘤的控制及促进细胞因子的分泌[5,26]。这可能表明BTLA作为抑制性的免疫检查点,同样参与了肿瘤的免疫逃逸。
然而,在一项黑色素瘤的过继疗法中显示[27],相比于CD8+BTLA-的肿瘤浸润T淋巴细胞,CD8+BTLA+的肿瘤浸润T淋巴细胞表现出更强的肿瘤杀伤作用,而且患者的生存率更高;另一项研究[28]同样发现,过继输入的CD8+BTLA+的肿瘤浸润T淋巴细胞对白介素-2(IL-2)的反应更强,并且输注后在体内的存活时间更长,相反,CD8+BTLA-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并未表现出增殖,反而促进T细胞耐受相关的基因的表达。这些研究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反,这提示BTLA似乎存在其他通路对T细胞产生影响,而这可能是由于BTLA区别于PD1的胞质区结构Grb2基序发挥作用引起的。Grb2连接的SLP-76和Vav相互作用参与IL-2的产生,并且Grb2的募集对于CD28诱导的IL-2产生是必需的[27],因此,CD8+BTLA+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表现出增殖和杀伤能力的增强可能与依赖BTLA的IL-2产生有关。对BTLA的进一步认识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到试验中证明。
4.2 BTLA与B淋巴细胞
随着BTLA在T细胞上研究的进行,BTLA对B细胞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在一项针对卵巢癌的研究中[29],作者通过对254例卵巢癌样本的分析发现,BTLA+的患者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更短,并且在卵巢癌小鼠模型中发现,相较于T淋巴细胞和NK细胞,BTLA在CD19hiB淋巴细胞的表达更高。而在卵巢癌的的侵袭过程中,IL-6和IL-10的浓度在腹水中会显著增加。作者进一步研究[30]发现在IL-6和IL-10的调控下,促进AKT和STAT3磷酸化诱导更多的BTLA+CD19hiB淋巴细胞,而通过抗BTLA的抗体治疗,能够显著降低荷瘤小鼠的腹腔肿瘤体积,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期。在另一项研究[31]中同样发现BTLA的表达上调会导致B细胞的部分功能如增殖能力、细胞因子IL-6,IL-10和TNF-α的分泌受到抑制,而趋化因子IL-8和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β(MIP1-β)的分泌并未受到BTLA/HVEM通路相互作用的影响,这表明虽然与T细胞相似,BTLA作为B细胞的重要免疫检查点,并不会对B细胞的所有功能均产生抑制,这也为BTLA同其他药物的联合治疗提供了数据支持。
4.3 BTLA与树突状细胞
DCs通过调节性T细胞(Treg)介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但目前尚不清楚树突状细胞具体如何调节这种耐受诱导。JONES等[32-33]的研究发现,DCs表面的BTLA分子通过与T细胞表面的HVEM结合,引起T细胞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激酶(MEK)的磷酸化,导致CD5表达的正调控因子(ETS1)的表达增加和CD5的负调控因子TCF-3表达下降,最终引起T细胞CD5的表达上调,进而促进FoxP3的表达。即使在稳定状态下,BTLA缺失的DCs不能诱导外周Treg的产生,因此,DCs需要BTLA和CD5依赖的机制来主动调节稳态条件下T细胞的耐受反应。在最新的一项实验[34]中发现,构建针对多种T细胞抑制受体特异性配体的DCs是一种产生耐受抗原提呈细胞的有效途径,分别包括PD1的配体PD-L1,BTLA的配体HVEM和CTLA4的配体B7-1,这些表达T细胞抑制受体特异性配体的DCs能够抑制T细胞的反应从而介导免疫耐受,并且这些细胞对多种T细胞抑制因子通路的激活可以有效地抑制正在进行的自身免疫。以上的证据表明BTLA/HVEM通路可能参与了树突状细胞对外周耐受的调控,也表明此通路可以作为自身免疫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
4.4 BTLA与NKT细胞
在肿瘤基线和治疗环境中,自然杀伤T细胞(NKT细胞)正在成为抗肿瘤免疫的关键调节剂。虽然Ⅰ型NKT细胞可以促进抗肿瘤免疫,但它们在肿瘤微环境中的活性可能受到抑制免疫检查点等负调节因子的限制。在一项小鼠乳腺癌模型研究中[35],作者在分析免疫检查点受体表达时,发现PD1和BTLA在Ⅰ型NKT细胞上表达比传统的CD3+T细胞表达更高,而且与PD1相比,BTLA在Ⅰ型NKT细胞表达更高,随后通过BTLA抗体阻断BTLA,观察到显著降低小鼠肿瘤生长和肺转移,而PD-1阻断在此肿瘤模型中基本无效。在早期的两项独立研究中[36-37],还发现BTLA还与Ⅰ型NKT细胞的活化有关,BTLA在肝NKT细胞上的表达缺失增加了肝脏炎症反应。以上的证据均表明BTLA对NKT细胞存在抑制作用,而这可能导致早期肿瘤免疫逃逸的发生,但是目前关于BTLA在NKT细胞的作用的主要集中在肝炎模型的研究中,对于BTLA对NKT细胞的具体抑制机制及在肿瘤免疫中的潜在治疗靶点需要在不同的肿瘤模型中进一步验证。
5 BTLA介导的肿瘤免疫治疗
BTLA同其他免疫检查点分子(如PD1、CTLA-4、Tim3)一样,在肿瘤浸润的淋巴细胞表面表达上调,并且与相应的配体结合后,会抑制T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肿瘤免疫逃逸[38]。应用单克隆抗体或小分子化合物阻断免疫检查点分子与其配体相应信号通路后,可逆转免疫细胞的耗竭,进而恢复免疫细胞的活性,抑制肿瘤发展,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已经成为肿瘤免疫治疗中的重要一环[39-41]。
虽然BTLA与PD1、CTLA-4同属于一个家族,但是配体家族不同,PD1、CTLA的配体家族均属于B7家族,而BTLA通过与肿瘤坏死因子家族产生作用,阻断BTLA可以解除BTLA/HVEM信号通路对T细胞产生的抑制,进而促进HVEM和LIGHT的结合,激活T细胞,因此具有双重作用。BTLA已经在几种肿瘤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疗效,并且在联合其他免疫检查点阻断剂时能加强其他免疫检查点阻断剂的治疗作用[5,26,29],同时,BTLA对肿瘤微环境中其他免疫细胞同样具有抑制作用。由此可见,BTLA独特的表达及其细胞内信号通路对靶向BTLA的肿瘤免疫治疗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6 展望
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问世,为许多肿瘤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与传统的手术治疗、化疗和放疗相比,肿瘤免疫治疗具有迅速、持久、有效的药物反应,同时也能与传统的放化疗相结合,进一步加强疗效,提高受益人群的比例。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在肿瘤免疫的研究中已经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而且正在尝试不同检查点的联合阻断,同样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一些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性分子如Tim3,淋巴细胞活化基因3(LAG3)、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蛋白(TIGIT)等的作用及机制尚不明确,它们与BTLA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尚未完全清楚,联合阻断的具体给药方案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此外,BTLA除对T细胞产生抑制作用外,同样也存在证据表明BTLA+T细胞增殖和杀伤能力增强,因此BTLA对T细胞的具体作用机制需要在更多的试验模型中进行深入研究,而且BTLA与HVEM的相互作用将TNF和CD28两大家族之间的信号相互联系,HVEM/LIGHT和BTLA/HVEM产生的正,负两种信号在肿瘤微环境中的确切机制需进一步阐述。因此,还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以优化BTLA相关的肿瘤免疫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