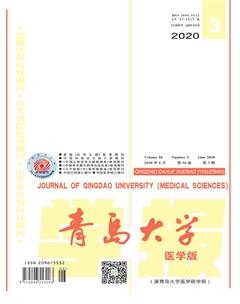老年人体位性高血压对靶器官损害的研究进展
2020-12-11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保健科,山东 青岛 266071)
长期以来,老年人血压的管理是医务工作者一直面临的挑战之一。人体生理活动、昼夜变化、季节变化、年龄因素、体位因素等都会使血压波动,而体位改变是重要因素之一。站立位时,有500~1 000 mL的血液集聚于下半身,导致机体心排血量降低,进而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产生代偿作用,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和体液调节机制维持血压稳定。但当机体生理功能衰退、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和体液调节能力下降时,无法完成代偿性调节,就会出现体位性低血压(OH)或体位性高血压(OHT)。目前,对OHT的研究少,OHT的定义不统一且发病机制仍不明,其研究主要围绕与动脉硬化等器官损害的相关性,但有一些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本文主要对OHT与靶器官损害的相关性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提高医务工作者对OHT的重视,并建立早期筛查方案,积极预防靶器官损害。
1 OHT的现状
1.1 定义
OHT通常发生于轻度或边缘性高血压病人,它是不稳定性高血压的重要类型之一。目前,对OHT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在参考文献中,不同的判断标准包括:直立后收缩压升高≥2.66 kPa、>1.33 kPa、>0.66 kPa(仅以收缩压变化为标准,不考虑舒张压变化);平卧位血压正常,直立后收缩压≥18.62 kPa和(或)舒张压≥11.97 kPa(以血压变化的绝对值为标准);舒张压从仰卧位的<1.97 kPa增加到直立位的>1.97 kPa(仅以舒张压变化为标准)[1-5]。
1.2 患病率
对一般人群进行主动站立试验、家庭血压监测、直立倾斜试验,测得OHT的患病率从11%到28%不等[3,6-8]。家庭和动态血压监测设备配置有位置传感器,且检测时不会产生白大衣效应,提高了诊断OHT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有少量研究表明,OHT的患病率高于OH。如RANDAL等[9]对2 781例青少年的研究显示,OHT和OH的患病率分别为26.6%和16.2%;MATSUBAYASHI等[10]对334例老年人研究显示,OHT和OH的患病率分别为8.7%和6.0%。
1.3 临床表现
OHT可能出现的症状有头晕、头痛、心悸、恶心、易疲倦、入睡快、出汗和晕厥等[11]。既往研究表明,OHT与直立性眩晕(OD)不相关[12]。然而LEE等[11]却发现,少数OD病人在倾斜位时会出现OHT。因此,OHT头晕的发病机制及矫正OHT后是否能够改善头晕症状目前尚存争议。此外,OHT病人还有3个特征:直立性心动过速、对利尿剂不耐受、站立时腿部皮肤变为蓝色。
1.4 发病机制
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被认为在OHT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关键作用,动物模型也证实直立性高血压是由交感神经介导的。OHT发病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体位改变(站立位)导致下肢静脉窦的“重力血管池”过度充盈,静脉回流减少,心排血量减少,血压一过性降低,进而刺激主动脉弓和颈动脉窦压力感受器,这种代偿性自主神经反应通过血管收缩和心率加快可在几秒钟内恢复正常血压。有研究表明,OHT病人由于直立时腿部静脉池过多[1],过度刺激α交感神经,导致外周血管收缩过度,使血压高于仰卧位水平;而使用抗重力服可预防过度交感反应的发生,则进一步证实该理论。②体位改变诱发体内神经体液因子变化。有研究证实,OHT病人直立位时去甲肾上腺素水平、血管加压素水平均高于非OHT病人,表明去甲肾上腺素和血管加压素分泌的增加可能参与OHT的发生[11,13]。③肾血管的结构或功能异常也可能是OHT的发病机制之一。立位应激可降低有效血容量,引起交感神经兴奋,致使肾入球小动脉收缩,肾血流量减少,激活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从而造成水钠潴留、血压升高[14]。此外,SCHIEFER等[15]研究表明,肾下垂病人发生OHT的概率较高。肾下垂可引起肾动脉的牵拉和扭转,造成肾血流量减少,从而引起OHT。④压力反射敏感性下降[16]。研究证实,年龄的增长可导致心脏大血管的压力感受器敏感性降低,压力反射不能将血压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引发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⑤动脉僵硬度增加和小动脉重塑。研究表明,OHT病人的动脉硬度、肱-踝脉搏波速度(baPWV)或颈动脉内膜厚度增加,从而加重直立交感神经反应,增加外周血管阻力,也可能是一个相关的促发因素[17]。⑥衰老、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嗜铬细胞瘤、血管肾上腺素能超敏反应等。以上疾病可增强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并导致自主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被认为是OHT的临床促进因素[18]。此外,自主神经系统紊乱也可增加OHT的发病率与疾病进展程度[19],例如心动过速综合征伴肥大细胞增多症病人OHT的发病率高达38%,血压最高为31.92/18.62 kPa。
2 OHT与靶器官损害相关性
2.1 OHT与认知障碍
老年高血压病人的脑血管储备能力降低,在日常活动中频繁出现的血压波动可能会导致无症状脑血管病,进而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造成认知障碍[20-21]。MASTSUBAYASHI等[10]研究显示,与体位性血压正常者相比,OHT病人的认知功能降低,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国内有研究显示,OH组和OHT组认知功能障碍所占比分别为18.2%和9.0%,作者认为虽然OHT病人发生神经功能障碍的概率较小,但不能排除OHT诱发认知功能障碍的可能[20]。然而,我国学者刘莉等[22]的研究却认为,OHT不能预测认知功能障碍。
2.2 OHT与脑卒中
近年来国内外对OHT与脑血管损害关系的研究较多。KARIO等[13]研究发现,OHT是老年高血压病人脑卒中的一个新的危险因素,也是发生隐匿性脑梗死和进展性深部脑白质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樊晓寒等[5]对4 000多例高血压病人进行研究发现,OHT组脑卒中发病率明显高于体位性血压正常组,OHT组脑卒中危险度增加1.76倍。OHT的血压变异可能伴有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和血小板、凝血系统的激活[23],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两者的相关性,但晨起血压波动与血小板聚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24],可间接表明血凝异常与血压变异可能存在关联。而晨起血压升高和血凝异常也可增加脑卒中的风险[25]。YATSUYA等[26]的研究揭示了体位性血压变化与缺血性脑卒中各亚型间的关系,非腔隙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与体位性血压的下降呈线性相关,而腔隙性脑梗死则与体位性收缩压改变值呈U 型关系。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在老年疗养院病人中,姿势血压变异性增加与卒中预后显著相关[27]。
2.3 OHT与心血管疾病
国外一项研究结果显示,OHT与冠心病发病风险呈正相关,直立后收缩压改变值(△SBP)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呈J型关系,且△SBP是IMT的独立危险因子,表明体位性血压调节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26]。最新研究发现,IMT和baPWV与OHT相关[28],外周血管病和左心室肥厚与△SBP均呈J型关系,说明OHT与心脏、血管的靶器官损害相关。KOHARA等[29]研究同样发现,OHT与隐匿性高血压、晨峰血压、血压变异性密切相关,可加速心血管重塑的进展,如颈动脉内膜厚度增加、左心室肥厚等,原因可能为体内交感神经过度兴奋,β和α1受体过度激活,引起内皮细胞损伤及心肌细胞肥厚。然而,TOMASZ等[30]研究表明,颈动脉内膜厚度、左心室质量指数与OHT的发生没有显著相关性。上述研究结果差异的可能原因为OHT评估方法或诊断阈值不同,有待制定相关标准后进一步研究。
2.4 OHT与肾损害
有研究结果显示,OHT病人的尿清蛋白排泄率(UEA)显著增加[31],尿蛋白排泄增多和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可造成慢性肾损伤,提示OHT可增加肾功能不全的风险。国内有研究结果显示,老年OHT病人的肾功能下降程度更明显,其卧立位血压的变化与肾功能损害的指标(如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血尿素氮、肌酐、胱抑素C水平升高)密切相关[32],原因可能与血流动力学改变有关,其相关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HOSHIDE等[33]研究发现,多沙唑嗪治疗OHT成功地减少了体位性收缩压的变化,而且UEA的降低进一步表明,OHT治疗减少了肾脏器官的损害,积极治疗OHT可显著降低病人的尿微量清蛋白。然而,也有研究指出,肾小球滤过率与OHT并没有显著相关性[34]。
2.5 OHT与代谢病
肥胖病人特别是中心性肥胖病人的交感神经兴奋性比非肥胖者高[35]。TABARA等[36]的研究发现,腹型肥胖是OHT的危险因素之一;同时还发现,弯曲的姿势可能是体位性血压变化的一个被忽略的决定因素,弯下腰的姿势可能是矫正直立不耐受症状的一种治疗对策。既往研究发现,相较于单纯糖尿病病人,糖尿病合并OHT病人的下肢振动觉较弱,提示OHT可能与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有关。进一步治疗糖尿病病人的自主神经病变可以有效降低OHT的发生率[16]。闫开华[37]通过对比每日限盐3.8 g和6.0 g的OHT病人血压变化情况发现,摄盐量少者血压变化更平缓。因此,该研究提出,OHT病人需合理膳食、严格限制盐的摄入量,这有助于控制血压的波动程度。
3 OHT的早期筛查
老年人若不及时发现、及早干预OHT,长期的血压异常波动会引起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同时也增加急性并发症发生率[38]。因此,应用合理、经济、高效的筛查方式,结合多种检查手段,建立预测OHT的发生风险模型,可以显著提高OHT检出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多项指标可用于筛查,包括睡眠时间、年龄、体质量指数(BMI)、立卧坐位收缩压、立卧坐位舒张压、baPWV、踝臂指数、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血脂、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叶酸、维生素B12、尿微量清蛋白、肌酐清除率、尿微量清蛋白排泄率、颈动脉超声(IMT、有无斑块)、心脏超声(左心室质量分数、舒张功能指标)、颅脑CT(脑白质高信号分数)、认知功能评估(MMSE评分)、腰椎CT(有无腰椎前凸[39])等。通过识别OHT的高危人群,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随访,是降低OTH患病率、减少OHT发生靶器官损害、遏制医疗费用增长和延长期望寿命的关键。
数学模型能客观地对疾病发生进行定量预测,可将与特定对象或某种疾病相关危险因素的内在规律近似地用数学结构表达出来,通过统计学语言、编程计算进行批量预测,已成为目前预测疾病发生发展的主流方法。如果预测对象为人群,一般可以预测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和传染病爆发点,然后根据预测结果,制定预防措施和卫生政策;如果预测对象为个体,则可以获得个体未来一定时间患病的风险,确定个体的危险因素,帮助个体改善其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有效地控制疾病并改善健康状况。其中较为常见的模型是列线图模型,该模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传染病、心血管疾病、肿瘤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预测[40-41]。但关于OHT的预测模型还有待研究开发。
4 结语
虽然OHT与靶器官损害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但大多数研究是围绕单一疾病进行的或是单一随机对照研究,未能系统、全面地概括所有可能的危险因素,也很少注重OHT早期筛查的重要性,未提及应用预测列线图模型的益处。因此,基于OHT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