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云深好无伴
2020-12-10水生烟瞳LoksT
文/水生烟 图/瞳Lok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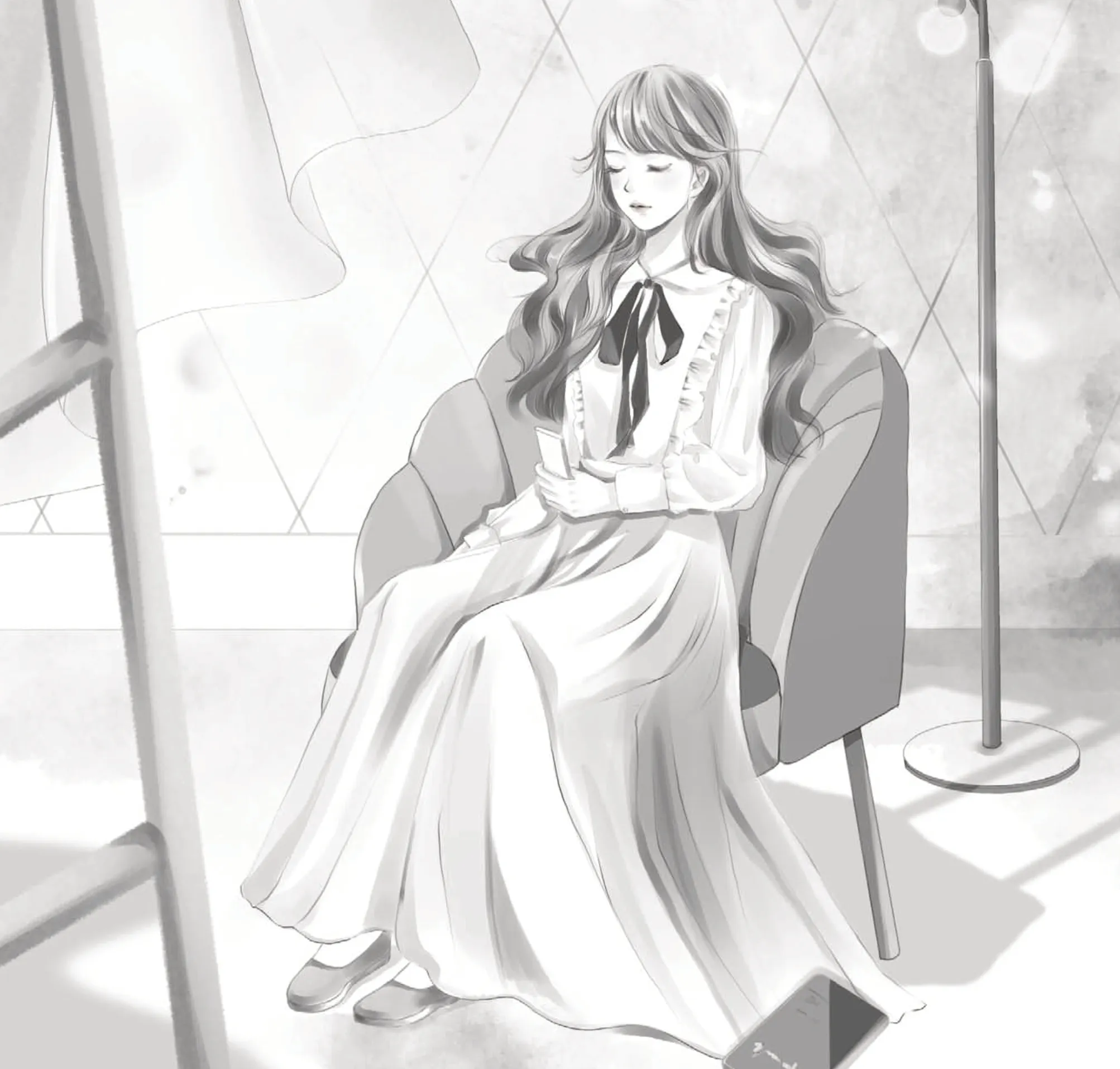
在时间与距离面前,生活里的积尘缓缓塌压,像地壳运动产生的断裂凹陷,将两人隔成彼岸。
1
秦苒和林耐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牵手,是在海洋馆里。
海底隧道里,当身形扁平的鳐鱼以俯冲之势飞游而来时,林耐问:“你看它像什么?”
“飞毯。”秦苒不假思索地回答。她看着旋转来去的鳐鱼,觉得它心底大概藏着许多慌乱不安,就和此刻的自己差不多。
林耐笑起来。背景是蓝色的光与水,在各色各样的水生物的搅动下,盈盈漾漾地晃眼。他站在那里,秦苒忽然不确定是这光影映亮了他的模样,还是他的笑容,让整条暗黑隧道生出了璀璨而神秘的光亮。
过人生与过隧道有无差别?就这样一条道走下去又能怎样?秦苒心头一热,便握住了他的手。
林耐的笑声一下子听不见了,像是被谁仓惶地按下了静音键。他的全部感知都集中在那只手上,却动也没动地保持着垂手的姿势,隔了一会儿才低声说:“飞毯游走了。”
秦苒忽然觉得很委屈——掌心的炽热,需要精神能量的输送,而他似乎不肯与她共鸣。她松开了手:“它被狗粮撑着了,遛弯消食去了!”
林耐转过脸,才看见身边站着一对亲热自拍的情侣,而秦苒已经径自向前走去。
“苒苒!”他叫了她一声,她没有应,却举起相机给两条红色的大鱼拍照,她的声音里带着夸张的笑意:“哇,快看快看!”
那两条交错浮游的红鱼,你追我赶地顾盼嬉游着,只一会儿便看不见了。
在昏昧失真的灯光下,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遥远而模糊,情绪却不会因此稀释,反而被酵解,变得膨大而浓稠,回忆沙聚成塔,像隧道穹顶一样压顶而来,除了向前走,似乎别无他法。
2
两年前,秦苒与林耐相识在敦煌金色的沙漠上,他们在同一个向导的带领下乘骆驼向营地进发时,骆驼刚立起前腿,就把坐在驼峰中间的秦苒抖了下来。
秦苒的体能和户外技能都不怎么样,迷迷糊糊了一路,这时的反应倒是异常迅速。大概生怕被这大牲畜再补上一脚,她落地后立刻蜷起身体,就势顺着坡地滚了出去。
走在她后面的林耐本来是想要过去帮助她的,结果脚下一滑,跌坐在地滑下斜坡的速度比她还快。已经坐直身体的秦苒被滑沙再次带离,她刚惊叫了一声,就吃了一嘴沙,赶忙闭紧嘴巴时,已经感受到了牙齿咬合时咯吱咯吱的响声。
两个人坐在沙地上狼狈地相视而笑,灰头土脸地交换了姓名,握手时两个人沾满细沙的手握在一起,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于是不约而同地用了点力气。林耐仰头看向天空的时候,秦苒偷偷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她觉得他手上的沙子大概尽数印在了自己的手心、手背上,正在微微发热、生痛。
后来他们骑在骆驼上摇摇晃晃地向营地里走去,骆铃在辽阔苍茫的沙漠里显得遥远而清晰。
沙漠里的夏天,天黑得很晚,砂砾降温的速度却极快,半夜里秦苒裹着披肩走出帐篷,看到林耐坐在篝火旁时,心里忽然生出了奇异的快乐与安稳,她问:“你怎么还不睡?”
林耐笑了,“同伴的鼾声太响了。你呢?”
“第一次在这种地方过夜,明明又困又累,却睡不着。”秦苒在离他一米远的地方坐下来,他正捡起柴禾投进篝火,火舌舔舐了几下,立刻窜起了热烈火焰。
交谈是自然而然就发生了的——后来秦苒再想起那一夜,总觉得交浅言深,后悔不迭。
就在那天夜里,林耐对秦苒说起了他的一位师兄,那是他的偶像——一位人文地理学家,他全年扎在遥远的村庄和田野山川里,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和分析。它们不仅有着向外的力量,同时也向内丰富并喜悦着自我。
林耐向往着那种辽阔和自由,他想要考取的研究院位于西北地区,而那里或许也将成为他的主要考察方向。他说:“人的一生太短暂了,怎么舍得平平淡淡地过完?总要做最热爱的事情才行。除了山川河流,这世间的一切,物质也好,感情也罢,都会随着时间褪色。”
赤色火焰吞吐、翻卷着,在黛蓝的天空下升腾起大团大团青白色的烟雾。在星月与篝火的映照下,他们的对话显得那么真实,却又那么梦幻。
秦苒来自威海,母亲以零售电商起步,到拥有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服装公司,正经地等着她大学毕业就回去以新鲜视角和专业能力发展经营。
纵然秦苒是个地理渣,也知道此地与家乡位于地图的两端,中间隔着万水千山。秦苒的眼里有星光有火光,那么明亮那么美。两个人的对话却出现了一小段空白,后来她说:“以后你来威海的话,我请你吃鲅鱼饺子!”
“你饿不饿?”林耐忽然问,变戏法似的从衣袋里掏出了两根香肠。
秦苒看着他用小刀修理着一截树枝,再将香肠送进篝火里,天地苍茫,火焰噼啪,香气升起来时,秦苒忽然就生出了热血与豪气,可是来自身后向导的大声惊呼,让她重回现实:“那是准备用三天的木柴!你们打算一晚上都给我烧完吗?”
3
略去南辕北辙的未来规划不提,林耐和秦苒就读于相邻两座城市的大学,大巴车行驶一小时二十分钟,再转三站城际公交,他就可以站在她的学校门口。
在后来的两年里,林耐走熟了那条路,目光抚过了一路的山岭起伏。
林耐第一次站在秦苒的宿舍楼下时,整个人显得慌张而拘谨,与沙漠篝火前侃侃而谈的青年全然不同。
那是秋天的午后,秦苒穿着灰蓝色休闲裤和白色卫衣,相比于在沙地上滚了几周,又利落坐起的形象,显得温柔明丽,而唇角和眼底的俏皮灵动,仍是他常常想起的模样。
站在万丈秋光里,秦苒觉得自己就像烤箱里第十五分钟时的可颂,整个人暖烘烘地膨胀起来。在四目相对的笑容里,她蓦然惊觉心底的期待和甜意涌上来,于是她红着脸垂下眼睑,像给可颂打上包装,又系了一个美丽的蝴蝶结。
那天下午,林耐发现秦苒似乎不太记路,她声称要带他去吃一家“超好吃”的餐厅时,在同一层楼足足转了两圈,又拉着他站上了下楼的扶梯,才终于找到了那家餐厅,坐下时她坦率地自嘲:“我有点紧张,让你见笑了!”
林耐笑容腼腆,眼光躲闪,他并不想表露自己从见到她开始就在持续飙高的欢喜和慌乱,但显然事与愿违了。而秦苒正笑眼弯弯地看着他:“因为你不是一般的男生啊!”
服务生递过来的菜单真像救命稻草,两个人各自垂眼,在话题自然转移的过程里,掩饰了两个人的心事。
第二天早晨,秦苒去找林耐。他入住的客栈要走过一段窄巷,两旁的人家伸出竹竿,晾着各色T恤、连衣裙和棉布床单,在风里起伏飘荡,摇摇晃晃,是最平实朴素的过日子的模样。走着走着,视野豁然开朗,一时间天也蓝了,地也阔了,桂花噙着凉丝丝的甜香,扑落在沾着晨露的青石地面上。
那家客栈的一楼,有一间大大的书吧,秦苒一边翻着书一边等着林耐,只是这座建造在山边的老房子有些冷,凉意不知不觉就从脚底漫上了小腿。
后来,林耐再来,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尽管听上去八成拙劣。而只要他来,都会住在这里,以致于有段时间,秦苒几乎以为他与女店主小敏在谈恋爱。那年春天,他帮小敏粉刷油漆剥落的花园木栅栏,他们穿着差不多款式的围裙,戴着一样的手套,秦苒站在他身边时,他却将油漆桶拿开了,“站远一些,味道很重。”
他还指着不远处的秋千架,说:“坐过去等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好。”
秦苒忽然觉得,自己与“他们”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心里乍然裂开的沟壑像是掉进了一整颗酸柠檬。她的目光落在他鞋面上的一滴白漆上,说:“忽然想起来了,今天上午学院有活动,我先走了啊!”
秦苒说完,一溜烟儿地跑了。
4
小敏走过来,用毛巾擦着额上的汗水,对林耐说:“有你这样谈恋爱的?她误会了!”
林耐手里的刷子更用力地油漆着木栅,他说:“这些油漆好像不太够,我再买一桶去!”
巷口的站牌下,秦苒垂着头,一下又一下地踢着凸起的马路砖,公交车停下又开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她仍旧站在那里。
林耐站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隔了一会儿,秦苒转过头来,脸上很快有了一抹浅淡的笑意,像是早晨极薄的雾气,她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还站在这里,他也没有问,却指着她脚边的马路砖,说:“它惹你了?”
秦苒扬起头,有些挑衅地看着他:“你惹我了,我踢你行吗?”
“如果这真能解决问题,我恨不能踢自己两脚!”林耐说着,近前一步,她却怂了,倏地转过脸去。
秦苒的声音很低,自言自语似的,像树上的新叶在风里轻轻地抖:“林耐啊,这广阔天地、大美人间,你怎么就非要去西北呢?”
她的心事远不止此,然而她的勇气却只有这么多,仅供她吐露至斯。她后退两步,身影很快落入了人群中间。
倾盖如故易,白首同心难。她害怕高估爱情,低估人性,更害怕成为人形绳索,让他不快乐——那样的话,自己又怎么可能快乐?
公交站牌下的人们在林耐和秦苒中间隔出了距离和屏障,林耐终于还是冲了过去,攥着她的手臂将她拉了出来。
秦苒踉跄着,额头撞在他的肩膀上,又赶忙直直站立。林耐用手指戳了一下她的额角:“你怎么这么倔啊?”
她就势抡起胳膊,在他的肩膀和胸膛上一顿捶打:“你才倔!你这头犟驴!”
秦苒忽然发觉现实生活和偶像剧真的差别好大!偶像剧演到这里,男主和女主大概率会有一个拥抱了吧?至少会有一方做出妥协了吧?可是林耐一动不动地任凭她拳打脚踢,与此同时,她发现他俩可真是心心相印——两头犟驴,就是应该各走各的路!
心事翻卷,泪水几次三番地想要冲出来,都被她生生憋了回去,后来她拽着他的衣袖向前走,大声宣布:“林耐,我要吃大餐!”
5
秦苒毕业前又去了小敏的客栈。小敏看着她的大件行李,不解地问:“你不回威海了?”
“我打算先在外面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些经验再回去。”
小敏径直问道:“是因为林耐吧?”
秦苒摇摇头,笑了:“他每天都以两万多的步数占领着微信运动的封面,可是每走一步,我都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
小敏剪着花茎上的刺,将它们插进清水瓶里,她说:“爱情如果不死于距离,大抵会亡命于时间,也许是我太悲观,但我没法乐观。正因为如此,我从来都没有劝过你们。”
小敏给秦苒讲了林耐那位师兄的故事。林耐时常说起他的坚定、洒脱与自由,却从来没有在秦苒面前提起过师兄的感情生活,尽管它听上去似乎只是一个落入俗套的故事——在时间与距离面前,生活里的积尘缓缓塌压,像地壳运动产生的断裂凹陷,将两人隔成彼岸。
秦苒怔怔地看着她,“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因为师兄的前女友就是我啊!”小敏眼也不抬,笑意只在嘴角,“我们都以为自己的爱情会与众不同,但事实上不过如此。刚分开时的热烈想念奔放得如同七月大河,时间久了就渐渐沉寂下去,即使偶有浪花,也充满了砂砾和猝不及防的冰碴。我们都想做圆心,让对方围着自己画圈圈。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山,让对方来就我,然而事实上我们都是水,会流走、会泄露、会蒸发消失……”
小敏从一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拿出一张纸条递给秦苒,上面是林耐有力的字体:“如果可以说我喜欢你,我多想现在就开口。”
秦苒觉得血液一下子涌进了脑袋,在太阳穴附近奔涌、啸叫,化作热泪奔涌而下。
6
林耐再见到秦苒,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秦苒实习的服装公司位于近郊,公司规模不大,但因为产品设计与经营理念的创新优质,营收利润呈逐月上升趋势。秦苒因为文能策划新品文案、武能蹲仓库打包发货,且有着不叫苦不叫累的吃苦耐劳精神,很快获得了同事们的认可。她是在加班发货后返回租住屋,经过扩建中的厂房,被木板上残留的铁钉扎伤脚掌的。
秦苒想要打电话给一同加班的同事李言,按照手机通讯录里字母排列的顺序,他和林耐的名字挨在一起,她不知道是因为手抖,还是下意识里的渴望,当看清屏幕上闪烁着林耐的名字和号码时,她觉得自己又被钉子扎了一下——这一次是在心里。
秦苒赶忙掐断了电话。
闻讯赶来的同事将她送到了医院。清洗伤口时,秦苒疼得面部扭曲,忽略了手机铃声。等到医生折断疫苗瓶颈,刚将银亮的针头插进去,她的手机就又开始响。直到注射结束,秦苒一手捏着棉签按住针孔,另一只手费劲地掏出了手机。
电话另一边是林耐,他说:“苒苒,怎么了?”
秦苒的喉咙像是被黏住了。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她才听见自己被挤压变形的声音终于突出了重围:“你在哪里?”
诊室里的灯光亮茫茫的,窗台上的盆花像是被泡在药水里,花朵、花叶全都亮晃晃的失了真,让人看得头晕目眩。电话另一端,林耐说:“你从来没有这么晚打过电话给我。出什么事了?”
医生看了秦苒一眼,大声说:“流血了!让你按着针孔,你看你的棉签按在哪里?”
她的手一抖,径自挂断了电话,接着自虐似的将酒精棉重重地按在了针孔上。
7
第二天早晨,小敏出现在秦苒的门口,她先是蹲在地上仔细地看了看秦苒缠着绷带的脚,然后站起身笑了:“林耐让我先过来把你接回去!听他的语气,我还以为你此刻已经打着石膏、坐着轮椅!”
秦苒脸热地推了她一把,“很疼!你有没有人性?”
两人回到客栈,秦苒刚坐下来,把肿起来的脚平放在椅子上,门帘哗啦啦一响,日光就流泻了一地。秦苒眯起眼睛,一道人影走进来,径直来到了她的面前。
秦苒想要将脚收回来,却不小心抻到了,疼得龇牙咧嘴。
林耐的脸色不太好看,他说:“你多大的人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天天加班到半夜,你的实习单位没问题吧?”
秦苒看着他。他似乎才剪过头发,短的发茬像是秋天里刚收割完的麦茬,在阳光下泛着晶亮的芒。
他迎视着她的目光,眉头仍未舒展,语气也带着生硬:“看什么?”
秦苒忍不住笑了:“看你的气质真像我老爹,开口就训人!”
他垂下眼睑,按了按她肿胀的脚背,语气软了:“还疼吗?”
“当然疼,不然你扎一下试试!”秦苒嚷嚷着,尽量不让语气里流露出甜腻和幽怨。
林耐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三秒钟,抬手用力地拧了一下她的鼻子。她“嘶”了一声,“你干嘛?神经病啊!”
林耐笑了,他的眼睛真好看,他说:“疼痛转移大法。脚是不是没那么疼了?”
秦苒忽然觉得心里泥沙俱下,掩埋了堤防,只剩洪流在澎湃、冲撞。她低垂着脑袋,为了不让林耐看见她的表情,她都快把自己折叠起来了。
好一会儿,她低声说:“你这气质太不稳定了!我爹每次训完人,都会给我买好吃的。”
林耐拍了拍她的脑袋,声音软得让她很想揍他:“我现在就去买。你想要什么?”
“牛肉干水果罐头辣条豆干蛋黄酥……”秦苒说着说着就哭了,一双手不受控制地攥住了他的衣襟:“我能要你的一个拥抱吗?”
她的眼泪落在他的肩膀上,抽抽搭搭地说:“你放心,我……不会上瘾的!就要这……一个……”
后来的两年里,秦苒再想起当时的情景,总感慨林耐生着一颗坚硬决绝的心。除了他有力的手臂和落在她耳际的深重呼吸,他始终不曾吐露半句承诺与妥协。
但奇怪的是,秦苒始终相信他所有未曾吐露的情感和誓言——就像相信一座山、一条河,像相信一整片星空的神秘与辽阔。它们就在那里,横亘着、连绵着,无止无息。
8
陪秦苒养伤的几天里,林耐似乎对“李言”这个名字发生了强烈兴趣。他坐在沙发上,手指一下一下地抠着扶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说:“这个李言啊,怎么也不来看看你?”
他暗戳戳地问着,又提议道:“哪天我们一起吃顿饭?”
“帮我撕开。”秦苒将一袋牛肉干扔给他:“你还真像我爸!我一提起哪位男生朋友,他就要请人家吃饭!”
“你扎的是脚,怎么手也不好使了?”林耐吐槽着,忽然心念一转:“那你提过我没有?”
秦苒摇摇头,忽然怔在那里:明明都是未嫁未娶的清白之年,他的名字为什么就成了不敢提起的秘密?
林耐像个忽然闹别扭的孩子,闷闷地生起气来,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她的房间。几分钟后,他重又开门进来,窗前桌前床前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终于停住脚步,又找不到更好的求和的办法,只好将桌上的水果茶递到她面前。
秦苒仰起脸,笑了:“凉了,不好喝!”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握着那个杯子转过身去,“我去给你冲一杯热的,等我!”
“林耐,你别走!”看着他的背影,秦苒脱口而出,只是他回过头时,她却又慌乱起来,补充道:“我不渴。”
他的目光里充斥着期待、失望、释然、悲伤,种种情绪缠绞着,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夜里月朗星疏,林耐扶她去院子里乘凉。坐在树下的藤椅上,她不太说话,目光长时间地盯着手机里的偶像剧,在充满槽点的情节里随着别人的快乐笑出了满眼泪花,也在别人的难过里泪光闪闪。有一次他收走了她的手机,秦苒觉得自己一定是受刺激了,才会说出那么没脑子的话:“你怎么还待在这里?林耐,你走吧!”
他愣愣地看着她,居然很认真地回答:“我请了一周的假,我不走。”
秦苒伸出手,“手机还我!”
他不给,两个人孩子气地对峙了一会儿,她将身子靠进椅背里,“好吧,我忍你一周!”
第二天上午,林耐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台轮椅,夸张地要推着秦苒出去遛弯儿。她不肯坐,他就自己坐了上去,“那你推着我?”
秦苒嫌弃地翻了个白眼,刚想转身往回走,就被林耐握住了手腕。他抓着她的胳膊,就像抓着一袋大米,将她强行塞进了轮椅里,“再闷在屋子里看偶像剧,你就哭长毛了。”
他蹲在地上替她整理裙角,她自言自语似地低声说:“我当然知道偶像剧都是假的,可是我的欢喜和难过都是真的。”
不知道林耐有没有听清,只将发顶留在她眼底。短短的头发,像一颗扎人的板栗。
沿着客栈旁边的石子路,他们一直走到了山脚下。路边有茂盛的灌木,树下野草丛生,枝枝叶叶的牵绊着。一处斜坡上长着两株结满红果的树,在阳光下鲜艳而光亮。
和沙漠上的初次交谈不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提起过彼此的未来规划了。这时,秦苒忽然问:“你们在野外会摘野果子吃吗?有时候会很辛苦吧?会想家吗?你……会想我吗?”
“会!”他言辞凿凿地答了。只是她问了几个问题,她不知道他在回答哪一个。
回来时他们吵了架。路上遇见了一只小黑猫,用滴溜溜的眼睛望着他们。她要抱,他不让,于是她像根炮仗似的一下子就炸了:“我非要抱!要你管?”
“你给我停下!”她站起身来,还踹了轮椅一脚。他低头看着路边石缝里鲜绿的苔藓,然后默默地转过身去。可是,那只小黑猫早被他们吓跑了。
林耐有些慌张,他的目光到处睃巡着,也没有看到黑猫的影子,等他回过神来,秦苒已经跛着脚走出了十几米远。
林耐追上来。他的眼底似乎有潮水席卷过了,正在无限退让。秦苒觉得如果自己再奋不顾身一点,大约便可以追上那片海,感受到真实的温热与咆哮。
可是,当轮椅的轮子与石板路重又发出平稳的碾压、摩擦声时,她听见身后林耐的声音:“我很难过。我害怕无论选择什么,以后都会后悔。苒苒,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折中的办法?”
秦苒没有回头,她说:“我害怕在等待中度过一天又一天,我没有那么伟大,用担忧和孤独来成全你的理想与热望。你说我狭隘也好,自私也罢,可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
“我同样自私,同样狭隘,又哪有资格指责你……”
三天后,林耐回校,一个月后,他出发去西北前,给秦苒打过一通电话:“我走了?”
“嗯!”秦苒的声音听起来响亮而健康,“下次回来记得给我打电话,请你吃饭!”
“好。”他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柔软,像个听话的小男孩。
她的难过和不舍于是又像被压在石头底下的细草,摇摇晃晃地钻出来,继而快速伸展得枝繁叶茂。她赶忙说:“就这样吧,我也要去忙了!”
9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里,他们之间的联系不多,像是默契地想要淡出彼此的视线。林耐似乎离理想越来越近,他加入了师兄带队的地理考察队,从照片上看,他穿着红色冲锋衣,戴着黑色登山帽,尽管她将照片放大再放大,仍旧捕获不到他脸上的表情。
盛夏,秦苒在考驾照。教练带着几个人一同上路练习科目三,其中一位学员开车上路时,另外几个人便在路边等。刚好刮了一阵风,将树枝摇得哗哗响,秦苒看着翻飞的叶子,猝不及防地想起了林耐。他在哪儿?是怎样的风日晴雨?
身边的女孩在向手机里的男友抱怨,好热好累太阳好大啊。秦苒掏出手机时,发现有一通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也是实在闲得无聊,秦苒将来电回拨过去,对方很快接通了电话,声线平稳温和:“苒苒,是我。”
秦苒怔住了。柏油路正在太阳底下发出难闻的气味,视线里的一切似乎都被蒸腾出了烟气与雾气,摇摇晃晃、迷迷蒙蒙,像是一场梦,却又分明不是梦。不远处,教练车正缓缓驶来,像是一艘船出现在烟笼雾罩的海平面上。她慌乱地说:“我还有事,回头打给你。”
接下来刚好轮到秦苒上车,受过伤的脚掌踩在油门踏板上时,曾经的痛感忽然柔软地再次袭来——那串电话号码,是属于林耐的啊!
副驾驶座位上的教练在说话,像是隔了一扇封闭的窗,听起来遥远而模糊。秦苒一直在走神,迟迟疑疑地踩着油门,完全掌控不好力度,忽地一脚踩得狠了,车子像青蛙一样弹跳了一下,继而猛地停下来,秦苒的脑袋撞在了方向盘上。教练刚吼了一声,她就把胳膊圈在方向盘上,接着把整张脸埋了进去。
年轻的教练气恼而又有些不知所措,他涨红了脸,说:“我不是骂你!”
秦苒抬起头:“车上还有别人吗?”
教练瞪着她:“你这个状态还是别练了,下车!”
秦苒的嘴角向下一撇,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扑簌簌落下:“凶什么?我要举报你!”
教练被她气笑了,他说:“失恋了?有什么想不开的?想要就再追回来呗!这一生那么长,长到足够试错,这一生又那么短,短得像是只有这一个夏天,虽然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穿着拖鞋和老头衫也没毛病,可是你说情侣装不香,还是婚纱不好看?”
秦苒觉得他说得还真有点道理。可是等她拿出手机,却失去了拨号的勇气,而林耐也没有再打过来。
10
又过了一年,秦苒家里的服装公司打算搬迁新址。在灯具城选购时,她流连于一款树枝型水晶落地灯,却矛盾于价位偏高且并不符合办公整体环境。一位高个子男人走过来,问她:“喜欢吗?给你打折。”
秦苒转过头,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她礼貌地笑了笑:“谢谢。”
“不记得我了?”男人笑起来:“我是当初那个差点被你举报了的驾校教练啊!”
“呀!你怎么在这里?”
“你喜欢的这盏落地灯,是我设计的!而在此之前,我总得做点什么养活自己。”男人笑容明朗,他说:“这里的灯具你随便选,保证最低价位、最优服务。”
她还没等说出客气的话来,男人又问:“你的男朋友,你们现在还好吗?”
秦苒笑了笑,轻轻地摇了摇头。
其实,秦苒几天前刚见过林耐的一张照片。是小敏发给她的,山脚下,林耐和他的师兄并肩站在一起,背景里的雪山遥远如梦境,连绵着耸入高天,汇入云深似海。
四个人,两样的情路历程,却收获了雷同结局——谁会庆幸?谁会后悔?
隔了很久,秦苒回复小敏:“希望他们平安健康,一切都好。”
秦苒搬进新办公室的前一天,灯具城的送货工人熟门熟路、不请自来地给她送来了一盏树枝型落地灯,枝丫伸展如鹿角,昂扬却又不失秀逸,叶片由水晶切割出棱角,折射着柔和雅致的光芒。她拨了一个号码,那人接电话的声音里带着笑意:“升级款,喜欢吗?”
她也笑了:“喜欢!”
那晚,秦苒终于拨通了林耐的电话。她笑着跟他说:“我搬去了新地址,如果以后你来的话,可不要走错了路。我挺好的,你也要保重。”
林耐沉默着,忽然问:“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还是那么了解她,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轻而易举地就会看进她的内心深处。秦苒仍旧在笑,她说:“放心吧。你知道的,我的眼光向来不差!”
“有一件事我还是要告诉你,上次打电话给你时,我正在国外生病,差点坚持不下去——想起来我还是会难过,你从来都没有挽留过我。如果你说,留下来,别走,我一定会动摇的……”
“可你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要不要跟你走……”
一阵沉默之后,他说:“保重,秦苒!”
他不再叫她苒苒了——“保重!”她答。
手指轻触,屏幕上弹出问询:确定删除联系人“林耐”?
确定?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