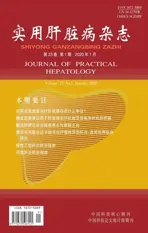肝细胞型胆汁淤积诊治进展
2020-12-09胡利琳王玮珺
胡利琳,王玮珺,杨 玲
胆汁淤积是由于肝内外胆管阻塞或肝细胞功能障碍所致的胆汁不能到达十二指肠而在肝细胞和血液积聚的一种病理学状态。肝细胞是胆汁合成和分泌的主要场所。当肝细胞上的胆盐输出泵(bile salt export,BSEP)、ATP结合盒(ATP-binding cassette,ABC)转运蛋白、多耐药相关蛋白2(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MRP2)功能障碍或受抑制,则可导致胆汁酸或其结合胆盐在肝细胞和血清中聚积引起肝细胞型胆汁淤积[1]。引起肝细胞型胆汁淤积的常见病因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感染、酒精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自身免疫性或药物相关性肝损伤、全胃肠外营养、重症相关(缺血性)肝内胆汁淤积、良性复发性肝内胆汁淤积(benign recurrent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BRIC)、进展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progressive familial intrahepatic cholestasis,PFIC)、ABCB4基因缺乏、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霍奇金病、转移性肿瘤、肉芽肿性肝炎和肉芽肿病、血管性疾病(如布加综合征和肝窦阻塞综合征)和各种原因的肝硬化等[2]。
1 肝细胞型胆汁淤积的“下降”病理生理学模式
在肝细胞型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疾病进展过程中,呈现一种“下降”或“自上而下”的病理生理学模式[3],即病变起始部位位于解剖学位置的上游—肝细胞,随着肝细胞内胆汁酸浓度的升高(尤其是疏水性胆汁酸浓度的升高)可直接导致肝细胞凋亡和坏死,最早出现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水平升高。随着病程的进展,凋亡和坏死的肝细胞可释放损伤相关模式分子,如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1,HMGB1)、趋化因子、活性氧等炎性介质,激活天然免疫(如 TLR9信号途径[2]),诱导中性粒细胞浸润和氧化应激反应,进一步导致下游的胆管上皮细胞受损,出现血清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ferase,γ-GT)水平升高及肝脏炎症反应。
2 常见的肝细胞型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特点和诊断
2.1 药物性胆汁淤积 某些传统的中草药,如何首乌、土三七等、膳食补充剂、天然药、保健品、生物制剂和各类化学药物及其代谢产物或辅料等均可诱发药物性胆汁淤积[4]。药物性胆汁淤积常由以下三类因素触发:(1)转运蛋白的改变,如转运蛋白的抑制、表达降低和(或)胆汁酸转运蛋白的亚细胞定位异常;(2)肝细胞膜流动性的降低、细胞骨架和紧密连接的破坏;(3)胆小管的扩张或收缩。上述改变诱导胆汁淤积,进而激活细胞的退化和适应性反应,细胞的退化反应以线粒体损伤、不同类型的细胞死亡,如凋亡、自噬或坏死、内质网应激、氧化应激及炎症为特征。细胞的适应性反应以激活大量的核受体阻止胆汁酸聚积为特征,常被激活的核受体包括法尼酯衍生物x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孕烷X受体(pregnane X receptor,PXR)等[5]。通常,药物性胆汁淤积有明确的用药史,多为急性发病,常在去除诱因后可快速消退。临床表现为黄疸、瘙痒和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受损表现,如纳差、厌油、乏力、恶心。部分病人可出现腹部疼痛、发热、潮红、皮疹,嗜酸性细胞增多等全身性临床表现。部分药物可引起慢性胆汁淤积,出现黄瘤、瘙痒、黑皮病等,和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相类似,但经治疗后通常可消退。药物性胆汁淤积的诊断是一种排他性诊断,主要基于详细的病史采集(临床特点和用药史)、肝脏生化学指标的动态改变,监测停用可疑药物后临床生化指标的改变及药物再刺激反应、肝胆影像学检查和肝脏活检。血清ALT、ALP及其R值(R=(ALT/ULN)/(ALP/ULN),正常上限值(the upper limit of normal,ULN))对于判断是否存在胆汁淤积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当R≤2或ALP≥2 ULN可诊断为药物性胆汁淤积。诊断所涉及的生化指标应以首次实验室检测值为依据[4]。
2.2 病毒性肝炎并发胆汁淤积 病毒感染后肝细胞出现炎症、坏死、膜结构和流动性改变,肝细胞对胆汁的排泌功能减退是病毒性肝炎出现胆汁淤积的可能机制。各型病毒性肝炎均可导致胆汁淤积,戊型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感染常引起急性淤胆型肝炎,临床症状较轻,常可自行缓解;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常导致慢性淤胆型肝炎,提示肝病出现严重进展或急性恶化[6],临床以黄疸、皮肤瘙痒、大便灰白、肝脏肿大、血清胆红素升高,以结合胆红素升高为主,伴有γ-GT和ALP升高。病毒性肝炎并发胆汁淤积的临床表现复杂,应根据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的动态变化进行综合分析,明确是淤胆型肝炎还是肝衰竭,并根据病原学检查结果明确病因。
2.3 酒精性肝病并发胆汁淤积 酒精性肝病是由长期大量饮酒导致的一大类肝损伤疾病,包括伴或不伴有纤维化的脂肪变性、酒精性肝炎(alcoholic hepatitis,AH)、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各类酒精性肝病均可发生胆汁淤积,且酒精相关性疾病,如慢性胰腺炎等,也可并发胆汁淤积样表现[8]。酒精性肝病相关胆汁淤积与酒精导致肝细胞肿胀、抑制胆汁酸转运蛋白活性或胆小管通透性增加有关。近期的研究显示酒精摄入能直接破坏肠道屏障,改变肠道菌群组分和功能,增加炎症细胞因子、内毒素进入肝脏,并增强胆汁酸合成和系统性炎症[9]。肠道激素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FGF19)水平与酒精性肝病胆汁淤积生化指标胆红素、GGT、总胆汁酸水平密切相关,可能是介导酒精性肝病胆汁淤积的重要信号分子。酒精性肝病胆汁淤积的诊断需要结合饮酒史(一般有超过5年的长期饮酒史,男性每日乙醇摄入量≥40 g,女性每日乙醇摄入量≥20 g;或2周内有大量饮酒史,每日乙醇摄入量>80 g,但应注意遗传易感性因素的影响)、临床表现(常缺乏特异型)、实验室检查,如AST、ALT、γ-G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平均红细胞容积(mean corpuscular volume,MCV)、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等指标升高,其中AST/ALT>2、MCV 升高、γ-GT升高是酒精性肝病的特点。酒精性肝病常并发胆石症或胰腺炎,因此常需要通过MRCP、ERCP等影像学检查排除有无肝外胆道梗阻[11]。少数疑难病例可进行肝组织活检,以明确病因和指导治疗。Maddrey评分(maddrey discriminant function,MDF,MDF=4.6×(患者的PT-对照PT)+总胆红素(mg/dL)可用于判断酒精性肝病患者的预后。MDF评分≥32为处于死亡的高风险,1个月内的病死率高达30%~50%,尤其并发有肝性脑病者将处于最高的风险状态。
2.4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intrahepatic cholestasis of pregnancy,ICP)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同时也是常见的可逆性妊娠期特异性肝病,通常发生于妊娠中晚期[12],与多个胆汁酸转运蛋白或核受体的基因突变有关,如MDR3/ABCB4、 ATP8B1/FIC1、 BSEP/ABCB11、FXR等。皮肤瘙痒是ICP的首发症状,最早出现于手掌和足底,通常于产后48 h内缓解,少数患者可伴有轻度黄疸,分娩后1~2周内基本消退。血生化检查显示血清总胆汁酸水平升高具有特异性,同时可伴有肝酶的轻度升高[14]。ICP的诊断也是排他性诊断。首先,需要排除引起瘙痒的皮肤疾病和其他的肝胆疾病,并且通过产后监测复查进行回顾性诊断。ICP诊断要点如下:(1)孕晚期出现无其他原因可解释的手掌、足底瘙痒;(2)空腹血清总胆汁酸水平≥10 μmol/L可确诊为ICP;(3)若胆汁酸水平正常,但出现无其他原因可解释的 ALT、AST、GGT水平升高,同时可伴有血清胆红素水平升高,以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IL)为主;(4)临床症状和血清学异常指标多于产后恢复。
3 各肝细胞型胆汁淤积性肝病的治疗
3.1 药物性胆汁淤积的治疗 首要治疗措施是及时停用可疑的肝损伤药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于2013年制定的停用肝损伤药物的原则如下:(1)血清 ALT或 AST>8 ULN;(2)ALT 或 AST>3 ULN,且 TBIL>2ULN或国际标准化比率(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1.5;(3)ALT 或 AST>5 ULN,持续2周;(4)ALT或 AST>3 ULN,伴逐渐出现的肝病症状如乏力、恶心呕吐、右上腹疼痛或压痛、发热、皮疹和 /或嗜酸性粒细胞增多(>5%)。符合上述任意一条则应该考虑停用肝损伤药物且该原则适用于临床药物试验中出现肝细胞毒性的患者。药物性胆汁淤积的治疗:(1)某些药物引起的肝损伤可尝试相关特殊药物治疗,如:考来烯胺散可治疗来氟米特引起的肝损伤、N-乙酰半胱氨酸(N-acetyl-L-cysteine,NAC)可有效缓解对乙酰氨基酚(paracetamol,APAP)所致的肝损伤等;(2)肝细胞保护剂,如甘草酸制剂、双环醇、多烯磷脂酰胆碱、S-腺苷-L-蛋氨酸(S-adenosyl-L-methionine,SAMe)、熊去氧胆酸(ursodeoxycholic acid,UDCA)等,可选择 1~2种;(3)在所有其他治疗无效时可考虑应用糖皮质激素,其可用来治疗药物性胆汁淤积性肝炎,但应权衡利弊及使用激素的不良反应。此外,对于失代偿期肝硬化和药物性肝损伤所致的急性肝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ALF)和亚急性肝衰竭(subacute liver failure,SALF)等重症患者,则考虑肝移植治疗[16]。
3.2 病毒性肝炎并发胆汁淤积的治疗 主要是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同时还需要针对胆汁淤积进行相关的治疗,但目前还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治疗原则以保护肝细胞、抑制炎症反应、改善肝脏微循环为主。异甘草酸镁是一种肝细胞保护剂,具有抗炎、保护肝细胞膜和改善肝功能的作用,是临床常用的肝细胞保护剂[17]。UDCA具有促进胆汁分泌、保护肝细胞、抑制肝细胞凋亡和免疫调节作用,可改善胆汁淤积引起的生化指标异常。SAMe通过膜磷脂和蛋白质的甲基化可以影响线粒体和细胞膜的流动性,而转巯基作用能增加肝细胞内还原性谷胱甘肽、牛磺酸及其硫酸根含量,可减少对氧自由基介导的肝脏损害,抑制TNF-α表达,从而减轻肝内胆汁淤积和肝细胞损害程度[18]。前列腺素 E1(prostaglandin E1,PGE1)可提高肝细胞内环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水平,拮抗血栓素,扩张小血管,改善肝脏微循环,促进胆汁排泌,减轻肝内胆汁淤积[19]。糖皮质激素可减轻肝细胞水肿,抑制肝脏组织炎症,激活核受体PXR,加快胆汁酸转运,快速降低胆汁淤积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胆红素水平,缓解瘙痒、黄疸等症状。对于急性病毒性肝炎患者不建议使用,但对于黄疸超过4周以上者,可考虑糖皮质激素的短程经验性治疗。
3.3 酒精性肝病并发胆汁淤积的治疗这种情况常常提示预后不良,且营养不良是其常见的并发症。因此,进行营养支持治疗是关键,如补充维生素B、维生素C、维生素K和叶酸,提供高蛋白低脂饮食有助于患者症状的改善。ALD的首要治疗原则是戒酒,但要注意在戒酒过程中发生酒精戒断综合征。对于不严重的酒精性肝炎患者戒酒通常有效。药物可选择甘草酸制剂、多烯磷脂酰胆碱、还原性谷胱甘肽、SAMe、水飞蓟素类、双环醇、UDCA等抗炎、降酶、保肝、降黄药物,但不宜同时应用多种抗炎保肝药物,以免加重肝脏负担和因药物间相互作用而引起不良反应[11]。美他多辛有助于加速血液中酒精的清除[11]。对于Maddrey评分 ≥32或MELD>20的严重酒精性肝炎患者通常预后差,如无应用糖皮质激素禁忌症,可考虑给予4周疗程的泼尼松龙治疗;在激素治疗1周后,应进行Lille模型评估疗效,Lille评分=3.19-0.101×年龄(岁)+0.147×白蛋白(g/L)-0.0165×胆红素(μmol/L,第 7天)-0.206×(有肾功能不全取1,无肾功能不全取0)-0.0065×胆红素(μmol/L,开始前)-0.0096×凝血酶原时间(s)。评分>0.45,提示糖皮质激素治疗预后不良,>0.56则提示应结束糖皮质激素治疗,评分<0.45则可继续完成4周的糖皮质激素治疗,然后减量维持2~4周或者停药[20]。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期间应密切监测肾功能和感染指标。对伴有细菌感染者,应及时使用抗生素[11]。对于严重的酒精性肝炎肝衰竭可考虑肝移植[20]。
3.4 ICP的治疗 治疗目标是:(1)缓解皮肤瘙痒症状;(2)降低血清总胆汁酸水平;(3)改善异常的肝功能指标;(4)合理延长孕周,改善ICP妊娠结局[14]。UDCA是治疗ICP的一线临床用药,可有效缓解瘙痒症状,改善ICP患者的肝功能和总胆汁酸水平、降低早产率、改善胎儿结局,推荐剂量为15 mg.kg-1·d-1,分3次口服[21]。EASL指南推荐UDCA用量为10~20 mg.kg-1·d-1。SAMe为临床治疗ICP的二线用药,推荐剂量为500 mg口服,2次/d或1 g静脉滴注,1次/d,疗程为12~14 d[22]。对于难治性ICP患者可考虑UDCA与SAMe两者联合治疗。此外,产前还可使用维生素K1以减少分娩时出血的风险。
4 肝细胞型胆汁淤积未来治疗策略探讨
目前,对肝细胞型胆汁淤积的治疗手段和疗效仍不令人满意。近年来,随着对胆汁酸肠肝循环调控机制和肠道菌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新药物不断涌现,部分药物已进入2期或3期临床试验阶段,已展示出令人鼓舞的疗效。这些药物包括:(1)针对胆汁酸受体配体的药物:包括针对FXR、PXR、维生素 D受体(vitamin D receptors,VDR)、G蛋白胆汁酸耦联受体(G protein coupled bile acid receptor,TGR5)、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α(peroxisomeproliferators-activated receptor-α,PPARα)等。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OCA)、非诺贝特分别为 FXR和 PPARα的激动剂,临床试验显示能明显改善UDCA应答差的胆汁淤积患者的生化指标[23];(2)FGF19模拟药物:如 M70(NGM282)可抑制胆汁酸的合成、减轻肝脏炎症和纤维化[24];(3)胆汁酸肠肝循环阻断剂,如胆汁酸结合树脂、尖端钠离子依赖的胆盐转运体(apical sodium-dependent bile acid transporter,ASBT)阻断剂(A3384、GSK2330672)可减少有害胆汁酸的肠道摄取,改善胆汁淤积[25];(4)钠离子-牛磺酸共转运多肽(Na+-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NTCP)阻断剂可减少肝细胞摄取和排泌胆汁酸,降低胆汁酸介导的炎症反应[26];(5)新型胆汁酸,如norUDCA是UDCA的同系物,较UDCA侧链少一个亚甲基,可抵抗牛磺酸和甘氨酸的结合,易被胆管细胞重吸收回肝血窦和肝细胞,而促进胆管细胞的排泌作用,具有抗增殖、抗炎和抗纤维化作用[27]。牛磺酸熊去氧胆酸(taurine ursodeoxycholic acid,TUDCA)是UDCA的牛磺酸结合物,具有抗肝细胞凋亡、抑制内质网应激作用,对胆汁淤积亦有改善作用[28];(6)调节肠道菌群的治疗策略。肠道菌群是调控胆汁酸代谢的关键因素,而胆汁淤积又可导致肠道菌群的功能和组分改变,并促进某些肠道菌群或其代谢产物、毒素进入肝脏,加重肝损伤和胆汁淤积[29,30]。因此,通过应用抗生素,补充益生菌或益生元/合生元,或粪菌移植恢复肠道微生态可能是未来治疗胆汁淤积性肝病的新方向[9,31]。近期研究显示肠球菌促进酒精性肝病进展,而特异靶向Cytolysin阳性肠球菌的噬菌体能缓解小鼠酒精性肝损伤,但还需临床试验证实[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