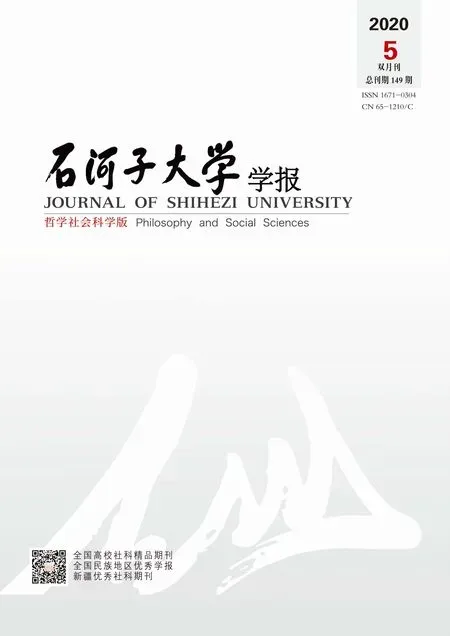一个人的文学自传
——论周涛《西行记》
2020-12-09雷小娟
郑 亮 ,雷小娟
(1.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2.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周涛于2018年2月在《当代》发表《西行记》,2019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应该说,这部小说是周涛不断突破自我、延展自我的表现,从诗人周涛到散文家周涛,再到小说家周涛,所体现的是作家在文体层面对自我创作的新要求,或许对周涛而言,只有以长篇小说的方式,才能够将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也即是青春时代的经历和盘托出。相较于《吉木萨尔纪事》《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伊犁秋天的札记》等散文,周涛将小说的背景放置在南疆城市喀什之中,之所以取名为《西行记》是因为西是没落荒凉之极,而向西的路于他们是极为遥远和艰难的,同时也是仅有的和向上的路。在时间上,周涛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选取了1972年至1979年这八年时间,通过回忆的方式记叙在此历史背景下几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的成长,以各自不同的遭际来表现时代和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也表达了对历史的关注和反思。“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1]63。结合《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可以发现,他在其中提到的喀什八年经历在《西行记》这一虚构作品中得到了拓展,作者在楔子中也非常认同郁达夫所提到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在这个意义上讲,《西行记》也就具有了自传的性质。菲力浦·勒热纳在《自传契约》中认为自传和小说一个相较于另一个而言更加真实、深刻,“具有揭示作用的是两类文本所同属、不为任何一类文本所独有的空间。通过该方法所获得的这种立体效果,就是为读者创造一个‘自传空间’。”[2]139如此,周涛的口述和小说为解读其喀什八年的经历和心境提供了可资互参的文本,我们对主人公在喀什八年的困境中对传统文化之“根”的追寻、对美好人性的坚守以及如何维护理想的光辉便可进行很好的诠释。
一、对根的追寻:人生困境中的精神依托
许子东在《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中认为,“文革小说,并不意味着一部小说要描述文革的全过程,或者小说情节全部发生在文革期间,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历史研究,很难找到小说严格从1966年写起到1976年结尾”[3]9。基于这种看法,周涛在《西行记》中对1972—1979年的文学叙述,也可视作“文革书写”。1940年代出生的周涛对文革有着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在被分配到喀什之前,他曾在1971年的时候到伊犁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军营式的管理与校园的舒适环境天差地别。1984年,他在散文《巩乃斯的马》中忆述那段时期:“第一次触摸到了冷酷、丑恶、冰凉的生活实体。……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打击我对生活的热爱,精神上的压抑却有可能摧毁我的信念。”[4]82而如何阐释这段距当下已经四十多年的喀什生活时光并对其加以反思和评价,则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考。周涛借助《西行记》中的“姬书藤”完成了他对文革的思考,“他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5]191。作为自传性质的小说,姬书藤作为故事的在场者和当事人,可以更直观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而这和作者对世界的感悟、人生经历、价值观念密切相关。作者笔下姬书藤的境遇一开始便有了造化弄人的意味,刚结束部队农场生活,就又被迫西行至完全未知的地域,感受到了来自于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的双重变化和压迫,有了外在的被沙漠彻底埋葬的恐惧,以及内在的归属感的丧失。“一两分畏惧,两三分好奇,三五分沮丧,七八分茫然,十分失落和痛苦”[6]16的心境,与小说开篇两人呆立荒野的背影相互呼应。
历史语境剥夺了主人公对人生道路的自主选择权。由于时过境迁,姬书藤从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变成边远土城的落魄文人,原先借以肯定自我的“贵族”意识被迫隐失,找到重新确立自我价值的依据成为当务之急。他的处境可谓举步维艰:父亲在文革中“失去”党籍使他的入党之路遥遥无期,担任体委乒乓球队教练不过是一时之计,想要摆脱不堪的现状却又无能为力。这时,“写作”成为姬书藤自救的选择,“他准备靠这一手突出绝境”[6]46,写一部有关石头怎么长大的长篇小说。与之相伴随的,就是他逐渐认识自我并探索人生之路的艰难旅程,在自身的经历中不断成长,对所处时代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也开始寻找自己精神上的依托,对根的追寻。
在这部小说中,“根”的含义有两重,一是对故乡的眷恋和追寻,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重返与借用。而后者往往成为主人公克服前者所带来焦虑的有效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群体应时代征召离城别家,投身基础事业建设或接受“再教育”,生活环境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于是将目光转向了故土,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家乡,以此来寻求到归属感,“思乡”成为他们最常有的情感体验。作为自传体小说而言,故乡对于姬书藤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他来讲,十八岁以前生活的地方,便成为了他永远的故乡。虽然在不断地变换居住的地方,但人的记忆却很难迁徙,它一直盘踞在从前生活的地方不愿离开。喀什虽承载了姬书藤最可贵的八年青春,但他乡非故乡,这段时光于他就是“一场大梦”、一个过渡,他对这个成就了自己人生大事——结婚生子的地方虽无强烈排斥和憎恨,却也并无半分留恋,他坚信自己的根在“钢蓝色的博格达峰守护的蓝天之下……才是他的摇篮、故宅和归宿”[6]196。同样的,小说中另一个关键人物成志敏虽热爱政治,却也深深渴望回到家乡赵庄的土地上,深怕埋骨异乡。“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传统文化心理使他们只有在故乡或是对故乡的回忆中才能寻求到归属感。
当身体的位移导致家园失落,随之而来的常常是身份焦虑和文化困境。“知识分子总是企图用‘单纯’的思考去征服敌对的现实,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沉湎于想象之中,人们便可以寻到归属或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在思想上征服现实。”[7]68姬书藤应对现实难题的方式是重返历史与传统文化。他借助传统文化典籍,在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筑起围墙,去构建一个理想中的精神世界,渴望回归历史和传统,借优秀的传统文化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使自己逃离“平庸也平静,无欲也无望”[6]50的生活,并以此实现精神的还乡。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此与世隔绝,看似“不合时宜”的古典主义追求恰恰也是姬书藤伸出围墙的触角,替他感知当时多变的社会气候和身边人不同的生命态度。他能借欧阳修的《秋声赋》认识政治局面动荡最为剧烈的1976年,看到古今时局的共通之处;以“运去黄金褪色,时来黑铁生光”[6]20的儒家传统命运观认识环境对人的重要作用;用“时不利兮骓不逝”来概括文学理想缺少天时地利就难以实现的事实;还把苏轼《留侯论》中“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人生态度作为判断成志敏斤斤计较的依据。往哲先贤成为姬书藤规范自己和评价他人的道德楷模,也为困境中的他指引生活方向。他每遇挫折就会想象他们如若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如何面对和解决,从而为自己找到避风港与精神依托。姬书藤向传统纵深处挖掘的姿态,可称之为“寻根”。
说到“寻根”,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知青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寻根文学”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对传统文化之根脉的回溯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坚守。《西行记》中沉浸于传统文化并以此为自身文学创作重要根基的姬书藤,先行一步汲取了精神养料,这种表面退守心灵的态度实则为其以后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即坚守自我。这也是小说之外作家周涛的选择。周涛以独立的创作姿态进行着文体与主题的持续探索,小说包纳了“乡土”“反思”“寻根”等等因子,其中所体现的对故乡的眷恋及传统文化的追寻,是在面临人生困境时的精神依托。而随着阅历的增加,他对现实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不断加深,处事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变化则体现出他对人生的态度和思索。
二、生命的自省:人怎样在岁月中显影
“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描写人及其情感、灵魂和精神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积累人生阅历与洞悉世态人情,尤其是形形色色、面目迥异的‘人’,往往是小说家最好的启蒙老师。”[8]65初试小说的周涛,也曾在学习识人和识己的路上历经坎坷。他出版于2011年的散文集《冬日阳光》正是一本“识人”的书,其中描写了几十位形色各异的人物形象,而这些描写又建立在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和与描写对象的长久相处之上。回望自己人生青年阶段,对自我内心深处的关注和发现以及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思索,透过自己的真实阅历来反映当时的生活更能体现其真实性。他在《人是怎样在岁月中显影的》认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有比较明显的关于文艺或体育方面的特长的话,在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方面是易于盲目的。这描绘的何尝不是擅打乒乓球又热爱写作的姬书藤?作为地委大院新来的青年人,他丝毫不懂人情世故,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地轻易评判别人,导致了许多误解和冲突。但屡次碰壁之后,他也开始与社会进行磨合,对现实的自我进行总结,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不足,不断地适应和改造,在谨慎观察中逐渐探索着与周围人的相处模式,在岁月累积中发掘他们身上逐渐显现出来的特质。
姬书藤面对的人多是军队老领导和单位机关干部,他们教会他如何“对待他人”。认识屈铭,他经历了初始的盲目崇拜,意识到对方并不肯定自己后的疏远,再到与之就文学话题倾心交谈后的五味杂陈,最后是深切的同情。理解程墙,他则经历了初见时的龃龉、长期的仇视,到对其谨守诺言的由衷钦佩,再到得知其跳崖自杀时的深切哀伤。了解成志敏,则是从初见面时的交锋,仔细的剖析,再到建立相互欣赏与合作共赢的关系,最后是自然而然的分道扬镳。结识司马义,则是从初识时替己受过,认为他人好不隔心,在工作中再次相遇,逐步见识到他由普通到爱好学习、尊重文化、为人谦逊等优点的显现及人生格局。“人是怎样在岁月中显影的?……往往不是那些明显的特征造成,而是那些不易被发现的品质逐渐成长发展的结果。”[9]1他发现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也有不同的长处,对于符合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可以学习借鉴,而那些违背自己原则的,虽无法阻止他人,但可选择洁身自好,在我们无力改变社会的大环境的情况下,也要坚守自己的人性不被改变。后来的姬书藤已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在屈铭遭到批判时能不为局势所动而保持沉默,得知程墙自杀后能设身处地感受对方如弃世者一般的悲凉,获悉文远之死于非命后的悲愤、百感交集。这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也源于他对生命强烈的自觉意识,对于逝者生命的惋惜使他意识到生命的可贵,也懂得了什么是人生。至于地委大院中的大多数人,则更像那因误判而导致马匹在绝望中坠亡深渊的车夫,由于自己同样的失误而将孩子烫伤留下终身烙印的邻居,自恃相貌英武却无知无畏的管教,以及那些在特定时期烧书而后又排队买书的大众,他们被时代所囿,缺乏自我独立的思考及对生活的预判能力,只能被动等待命运的安排。就像这部小说一开始的名字“混沌初开”,在姬书藤眼中,他们构成了黎明到来之前最黑暗混沌的背景。
相较之下,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则始终保持着善良的人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男性的救赎者。庄延独具慧眼,沉着谦逊,既能在姬书藤落魄之时欣赏、接纳他,又能主动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以性格和能力上的互补助他前行;赵菊香有大地之母的气质,朴素实在、不慕名利,使丈夫成志敏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本;叶秋大胆热烈、充满活力,对屈铭的爱情让她甘愿付出一切;陈小柠则聪明精干、颇具识人的眼光,竭尽所能保护朋友不被迫害。这些“永恒之女性”都践行着朴素的生活哲学,显示出大地般的坚韧和宽容,同时也塑造并完满着包括姬书藤在内的男性。
至于如何“对待自我”这一功课,姬书藤则是在两次遭遇并化解人生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一次关乎思想改造。因为和程墙一次不合时宜的谈话内容,他被告发审查,往日的盛气凌人只剩下方寸大乱。好在有成志敏的及时指路,他开始在连续写检查的过程中彻底剖析和建构自我,最终实现了一次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蜕皮”重生。他终于认识到灾难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也明白“自己是不适合从政的人了……书生之见,总不能为世用”[6]166。这一过程虽然艰难,但既无抉心自食的剧烈创痛,也没有对自我信仰的强烈怀疑。另一次磨难则来自肉体。姬书藤刚刚收到小说见刊的喜报,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生子危机,这对一个在繁衍后代上有着巨大渴望的男性而言,无疑是重大的打击。认为在自己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却备受折磨煎熬,但在妻子的劝导下,姬书藤开始遵照医嘱疗养身体,并从这一危机中对“人”之本能和欲望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历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渡劫后,他实现了对个体生命的自省,对自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在状写文革中青年知识分子命运的文学作品序列里,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视点,有王蒙小说中《布礼》式的自我分裂和挣扎,也有张贤亮作品里“许灵均”型的极端压抑和自我怀疑,哪怕到了新世纪,苏童的《河岸》中依然有主人公为证清白的自我阉割。相对照下,《西行记》这种看似“轻盈”的描述让我们得以窥知文革的集体记忆在个体身上呈现出何种不同,也对生命状态进行深刻的自察。时代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周涛审视的正是历史大事件边缘上的小人物。他们形形色色人生状态的“显影”,让这部作品在传统的“伤痕”“反思”范围之外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通过对生命的自省及自我深入的剖析和对他人的不断认知,对人性有了自己的思索,感受到了对于人性坚守的重要性,也逐渐认识到了人各有志,由于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人们的理想是有差异的。
三、理想和现实:作为文学自传
“从我20岁开始,就认定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完成自己的一生,需要靠的船是文学。虽然是个小破船,但它能帮助你走过一生。”[10]周涛如是言说他的文学志业,姬书藤也正是他的代言人,他将历史时代背景与个体的理想融合在一起。不过,“认定”之前,姬书藤也经过了长久的探索,看到自我与外在环境的矛盾及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经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感悟,呈现出特定历史境遇中个体的成长历程及身心变化。除了那次转折性的“蜕皮”,文中多次出现关于人生选择/理想的讨论。第一次是与屈铭探讨如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看待文学理想。第二次是和成志敏谈论何谓文学与政治,什么人适合从政或者从文。第三次则是与王镰分析是否在文革结束之后选择考研以重寻出路。姬书藤的文学理想也正是在这些思辨中逐步明朗的,他认为没有理想的人生不能称之为人生。小说接近尾声时有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乒乓球友谊赛,与小说开头的体委教练不同,这场体育比赛让他最终确定:精神独立的文人才是他永久的崇拜者,从政只是短暂而不切实际的幻梦。他坚守着思想上的自由,认为人是靠思想站立着的,无法抵达到人的精神深处的活动,都不值得当作毕生的事业。姬书藤确实也做到了对理想的坚守,在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和军区创作组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人物性格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他自己的情致所显示的力量和坚定性”[11]307,姬书藤这一人物的性格魅力也正来自于他对文学理想最纯真的热忱。“一灯可亮千年暗室”[6]239,一灯也可照人前行,周涛的文学创作之途也正始于这个关键抉择,甚至在《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中提到如果有文学才能的话,下辈子也坚持干文学。
遭遇困境的“文学青年”形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从不少见,文革中更是充满了需在政治“大我”和文学“小我”之间作出取舍的痛苦身影。不过,“文学”在姬书藤的人生中并不担负排解家国忧患、重塑国民性格等重大使命,而仅作为一个普通人借以在困境中坚守人性和抵达理想的涉渡之舟。那么,又是什么东西使文学这艘船安然航行、不至沉没呢?
第一,源于他富有理性和智慧的人生观。何谓“人生”的成功,周涛有独到见解,他认为“人生要有战略思维,必须有战略思维才能打赢。”[12]应该将历史时代背景与个体的理想融合在一起。他毫无掩饰地对自我进行剖析,非常坦率、真诚地书写出自己的切实想法。姬书藤的“战略思维”主要就体现在既有文学理想的高蹈,又立足现实因素的考量,即在缺少天时地利时努力争取“人和”。这点在他对待婚姻的态度上尤为明显,正与选择庄延作为伴侣一样,周涛也在口述自传中坦承自己对婚姻问题有着“政治考量”——他并不信奉爱情,只是通过出身好、社会地位稳固的家庭关系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姬书藤对人际关系的思考也非常现实,离开喀什之前,他对在此地建立的“友谊”并无不舍。这些实用主义的想法与他“无功利”的文学梦看来很不协调。然而,相对于特定历史时空带给人的现实困顿,“人文理想”的过度张扬反而显得不切实际。
第二,便是他的“弱者”姿态。在他处于人生的低谷、困境时,随着对社会的认知加深之后,慢慢意识到自己对于现状的无能为力,对政治的认知方面更是不足,越来越清晰的自我认知使他选择用弱者的姿态来感知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用心来感受现实社会的“文人”,在现实生活稍不顺意,便缩回自己的白日梦里,用想象建构一个旁人无法探知的虚拟世界,蛰伏其中不断地演绎、推翻、重建。这较之他身边的人就显得十分消极。然而,热爱文学的屈铭不知自己缺乏天赋,终究默默无闻;官运亨通的柳司理遭人刺杀,重伤在床;曾经的风云人物程墙身陷囹圄,最终生死未卜……从这些“强者”的命运中,姬书藤看到了人生的变与不变,也选择了自己的永恒文学理想和瞬息处事策略,在时代环境下依然坚守着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
第三,则是南疆喀什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的影响。这座偏远之城远离内地,有着质朴的城市性格和多民族文化浸润下的多元样貌。无论是世外桃源般的小巷庭院、独具一格的“毛驴列车”、别有风味的维吾尔族美食,还是富有民族风情的乐器、十二木卡姆、刀郎文化,抑或是醉汉阿不都克里木这样憨厚挚诚的居民、成为全疆第一个女子乒乓球冠军的维吾尔族姑娘、下乡考察时村民的礼节……都为这段原本失意的生活增添了动人的颜色。此外,存在于地理和心灵上的“新疆时间”也延缓并减轻了政治风暴的冲击,沙漠是“死亡之海”亦是“生命之源”,文革中一切激烈的场景在这里更像是慢动作播放,痛苦的思想改造变得相对容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因同命相怜而更多同情和体谅。新疆给人们“一种脱离时间的可能。一直向后走的可能”[13]48,这也与姬书藤对传统文化的回溯姿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由上而观,文革之后的新时期不但不会使他不知所措,反而赐予他天时和地利。他对于自己的处境也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想要的是对于独立性和个体性的追求,所以当王镰考研、哈皮升迁、屈铭上访……周围人拼命为各自的前途寻找出路时,他也迎来了自己命运的转机,他回城之途上几乎顺风顺水,没有经历任何强烈抗争便迅速找到了自我站位。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独立与思想上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经历和遭遇就是他的资源,发表作品、参加改稿会,得到著名作家徐迟和曹禺的认可和称赞,在新疆文坛初露头角……“他的身体,他的生命,像弹簧一样被整整压制了十个年头。现在,他觉得可以释放积蓄的能量啦!”[6]155严冬后的惊雷唤醒了蛰居的姬书藤,之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失落,看不到人生转机的迷茫一扫而空,个人的心声立时融入了新时代春天的宏大主题之中,在小说的最后,他终于拿到了自己创造的《石头是怎样长大的》样书,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转变看似突兀,实际上有着坚实的依托。除了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也正是文学和政治开始走入“蜜月期”这一时代特征在个人身上的印证。我们知道,作者周涛也正是在进入军区创作组之后以诗为旗,以散文为翼,直至收获文学志业的累累硕果。
“西行”的故事由此告一段落,作为作者几十年后对已逝岁月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在喀什八年的生活经历和心境变化,而这又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透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展现了具有个人化特征的对于文革时期的文学书写,在经历了人生困境、自我迷茫困惑后,如何保有真实的自我,保持对自我理想的坚守;同时也展现了作者对于走出文革的一代青年如何应对时空暌违带来的不适和彷徨,找寻新的人生之路的一种思索。这样看来,在作者笔下最终得以加入军区创作组走向创作之路的姬书藤,借助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等内在的精神依托来面对人生困境,并通过自我的不断成长完成对生命的自省,坚守理想,以自我人生信条为范导的人生态度,确实为解决这个人生难题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涛在七十多岁时,得以完成自己多年的理想,用最能承载丰富内容的长篇小说追述自己“西行”的精神历程。《西行记》作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看出其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喀什作为中国最为偏远的地方,在文学上受到的关注较少,作者对自己生活过八年的喀什进行了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描写,同时着眼于喀什的城镇与乡村,从侧面展示了不同的喀什形象。通过对“文革”的书写和自我剖析,挖掘出背后的深意,而青年姬书藤,正是“从无路之路中走出来……改变了命运”[6]3。周涛的文学自传将个人经历与时代相融合,为在文革中度过青春岁月的一代人增添了更加丰富的生命内容,也为周涛自己始终葆有少年锐气的人生做了精彩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