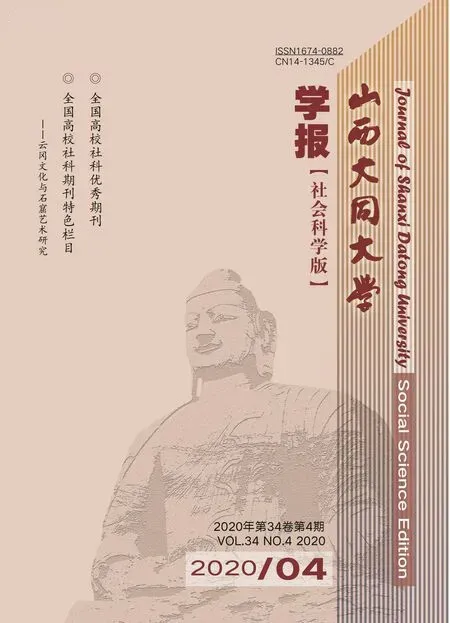钱锺书小说创作中服饰描写的文化批判意味
2020-12-09马桂君
马桂君,刘 莉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服饰,原本的范畴属于基本生活层面,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负载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功能。原始时代的御寒蔽体等对身体进行保护的实用功能已经弱化,而其代表个人的地位、职业、文化选择的内涵愈则加复杂。对现代社会的个人来说,服饰是展示自己第一性的直观语言,从服饰中可以判断出个人的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及文化心理等等。服饰的朴素或奢华、简洁或繁复,实际上寄托了主体对自身的设计或者理想定位,并强调出“我”与他人的差异。所以服饰可以作为一个符码,来实现所有者和关注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实现双方的文化定位和判断。
沈从文曾说:“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1](P491)作为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内容的第一要素,服饰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决定了文学对人物和生活的描摹是缺不了这一项的,而对女性服饰的关注尤其值得重视,通过服饰能够呈现出叙述者基于时代和文化的视角和立场。相应的文字描摹,叠加上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作家的个人风格、语言、文化选择,在文学中表现出各具特色的服饰书写景观。诸如张爱玲笔下的旧摩登女性风采,庐隐的五四新女性露莎们的穿着气质,萧红在艰难生活中对漂亮衣服的喟叹……
钱锺书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两方面都有很高成就,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融汇通达。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横纵坐标上,他能够以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统领,加入现实的思考,表现出清醒的民族意识和深刻的世态洞察,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通共进方面,起到了联接作用。他既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也犀利地指出其局限性和封闭性;既看到西方发达社会的文化优势,又能站在精神的高处自由嘲笑欧美中心主义思想。在其代表作《围城》及短篇《猫》、《纪念》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钱锺书文化批判的特点,即谐谑揶揄,举重若轻,将人们生存中可悲可笑的细枝末节尽展笔下。这样的文化优势源自钱锺书犀利的眼光,和对中西文化深入精当的把握。渊博的学识配合上独到的眼光,辅助以巧妙的联想,信手拈来的轶事典故,不管是世态风俗还是人情世故,都被他提取出来进行评判,诙谐自如,又能发人深省。
钱锺书在人物的提炼方面与一般的小说创作路径相反,即从面到点,而非从点到面。尤其是在对女性及其服饰的表述上,钱锺书从整体俯瞰,然后惜字如金地点出在服饰涵盖之下的人物的内在神韵。
一、通过对服饰符号化的概括对主体精神心理进行嘲讽
张爱玲说过,在她的小说里,不仅是人物的面目,甚至他们的姓名,都有现实的人物特征作为描写的依据。王安忆也表达过类似的经验,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就算是虚构的人物,也要有实在的相貌体态,才能推演出符合其性格特征的生命过程。安德烈·纪德小说中一个人物这样说:“我已念到第三十页,但竟不曾发现一种颜色或是一个描写的字。作者在讲一个女人,但我连她穿的衣服是红色还是蓝色都不知道。在我,很简单,如果没有颜色,我就看不到什么。”[2](P5)这是一种普遍的经验。在现实生活中与文本中一样,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可以从中窥见人们的心理定位和欲望倾向。其特有的色彩、纹样、体式,既能体现个人的审美喜好,又彰显主体的心理和欲望。服饰从小处说可以表达个体的精神追求,从中可以窥见人的情绪、态度、喜好等;推及到大的文化历史语境,又可推演出一定时段历史文化的具体表征。
男性作者,从社会性别角度看,自然有像茅盾、郁达夫那样对女性的服饰、身体表现出露骨的欲望心理之人,将服饰描摹呈现在作品中成为后来文化分析的材料。但是钱锺书非此类型,由于过分优越的文化心理的缘故,他对人的观照总是直接透到骨子里,外在这些皮相的东西,就成了熬药炼丹剩下的渣滓,只是作为言说的路径,目的地却远非在此。正像他在《围城》的序言中所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3](P1)即使是虚构的人物,要传达的仍是作者的心理分析。在钱锺书的视点里,就算他(她)穿了衣服,也不算是穿衣服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其比较稀少的表现骨相的材料,分析钱锺书怎样透过他只是一瞟而过的点滴服饰,发挥高超的心理刻画和讽刺才能,对人物进行精神嘲讽的。
作为知识分子视点的文化批判小说,《围城》着力表达了作者站在文化制高点上,对人生细致入微的观照。文本不以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为胜,人物成了作者暴露和调侃的靶子,于是在蕴含着浓重的人生悲剧性的轻松笔调之下,民族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对表象简略至极的文字描写中,服饰的描写竟然占了不小的比重,其中的折射出的性别心理和现代精神意识具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故事以海上归途景象开始:“那个戴太阳眼镜、身上摊本小说的女人,衣服极斯文讲究。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那男孩子的母亲已有三十开外,穿件半旧的黑纱旗袍,满面劳碌困倦加上天生的倒挂眉毛,愈觉愁苦可怜。”[3](P2-3)
在小说的一开始,浓重的戏谑气氛便升腾起来,卑怯苟且,借女人和别人调情,自己占小便宜的外国男人;口头上一片赤诚,为纾解乡愁奋力打麻将的中国男人。在这样荒谬的背景衬托下,不适合出演正剧。确实如此,中国的女性出场——那个不算是小孩子的妈妈, 就算是随丈夫到欧洲陪读,依旧是一个未经改造的旧式女人,思想狭隘,目光短浅,刻薄世俗。这些印象,从她半旧的黑纱旗袍、局促的眉眼、絮叨抱怨中即可了解。另一个貌似是新派,因为带着太阳眼镜,她的衣着只是笼统的印象——斯文讲究。根据当时的审美风气,讲究的服饰是加入一些西式元素改良后的中式,所以应该是质地精良、样式新潮的旗袍。苏小姐不是不好看,是不够性感有型。皮肤干燥苍白,嘴唇过薄,身材比较干瘪,无曲线,所以整个人比较显老气。这样一个从西方审美角度看僵硬无趣的女性,其实在中国的传统视角下,薄嘴唇、眉清目秀的她还是比较有风致的。因为中国对女性的审美不是现实型,而是抽象型,不要那么肉感,触目惊心,要淡定平和,有写意画的韵味。悲哀的是,投向苏小姐的眼光,都是经过西方文化改造后的混合口味,她自己的出洋经历,也不能给她添加信心,更何况马上就有对比物出现干扰她。这样两个女人,一个是永远被生活拖累在深渊中,只剩下刻毒的抱怨;另一个貌似以学问做背景,精神有所超越,但事实却未必。
时髦新潮的性感尤物登场了,“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在热带热天,也许这是最合理的妆束,船上有一两个外国女人就这样打扮。可是苏小姐觉得鲍小姐赤身露体,伤及中国国体。”[3](P5)作者比较公允地道出,这样的装扮在热带完全正常,但是苏小姐认为作为女人暴露了身体,便会伤及国体,足见她对鲍小姐这样无顾忌表现身体而出风头的嫉恨,也不经意地展示了苏小姐精神意识中那些迟滞于时代的传统积垢。那些对鲍小姐意淫连连而需要遮掩的男人,却要通过讽刺批评表现自己对其不屑弃绝来纾解自己的欲望。扭曲的心理症候及狭窄的释放通道,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熏染后,并未有所改观。人的精神无法释然超越,只是多了调侃掩饰的渠道,这是知识世俗化的悲哀。
说起苏小姐对鲍小姐与方鸿渐调情的反感,作者这样交代苏小姐和方鸿渐关系的来由:“在大学同学的时候,她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那时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3](P12)研究法国文学要写中国白话诗的论文,这样的女博士何其可笑! 作者把她的一份春心比喻成过分珍惜而错过时令的衣服,那种叹惋大概女性会很理解,但是作为男性的讽喻却是很有批判性。衣服最重要的功用是展示,所以花色和样子是其存在合理性的标志,而不是要蔽体保暖的实用功能。女性的婚姻定位也和衣服一样,其实用性要求不如虚荣心来得重要。现在如同过时的旧衣服一样,苏小姐的情感寄托完全无用武之地。
不过苏小姐完全不用这样沮丧,方鲍之间貌似火热的情感游戏,由于女主角抵达目的地戛然而止。“鸿渐回身,看见苏小姐装扮得袅袅婷婷,不知道什么鬼指使自己说:‘要奉陪你,就怕没福气呀,没资格呀!’他说这冒昧话,准备碰个软钉子。苏小姐双颊涂的淡胭脂下面忽然晕出红来,像纸上沁的油渍,顷刻布到满脸,腼腆得迷人。”[3](P23)又是很具写意风味的概括“袅袅婷婷”,东方式的审美意蕴,于是在落寞情绪中的方鸿渐,也看到了苏小姐羞涩可人的韵致。本来高傲的苏小姐,眼里并没有过方鸿渐,但是由于现实紧迫,时光不待人,就算是女博士也要放低身段,不计前嫌,努力自我推销。当然方鸿渐无力拒绝送上来的好运,这是他的弱点。不知道是因为怕伤害人,还是骨子里的怯懦,有点聪明才华,但是才情还没到足以支撑他睥睨一切的程度。他既不敢大胆主动追寻自己心仪的对象,又不敢直截了当拒绝无感的异性,这也是他后来进退维谷,永远处于失意境况的根本原因。
带着苏小姐伴行的微微得意,方鸿渐走出归乡的车站,“但看人家这样郑重地当自己是一尊人物,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他才知道住小地方的便宜,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3](P32-33)虽然羞愧于伪造学位之事被公之于众,但是源于海归博士名头而受人瞩目,还是让方鸿渐的自尊心膨胀起来。这自尊因为缺少内在精神的有力支撑,需要依靠外在的物质条件——新一些的西装。
方鸿渐表现出的是典型的精神贫困症状,所以要讲究衣着。接下来的相亲失利没有令他在意,赢了钱便兴冲冲地入手了想念已久的外套:“方鸿渐因为张先生请他早到谈谈,下午银行办公室完毕就去。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獭绒西装外套,新年廉价,只卖四百元。鸿渐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3](P41)奢侈品的实用功能已经被其背后的社会暗示所取代,它可以证明穿着者的社会地位——有地位、有财富、有品位。精神充实到强大程度的人,完全可以忽略衣服与衣服之间的差别,在他们眼里,衣服就是衣服,而不是其他的种种社会定位符号,他们有能力给自己定义。而方鸿渐像女人一样对衣服的材质功用及文化符号左右衡量,抵抗不了拥有的欲望,因为衣服可以建立起他那足以让不知情者仰视的上等人形象。
二、通过服饰选择的困境表现人物的心理困境
如何界定服饰是否合体合宜,很简单的一个标准是穿着者与服饰互相彰显,能够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正如一个纺纱女工最好看的衣服是简便轻捷的工作装,而一个外交官更应该衣冠楚楚、器宇轩昂,弹古筝的女孩适合古风衣饰,快节奏下的白领适合西装。在文学对人物的表现上,服饰的不合时宜,一定程度上投射出被描述对象的精神和心理困境。
依旧回到《围城》里,不管是苏小姐还是唐小姐的机会,方鸿渐屡次被动行动依旧是尴尬的结局,最后还是不打不相识的情敌成了最可靠的朋友。在赵新楣家里,方鸿渐看到了一张苏小姐的照片,即使他从没有真正爱过她,但是还不能控制内心的波动:“最刺眼的是一张彩色的狭长照相,内容是苏小姐拿棍子赶一群白羊,头上包块布,身上穿的像是牧装,洋溢着古典的、浪漫的、田园诗的、牧歌的种种情调。”[3](P128)扮成牧羊女,制造欧洲古典主义情调的照片,作者调侃地换了叙述视角。以方鸿渐的经验判断,认定头巾是包了一块布。就算是如此拙劣的模仿,方鸿渐也认为很好看,因为完全不同于他痛恨却脱离不了的小城风气。这种心理定位在回乡伊始家里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就明确表达出来:“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3](P34)方鸿渐的价值判断因为有了西方做参照,而对国内盲目模仿的风气有所反感,但是他同样无法超越,对另一种形式的模仿却很艳羡。
这模仿继续到苏小姐的婚礼上。因为是一对洋气的人结婚,所以反对旧式选择黄道吉日,而专挑洋日子,选择了最宜结婚的六月,而且是最宜结婚的星期三。无国界的时间被以地域文化意识划分,在中国叫做黄道吉日,所以被留洋的新人所不屑,同样选择的好日子,因为遵照西方的习惯便表现出一派洋气:“礼堂里虽然有冷气,曹元朗穿了黑呢礼服,忙得满头是汗,我看他带的白硬领圈,给汗浸得又黄又软。”[3](P143)结果赶在了最热的天气里,穿着西式的服装的两个新潮人物,大大地受了罪出了丑。就算有过留学的经历,可两个人的盲目性和形式主义,变本加厉地表现出来,更显示出两人价值意识的卑微可笑。
形式主义模仿者苏小姐一直以虚伪可笑的女才子形象示人,而另一位太太则是狰狞残酷地搅动着生活世界:“汪太太出来了。骨肉停匀,并不算瘦,就是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擦胭脂,只傅了粉。嘴唇却涂泽鲜红,旗袍是浅紫色,显得那张脸残酷地白。长睫毛,眼梢斜撇向上。……十指甲全是红的,当然绝非画画时染上的颜色,因为她画的青山绿水。”[3](P237-238)居家的女性,却以敷粉过多残酷的白脸和血红的嘴唇见人,这与亲切随和的主妇形象不符。其中的深意,随着情节推进一点点明朗起来。典雅的外貌、孤高的气质,尤其不容易的是还略具才艺,汪太太的病其实源于缺少社交机会。她脸色白到了残酷,象征着一潭死水似的生活状态;而那血红的嘴唇和指甲,又透露出躁动的激情。她不甘无尽的寂寞,拿出自己过剩的时间和魅力,与小范围内的青年人来往。汪太太这类型的人物,虽说在旧时代的生活限定中,心思却蠢蠢欲动。不过她的动仅限于安全范围内的撩动,不做出实质性的举动。就算这一点点波动,也将平静的生活打破,致使赵新楣仓皇逃离了教职。
同样是受过教育的孙柔嘉,其世俗性由于加上了经济条件有限的拖累,更显得卑微琐碎,导致生活令人不堪烦恼啮咬的状态,这也是她和方鸿渐日后婚姻的一个破坏因素:“‘我衣服都没有,去了丢脸。’鸿渐道:‘我不知道你那么虚荣!那件花绸的旗袍还可以穿。’孙小姐笑道:‘我还没花你的钱做衣服,已经挨你骂虚荣了,将来好好的要你替我付裁缝账呢!那件旗袍太老式了,我到旅馆来的时候,一路上看见街上女人的旗袍,袖口跟下襟又短了许多。我白皮鞋也没有,……’”[3](P288)就算是受过了高等教育,却对学问毫无心得,孙柔嘉仍是一个平常而且世俗的女人。她不笨,虽然没有特长,却有自己的现实打算。现实的境况无法与她的期望对应,所以她的生活注定是无尽烦恼的。她不美亦不富有,可以说并无时尚的资本,却能关注到时装细微的潮流更迭。对女性来说,这一点点的追求必须要坚持,因为她们没有更大的野心要坚持,仅仅是一件新样式的旗袍,一双流行的白皮鞋,就能赋予生活以意义,赋予自己以存在感。
服饰给予女性的支撑性自信非常有力。大多数女性在想象中,依托新衣服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理想的自己,并且是完美的自己,可事实并不如此简单乐观。白皮鞋、新衣服给了孙柔嘉自信,使她敢于与有所耳闻的苏文纨正面遭遇:“苏文纨比去年更时髦了,脸也丰腴得多。旗袍搀合西式,紧俏伶俐,袍上的花纹是淡红浅绿横条子间着白条子,花得像欧洲大陆上小国的国旗。手边茶几上搁一顶阔边大草帽,当然是她的,衬得柔嘉手里的小阳伞落伍了一个时代。”[3](P301)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顺便做些生意,苏文纨表现出来的时髦已经有了商贩的气息,然而这依旧是孙柔嘉望尘莫及的,她一败涂地。再加上苏文纨尖刻的奚落,她勇敢的最终结果是自取其辱,烦恼又加上一成,并迁怒于方鸿渐。外交失败,内政也是混乱不堪,她勉力追求的时尚到了内地成了不合时宜:“到了方家,老太太瞧柔嘉没有相片上美,暗暗失望,又嫌她衣服不够红,不像个新娘,尤其不赞成她脚上颜色不吉利的白皮鞋。”[3](P318)孙柔嘉第一次亮相在夫家未受到好评,还间接导致了更多的家庭纷争,直致最后她和方鸿渐令人悲哀的结局。
三、通过服饰描写表现女性隐秘心理
钱锺书的小说,除了通过衣饰描述间接实现对现实和人物心理的幽默嘲笑,同样也以衣饰为参照路径对女性隐秘心理进行了描摹:“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使她脚痛,同时使她担心;因为她穿的高跟鞋还是前年路过香港买的,她到内地前最后的奢侈品。”[4](P96)暮春的短暂,一如曼倩韶华将逝的伤感。她经历的事情使心理处于失序状态,临到家门才感觉到疲累异常。然而脚疼的时候,她担心的却是脚上的高跟鞋,她最后的奢侈品,一如她最后给予天健的诱惑。女性对于的附属物,比如服饰的象征性,已经胜过对自身的关注。
介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已婚女性,她们的生活乐趣之一就是期待一些无利害的情感暧昧,用来调剂生活的平淡无奇。初见天健的时候,曼倩是有所期待的,但是这期待也仅限于给平淡的生活加入一点新鲜。“虽然如此,曼倩还换上一件比较不家常的旗袍,多敷些粉,例外地擦些口红。”[4](P105)而天健的样子确实没有让曼倩失望:“身材高壮,五官却雕琢得很精细,态度谈吐只有比才叔安详。西装穿得内行到家,没有土气,更没有油气。”[4](P108-109)
实际上曼倩有点汪太太的心理,只不过她的诱惑更加隐秘平和:“假使她知道天健会那样动蛮,她今天决不出去,至少先要换过里面的衬衣出去。想到她身上该换洗的旧衬衣,她还面红耳赤,反比刚才的事更使她惭愤。”[4](P98)物质的服饰,对女性而言,已经具备了形而上的意味。外在的服饰具有公众性,而内衣则是隐藏起来的,更具私密性。对于私密交往的人来说,内衣才最重要,能体现女性精致自爱的尊严。然而不期中,曼倩领地尽失。她只想给对方一个遥不可及的想念,却暴露了自己不堪的现实。不洁的旧内衣,已经足够将她苦心营造的影像毁损殆尽,与刚刚不情愿失去的贞洁相比,失去的面子更让人不可接受。
钱锺书的文字风格,不会直接写两个人的私密场景,而是通过婉转曲折又非常简洁犀利的心理来透露情节的进展。这种曲笔需要作家非凡的提炼能力,才能以最少的文字表现出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皮大衣快褪毛了,这衬绒旗袍颜色也不新鲜了。去年夏天以后,此地逐渐热闹。附随着各处撤退的公共事业,来了不知多少的时髦太太和小姐,看花了本地人的眼睛。曼倩身上从里到外穿的还是嫁时衣,未尝不想添些时装。”[4](P99)女人坚持着换了衣服才休息,因为爱干净,更重要的是也爱惜衣服。在困难时期,衣服的安慰作用,有时候可以取代情感。可以这样假设,如果曼倩能称心地多做一些衣服,心里似乎也不会这样空虚了。
四、结语
纵观钱锺书的小说文本可以发现,服饰之于作者,因其存在的现实普遍性,并非要给所描写人物必要的交代,而是可以利用其象征意义进行打趣的对象。他比喻方鸿渐备课不充足上课的情况,正像料子不足而非要做出合适的衣服的困难。他嘲笑几位教授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被旅途艰难折磨得斯文尽失的窘境:旧式夹袍长度尴尬,露出半截西式长裤;舶来品外套和裤管虚肿肥胖如同空心的国家支柱;号称不皱的洋领带已经缩水成了前清遗老的辫子。作者通过叙述衣服的形态,即实现了对中西方某些具有代表性文化符号的解析。
钱锺书的小说文本中常见的对服饰的表达简单到笼统抽象的程度。比如说某小姐身材高大,着色鲜明,穿衣紧俏;某太太生得怪样,打扮得妖气;孙小姐,打扮得很素净;刘小姐身体很丰满,一动衣服就起皱。在钱锺书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描摹和情节的叙述,绝非通过绘声绘色、浓墨重彩来加以表现。他似乎是刻意在避免上面的情况,而尽量用简洁的线条勾勒轮廓。杨绛这样评论孙柔嘉:“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5](P168)
像孙小姐一样聪明地将汪太太的特征扼要地表现出来,这是钱锺书的审美理想:不走古典现实主义的套路,只用简单线条白描出对象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来。所以钱锺书的小说人物众多,但是都比较分散,叙事功能并没有常见的错综复杂的铺垫和呼应,也不刻意于戏剧化的因果逻辑安排。他不着意塑造立体式的形象和油画般的质感效果,甚至连人物的形体外貌都简略到可以忽视的地步,更不要说对其衣着服饰的细致描摹了。所以他作品中呈现出的人物都是线描型,重点传达其言行,表现与言行并行的精神存在状况,尤其是人性上的错综明暗。传统小说的种种要素和规约,比如坚实的结构框架,戏剧性的情节冲突,性格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令人拍案惊奇的结尾等等,在钱锺书的小说中都隐去了。他超越了技巧的诱惑,轻松自如地放弃了各种技术手段,直接进入文化批判,从而使文本的深刻性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