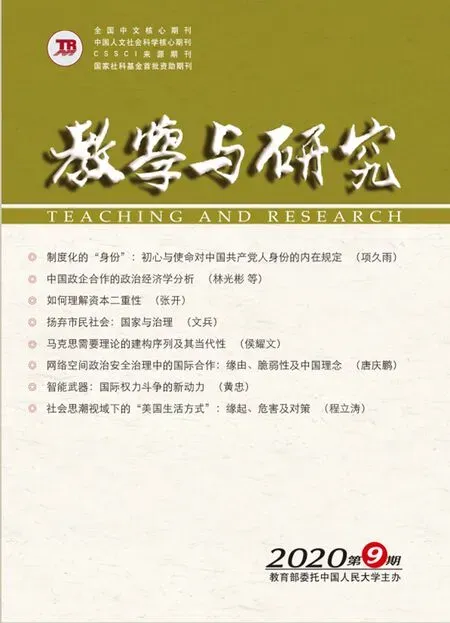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中的国际合作:缘由、脆弱性及中国理念*
2020-12-08唐庆鹏
唐庆鹏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在国家安全与网络空间对接衍生的各种新安全议题中,最为突出的也是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根据一项最新统计,过去一年里全球国家政治领域(包括外交、政党、政府、选举等)仍然是高级持续性威胁(APT)攻击重点,在全部网络攻击事件中占比最高,达到24.5%。(1)奇安信威胁情报中心:《2019全球高级持续性威胁(APT)研究报告》,2020年1月3日,https://www.qianxin.com/threat/reportdetail?report_id=44.历史地看,在关涉一国政治安全事务时,国家通常敏感且保守。维护政治安全被视为国家的固有职能,不能指望外力来实现。然而,网络空间具有高度全球化特性,这使得“网中之事”往往会跨越国界、跨越领域。在开放互联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维护虽然不能完全依靠别国力量,但一些外部资源和力量却可以为我所用,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协调配合。基于此,本文从安全研究的理路出发,规范分析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的缘由、脆弱性,进而探索中国参与和促进国际合作的着力点与基本路径。
一、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中国际合作的缘由
在安全研究中,威胁被视为引发安全行动的外在逻辑动因。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最直接的缘由也正是日趋严峻的全球性网络空间政治威胁,这使得全球各国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上有了“共同命运”。网络空间政治威胁所表现出的全球化特征,首先源于网络空间的高度开放互联性。开放互联性内嵌于互联网的技术基因,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排斥任何行为体接入其中,当然它也意味着会对怀有不良意图的行为体开放。可以说,开放互联的网络空间为任何攻击者提供了一个目标丰富的无边界环境,网络所覆盖之处,都有可能成为诱发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问题的可能所在。例如,近年来,无论是网络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网络政治操控威胁,仅2017年就有18个国家宣称在政治选举中遭遇了网络操纵和虚假民意信息策略。再比如,互联网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新的高效联结方式,网络恐怖主义对全球各国的威胁能级被放大。最近的例子是2019年恐怖组织ISIS利用Facebook全球招募圣战者、新西兰恐怖直播事件等。对此,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高呼“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应付这个全球性问题。”此外,在互联网的串联下,当今各国在多个领域的交互、联动极为紧密,一些原发于一国的政治安全威胁可能波及别国,产生威胁的涟漪效应。例如2011年的“占领运动”,在互联网的策应下,从华尔街升级到美国各大城市,并进而蔓延到全球80多个国家。总之,共同的威胁需要国家间协力合作的行动应对,共同的政治安全威胁由此也就成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外在推力。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威胁越出传统的主权国家管辖边疆,深刻挑战既有国家安全治理能力。伴随网络空间的发展,国家边疆形态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由实体的物理空间拓展到国家安全和利益所涉及的虚拟空间。(2)许开轶:《网络边疆的治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新场域》,《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7期。国家边疆的拓展意味着国家维护政治安全行动范围的扩展,安全治理相应超出主权国家现实地理和物理边界的限制,面临更多跨国界治理的复杂性挑战。而在安全治理领域,“最棘手的安全挑战正是跨越国界的安全威胁”,因为它“既不尊重国家边界也不尊重组织边界,单方面国家措施不足以应对。”(3)Bruce McConnell, “Transnation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Cyberspace Security”, 2017-6-27,https://www.eastwest.ngo/idea/transnational-security-governance-and-cyberspace-security.并且,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威胁源广泛多样,既包括传统的国家行为体,还包括与政府没有隶属关系、没有政府指导或资助的非国家行为体,并且借助网络空间的网络关系和信息传播的特殊性,网络空间的政治安全威胁往往很难被溯源,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增大了单方面国家安全治理的难度。甚至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中,“即使是最有能力的国家也无法期望自己预知并抵御所有网络攻击,最先进的国家可能也是最脆弱的国家。”(4)A.Naugle, “Cooperation and Free Riding in Cyb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 Dynamics Applications, 2017, 6(2):71-85.鉴于单方面国家安全治理的局限性,合作对于确保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便显得重要起来。
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博弈中,合作利大于弊。正如其他国际领域一样,网络空间同样既是一个合作又是一个利益之争的领域。对于国家而言,选择以及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还取决于其认为合作的预期收益超过不合作的可能代价。基于国家本位主义,现实中被动的网络防御、主动的国家威慑等传统安全方案也往往成为不少国家本能的优选项。而且,合作本质上意味着以放弃一部分自主性为代价,特别是对于处于互联网优势地位国家而言,可能短期内会缺乏明确的激励。在网络空间安全全球治理博弈中,仅从本国出发的保守安全行动,可能短期内产生有限的安全效应,但是长此以往则可能陷入彼此互疑互防的安全困境之中,出现零和甚至负和博弈,这样在长期上不仅拉低安全收益,而且提升了各自的安全成本。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家之间建立信任和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合作才是持久网络安全最有希望的途径。”(5)Sico van der Mee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yber Security”,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2015, 2(6):193-205.基于长期和全局考量,理想状态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可以使得各国能更为有效应对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威胁,而且能够减少可能被误解为敌对国家行动的事件,降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成本、增进网络空间政治利益。例如,2015年中美围绕网络安全达成初步共识后,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双方就在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安全事件处置、网络恐怖活动情报交流等方面“成效显著、效果明显”。(6)周栋梁:《推动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快速发展》,《人民公安报》2016年12月9日。就此而言,“营造一个稳定和安全的全球互联网合作治理局面所带来的社会价值是难以估量的。”(7)[美]劳拉·德拉迪斯:《互联网治理全球博弈》,覃庆玲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全球各国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领域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与前景。一方面,国家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各国维护和发展自身政治利益的共同需求也构成了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内在动力。在相互依存关系加强、互动关系加快、互惠关系加深的网络空间,国家在政治安全与发展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诉求,在追求安全和发展利益时也必须考虑到他国的反应及合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例如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金砖五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延续并深化在网络等领域的政治安全合作,符合彼此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期待。当然,全球各国开展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并非从零开始。事实上,在互联网全球化的进程中,逐渐增长的互联度产生了互相交往和互相依赖的复杂形势,国家间的包容与互信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不断增强。(8)张国庆:《互联网全球治理的国际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8日。这些无疑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际合作积淀了“国家社会资本”。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具有广阔的国际合作内容和前景。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是以信息为中心的新的政治安全范式,(9)刘远亮:《网络政治安全内涵探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内容上至少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包括支撑政治运行的硬件设备、信息系统和网络软件等正常运行、免受破坏),以及信息内容的安全(包括政治信息资源、政治传播秩序、意识形态安全等)。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在信息基础设施还是信息内容治理上,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不足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特别是对于内容治理,虽然逐渐为各国高度重视,但“未来两三年关于网络空间内容治理的国际合作进程仍难有实质性进展。”(10)戴丽娜:《2019年全球网络空间内容治理动向分析》,《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20年第1期。辩证地看,合作不足的另一面也意味着一个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有待进一步推进。而且,伴随网络空间的迭代发展,安全威胁也会不断演化,为改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而进行的国际合作还将变得愈加复杂而艰巨。
二、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中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分析
在安全科学领域流传一句格言,“系统没有绝对的安全,因为脆弱性始终存在。”(11)RG Johnston, “Assess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Tamper Indicting Seals”, POR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2005,25(3):155-157.而国际政治研究者也认为“安全或不安全指的是内部及外部的脆弱性,它们对国家结构、领土、制度和统治机制构成威胁。”(12)[英]阿兰·柯林斯:《当代安全研究》,高望来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第3页。具体到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的缺失也势必会造成事实上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的脆弱性。考虑到理想化的国际合作是国家间基于互信的协调行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中的国际合作脆弱性至少表现在主观的价值理念以及客观的治理行动两个方面。
(一)分歧的理念: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的意识形态化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的脆弱性首先表现在理念原则的争议。理念上的最主要争议是关于网络空间属性认知之争。美国官方及其拥簇学者极力宣扬“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论”,认为网络空间与深海、外层空间等无主物一样,属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领域。美国式“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论”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争议,遭到中俄等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为,按照全球公域的“无主共有”特征,网络空间算不上是全球公域。虽然国际网络空间的活动互通互融,但网络空间却是建基于现实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之上。也就是说,网络空间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公共领域,但实际上是一个共同管理领域,包含了多个相关的权力所有者。那么,美国为何一再力推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论?对此,有学者指出,有关网络空间属性的不同概念性辩论,反映的恰是主权话语如何为不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利益服务。(13)M.Warner, “Borders in Cyberspace: Strategic Information Conflict since 9/11”, The Cyber Defense Review, 2019, 1(1): 245-266.美国谈网络空间全球公域,恰是为自己长臂干预国际互联网络空间提供正当性辩护,其实质也是服务于美国霸权战略。如果遵循美国所谓的网络空间全球公域的理念逻辑,那么,包括中国在内网络发展中国家网络空间政治权益断难得到保障,甚至时刻有受到网络强权国家威胁的风险。
另一个理念上的争议是网络空间主权和人权之争。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发生障碍首当其冲源于东西方就主权与人权理念“工具价值”的不同判断。(14)林婧:《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的障碍与中国作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长期以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高擎人权大旗,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并据此为干涉别国内政提供意识形态辩护。在网络空间,美国同样没有忘记其人权大棒,在“互联网自由”口号下,继续扮演着“网络人权卫士”,对他国网络空间治理横加指责。例如,美国在其2018年有关中国的人权报告中,就妄言谬评“中国原本已是全球网络言论审查最严厉的国家,过去一年又加强了对教育和传媒的思想管控。”中国一贯反对以“人权高于主权”的理由干涉别国内政,邓小平就多次指出,西方一些国家拿人权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在新兴的网络空间,中国也是坚定的网络主权主张者,认为“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15)《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7日。而且,主权与人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网络空间主权是管辖本国网络空间事务、保障本国人权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网络空间属性的不同理解,关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模式的选择也存在着激烈争议。其中,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和多边主义模式之争最为突出。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认为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应该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的进程,这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私营企业机构、技术性组织、利益团体及个人,公民社会等,当然也包括政府和政府间组织。表面上看,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主张的是一种广泛主体参与的共治模式,但实际上是在削弱政府管辖权,本质上仍然是现有的治理格局的延续,甚至是既有网络资源分配结构的强化。因此,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发达国家才会不遗余力地推进该模式,实际上美国只不过是在多利益相关方幌子下维系其在国际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而已。鉴于此,中俄等为代表的网络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在多元主体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进程中强调国家的责任。多边主义模式认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应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坚持网络主权原则,在联合国框架内协调合作解决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不能绕过国家层面,应该以各国的意愿和能力为前提,以相互承认的政治为基础的平等合作。国家必须带头促进网络空间的更大安全,因为它们是激励协调一致安全治理行为的主要行动者。这样,有关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模式上,各国基于不同理念似乎已经悄然形成了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多利益相关方以及以中俄等为代表的多边主义模式。
总之,当前网络空间的国际合作存在较为深刻的争议,这给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未来发展蒙上了一层不可测的阴影。一些学者悲观认为,“目前来看,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从观念到实践都呈现出一种混乱的‘元状态’,虽未达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状态,却也相差不远。”(16)刘志云、刘盛:《基于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全球治理》,《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因此,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着力寻求共识、协调一致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也就变得异常困难。
(二)困顿的行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观念上的分歧最终体现在行动上的困顿。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这些困顿既有传统安全悖论的新表现,也有网络时代新的合作问题。探索问题的根源,需要深入既有世界权力分配格局与关系之中。
1.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悖论的客观实在性。
安全悖论(security dilemma)是国际政治中使用的一个经典术语,被视为是造成国家间关系紧张与冲突的最常见缘由。对这一概念,其创造者约翰·赫兹给出的解释是:安全悖论是“一种结构性概念,国家为了保护其安全需要而进行的自助尝试往往会导致其他人的不安全感增加,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措施解释为防御性的同时而将别国的措施视为可能的威胁性”。(17)J.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1950, 2(2):171-201.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悖论同样存在。21世纪以来,互联网在政治领域展示出越来越大的政治威力,特别是互联网带来的负面乃至是颠覆性政治影响(如“颜色革命”等),各国相继加强对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维护。一个显著的国家表现就是,“网络军备竞赛”的兴起。据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统计,全球有近四分之一的国家组建了网络部队,而这还是5年前的数字。此后,这一数字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全球已经有112个国家成立了网络部队。(18)周鸿祎:《对全球角力网络军备竞赛要保持战略思维》,《中国报道》2019年第8期。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成立网络部队的国家,其对外宣传的正当理由都包含了对他国网络政治军事威胁的担忧。即使是强如美国,也一再宣称遭受或可能遭受他国网络安全威胁。例如奥巴马在其总统任期内,多次表示“美国必须面对快速增长的国家网络攻击威胁”。而特朗普在2018年“国家网络战略”中,更是明确将中俄列为主要敌手,并视为是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主要威胁源。美国热衷于通过互联网对他国施加政治影响,但其自身似乎也饱受网络政治安全威胁。譬如,2018年北约在其网络战规则中添加“攻击性防御”条款,这项条款虽然以防御为名,但实际上旨在能够更广泛地部署网络攻击性武器。人类热战或冷战的历史,已然深刻揭示出国家间若深陷安全困境必将导向互害结果,互联网时代也不例外。譬如,美国试图长期延续对互联网根区的控制权,其理由是为了维护“全球域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然而,事实却是截然相反,“在一个拥有超过200个主权国家的世界,赋予一国对某一共享的关键资源以特殊的影响力将对其他国家构成持续的刺激,最终损害稳定与安全。”(19)[美]弥尔顿·L·穆勒:《网络与国家: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政治学》,周程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7页。安全悖论的背后是国家间在网络空间议题上的互信缺失。在缺乏相互理解的共识约束下,各国为维护自身的政治安全的行动,反而对别国构成新的安全威胁。
2.不对等的依赖关系带来的合作脆弱性。
国际政治的历史表明,不对等的依赖关系通常会带来不同国家行为体在政治安全上的不同脆弱性。具体到网络空间,这种不对等关系至少体现在三个层次:
第一,不对等的技术依赖关系。环视当下网络空间的技术环境,以美国为首的网络强国垄断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全球各国特别是网络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仍存在高度的依赖性。这样,掌握核心技术的网络发达国家可以在减少自身网络安全成本的同时,还能够利用网络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脆弱性来进行操纵和控制。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发力前行,在一些技术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跑者”转变,但在核心技术领域,短板和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美国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如果不能克服和补齐这些短板,即使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快车道上中国能成为暂时的 “并跑者”,但长远来看只会沦为随时可能掉队的“跟跑者”,更遑论成为互联网技术的“领跑者”。
第二,不对等的话语依赖关系。虽然中国在国际网络空间的话语权比重日渐提升,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仍然处于相对话语弱势地位。譬如,通过对线上前1 000万个网站内容语言估算发现,目前国际网络空间中英文语言内容的网页占比高达59.1%,高居首位,而中文网页占比仅1.3%(位列第11)。(20)相关数据参见https://w3techs.com/technologies/history_overview/content_language.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外在表征,就其背后的文化而言,自由主义文化仍然在国际网络空间占据主导优势,西方国家所高擎的普世价值理念对国际互联网的影响极为深刻,这种文化影响力源自现实、并放大于全球网络空间。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当下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话语优势,不断制造舆论,抹黑对手、粉饰自己。而针对中国,美国更是广泛利用互联网建构“中国威胁论”的国际话语氛围,误导其他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消减中国的国际认同,从而阻碍中国对外合作进程。
第三,不对等的权力依赖关系。由于技术的、历史的原因,在看似平等的网络空间,巨大的网络强权场景却是客观现实。网络空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很大程度是现实国际政治格局的延伸和固化,譬如美国在现实世界的霸权地位也延续到虚拟网络空间。美国是当今最大的网络发达国家,但也是最大的网络霸权国家,其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客观而言,在应对共同的网络政治安全威胁方面,需要美国的通力合作。并且,在制定全球层面的网络规则时,如果没有掌握关键网络资源的美国参与,也势必很难推进。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美国对待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态度,总体上是消极的。美国更偏好于单方面的“长臂管辖”,而不是平等的共治合作。近年来在一些全球互联网治理议程上,美国屡唱反调。典型如2012年国际电信大会上,美国拒绝签署已得到89个国家支持的新《国际电信规则》。而在2019年的一项多国参与的、旨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内容的倡议(即“基督城呼吁”)上,美国同样拒绝加入。
3.国家间协调力量的虚弱导致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不稳定性。
由于国际社会中各国国家本位主义的限制,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需要具有公信力的中立第三方来协调各国力量。这其中最权威的国际协调力量无疑是联合国及其相关下属机构。然而,联合国相关协调机构本身却是非常碎片化的。例如,仅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下就有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反恐执行工作组等组织性平台涉及网络治理相关事务。大量的相关机构增加了全球网络治理协调的繁琐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作为整体的协调机构的影响力。一方面,虽然相关网络空间国际协调平台和机制目前已有很多,但其中不少在具体工作开展中依赖不稳定的论坛或专家组形式。这种不稳固的合作关系在面对大规模的网络空间安全冲击时,往往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国际协调平台的分散化也降低了合作治理的效能。大量的多边合作平台在提供多样化合作交流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单个平台本身凝聚力的降低。因为基于各自利益诉求的国家在某个平台得不到有利回馈的时候,容易转向其他平台,而不同平台的规则与运行机制也不尽相同,由此产生国际合作的碎片化势必也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此外,联合国等国际协调组织的成员来源往往来自利益相关国家,理论上存在受到本国影响和操控的可能性,因而其中立性也一度受到质疑。一些学者提醒人们特别需要注意相关国家利用某些国际协调组织平台的情况,例如近年来国际社会流行这样一种传闻,即“UNODC(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是一个受‘美国人’影响的组织,而ITU(国际电信联盟)则处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之下。”(21)[美]蒂姆·毛瑞尔等:《联合国网络规范的出现:联合国网络安全活动分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虽然目前这番判断还只是停留在传闻阶段,尚没有确凿证据,但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社会各界对此可能性的担忧。
可见,虽然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中,国际协调力量相较过去已经取得了颇令人振奋的进步,并且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是网络空间国际协调力量仍然存在虚弱一面。这既不利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也限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积极推进网络空间全球合作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三、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维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国际合作既是切实维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需要,也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国际政治发展的应然趋势。站在新的时代前潮,我们需要着眼全球的思考、立足本土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我们应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着力点,消减国际合作脆弱性,不断扩大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的“朋友圈”。
(一)研究与倡议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升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话语影响力
深化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中的国际合作,首要的是消减理念分歧带来的脆弱性,让体现合作精神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占据话语高点,才能把握国际合作的主动性。但是,目前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认知上,各方或多或少地还存在一些误区甚至质疑。理念受到质疑,既有囿于各自立场和利益上的考量而采取否定态度,但也部分说明理念诠释不足而导致共识不够。例如,国外有学者就表示,中国虽然对外积极倡议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然而并未能传达出这一术语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涵,并担忧该理念“将可能会因为缺乏国际认同和统一规范而行之不远”。(22)Moritz Rudolf, “China’s Silk Road Initiative Is at Risk of Failure”, 2015-9-24,http://thediplomat.com/2015/09/chinas-silk-road-initiative-is-at-risk-of-failure/.因而,“廓清观念迷思,就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必须首先解决的困扰。”(23)支振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与中国担当》,《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7日。
廓清观念迷思,首先要能够科学把握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与逻辑关系。就逻辑关系而言,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一脉相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有中华传统的“和”文化基础,也有来自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的指导,以及长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与国际战略思想,当然也积极借鉴了西方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有益成分。显然,中国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临时之举,更不是被个别西方力量所污蔑的“中国称霸”的思想工具,而是我们一以贯之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所提供的中国智慧。其次,要能够深入研究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内容,形成更多理论共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极为丰富,需要进行理论挖掘的内容较多。仅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围绕权力维度(如互相尊重网络空间主权问题等)、目标维度(如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保障网络安全)、方式维度(如网络空间开放合作与全球治理等)等内容展开进一步研究和阐释,提升理念体系的解释力和科学性,从理论源头奠定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影响力。
当然,提升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中的话语影响力,不仅要设法用学术话语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解释力,还要能够在现代国际语境中具备全球传播力。加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让世界了解并认同中国的国际合作主张,需要加强对外议题传播的管理。也就是说要树立国家战略传播的“议题管理”科学思维,加强国际政治传播议题的顶层设计,将媒介传播作为国际关系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同时要遵守政治传播的规律,根据不同的传播对象国家受众特点,积极融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话语,开展有针对性的政治传播,彰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议题在解决网络空间安全与发展问题上的价值,主动赢得全球价值认同。
(二)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提升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制度方案供给能力
首先,积极开启和引导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规则制定议程。公平正义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然而,一方面,当前国际网络空间仍处于“‘规范兴起’的起始阶段”,(24)郎平:《全球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合作与博弈》,《国际展望》2014年第6期。甚至,“目前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构建进程已进入僵局状态。”(25)方芳、杨剑:《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问题、态势与中国角色》,《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结果就是,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规则需求日趋强烈,但规则供给却严重滞阻。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的网络空间主导者的美国,原本应该是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规则供给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私心太重、私欲太强,再加上“棱镜门”等负面事件影响,使得其在国际社会离心离德,难以发挥规则供给作用。在此情况下,中国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规则构建中获得了更大作用空间。当然,中国作为网络大国也应当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构建国际合作规则中主动作为,必要时甚至可以主动开启相关规则议程,发挥主导性作用。
其次,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框架下寻求规则制定的共识。规则要产生约束力,其前提是得到受规约对象的认同。国际合作规则的主要参与者和规约对象是各民族国家,要取得各类国家的认同尤为困难。当前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供给滞阻,其原因也在于各方在网络空间治理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取得共识。因此,要从根本上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规则产生,首要的是从价值上取得共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准确反映了国际社会期盼网络空间安全与发展的愿景,呼应了世界人民的共同需求,不仅具有政治正当性,而且能够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中国要基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求同存异,寻找各国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当然,共识不是依靠无原则的退步来获得。中国在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规则制定的共识形成中,要始终坚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所确定的价值框架,在诸如网络主权等原则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退让。
再次,在策略上循序递次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规则的供给。开展切实有效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需要一整套规则体系支撑。就规则的内容而言,包括互联网技术上的国际标准规则、网络治理规则以及传统的国际规则体系,这些类别的规则体系有的需要加紧新制,有的则需要更新接轨,相关任务较为艰巨。就规则的范围层次而言,可以分为全球层面的国际合作规则、多边国际合作规则以及双边国际合作规则。相对而言,全球层面的国际合作规则的形成难度最大,后两者次之。在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规则供给中,可以按先易后难、轻重缓急的思路,先与一些典型国家就焦点问题达成共识、建立双边合作规则,再以此为基础,寻求与更多国家达成共识规则,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开启全球层面国际合作规则的制定议程。
(三)积极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行动,提升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执行能力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不能仅停留在口号上,还应落实于网络空间国际合作行动中,所考验的是“网”中各国对国际合作共识和规则的执行力。首先,要衔接与协调好国内网络空间相关法制与国际网络空间规则。目前来看,国内网络法制建设中,积极对接国际相关规则的偏少。以《网络安全法》为例,该法全文未见涉及网络安全国际合作以及与国际网络安全规则对接的相关条款,这反映了我国网络立法过程中一定程度存在国际化视角的缺失。中国积极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并非是要将既有的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完全推翻重来、另起炉灶,而是要对目前国际网络空间合作所形成的共识规则,要严格比较、及时进行对接。
其次,围绕争议问题积极展开平等协商对话。中国积极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并不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身上,而是在相互尊重各自主权地位的基础上,开展平等协商对话。对于一些争议性的网络空间国际问题,要本着有事好商量、有事能商量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的正义性在于主体的平等参与地位、理性的思维以及公正的程序。但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互联网的国际舞台,网络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地位、话语权力没有真正得到平等对待。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网络发展中国家实力与网络发达国家相比较为弱势,在相关国际合作对话中,往往比较吃亏。中国在推动网络空间平等协商对话中,要能够围绕治理问题,有意识地动员、促成更多国家(特别是网络发展中国家)参与网络空间协商对话。
再次,围绕共同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威胁开展合作治理行动。基于共同的安全威胁,各国应在实践中扩大合作治理的行动边界。例如,针对大规模的网络病毒攻击,各国相应加强计算机安全响应小组(CERT)交流合作。在这方面,中国早自2005年以来就与日、韩建立了网络安全应急三方热线机制。但是,这种地区性的合作机制在广度和深度上仍然十分有限,还应进一步扩大到全球层面。当然,围绕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共同行动,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间,私人组织、技术团体乃至普通个人均应得到鼓励,这些非国家行动体往往在灵活性、专业性等方面有助于弥补国家间合作的不足。此外,在推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进程中也必然会有一些阻碍力量和不和谐的声音,新近的例子是2019年美国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信息传播秩序面临新的挑战。因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局势,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维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中国还应做好破逆而行的充分准备。
结 语
互联网的全球互联互通显在地影响着国家政治安全,无论是从安全威胁因素、安全行动关系还是安全发展利益来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都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议题。全球性议题需要国际合作治理,然而囿于网络空间国际权力格局的失衡和共识价值的缺失,这一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存在更多的脆弱性。在此情况下,“帮助行为体形成共识,保证行为体采取自发集体行动,比起普世价值对国际社会合作最大化的促进来说更有必要”。(26)苏长和:《中国与全球治理——进程、行为、结构与知识》,《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加强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不仅有助于构建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有效应对日趋严峻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威胁,而且也关系着未来全球网络空间发展,并对当下曲折变化中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积极影响。立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探索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国际合作治理之道是一个有着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的新研究命题。本文更多地是在理念与规范层面进行探究,而关于中国理念的国际传播与共识生成、网络空间国际合作关系结构与行动机制建构等具体方面问题,则是后续有待进一步展开的研究论域。